解读海子诗歌的麦子意象.docx
《解读海子诗歌的麦子意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解读海子诗歌的麦子意象.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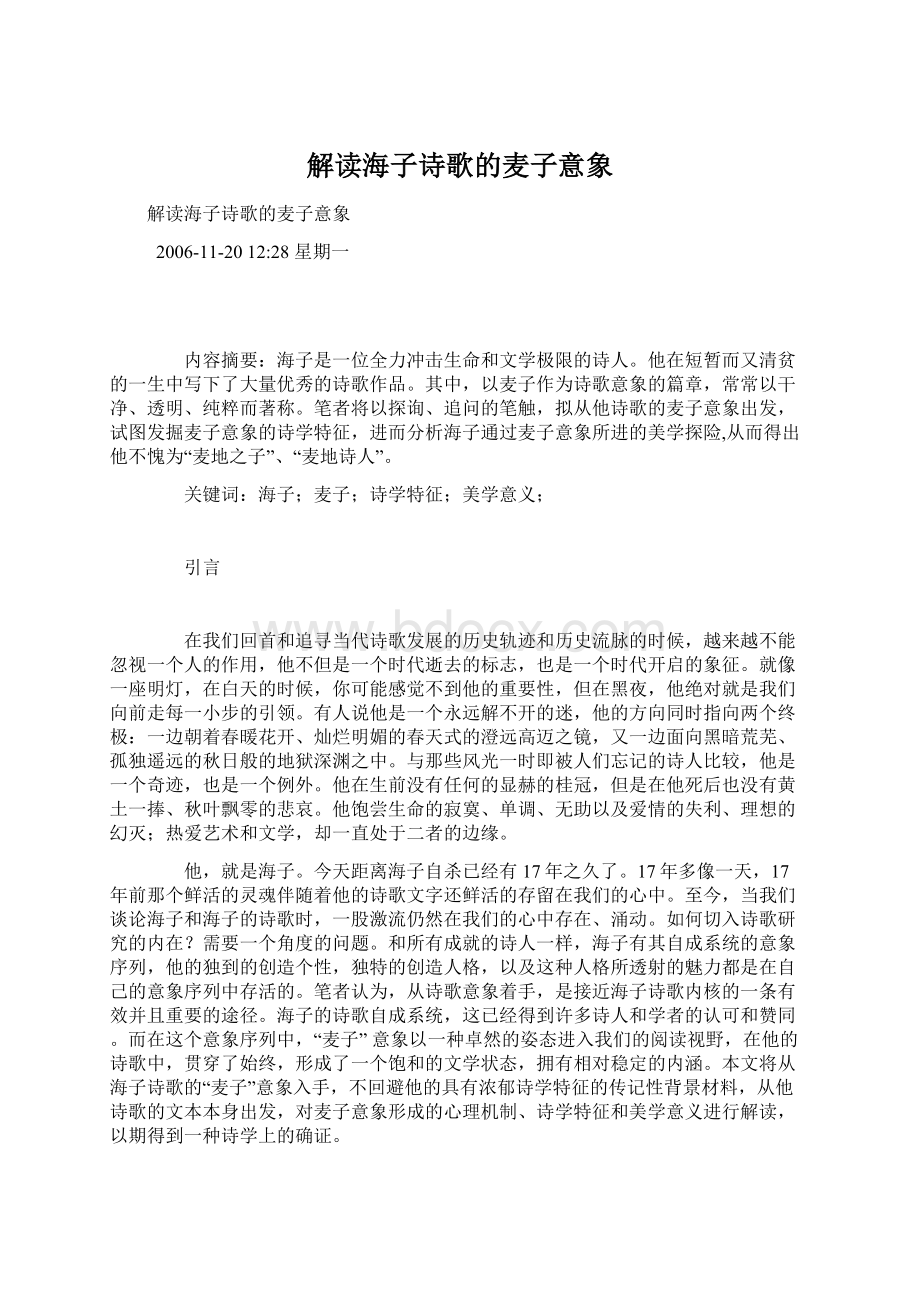
解读海子诗歌的麦子意象
解读海子诗歌的麦子意象
2006-11-2012:
28星期一
内容摘要:
海子是一位全力冲击生命和文学极限的诗人。
他在短暂而又清贫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
其中,以麦子作为诗歌意象的篇章,常常以干净、透明、纯粹而著称。
笔者将以探询、追问的笔触,拟从他诗歌的麦子意象出发,试图发掘麦子意象的诗学特征,进而分析海子通过麦子意象所进的美学探险,从而得出他不愧为“麦地之子”、“麦地诗人”。
关键词:
海子;麦子;诗学特征;美学意义;
引言
在我们回首和追寻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历史流脉的时候,越来越不能忽视一个人的作用,他不但是一个时代逝去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开启的象征。
就像一座明灯,在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他的重要性,但在黑夜,他绝对就是我们向前走每一小步的引领。
有人说他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迷,他的方向同时指向两个终极:
一边朝着春暖花开、灿烂明媚的春天式的澄远高迈之镜,又一边面向黑暗荒芜、孤独遥远的秋日般的地狱深渊之中。
与那些风光一时即被人们忘记的诗人比较,他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例外。
他在生前没有任何的显赫的桂冠,但是在他死后也没有黄土一捧、秋叶飘零的悲哀。
他饱尝生命的寂寞、单调、无助以及爱情的失利、理想的幻灭;热爱艺术和文学,却一直处于二者的边缘。
他,就是海子。
今天距离海子自杀已经有17年之久了。
17年多像一天,17年前那个鲜活的灵魂伴随着他的诗歌文字还鲜活的存留在我们的心中。
至今,当我们谈论海子和海子的诗歌时,一股激流仍然在我们的心中存在、涌动。
如何切入诗歌研究的内在?
需要一个角度的问题。
和所有成就的诗人一样,海子有其自成系统的意象序列,他的独到的创造个性,独特的创造人格,以及这种人格所透射的魅力都是在自己的意象序列中存活的。
笔者认为,从诗歌意象着手,是接近海子诗歌内核的一条有效并且重要的途径。
海子的诗歌自成系统,这已经得到许多诗人和学者的认可和赞同。
而在这个意象序列中,“麦子”意象以一种卓然的姿态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在他的诗歌中,贯穿了始终,形成了一个饱和的文学状态,拥有相对稳定的内涵。
本文将从海子诗歌的“麦子”意象入手,不回避他的具有浓郁诗学特征的传记性背景材料,从他诗歌的文本本身出发,对麦子意象形成的心理机制、诗学特征和美学意义进行解读,以期得到一种诗学上的确证。
一、麦子意象形成的心理机制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把这个世界比做一盏灯,把人的心灵看作是一面镜子,而世界在镜子中的映照也并非一成不变的。
透过海子诗歌麦子意象的考察,笔者发现麦子在海子的心灵里是如何映射乡土世界的光辉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称的“麦子”意象,其构成元素包含“麦子”以及由此衍生开去的一系列的语汇——“麦地”“土地”“粮食”“青稞”“稻谷”等等。
它们是如此的平凡,却浓缩了天、地、人的精髓,在海子诗歌中,这些语汇俯拾即是。
本文认为:
海子对“麦子”的体验是复杂的,有其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即对乡土的眷顾和思念以及对生命本真的关怀和追问。
(一)对乡土的眷顾和思念
乡土是人的生命之根、存在血脉与归宿形式,观照乡土一直是文学的永恒母题;因此有人说“决定作品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的,首先是对童年所抱的态度和对乡土的感情”[1]。
海子的诗歌里弥漫着对故乡的眷顾和思念。
作为农民的儿子,海子心中先验存在的大地乌托邦和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理论的启示,使他自然地将土地当作生命与艺术激情的源泉、沉思言说的“场”和超离世俗情感、社会经验的神性母体,以对童年记忆的诗意抚摸、乡土命运和情感旋律的切入,从“最深的根基”——在故乡/乡土催生出缪斯的芽苗。
不论是他的《五月的麦地》:
“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还是《答复》: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甚至后来的《黑夜的献诗——给黑夜的女儿》:
“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都是取材于农村生活。
这里的称呼是农民兄弟自己的称呼,他驾轻就熟地用农民的思维来表达对生活苦难的自觉承担和诉说。
远离故乡时,他的心里装满了失落:
“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
大地本身恢弘的生命力只能以欲望来代替和指称,可见我们已经丧失了多少东西。
”[2]从海子的这番表白中,可以体味出他的愤懑和无奈、痛苦和挣扎。
虽然进入了都市生活,海子仍旧是故乡的儿子。
海子在城市的边缘游荡着,放飞自己的灵魂,成为都市的浪子。
机械的轰鸣、摩天的楼群、冷漠的人潮等都市的纷乱喧嚣,在驱赶走恬静舒缓的田园诗意同时也把他逼向孤寂失落的角落,变得越发的孤独。
在《昌平的孤独》中,他写到:
“孤独是一只鱼筐/是鱼筐中的泉水/放在泉水中……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从中可以发现,这里环境被异化为困境——“一只鱼筐”,虽然他也试图“放在泉水中”去打破已然的异化,甚至去寻找现代文明和乡土文明的结合点,但“拉到岸上还是一只鱼筐/孤独不可言说”。
这种天然地眷恋乡土自然、拒斥工业文明和为汲取生命的灵性淳朴诸种因子的聚合,决定了他的情感天平不自觉地向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乡村和自然倾斜,并把之作为灵魂的家园和栖息地,诗歌也随之呈示出农耕庆典意味,恪守农业家园的土地乌托邦中的事物,遍布和大地相邻的麦子、麦地、谷物、河流、村庄等呈现着古朴、原始、本真魅力的意象。
在《麦地》里,“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麦地的情思作为触发点引动了诗人的一腔乡情,回忆的视点使“麦地”成了宁静美丽温暖而“健康的”眷顾和思念的地方。
麦子在这里喻指了全部的乡村生活,显得很透明,纯粹,干净。
美丽的故乡抑或乡土中国,在诗人的笔下只有其乐融融的农业家园,那里山清水秀,那里才是可以慰藉人的心灵的地方。
诗人的对故乡的眷顾和思念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但最后,麦子枯萎了,伟大的农业帝国还是如此的破落和凋零,麦子都已经愤怒和绝望了,开始诅咒那吹刮不息的风和那毫无生机的大地。
这种言说是借助麦子而来源于生活的。
海子关注农村,关注生命个体的存在方式,在他的诗歌里,已经没有了仇恨和种族,已经没有了退守田园的想法。
他只想回到故乡,借助麦子来宣泄心中的一切愤懑和愁苦,只想“走在路上/放声歌唱”[3],只想大声的“背诵中国诗歌”,(《五月的麦地》)使灵魂得以皈依。
(二)对生命本真的关怀和追问
我们都知道,海子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时年仅15岁,相对于同龄人来说,他是早慧的,这注定了他是学与思并行的。
在短短的四年时光中,他不但以优异的成绩修完全部的专业知识,也同步完成了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主干课程,这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谙熟、西方经典文化广涉可以看出。
在这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熏陶下,他对生命本真做了积极的探询和追问,对生命的存在方式——生与死做了深刻的思考,在他的诗歌中也得到应证。
海德格尔说过:
“死亡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是每一种生存都不可能的可能性。
”[4]他认为,人之作为人就在于他能意识到这种根本的不可能性,并且把它作为实现自我的整体性筹划的前提,一种在被抛入世的沉沦之境生存的先行决心——向死亡存在。
当代中国诗歌,尤其是80年代的诗歌浪潮,几乎所有中国诗人都在此运动中遭遇和痛苦的体验到这种自我的根本的不可能性,海子也不例外。
但他比所有人走得更远:
把这种不可能性的体验转化为对生存的拷问,退化为对自我肉体的毁灭,表现为强烈的死亡意识。
在海子的诗中,弥漫看一种神秘的死亡气息,这种死亡“本质的光焰”[5]己经到处在喷射。
他不但写了标题为《死亡之诗》的两首诗,且在许多诗中涉及到死亡。
在《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写道:
“请在麦地之中/清理好我的骨头/如一束芦花的骨头/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我所能看见的/纯净的少女,河流上的少女/请把手伸到麦地之中/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凌乱的骨头/放入一个小木柜。
”[6]在这里,海子清晰地描述了死后的一幅如诗的图景:
死人的骨头不再是白森森的、令人害怕的,不再是死亡的象征;相反,骨头好像是一件原始的用做装饰的图腾,须由“纯净的少女,河流上的少女”带回家带回麦地,并且要将其整理好“放入一个小木柜”中。
海子把对死亡的追问指向麦地,以求在麦地里得到自己的“答案”,即对死亡的超越,“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
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到死亡的悲伤,感觉不到尸骨的恐怖,因为这实在是一幅太过凄美的图画。
在论及海子诗歌时,诗人陈东东说“他的歌唱不属于时间,而属于元素,他的嗓子不打算为某一个时代歌唱。
他歌唱永恒、或者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歌唱生命。
”[7]这段知音之谈道出了海子以生命本体论为核心的诗学观内涵。
他没有像朦胧诗人那样将抒情的主体向宏大的时代、历史等意识形态境域外倾,而延续抒情传统的同时时、在民族的大形象背后更注重抒情的“小我”,要在现实的面前“把眼睛闭成两根绳索”(《但愿长醉不愿醒》),这种与现实相分离的意志,是对现实的弃绝。
海子始终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将“关注生命存在本身”[8]作为诗歌理想,并坚信这是中国诗歌自新的必由之路。
所以他的诗常有意识地远离表层社会热点,在贫瘠的诗歌语境里寻找神性踪迹,以对生命、爱情、生殖死亡等基本主题及其存在语境麦子、麦地、粮食、青稞、稻谷甚至一切自然之象的捕捉,致力于精神世界和艺术本质的探寻,于人间烟火的缭绕中通往超凡脱俗的高远的神性境界;并借助这神性的光辉冲破当代文化和历史的樊篱,提升了时代的诗意层次和境界。
海子深知没有主观的艺术是不存在的,作为内视点的诗歌艺术“个人化”的程度愈高,诗的价值就愈大;所以盛赞他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歌唱生命的痛苦”[9],他自己创作的情感中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一次性写作本质问题上强调“写作与生活之间没任何距离”(西川语)的海子,实现了诗歌文本和现实文本的统一,使他那些自传性质浓郁的作品里再现了生活中的海子,“单纯,敏锐,富于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
”[10]既要做“物质的短暂情人”又要做“远方的真诚儿子”(《祖国或以梦为马》)的海子,从“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向来把追问和探询作为生命本源的第一性形式,这种心灵化的理论前提、选择注定了他只能遭遇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对抗的痛苦冲突,并以生命外部困境和生命内部激情间的矛盾搏斗结构成诗歌主题的基本模式。
海子的情思抒唱没有分居八方地随意漫游,而主要辐射为对生命和死亡的真理性揭示。
这种揭示实质上是指一种超越经验方式与思维过程的直觉状态,它以先验的方式接通某种存在的真理,并在主体认知和判断事物之前形成先在的结论和语境。
这种“神启”情绪,与荷尔德林的“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11]一脉相承。
“吃麦子长大/在月亮下端着大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直没有声响”(《麦地》)“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刀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油灯下/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只有水烟袋依旧咕噜咕噜/谁的心思也是/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呀!
”(《熟了麦子》)“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麦地守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答复》)都是这方面的杰作。
海子的麦地诗歌就是精神的还乡之路,是海子十五年的乡村生活赋予他淳朴的天性,对乡村、农事和田园有着血脉相连的亲和关系的表现。
海子非常睿智地通过他早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找到了通向神性的道路,即通过麦子来洞察生存的终极根源,以一种接近直觉和本能的原始经验直接描述着存在的感受,放射出不同凡响的灵性之光。
海子在其诗歌中一直寻求人类诗意生存的根据,虽然诗人最终还是没有战胜生存虚无的本性,以生命为代价走上了诗歌神圣的祭坛,但是,他独特的生存体验方式和诗歌理想,在精神向度上,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诗人。
二、麦子意象的诗学特征
意象是现代诗的基本艺术符号,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境界和情调的东西,它既来源于诗人的感性生活,又来源于诗人精神深处的理性思考,它体现了诗人内在的生命律动以及诗歌自身的艺术张力。
“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意象系列,他的诗歌语言与前此流行的新诗潮的语言全然有别”。
[12]“麦子”意象作为海子诗歌的核心意象之一,有其独特的诗学特征。
笔者武断的将起归纳为三点:
心象化、感伤化和乌托邦色彩。
(一)心象化
在海子那里,诗歌中的麦子意象和现实的、故土的麦子都心象化了。
所谓“心象化”,是指海子诗歌中的麦子以文本的姿态出现时,在表述上带有很大的虚拟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子诗歌中对于饥饿的体验,对丰收的幻觉,以及对故乡的无限眷顾都是心象的表现,都经过情思的改造。
他写麦子,一方面时对童年记忆的眷顾,一方面又是从一种普世的情怀书写劳动、赞美丰收的。
他在《麦地》一诗中这样写道:
吃麦子长大的/在月亮下端着大碗/碗内的月亮/和麦子/一直没有声响//和你俩不一样/在歌颂麦地时/我要歌颂月亮//月亮下/连夜种麦的父亲/身上像流动金子//月亮下/有十二只鸟/飞过麦田/有的衔起一颗麦粒/有的则迎风起舞,矢口否认//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妻子!
这首诗似乎要告诉我们的是:
借助“麦子”来实现和平和富裕,因此就说要“握手言和”“月亮下,富人、穷人和我,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
可以看出,引发作者完成这首诗的初衷或许就是这溢于言表的乡情。
正是如此,诗人希望麦地健康、麦子健康,那样才能实现性命的养育。
通过这种现实与幻境的心象化过程,种麦时父亲身上流动黄金,收麦时我和仇人握手言和、心满意足的接受丰收和眼前的一切。
两个季节都写得异乎美丽。
这或许是海子对童年生活的一种记忆的方式。
而回忆总是比眼前的一切更美。
诗人的情感随着两个季节的麦子的描写映照出来了,那就是思念故乡,眷恋童年!
再细读此诗,作品中把“我”的成长与麦子的生长结合起来抒写,体现了诗人的人类大同式的梦想。
诗人在想象中,完成了自己的成长、成熟、恋爱和在丰收中与仇人握手言和的生命与生活过程,在月光(母性之光)的照耀下,和平富足地生活。
最后,则从梦想中回到现实,重新吁求梦想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与麦地相对的“城市”空间,即现实中的诗人乃是身处在城市中,梦想着麦地的,因而,麦地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之地,麦地只能生存于诗人的心智之中,被心象化,麦地就这样成为诗人精神生命的原型之一。
因为“麦地”在诗人心目中占据了生命原型的位置,与“麦地”相关的其他一些形象如村庄、粮食、谷仓等,也都包含了与生命本体相关的意义。
“村庄”是“麦地”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型形象。
因为诗人在诗中经常地使用同一词语,并赋予它独特的寓意,一种形象才可能具备原型的意义。
而原型的力量在诗歌中是如此强大,以致于读解诗人的诗歌文本时不得不抱着从中探寻秘密的好奇心理。
“麦地”多少是由诗人的梦想构筑的一块想象中的精神圣地,一块充满了诗人理想精神的心愿之乡,而“村庄”则更多地烙上诗人的成长记忆和种族无意识印痕。
早先的诗歌中,涉及到“村庄”时,这个词语的涵义基本上等同于现实中诗人的家乡。
因为村庄是诗人最终的情感归宿,麦子在其中健康的成长,是生活的陈述。
联想到一种平静生活的可贵,而其潜台词构成了对都市生活中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反讽。
也正是有了这样一点乡情的冲动,他才把麦地的两个季节写得那样的美丽。
写种麦的父亲那汗珠在月色的照耀下如金子般闪烁;写看麦子的“我”在月下麦地的感觉宁静有如梦幻。
这样的描写其中可能有着他少年生活的某种回忆。
回忆总是比现实更为美丽。
他的思乡情怀在这诗里被泛化了,扩展了,由家乡而及于大地。
《五月的麦地》也是这样,他写到家乡的麦地,又想象着“全世界的兄弟们鹰在麦地里拥抱”在《麦地与诗人》中,他把自己的痛苦与对故土、对生活的感恩,借着麦地的询问表达出来。
这里,既有温暖的生命记忆,也有对当下生存的惶惑和痛惜。
又如《熟了麦子》一诗中,开篇的一个“那”,我们就知道海子是在追忆往昔,其实他的心思也是“半尺厚的黄土”。
在这里作者做了这样一个虚拟:
“兰州”当然不是实指,应该是对乡土中国的指称;“在水面上混”象征了一种漂泊状态,而且是三十多年,最后终于在新麦熟了的季节回家了,标志了精神还乡的成功,表达了作者对乡土的无限眷恋。
麦地成了他的乡土情怀借以抒发的深度意象。
这一意象的含义是泛化了的,海子以故土情结生发出来的对于广大乡土的眷恋之情,与工业社会人们精神的麻木、空虚构成对照,诗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乡愁。
(二)感伤化
纵观海子诗歌,感伤命题贯穿了其诗歌生涯的始终。
围绕这一命题,海子内心激烈而超于常速地走过麦子乌托邦心里时期,我们将会看到,诗人在这之中怎样地步步受伤、步步退让,最终彻底地绝望,引发1989年春的那场大爆炸。
所谓受伤命题,即海子从诞生在人世间开始,就一直与“感伤”这种宿命紧密相连。
究其感伤的缘由,有这么几个:
1、招魂童年生活、实现精神还乡、物化宣泄欲望、外化创作激情的产物
从创作心理学角度看,乡土文学是作家向过去、向童年生活招魂的产物,他们创作乡土作品的过程就是一次精神还乡的过程。
海子以“麦子”为母题的乡土作品中,我们到处可以发现。
上文提到的《麦子熟了》、《答复》、《五月的麦地》等,具是可以佐证的。
以弗洛伊德关于童年创伤性经验对艺术家创作起重要作用的论点作支撑,我们认为,乡土作家童年时期遭遇的家庭不幸、生活困顿,必然给他们心灵上烙下很深的情感印记,使他们日后走上创作道路时,定然如鲁迅所言“屡次忆起”,产生思乡的“蛊惑”,并对乡土、对故旧生活“时时反顾”(《朝花夕拾•小引》)。
海子也不例外。
2、“我们已经丧失了多少东西,只剩下肤浅的欲望。
”(《诗学:
一份提纲》)
让我们来回顾我们这个深重遭受机器工业文明破坏的时代。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指称这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技术,现代科技发展到了可以控制我们生活的程度,文学抑或诗歌所维护和寻觅的是个性得到自由伸展的空间;面对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价值尺度普遍遗落的时代,金钱和物欲无孔不入,但道德和价值却无人问津,我们的心灵离神圣和纯洁越来越远时,文学和诗歌应该坚定的站在纯真的韧性和崇高的精神一边,担当穿越现实的使命。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诗人都会对这种痛彻心肺的现实有所呼应,荷尔德林说:
“我要回到生长我的土地,倘使怀中的财富多得和痛苦一样时。
”[13]
无疑,海子也痛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尽管他现实中极端的贫困。
“土地死去了/用欲望能代替吗?
”(《土地》)
“情欲老人,死亡老人/强行占有了我——人类的处女欲哭无泪”(《土地》)
在这里海子清晰地指出了现代机器工业文明及其附着物致使现代人道德沦丧、价值遗落,“人”如何奸污了人类自处女时代以来的古老的圣洁精神。
面对人类生于斯死于斯的客体——土地的丧失,海子异常的沉痛:
“这些现代的漂泊的灵魂必须寻找到一种替代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
3、源于他的生存现实和理想的破灭
从安徽怀宁高河查湾走出的海子,和所有的6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样,是伴随着文革的阴霾和沉重,伴随着饥饿和雨水成长起来的。
尽管他生活在大都市近10年,但面对聒噪的都市生活深为不满,“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这必然使得他倍加“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的村庄,也倍加珍惜和怀念那片养育了他15年的村庄。
他说:
“针对村庄我可以写作十五年”,可他未及写满十五年就早早的逝去了。
在这里,记忆的村庄和他诗歌得到了一种完美的呼应,这是一种回归家园的暗示,精神上的契合。
于是,灵魂深处他记忆中“村庄”的理念便在诗歌中通过麦子诞生了,也不仅仅是一种回归,更成为了一种敏锐的诗歌意象,成为他乌托邦式精神家园的现实原型。
在他进入这片村庄以前,回到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家园以前,这里的一切显得荒芜,但海子用文字、用诗歌将其开发成沃土。
在海子这里,村庄不仅仅有生计的存在,重要的是他把这片土地借麦子的耕种实现了“以梦为马”,实现了富足和丰饶:
白云可以做棉被,而黄金般的麦草可以编成柔软的凉席,成为他灵魂的栖息处,那沉甸甸的麦子,又是他精神饥饿时唯一的粮食,“当人们收走了一年的收成/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留在地里得人,埋的很深”,他“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走在路上/放身歌唱/大风刮过山冈/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他寻觅着,心中装着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梦想,而双手举起临行前“四姐妹”赠送的“一粒空气中的麦子,”向大地,向他的村庄边缘突围,向“道路前面还是道路”[14]的方向突围。
笔者相信真正的诗歌是为了表达心灵需要而写作的,但这种写作、这种抒情,又不是仅仅指内心个体情感、经验、和理想地传达,对海子而言,更大程度上是对民族心灵或者说宏观心灵表达地需要,即以一颗真诚的炽热的内心,去探寻、追问诗歌何在、真理何在、民族何在、实体何在?
在海子那里,真理、民族和实体是融为一体的,都是诗歌的精神内核,他说:
“诗,说到底,就是寻找对实体的接触”[15],“诗应是一种主体和实体间面对面的解体和重新诞生。
诗应是实体强烈的呼唤和一种微微的颤抖。
”[16]
海子在描写麦子/麦地的时候,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力度很大的感伤。
他常常以一种难以避免无法抑制的悲情来书写麦子以及诸于此类的话题。
这时,麦子本身与麦子作为诗歌意象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分离与反叛,麦子本来干净、青春,但是化做在海子的诗歌中后,便成为了一种意象,一种情绪,一种心象。
如《四姐妹》:
“空气中的一棵麦子/高举到我的头顶/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冈/怀念我空空的房间,落满灰尘/……//四姐妹抱着这一棵/一棵空气中的麦子/……/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
这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在这里,我与麦子之间仿佛成了对话者,言说的对象,一种完全沉浸在悲情中的对象。
在这种无休无止又无可诉说的悲情中,麦子可能是一个或隐或现的着落点。
我们知道,海子是一位才华横溢、激情迸射的青年诗人,他热爱生活近乎疯狂,但毕竟过于年幼,未竟经历太多生活本来面目的磨砺,这就往往会给他带来更多的伤感和失望。
他说:
“随着生命之火、青春之火越烧越旺,内在的生命越来越旺盛,也就越来越盲目。
因此燃烧也就是黑暗,甚至是黑暗的中心、地狱的中心。
”[17]黑到如火般的燃烧,既是青春的激情,也是死亡逼迫的阴影,既是希望,更始挫折和失望甚至绝望。
而这如火如荼的悲伤心灵的落脚处便是家乡远远生长的麦子,养育我性命的麦子。
当难以抑制的悲哀和苦痛笼罩心头的时候、家乡的麦子、记忆中麦子似乎是唯一可以言说和自况的对象,是唯一可以停泊的港口,在这里所有的失望、孤独、漂泊无依最后因麦子化作了文字,感伤的呈现给了我们。
如《五月的麦地》:
“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回顾往昔/背诵各自的诗歌/要在麦地里拥抱//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梦想众兄弟/……/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里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
(三)乌托邦色彩
海子诗歌中的麦子意象值得注意的另一点特征,是在言说的途中给麦子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幽怨、古老的色彩,笔者将其归纳为乌托邦色彩。
海子一直沉思“现代文明”中的经验方式与话语方式,所以,他的麦子意象最终必然要走到乌托邦的阶段。
进入麦子乌托邦的时期,是诗人在理想次第上的一次大退让,也是诗人最惨痛、最悲壮的大退让。
尤如圣哲苏格拉底的遗言道:
让我死去,让你们活着。
谁的结果更好,只有神知道。
这种退让中又不乏另一种向度的清醒与沉醉。
但是海子也认识到它必须放弃诗人的王位,而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