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家权流变看村落社会的内聚与离散.docx
《从当家权流变看村落社会的内聚与离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当家权流变看村落社会的内聚与离散.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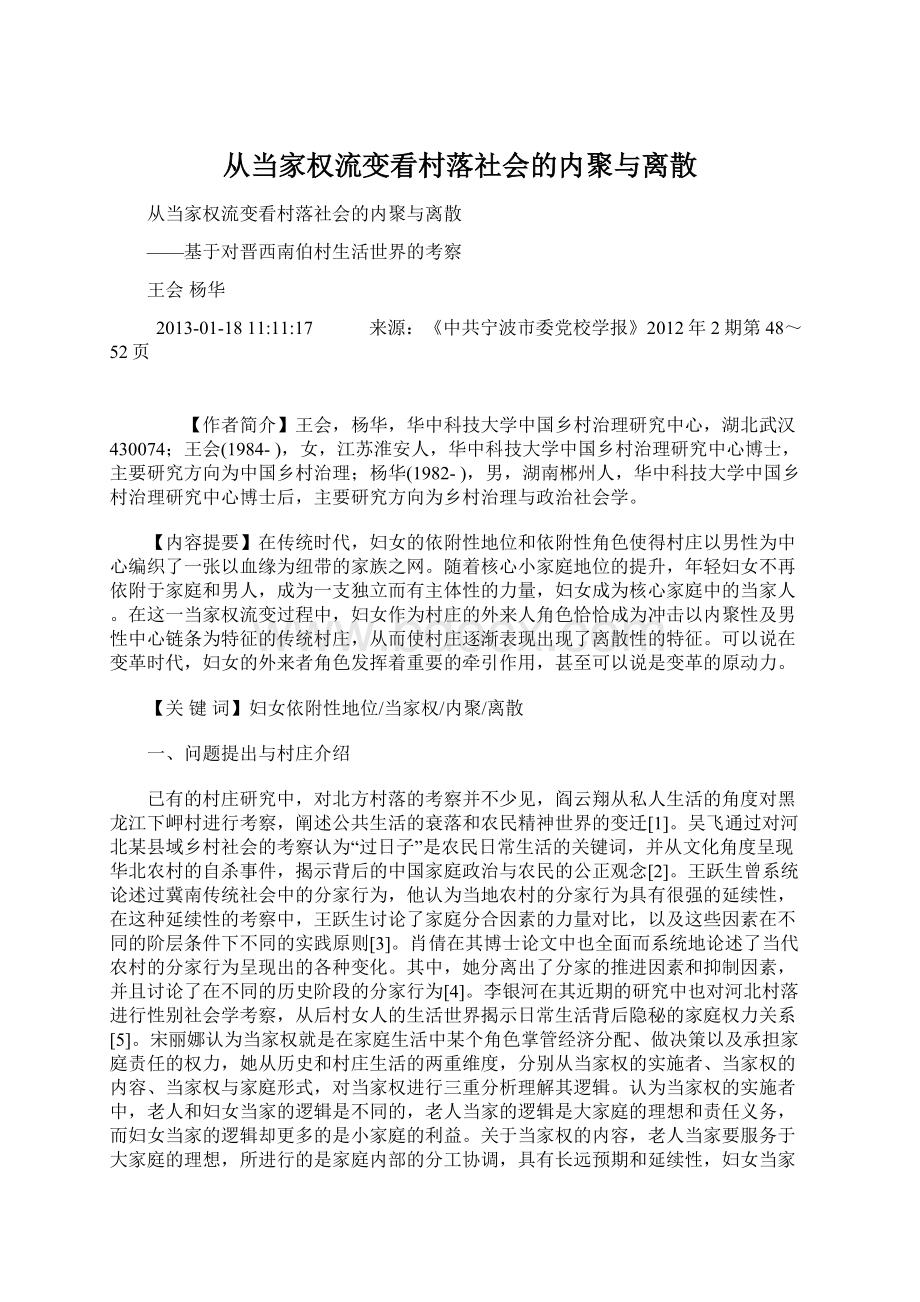
从当家权流变看村落社会的内聚与离散
从当家权流变看村落社会的内聚与离散
——基于对晋西南伯村生活世界的考察
王会杨华
2013-01-1811:
11:
17 来源: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2期第48~52页
【作者简介】王会,杨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王会(1984-),女,江苏淮安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乡村治理;杨华(1982-),男,湖南郴州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政治社会学。
【内容提要】在传统时代,妇女的依附性地位和依附性角色使得村庄以男性为中心编织了一张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之网。
随着核心小家庭地位的提升,年轻妇女不再依附于家庭和男人,成为一支独立而有主体性的力量,妇女成为核心家庭中的当家人。
在这一当家权流变过程中,妇女作为村庄的外来人角色恰恰成为冲击以内聚性及男性中心链条为特征的传统村庄,从而使村庄逐渐表现出现了离散性的特征。
可以说在变革时代,妇女的外来者角色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变革的原动力。
【关键词】妇女依附性地位/当家权/内聚/离散
一、问题提出与村庄介绍
已有的村庄研究中,对北方村落的考察并不少见,阎云翔从私人生活的角度对黑龙江下岬村进行考察,阐述公共生活的衰落和农民精神世界的变迁[1]。
吴飞通过对河北某县域乡村社会的考察认为“过日子”是农民日常生活的关键词,并从文化角度呈现华北农村的自杀事件,揭示背后的中国家庭政治与农民的公正观念[2]。
王跃生曾系统论述过冀南传统社会中的分家行为,他认为当地农村的分家行为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在这种延续性的考察中,王跃生讨论了家庭分合因素的力量对比,以及这些因素在不同的阶层条件下不同的实践原则[3]。
肖倩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当代农村的分家行为呈现出的各种变化。
其中,她分离出了分家的推进因素和抑制因素,并且讨论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分家行为[4]。
李银河在其近期的研究中也对河北村落进行性别社会学考察,从后村女人的生活世界揭示日常生活背后隐秘的家庭权力关系[5]。
宋丽娜认为当家权就是在家庭生活中某个角色掌管经济分配、做决策以及承担家庭责任的权力,她从历史和村庄生活的两重维度,分别从当家权的实施者、当家权的内容、当家权与家庭形式,对当家权进行三重分析理解其逻辑。
认为当家权的实施者中,老人和妇女当家的逻辑是不同的,老人当家的逻辑是大家庭的理想和责任义务,而妇女当家的逻辑却更多的是小家庭的利益。
关于当家权的内容,老人当家要服务于大家庭的理想,所进行的是家庭内部的分工协调,具有长远预期和延续性,妇女当家却更多的是服务于小家庭的利益[6]。
可见当家权与家庭形式关系密切,与老人当家相符的家庭形式是大家庭,妇女当家使得老人因为生存策略的考虑主动分家,从而带来家庭日益核心化。
以上研究均关注到了农村家庭的日常生活政治和性别政治。
本文认为从性别及当家权变迁考察熟人社会,可以深化对熟人社会的理解。
费老讲的熟人社会核心在于共同体概念,熟人社会是一个生活共同体,传宗接代及稳定的村庄预期是熟人社会形成共同体的基础。
笔者认为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形成的夫权链条是传统村庄联结性力量,村庄得以具有内聚力及强社会关联,为每个人提供社会支持网络,行为有度、不至于走极端。
这是熟人社会的意义和基石。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及现代家庭关系的不断民主化,农村社会已经由传统型村庄走向变革时代,当家权流变和妇女角色的变化与村庄的整合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对正在经历这一变迁的伯村进行考察,力图片面而深刻的展现这一巨变的图景。
山西伯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型村庄,人口2000余人,5个村民组。
伯村对男女两性的要求和规训截然不同。
伯村老式院落的门楼上仍然可以看到醒目的横幅,“家和万事兴”、“康泰祥和”、“耕读传家”等。
族谱上对男性的规训是“治家:
勤俭为本,艰苦度日;立身:
孝悌当先,温良恭让;处世:
谦慎忠厚,律己宽人;传家:
耕读并进,农茂书香。
”对女性的则强调温良孝顺,勤劳能干。
治家、立身、处世、传家是对男性的定位和要求,对女性的定位和要求则显然限制在“屋里”,勤劳能干、相夫教子、孝顺公婆。
二、伯村的生活世界与两性分工
1.妇女作为“屋里人”
调查期间一位村小中年女教师说,伯村妇女的活动主要限制在家里、村里,伯村三十五岁以上的男性称呼妻子都为“屋里”。
客人来串门时,提到自己的妻子是“我屋里如何如何”,同样客人问话时涉及到主人的妻子也是“你屋里如何如何”。
这种称谓正是村庄给妇女的角色定位。
伯村的妇女在外工作的很少,多数人婚后就在家做家务、生养孩子、照看庄稼,年轻一代妇女也很少外出工作。
伯村多数是男人当家,妇女当家是个别现象。
村民说妇女当家的情况除非是丈夫无能,妻子非常能干才行。
“谁能干谁当家,女的都没有男的能干。
”问及为什么男的就比女的能干,村民说男的在外朋友多,能办正事,吃得开。
也确实,伯村的人际关联网络,如人情圈、同学圈都是以男人为中心建立的,妇女的朋友圈子主要都是其丈夫同学的妻子,即妇女以丈夫为中心建立自己的生活圈和朋友圈。
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地位的低下,不少妇女都说自己的丈夫有很多同学、朋友,家里办事情都有人帮忙,妇女虽是以丈夫为中心交朋友,但这些朋友都非常亲密,如果是丈夫非常好的同学的妻子,那么她们的关系往往更加好,“甚至比姐妹要亲”。
两家人互通有无,互相帮忙就更为频繁,这就不是男女地位高低的问题,而是双方家庭同舟共济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增加双方家庭抗风险能力和扩大发展空间,即男女双方都以家庭为中心。
调查中另一位妇女说她2009年得脑瘤在运城住院,怕娘家人担心就没告诉娘家人,婆婆又要在家带孙子做饭,因此住院一个月全是两个兄弟媳妇(即妯娌)轮流照看,住院期间去医院看她的多是丈夫同学的妻子,她们也是她最好的朋友。
因为去运城来回车费要花费100元,加上买东西,花费很大,邻居、亲戚多在她出院回家疗养时到她家离探望。
这种现象在伯村并不少见。
2.妇女作为村落的“外人”
妇女作为夫姓的外人,在夫姓家族和村落也就没有主体性的地位,是一种依附性存在。
其结果之一,妇女在夫姓村落仪式活动中没有正式的身份,因此也就无需拘泥太多的礼节。
比如在酒席中,主要的席位都是由丈夫就座,仅“请座”一个环节就要拉扯、礼让半天,若不到位还会引发情绪。
而妇女,无论再珍贵,即便是姥娘也是与其他人混坐,一屁股坐下就是吃饭,没有多少礼数。
结果之二,妇女没有自主的“面子”观,因此她也就可以在很多事情、场面上不要面子。
很多男人去办被认为没有面子但又必须去办的事,往往就差女人前往。
结果之三,妇女的某些行为被家族、村落看成是外人的行为,而不被认为是家庭、丈夫的真实意图,便予以忽略或谅解。
3.“正干”——村落文化对男性的规训
在伯村,村民形象的比喻说“丈夫是大将,老婆是军师”,“丈夫是老板,老婆是出纳”,“丈夫是老板,老婆是会计”,总之,妇女有地位,但是掌握当家权的主要还是男性。
一位当了三十年的民事调解员兼红白喜事主持说他遇到的纠纷主要就是三种,一种是养老纠纷,一种是婚姻纠纷,再就是妇女吵架。
“男的跟男的闹矛盾很少,都是妇女闹矛盾、吵架,争不正经事,吵架的都是不正经事,正经事不会吵架的。
”这位民调员的分析很有意思,男性之间闹矛盾的很少,农村里闹矛盾都是女的闹,闹的都是不正经事。
他的“不正经事”指的是斤斤计较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村庄里的男性都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规训,要求他们能够治家、立身、处世、传家,使得村庄里的男性多数都正直、讲义气、不计较,每一位男性都代表整个家,男性都争取着能够在家谱上留下辉煌闪光的一笔,成为家族里可圈可点的人物。
如此,妇女之间的纠纷矛盾就属于小矛盾,很容易化解。
伯村的男人多数都“正干”,伯村没有耙耳朵的说法,也没有耙耳朵现象,村民说如果哪个丈夫当不了家都会被人瞧不起,不“正干”的男人往往当不了家,被人背后骂为懒人,在村庄公共场合抬不起头也没人搭理。
年轻人到了十七、八岁就开始有亲戚、朋友帮其“说媒”,这时双方家族具体情况、双方的人品性格、家庭条件都被列为考察对象。
自谈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村民多会避开不提。
父母正干、家庭和睦的家庭,帮忙介绍的就多,而家庭不好的人家没人帮忙介绍,因此,伯村的男孩到了十八、九岁,帮忙介绍的人多就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而没人介绍,父母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村庄的巷道、小店、池塘边、大舞台都属于伯村的公共空间,常常有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聊、娱乐,不正干的人加入其间“自然会觉得格格不入,大家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他走后,大家都要拿他开玩笑”。
这样的人媳妇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因为这样的人的媳妇多是自谈的,很少人愿意为这样的人介绍媳妇,混得时间长了,媳妇不是这样的人也成这样的人了。
”这种不介绍媳妇的惩罚非常有效,正因为有这种舆论评价机制和排斥机制,这种不正干的人将遭到“讨不到媳妇”的根本性惩罚。
伯村有2000余人,经统计不正干的人只是极个别。
男人的“正干”才使得这里虽然男人当家,但妇女地位并不低。
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需要挑起家庭的重担,传宗接代、建房、教育投资、为儿娶媳、养老送终都离不开男人。
伯村游手好闲、沉迷于赌博的人也几乎没有,男人需要把大多数精力都放在挣钱养家上。
有能力有胆量的男人在外创办企业、养车开车,能力不够的则在工厂打工。
挣的钱不需要交给妻子,妻子也不会要管钱。
她们对丈夫很放心,知道丈夫有钱会往哪里投资,不会乱用乱花。
调查中一位老人跟我们说,他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他前几年住院做手术花了三万多,两个儿子家庭条件都不好,于是三个女儿先垫的钱,但两个儿子后来一人出了一万五把女儿花的钱都还上了。
“养老就该是儿子的责任”,我们问及儿媳妇有没有意见的时候,老人说儿媳妇根本不会过问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该儿子管,即使媳妇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意见,治病是正当用途。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在伯村显得格外和谐,女人始终是家庭中的女人,当丈夫能够给她们提供舒适的生活和安全感的时候,她们对家就会产生深深的依恋,愿意呆在家里。
不少妇女提及自己的打工经历时都反映只打了几个月的工就很想家,不想在外面待,于是伯村很多妇女的打工生涯就是几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伯村的婆媳关系较为和睦,伯村村民说极个别不孝顺的媳妇到了35岁以后自然就孝顺了,并且婆媳闹矛盾,儿子多会站在父母一边,“父母嘛,父母肯定是没有错的”。
儿子有这样的判断很符合生活逻辑,父母将毕生的经历都放在儿子身上,为儿子建房娶媳,父母怎么可能错呢?
在伯村,传宗接代、建房娶妻是一项根本性任务,村民的日常生活都围绕此展开,村庄的舆论、评价机制也由此产生,男人必须“正干”、“会活人”,女人应该贤惠、孝顺。
简单地说,在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下,村庄的内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个方面:
首先价值层面,强调传宗接代本体性价值,村庄具有当地感和历史感;其次村庄公共生活具有公共性,舆论有实质效力。
村庄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家族体系和血缘共同体。
三、从内聚到离散:
变革时代的妇女角色与村庄整合
前文呈现了一个传统村庄的性别权力关系和整合模式,即“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在传统时代,妇女的依附性地位和依附性角色使得村庄以男性为中心编织了一张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之网。
最近几年随着当地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伯村逐渐掀起了打工潮,妇女的外出打工从根本上改变的了原有的性别分工模式。
在这一变革时代,年轻妇女不再依附于家庭和男人,成为一支独立而有主体性的力量,妇女成为核心家庭中得当家人。
在这一当家权流变过程中,妇女作为村庄的外来人角色对于村庄整合而言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妇女的外来人角色恰恰成为冲击以内聚性及男性中心链条为特征的传统村庄,从而使村庄逐渐表现出现了离散性的特征。
可以说在变革时代,妇女的外来者角色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变革的原动力。
妇女掌握当家权与村庄整合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展现:
首先,妇女的外人气质作为家族的分割力量表现得更为明显,她将丈夫从家族往小家庭拉扯的力度更大,并因为作用力的另一方——家族的越发软弱无力,妇女每每都能轻易得手。
而且事实上,在2000年以后,年轻丈夫已经全然站在妇女的一边了,这个时候,在家族、大家庭的利益争夺过程中,丈夫也参与进来了。
但是男人由于血缘、亲情、面子的关系,始终撕不下脸面而直接与兄弟、族人争夺,于是妇女又被推到战斗的第一线。
但此时,已不是妇女一个人在战斗了,她不仅消除了家庭的阻力,而且有着丈夫的后勤补给,从而更有战斗的动力和劲头。
妇女依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外人、没有自主的面子观的角色与气质,在为小家庭争夺到了利益的同时,还保护了丈夫的脸面。
女人的外人气质,为男人遮风挡雨。
于是深夜里小夫妻俩在为合谋成功而窃笑。
阎云翔在他新近的书里描述,小夫妻从谈恋爱时就开始算计父母和大家庭,我调查的伯村也有这样的苗头。
其次,随着妇女“裹挟”丈夫之后,小家庭相对于家族就越来越“外化”,家族认同越来越弱,那么家族内部就越来越计较“人情”。
出嫁女阿信访谈时提到一件事,她丈夫阿哲的近房有一家在盖房子,阿哲主动去帮忙。
阿信得知后十分气恼,硬是当着众人的面,将阿哲从工地上拉回来,令主家甚感尴尬。
阿信对我解释说,一方面是丈夫阿哲给人家帮忙事先她不知道,另一方面她认为,人家没有来请帮忙,是阿哲自己主动去的,因而人家不会记阿哲这个人情。
按照阿信的意思,除非人家主家主动来邀请,而且事先经过了她的同意,阿哲才可以给近房去帮忙。
在这则案例中,作为家族一员的阿哲看到的是血缘亲情,而作为外人的阿信看到的是“人情帐”,思维逻辑完全不一样,但妇女裹挟丈夫按照人情的逻辑办家族的事。
妇女对夫姓家族的认同越疏远,家族内部的人情就越重要。
再次,妇女地位提高,掌控家庭的各项大权,若按照固有的规则运作,则她的行为是会起到滋润家族、村落社会关系的作用,但若妇女一旦改变游戏的规则,则很可能会离析原来的关系。
比如解放以后,家庭的人情事务一般都由妇女操持,丈夫不再操这个心。
但是如果妇女不按照既定的人情法则来办的时候,家庭的人情就可能偏离原来的轨道,而丈夫则可能根本不知情,或者知情亦无力挽回。
特别是在对待兄弟、宗亲的人情上出现偏差,后果严重而且难补救。
梅嫂的丈夫有五兄弟,以前每年吃“团年饭”都是轮流到一家,这几年因为妯娌矛盾,轮到某一家时,刚好这一家与另一家有矛盾,则不会叫上后者,到轮到后者时亦复如此,这样每次团年饭总会缺一两家。
梅嫂说,男人之间没有矛盾,但是团年饭“合不合在一起,妇娘人讲话算数”,其他事如互助、合作也如此。
这便是说,家庭的人情往来、亲情维系都可能最后屈就于外来者的喜怒偏好,且男人可以用“妇娘人做的”,即外人的行为来脱离责任。
又次,外人气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妇女的工具色彩,如性、生育、劳动力。
因为工具性,妇女被排除在夫姓家族的自己人范畴。
生育的工具色彩在变革到来的时候,在婚外性中体现得很明显。
当家族对妇女的婚外性无能为力时,就会发出“反正她不能生孩子了”的消极感慨,即妇女为夫姓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且已结扎,不会因跟人发生关系而生育,造成家族的血缘混乱,被人讥讽家族出了“野崽”。
如此,人们就更可能平静地接受家族妇女的婚外性及给自己带来的耻辱感,同时也脱卸自己的管束责任。
另外,在妇女那里,既然自己是生育的工具,那么完全可以不做这个工具,或者将这个工具交给谁都可以——反正是要生孩子,跟谁生还不是生。
这样,传统的生育的价值理念就容易在妇女身上急剧淡化。
妇女在对待自己的性的问题上,也容易从工具色彩的角度去思考。
最后,对于妇女本人而言,既然自己扮演的是外来者的角色,那么完全可以撇开夫姓家族与村落,也可以不顾及娘家的脸面,做出极致的行为;对于夫姓家族而言,既然妇女是外人,那么她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被看做是外人的行为,而与自己无关,特别是在极端无奈的情况下会做出如此解释,或者干脆当做阿Q式的精神救济法:
娘家亦可以将出嫁女儿看做绝对与自己无关的外人,不再把她的行为牵扯到自己头上。
下面章节将看到,大冶农民一旦发现女儿在外做小姐,唯一的措施就是尽快把女儿嫁出去,尽早脱离干系。
这是外来者角色内含的最具杀伤力的变革因子,它潜伏于社会结构之中,伺机而动。
笔者认为,在当下的变革时代,可以看到当下村庄正在经历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一,传宗接代观念的减弱,由此带来农民本体性根本价值观念的丧失[7];其二,夫妻关系成为核心,父子、婆媳、兄弟甚至朋友关系均靠后,即村庄走向原子化甚至个体化;其三,以男性为中心的圈层被打破,包括人情圈、同学圈、朋友圈、业缘圈等;其四,村落公共生活的衰退。
这几个变化的直接后果是,村庄预期变短,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
传统社会的信任步步缺失,进而村庄具有离散性,从村庄整合的角度看,男人具有家族性和社会性,女人具有家庭性、社区性[8],传统村落共同体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的联结纽带不仅仅是人情,而是基于夫权的面子、生命礼仪、互助交往和人情往来,从而使得传统村庄是一个情理社会。
[9]然而,妇女当家对村庄共同体是一股冲击性力量,核心小家庭的利益得以保障和强调,而夫姓村庄作为一个共同体则呈现出离散性特征。
四、简短的结语
本文讨论夫权和当家权流变不是单纯的讨论夫权或者褒贬夫权,而是力图从性别权力的角度去揭示熟人社会的深刻内涵,深化对熟人社会及村庄共同体的理解,从而理解村落从传统到现代,从夫权到妇权,从熟人社会到夫妇联结社区的变迁图景。
近些年,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村人情的异化、老年人地位的严重下降、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的意义的丧失、村落伦理的变迁是共同体遭受冲击的表征,与此同时,核心小家庭的地位无以复加的提高。
[10]可以说,对村庄而言,妇女普遍当家是一股离散性的力量,是对传统村庄联结方式的挑战也是对熟人社会及村落共同体的瓦解。
可以预见的是以夫姓为基础的形成的血缘社区将得以改变,娘家人与婆家人的位置也将与传统村庄大不相同[10]。
当下村庄面临共同体的断裂和重新整合,正如同笔者在湖北、四川等地新兴的“两头走”婚姻模式一样,血缘、地缘的共同体模式将逐渐模糊[11]。
而在这一巨变过程中,尤其需要重构村庄公共空间,输入公共文化,引导舆论导向以减轻转型过程中的农民的阵痛。
【参考文献】
[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吴飞.浮生取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王跃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南农村分家行为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4).
[4]肖倩.制度再生产:
中国农民的分家实践——以赣中南冈村为例[D].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5]李银河.后村的女人们[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6]宋丽娜.农民分家行为再认识[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4).
[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贺雪峰.村治模式:
若干案例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9]杨华.妇女何以在村落里安身立命?
[J].中国乡村研究第八辑,黄宗智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10]王会,杨华.规则的自我界定:
对农村妇女主体性的再认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11]王会,狄金华.两头走:
双独子女婚后家庭居住的新模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