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世界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doc.docx
《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世界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doc.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世界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doc.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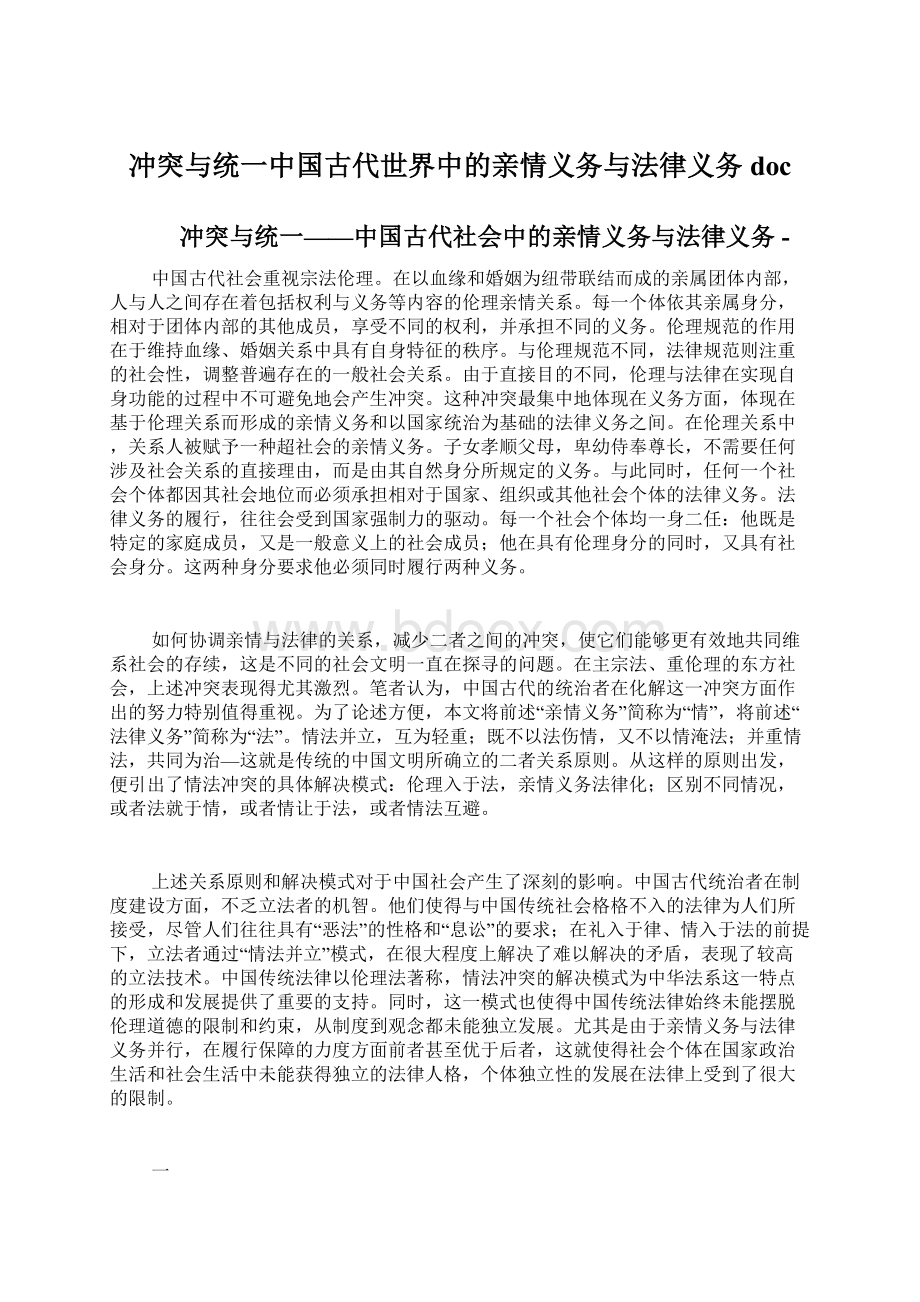
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世界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doc
冲突与统一——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
在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联结而成的亲属团体内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的伦理亲情关系。
每一个体依其亲属身分,相对于团体内部的其他成员,享受不同的权利,并承担不同的义务。
伦理规范的作用在于维持血缘、婚姻关系中具有自身特征的秩序。
与伦理规范不同,法律规范则注重的社会性,调整普遍存在的一般社会关系。
由于直接目的不同,伦理与法律在实现自身功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这种冲突最集中地体现在义务方面,体现在基于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之间。
在伦理关系中,关系人被赋予一种超社会的亲情义务。
子女孝顺父母,卑幼侍奉尊长,不需要任何涉及社会关系的直接理由,而是由其自然身分所规定的义务。
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因其社会地位而必须承担相对于国家、组织或其他社会个体的法律义务。
法律义务的履行,往往会受到国家强制力的驱动。
每一个社会个体均一身二任:
他既是特定的家庭成员,又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成员;他在具有伦理身分的同时,又具有社会身分。
这两种身分要求他必须同时履行两种义务。
如何协调亲情与法律的关系,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共同维系社会的存续,这是不同的社会文明一直在探寻的问题。
在主宗法、重伦理的东方社会,上述冲突表现得尤其激烈。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化解这一冲突方面作出的努力特别值得重视。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将前述“亲情义务”简称为“情”,将前述“法律义务”简称为“法”。
情法并立,互为轻重;既不以法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并重情法,共同为治—这就是传统的中国文明所确立的二者关系原则。
从这样的原则出发,便引出了情法冲突的具体解决模式:
伦理入于法,亲情义务法律化;区别不同情况,或者法就于情,或者情让于法,或者情法互避。
上述关系原则和解决模式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制度建设方面,不乏立法者的机智。
他们使得与中国传统社会格格不入的法律为人们所接受,尽管人们往往具有“恶法”的性格和“息讼”的要求;在礼入于律、情入于法的前提下,立法者通过“情法并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表现了较高的立法技术。
中国传统法律以伦理法著称,情法冲突的解决模式为中华法系这一特点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同时,这一模式也使得中国传统法律始终未能摆脱伦理道德的限制和约束,从制度到观念都未能独立发展。
尤其是由于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并行,在履行保障的力度方面前者甚至优于后者,这就使得社会个体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获得独立的法律人格,个体独立性的发展在法律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
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这决定了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论其社会地位、亲属身分、自然性别如何,均得无条件遵守。
关于这一点,不仅先秦法家曾经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并竭力提倡,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建立以后的历代皇帝、官吏也多有认识。
然而,由于宗法亲情对于整个社会的深重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向宗法伦理倾斜:
法律规范就靠于亲情关系,往往因为法律关系人的亲情身分而改变。
首先,尊卑长幼及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
这种不平等地位集中反映在区别对待尊卑长幼之间及夫妻之间相互侵犯行为的处理规定中。
汉唐明清各朝法律都规定:
尊长与卑幼之间发生相互骂、殴、伤、杀等行为时,作为卑幼一方总是要承担更多的刑事责任,受到更重的法律制裁。
同样,夫的地位高于妻,夫享有较之于妻更多的法律特权。
夫与妻之间发生相互骂、殴、伤、杀等行为时,妻须承担较多的刑事责任,并要承受较重的法律制裁。
在维系婚姻关系方面,妻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
妻如果不履行法律所规定的特定义务,夫则有权依据“七出”的规定解除婚姻关系。
但是,法律却从未授予妻以相同的权利。
另外,对于子女,父亲拥有的权利也较母亲更多。
亲属关系中尊卑长幼身分不平等,在中国古代法律中规定得极其明确,其等级落差也极为悬殊,超过了一般社会身分差别。
这种有悬殊落差的身分性不平等的法律关系何以历朝相沿,并未受到重大冲击,其原因不仅来自社会,也来自法律本身。
尊卑长幼的亲情关系是一种相对关系。
尊长并非永远是尊长,卑幼也并非永远是卑幼。
在宗法血缘的网状结构上,每一个人都具有与其亲属身分相对应的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状结构的亲属伦理关系自然更替,“先为人子,后为人父”,原先处于卑幼地位的人由于自然原因而获得尊长身分。
伦常之网在自然力的推动下,缓慢地垂直移动,网上每一节点皆机会均等地经历着由低而高的旅程。
法律承认这种自然演变,并同样保护新尊长的特权地位。
这样,每一名家庭成员在法律上都受到了完全等同的对待:
先卑幼,后尊长。
某一时刻上的身分性差别被一段时间内的机会均等所替代。
法律所强调的一体对待原则虽然不在现实的亲情关系中体现,但却完整而真实地反映在由自然力所推动的血缘伦理之网上。
因此,法律本身仍然是公正的—它并没有袒护任何一种具体的人,只是保护着一种含有社会内容的自然关系;而在自然关系中,人人机会均等。
体现等级身分制的法律扎根于人人机会均等的自然关系基础之上,法律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其内在的平等性,因而也长期并广泛地获得了社会的接受。
某种法律制度的不公正因素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将其建立在一定的自然基础上,那么,这一制度往往仍然能为社会所接受,或者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能有效地减少来自社会的阻力。
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尊卑长幼身分不平等及男女地位的区别,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制度与自然因素相联结,并以自然差别为基础确立社会不平等的特征。
现代法律中的继承制度,也含有不平等因素,但由于它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因此也为注重社会公正、讲究社会平等的现代人以及现代法律所肯定。
其次,法律确认家庭为国家统治下的基本单元,并强制保护家庭内部的伦理凝聚力。
在中国古代,家庭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国家统治未能在各个方面完全延伸到家庭内的每一个成员。
法律确认这种状况,在某些方面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要求其内部成员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并授予家长一定的治理权。
在经济上,法一津确认家庭是一个整体。
家长代表家庭,对外参与经济交往和财产交换;在家庭内部,依法独自享有对家庭财产的所有权。
家庭其他成员在财产关系上不具备独立的主体资格,也不得以个人名义从事经济活动,否则构成犯罪。
唐律规定:
“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答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疏议曰一:
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
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
”(《唐律疏议?
户婚》))家庭的存续,以家长的存在为前提。
原家长去世,以其为核心的家庭随之解体,并同时形成新的家庭。
但若原家长在世,法律规定,其子孙即便长大成人,也不得分别财产,自立为家,否则构成犯罪。
法律设立“别籍异财”罪,严刑惩处在祖父母、父母尚在的家庭中实施分家析产的子孙。
在某些刑事法律关系中,法律视家庭为一个独立的责任主体,并授予家长以一定程度的监管权,包括对子孙的教令权、惩戒权等。
与家长权相联系,家长向国家承担着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多的法律义务。
家庭内部成员犯罪,法律不考虑具体的行为人是谁,而只是将家庭作为二个整体来处罚。
其具体的方式是追究家庭法定代表人一一家长的法律责任(失于监管),而不追究实际行为人的责任。
唐宋明清律皆规定:
家庭成员共同犯罪,由尊长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其他成员无罪;婚嫁活动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犯罪,且由祖父母或父母主婚者,由祖父母、父母独立承担刑事责任,婚姻当事人无罪。
罪犯家庭的特定状况,甚至能改变已生效的法律判决,使得对于罪犯本人的刑事处罚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
法律规定:
犯徒、流罪者因其祖父母、父母疾病,而家中无其他成年男子侍奉,可免除执行依法应受的刑罚,或改易其他刑罚,以便该罪犯能返家侍养祖父母、父母;即使所犯为死罪,也可通过特别程序改易其他刑罚(《大清律例?
名例》。
清代对监候死刑犯的处理方式之一即为留养承祀。
案犯犯罪情节较重,依法应执行死刑,但由于其为独子,或者其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于处死,改判他刑,以便于其侍奉亲老,承继血脉。
法律强调以家庭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加强对于家长权的确认和保护,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凝聚力。
在某些方面,甚至不惜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国家司法权为代价。
财产所有权以同居共财的家庭为基本单位。
一个家庭以本家庭财产权的所有者身分与其他财产权所有者均是各自独立、相互平等的所有权主体。
如果相互之间发生了侵害财产权的情况,自应依照法律关于保护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加以处理。
但是,古代法律在确定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的同时,对于发生在具有特定伦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财产侵权行为却规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
法律规定,非家庭成员,但属于五服之内、具有亲属伦常关系的成员之间窃盗财产,构成犯罪;但对于行为人不得依照一般窃盗罪处理,而应在普通窃盗罪法定刑罚基础上减等处罚(《唐律疏议?
贼盗》)。
八议制度的实施,从立法上给予贵族、官僚一系列司法特权。
这一特权的受惠者既有皇亲、国戚、贵族、官僚本身,也包括他们的一部分亲属。
这样,部分社会成员由于他们特定的亲属身分,则可享受八议特权。
即便犯罪,也可因此在实体上或程序上享受超出法律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权。
唐宋明清律对此都有规定。
法律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
除了司法机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于囚犯实施拷讯、家长对于卑幼实施法定教令权之外,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以殴打方式侵犯他人人身权,否则构成犯罪。
但是,法律同时又授予身为子孙者一种救护权。
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子孙对他人实施殴打行为。
这种特定情况专指祖父母、父母被他人殴打。
唐律规定:
祖父母、父母被他人所殴打,子孙当即殴击对方,子孙无罪;即便殴对方致伤,也较普通殴伤罪减等处罚(《唐律疏议?
斗讼》)。
他人殴打自己的父祖,其行为已构成犯罪,自应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此时允许被打者的子孙为救护其父祖而还殴对方,实际上是以牺牲国家司法权为代价,强化家庭中的伦理凝聚力。
尽职国家,服务社会,这是文明时代对于社会个体的基本要求之一。
中国传统社会也确立了一套鼓励社会个体为官入仕、为国尽责,并对国象官吏给以优厚待遇的机制。
然而,在为父母尽孝与为君国尽忠发生冲突之时,法律又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一般情况下,尽忠之责应让位于尽孝之情。
《礼记?
王制》规定:
父母“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
”父母年老或有疾病,其子若仕宦在外,必须弃官离职,以侍奉父母。
为尊崇父祖的名字,子孙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为亲者讳”;如果某一机构或官职的名称中有与其父、祖姓名相同的字,该子孙则不得在此机构中任职或不得就任该官职。
父母去世,子女应为其服丧。
服丧期内,子女不仅不得嫁娶,不得作乐,也不得继续在官府任职,而必须“丁忧”回家,为父母服丧守孝。
与上述制度相适应,法律设立了“委亲之官”、“弃亲之任”、“犯父祖名讳”、“冒哀从仕”等罪名(《唐律疏议?
职制》、《大清律例?
礼律》),对于为贪图官职、眷恋富贵而丢弃尽孝之情、不履行亲情义务的官吏严加惩处。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仅在立法上,而且在司法活动中也积极贯彻加强伦理凝聚力的原则。
历朝司法官吏,从州、县正印官乃至朝廷大臣、皇帝,在具体的审案过程中,常以“执法原情”、“为孝子屈法”为由,直接改变对法律的正常适用而“屈法伸情”。
当然,法律对于亲情的倾斜,是有其内在限度的。
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特殊性,要求法律必须将其作用的重心放在维持一般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上。
法律的大部分内容仅涉及一般社会关系,它以调整这些与伦理亲情无直接关联的社会关系为主要任务;对于法律所重点保护的一些特殊社会关系,即使涉及伦理亲情,法律也不再作出让步,而是舍弃亲情原则,基于法律的内在标准,行使法律的自身功能。
例如,对于“免死充侍”、“存留养亲”制度的适用,法律便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件。
其中,犯谋反、谋叛、谋大逆等十恶重罪,因其严重侵害对于国家统治有特殊意义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便不得适用特别程序以减刑或改易他刑,必须一体适用普通法律。
法律严禁子孙向官府告发祖父母、父母,否则构成犯罪,但如果祖父母、父母所犯为谋反、谋叛、谋大逆的“三谋”大罪,法律又例外开禁,赋予子孙如常人一样的普通告诉权。
另外,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与其相应的亲情义务也渐次淡化,逐渐让位于具有一般社会意义的法律义务。
在亲属容隐制度中,历朝法律皆严格限定了适用范围,小功以下亲属,不得容隐。
在亲属之间的赡养方面,法律规定兄弟伯侄之间相互不承担此义务。
二
在亲情义务与法律义务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解决矛盾的办法或者是法就于情,或者是情让于法,其基本依据是各自所反映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孰高孰低。
然而,社会生活是复杂的。
发生冲突的法律关系与伦理关系有时会出现难分伯仲的状况,即它们所体现的政治、伦理准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受到大体相等的重视。
对于此种冲突的解决,既不能法就于情,也不能情让于法,否则便会在社会生活中引起震荡,其结果必然是或者伤情,或者损法,二者均不利于社会秩序的规范化。
中国古代法律在解决这类问题方面,规定了一种相互避让的基本原则。
这种通过相互避让的方式来化解冲突的情形,首先表现在复仇制度及复仇观方面。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血亲复仇,原本是人类的一项权利,也是义务。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很长一个时期,这种复仇权利仍然为一般社会成员所享有。
随着国家作用的扩大和地缘政治的强化,生杀之权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国家,复仇权也逐渐受到种种限制。
《周礼》主张区别不同的杀人行为而给以区别对待,“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
仇之则死。
”(《周礼?
地官?
调人》)《春秋公羊传》则进一步明确: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春秋公羊传?
定公四年》)父母被他人所杀,子女若不能为其复仇而苟且偷生,则于情于理不容,不孝之名难以摆脱;但若复仇杀人,则势必引起反复仇杀,导致社会混乱,危及国家政权,同时也会直接侵损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权。
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重视宗法伦理的国度里,国家法律对私人复仇从认可、允许,到限制、禁止,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直到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相对健全完备的唐代,社会对于禁止复仇一事仍然久议不决。
唐朝统治者本有强化国家统一司法权的总体设想,试图较大幅度地加强法律的强制性,禁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国家司法权的民间复仇行为,但这一点又与唐代尚礼法、重伦常的基本国策相悖。
于是,从朝廷、官府到民间,围绕着是否允许复仇的问题,一场广泛的讨论展开了,赞同、反对、调和的意见都获得了表达的机会。
唐武则天时,同州人徐元庆因其父为县吏赵师韫所杀而杀赵报仇,并自投官府服罪。
针对关于如何处置徐元庆的种种不同主张,谏官陈子昂建议,一方面,对徐元庆杀人行为依照法律宁罪量刑,处死徐元庆;另一方面,对徐的舍身尽孝行为据情据礼给以表彰,由朝廷出面,为其立碑设匾,族表其门。
陈子昂还建议,将此种处理方式“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旧唐书?
幸义传》)。
陈子昂的立论基础在于,他肯定法律与亲情之间的冲突;但同时认为,这种冲突并不表明法律与亲情之间任何一方的不公正、不合理。
二者的基点不同,故有不同的评判标准,社会对于这两种标准不能采取简单的取此舍彼的方法,而应该分别情况,同时采用。
陈子昂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君臣上下的认可。
唐顺宗时,礼部员外郎柳宗元对陈子昂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
他引用《春秋》之语“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春秋公羊传?
定公四年》)来申说自己的意见: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有罪当杀,那么,县吏赵师韫杀死徐元庆之父只不过是依法办事,是代天子执法。
徐元庆杀赵则是仇视法律,仇视天子。
对于这样的人怎么能再族表其门呢?
反过来,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是无辜被杀,赵师祖韫纯粹是报私怨,而且各级司法机关又不为徐元庆洗刷冤情,那么,徐元庆的行为就符合经义,“是守礼而行义也”,又怎么能对徐元庆定罪量刑呢?
在后一个假设中,柳宗元立论的依据仍然是经义。
柳宗元将法律与经义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否认法律与经义、法律与亲情的冲突。
他认为,违法则不得族表其门,因为它同时也不合经义;符合经义则不得处以刑罚,因为它不违反法律。
“族与诛莫得而并焉。
诛其可族,兹谓乱,黩刑甚矣。
族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柳宗元提出,应严格限定“仇”的含义,通过排除那些与法律发生直接冲突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达到法律与亲情、与礼的一致。
“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
”(柳宗元:
《驳复仇议》,《柳河东集》卷四)
公元811年(唐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悦为报父仇而杀死秦果,并至县衙投罪自首。
对于杀人者梁悦该如何处置,在社会上又引起了议论。
案件上报至朝廷,宪宗拿不定主意,命尚书省评议。
他在诏书中说:
“复仇之事,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
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
”职方员外郎韩愈在其给皇帝的上书中分析了对复仇行为难以处置的缘由,以及法律回避复仇—既不加以禁止、又不规定允许的原因。
他指出: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之、罪之者也。
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圈之也。
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恃法专杀,无以禁其端也。
韩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宜定制日:
凡有复父仇者,事先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
”(《旧唐书?
刑法志》)
唐朝是中国古代在礼法关系、情法关系方面矛盾较为突出的时代。
一方面,儒家德治、礼治思想作为治国治民的基本方针,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统一的中央集权确立,各项制度趋于完备,国力较为强盛,强化国家政治统治对社会的渗透成为必然。
这样、重亲情的礼与以维系政治统治为目的的法之间的冲突便无可避免,且愈演愈烈,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折衷其义,相互避让。
从陈子昂的诛其罪、族其情,到韩愈的“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都体现了相互避让的精神。
以相互避让的方式解决情法冲突,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移乡避仇制上。
杀人者依律应处死刑,但若遇赦,则能免罪。
被赦者回居故里,极有可能与原被杀者的子孙同处一地。
如果被杀者的子孙为报父祖之仇而与被赦的杀人者之间再次发生仇杀行为,那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
法律尽可以以其强制力,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杀人行为,而无论其有何种理由。
但是,如果实行这种纯粹的国家司法主义政策,又必然形成对于亲情和礼的直接侵害。
对此,唐律采取了一种相互避让的立场。
它规定,杀人者遇赦免刑,而被杀者家中尚有较近(“期以上”)的亲属,为执行赦令,又防止仇杀,被赦的杀人者不得返居故乡,而要移居千里之外落户(《唐律硫议?
贼盗》)。
空间上的距离一则可以淡化复仇的情绪,二则可以给复仇行动造成一定的难度。
法律有移乡避仇的规定,并不是说被杀者的子孙或其他亲属有权仇杀遇赦回乡的杀人者。
如果发生这种仇杀,法律仍然要处罚实施报仇行为的人。
一方面回避,另一方面仍然禁止,用双重规定来防止仇杀的恶性循环。
应该说,移乡避仇,是一种消极的防范措施,而且其实际功效也不一定显著。
然而,在既重法、又顾情的原则下,以这种相互避让的方式来缓解二者之间的冲突,也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
唐律未规定允许复仇。
从立法上看,复仇不被当做一种特殊的行为,而只被当做一种普通意义上的伤害行为。
同时,从唐律的一些相关条款中,仍可看出法律对于复仇行为的微妙态度。
《唐律疏议?
斗讼》规定:
祖父母、父母被别人殴击,子孙可以帮助还击,只要未将殴击其父母者致伤,不构成犯罪。
即使打伤,也较普通斗伤罪减三等处罚。
关于此项规定的适用,唐律还作了一些情节上的限制。
第一,实施还击行为的子孙,应是未与父祖同行者;第二,子孙还击,应在其父祖被殴之时即刻进行。
前者的立法意图在于要求子孙力劝双方,阻止争端,或者选择较温和的方式,救护其父祖,而不应施以激烈的还殴行为。
后者的立法意图则在于申明子孙还击是一种急切的自救方式,只是在危急情况下方可实施。
如果时过境迁,危急不复存在,对任何事件的处理则都应纳入正常的法律程序。
关于“即刻还击”,明清律规定得更为具体明确。
清律规定:
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子孙即时还殴,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斗三等。
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即时杀死行凶者,勿论。
何为“即时”,清律附加说明:
“少迟即以斗殴论”,“少迟即以擅杀论”(《大清律例?
刑律)))。
唐明清律在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基础上允许还殴,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法律与亲情相互避让的原则。
中国古代法律确立了亲属相容隐的制度。
家庭内部有人犯罪,其他成员可以向官府隐匿其罪行,甚至可以向其透露消息,使其逃逸,以免受法律制裁。
对于子孙来说,为亲者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法律不允许子孙向官府告发祖父母、父母。
唐律规定,。
子孙若向官府举报,即构成“干名犯义”罪。
问题在于,在子孙告发父祖的情况下,被告发的父祖应作何种处理?
从理论上讲,如果被举报的情况属实,则说明被举报人的行为侵害了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触犯了法律,因此不论举报人是谁、其动机如何,也不论对举报人应作何种处理,被举报人都应该依法承担责任。
唐律规定,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子孙处绞刑;而被告之父祖,则不论所告是否属实,均视作自首而免于处罚。
这就是说,同样是犯罪,若被外人举报,应依据法律承担责任;但若被子孙举报,罪犯即可免于处罚。
根据清代学者的分析,古代法律之所以作如此有悖常理的规定,是为了让子孙在父祖犯罪的情况下,能够以极端的方式舍身救父祖,以自己犯罪受罚为代价换取父祖的免于处罚。
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再次作出退让,允许用连环犯罪的方式,以后罪排除前罪,惩处后罪而免罚前罪,以实现对亲情义务的肯定和保护。
而就法律自身而言,则是以一种曲折的方法,适用罪有所罚原则,在形式上保持国法的严肃性。
这种法律与亲情相互避让的原则,除了体现于父祖子孙关系,在其他亲属关系中也有所体现(《唐律跳议?
斗讼》)。
另外,父祖告子孙,即使为诬告,也不构成犯罪。
若所告属实,告者当然无罪,但如何处理被告者?
唐律规定:
被告亦同自首法,即免于处罚。
这与子孙告父祖又有不同。
在子孙告父祖的情况下,虽然父祖被免罪,但子孙仍得受罚,父祖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通过子孙违法举告的方式,转移到子孙身上;但在父祖告子孙的情况下,双方均可依据法律免于受罚。
这一制度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只能从法律与亲情的相互避让方面来理解它的设立宗旨。
三
伦理关系本身有亲疏远近之分,表现在人们的亲情义务上则是轻重程度的不同。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事涉两名以上互具伦理关系的人员,便会出现这一亲情义务与那一亲情义务的冲突。
为了化解这种矛盾,中国古代法律引入了丧服制度,使伦理关系的亲疏程度精确化,并且规定了“重情压轻情”的原则:
法律关系当事人只对与其有较亲伦理关系的当事人承担由亲情义务而演变出的法律只务,而对伦理关系相对较疏的当事人则不再承担这种义务。
唐律规定,民人犯罪,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互为容隐,不承担向官府举报的义务。
显然,这一规定是基于对亲情关系的保护而确立的。
但是,如果某人与加害人及被害人均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对于二者均须承担一定的亲情义务,那么两种亲情义务便会发生直接的冲突。
例如,子女应为犯罪的父母隐匿罪行,但如果是母亲杀害父亲,子女则处于两难境地。
为母容隐,这是子女应尽的基本的亲情义务之一,既为礼所规定,也为法所确认。
然而,仇人之中,没有比杀父者更为可恨的。
此时的子女在履行亲情义务方面,再难两全。
如何解决这一冲突?
唐律采取了重情压轻情的原则。
它规定,母亲杀死父亲,不论是嫡母、继母,还是慈母,作子女的皆不再受子孙不得告祖父母、父母禁令的约束,也不再履行为母容隐的义务,可以而且必须向官府告发(《唐律蔬义?
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