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docx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docx(5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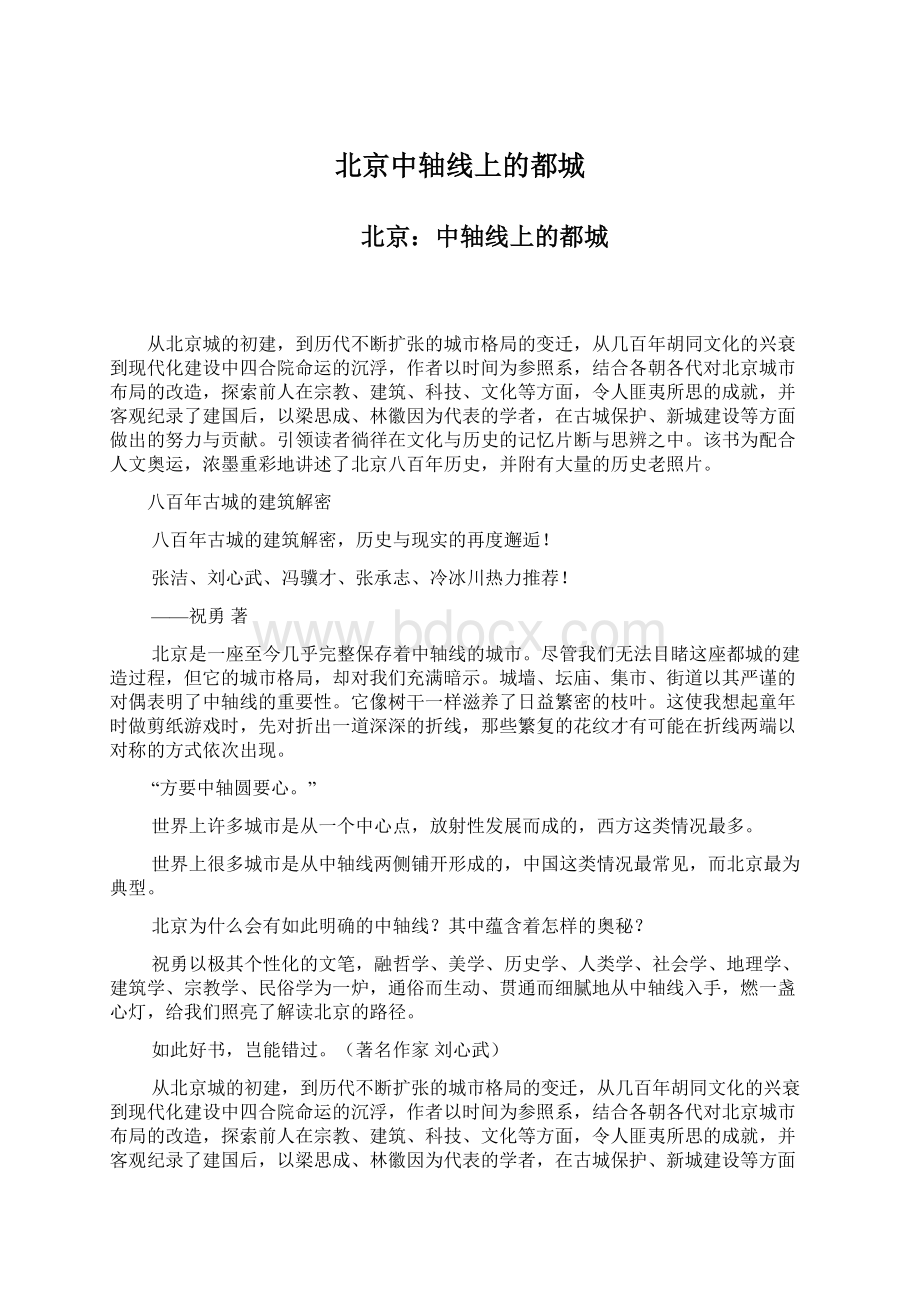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北京:
中轴线上的都城
从北京城的初建,到历代不断扩张的城市格局的变迁,从几百年胡同文化的兴衰到现代化建设中四合院命运的沉浮,作者以时间为参照系,结合各朝各代对北京城市布局的改造,探索前人在宗教、建筑、科技、文化等方面,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就,并客观纪录了建国后,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学者,在古城保护、新城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引领读者徜徉在文化与历史的记忆片断与思辨之中。
该书为配合人文奥运,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北京八百年历史,并附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
八百年古城的建筑解密
八百年古城的建筑解密,历史与现实的再度邂逅!
张洁、刘心武、冯骥才、张承志、冷冰川热力推荐!
——祝勇著
北京是一座至今几乎完整保存着中轴线的城市。
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都城的建造过程,但它的城市格局,却对我们充满暗示。
城墙、坛庙、集市、街道以其严谨的对偶表明了中轴线的重要性。
它像树干一样滋养了日益繁密的枝叶。
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做剪纸游戏时,先对折出一道深深的折线,那些繁复的花纹才有可能在折线两端以对称的方式依次出现。
“方要中轴圆要心。
”
世界上许多城市是从一个中心点,放射性发展而成的,西方这类情况最多。
世界上很多城市是从中轴线两侧铺开形成的,中国这类情况最常见,而北京最为典型。
北京为什么会有如此明确的中轴线?
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奥秘?
祝勇以极其个性化的文笔,融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宗教学、民俗学为一炉,通俗而生动、贯通而细腻地从中轴线入手,燃一盏心灯,给我们照亮了解读北京的路径。
如此好书,岂能错过。
(著名作家刘心武)
从北京城的初建,到历代不断扩张的城市格局的变迁,从几百年胡同文化的兴衰到现代化建设中四合院命运的沉浮,作者以时间为参照系,结合各朝各代对北京城市布局的改造,探索前人在宗教、建筑、科技、文化等方面,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就,并客观纪录了建国后,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学者,在古城保护、新城建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引领读者徜徉在文化与历史的记忆片断与思辨之中。
该书为配合人文奥运,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北京八百年历史,并附有大量的历史老照片。
作者介绍
祝勇,著名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大抵分为两类:
思想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前者多发表于《读书》《书屋》等刊,后者多见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刊。
已出版个人作品二十余部,其中有《禁欲时期的爱情》《改写记忆》《旧宫殿》等,并有三卷本《祝勇作品集》行世。
主编有《重读大师》《布老虎散文》等。
曾担任CCTV2005年大型历史电视片《1405,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的总撰稿人。
序
“中国”的“中”字,是对于古代城市中轴线的最好的图示。
从这个象形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座四方的城池,和贯穿城池南北的中轴线。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轴线先于城池,还是后于城池?
它在中国人的城市观念中发生过怎样的影响?
显然,中轴线为我们进入古代城市提供了一条最便捷的途径。
北京是一座至今几乎完整保存着中轴线的城市。
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都城的建造过程,但它的城市格局,却对我们充满暗示。
城墙、坛庙、集市、街道以其严谨的对偶表明了中轴线的重要性。
它像树干一样滋养了日益繁密的枝叶。
这使我想起童年时做剪纸游戏时,先对折出一道深深的折线,那些繁复的花纹才有可能在折线两端以对称的方式依次出现。
中国人的房屋、城市以方形为主,这也许与天圆地方的观念有关。
而在这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中,坐标原点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商代甲骨文中,也透露出当时中国人已经具备关于东西南北中的认识。
在所有的方位中,“中”无疑致关重要。
它是空间的起点,是所有方向的交汇处,因而,它是最尊贵的方位。
无论对于一个家族、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国家,莫不如是。
“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
”(《吕氏春秋·慎势篇》)
《周礼·考工记》中对于宫城建设格局有着严格的规定,表明了宫城位于都城中心的原则。
此后,随着礼衰典废,克己复礼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选择,并因后世尊儒而成为中国人文思想的一条主线。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周礼》中的建城思想在许多王朝中并没有得到贯彻。
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都城格局也很分散,大多根据自然条件布局,缺乏严谨的规划。
这是我们在许多古都无法寻找到一个清晰的城市中轴线的原因。
金朝在北京规划中都时,开始借鉴宋朝的城市规划经验,设置了一条城市中轴线。
元朝忽必烈进京,规划元大都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一座中心台。
关于这条轴线与这座都城的关系,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所幸的是,这条中轴线以其巨大的魅力和严谨的科学性,抗拒了时间的损毁,一直延续到今天。
梁思成先生说: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伟大的中轴线》,《梁思成全集》第卷,第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年版)
作为一座曾经浩劫的古代都城,北京的城墙、民居、街巷都曾遭遇灭顶之灾,惟有中轴线保持着原有的完整性,使得我们这些后来者有机会亲历这座都城的秩序和美。
进入北京的方式有很多,但从中轴线进入北京,或许是最好的一种。
它不仅是空间的线索,也是时间的线索。
从元代到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历史都能从这条轴线中找到依据。
这也是许多旅行者在抵达北京后,最先踏访中轴线的原因。
二OO二年秋天,北京电视台制片人吴群找我,准备投拍一部以中轴线为线索呈现北京八百多年建都史的人文纪录片。
这部片子使我有机会悉心打量这座不平凡的城市。
从那以后,我用了两年时间为那条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寻找历史证据,访问了许多历史见证人,并把剧本拓展为一部书稿。
由于在写作时需要考虑电视受众,因而,即使将其转化为著作,也充其量只是一个普及读本,但我相信面对北京,所有的书写者都不会流露出轻慢的表情,他们会谨慎对待笔下的每一字。
这座坚硬同时脆弱的古都将会使所有与之相关的话题显得庄重沉静,小心翼翼。
二OO四年十月十八日
印象:
贯穿八百年的线索(图)
50年代,北京的一次施工,从地安门地下挖出一只石鼠,从正阳门地下挖出一匹石马。
这两件孤立的文物,在地下埋藏了多久?
它们同时出现在中轴线上,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
景山并不高峻,但高度刚好适宜人们俯视这座古老的城市。
景山制高点上的万春亭,是北京中轴线上惟一没有实用功能的宫阙建筑,然而它却被赋予更加重要的意义——这座突起的四角攒尖式古亭却给人们观察这座古城提供了最佳视角。
每到重阳,明朝的皇帝都会登临景山,圣驾在山顶升座,俯视他的重重殿宇,和无限江山。
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北京这座古老都城的几何中心,一颗曾经跃动的心脏,它决定了城市的轮廓,以及道路经脉的方向。
这个几何中心,从明代至今,从未偏移。
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进行的一次考古发掘,从在景山北墙外探出一段宽十八米的南北大街,并在景山公园内寿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筑夯土基址,这些证据无疑给历史学家们带来意外的惊喜——这里不仅仅是明清都城的中轴线,元大都的中轴线也自北向南从这里穿过,从而将这条中轴线的历史提前的一百年。
当学者们为元大都的中轴线是否穿过北海中的琼华岛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这次发掘证实元大都的中轴线与目前这条中轴线完全重合,只不过是起止点不同罢了。
从景山上向北看,最瞩目的建筑便是鼓楼。
元朝初年,大画家王冕买舟下东吴,北游燕都,便在鼓楼边的胡同里,隐居多年。
喋喋不休的争论终止以后,学者们已经认定那一带是元朝都城的几何中心,元朝建城时兴建的“中心台”就在那里。
它最早确立了北京目前这条中轴线的位置。
那么,元朝为什么要选择那里建造“中心台”,而明代,又为什么将城市中心点南移到景山的位置上?
古人建城,都要建立“中心台”,作为整个城市的几何中心。
北京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
从西周时期到辽金时期,北京作为地方割区的首府,城市的中心点和中轴线不断漂移。
直到元代,蒙古铁骑扫荡了华夏四方,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蒙古骑兵在金朝皇宫内点燃的一把大火中,告别了那个已经瓦解的女真王朝。
公元1260年,踌躇满志的忽必烈第一次踏进这座梦境一样的城市。
金宫的废墟已无法居住,城外东北方向一片湛蓝的湖水却吸引了他。
那片水当时名为积水潭,今天叫北海。
两年后,有人把一整块玉石雕琢而成、名叫“渎山大玉海”的大酒瓮进献给忽必烈。
也是在这一年,忽必烈批准了著名水利工程学家郭守敬提出的放弃金中都的莲花池水系,引导高梁河水系进入积水潭,为未来的都城取得更丰沛的水源的设想。
新城市的中心点,终于在积水潭东北岸,也就是今天鼓楼的位置上,尘埃落定。
中心点确定之后,城市中轴线和城池的位置也自然得以确定。
丽正门(今天安门)内的干道,向北穿越皇宫,直抵钟鼓楼附近的“中心台”,正是沿中轴线开辟出来的。
中心台仿佛投入平静水面的一颗石子,而宫城、皇城和外城,则如辐射的涟漪,环环相套。
忽必烈或许没有想到,他所确定的中轴线,在八百年中再未改变。
仿佛一只沉甸甸的镇纸,压在漂泊的地图上。
然而,当一座帝王之城日渐清晰地显露形骸的时候,中心台却悄然消失。
如同一个魔术师,在“变”出一系列新奇的事物之后,悄无声息地,收回他的道具。
明代以后,中轴线没有再度漂移,只是城市中心点悄然向南滑动,固定在景山这个位置上。
景山原名“万岁山”,用挖掘护城河和南海的泥土堆筑而成。
古代风水学要求宫殿“背山面水”。
而都城北面,只有琼华岛上有座土山,这也是有学者误认为元大都中轴线穿过琼华岛的原因之一。
但是,让中轴线被水域割断,显然并非理想的设计。
用河泥筑山,这项聪明的方案,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土方堆积的难题,而且符合了古代建筑的山水形制,成为新都城设计施工中的不二之选。
于是,景山,就成了宫城背后的靠山,而它面临的水,是同样由人工开掘的金水河。
还有一个问题是,都城的中心点为什么出现在现在这个地方?
原来万岁山中峰,恰好居于元代宫城最重要的宫殿——延春阁的位置。
于是,万岁山的另一层意义便显露出来——用于压制前朝的“风水”,让它永无翻转的机会。
所以万岁山也叫“镇山”,而“景山”一名的使用,则是从清代开始。
也许我们能够借助想象复原明代中轴线上宏伟的景观。
自南向北,分别是:
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神武门、北上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殿、地安门、鼓楼、钟楼。
它们从永乐、嘉靖时代起,就占据着都城的轴心位置。
中轴线是一条抽象的线索,但它因这些建筑而有了具体的形迹,甚至随建筑高度的起伏而具有了跳动的乐感。
清朝时,一位外国公使抵京,要面见皇上,但又拒绝下跪。
礼部官员于是“别有用心”地安排他从正阳门进城。
这显然是一次不平等的对话,一方是渺小的个人,另一方是规模宏大的东方建筑群落。
他走过大清门、千步廊和御道,天安门金色的重檐、深红的城楼、洁白的阶石栏杆、石狮华表,以深远的蓝天为背景,如同梦境里的布景,令他倾倒。
走过端门,凹字型的午门,充满东方王朝的神秘力量;而午门后的太和殿广场,却又豁然开朗,节奏变得舒缓,有内金水河弯曲流过,如天国般宁静深远。
在太和殿上,他身不由己地跪倒,不仅因为宫殿道路的巨大尺度令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更是被中轴线上透露出的王气所征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解开出土石鼠和石马的谜团。
天干地支中,子为鼠,午为马。
这两只分别被埋藏的石雕,暗示着中轴线实际上是城市的子午线。
整个城市的建筑都以此为对称。
即使大地上的景物不断被时间篡改,这两只被埋藏的石兽也将恒久述说曾经存在的真相。
如今,北京市政府做出恢复永定门城楼的决定,从而使这条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的完整性得以复原。
此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设计方案在招标中,中轴线的长度,正随时间一起延伸。
格局:
方形城池(图)
这是一张明代的凤阳城地图。
这是一张明北京地图。
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这两张古老的地图,布局上居然惊人的相似。
凤阳是一座明代都城,但比起西安、洛阳、南京、杭州这些古城,人们却知之甚少。
这座从前的繁华都城如今显得空疏寂寞。
但是,北京的史学和都城学家们,却时常到这里研究、考察。
显然,凤阳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什么吸引了专家们的脚步?
那些倾颓的城廓和被野草遮蔽的小径,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时间的流向永远向前。
对于古代建筑上残留的历史记忆,人们已经熟视无睹。
一个古王朝的伟大梦想,早已淡出他们的视线之外。
东土城路、西土城路、北土城路。
这些地名对于北京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谁能想到,这些平直通畅的大路,与八百年前雄关高墙的联系?
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北土城路东段辟建元土城遗址公园。
仿佛未随时间流逝的只言片语,保留着些许历史的证词。
只有细心的人,才能透过残迹中那些雕刻精美的排水孔道,推想这座都城昔日的繁华气派。
明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朱棣到北京巡狩的第三天,“交趾进白象,泰宁侯陈 率文武百官上表贺”。
《太宗实录》记载了这一事件。
皇帝打猎和外国进贡白象仅仅是一种表象,而背后的秘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那就是在北京营建都城,为从南京迁都北京做准备。
泰宁侯陈 成为这一计划的秘密实施者,而且与皇帝朱棣保持着单线联系,可以越级请示。
五个半世纪以后,即公元195X年,北京在拆除明代城墙的时候,在西直门一带(?
)意外地发现了包裹在城砖里面的元代土垣,从而证明了一个事实:
明代城墙是在元代城墙的基础和位置上修建的——至少东西两侧是这样。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陈 的这一方案,很可能包含着两层目的:
一是为了保密,即使施工初期就显示出这座城市的规模比起南京要大得多,但在当时却未必有人推测出这一营建的真实目的;二是保证都城的布局,使宫殿的位置刚好出现在中轴线上。
公元19XX年,在崇文门至宣武门一线的另一次考古发掘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
在这里深达五米的流沙层中,纵横交错、相互叠压着深达十五层的木料。
这些木料,彼此间都用铁扒锔钉牢,组成一个整体,木料间的空隙用沙土填实,上面再起各层夯土夹筑碎砖层。
在地面的景物消失之后,地下的埋藏中无疑充满了岁月的暗示。
这些出土器物,为明代南城墙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显然,它们都是城墙的地基。
明朝缩减了居民稀少的北部,从元都北城墙向南收缩约五里。
南城墙也随之南移了五里,由今天长安街的位置,平移到崇文门—宣武门一线。
于是,拆除了元代的南城墙,填平护城河,并在新城墙的位置上重建地基。
原来居全城中心的钟鼓楼,偏至城北,成为新中轴线的起点。
如果说此时已退至塞外的蒙元势力对故都的格局还能施加什么影响,那就是蒙古骑兵不断南下骚扰,迫使明世祖朱厚熜采纳大臣建议,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一五六四年),决定在原有的外郭之外,再加筑一圈城墙。
于是在南郊,修筑了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因财才不济,南城墙修成后,便匆忙北折,形成了北京“凸”字型轮廓,并把位于中轴线南端的天坛和山川坛纳入外城墙以内。
清代以后,新的政权并未对北京的城市格局进行大的改动,只是规定了“内满外汉”、分区居住的等级制度。
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在中轴线上建立了连线。
有别于元代以前各个朝代的巨大颠覆,北京城处于继承性发展的稳定阶段。
然而,当笔者如大多数人一样,习惯于从时间的追溯中复原历史的时候,却遗忘了历代都城在空间上的暗示。
显然,从茫漠的空间中搜寻历史的脚步将更加艰难。
我们从此看到了精研历史的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他们发现了凤阳的奥秘,发现了一个遥远而偏僻,绝少被人提及的废都,在北京建都史上发生的重大作用。
所有秘密都从这些发黄的地图上显现出来——从来没有一个古代都城,像凤阳这样最大限度地还原着《周礼·考工记》的建城设想,无论宫殿、衙署、千步廊的序次排列,还是左祖右社的位置,都纠正了所有朝代(包括元朝)的“偏差”。
《周礼·考工记》是一部成稿于西周时期的著作,讲述了用礼制思想营建都城的设想,制定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基本法则。
但这一法则在以后的朝代中并未得以准确的实现。
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王城图》被认为是对《周礼·考工记》的图景解析。
这个王城图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古人把方形认定为都城的理想格式,而不采用其他几何图形?
比如圆形,或者三角形?
——实际上,在周长相同的情况下,圆形的面积最大。
方形城池的出现也许与古人对大地的认识相同。
他们用“天圆地方”来注解天地的形状,所以祭天的坛丘,一律使用圆形,而帝王的居所,要占据城市的中心,也必将使用“城中城”的模式,而方形城池,最有利于形成对称格局,形成庄严的礼制秩序。
凤阳和北京,如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一样,保持着密切的血缘传承关系。
区别仅在于当后者在华北平原的万千气象中一天天壮大,前者却如尸体般在时间深处腐烂和消失。
朱元璋称帝后,一度决定把自己的家乡安徽临濠(凤阳)定为国都,让自己的出生地成为世界的中心和时间的起点。
不同于汉长安、曹魏邺城、隋大兴、唐长安等都城,他试图让自己的都城最大限度地贴近《周礼·考工记》的设计思想。
可惜的是,这项从洪武二年开始的工程,仅持续了六年,就戛然而止。
那个偏僻的一隅,显然不具备建都的条件。
他只好暂时回到南京,以为京师。
成祖朱棣决心迁都北京。
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安排。
他显然知道中都凤阳的地位。
他在七八岁时目睹过营建中都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青年时代,他奉命与兄弟诸王在凤阳练兵,又亲历了改建皇陵的工程。
决定迁都之后,他多次亲赴凤阳,实地堪察。
这两座遥远的都城,又怎能不保持天然的联系?
地理交通上的先天不足,毁灭了朱元璋的梦想。
XX年后,他的儿子把凤阳搬到了更具王者气象的地方。
明永乐十七年年底,明成祖朱棣在新落成的紫禁城太和殿接见了来自西亚波斯帖木儿帝国哈烈的沙哈鲁使团,并不无炫耀地邀请他们参加了新宫落成的庆祝典礼和新年大赦令的颁布仪式。
这一年的四月,也就是在新都建成之前,陈 已经离开人世。
宫城(上):
中央之城(图)
将近40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植物园一位名叫溥仪的园丁,买了一张故宫的门票。
然后,他随同许多游客一起,参观了这座昔日的宫殿。
自从一九二四年,他作为废帝被驱逐出这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一切都没变。
紫禁城这座豪华的宫城,在清代末期已经破落不堪。
太和殿广场上的杂草已长到一人多高,空旷的风声取代了朝仪的礼乐,百官列队的地方堆满垃圾。
我们仿佛看见了一种制度在最终完结时那幅荒凉颓废的表情。
与溥仪记忆中的衰草枯杨不同,整修之后的故宫,在天空的无限背景下,殿宇威武宏伟,如梦境里的布景。
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它既可以破坏一切坚固的楼宇,也可以修复残缺的旧迹。
尽管早在1925年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但是由于当时财力所限,故宫雉堞圮毁,椽望糟朽的状况直到建国以后才有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几度对故宫进行大规模修缮。
那时的溥仪不知是否会想到,三十多年后,国家再度为故宫古建保护拨款数亿元。
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组群,故宫将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故宫,就是宫城,通常又叫紫禁城。
紫禁城这个名称中,包含着来自天空的某种暗示。
紫微星垣(即北极星)位于天空的中央,被群星所环绕,那里是天帝永恒的居所,名叫紫宫。
天子是上天之子,他以上天的名义统治人世。
于是,明清皇帝把自己的宫城称为紫禁城,来与天帝的宫殿相对应。
中国古代建筑是以群体建筑在空间上的分割搭配见长,通过建筑之间的序列关系,而这所有序列的基点,都是“以天子为尊”。
紫禁城,是封建礼序的视觉化体现。
它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四合院,其中又包含着无数个小四合院,那些小四合院分别有着各自的中轴线,同时又以紫禁城的中心轴为对称(或大体对称),如同杂乱无章的世界,依靠神圣庄严的礼制思想,建立起井然的秩序。
建筑设计必需遵从礼的规范,表达出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
皇宫的设计者们娴熟地运用着礼制的法则,哪怕半点差错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紫禁城是中央之城,那么,紫禁城的中心又在哪里?
如果我们在前朝院落的四角划一对角线,那对角线的交叉点刚好落在太和殿上。
太和殿是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一般只有皇帝登基、册立皇后、每年三大节(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等重大活动时,皇帝才能亲临。
显然,这里是整个宫殿的核心。
1908年,权力顶峰上明争暗斗的两个致关重要的人物——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
一个三岁的男孩被抱到了太和殿的中央,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
也许这个孩子还意识不到,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
他甚至被丹陛上、丹墀中和庭院里整齐站立的臣子们山呼万岁的巨大回音所吓哭,但是,对于他的国家和子民来说,一个孩子在太和殿的朝仪上出现,与他在后宫中嬉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百官们听不到一个孩子哭闹。
他们只知道在飘荡的旌旗和缭绕的香烟后面,皇帝端坐在宫殿深处,在三层台基的高度之上,接受他们的朝觐。
宫殿是一件真正的龙袍,即使在远处,廷臣们也能分明感到皇帝的威严。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是太和殿,而太和殿的中心,则是皇帝的宝座。
只要坐在那雕龙金漆的宝座上,就等于出现在世界的中心。
群臣和万民的欢呼,在他的耳中,无疑是最动听的合唱。
被一层一层的宫墙、一重一重的宫殿包裹和庇护的,正是位于核心位置上的那把龙椅。
它是所有野心的目标,所有动荡的源头。
而它在高大的金銮殿里,却试图成为城市营建的理由和一切秩序的核心。
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建立了大顺国,但还没来得及坐上这把宝座,就失败了。
太和殿中央的这把御座上,总共坐过明清两朝的24个皇帝。
解放后,曾一度不知下落,最后专家们根据照片上龙椅的式样,在一个存放破旧家具的仓库中找到了这个破损严重的龙椅。
宝座的丢失,仿佛一种暗示,标明着紫禁城这座中央之城权力象征意义的最终瓦解。
不仅宫殿的排列顺序有着严格的规范,人们在宫殿中的行为也有严格的等级约束。
那些左右(东西)平行的路径、桥梁、台阶,分开了人们的行列——皇帝走中路,王公们走右路,大臣们走左路。
身份规定了他们一生的道路,超越位置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只有皇后大婚时,可以乘凤舆由午门正门入宫。
这是那个幸运的女人一生可以炫耀的资本。
慈安皇后(?
)就曾因此向从后门入宫的慈禧表露出她心理上的优越感。
这些严格的制度,并没有阻止集权统治的衰落。
礼制的辉煌,到了清末,就再也难以维系了。
光绪二十五年,即1900年八月初四,对于中国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个惨淡的日子。
但是八国联军及其使馆人员无疑都有很好的心情,他们在午门外聚齐,然后在俄军司令官利维涅奇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人去楼空的紫禁城。
他们轮流坐到乾清宫的御座上,出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紫微星垣所在的地方。
而300年前的1601年1月24日,他们的祖先利玛窦,在抵达中国十八年后,才带着四十多件珍贵的贡品,艰难地叩开这中央之城的大门。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年,各国领衔公使葛络干代表列强照会清廷议和大臣,此后他们取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权——在呈递国书或敕书时,从过去只有皇帝才能通过的御道上,进入紫禁城。
在以前的祖制中,这无疑是杀头之罪。
溥仪再次行走在雕刻着宝山龙纹的御道上。
这次是以游客的身份——今天的游人们进出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一律从正门通过,寂寞的中轴线变得拥挤和喧闹。
溥仪微笑着看着他身边的人群。
对历史深处的禁忌,他们所知不多,也没有必要遵循。
他们站在现在的时空里观察遥远时代的标本,他们纷乱的步伐湮没了皇帝的脚印。
宫城(下):
数字里的密码(图)
当人们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