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理论的转换.docx
《小说创作理论的转换.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小说创作理论的转换.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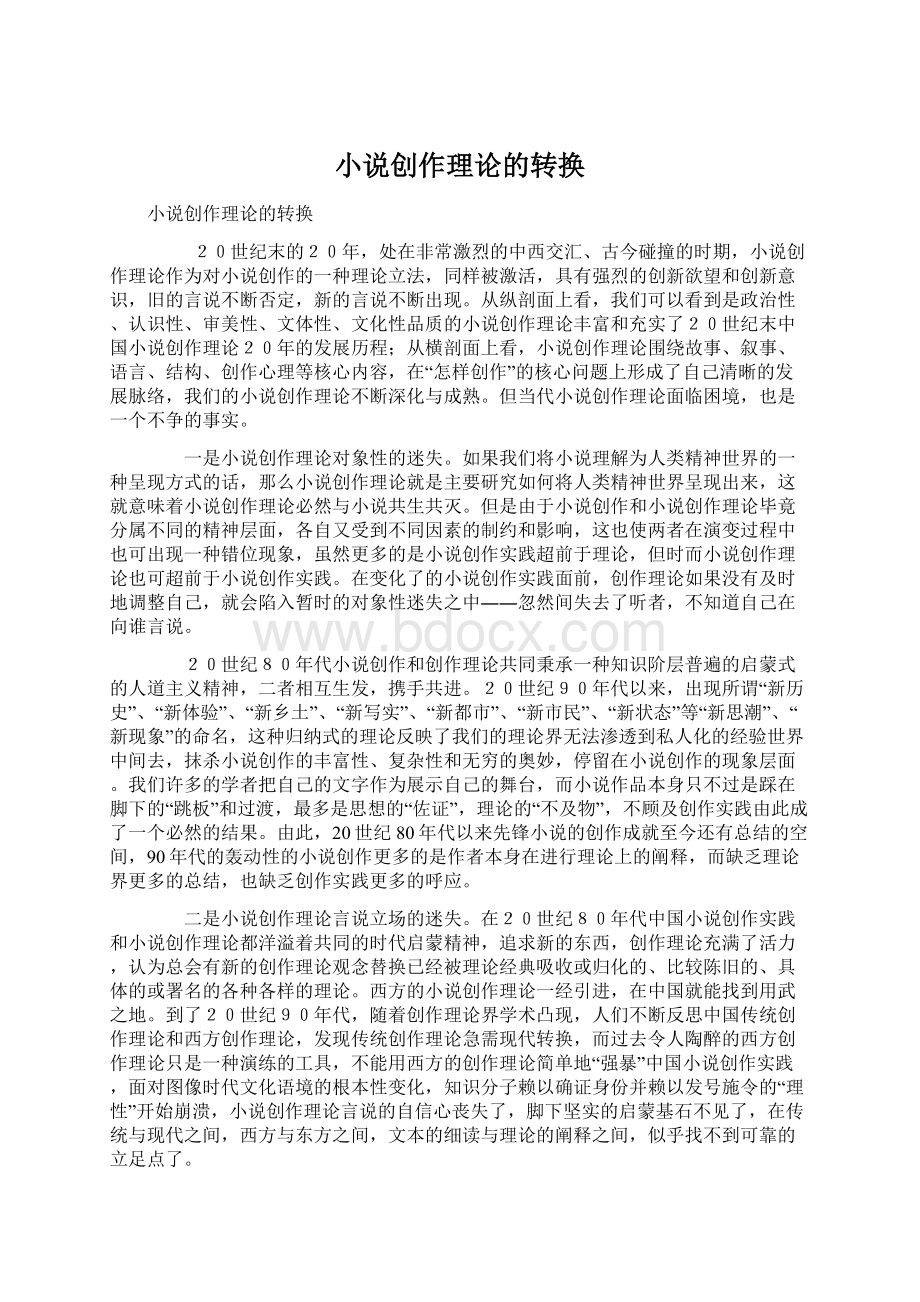
小说创作理论的转换
小说创作理论的转换
20世纪末的20年,处在非常激烈的中西交汇、古今碰撞的时期,小说创作理论作为对小说创作的一种理论立法,同样被激活,具有强烈的创新欲望和创新意识,旧的言说不断否定,新的言说不断出现。
从纵剖面上看,我们可以看到是政治性、认识性、审美性、文体性、文化性品质的小说创作理论丰富和充实了20世纪末中国小说创作理论20年的发展历程;从横剖面上看,小说创作理论围绕故事、叙事、语言、结构、创作心理等核心内容,在“怎样创作”的核心问题上形成了自己清晰的发展脉络,我们的小说创作理论不断深化与成熟。
但当代小说创作理论面临困境,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是小说创作理论对象性的迷失。
如果我们将小说理解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呈现方式的话,那么小说创作理论就是主要研究如何将人类精神世界呈现出来,这就意味着小说创作理论必然与小说共生共灭。
但是由于小说创作和小说创作理论毕竟分属不同的精神层面,各自又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也使两者在演变过程中也可出现一种错位现象,虽然更多的是小说创作实践超前于理论,但时而小说创作理论也可超前于小说创作实践。
在变化了的小说创作实践面前,创作理论如果没有及时地调整自己,就会陷入暂时的对象性迷失之中――忽然间失去了听者,不知道自己在向谁言说。
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和创作理论共同秉承一种知识阶层普遍的启蒙式的人道主义精神,二者相互生发,携手共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所谓“新历史”、“新体验”、“新乡土”、“新写实”、“新都市”、“新市民”、“新状态”等“新思潮”、“新现象”的命名,这种归纳式的理论反映了我们的理论界无法渗透到私人化的经验世界中间去,抹杀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无穷的奥妙,停留在小说创作的现象层面。
我们许多的学者把自己的文字作为展示自己的舞台,而小说作品本身只不过是踩在脚下的“跳板”和过渡,最多是思想的“佐证”,理论的“不及物”,不顾及创作实践由此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由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创作成就至今还有总结的空间,90年代的轰动性的小说创作更多的是作者本身在进行理论上的阐释,而缺乏理论界更多的总结,也缺乏创作实践更多的呼应。
二是小说创作理论言说立场的迷失。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实践和小说创作理论都洋溢着共同的时代启蒙精神,追求新的东西,创作理论充满了活力,认为总会有新的创作理论观念替换已经被理论经典吸收或归化的、比较陈旧的、具体的或署名的各种各样的理论。
西方的小说创作理论一经引进,在中国就能找到用武之地。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创作理论界学术凸现,人们不断反思中国传统创作理论和西方创作理论,发现传统创作理论急需现代转换,而过去令人陶醉的西方创作理论只是一种演练的工具,不能用西方的创作理论简单地“强暴”中国小说创作实践,面对图像时代文化语境的根本性变化,知识分子赖以确证身份并赖以发号施令的“理性”开始崩溃,小说创作理论言说的自信心丧失了,脚下坚实的启蒙基石不见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西方与东方之间,文本的细读与理论的阐释之间,似乎找不到可靠的立足点了。
鉴于上述情况,创作理论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调整自己的思考模式,以应对已经变化了的生存环境:
从小说创作理论实际的角度看,我们必须看到小说创作理论的确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对小说创作实践的巨大影响作用,但因此气馁则大可不必。
对文学研究的未来,米勒是清醒的,惟其清醒,他才能够“执著”下去;也惟其清醒,他才能够以变通的方法坚持自己的执著,坚持文学研究的不可取代性以及与人类的永恒相伴。
按照米勒的思路,同样小说创作理论也会与小说永恒相伴,与人类永恒相伴,只是内涵和方式变化了,或者说该死的小说死了,自然以它为研究对象的那部分小说创作理论也消失了;而该活的小说活着,自然以它为研究对象的创作理论也应该活着。
而且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的学术反思,中国的学者已经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西方的新潮文艺理论包括小说创作理论与本土文化根基、本土的创作实践间的某种隔膜,我们应该渴望在中国现实土壤中找到扎扎实实的生长点。
的确,古老的民族自尊心和崭新的“后殖民”理论共同支持这样的结论:
本土的理论更适合于阐释本土的事实。
当然,本土的理论并不是传统的理论。
对小说创作理论而言,它根据中国小说自身的演变而不断丰富,这种丰富既包含传统理论的继承,也包含异域理论的移植。
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应立足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实践,在与传统与异域的理论融合之间不断增强自身的生命活力:
小说创作理论必须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小说的内部结构逐渐明晰:
主流小说、先锋小说、通俗小说三分天下。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先锋作家诸如叶兆言、苏童等很快收敛起实验探索的锋芒,热衷于故事性文本的创作,叶兆言甚至就已经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通俗作家。
到晚生代的小说创作,将欲望游戏,猎奇经验等表象化的书写奉为基本的叙事法则,这种姿态就已经与通俗小说殊途同归了。
可以说,这种雅俗的分化和移易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是常有的。
但在图像时代,这种事例又有了新的内涵,这一轮由对峙到互动融合的趋势,主要是以纯文学放下架子自我还原为特征。
对于纯文学的归附,通俗小说不计前嫌,其实通俗小说早就悄悄地将纯文学的革命成果变成自己的血肉,比如纯文学所追求的人性深度,通俗小说已将其转换为招徕读者的手段;在故事模式上,反大团圆也常常为其所用。
事实上,通俗小说自身固有的“轮换”策略、独特的创新机制以及类型自身配方程式的不断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比一些自我重复的纯文学文本更能表现文学的创新能力,尽管这种创新的动力来自市场法则。
在图像时代,小说创作实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仅有小说和其它文体的相互交融,更有审美与科技、审美体验与生活体验的融合互渗;不仅有小说创作观念、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有小说艺术的整体存在方式的变化;不仅审美感知经验发生了变化,作家、读者等人的精神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传统的小说样式发生变化,而且还出现了网络小说、短信小说等新的小说样式。
在这样巨大的变化面前,小说创作理论没有理由恪守自己的研究边界,而应该积极地去研究小说样式新的变化新的动向,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和新的动向,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小说创作理论还必须深化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21世纪初,文艺学“边界”论争存在不同知识分子角色的基本冲突,一些知识分子做学问以“立法者”自居,更多学者认识多元时代学术应以“阐释者”出现,阐释就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是一种理解的行为。
具体到小说创作理论而言,同样也应以“阐释”的面目出现。
这种方法运用到小说创作理论领域,阐释就意味着理论的言说必须放下架子,学会倾听创作实践的细微的声音,不要试图进行单向的立法活动。
而应在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创作理论主体的精神世界之间进行充分的对话与交流。
政治性的小说创作理论因想“立法”而遭拒斥,审美性小说创作理论因重视主体性而弘扬,但也因单一的主体性,忽视“主体间性”,缺乏对话和交流而需要进一步的更新与发展,文本性小说创作理论因回归文学本位拓展了小说创作理论的研究领域,但同样割断了对话的渠道,变成一种自吟自唱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惟有文化性的小说创作理论深昧小说创作实践是极其复杂的多面的流动不居的精神文化现象,单一的创作理论无法全面深刻把握小说创作活动的奥秘,在文化性小说创作理论之下,各种不同的创作理论观念,强调政治性、社会性也好,强调文本,强调心灵也好,强调古典也好,强调现代、后现代也好,这些众多单一的声音共同喧哗,如能走综合创新之路,则预示“阐释”性小说创作理论的出现有了更多的机会。
小说创作理论还应转换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
中国传统的小说创作理论因重经验、直观、体察、感悟而在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方面追求模糊、多义、不确定性,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一种印象式、点评式。
而当代形态的小说创作理论则更多地转向了理性、思辨、推理、归纳,对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严格界定,在理论形态上则表现为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追求一种系统化。
这种强大的思辨的力量将感性的光华遮蔽得微乎其微,概括和条分缕析一点一点地蚕食了飞扬的文采,不见了澎湃的激情,不见了诗化的传达,不见了小说创作个体的整体感,不见了小说创作自身鲜活的魅力。
也许这种小说创作理论能提升人们对小说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但一些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却在理论的束缚中被淡化,被舍弃。
而当代一些作家的创作理论观念的表达虽才情勃发、知识灵动、情感饱满,但因过于感性,经验局限,视野不够开阔,无法熟悉复杂的小说创作实践。
王安忆的《心灵世界》为我们当代小说创作理论提供了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它既不同于逻辑严密,以思辨见长的学院派小说创作理论,也不同于过于感性的创作随笔,她从个人性和心灵性出发,着重通过个案说明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着重评析小说“为什么创作”和“怎样创作”,并印证“小说是个人心灵世界的表现”这一中心论点。
这种小说创作理论确定了一个可靠的理论支点,在感性的灵光辉映之下,理性的结论也没湮没于具体的场景之中,也能水到渠成地传达自身特定的观念。
这种理论的言说方式,使小说创作理论的言说充满了文学的灵性,阅读的快乐使理性不必经过各种理论前提的推断、思索便可抵达我们的心灵之岸。
小说创作理论也可远离“僵死”“刻板”“艰涩”“玄奥”之类的指责,虽然这不是我们小说创作理论最理想的表达方式,心灵世界应该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联,但这是目前在图像时代小说创作理论寻求突破的一种可喜的努力。
戴燕曾经谈到“当文学已经非常地意识形态化、非常地体制化的时候,以一种瓦解的姿态,首先令文学重新回到真正文学的位置,令人们对文学的感性得以恢复,得以自然蓬勃地生长,大概正是必须要经过的步骤”。
戴燕是想文学回到文学,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话语表达方式也是使中国小说创作理论回到中国小说创作理论的一个必经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