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要和经典对话一余秋雨的为学与为人.docx
《青年人要和经典对话一余秋雨的为学与为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青年人要和经典对话一余秋雨的为学与为人.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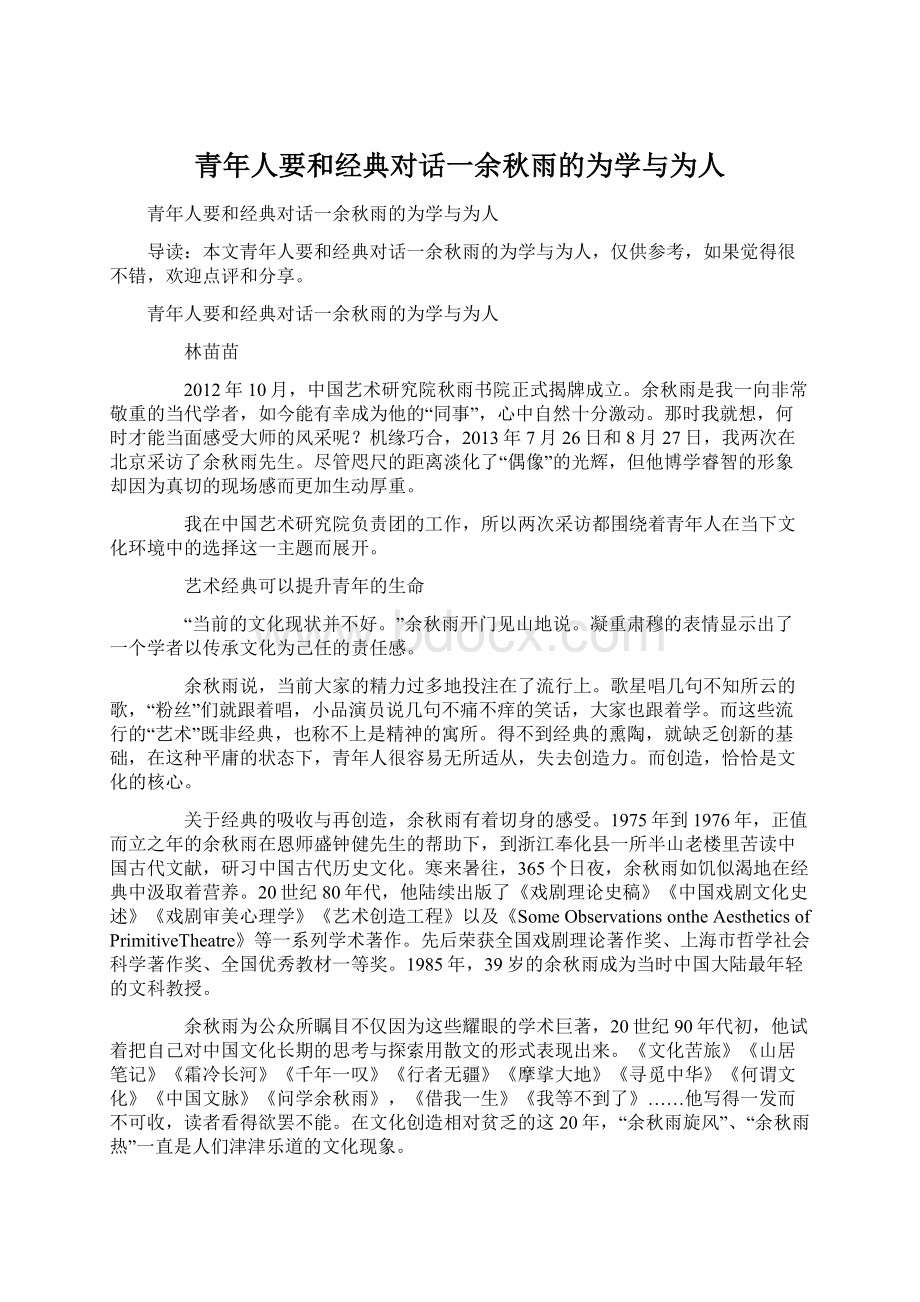
青年人要和经典对话一余秋雨的为学与为人
青年人要和经典对话一余秋雨的为学与为人
导读:
本文青年人要和经典对话一余秋雨的为学与为人,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青年人要和经典对话一余秋雨的为学与为人
林苗苗
2012年10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正式揭牌成立。
余秋雨是我一向非常敬重的当代学者,如今能有幸成为他的“同事”,心中自然十分激动。
那时我就想,何时才能当面感受大师的风采呢?
机缘巧合,2013年7月26日和8月27日,我两次在北京采访了余秋雨先生。
尽管咫尺的距离淡化了“偶像”的光辉,但他博学睿智的形象却因为真切的现场感而更加生动厚重。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团的工作,所以两次采访都围绕着青年人在当下文化环境中的选择这一主题而展开。
艺术经典可以提升青年的生命
“当前的文化现状并不好。
”余秋雨开门见山地说。
凝重肃穆的表情显示出了一个学者以传承文化为己任的责任感。
余秋雨说,当前大家的精力过多地投注在了流行上。
歌星唱几句不知所云的歌,“粉丝”们就跟着唱,小品演员说几句不痛不痒的笑话,大家也跟着学。
而这些流行的“艺术”既非经典,也称不上是精神的寓所。
得不到经典的熏陶,就缺乏创新的基础,在这种平庸的状态下,青年人很容易无所适从,失去创造力。
而创造,恰恰是文化的核心。
关于经典的吸收与再创造,余秋雨有着切身的感受。
1975年到1976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余秋雨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
寒来暑往,365个日夜,余秋雨如饥似渴地在经典中汲取着营养。
20世纪80年代,他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以及《SomeObservationsontheAestheticsofPrimitive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
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39岁的余秋雨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余秋雨为公众所瞩目不仅因为这些耀眼的学术巨著,20世纪90年代初,他试着把自己对中国文化长期的思考与探索用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何谓文化》《中国文脉》《问学余秋雨》,《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他写得一发而不可收,读者看得欲罢不能。
在文化创造相对贫乏的这20年,“余秋雨旋风”、“余秋雨热”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现象。
余秋雨的这些著作,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
《借我一生》因为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题材,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世界十大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一个专注于经典的人,如今成了经典的创造者。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余秋雨的学术专著属于专门的、小众的精神食粮,他们更喜闻乐见的,是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
在他之前,散文这种文体一般用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感,文笔自由,主题虽明却并不刻意突出,所谓形散而神不散。
而余秋雨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
他的散文有史实的叙述,有深沉的思考,还有鲜活的人物与生动的情节,厚重的主旋律之外,更有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
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用合理的想象把抽象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
当然,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学养和人文情怀的学者型作家,余秋雨并不是在肤浅地卖弄文笔和技巧,他的散文描写、记叙、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但他的核心表达方式仍然是议论。
只是这种沉甸甸的议论多与抒情融合,深入而浅出,举重而若轻。
称余秋雨为历史文化散文这一派的开山鼻祖并不为过,称他所创作的模仿者甚众的作品为经典也不为过。
“在如今的文化环境中,年轻人要怎么办呢?
你们有非常珍贵的青春时间,要接触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典,通过这种学习,你的生命就得到了提升。
对每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被艺术经典陶冶过和没陶冶过完全不同,他们今后的生命将会呈现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余秋雨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经典,他苦口婆心再三劝诫青年人要多读经典的那份诚恳也很让人动容。
对当今文化环境的“不好”,余秋雨具体指出了两点。
一是对经典的选择,二是当代的创造。
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二者的关系不是并列,而是递进,逻辑关系极其严谨。
“对于文化,什么才是真正人类的经典?
”余秋雨发问。
他认为,当前我们总结选择的环节做得很差。
“选一些乱七八糟的古代的那种权术谋术之类故事,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不是这样的,文言文或者三字经就一定全部是经典吗,也不是这样的。
”
余秋雨认为,真正的文化精英是存在的,而且对国家社会非常重要。
但是近些年来,掌握文化话语权的人并没有很好地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而是更多地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来对文化经典做出有偏差的选择。
对于这些人,余秋雨称之为“伪精英”。
而对于急需经典滋养的年轻人来说,由于他们的文化积累还不够,总是会对自己不懂的文化话语心存敬畏,这种敬畏心理却被那些‘伪精英’利用了。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里,“伪精英”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称之为假洋鬼子阶段,第二阶段是所谓拒绝世俗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所谓咬文嚼字的阶段”。
源既然不清,流自然浑浊。
“伪精英”们没能选择出正确的经典,那么这样的传播过程就是无效的。
“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
但是,余秋雨并不因为现状的不堪而悲观,他说,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
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的高峰的向往。
关于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余秋雨并没有一概而论,他把这个问题置于“文化”这一具体范畴来讨论。
“如果就文化而言,我坚持要以艺术经典为主,而不是历史经典。
因为历史它已经过去了,而艺术经典它和当代的人直接有关系。
无论是画、无论是诗歌、无论是音乐,好的作品是没有时间限定的,经典就是经典。
历史的记载可以过去,但是这种艺术经典不会过去,诗经还是那么美,离骚还是那么美,李白杜甫永远可以读下去。
当然我们也不能局限于眼前的风景,经典还包括国外的一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艺术作品,比如贝多芬、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罗丹。
遗憾的是,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的普及工作做得很差。
一些名家的名字大家也许知道,但是深入了解并且酷爱这些经典的人就很少了,对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也很少”。
余秋雨用艺术大师罗丹的一句话来打比方。
他说,曾经有人问罗丹,什么是雕塑?
罗丹回答,雕塑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
青年人的成长也正是一个雕塑自身的过程,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
“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那么,青年人用来雕塑自己的刻刀又是什么呢?
余秋雨的答案是,阅读,对艺术经典的阅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
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
”好奇心是青年人雕塑自己的重要动力,而对经典的阅读可以使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余秋雨还引用黄山谷的一句话来佐证他的观点:
“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
”
至于第二步的创造,余秋雨认为宏观上,当代缺乏好的风气;微观上,青年人对此也没有太大兴趣。
他给青年人开出的良方,依然是学习经典。
“更高一层来讲,年轻人可以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当然,这种创新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
要体现出自己,不要盲目地追随潮流”。
熟悉经典后要找到自己
“年轻人要用经典来提升自己,但是提升之后要注意,不能成为经典的奴隶。
”
如果不和他的一个观点“文化是一种创造”联系起来,余秋雨的这句话还是很令人费解的。
经典就是经典,是经过了时间和空间考验的人文遗产。
既然要提升自己就要别无选择地去学习它,那么提升之后便摆脱它是不是有数典忘祖之嫌?
余秋雨说,“创造文化”是年轻人的重要使命,所以平庸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敌人。
经典是属于古人的,如果年轻人一味地崇拜经典,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我们的文化岂不是要一直停滞下去?
熟悉经典是为了让年轻人的创造尽快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且,“趁年轻的时候把经典尽快地熟悉,越早熟悉越好”。
从这番话中,可以体会到余秋雨对年龄的一种敬畏。
其实,对时间,包括年龄的思考是秋雨散文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年代。
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这句话里,余秋雨对“青年”一词可以说是爱恨交织。
这是因为他是一个“过来人”,一个有智慧,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过来人。
他担心,青年如果不能在经典中塑造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会面临一个可怕的境地:
迷失自己。
在《关于年龄》一文中,余秋雨说,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
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
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是很大。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这段话又可以为青年与经典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很好的解读与参考。
经典之于青年,有什么具体的功用?
其一就是让他们在“无限的可能性”中找到相对正确的那一种。
人生的几个阶段,看似漫长,但关键的选择只有几次。
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客观条件对于选择有诸多限制,青年如果对于年龄的优势盲目乐观,过分大意,甚至挥霍,那就会在这个本应创造力十足的年代为自己埋下方向性错误的伏笔。
“一个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
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历史上推崇青年时代者并不少,其中不乏一些深刻的哲人,他们用优美的词句和十足的热情来歌颂青年,以此弘扬社会的生命力。
但余秋雨对这种现象冷眼旁观,他从中看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二律背反:
“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持相斡旋。
”
青年需要经典来提升自己,但囿于阅历和理解力,他们对经典的内涵不一定能完全领悟。
在余秋雨看来,刚刚放下历史课本的青年,很难能体察到历史的苍凉。
他们虽然也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侃侃而谈,但对于民众的质朴需求却不见得了解;他们引经据典地谈论文化,却不一定思考过文化的原始使命。
这个时候,如果把沉重的历史使命压在他们的肩上,不太公平。
假如再对他们一边加压一边怂恿,那“只能使他们变成一堆扭曲的形体和尖利的声音”。
这样的悲剧,“文革”初期就曾经真实地演出过。
有意思的是,余秋雨在对青年表现出诸多担心的同时,却对自己正身处的中年大加赞赏。
他说,“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同样的事情,只因年龄的不同,竟可以泛起不同的涟漪,这是一种“偏见”吗?
余秋雨似乎对青年能否在穿越经典之后找到自己不太乐观,在他的笔下反映的,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后,青年方能成熟、智慧,得体地应对环境与各种变化。
他说,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
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这样“自立的成熟者”当然应该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余秋雨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遭遇了某种荒唐的乱局,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不过,责任太大也会让人感到负担太重,人生的意味便会少了很多。
从这个角度讲,余秋雨赞赏中年,却并不歌颂中年。
他曾用诗来形客人生的三个阶段,老年是如诗的岁月,青年激情太多而缺少意境,是诗,但算不得好诗,中年太实际、太繁忙,都算不得是诗……
由激情而粗糙的诗到优雅从容的诗,“丰满”的中年原来只是个过渡。
可见余秋雨对青年其实是爱之深责之切,他鼓励青年要通过学习经典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想让他们把这一时期的多元体验转化为明确的定位和选择,这样才能在之后的中年时期坚定而强大,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顺利地度过人生的这一“精神断奶期”,最终写出一首意境幽然的诗。
那么,青年最可贵的品质,或者说最合理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呢?
在余秋雨看来,是真诚的谦虚。
他认为,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很精彩很复杂地存在过无数年,如果刻苦数年,我们可以在这块丰饶的土地上扎下根去,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连,那也就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了人类。
青年应该为这种接通而惊喜,这种接通可以使自己领略崇高,问津壮丽,体验多元,这种谦然安然的生态,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无谓浪费,让青年人有可能欢天喜地地活得像一个真正的青年。
经典,是这种“接通”的媒介。
而如果抱残守缺,不能打开创造之门,那就是接而不通,难以写出真正青年的诗了。
“创作可以让青年找到自己。
”余秋雨说,“三样东西的选择,经典、流行、自己,把流行去掉,要让自己和经典对话,让经典提升自己,让自己在经典的基础上,站在经典的肩上投入文化的创造。
最终,经典自己。
”
自从《文化苦旅》热销以来,余秋雨很多年都在作家富豪榜上位居三甲。
在当代中国,能将学者、作家、富豪这三种身份完美融合的,余秋雨绝对是一个代表。
而这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流行。
采访中,余秋雨没有追捧流行,也没有鄙弃流行,只是淡淡地把它置于一旁。
他说:
“在非常得意和骄傲的时候都要准备好被人家忘记的快速,快速的流行和快速的遗忘是一件事。
”
“流行的方式也会改变。
”余秋雨补充道。
这句话提醒我,已渐渐步入“诗一样”年龄的余秋雨,还一直保持着对新技术、新信息的敏锐感觉。
这是他一贯大智慧、大胸怀的自然体现。
几年前,余秋雨的散文如日中天的时候,有“好事者”从中找出许多文史知识的“硬伤”来。
《咬文嚼字》杂志的资深编委金文明甚至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三本散文集中的错误集中阐释,出版了一本20万字著作,书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
诸如吕洞宾不是道家始祖,娥皇、女英不是舜的女儿,莫高窟不是建在沙漠之中等等,足有130多处。
面对这样的质疑,余秋雨的应对很大气。
之前他已经就此发表过一封《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
“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
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而对金文明先生就事论事的纯学术的商榷,他又表示,金先生的书,大家读了也是有益的。
一晃数年,尽管这些“硬伤”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余秋雨的书依然占据着各大书店的显著位置,余秋雨的散文对一代又一代青年来说,已经是极具余秋雨个人风格的经典作品。
这正应了那句经典的话:
瑕不掩瑜。
我和马兰的婚姻也是经典
王菲离婚了,汪峰离婚了……一个个爱情童话的破灭让人扼腕叹息。
我不是热衷于小道消息的狗仔队,对公众人物的绯闻八卦不甚关心,第一次采访余秋雨,对是否触及这一话题心存疑虑,毕竟,余秋雨和马兰夫妇这几年深受此类谣言困扰,就在今年4月,微博还在热炒他们即将离婚的消息。
但是,婚恋对于青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懂爱,不信爱,不会爱等现象十分普遍。
既然难得地和这样一位大家谈论青年,错过这个话题也十分可惜。
而余秋雨看我如此犹豫,却大大方方地说,我可以谈一下我和马兰,我认为,我们的婚姻也是经典。
余秋雨的夫人马兰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她13岁考入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工作第二年就主演了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
1989年,马兰凭借电视剧《严凤英》,一跃成为中国最知名的黄梅戏演员。
如今的黄梅戏观众,一说起《女驸马》《红楼梦》等代表剧目,无一不在第一时间想到,这是“马兰的戏”。
马兰和余秋雨相识是缘于他的一本书。
当时,初出名的马兰正陷入生活与艺术的双重困惑。
这时,一位她素来敬重的老师送给她一本《艺术创造工程》,还很严肃地介绍说:
“艺术工作者一定要读读这本书。
”也许是出于好奇,马兰一页一页认真地读,竟豁然开朗地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难题。
掩卷之余,她不禁对“余秋雨”这个作者顺带地好奇起来——他一定是一位阅历丰富、满头白发,带着点学究气的老先生吧。
所以,当1991年二人第一次见面时,马兰多少有些吃了一惊,面前的余秋雨虽然书卷气十足,却绝无学究气,年龄也比想象当中年轻得多,40出头,正值壮年。
二人的相恋也不复杂。
几次接触之后,心灵的高度契合使双方都十分珍视这段难得的缘。
终于有一天,余秋雨突然对马兰说:
“我觉得,你做我的老婆挺好的。
”马兰立即回了一句:
“我觉得呀,你做我的老公也不错。
”
这段婚姻起初并不受人祝福,16岁的年龄差距在当时很有些“石破天惊”。
甚至20年后,还有人捕风捉影地对他们进行攻击。
余秋雨夫妇却不受任何影响。
他们经常手拉手去菜市场买菜,共同看望双方父母,请朋友吃饭。
闲暇时,两人就在家中一起观看外国戏剧表演录像,或者互不干扰地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
他们还经常互相吹捧,马兰会说:
“余老师,我喜欢你的书。
”余秋雨则说:
“马老师,我喜欢你的戏。
”8月底的第二次采访,马兰也恰好来京,二人相携而行,寸步不离。
我上前致意时,余秋雨很自然地伸手介绍说:
“这是我的夫人马兰。
”那份和谐让人动容,倘若那些编造谣言的人在场,一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关于这次选择,余秋雨也归因于岁月带来的心智成熟。
他说,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
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
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
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
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人的一生,“唯一”的选择并不多,因为其难得,才更显其珍贵。
余秋雨本已豁达地做好了“无法实现”的心理准备,而上苍却执意给了他这桩注定的姻缘。
这样的婚姻,怎么能不是经典呢。
马兰曾对他们“老少配”的婚姻做过一个精辟的总结:
“我们的婚姻就如同红木家具,越老越有价。
”此次采访,余秋雨的一句话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他说: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哪段婚姻能比我和马兰更幸福。
”感谢阅读,希望能帮助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