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docx
《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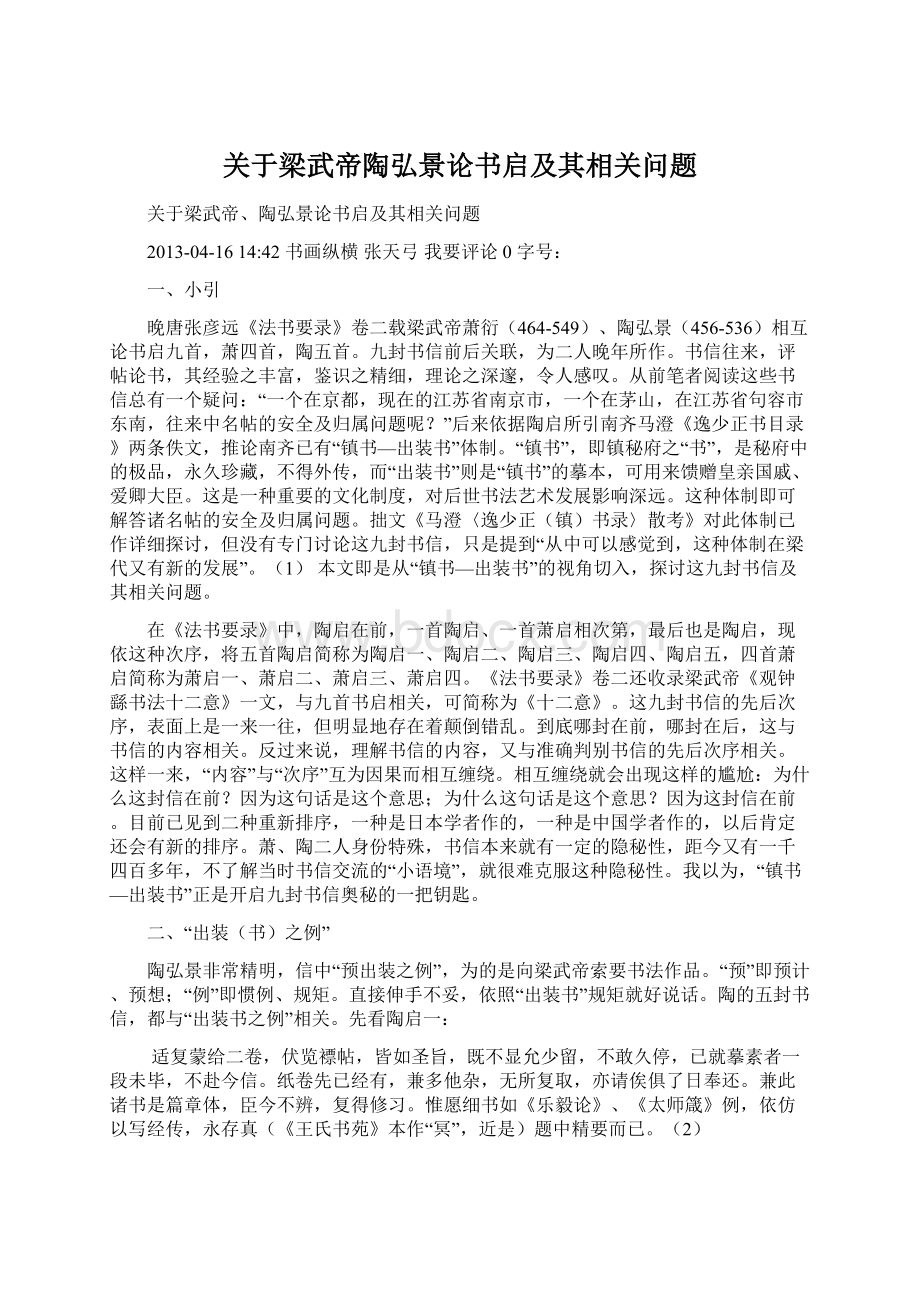
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
关于梁武帝、陶弘景论书启及其相关问题
2013-04-1614:
42书画纵横张天弓我要评论0字号:
一、小引
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载梁武帝萧衍(464-549)、陶弘景(456-536)相互论书启九首,萧四首,陶五首。
九封书信前后关联,为二人晚年所作。
书信往来,评帖论书,其经验之丰富,鉴识之精细,理论之深邃,令人感叹。
从前笔者阅读这些书信总有一个疑问:
“一个在京都,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在茅山,在江苏省句容市东南,往来中名帖的安全及归属问题呢?
”后来依据陶启所引南齐马澄《逸少正书目录》两条佚文,推论南齐已有“镇书—出装书”体制。
“镇书”,即镇秘府之“书”,是秘府中的极品,永久珍藏,不得外传,而“出装书”则是“镇书”的摹本,可用来馈赠皇亲国戚、爱卿大臣。
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制度,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
这种体制即可解答诸名帖的安全及归属问题。
拙文《马澄〈逸少正(镇)书录〉散考》对此体制已作详细探讨,但没有专门讨论这九封书信,只是提到“从中可以感觉到,这种体制在梁代又有新的发展”。
(1)本文即是从“镇书—出装书”的视角切入,探讨这九封书信及其相关问题。
在《法书要录》中,陶启在前,一首陶启、一首萧启相次第,最后也是陶启,现依这种次序,将五首陶启简称为陶启一、陶启二、陶启三、陶启四、陶启五,四首萧启简称为萧启一、萧启二、萧启三、萧启四。
《法书要录》卷二还收录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一文,与九首书启相关,可简称为《十二意》。
这九封书信的先后次序,表面上是一来一往,但明显地存在着颠倒错乱。
到底哪封在前,哪封在后,这与书信的内容相关。
反过来说,理解书信的内容,又与准确判别书信的先后次序相关。
这样一来,“内容”与“次序”互为因果而相互缠绕。
相互缠绕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
为什么这封信在前?
因为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封信在前。
目前已见到二种重新排序,一种是日本学者作的,一种是中国学者作的,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排序。
萧、陶二人身份特殊,书信本来就有一定的隐秘性,距今又有一千四百多年,不了解当时书信交流的“小语境”,就很难克服这种隐秘性。
我以为,“镇书—出装书”正是开启九封书信奥秘的一把钥匙。
二、“出装(书)之例”
陶弘景非常精明,信中“预出装之例”,为的是向梁武帝索要书法作品。
“预”即预计、预想;“例”即惯例、规矩。
直接伸手不妥,依照“出装书”规矩就好说话。
陶的五封书信,都与“出装书之例”相关。
先看陶启一:
适复蒙给二卷,伏览褾帖,皆如圣旨,既不显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毕,不赴今信。
纸卷先已经有,兼多他杂,无所复取,亦请俟俱了日奉还。
兼此诸书是篇章体,臣今不辨,复得修习。
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永存真(《王氏书苑》本作“冥”,近是)题中精要而已。
(2)
这是收到梁武帝“复给二卷”后的回信;前给二卷,没有回复,又给二卷,此一并回复。
后二卷,梁武帝没有明确表态,“不显允少留”,“少留”即留一段时间,陶启一说不敢久留,赶紧摹写而一段未成,不能随此信奉还。
前二卷是“纸卷”,现在也不能随信奉还,请允许“俱了”后奉还。
总之,一共收到四卷,以后再奉还。
萧启一是回信,对如何处理四卷表了态:
后二卷可以“少留”,前二卷“纸卷”,“是出装书,既须见,前所以付耳,无正,可取备于此”。
“正”,是指正本、原本,作为“镇书”藏之秘府。
不能看到正本,有摹本“出装书”就行了。
言下之意,“出装书”可以留存,不必送还了。
耐人寻味的是,陶明知前二卷是摹本,正本在府库,也知道南齐以来“镇出一出装书”制度,但不称“摹本”,也不及“出装书”,而是称“纸卷”。
我想,陶当然想留存下来,对朝庭(廷)来说多制作一套摹本并非难事,但他心中无底,只好赶紧摹写,制作摹本的摹本,等“俱了”后奉还。
梁武帝回信对“纸卷”定了性,“是出装书”,这对陶隐居来说确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恩赐。
有了皇上的恩准,陶以后就可以“预出装之例”。
这可以作为判别陶启先后次序的一条重要的线索。
顺便说明一点,陶启透露出一条重要的信息,凡“出装书”均为纸卷。
陶启二是收到萧启一的回信。
开篇说同意萧启一结尾以为《乐毅论》“恐非真迹”的观点。
接下来,陶写道:
许静素段,遂蒙永给,仰铭矜奖,益无喻心。
此书虽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间细楷,兼复两玩。
先于都下偶得飞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尝别见,无以能辨,惟觉势力惊绝,谨以上呈。
于臣非用,脱可充阁,愿仍以奉上。
臣昔于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录》一卷。
澄云:
“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余首,皆作今体,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细。
”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
澄又云:
“帖注出装者,皆拟赉诸王及朝士。
”臣近见三卷,首帖亦谓久已分,本不敢议此,正复希于三卷中一两条更得预出装之例耳,天旨遂复顿给完卷,下情益深悚息。
近初见卷题云“第二十三、四”,以欣其多,今者赐书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惊讶无已。
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
前后都已蒙见大小五卷,于野拙之分,实已过幸;若非殊恩,岂可觖望。
此段比较复杂,又相当重要,拟一一解说。
(1)永给“许静素段”。
“素”,未染色之丝织物,“素段”当是指原作。
许静,不详生卒年,唐·李嗣真《后书品》“中中品十二人”中有其名,与“谢安”、“康昕”等人同列,又称“宗炳放逸屈慑,颇效康、许”,(3)可推知许静约是东晋时书家。
此素段两面有书,背面是“细楷”,既非纸卷“出装书”,又非“镇书”,陶说“不在法例”,“遂蒙永给”。
为何永给?
陶启一曾向梁武帝请求,“惟愿细书如《乐毅论》、《太师箴》例,依仿以写经传”,萧启一回复说,前者“恐非真迹”,后者“书体乖异”,言下之意是说不必制作摹本,但永给许静“细楷”素段,即是作为一种替补。
这一点对于解说仿写道经之事很重要,下文还会涉及。
(2)礼尚往来,奉上王羲之飞白一卷“充阁”,作为永给许静素段的回报。
此飞白一卷先前得于京都,恐是在南齐,人称是“好迹”,此奉上“充阁”。
“阁”即秘阁,宝藏“镇书”之所。
“充阁”,意思是列为“镇书”收藏在秘阁。
陶启很讲礼仪,先说“上呈”,再说“奉上”。
“上呈”是说此飞白好迹已随信送来,请鉴赏。
鉴赏完了如何处置?
可以“充阁”,自已“愿仍以奉上”,也就是捐赠。
能否“充阁”,请梁武帝定夺,这恐是“镇书”制度的规矩。
结果如何,未见下文,我想,梁武帝不会拒绝陶的美意。
(3)就“充阁”之请,陶回忆起马澄,引用《逸少正书目录》两条佚文。
此“正”恐传抄中讹误,原为“镇”,音近而误。
笔者已作考证,现再补充三条理由。
其一,回忆之前讲“充阁”,即是讲“镇书”。
其二,陶引用佚文有“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紧密”云云,其《急就篇》为章草,(4)非“正书”,但可作为“镇书”。
其三,萧启一关于“纸卷是出装书”的表态在先,陶这才追忆起《逸少正书目录》,而“出装书”与“镇书”相关。
这里引用其佚文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重温旧谊,“近脱忆此语”仅只两条,一卷目录中的两条,“当是零落”,原目录“已不复存”,马澄也不复存。
睹物思人,人之常情。
南齐永明五年,萧衍任南郡王文学,马澄任南郡王侍书,当然有交情,陶说“已不复存”,可谓意味深长。
二是明确“出装书之例”。
其佚文说:
“帖注出装者,皆拟赉诸王及朝士。
”这是南齐以来“出装书”的规矩,馈赠范围是“诸王及朝士”,“出装书”上还要注明馈赠对象。
由此可明白陶弘景为什么此前对二卷摹本心中无底,只能称“纸卷”;他是隐逸,不是朝士。
再者,陶启下文说“预书装之例”可得“三卷中一两条”,“一两条”即一两件书作,据陶启三所记,一卷有十余条、二十余条不等,可知老规矩没有出装整卷的。
陶现在明确这些“出装(书)之例”,是为了表示深感梁武帝的“殊恩”,让自已享受朝士待遇,还出装整卷。
所以陶隐居接下来表态,“愿作主书令史”,还以为在山中作“顽仙”,不如在朝中作“才鬼”。
陶当然不可能出山,但表一下态还是需要的。
(4)给书“五卷”。
陶这里提到三卷“出装书”,哪三卷?
梁武帝定性为“出装书”的“纸卷”有二卷,另一卷应是指“第二百七十卷”。
萧启四云:
“近有二十许首,此外字细画短,多是钟法。
今始欲令人帖装,未便得付来,月日有竟者,当遣送也。
”这二十许首王羲之书,可合为一卷,个把月内能完成“帖装”,当遣送,很可能就是指“第二百七十卷”。
萧启四应在陶启二之前。
这里说的“第二十三、四卷”是秘藏原本,恐是请陶鉴定,陶启三将此二卷原本、“疏注如别”及“窃所摹者”一并送还;《乐毅论》、《太师箴》即在此“第二十三卷”中,可知陶启一即是收到“第二十三、四卷”的回信。
陶很守规矩、讲信誉,原本哪怕不是“镇书”,未经恩准,也不私自摹写留存。
三卷“出装书”与此二卷原本,即陶所谓“蒙见大小五卷”。
“蒙见”一词用得很别致,为了突出“五卷”之多,不管是留存的还是不能留存的,都算一饱眼福。
在此书信往来期间,梁武帝遣送给陶弘景的书作,除单帖外,一共五卷,三卷永给的“出装书”,二卷须送还的原本。
现在可以把“镇书一出装书”制度的新发展归纳一下:
其一,“镇书”的范围扩大。
刘宋时“镇书”只限于二王,虞龢所编《二王新装镇书定目》是大王六卷,小王六卷。
南齐·马澄编的镇书目录只是大王一卷,很可能没有小王。
梁武帝时代肯定不限于大王,至少要包括钟繇,还应有张芝。
其二,“出装书”馈赠的范围扩大,南齐是“诸王及朝士”,梁武帝扩大到隐逸。
其三,制作“出装书”由原来的单帖扩大到整卷。
其四,确定“镇书”范围及“出装书”馈赠对象,在宋齐恐非完全由皇上钦定,而梁武帝是行家,又研究书学,很可能是由他说了算。
其五,“出装书”的范围可能比“镇书”更大,也就是说,“镇书”是秘藏中的极品,但秘藏书作不只是“镇书”,也可以制作摹本“出装书”。
陶启五即是依据“出装之例”索要阮研书作的摹本,阮研恐怕很难被纳入“镇书”。
此外,“镇书”、“出装书”上的“褾题”、“签署”可能也有一些变化。
三、九封书信的先后次序
陶弘景五封书信的先后,可以“预出装之例”为尺度,索要作品而未明言“出装书”者,在陶启一说“纸卷”之前,明言“书(出)装书”者在其后。
五封之中,仅陶启四索要钟书摹本而不及“出装之例”,当在最先。
陶启三有“第二十三、四卷”的注疏,先后关系比较明确。
陶启二、陶启五都说到“出装书之例”,应在陶启一之后。
有了这样的大体定位,梁武帝的四封书信即可寻查相应的前后关系。
陶启四是收到梁武帝《十二意》摹本的回信。
全篇较长,主要说了四个问题:
(1)评述《十二意》的内容;
(2)分析《十二意》的摹本;(3)赞许三首“圣旨”的字迹;(4)讨论学习“钟法”。
萧启二是收到陶启四的回信,针对篇中所谓《十二意》及摹本、三首“圣旨”的书艺及相关书理,大讲书法理论及“运笔”。
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下文拟分别详述。
陶启四篇末说到学习钟繇时,趁机提出“冒愿得工人摹填数行”。
萧启四是答复:
“钟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但有逸少“多是钟法”的二十许首,个把月内可“帖装”完成当遣送。
萧启二、萧启四均在陶启四之后。
接着萧启二、萧启四的是陶启一。
篇中说“前奉神笔三纸,并今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画画抽心”。
陶启四已说到三首圣旨,也就是“神笔三纸”。
这里又说到二首圣旨,其一明显是指萧启二,萧启二对自已的书艺谦虚一番,陶回信便更加赞赏“字字注目”、“画画抽心”;另一旨当是指萧启四,萧启四已有缺佚,恐是遣送“第二十三、四卷”或二卷“纸卷”的书信。
陶启三是送还“第二十三、四卷”及“注疏如别”并摹本,还上呈“许先生书、任靖书”,“许先生”是许谧。
萧启三是回信,将“许、任二迹并摹者并付及”。
这也是礼尚往来,你送还原本并摹本,我也送还原本并摹本。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判别陶启三及萧启三的前后关系。
我们知道,陶启一是收到“第二十三、四卷”的回信,陶启三肯定在陶启一之后,“注疏如别”对《乐毅论》作了鉴定,即陶启二开篇所言“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陶启三肯定在陶启二之前。
萧启一说可以“少留”的“近二卷”,即是“第二十三、四卷”,这就是说还未收到此二卷,即陶启三。
陶启三的“注疏”认为《乐毅论》“非甚用意”、“颇有坏字”,不敢轻言其摹,即没有见到萧启一的鉴定“恐非真迹”。
可见在陶启一与陶启二之间有一段小插曲:
萧启一与陶启三相互不知,恐是在遣送的路途中错过了。
京都与茅山相距数百里,书信送达须费时日,萧启、陶启完全有可能同在路途中。
当时的实情可能是,收到“第二十三、四卷”后即作陶启一,请允许“少留”;又赶紧摹写,并“注疏如别”,完成后还未见到梁武帝的回信,便将原本、摹本及“注疏”一并送还了,而此时梁武帝的回信还未送到。
所以陶启三应排序在萧启一之后,陶启二之前,萧启三则在陶启二之后。
今论者将九封书信设想成一来一往,《法要要录》本的先后次序也是一陶一萧的思路。
其实,京都与茅山书信往来,有可能在途中错过,而且萧、陶二人并非是每函必复。
陶启一即是收到“复蒙给二卷”后的回复。
这很容易理解,先收到“纸卷”二卷,赶紧摹写,尚未“俱了”便延误几日,不料又收到“第二十三、四卷”,这才一并回复。
一来一往的思路,根本无法理解这九封书信,于是出现了九封书信被分割成两次讨论,两次讨论也找不到时间上的关联。
最后一封是陶启五,篇首恐有缺佚,今存本开头说王羲之早年书、“未(末)年书”、晚年代笔人及献之早年仿代笔人等等,据信中所言“今圣旨标(当为“褾”)题,足使众识顿悟,于逸少无复末年之讥”,这些说法当是“圣旨标(褾)题”。
萧的四封书信未见此“褾题”内容,当另有所出。
陶启五也说到“出装之例”,应在陶启一之后。
陶启一之后给付的羲之书作,有多是“钟法”的二十许首,前面说到当是“第二百七十卷”,永给的“出装书”,而“出装书”可作“褾题”。
陶启五所谓“圣旨标(褾)题”,很可能就出自此卷。
这里陶又在“预出装之例”,索要阮研书作摹本,为了鉴别仿阮研书者。
陶还提出了时间要求,“复蒙垂给至年末间不(同“否”)”,也就是希望在年底以前。
此事未见下文。
总之,这九封书信此(比)较连贯,萧启三篇末署“右三纸正书,二十六日至”,不及月份,可推知书信往来非常频繁,一封接一封,没有什么间隔。
这九封书信实际的先后次序,依写作时间应是:
1、陶启四,2、萧启二,3、萧启四,4、陶启一,5、萧启一,6、陶启三,7、陶启二,8、萧启三、9、陶启五。
此外,还有几封书信散逸,一开始就有五封,萧的“神笔三纸”,陶应有二封回信。
二次遣送四卷的书信,至少缺一封。
遣送“第二百七十卷”还应有一封。
收到逸少飞白一卷,是否“充阁”也未见回复。
索要阮研书摹本,也未见下文。
四、书信往来的缘起
陶启四在九封书信中为最先,开篇云:
“伏览书用(《墨池编》本作“论”,近是),前意虽止二六,而规矩必周,后字不出二百,亦褒贬大备。
一言以蔽之,便书情顿极。
”此“书论”,即是指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之文。
陶的总评是,书法艺术的情理顿时穷尽其极。
这封信是收到《十二意》之后的回复。
信中说:
“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觉劲密。
”其一旨当随《十二意》送达,此前还应有二旨,今不存。
前二旨说什么?
陶的下一封信即陶启一,篇首说到“每惟申钟、王论于天下”。
“每”是多次;“于天下”即包括茅山。
陶启一是收到萧启二的回复。
萧启二讲书理及“运笔”,未及“钟、王论”。
多次“申钟、王论”在哪里?
。
送达《十二意》并书信只一次,前二旨也应有“申钟、王论”。
既然有前二旨,也应有陶回信,今不存,估计也会谈到“钟、王论”。
萧、陶二人有数十年交谊,陶还有“山中宰相”之称,书信往来肯定不少。
除此九封之外,仅存数封,都是相敬以礼。
譬如,梁武帝请陶赴朝中为官,陶上表婉谢,梁武帝作《答陶弘景解官诏》云:
“尚想清虚,山中闲静,得性所乐,当善遂嘉志也”(5),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频繁书信往来,集中探讨书艺,依常理推测,当是梁武帝起头,先透露自已的钟、王新论,试探一下,或征询意见,在得知陶的认同后才拿出《十二意》之文。
《十二意》既是直接起因,便引导着这次集中讨论的走向。
陶启关于钟、王的评价,与《十二意》完全一致。
这有迎合梁武帝的成分,还有明显的过誉,但基本上仍是陶的真实思想。
有了“钟、王论”的契合,讨论才较为融洽,讨论才得以继续,才有了深入探究书理,才有了遣送五卷书作,赏鉴具体作品。
陶弘景收到的《十二意》之文,不是手迹,而是摹本,还存在“採字”问题,颇令人费解。
近见王家葵先生《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研究》(下简称《论书启研究》),对九封书信作专门探讨,重新编排次序,考证写作时间,解说主要内容,给人以启迪。
遗憾的是,该篇将此摹本误解成周兴嗣《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文)》(6),结果造成一系列的误读、误判,包括重编次序与考定时间。
《十二意》的摹本问题必须慎重对待。
陶启四在赞扬《十二意》的书论后写道:
今奉此论,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愿以所摹,窃示洪远、思旷。
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当赞仰踊跃,有盈半之益。
臣与洪远虽不相识,从子诩以学业往来,故因之有会。
但既在阁,恐或已应闻知。
摹者所字,採大小不甚均调,熟看乃尚可,恐竟(《书苑菁华》作“笔”,近是)意大殊;此篇方传千载,故宜令迹随名偕,老益增美。
这里是说,看了《十二意》后兴奋不已,便私下将“所摹”给洪远、思旷看。
二人是“均思”者,当有“盈半”之益,这是借用《十二意》中的说法,可明证“所摹”即是指《十二意》。
私下示人不妥,为何要明说?
洪远“在阁”,即是在朝中任职,梁武帝作为至尊,恐已知道,也应该知道此事。
既然洪远已看到摹本,替梁武帝着想,摹本的字“大小不甚均调”、“笔意大殊”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所以建议摹本的书迹应与《十二意》之文相匹配,以流传千载而长久增美。
摹本肯定不是陶所为,而是朝庭(廷)所为。
这有一个疑难,按常规摹本是依原作摹仿,当时的作法是廓填(陶启五称“比郭摹”),怎么会出现“採字”?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对于前代制作诏书的程序、形制、称谓及用纸、用绢等,都有说明,还提到属员“修补制诏匠五十人”。
(7)陶启所谓“摹者”,可能是指这种“修补制诏匠”。
另外,《法书要录》本《十二意》明显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十二意(即“字”)”,即“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每一字下有随文小字注,前无导言,后无结语,未明言何所指;另一部分是“钟、王论”,自成一体,与“十二字”毫无衔接。
这显然不是正规的文章款式,制作这样的摹本,恐怕字迹“大小不均”、“笔意大殊”的问题在所难免。
这仅是一种推测,原本到底如何无法查证。
然而清楚的是,摹本的这些问题,不宜说是摹者的问题,摹者的问题实际上是梁武帝原本的问题,聪明的说法是“採字”的问题。
说完“採字”问题后,紧接着陶就大加赞赏“三旨”的书迹,称“下情欢仰,宝奉愈至”。
陶不愧是作文高手,这一段真是写得一波三折、曲尽真(其)妙﹗
陶论摹本,提出了“迹随名(诗文)偕”说,再作申发,论“三旨”又提出了“意·言—手—笔”说,这两个理论命题都非常精湛。
梁武帝读后,不知是激发起理论思维的兴致,还是激发起不甘示弱的自尊,答启即萧启二,着重阐发书理及“运笔”。
陶启说“规矩必周”、“褒贬大备”,这还不足称道,而真正的“书情顿极”则在此萧启二。
下面将会专门讨论陶、萧二人的理论创见,这里想说明的是,《十二意》之文引出了这次书信往来讨论书法,而真正激发讨论向纵深发展的则是《十二意》的摹本问题。
当然,这种抛砖引玉,是当初梁武帝遣送摹本时所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不能准确的理解“摹本”,就无法判别哪一首萧启是答启。
《论书启研究》正是将此摹本误解为周兴嗣《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文)》,就无法解读萧启二,把萧启二中的数句当成陶弘景的“原话”,推论之前还有一首“已佚”的陶启,于是把萧启二列为九封书信之首,反而把陶启四判为萧启二的答启,正好颠倒。
(8)现将信中涉及到所谓“原话”的语句对比如下:
(1)陶启四:
一言以蔽,便书情顿极。
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进退其间,则玉科显然可观。
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永遂沦迷矣。
萧启二:
故宜当微以著赏,此既胜事,风训非嫌云云。
(2)陶启四:
知摹者所采字大小不甚均调,熟看乃可,恐笔意大殊。
此篇方传千载,故宜令迹随名偕。
萧启二:
吾少来乃至不尝画甲子,无论于篇纸,老而言之,亦复何谓。
正足见嗤于当今,贻笑于后代,遂有独冠之言,览之背热。
《论书启研究》说:
“最难判断的是萧启二,按书信的体例,‘故当宜微以著赏’云云,‘独冠’云云,均应该是陶弘景来书中的原话,但陶启一至五并未见此类语句,故梁武帝此函所答者应是陶弘景的另一封书信,而此书信已佚。
”笔者以为,“著赏”与后句“风训”相对,意思是提出“钟、王论”即“画龙画虎”之说。
“微以著赏”显然不是陶的原话,这种说法太不恭敬,而作为梁武帝的自谦倒是合情合理。
“风训”也不是陶的原话,而是陶启四中的原意,如“若非圣证品析,恐爱附近习之风”云云,意思就是“风训”。
“风训非嫌”,是说“风训”没有避嫌、避讳。
全句的第一个字“故”,应训为之所以,而“微以著赏”、“风训非嫌”云云,是梁武帝用自已的话来表达陶启四中的意思。
“独冠之言”也不是陶的原话,而是陶启四中的原意,所谓“书情顿极”、“圣证品析”云云,都是“独冠”的意思。
所以梁武帝谦虚地说,看了使我臊得背都发烧。
最明显的是,“独冠”指《十二意》的书论,与前句“见嗤”云云合观,全句正是针对陶启四所谓“宜令迹随名(文)偕”。
文则“独冠”,使人“背热”,“所摹”则“笔意大殊”,即“见嗤于当今”、“贻笑于后代”。
为何会“见嗤”、“贻笑”?
梁武帝自谦年少时没有认真习字;“画甲子”,大意为幼童一天写二十二个字,(9)“不尝画甲子”,更何论整篇整纸。
值得寻味的是,梁武帝没有诿过于“摹者”以“採字”问题相敷衍,而是自已担当,这自当是别一种境界。
隐士,也有不能免俗的时候;皇上,偶尔也有脱俗的高尚,这是历史的真实。
从这种对照中,我们能够具体地见识陶、萧二人如何围绕《十二意》之文与《十二意》之摹本展开交流、进行讨论,同时还能感受到二人的性情流露。
五、《十二意》与《古今书评》的成文先后
《法书要录》卷二收录梁袁昂《古今书评》,署“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内侍中、尚书令袁昂启”。
篇中说到“钟司徒书字十二种意”,此“钟司徒”即是钟繇,(10)这就为我们探究《十二意》的成文时间提供了重要线索。
今有论者以为《古今书评》在先,梁武帝《十二意》在后,但没有提出具体理由。
《论书启研究》则认为《十二意》在先,也没讲具体理由,只是说袁文“已提到梁武帝的十二意”,并断定《十二意》成于普通四年(523)以前。
检《古今书评》全篇,此文确是“奉敕”而作,但不详敕旨的具体内容,只知道是“遣臣评古今书”,也没明说“钟司徒书字十二种意”是敕旨的内容,或梁武帝的观点。
这样看来,二篇先后问题尚需专门探究。
(1)《古今书评》所谓“十二种意”,恐怕不是实指什么具体的十二种意。
“十二”可表示极多,是虚指。
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卷九收无名氏《歌辞二首》,其二云:
“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
“十二”与“五”相对,当是虚指,意思是极多。
此歌辞曾被后人记于梁武帝名下,不可信,大概是齐梁以前的作品。
(11)西晋·傅玄《筝赋》:
“玄(一本作“絃”)柱十二,拟十二月。
”又《琵琶赋》:
“柱有十二,配律吕也。
”(12)可知南朝时以“十二”为数极,是比拟一年十二个月,或十二音律。
袁昂所谓“十二种意”,意思是书意非常丰富。
我们知道,《古今书评》的品评方法,基本上是基于整体直观的形象比拟,“十二种意”不太可能是另一种分析性的实指,其表述还特别强调“意外殊妙,实亦多奇”。
梁武帝的“十二意”,显然是实指,“十二意”即十二个“字”,虽名为“意”,实际上是指技巧、规矩,所以陶弘景称“规矩必周”。
从认识发展过程看,当是模糊虚指在前,分析性实指在后。
(2)《古今书评》篇尾总评中提出“四贤”说:
“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
”而前文的具体评述,比较推崇钟繇,对王献之则略有贬意,如“举体施(拖)沓,殊不可耐”。
这种褒钟贬王,与梁武帝的“画龙画虎”之说也有较大差异。
“龙”指钟繇,高高在上,羲之居中,“虎”则最下,定位非常明确。
尤其是袁昂对晋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