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啊.docx
《好文章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好文章啊.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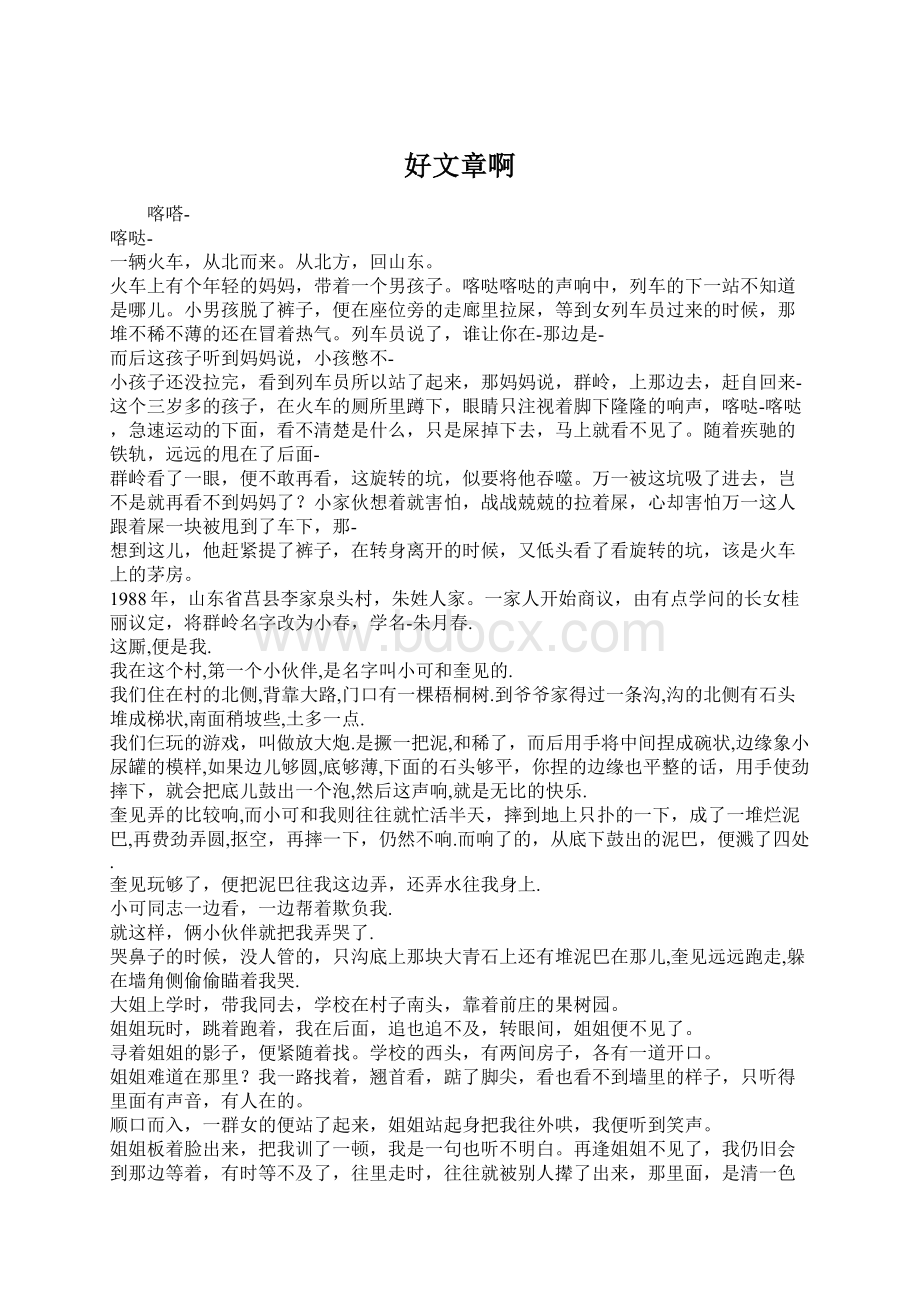
好文章啊
喀嗒-
喀哒-
一辆火车,从北而来。
从北方,回山东。
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一个男孩子。
喀哒喀哒的声响中,列车的下一站不知道是哪儿。
小男孩脱了裤子,便在座位旁的走廊里拉屎,等到女列车员过来的时候,那堆不稀不薄的还在冒着热气。
列车员说了,谁让你在-那边是-
而后这孩子听到妈妈说,小孩憋不-
小孩子还没拉完,看到列车员所以站了起来,那妈妈说,群岭,上那边去,赶自回来-
这个三岁多的孩子,在火车的厕所里蹲下,眼睛只注视着脚下隆隆的响声,喀哒-喀哒,急速运动的下面,看不清楚是什么,只是屎掉下去,马上就看不见了。
随着疾驰的铁轨,远远的甩在了后面-
群岭看了一眼,便不敢再看,这旋转的坑,似要将他吞噬。
万一被这坑吸了进去,岂不是就再看不到妈妈了?
小家伙想着就害怕,战战兢兢的拉着屎,心却害怕万一这人跟着屎一块被甩到了车下,那-
想到这儿,他赶紧提了裤子,在转身离开的时候,又低头看了看旋转的坑,该是火车上的茅房。
1988年,山东省莒县李家泉头村,朱姓人家。
一家人开始商议,由有点学问的长女桂丽议定,将群岭名字改为小春,学名-朱月春.
这厮,便是我.
我在这个村,第一个小伙伴,是名字叫小可和奎见的.
我们住在村的北侧,背靠大路,门口有一棵梧桐树.到爷爷家得过一条沟,沟的北侧有石头堆成梯状,南面稍坡些,土多一点.
我们仨玩的游戏,叫做放大炮.是撅一把泥,和稀了,而后用手将中间捏成碗状,边缘象小尿罐的模样,如果边儿够圆,底够薄,下面的石头够平,你捏的边缘也平整的话,用手使劲摔下,就会把底儿鼓出一个泡,然后这声响,就是无比的快乐.
奎见弄的比较响,而小可和我则往往就忙活半天,摔到地上只扑的一下,成了一堆烂泥巴,再费劲弄圆,抠空,再摔一下,仍然不响.而响了的,从底下鼓出的泥巴,便溅了四处.
奎见玩够了,便把泥巴往我这边弄,还弄水往我身上.
小可同志一边看,一边帮着欺负我.
就这样,俩小伙伴就把我弄哭了.
哭鼻子的时候,没人管的,只沟底上那块大青石上还有堆泥巴在那儿,奎见远远跑走,躲在墙角侧偷偷瞄着我哭.
大姐上学时,带我同去,学校在村子南头,靠着前庄的果树园。
姐姐玩时,跳着跑着,我在后面,追也追不及,转眼间,姐姐便不见了。
寻着姐姐的影子,便紧随着找。
学校的西头,有两间房子,各有一道开口。
姐姐难道在那里?
我一路找着,翘首看,踮了脚尖,看也看不到墙里的样子,只听得里面有声音,有人在的。
顺口而入,一群女的便站了起来,姐姐站起身把我往外哄,我便听到笑声。
姐姐板着脸出来,把我训了一顿,我是一句也听不明白。
再逢姐姐不见了,我仍旧会到那边等着,有时等不及了,往里走时,往往就被别人撵了出来,那里面,是清一色的小丫头片子。
姐姐常玩跳绳,两个小姑娘用环状的绳子挂到腿腕,而后一个小姑娘就在这绳子上踩,踩一根,而后跳进圈里,然后双脚叉开,再跳进去,再从另一侧跳出,再前跳,把一根绳子压到另一根上,然后从另侧翻出,再跳回原地,就算过了这关了。
接着再是膝盖,再是大腿。
碰到缺人手的时候,我能当个撑绳子的,站着不动,看她们跳上跳下。
腿一松,结果就看到她们不悦的脸色,把我又撵到了一边。
脑袋里带着这些景象,我想,我的童年,该是没有开始的。
既然没有什么叫做开始,也就无关乎细致的时间概念了。
粗略介绍下自己的村子吧。
村碑上写着,李家泉头,据传,李,王,邵等姓立村于明初,因有肖阳岭有南,中,北三泉,此村傍北泉,初名北泉;明末大水毁村后,李氏于故村西北建家园,改名李家泉头。
我们家住在家后,村子分家前,家后,家西,家东,庄里几个部分。
临村有前庄,后庄。
前庄是王家泉头,后庄是邵家泉头。
常听长辈说,前庄里,后庄里,拉屎拉面缸里。
我的活动区域,局限于家后。
有时走远了,妈便焦急的惦记着,如果没打过招呼的,就会狠命的扇我几个巴掌,看我是不是还不听话。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家东和家后搭界的地方有个小汪,围着这个五六平米的小汪住着两户人家。
一户是门口朝南的,朱义家。
一个是克亮家,毛子大娘家。
这毛子大娘,是从郯城来的,脸胖乎乎的,屁股圆圆的,皮肤很白净。
不知怎么就跟了瘸腿的克亮。
妈让我叫大爷,叫毛子大娘是二大娘。
毛子是把妈介绍到这村儿的,所以我便常到她家。
她家里有一个大枣树,结的枣数也数不清。
大娘拿了长竹竿,挥手几下,地下便哗啦哗啦的,拣都拣不完。
有几个姐姐,便一块儿拾,名字是红珍红玲素珍素玲的。
这大枣好吃,还很脆,我贪吃,嘴里咬着,两个兜里还塞的满满的。
等到妈找到我时,让我把枣留下,还满脸愠色。
大娘哈哈笑笑,声音洪亮,震的枣树又落下几个大枣来。
等不及妈转身,我从背后又拣了两个,出了门口。
碰巧有个窟窿眼的老太太从南面来,眼睛窟窿着,模样却和善。
妈就让我叫她二奶奶。
过了桥,桥东面第一户人家,是叫凤的,家里俩女孩一小子。
回了家,妈便用巴掌拍我,说我乱要人家东西,一边打,一边骂,还说我不听话。
叫我下次别拿别人东西。
我抠抠兜里的枣,已经没剩下几个了。
妈平常就上坡,锄草,苗肥。
每当回家时,便太阳快落山了。
有时带上我一块锄草,我看着天边的红云彩,吆喝妈回家回家,妈转身再锄几锄头,然后拎了我的手,抗了锄头回去。
家里一般就是哥哥姐姐放学了,妈便开始烧火作饭,然后吆喝鸡,唤唤猪,而后骂着别呼噜了,等烧开水着就烫,烫。
我有一个哥哥,叫月来。
有俩姐姐,大姐月桂,二姐月竹。
大姐大我五岁,二姐大我三岁,属鸡,哥哥属猴,大我四岁。
爸爸是开车的司机,平常很少在家,我们娘俩,娘仨,娘五个。
妈经常念叨,娘俩干啥,娘仨干啥。
我睡觉的床在里屋,一张很小的床,靠着爸妈的大床一米多远。
二姐在堂屋的东北角,比我的床大些,还挂着蚊帐。
哥和大姐,在奶奶家睡。
傍晚时候,姐姐洗完碗,然后就在煤油灯下写几个字。
妈则拿了针线玻箩,凑近了补几下我的衣服,我的裤子,经常是膝盖磨个大窟窿,然后挨完了几巴掌,还得让妈给缭几个补丁。
有的是方形的,在膝盖上。
有的是圆形的,在屁股后面,两个圆重叠在一起,然后是一圈一圈的旋转的黑线。
晚上的夜,是漆黑的,尤其是煤油灯的烟熏了一阵,然后用手摸一下芯子,凑近一看,跟夜是一样的黑。
吹灭了的灯芯,一闪一闪的,露着红的小点,然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卟的一下,让脑袋里只有那小红点,闭上眼后,是能看的见小红点的,可睁开了眼,是什么都看不见。
问几句妈,妈恩哼几句,就不答了。
我只闭了眼,还看着那细细的烟线,黑黑的,红红的,象是,象是-
有一条河,黑黑的,有几丈宽。
有一条船,灰的只有轮廓。
象是在飞,又象是丝毫不动一样。
等到我反应过来,船已飞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上面一个黑色的影子用力的摇着浆,然后只看到黑色的河,不敢再看。
那男人把我放在船上,只拼命的摇着浆。
一会他哈哈大笑好象,一会象飞的船又停下,又飞快的前进着。
我看着岸边,怎么也看不到头,虽然那岸边我再伸长点胳膊就够到了。
可是够不着,只能看着黑色的旋涡,就那么看着。
妈不见了。
妈被人抢走了。
我也没见到爸爸,我也不知道爸爸是谁。
妈,爸,哪儿,你在哪儿-
黑色的旋涡仍在旋转,一丝明晃映入眼帘,黑亮黑亮的,又倏忽不见。
我和哥又躲到了一个螺旋的楼梯底里,象是田螺一样的蜗旋,在里层,转一圈,又一圈。
哥拉了我的手,好象又没拉。
好象说,别说话,咱妈被人家抢走了,咱们不说话,等等瞄着,看看呆哪-
一会我又落到那张筏子上,黑的仍不透底,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是黑影子的轮廓,还有黑色的河,黑色的旋涡,我自己就在这旋涡的上面,就在这旋涡的上面..
吃完饭,我的任务就是玩,玩什么,自己全然不知道。
去和姐姐上学,姐姐不领了,告状说是我老是往女茅房里跑。
我想说我是看你不见了找你,可是我又没说。
我看着哥哥姐姐上学去了,我一个人在家里,也不知道干些什么。
幸好妈给了我一个大苹果,那是在他们都上学走了之后的。
哭,我自然不哭的,总免不了调皮一番,惹妈打一顿,眼泪没崩出来,又去造孽去了。
秋天来了,冬天又来。
虽然梦里经常的出现那个黑色的旋涡,我也没告诉妈,虽然我害怕,虽然有时也出现自己在一个小篱笆里面,然后看着苞米,看着一个老太太,然后等到妈看不到时偷偷跑到雪里面打雪洞,那在雪洞里的样子-
可是那个老太太并不是我现在的奶奶啊,那她是谁啊?
那帐子也在这里看不到,又是哪里的帐子啊?
那雪洞,是去年打过的么,怎么都忘了似的?
我老疑惑这些事,可又不敢问妈妈,也不敢把别人把她抢走了的事和她说,成日里我提心吊胆的,不过给我一个大苹果吃我就好了。
过节的时候,我戴上了大盖帽,特别威风。
只是有时候经常被大盖帽戳到鼻子,可是我还是很愿意带它。
只是有时我想带,妈便把它放的高高的,我怎么伸手都拿不到。
春节我给谁磕头了啊,得仔细数数看。
大娘大爷,三婶子三叔,还有爷爷奶奶,大婶子大叔,还有四奶奶,一大堆的人,我数都数不过来。
有人给我压岁钱,几毛的都有,我拿给妈妈,兜里又变的空空的了。
村东头有个开合作社的,里面卖东西,妈说是大圣开的。
于是大爷家的二姐便经常买瓜种,大家一块吃。
两毛钱一包,几个人的兜里都可以装的满满的,可以吃上一个下午。
可惜我是没有份的,我凑在里面,拿几个瓜子,然后跟着跑,有时跑丢了,就去找爸爸。
爸在屋子里打扑克,还有学礼克华谁的。
妈曾说叫克华大叔,我便叫过了。
大叔穿的很整齐,兜里掏出一把黑色的东西来。
那一个个的象瓜子的东西真香,满屋子的烟也抵不过这瓜子的香味。
我咽了咽唾沫,看着左面大叔右面爸爸打着的牌。
我坐在板凳上,眼里看着大叔的手,一捏扑克,然后又拿了黑色的香喷喷的东西往嘴里一扔,然后一磕,再把皮吐到地上。
我又咽了咽唾沫,看着大叔。
大叔还是穿的很干净,都打了好多把了,地上的瓜子皮已经一堆了。
桌子上也是瓜子皮,他掏了一把,然后一个一个的磕着,然后又吐到地上。
我看着他用手剥,又看着他用嘴磕,心里馋的不是个滋味。
我看着他,看着他,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样子。
他为什么不给我两个呢?
我拣起地上的瓜子皮,黑色的有点油亮,中间一道开口,里面是黄色的,象是土的颜色。
另一面有点土,不过我已经捏着送到嘴唇,甜甜的皮,上面有点甜,有点咸滋滋儿的。
我咬了下嘴唇,口水已经又咽了一大口,皮下面的土有点干的味道,面面的,没啥味了。
我舔着这瓜子皮儿,口水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
正好大叔又往口袋里掏了一把,漏出一个来。
可是我眼睛巴巴的看着他给了别人,我满眼地上找,也看不到那个瓜子跑到哪里去了。
瓜子皮上的土,有的湿了的,到了嘴里不是个味。
我忍不住把手伸向了大叔的口袋旁,正在往里摸时,大叔一把打了我的手。
我便含着嘴里的瓜子皮儿,哭咽着,还不能哭大声,让瓜子皮梗在了喉咙,干涩的,没了味道。
这个地方究竟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妈在这里,所以我在这里,我想。
好在时间不会给一个孩子太多多余的思考。
未知的世界总等着孩子去探索,许多的未知需要开发,自己的事,便渐渐的落空了。
七叔结婚了。
七叔是四爷爷家的第七个儿子,跟爸学开过开车。
他家在桥头上,门口朝南,在路西侧。
先是鞭炮齐鸣,然后新媳妇过门,满门上都是红对子红纸,还有大门屋檐顶上一个红纸围起来的方盒子。
我们一群孩子和大娘婶子们,就看着红红的蜡烛,和红衣服的新媳妇,然后等着七叔把手往布袋一掏-
哗啦啦,大家便都弯了腰抢喜糖。
七叔撒了三四把,就不撒了。
小可说他拣了两块,奎见说拣了几个果子,三婶子抢了几个红的,还有红的糖。
我弯腰慢,只拣了一个红果子,上面染着玫瑰红。
我正在地下找着呢,看看有没漏下别人没捡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的,大家一阵子往堂屋里面跑,差点把我绊倒了给。
一边往布袋里塞那个花生,手还攥着怕挤了出来,还得跟着大家向里挤,有人说了,抢栗子枣啦-抢栗子枣咯-
等到我开始翻被角时,奎见已经跑到另一个角上了,我这个地方刚被三婶子拽过。
我又抠了下,上面还有几个零星的栗子,干瘪的。
我又跑到另一侧,掀了上面掀下面,看到红线都已经被拽断了,枣和栗子早让别人给抢去了。
我低头往外走,看到门后里有一个,红枣,也是瘪的,可能是别人拽急了跳到这儿的。
咬了一口枣,干干的,不过越细细嚼味道还不错,有点甜。
连象钉子的枣核我也嚼了好几遍,才舍得吐出来。
回了家,和妈说,看,我抢了几个栗子。
喃喃,糖也没抢着-
妈问我,看你七婶子了么-
我哪里注意到新媳子了?
她不是坐在红蜡烛旁,盖着红头巾么。
看了,我说。
可是我的七婶子长什么模样,我倒真说不上来。
反正是个女的,穿着红衣服,顶着红头巾。
晚上,七叔点上嘎丝灯,把夜里照的贼亮。
不过我就呆了一小会,就趁着有点光,回家睡觉了。
那嘎丝的味道,真的不很好闻,就象是臭了的鸡蛋刚刚打碎的味道。
89年,这是个值得记忆的时间。
因为我上学啦。
不用再成天跟着姐姐们,也不用再天天玩泥巴了。
学校还是那个。
我读育红班。
老师叫李俊娜,个头挺高的,不过她没有王顺莲漂亮,也没有王顺莲教的好,还有,她不太经常笑。
可是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第一个小学老师。
她会教我们A,O,E/
于是我就开始学习这拼音,然后学数数。
老师第一堂课问了,你们谁可以数到一百啊?
有的起立答了,数到五十七就数错了,还有的才数到四十几。
还有的连十都数不到。
可是我能数到一百啊,我能数到一百好几呢。
我想,老师你快提问我吧,我能数出来啊。
老师叫了四五个同学数后,就没再叫,然后就开始上数学课,从一开始,数到十。
我们班的同学有很多,粗略数下,有二十个吧。
有班长朱淑国,学习委员王晓艳,副学习委员李俊彩,活动委员朱月升,还有朱经理,朱克习,王凡明,朱立军,王祥宾,朱月宾,朱淑臣,朱月东,朱月成,朱月军,朱月珍,朱月秀,朱桂敏,朱永玲,朱军梅,朱桂艳,李海艳,王祥丽,朱云云,张西芬,张庆荣,大莲莲,大瞪眼。
不过我记的很快,他们家住在哪里我都知道,虽然我没去过。
上学了,床便分的更远,我的小床又向里挪了挪。
秋天的时候,要地震。
于是大家要穿红的,挂红绳在手脖子上。
挂完了红绳后,大家都把床加固了。
我呢,就不同了,把我的小床安到了天井里,一个白蚊帐,然后两根棍子撑着,晚上我就独自在天井里睡着。
我睡觉的时候,什么就都不知道了。
只知道醒来后天就是亮的了,如是三四天。
可是为什么姐姐们不在外面睡呢?
爸妈为什么也不在外面睡?
就我一个人,在天井里面睡,还有蛐蛐叫,还有走路的声音,还有狗叫。
堂屋里的地是一边是水泥的,亮堂堂的,一面是土的,使劲一跺脚,就能起一阵土。
天井的一小半是水泥的,靠近堂屋。
从锅屋到羊沟口,便都是泥。
找个大钉子,然后划一道直线,哥要一头,我要一头,开始用铁钉钉眼,钉了眼的地方,从自己的那点划线,然后另一个人要跟着划,俩人划成一个个圈状,谁先用圈把谁包围住,然后正好再甩一下钉子,钉到自己的线上,那么就算赢了。
通常我们分不出谁赢来,只是哥哥划的圈把我的套住了,我在甩向外面的钉子眼里划线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他的线,我不得不多甩几次钉子,才能逃出他设的机关。
有时甩的太用力了,手都会碰到地上,一阵生疼。
再有划线划狠了,会带出蚯蚓来,蚯蚓向上推起一小段泥巴,然后又钻了进去。
等到俩人玩够了,就把地上一堆堆的蚯蚓粪便捡起来,有时抬起来,正好有蚯蚓在里面,腾的就缩回头去,让我一个人看着长长的孔发呆。
刨花生,晒地瓜,好象秋天的农活,总也干不完。
我一起上坡时,看着嫣红的晚霞,听着嚓嚓的锼地瓜的声音,便在地头蹲着,啃地瓜。
八号地瓜是大多长条的,细,不过皮是玫瑰红,里面白似乳汁,甘甜。
5号地瓜则是圆个的多,胖,皮是一般的褐色的红,里面发黄,味道面。
我想拿锼子锼地瓜,妈不让,吆喝着让我搁下,主要是担心把我手给割伤了。
于是我就摆地瓜皮子。
妈把地瓜秧全部拔完,爸开始用镢头刨地瓜,然后姐姐和妈用锼子锼地瓜,把地瓜锼成薄片,然后大家把地瓜皮子摆到地上,一个一个的摆好,不能压箩,不能叠到一块儿,不然就会烂掉说是。
我摆了三四箩就摆够了,于是就挨顿骂,然后自己顾自己的玩。
如是几次,我便从挨打,到没饭吃。
甩花生我不干,摆地瓜皮子也不行,我就扶着家后的树,一个人哭。
哭到累的时候,也没人管我。
爸妈不让我回家吃饭。
我哭着,有时就一个人抽泣。
大叔和大婶子从北面的后大路上来,就问我为什么哭,然后大婶子便把我拎到她家,和奎见月珍一个桌子上吃饭,喝个稀粥。
不到七点,妈便找到大婶子家,把我拎回家,路上还不忘数落着。
你看看你,也不干活,X你娘的,你这个什么东西!
你看看人家奎见,给家里干多少活啊,你再看看你,死懒不动弹-
我在黑夜里,挨着骂,然后在自己的小床上,独自睡去。
我的第一个女伙伴,是朱桂艳。
她小名叫小罗罗,长的有点龅牙,不过我并不讨厌她。
我俩经常在一起写作业,然后这个怎么写,那个怎么做。
有时她家没人在家,我家也没人在家,我们俩就在梧桐边上,你一块石头,我一块石头写作业。
我跪在左面,她跪在东边。
我们经常编顺口溜,说这个那个的。
我也琢磨了半天,给小罗罗物色了一个好的,叫朱桂艳,大白蛋。
可是我始终没叫过。
她却经常叫我小臭椿,我也并不觉得难堪。
可是后来她不来我家了,也不到梧桐边写作业了。
不知道她心里是不是知道了我想的。
班长金涛在班里很厉害,经常代替老师布置作业,我们都很怕他。
当然,他的后面也跟了不少人,月升,月宾等。
大家经常问我,名字叫什么。
当然,他们指的是小名。
我便不回答。
于是这更激起了大家的求知欲望。
老八长的很高,也过来问我。
然后其他的人,也追着到茅房里问。
唉,我经不住这么多人的问话。
金涛又来问我,我只好说,你可别和别人说啊,金涛答应了。
在那棵槐树底下,我说,我那个小名叫群岭。
金涛跑走了。
一会老八又问起,这个凡明,个头高大,是班里顶高的人,这会又问我,我该怎么办啊。
老八说,你光和我说,我不和别人道。
那好吧,我点头,然后和他说,群岭。
我并不希望自己所有的事都被别人知道。
可是,有些事,由不得你做主。
还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守信用,比如老八,比如金涛。
当班里大部分人都知道我的小名是什么时,我仿佛是个老鼠,注定要钻窟窿。
可是地洞却没寻到,只是在人群中四目圆睁。
好在六一来的真快。
一年的时间,就象是跳绳一样。
拾完了石头疙瘩,跳完了绳子,就到了六一儿童节了。
海艳和我搭档唱儿歌,本来是预定好了的节目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王老师不排练我们了。
我们只看着经理晓艳月升他们,唱着歌,跳着舞。
学校里又来了个新老师,穿着一身绿衣服,说是大队书记的儿子,叫朱军礼。
王老师经常和她说说笑笑的。
六一节真的快要来了。
不由得我们盼望了半年,它还是很准时的来了。
就是明天,不是吗?
晚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大问题。
我没有红领巾。
家里翻遍了,也找不出多余的红领巾来。
哥哥姐姐们都有,独我没有。
我不由得哭泣起来。
越哭越委屈,不知如何是好。
难道明天不能参加么?
别人都有红领巾,为什么我没有?
本来平日里要睡觉的时候,一家人还在为红领巾折腾着。
妈领着我,打着手电筒,和姐姐一起,到凤家的南面,克亮的哥哥克明家。
大爷不在家,大娘在家正准备睡觉。
克明有三个孩子,两儿子。
大的叫大兵子,小的叫小兵子。
女儿叫红艳艳。
大兵子哥哥长的漂亮俊俏,小兵子哥哥却歪着嘴,鼻子塌陷,人家都叫他趴鼻子。
可是这个小兵子哥哥,给了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红领巾。
我第一条红领巾,便是这条。
早晨天没亮,我便到了学校。
一夜的盼望,就是为了这个早晨。
学校里来的人不多,只有中间的那个门亮着灯。
我进去了,一面搓着手。
这是庄老师的房间。
庄老师岁数很大了,胡子都有白的,我们经常找他在作业本上写名字。
他会歪着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朱月春。
于是他就郑重的,一笔一画的在本子上写上我的名字。
姓名,班级。
他的字,比我们写的好多了,就象是神仙写的那样。
我们不知道他教了多少年级,也不知道他在这儿多久了。
反正从我上学,他就在这儿,我想。
他住在学校里,这会看着我,用他的大手拉了我的小手,问我,你来这么早啊。
我答应着,一边呵着气。
我想啊,他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呢?
我一定会象他给我的新本子写名字时那样跟他说,我叫朱月春。
他没再多问,从里面拿出一袋子饼干。
这种包装我见过,可是我从未吃过。
我不要,老师非塞到我的手里。
我就拎着这袋子饼干,看了整场的节目。
只是里面没有我。
散场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顺路走着走着。
走过那道岭,再过了那个坡。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走到姥姥家了。
姥姥显然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过来,然后问我从哪来,和妈说了没有。
我从刘官庄大礼堂来的,我说。
我并不知道,一路上走着,到姥姥家已是下午了。
我肚子饿的慌,幸亏有老爷爷给的那包饼干。
这是第一次收到老师馈赠的东西。
而且我想庄老师或许并不知道我是谁。
姥姥开始煮小米粥,三舅在家,然后看着我。
等到黄昏时分,姥姥家的小屋子已经没有多余的光线了。
油灯下,三舅班驳的脸我已经看不分明。
只是肚子实在饿的慌。
用红色的小塑料碗,盛了小米给我,黄澄澄的,还泛着光。
我喝着粥,而后吃着煮熟了的鸡蛋。
等到我喝了两碗粥,吃了八个鸡蛋的时候。
我坐在椅子上,头向天上看着,脖子顶到了椅子的上缘,我想说,喝水,喝水。
可是我说不出,头只能仰着,看着那根黑木头,还有上面的一排排苇子。
三舅不知道在干什么,我想转头也转不动,看不到他,看不到姥姥,也看不到自己吃饭的小碗,更不知道水在什么地方。
等到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金子有一筐头的时候,姥姥问我吃饱了么,我只是答不上来。
这会子三舅急了,把我从椅子上抱起来就往医院跑。
我是想说啊,三舅你给我点水喝,可是我说不出,倒是跑的时候,我觉得喉咙里好受了些。
村里的医生看了我,给我冲了点白开水,立刻我就好了。
我让鸡蛋黄给噎住了。
妈把我接到泉头里,已经是第几天了。
自然免不了顿训话,主要以骂为主,巴掌为辅。
内容是,以后不和妈说,便去不得任何地方。
哪里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