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绿色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docx
《激情燃烧的绿色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激情燃烧的绿色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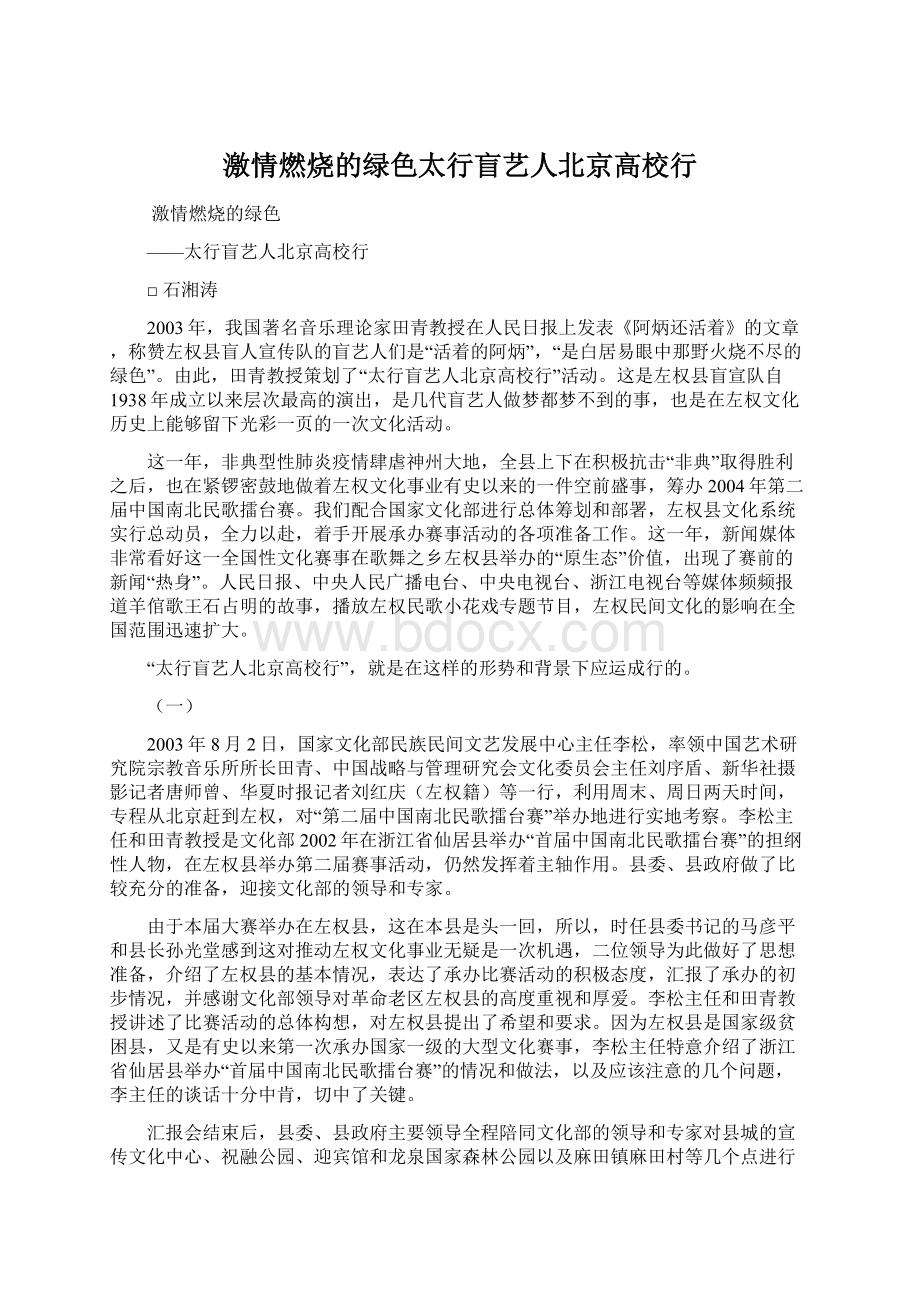
激情燃烧的绿色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
激情燃烧的绿色
——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
□石湘涛
2003年,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田青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阿炳还活着》的文章,称赞左权县盲人宣传队的盲艺人们是“活着的阿炳”,“是白居易眼中那野火烧不尽的绿色”。
由此,田青教授策划了“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活动。
这是左权县盲宣队自1938年成立以来层次最高的演出,是几代盲艺人做梦都梦不到的事,也是在左权文化历史上能够留下光彩一页的一次文化活动。
这一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全县上下在积极抗击“非典”取得胜利之后,也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左权文化事业有史以来的一件空前盛事,筹办2004年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
我们配合国家文化部进行总体筹划和部署,左权县文化系统实行总动员,全力以赴,着手开展承办赛事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一年,新闻媒体非常看好这一全国性文化赛事在歌舞之乡左权县举办的“原生态”价值,出现了赛前的新闻“热身”。
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等媒体频频报道羊倌歌王石占明的故事,播放左权民歌小花戏专题节目,左权民间文化的影响在全国范围迅速扩大。
“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应运成行的。
(一)
2003年8月2日,国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率领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音乐所所长田青、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委员会主任刘序盾、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华夏时报记者刘红庆(左权籍)等一行,利用周末、周日两天时间,专程从北京赶到左权,对“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举办地进行实地考察。
李松主任和田青教授是文化部2002年在浙江省仙居县举办“首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的担纲性人物,在左权县举办第二届赛事活动,仍然发挥着主轴作用。
县委、县政府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迎接文化部的领导和专家。
由于本届大赛举办在左权县,这在本县是头一回,所以,时任县委书记的马彦平和县长孙光堂感到这对推动左权文化事业无疑是一次机遇,二位领导为此做好了思想准备,介绍了左权县的基本情况,表达了承办比赛活动的积极态度,汇报了承办的初步情况,并感谢文化部领导对革命老区左权县的高度重视和厚爱。
李松主任和田青教授讲述了比赛活动的总体构想,对左权县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因为左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承办国家一级的大型文化赛事,李松主任特意介绍了浙江省仙居县举办“首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的情况和做法,以及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李主任的谈话十分中肯,切中了关键。
汇报会结束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全程陪同文化部的领导和专家对县城的宣传文化中心、祝融公园、迎宾馆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以及麻田镇麻田村等几个点进行考察参观。
期间,我们还安排左权县小花戏艺术团和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艺术团做了两场演出。
还利用早晨时间,陪同到祝融公园广场和宣传文化中心门前广场,感受群众自发表演文艺节目的浓厚气氛,以便尽可能地给文化部的领导和专家多留点美好的印象。
8月3日,太阳落山时分,我们陪同北京客人在从麻田返回县城的途中,刘红庆对我说:
“看了两场明眼人的演出(指左权县小花戏艺术团和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艺术团),节目都一般,专家们看后留不下多少印象。
”因为都是左权老乡,彼此对保护传承民间传统文化又有相近的观点和志趣,他没有遮掩拐弯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接着,他和我商量,“能不能让左权盲宣队给北京专家演出一场?
”我当即就说,没有什么不行。
只是担心事先没有一点准备,让盲艺人临时上场,效果好不了,怕交待不了北京专家。
刘红庆不以为然,说,“反正是盲艺人的演出,他们唱得有味,有和别人不是一个味的味,相信专家能够接受。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对盲艺人传承优秀文化的认识还不是很高,总觉得,他们唱得虽然地道,但从来也没有登过什么大雅之堂,是一个带有“土味”、甚或是带有残疾的特殊人群。
所以,对安排让专家看这场演出能不能为左权文化加分,我心里是有疑虑的。
但又考虑到,这个要求是刘红庆提出来的,他是左权老乡,也是文化部考察组的随员,我相信他,就尽可能地满足他,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下,我立刻拿手机打给在单位的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田建林,让他安排此事,通知盲艺人。
当时,盲宣队分为两个小队,第一小队由盲宣队队长王玉忠兼任,在乡下农村演出;第二小队由张林庆带领,正在县城各机关单位轮演。
盲宣队第二小队接到通知后,就早早地赶回自己的驻地——古戏台上等候。
田青老师一行下榻在县迎宾馆。
当晚,宴客快到尾声了,刘红庆自己壮了壮胆,试探性地和田青、唐师曾、刘序盾等人说,“县里有个盲人宣传队,常年在城乡演出,咱们来左权反正是听音乐,晚饭后让盲艺人给咱们唱一唱行不行?
”为了引起田青教授的重视,刘红庆下意识地加了一句:
“我弟弟刘红权也在这个宣传队里。
”田青教授抹去脸上已布的倦意,爽快地答应了,算是给了刘红庆近乎于恳求的面子。
约摸晚上9点半多了,我和文化艺术中心的两位副主任田建林、郝枫林陪同李松、田青、刘序盾、唐师曾、刘红庆等赶到了古戏台上。
盲艺人因为等我们等不来已经解散了。
田青教授安慰我们说,“以后有的是机会,下次来了再听。
”大家在戏台上转悠了一阵正准备离开时,我单位的工作人员把刘红权接来了,刘红权是盲艺人主扛,这一来,想不到竟留住了来客。
8月正是盛夏炎热的季节,古戏台除了盲艺人隔间成几个宿舍外,没有多少空间可以用来表演,我们几个就索兴把盲艺人们吃饭用的圆桌子搬到院子里,就近从厨房拉出一根电线,把灯泡挂在山墙上来照明。
张林庆、刘红权、陈玉文、王贵明、药成江、曹建红六人围着圆桌坐定,乐器摆在桌子上。
交头接耳了一番,确定了唱的曲目,摆开了演唱阵势,只坐等着开演的一刻。
古戏台院子,夜色下四周寂静,电灯发着微黄的光芒。
大家围在了他们身旁。
盲艺人们以器乐合奏开场,这是他们多少年来形成的演出惯例。
接下来又依次演唱了《光棍苦》、《大实话》、《打假》、《冯魁卖妻》、左权民歌《开花调》。
这几个节目,都是盲宣队的看家节目,多年传唱,百听不厌,民众颇具认同感和亲切感。
李松主任两臂相抱一动不动地听着。
唐师曾一边听、一边拍照,他顾不得自己身体肥胖一会儿站、一会儿蹲,从不同角度把盲艺人摄入镜头。
刘序盾瘦高的身躯像棵树一样在那听得入神;刘红庆怀着感同身受的情绪,第一次听有他弟弟表演的盲人节目,泪水止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田青教授更是以一个音乐家特有的激情和敏锐,一边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用双眼盯着盲人听,生怕自己的呼吸声大了影响到自己听音乐;一边头偶尔微微一动,像是在思考着什么;一边又情不自禁地取下眼镜轻轻擦去模糊了眼睛的泪花。
我陪伴在客人们中间,一边同他们一道欣赏演唱,一边为有这么尊贵的客人来欣赏自己队伍演唱的节目而感到欣慰,内心里企盼着这些客人能为我们这群可歌可敬又可怜的盲人兄弟带来些许命运的福音,以至于给左权文化带来些许的变化。
演出继续进行着,那震天作响、深沉激越的音乐,也引来不少邻居百姓,他们的情绪和盲艺人每一次演出的情绪共起伏,随着演出剧情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
只是也许因为有不寻常人物在场内,少了往日的几多嬉闹,而多了几分沉静,显得不同寻常。
想来,那天夜里,盲艺人铆足劲地表演了五、六个节目,时间确实已经不早了。
我们不得不顾及北京客人旅途颠簸困顿,让盲人们暂且结束了演出。
李松主任和田青教授走上近前和盲人握手、交谈,充分肯定他们的演出。
田青教授当即表示,要带他们到北京演出。
盲人们听了田青教授的话,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药成江、陈玉文接连发出疑问:
“还带俺们去北京演出哩?
”“这些都是唱给山沟沟人听的节目,北京人待听?
”田青教授对着盲艺人和身边的大家说,“我们有主流音乐没有的东西,唱的有真情,唱传统的东西,比如冯魁卖妻,这是先辈留下来的东西,音乐学院也没有学过,大家不要小瞧自己。
大部分人不会。
北大学生只会念书,卖妻、光棍苦他不知道,它留传一百年、二百年,有艺术价值,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不好的东西早就完了。
不要没信心,我们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土气值钱。
通过演出,让学生知道先人唱什么,过什么生活,除了港台节目外,民间还有好的东西,我们有责任传给下一代。
通过演出,也能更好地提高一下左权知名度,让全社会都知道。
”
那天夜里,田青老师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起来,至于盲宣队的艺人们,个个都显得异常兴奋,做起了他们从来也没有做过的甜美之梦……
听完盲艺人演出的第二天一早,李松主任一行人员就乘车返回了北京。
临走道别时,田青教授告诉我,他回北京马上就着手策划“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事宜,要我们加紧做进京演出前的基础性工作,并告诉说,“过一段时间我再来左权,解决演出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
”我们和田青教授就像同行在大海中的船一样,他是舵手,掌管宏观方面的大事,我们是操浆手,负责做微观方面的具体事情。
彼此上下呼应,默契配合,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朝着既定的目标航行。
(二)
多年来,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有个传统做法:
就是深入城乡演出,按两个小队分头行动。
那天夜里田青教授一行在古戏台院里听演出,出场的是盲宣队第二小队。
因此,我们在加紧盲宣队进京演出的准备过程中,必须对两个小队进行充分整合,抽出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田建林专门负责盲宣队事务,迅速通知盲宣队第一小队从乡下赶回县城与第二小队汇合,组成一个团队,备演阵容显得有了声势。
按盲宣队在册员额,当时一共有14名队员,可我们通过摸底发现,在这14人里,其中王明和、李俊林、刘红伟因病离队回家疗养,实际在队的仅11个人。
他们的各个情况是:
一类演员刘红权、王树伟、张林庆、程现庆能拉会唱,声情并茂,是主唱;二类演员王玉忠、陈玉文、药成江、李永兵也能拉也能唱;三类演员王贵明、刘双明、曹建红只能拉不会唱。
这就是当时的实情。
因此,我们认为,让11名队员组成一个演出团体,显然人数偏少;而且表演水平有高有低,有的甚至很差,平时还马马虎虎。
但这次是上北京演出,用盲宣队老队员陈玉文的话说,是到红太阳升起来的地方演出的,谁不高兴。
所以,悉数上场是十分勉强的。
但又没有任何好的替补办法,所以,只好让大家全上场,等田青教授来了征求他的意见以后再做最后决定。
盲宣队多年来的看家节目,在当地不少是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光棍苦》、《大实话》、《冯魁卖妻》等几个曲目。
除此而外,剩下的一些节目就一般化了,原生态味道不浓,上北京演出不大合适,而精品节目偏偏又不够演一台的长度。
怎么办呢?
大家一时心里还没谱儿。
有道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想到走群众路线,请有文艺专长的同志召开诸葛亮会,寻找解决困难的好办法、好途径。
当时,我们请到的与会同志,无论专职的、还是业余的,都是当地有声望,热心文化事业的“行家里手”。
他们是王保牛(原左权县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亦即我的前任)、赵联庆(原左权县文化馆馆长、享受省政府津贴的文艺专家)、孙如明(原左权县文化馆党支部书记、《大实话》节目作者)、李保定(原左权县晋剧团团长)、刘永前(原左权县总工会副主席、文艺创作者)等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把好主意、好办法提出来了,进而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
这台节目要加进左权民歌小花戏的元素,把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艺术特色反映出来;要立足于左权盲宣队的实际情况和盲宣队每个队员的演唱特点,认真筛选节目;要把革命老区和左权将军品牌贯穿在节目当中;要围绕北京专家的意见尽可能地保持原生态的乡土风格……。
应该说,这次诸葛亮会,对我们理清思路是十分必要的。
随后,我们根据大家提出来的这几个金点子,初步确定了演出节目,共八组:
民间器乐曲《听花戏》,是将传统左权小花戏《放风筝》、《送小姨》、《卖扁食》的曲牌连缀成曲。
传统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张林庆主唱),《亲圪蛋下河洗衣裳》(刘红庆主唱),《会哥哥》(张林庆、王树伟对唱),《两相爱》(刘红权、王树伟演唱)。
琴书《光棍苦》(刘红权主唱)。
传统左权民歌《开花调》(张林庆、李永兵演唱)。
琴书《大实话》(刘红权主唱)。
左权抗战民歌《逃难》(刘红权主唱)、《红都炮台》(陈玉文、王玉忠、程现庆、王树伟演唱)、《左权将军》(刘红权领唱)、《土地还家》(刘红权、王树伟演唱)。
琴书《冯魁卖妻》(刘红权主唱)。
民间器乐曲《十样景》,采用左权小花戏《四季生产》、《摘花椒》、《感谢共产党》等经典曲牌编配而成。
9月5日,田青教授由刘红庆陪同又专程从北京赶来左权,敲定上北京演出的节目。
田教授通过听我们汇报,吸取多方意见,和大家一块决定了这样几件事情:
盲宣队除了在家养病的队员,其余全部参加演出;以先前准备的八组曲目为演出的正式节目;尽量保持盲宣队多年来形成的演出风格和表演特点,切忌增加现代舞台上的浮华东西,以原生态为主旨,以土取胜;适当购置一些乐器,更换陈旧难用的设备;为每个队员量身定作一套中式演出服装;吸收羊倌歌王石占明演出,增加演出效果,扩大影响力;设计印制一册节目单,名称叫做《向天而歌——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故事》。
对于田青教授这次赴左权指导工作,我是从心底充满感激的,更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聆听了他的“传经之谈”,所以,当下我向田青教授表态说,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按照专家的意见和要求办事,专家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一定干什么,专家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专家不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坚决不干什么,决不跑偏。
我知道,田青教授和我们合作共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左权县民歌小花戏创新与发展研讨会”和“首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活动中,我们彼此就有深度交往,配合得也很默契。
看得出,这一次,他对我们的做事还是认可和放心的。
大的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接下来,田青教授带着袖珍录音机到古戏台上录制盲艺人演唱的几组经典曲目,录音的时候,我就站在他身旁。
当时,古戏台里静如古寺,静得连地下掉一根针也能听见。
他全神贯注,就象信徒聆听高僧大师讲经一样虔诚。
我默默地感受着。
田青教授对我讲到,“这些东西都是多少年留下来的,是民族文化中的珍品,是靠一代人一代人口传心授留下来的。
如果不好好加以抢救保护,很容易人亡艺绝。
所以,必须得想办法把它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接着,田青教授和我谈到了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硕士研究生的老师杨荫浏,我在一旁静静地聆听。
他对我说,“杨荫浏对我国民族音乐遗产包括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戏曲音乐的发掘、抢救、搜集、整理、研究工作,都有很大成就和贡献,他对阿炳的乐曲进行了抢救和整理,并编成《阿炳曲集》。
他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举世公认的。
你知道阿炳的《二泉映月》吧?
就是杨先生把它推到全世界的。
”听着田青教授讲述这些传奇的故事,我感慨不已,敬佩之情由然而生。
我对田青教授说,您对盲宣队这么关心,这样重视,并且带他们到北京去演出,很让我们感动啊!
田青教授说,“缘,这些都是缘,佛家讲究缘,是缘分。
我们随缘吧!
”
这缘真不浅。
我从心里这样默默地想,我,应该感谢缘。
是缘一次次把我带到田青教授身边,和他零距离相处,让我更清楚了他的性格、行事方式和言谈举止,更觉得他侠肝义胆、胸怀坦荡、耿直率真,对优秀的民间文化挚爱有加。
对他,可以说,我是在原来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了解,在旧的钦佩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钦佩。
但是,回过头来看,说句实在话,我们身处文化领域最基层,毕竟受自己的眼光和见识所限,对田青教授给予盲宣队关注的浓度、评价的高度以及对民族民间优秀文化抢救、挖掘、整理所怀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强度,理解还是很有限的。
我们想走近他,也许于其身不难,若于其心,怕是还待来时。
不用说,事实也正如此。
让我更为感动的是,此次离开左权回到北京,田教授怀着对乡土诗意的、宗教般的虔敬,饱蘸着激情的笔,写出了盛赞左权盲艺人而又醒世骇俗的那篇——《阿炳还活着》,发表在《人民日报》,进入了我的眼底,直抵我的心灵深处,他在这篇文章里说道:
“作为一个以听音乐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
但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沱。
“这是民间小调《光棍苦》。
从他唱出的第一声开始,我便被那声音震撼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
他的声音苍凉而又高昂,高音区雄劲刚烈,中低音区浑厚、坚实、略带沙哑,充满磁性,转折处如云天裂帛,低回处如巨石夯土。
也许,正因为他看不到观众,所以养成了他向天而歌的习惯,也许,正因为他无法眉目传情,所以他没有现在许多职业演员和歌手的毛病,没有丝毫的做作、虚伪和职业化的表情。
他似乎不在意你听不听,喜欢不喜欢。
他只是唱,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唱自己的心中事,唱自己的生活。
听他的歌唱,你觉得他仿佛不是用嗓子在唱,而是用心在唱,用灵魂在唱,用他的整个生命在唱!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眼泪开始流下面颊的,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流泪。
在艺术中,我最怕两个字:
真实。
每当我不经意间在艺术中与它邂逅,我都很难自已。
让我庆幸的是,这两个字其实真的很难遇到。
但这个晚上,在这座残破的古戏台的房屋下,我听到了真实的歌声。
他的感情是真实的。
他和他的盲人伙伴都是光棍,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发自他的内心;他的歌声是真实的,没有被专业音乐教育用“科学”的锉刀打磨掉个性的毛刺。
悲是真悲,声是真声。
十二个月,十二段光棍的凄凉心情和凄凉故事,用一段与《绣金匾》近似的曲调反复唱了十二遍!
但是,人们居然没有听够!
“昏黄的灯光下,音乐在生它养它的这片热土上自然流着,刮着,就像山野林间的水,就像田边小路上的风。
我忽然感到,我现前的这些盲艺术家,就是师旷再世,阿炳重生。
“上世纪后半叶,第一次听到二胡曲《二泉映月》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以手掩面,涕泗横流。
据说他当时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这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
随后,这首盲人创造的乐曲,逐渐走出国门,成了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音乐作品。
现在,只要提到中国民族音乐,《二泉映月》恐怕是第一个跳进人们脑海里的曲名。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知道“瞎子阿炳”的比知道他的本名“华彦君”的人多,知道《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比知道其他任何一首民族器乐曲的人多,但能想到中国最伟大的音乐常常是盲人的创造,恐怕很少。
“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假如阿炳还活着》,在这个夏夜,我终于看到了活着的阿炳。
“次日,回到了北京,但这段发生在三百年前的故事、这些盲音乐家们他们饱含感情的声音和没有表情的表情,却一直跟着我。
一个月之后,我又一次专程来到左权,和他们一起下乡。
当我搀扶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在山间小路上艰难地鱼贯而行的时候,当我在村口的空场上和乡亲们混坐在一起围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当我又一次在那座破败的古戏台下听他们歌唱并为他们录音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大的欣慰,因为,我亲眼看到了这些师旷的后裔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辛勤而尊严地生活着,我亲耳听到当代的阿炳们依然在用他们美好的艺术回馈着社会,像遍野的春草一样一年一年地传承着绿色。
‘秦时明月汉时关’,而这绿色,不就是白居易眼中那野火烧不尽的绿色吗”?
写到这里,让我联想到了2006年的一幕:
这年正月,文化部等九部委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
展览分综合展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展区。
在综合展区一个大块展板上,阿炳照片被放得大大的,展柜上还陈列着杨荫浏录制阿炳曲目的钢丝录音机。
因为有2003年“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的经历,我对这一块展览是在留心上又增加了一份留意,特意照相留影。
所以,我敢说,杨荫浏先生对抢救民间音乐的贡献有多大,田青教授对盲艺人音乐抢救的贡献就差不多有多大。
这样来评价,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妥吗?
这话有点说远了,现在收回来。
我还想说说,田青教授与我谈“缘”的那次左权行。
当时,陪田青教授参观了座落于县城附近的石佛寺,他看了南山观音堂,顺着山沟,穿过大片松林,在石佛洞停站了好长时间,对大小不等的几个洞窟看得很仔细,对里面雕刻的石像格外感兴趣。
在下山回城的路上,田青教授嘱咐我,要采取些办法,好好保护保护,并答应回北京筹点款用于石窟的维修保护。
田青教授为什么会如此关注石佛寺呢?
我以为,这跟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音乐研究所所长,多年来一直在宗教领域的经历不无关系吧。
田青教授是“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演出活动的组织者,并亲自兼任演出的主持人。
为了增加更多一点的感性认识,他又跟随盲艺人到乡下农村,感受盲艺人和村民们那种水乳交溶、其乐融融的氛围。
不难看出,赴北京演出前的这段日子,盲宣队的盲艺人们像孩童们盼过年、过“六·一”一样兴奋。
我们又在古戏台上召开近似于誓师的动员会,以进一步提高大家的重视程度和认真程度。
我用盲人们容易接受的话语给盲艺人们讲:
大家不是相信命吗?
命是什么?
命字就是人下来一个叩。
叩是什么?
叩就是礼仪、礼数,礼仪、礼数就是文化。
所以,命运就是文运。
我们大家唱的这一套都是文运的东西。
这一回是要到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北京城去演出,我们几代盲艺人哪一代去北京演出过?
就是大家有这个福气,赶上好时候了,遇上田青老师这个大贵人啦!
咱们能不好好演吗?
能往田老师脸上抹黑吗?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不能!
大家好像都成竹在胸,早做好了演出的准备。
我讲完话,接着是田建林副主任动员。
他提醒说:
“大家不能翘尾巴不当回事,自以为是。
演出和种庄稼一个道理,要深耕细作,一锄头一锄头种‘庄稼’。
得在平时认真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万个认真。
把节目的精彩之处落在每一个队员的努力上。
”可以说,田建林副主任的讲话言近旨远,也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这一次,盲宣队也有人说了话。
第一个说话人是盲宣队队长王玉忠,他代表大家做表态发言:
“咱们天天彩排,其实不叫彩排,咱们这叫天天现场直播。
以前是唱给村里人听的,这回是去北京,唱给北京人听的,哪敢马马虎虎。
咱们不能出洋相,丢人败兴,谁出洋相咱治谁。
坚决不能一圪瘩烂肉,坏了满锅汤。
”
“对!
”刘红庆接过话茬,对着自己的弟兄们做了强调:
“大家平时在乡下怎么演,这次去北京也怎么演,关键是保持住平时演出的状态和风格,不要把花里忽哨的东西加进去,搞得不伦不类,变了味、变了样。
”
看得出,我们这次动员,确实发挥了作用,盲宣队的队员们的劲头更足了,天天做着精雕细刻式的高强度训练。
盲宣队进京演出的前前后后,有一位已经成为我们要好朋友也和左权的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传播着绿色,成为传播绿色的使者。
她就是时任浙江电视台《亚妮专访》栏目制片兼导演的亚妮。
我在这里不能不提及她。
早在2002年浙江省仙居县举办“首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上,她和田青教授作为主持人,一同主持着赛事。
田青教授很欣赏她,把她视为同道和知己。
从此以后,她就和田青教授、石占明以及我们结下了情谊,而且是日久弥深的情谊。
石占明在仙居得了歌王奖回到左权不久,亚妮就带着摄制组跟踪而来,拍摄专题节目——《进城记》,首次把石占明宣传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公众人物。
9月5日,也就是田青教授又一次到左权的同一天,亚妮也带着她的摄制组又一次赶到了左权,拍摄反映全县民众唱民歌、跳小花戏蔚然成风的专访节目《翻过山是孔家庄》。
这是我们县举办“第二届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的一个重要的预热性节目。
曾几何时,当亚妮得知田青教授策划左权盲艺人进京演出而且很快就要成行的消息之后,她以一个记者特有的职业敏锐和对田青教授的崇拜,立刻就在自己的脑子里进行构思,打起盲艺人的主意,作起了盲艺人的节目。
她一边拍摄《翻过山是孔家庄》,一边又不失时机地抢拍田青教授和盲艺人在乡村的镜头。
紧接着,她的身影又出现在“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的现场。
从此以后,她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作盲艺人的电视节目,而且还变卖了自己的房产作盲艺人的电影。
这是后话,我暂且表到这里。
临行前,盲艺人们以焕然一新的面貌,给县四套班子领导做了汇报演出。
县领导热情地鼓励了一番,以壮行色。
(三)
“太行盲艺人北京高校行”的演出日期在国庆节前已经排定。
从10月10日至16日,分别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残联、人民日报社、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招待所等院校和单位演出。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是主场演出;在北京市海淀区残联的那场是纪念国际盲人节的联欢性演出;在人民日报社的那场是由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左权籍老乡段存章邀约的慰问性演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招待所的那场是为了感谢为盲艺人在北京演出提供热情帮助、在海军大院工作的左权籍老乡李晋军等的联谊性演出。
10月8日,我们一行乘坐一辆租用的大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