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司公案皇明诸司公案续廉明公案传 明 余象斗编述3.docx
《诸司公案皇明诸司公案续廉明公案传 明 余象斗编述3.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诸司公案皇明诸司公案续廉明公案传 明 余象斗编述3.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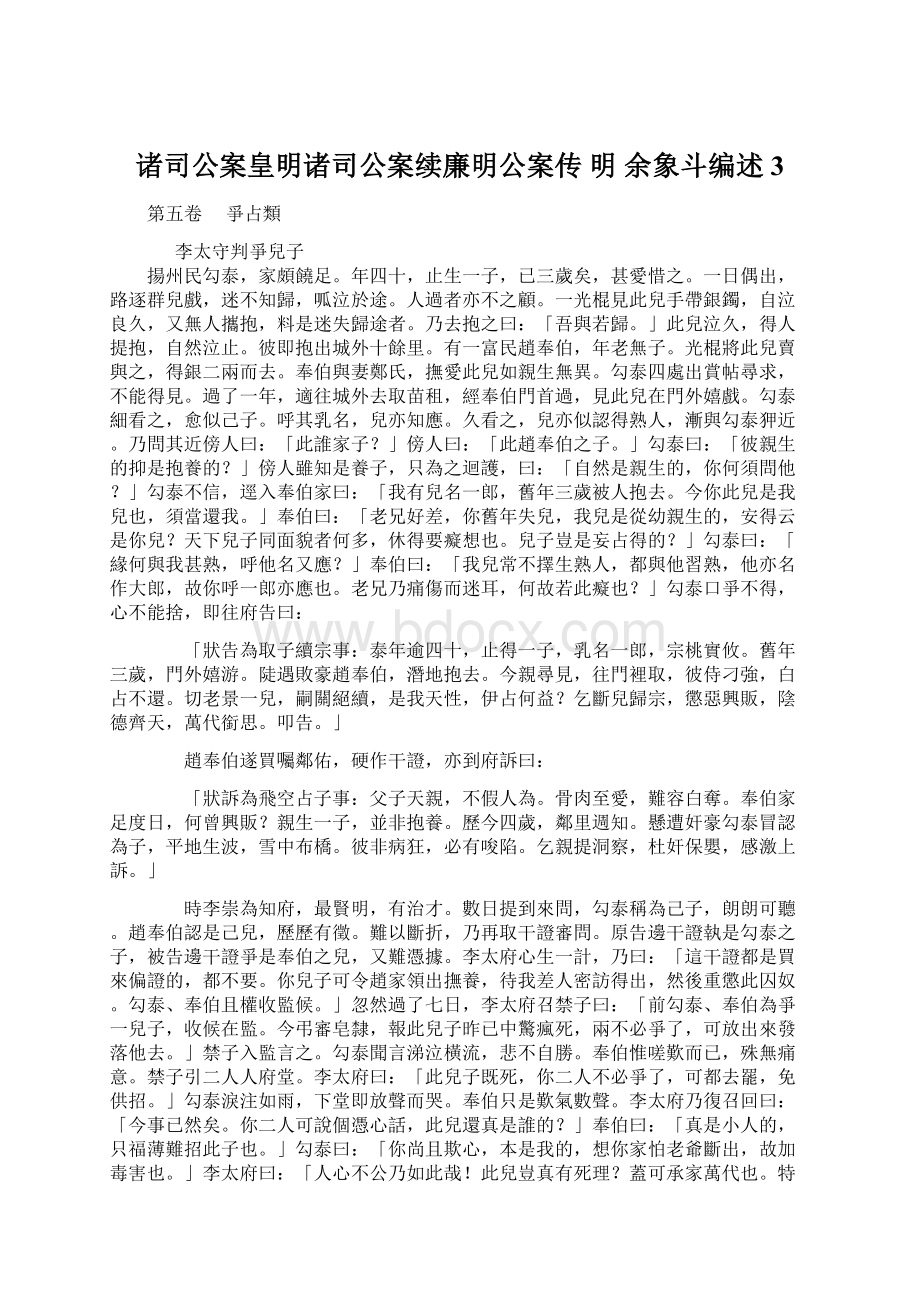
诸司公案皇明诸司公案续廉明公案传明余象斗编述3
第五卷 爭占類
李太守判爭兒子
揚州民勾泰,家頗饒足。
年四十,止生一子,已三歲矣,甚愛惜之。
一日偶出,路逐群兒戲,迷不知歸,呱泣於途。
人過者亦不之顧。
一光棍見此兒手帶銀鐲,自泣良久,又無人攜抱,料是迷失歸途者。
乃去抱之曰:
「吾與若歸。
」此兒泣久,得人提抱,自然泣止。
彼即抱出城外十餘里。
有一富民趙奉伯,年老無子。
光棍將此兒賣與之,得銀二兩而去。
奉伯與妻鄭氏,撫愛此兒如親生無異。
勾泰四處出賞帖尋求,不能得見。
過了一年,適往城外去取苗租,經奉伯門首過,見此兒在門外嬉戲。
勾泰細看之,愈似己子。
呼其乳名,兒亦知應。
久看之,兒亦似認得熟人,漸與勾泰狎近。
乃問其近傍人曰:
「此誰家子?
」傍人曰:
「此趙奉伯之子。
」勾泰曰:
「彼親生的抑是抱養的?
」傍人雖知是養子,只為之迴護,曰:
「自然是親生的,你何須問他?
」勾泰不信,逕入奉伯家曰:
「我有兒名一郎,舊年三歲被人抱去。
今你此兒是我兒也,須當還我。
」奉伯曰:
「老兄好差,你舊年失兒,我兒是從幼親生的,安得云是你兒?
天下兒子同面貌者何多,休得要癡想也。
兒子豈是妄占得的?
」勾泰曰:
「緣何與我甚熟,呼他名又應?
」奉伯曰:
「我兒常不擇生熟人,都與他習熟,他亦名作大郎,故你呼一郎亦應也。
老兄乃痛傷而迷耳,何故若此癡也?
」勾泰口爭不得,心不能捨,即往府告曰:
「狀告為取子續宗事:
泰年逾四十,止得一子,乳名一郎,宗桃實攸。
舊年三歲,門外嬉游。
陡遇敗豪趙奉伯,潛地抱去。
今親尋見,往門裡取,彼侍刁強,白占不還。
切老景一兒,嗣關絕續,是我天性,伊占何益?
乞斷兒歸宗,懲惡興販,陰德齊天,萬代銜思。
叩告。
」
趙奉伯遂買囑鄰佑,硬作干證,亦到府訴曰:
「狀訴為飛空占子事:
父子天親,不假人為。
骨肉至愛,難容白奪。
奉伯家足度日,何曾興販?
親生一子,並非抱養。
歷今四歲,鄰里週知。
懸遭奸豪勾泰冒認為子,平地生波,雪中布橋。
彼非病狂,必有唆陷。
乞親提洞察,杜奸保嬰,感激上訴。
」
時李崇為知府,最賢明,有治才。
數日提到來問,勾泰稱為己子,朗朗可聽。
趙奉伯認是己兒,歷歷有徵。
難以斷折,乃再取干證審問。
原告邊干證執是勾泰之子,被告邊干證爭是奉伯之兒,又難憑據。
李太府心生一計,乃曰:
「這干證都是買來偏證的,都不要。
你兒子可令趙家領出撫養,待我差人密訪得出,然後重懲此囚奴。
勾泰、奉伯且權收監候。
」忽然過了七日,李太府召禁子曰:
「前勾泰、奉伯為爭一兒子,收候在監。
今弔審皂隸,報此兒子昨已中驚瘋死,兩不必爭了,可放出來發落他去。
」禁子入監言之。
勾泰聞言涕泣橫流,悲不自勝。
奉伯惟嗟歎而已,殊無痛意。
禁子引二人人府堂。
李太府曰:
「此兒子既死,你二人不必爭了,可都去罷,免供招。
」勾泰淚注如雨,下堂即放聲而哭。
奉伯只是歎氣數聲。
李太府乃復召回曰:
「今事已然矣。
你二人可說個憑心話,此兒還真是誰的?
」奉伯曰:
「真是小人的,只福薄難招此子也。
」勾泰曰:
「你尚且欺心,本是我的,想你家怕老爺斷出,故加毒害也。
」李太府曰:
「人心不公乃如此哉!
此兒豈真有死理?
蓋可承家萬代也。
特假此試汝二人心耳。
此兒明是勾泰的,故聞死而深悲。
奉伯惟略歎息,便見非天性至親,故不動念也。
今此兒當歸勾泰。
」即命領去。
欲加奉伯刑,乃供出昔用銀買得,非己之興販人口也。
李侯判曰:
「父子天親,不假人為。
死生大變,乃見真性。
今勾泰連老得子,惜如掌珍。
出外忘歸,茫如喪命。
想昔孤雛之失道,何弄彀雀之離巢。
趙奉伯雖買自棍徒,原非販賣,但認於親父,理合送還勾姓。
非趙宗,豈楚方而楚得。
人心合天道,自塞馬而塞歸。
胡乃執迷,坐生訐訟。
及至謬傳詐死,全無悲心;便非屬毛離衷,故不濺淚。
爾不予人之子,人安親汝為親。
骨肉重完,一郎自歡。
有父箕裘可紹,勾老豈恨無兒。
思移異姓以承宗,奉伯宜加深罰;姑念辛勤於撫子,計功且示薄懲。
」
按:
勾、趙皆富而無子,其爭必堅。
幼兒又無知,何以辨之?
惟詐傳兒死,則親父必然痛心,養父自不深悼,便可知其真偽矣。
其妙全在此處也。
袁大尹判爭子牛
南安縣民董惟仁、賈懷遠兩家,各畜有牛母,同月各生一牛子,嘗晝則共牧,晚則同歸。
兩月後,惟仁之牛母跌死,其牛子與懷遠之牛母共牧,時亦混食其乳,夜共同宿其欄。
惟仁心以為便,省得人工看顧。
再經四個月,牛子已長,將取買與人。
懷遠曰:
「此是我家牛子,汝何得盜賣?
」惟仁曰:
「我牛子寄與你牧;安得白占去?
」懷遠曰:
「汝無牛母,安有牛子?
你欲冒認,反改說我白占。
」惟仁不甘,赴縣告曰:
「狀告為領占事:
刁惡賈懷遠,貪婪昧心。
仁畜牛母孳生牛犢,牛母跌死,犢孤無伴,寄宿遠欄,朝夕共牧。
昨取犢賣,遠起占心,賴稱伊物。
千金寄人,理難費用。
一牛寄欄,公然白占。
有此強豪,賴占不甘。
乞斷物還主,庶杜刁頑。
上告。
」
賈懷遠訴曰:
「狀訴為強買刁誣事:
家畜耕牛,孳生二子。
刁棍董惟仁丟價強買,爭價角口,砌情告臺,冒稱伊牛寄欄畜養。
彼我非親,何同畜牧?
二犢同乳,熟為伊物?
乞訊捏誣,剪減刁風。
上訴。
」
縣主以所爭微細,亦當審問明白。
於是嚴提原被告並一母牛、二牛子俱到。
惟仁稱一牛子是他牛母生的。
懷遠稱二牛子都同此牛母生的。
兩相爭辯,不肯屈服。
袁大尹曰:
「你二人爭辯又無干證,吾將此二牛子起作證,看是誰的。
」將一繫於堂前左邊松樹,將一繫於右邊松樹。
各用棍其後腳,牽牛母於甬道中。
牛母見牛子動,號痛趨奔於左邊小牛之傍,嘴近同號,若有憐念之意。
而右邊的全不顧。
及袁尹命復牽牛母於中,解放二小牛之。
一放後,左邊小牛奔依牛母之旁,眷戀傍附。
右邊小牛遂逃於門外去,全不戀著牛母也。
袁大尹曰:
「此牛子分明是董惟仁的,賈懷遠之牛母只是一子。
凡畜物皆有天性。
你看之時,牛母惟憐惜己子,而右邊的不顧。
及解之時,親牛子便依附親母,而非牛母所生者,脫難之後,超然逃去,豈復顧同欄之伴哉!
」乃將懷遠責十板,以牛斷與惟仁去。
人皆服袁公之明察。
袁尹判曰:
「審得董惟仁、賈懷遠皆畜牧家也。
惟仁之牛母死,而牛子寄牧於懷遠之欄,亦同儕借便之情則然。
懷遠以二犢共一牛之乳,同欄經四月之久,遂因而占之,以致訟爭。
及將兩犢加,而牛母惟憐所親之子。
既解挾之後,而牛子惟戀所生之母。
則懷遠安得並據兩犢,同出一牛之養哉!
如當日不欺心賴占,惟仁當貼四月代牧之工。
今且冒掩人物,妄指人刁,則罪已浮於勞矣。
故勿計功,以酬其勞;亦勿科贓,以罰其罪。
詐窮而薄懲以衍揚,小事姑免供乎紙贖。
」
按:
袁尹察物之明,治人之恕,不言而可知矣。
抑因是而有感焉。
夫以畜物之天性,母子且知相愛。
乃世有為父母而淹女,及懦夫受制於妒妻,不敢舉妄所生之子者,則自戕其天性,是牛母之不若矣。
為子而厚於妻,子薄於父母,視天親如路人者,則自絕其本根,是牛子之不若矣。
乃後母而岐視前子,養子而陽順嗣父,陰厚生父者,又無怪其然。
何者?
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外屬終非性生也。
一本之義大矣哉!
於縣丞判爭耕牛
益州府安固縣民任天真,家頗饒足。
欠方以一牛犢,還之。
鄰近杜近高,求牛代耕,為之牧養,歲納其租。
其牛後益壯大,既能犁田,又歲出一犢,甚得倍利。
天真問之取,近高曰:
「此牛係我養大,今僅獲微利,尚未足以酬勞。
願更牛已老,孳生利少,畜之何益?
」近高曰:
「你牛前矮小,今壯大,加倍於前。
你欲取去,須貼我工力銀一兩。
」天真曰:
「牛養一年,自然加長一年。
你得一年代耕,又得牛子,足以還你工力有餘。
今日隨小大肥瘦,原是我的自應還我,那有更貼工力之理?
」只管欲牽歸,近高來爭曰:
「是我畜的牛,你未還價,如何牽得去?
」天真與之爭。
近高曰:
「我前用價買過了,誰人不知是杜家的牛。
今日全不還你,憑你何如。
」任天真告於府曰:
「狀告為刁占事:
前歲價買耕牛一頭,費銀四兩。
刁徒杜近高希圖代耕,孳生牛子。
脫去代牧歲稅租銀三錢,真思本重利輕,取還自畜。
惡先哀乞牧,次索工資。
理折弗與,計窮變生,遂欲白占,反行兇毆。
本買牛種,租否由我,恃刁強佔,情理何甘。
乞親提懲惡,還牛做刁,庶物有主,民不橫行。
上告。
」
杜近高訴曰:
「狀訴為勢奪事:
先年用價二兩,賈豪任天真牛犢一頭,今牧三年,壯大倍前。
豪貪私宰,丟價三兩,勢逼強賈,高不甘賣,致爭角口。
豪反臺告,冒稱伊牛,租高牧養。
懸捏鬼情,有何證據?
懇天提究,斧折豪強,民知有法,不敢刁誣。
叩訴。
」
刺史韓伯攜,初提審之,兩家互相爭辯,干證各為偏證,不能剖決。
心自思曰:
「縣丞於仲文,少年聰察,試令決之何如。
」即批:
「仰安固縣縣丞於,詳問解報。
」仲文令任、杜兩家同牽牛到,全不審之,但言曰:
「我於某心如寶鏡,眼如明珠,你看我蒞任以來,凡百訴訟,皆辨得真情,那有一個冤枉?
何況,你所爭一牛,現有物在,此有何難察?
但我午前無暇,你兩人且牽牛去,下午即來聽審,定斷得牛屬真主。
」任、杜依命;復牽牛出。
於二尹令腹心皂隸沈薦喻之曰:
「你可去故令人刺傷此牛,看任、杜二人喜怒若何,即速來報。
」沈薦出見兩個樵子,肩荷竹擔,將去採樵。
薦以新錢二文買糖與二樵子吃,曰:
「你那個刺傷得這牛,我再買糖與你吃。
」二樵子曰:
「恐怕罵人。
」沈薦曰:
「他是鄉下村農,有我衙門人在此何怕他!
」二樵子便以竹擔假相殺,走近牛邊,以竹擔刺傷其腿,曰:
「宰此牛來賞軍。
」任天真便罵二樵子,不合傷他牛。
杜近高默如也。
沈薦前去曰:
「豎子輩相,你這山巴老,那是你罵的!
」又叫二樵子回,買糖與吃訖。
入報於公曰:
「適刺傷那牛,任犯便罵,杜犯自若。
」下午弔來審。
於公故意相觀其牛曰:
「此牛生得好,必會犁田,會出子,果是否?
」杜近高曰:
「果是如此。
」於公曰:
「你兩人不消開口,我但看此牛,便知你相爭之由矣。
想是三年前,任天真將牛與杜近高牧時,其牛尚小。
今三年後,牛已壯大,又有出息,故天真欲取回,近高不肯。
及欲取得急,近高便強佔為己物,以致告訟。
此牛乃是天真的,而近高強佔之也。
」天真磕頭曰:
「老爺神見,事情來歷果是如此。
」近高正欲辯,於公喝曰:
「你該打十五板矣!
再說一句,便打三十。
」近高乃認罪。
打十五訖,將牛斷與任天真去。
人皆服其明。
於尹判曰:
「審得杜近高草茅賤漢,田野村夫。
百畝是生涯,晝永鋤移桑下日;一家勤未耘,春深耕破隴頭云。
荷插扶犁,既事於耜舉趾之業;耕食鑿飲,當安胼手胝足之勞。
欲圖引重以代耕,因借牛種於任氏。
數年既獲子利,今日應還本牛。
胡為久假不歸,欲據倍收之息。
敢爾取非其有,番織勢奪之詞。
紛訟公庭,尚恣齲齒簧舌之辨;斷經州郡,不輸鉤金束矢之情。
刁占之惡可憎,健訟之風宜剪。
公取皆以盜論,計贓而免黥刑。
」
判訖,即申文連人解報於府。
韓太守問:
「於丞何以審汝?
」任天真曰:
「原被都未出一言,於爺但看牛之壯大,便知三年之前與牧之時牛小,而今欲取之,杜近高不肯退還,因一發賴占,不待二人執對半句,而真情灼出矣。
」韓太守歎曰:
「異哉!
於亟之明,可以稱『霹靂手』矣。
予不之及也。
」自後凡有疑獄,皆批與判,悉當於情。
於丞遂名重於時,實自此判始。
齊大巡判易財產
長垣縣鄉宦戚世美,家富於財,產業不止十餘萬。
嫡子繼禮為太學生,母示以父藏銀之所,私兜去銀一萬兩。
妾母生子繼祚為秀才,甚得寵於父。
因繼禮私取銀之後,父亦另積銀一萬兩付幼子繼祚,實則均平,無偏厚薄也。
父在日,親寫分關二扇,將產業田宅均分與二子收管。
及父故,繼禮要求父餘銀出分。
妄母曰:
「業次早已分定,銀兩亦各有定歸。
爾的歸爾,弟的歸弟,父所代掌者,乃弟之田租所出自,豈有將弟分銀出與爾共乎!
」繼禮曰:
「前日止分田產,銀並未分。
以我父之家,豈無數萬積銀乎?
」妾母曰:
「父一生積銀數萬,與大娘共埋於地。
你都掘去,全無一些分弟。
今後那得有銀?
」繼禮曰:
「我只納監,費去父銀不過於兩,以後父積累年銀何可算!
今日必須將來均分,難容你子獨佔。
」妾母與弟繼祚,自是不聽之矣。
戚繼禮先去大名府告曰:
「狀告為孽庶刁占事:
故父家貨逾十餘萬,所積餘銀不下數萬。
禮居嫡長,弱冠納粟,身居太學,不任家務。
父寵妖妄,偏愛幼子。
先年分關止開田產,餘銀俱存,議定後分。
父病驟故,孽弟繼祚刁占獨兜,庶反凌嫡,弟得壓兄,肥瘠不均,全占難忍。
乞弔父賬目,稽出入數,明算均分。
遺銀共沾,黏單上告。
」
戚繼祚去汗告曰:
「狀告為霸佔軋幼事:
鱷兄繼禮,倚恃嫡長,貪縱殘毒,轢庶孽。
父共嫡母,埋銀數處,通計三萬兩有奇。
母私親子,指示繼禮。
父今病故,伊悉掘去,百十無分。
切兄納監諸費,母私積贏餘,祚不敢論。
故父厚積,理當共分。
嫡庶雖殊,所讓盡多。
遺銀獨無,偏厚天淵。
乞臺垂念祚亦父脈,斧斷分給,庶幼沾恩,亡父瞑目。
叩告。
」
張大府親提審之。
繼禮曰:
「吾父私寵於妄,因溺愛少於。
前分時,止將田產均分,其銀都在,今繼祚獨謾去。
是庶幼更強於嫡長也。
彼謂我掘銀去,今父雖故,二母共居一房,從何處掘得,有何證據?
」繼祚曰:
「父分我住新屋,身與二母同。
兄住祖屋,銀必隨身。
豈有身居兄家,而銀藏弟屋者乎?
彼取去埋銀,鄰里都聞,何謂無證?
」又問干證時,受繼禮賄者為兄;受繼祚賄者為弟,皆不得直。
張太府已納兩家關節,只大罰其罪,並未動刑,模稜判去。
二人不服心,又兩相汗告。
如此者五年,幾經十餘斷,不能息爭。
及齊賢為當街御史,繼禮、繼祚又來告。
齊院早聞其爭訟累年疊告不休。
乃謂之曰:
「兩兄弟積訟,吾早已訪得其實。
今當為兩判之,求息其爭。
兩人可各將父手分關並籍記、自置物業、大關物件,一一開報來。
各處鎖鑰都交付來。
又兩家親丁,不論男女老幼、主婢僮僕,都到衙一審,傾刻即放回,便可永杜爭端矣。
」兩人依命,將兩家丁口都抬到衙,以分關鎖鑰並莊田記籍,盡數遞上。
齊院問繼禮曰:
「看汝兄弟分關既均,田宅婢僕亦恰相當,而苦告弟不休者,必謂弟家之銀多於汝也。
」繼禮曰:
「故父遺銀,皆係弟得。
故累告者,正為彼銀多也。
」齊院曰:
「汝弟之銀,藏於自家乎?
抑寄於外親乎?
若盡搜弟銀與你,今後肯息訟否?
」繼禮曰:
「銀必在弟家中,不寄在外親也。
若以弟銀與我,更多我家數倍。
」齊院呼繼祚問曰:
「汝之告兄,亦必謂兄之銀多也。
倘以兄銀與汝,今還息訟否?
」繼祚曰:
「父所埋銀,皆兄掘去,果為銀多,故告之。
若得兄銀共分,於願足矣,何敢再告。
」齊院曰:
「繼禮既謂弟之家當銀多,今以弟之分關、記籍、鎖鑰悉付繼禮,使入居弟之宅,掌管弟之業。
繼祚既謂兄之銀多,亦領兄之分關、鎖鑰去入居兄之宅,掌管兄之業。
如那個再有一句反悔,便抄沒其家,將家屬盡流煙瘴地方,勿留之以敗壞風俗。
」即刻命公差押去,兩相換易。
繼禮、繼祚出,兩家婦女,皆思戀自家器物,都不肯換。
乃相與人哭於巡按之前曰:
「小的兄弟不肖,不合激惱老爺,今蒙教誨,兩相換易,誠至公至明之斷,豈敢不遵?
奈兩婦女都戀自家,器與手熟,居與身熟。
從今不敢起訟,願兄弟各掌己業,勿致相換。
如有再爭,甘服大罪。
願天臺俯循民望。
」齊院曰:
「吾判已出,不可再移。
如不願換,須籍沒家產,各流遠地,以儆悖逆兄弟刁訟之風。
」兩家又叩頭求赦。
齊院曰:
「兄弟本無所爭,但財多勢大,黷利喪心,下則買賂干證,上則交通關節,自謂終訟無妨,蔑視官府,以為官莫奈爾何也。
今斷相換,都不願換,則兩家俱富可知。
何為汗告累年,豈非多財為崇乎?
今據汝兩詞,俱稱父家十餘萬,其各罰一萬充邊用,再不得起訟,然後免汝相換。
」繼禮、繼祚心又欲換,卻不敢再說,只是從罰。
自是亦不敢再訟。
齊院判曰:
「審得戚繼禮、戚繼祚一弟一兄,雖有嫡庶之分。
而共父共脈,何殊手足之親。
兄告弟刁霸父銀,獨享豐腴;弟告兄私掘地窖,盡竊羨餘。
根引株連,訐訟累歲。
蝸爭蟻鬥,經斷幾官。
骨肉化為仇讎,同氣分為異體。
除非兩易其產,方可並息其爭。
茲斷彼此換資,便乃復老幼號陛。
願各利其利,各居其居。
固知兩家之房富則同,亦見二犯之險健相比。
皆因財為崇,故以官為嘗。
宜痛削其無算之資,庶少抑其終惱之性。
各罰萬金,以充邊用。
斯明一體,以敦友於。
」
按:
二戚構訟,起於繼禮先私萬金。
而繼祚亦受萬金於父,乃不少屈於兄,故疊訟無已。
信乎其多財為崇也。
齊院之重其罰,若過於深文,而不合於律。
然不重創,則不深懲,何以儆其後哉!
是宜省而猛者也。
吾謂不獨懲二戚當然,凡兄弟之爭財而訟者,惟小家而急於衣食,計較銖兩,此特渺小之徒,不必厚責。
若萬金以上者,分產雖小有偏虧,惟在立志自充拓耳。
而世之永訟者,多出於富厚之子,皆可重罰以抑其財勢,則訟自清矣。
此去薪止沸之法也。
齊院之判,不特易產一節,能折橫逆之徒,而重罰亦良方也。
江縣令辨故契紙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起濤,姦宄狡黠,獵騙鄉民。
見鄰婦有夫死者寡守幼子陳巽繹,家頗富饒。
嘗遣僕收租,佃多頑欠不完。
有南塘一路,田可百畝,路遠尤難追收。
起濤亦有數佃在南塘,便有謀陳宅田之意。
故誑其寡婦曰:
「南塘路遠人刁,苗租多不完納。
我亦有田在彼處,你不如以田租我,代爾收其稅,納銀還汝,豈不甚便?
」寡婦許之。
其租果收得完足。
三年之後,起濤往囑各佃曰:
「向者,陳寡婦以田當與我撥租,我收准息。
今已全賣與我,你各人須立荷當來,然後我給歷頭,與你耕作。
今後畝租俱宜還我。
」各佃悉皆遵之。
彼外收佃戶之租,內納陳宅之稅。
佃惟知洪是己主人,陳不知洪已外冒占伊佃。
忽逾二十年,陳寡婦已故。
洪起濤乃偽為券契,以茶染紙,為淡黃色,若類遠年舊紙者。
遂不納陳巽繹之租。
及來徵索,起濤曰:
「你令先堂前田已全賣與我,特田價未完,故收數年租補你。
今價已滿足,田係我家物業,豈更納汝租乎!
」巽繹曰:
「你租我田代收,我家何曾賣田與你?
」遂往南塘去收租。
各佃都曰:
「我耕江主人田已經二十年,不認陳宅是我主也。
」都不肯還。
陳巽繹赴縣告曰:
「狀告為刁豪脫占事:
繹幼孤母寡,佃多頑欠。
刁豪洪起濤,計租繹田,代收納租。
伊得秤頭,繹享歲入,不費徵索,佃無敢欠。
經二十載,全無變異。
詎豪變計,冒稱伊業,歲租不納,田盡霸佔。
脫管於前,熟交各佃;刁占於後,欺繹孤弱。
乞懲惡斷租,田復歸主。
庶儆刁風,孤弱有賴。
上告。
」
洪起濤訴曰:
「狀訴為唆騙罔誣事:
濤先年用價銀二百五十兩,買陳巽繹田一百頃,契書明白,中見可證,歷今二十餘年。
兩經造冊,未肯射產,歲貼糧役銀七兩五錢,毫無虛欠積歇。
洪策唆繹重索補價,奸騙不遂,又唆告臺,捏稱脫占。
時價明買,何謂脫管?
契書可據,安在刁占?
乞剪唆究誣,民安訟清。
叩訴。
」
江縣令提審之。
陳巽繹曰:
「起濤為我甲頭,代我收租耳。
我手接他租已經十餘年。
今一旦冒稱田賣與他,白占何甘?
」洪起濤曰:
「小人有契書在此,是伊母親手花號,二十年物業,今日如何強爭得!
」江大尹取契一看,即折曰:
「此是假契,陳巽繹之母末賣田也。
汝但代彼收租而已。
」起濤曰:
「遠年舊契,何以假得?
更有中人在此可問。
」江大尹曰:
「你謀占人二百五十兩銀田產,豈不能許數十金買中人?
此干證亦不消問矣。
我叫吏取二十年前案卷紙與你看,其外蒙塵,受風煙則黃;其中,紙色俱白。
今此契表裡如一,乃是用茶染的,故知是偽也。
」因命用。
起濤不認。
又欲中人。
中人見起濤真情已被察出,為他受刑無益,不待用,遂招出原日並未為中,特起濤許銀二十五兩,買他為證。
江尹以其未敢欺瞞,遂釋之。
而擬起濤以欺占之罪。
江尹判曰:
「審得洪起濤斗筲賤品,鷹犬下材。
既舞智以御人,復因機以罔利。
欲剝騙民之膏血,代收寡婦之畝租。
催督早完,內受工直,徵收加重,外克羨餘。
民間謂之甲頭,在官謂之攬戶。
蠶食百家之內,志氣風生;狼貪一里之中,稜威日肆。
孤見無識,寄心腹於豺群;寡子何知,委膿鮮於虎口。
彼貪心尚未養足,乃狡計復爾橫生。
偽作契書,欲掩襲他人之業;強為抵賴,將覬覦非分之圖。
久假不歸者非仁,取非其有者悖義。
死寄金而歸主,昔人且靡負盟;生佃田而霸佔,此日忽聞異事。
宜加嚴罰,用警貪夫。
罪坐杖提,業追還主。
」
按:
洪起濤這計甚狡。
彼抱田而代之收租,便詐稱田賣於己。
給歷頭於各佃,則佃戶自認彼為主矣。
又經二十年之久,偽作契書為證,幾何而不落彼圈套乎。
惟江侯因契書之假舊紙,則欺占之情立灼見矣。
今之假批契者,往有之。
故舉其一,以示司刑者慎辨之。
彭知府判還兄產
合州人趙愷,以鄉科為知縣,同弟趙懌往任中。
所得宦金,每托弟先攜歸置產,前後共六千餘兩。
弟懌買田地,其券契皆用自己名,居然收掌管業。
兄一意信仗,毫不防其欺瞞也。
既而兄愷卒於官,嫂楊氏,生子趙志忠,年甫八歲,自任扶櫬歸家,所剩餘金不滿千矣。
問叔懌取夫所寄之銀,趙懌曰:
「吾向所得者,是兄所與我的,豈問他借而今日取乎?
你今滿載而歸,兄死並無手澤與我,反問我取甚銀?
」遂絕無所與。
嫂楊氏不勝憤恚,奈無記籍可稽,只得訴於州曰:
「狀告為霸業絕命事:
故夫趙愷官授知縣,歷積俸金三千餘兩。
夫狼弟趙懌,前後攜歸,買置產業,坐享膏腴。
夫卒於官,扶櫬空歸,理取前銀,叔毫不吐。
氏寡子幼,朝夕枵腹。
二命難度,貧宦可憐。
乞提狼叔,追夫宦金,給幼度命,孤寡沾恩。
迫告。
」
趙懌訴曰:
「狀訴為唆占事:
懌與兄愷異籍十年。
懌勤生理,苦積資財,稍堪度日。
兄任知縣,為官清廉,不幸病故,家資淡薄。
富貧皆命,豈得混占?
嫂楊氏,信伊棍弟楊大進教唆,捏情誣告。
稱兄宦金寄懌置業,既無記籍,又無收票,茫無根據,欺罔殆甚。
唆弄骨肉,妄生爭占。
乞依法究唆,杜占安民。
上訴。
」
郭知州提審之。
楊大進曰:
「婦人告狀,自然有抱告,豈得便是教唆?
我是外人,他係至親嫂叔。
嫂贏是趙家之嫂,叔贏是趙家之叔。
我何與焉,而用教唆為憑。
老爺審我老姊,看是教唆否?
」楊氏曰:
「小婦人忝為命官之妻,苟非不得已,豈肯拋頭露臉,跪對公庭,不惟羞及亡夫,且玷辱朝廷。
今日之告,萬萬不得已也。
夫在任時,懌叔來任三次,每次皆寄銀二槓發歸。
雖未知其多少,此親目所見者。
今分文不還,世間有這樣欺心人乎!
若非我夫之銀,他數年內,安能發得許大家財?
」趙懌曰:
「小的與兄分居十載,罄半生所發,家貲未滿五千,皆刻苦生放所得。
雖到兄任三次,不過為秋風而去,一次只有二百兩。
兄若寄積與我歸,我必有收票。
向後二次去,若是他銀買田產,必交契與他。
縱兄不堤防,這樣潑嫂,豈肯寄銀三千餘兩而不索我收票乎!
老爺可以詳情。
他是夫故官清,宦囊淡薄,欲取三次秋風銀未得,聽楊大進教唆,遂告此假狀,無楊大進亦不有此狀告矣。
」郭州牧曰:
「汝既有五千金之家,盡足自給。
楊命婦又家貧子幼,則你三次所得秋風銀,亦不論多少,只判五百銀還嫂姪,一可不利兄之有,二亦親姪所得,非與外人。
」趙懌曰:
「小的何曾得他五百金?
是前日非打秋風,乃借債也。
小的實出不得。
」郭州牧曰:
「就是你發財,亦是倚兄官勢乃起家,容今斷五百金與姪,你亦未貧,就當你為官,而姪打你秋風,有何不可?
」趙懌乃曰:
「依老爺鈞旨,小的不敢違。
」楊氏心終不甘,問弟何以再告之。
楊大進曰:
「聞鄰封彭爺聽斷極明,可往彼處投告,或能察得懌叔欺瞞之情。
」楊氏即命大進往眉州去告。
時彭祥為太守,見異府百姓來投光,即面審問,已得其詳細。
便吩咐曰:
「你可討保在店中候,不可揚言你來告狀,我自提來,為爾斷之。
」乃命刑房吏寫關文,逕往合州去:
「見得劫賊危諧,現劫眉州鄉村被獲,指出窩家趙懌。
可速解來並審。
」關文一到,郭知州以賊情事重,即拿趙懌解去,至眉州投到。
彭太守先於獄中取出劫賊危偕,教他指趙懌為窩家,三年前同在數處打劫,因此他得財致富。
及趙懌到,令與懌執對,賊一一說來:
見得趙懌是同伙劫賊,又為窩家,故五年內致萬金巨富。
彭太守便喝先打後問。
趙懌曰:
「願容一言分辯,後打死亦甘心。
」彭命曰:
「且容你言。
」趙懌曰:
「小的素來良善,亦有二千金家資。
後故兄為知縣,前後寄銀六千兩,將來置買田地,皆有入收賬目,何謂是打劫?
豈有兄為鄉官,而弟為劫賊者?
」彭公急追賬目、圖簿契書來看。
見其賬目上記收兄銀三次,果其六千兩。
後用去買田銀數,都開寫明白。
然後命收入監。
拘嫂楊氏到,再取出執對。
彭公曰:
「你非劫盜,尤甚於劫盜;盜惟劫外人,汝且劫嫂姪。
盜贓重不上百,汝贓已滿六千。
今物業皆是嫂姪者,可將契書當堂一應交付,批執照與楊氏掌管。
但原銀六千兩,今田價共五千兩,該更追銀一千與楊氏領。
其三年內花租,姑免究。
」趙懌哀求於嫂曰:
「我代你所置田業,今都追還,後一千兩可要與我,勿再催領罷。
」楊氏乃稟曰:
「懌叔亦夫親弟,田既還我,後一千兩銀,情願與他。
一當顧他代買田業,二當為兄之手澤,三且令他照顧幼姪,勿結冤仇。
」彭公曰:
「言亦有理。
田令楊氏領去管業,後一千兩免追。
」彭公判曰:
「手受寄金,豈錙殊之可昧;義無苟得,難生死而不移。
惟取寄如攜,偉哉曩賢高誼。
鬫敞受長官之托,過數而還。
其孫京郎,領鄉人之資,如期而付。
其於少取寄來之、來式,彰庾詵之賢聲,久讓故人之金,自致包公之義判。
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