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docx
《梁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梁衡.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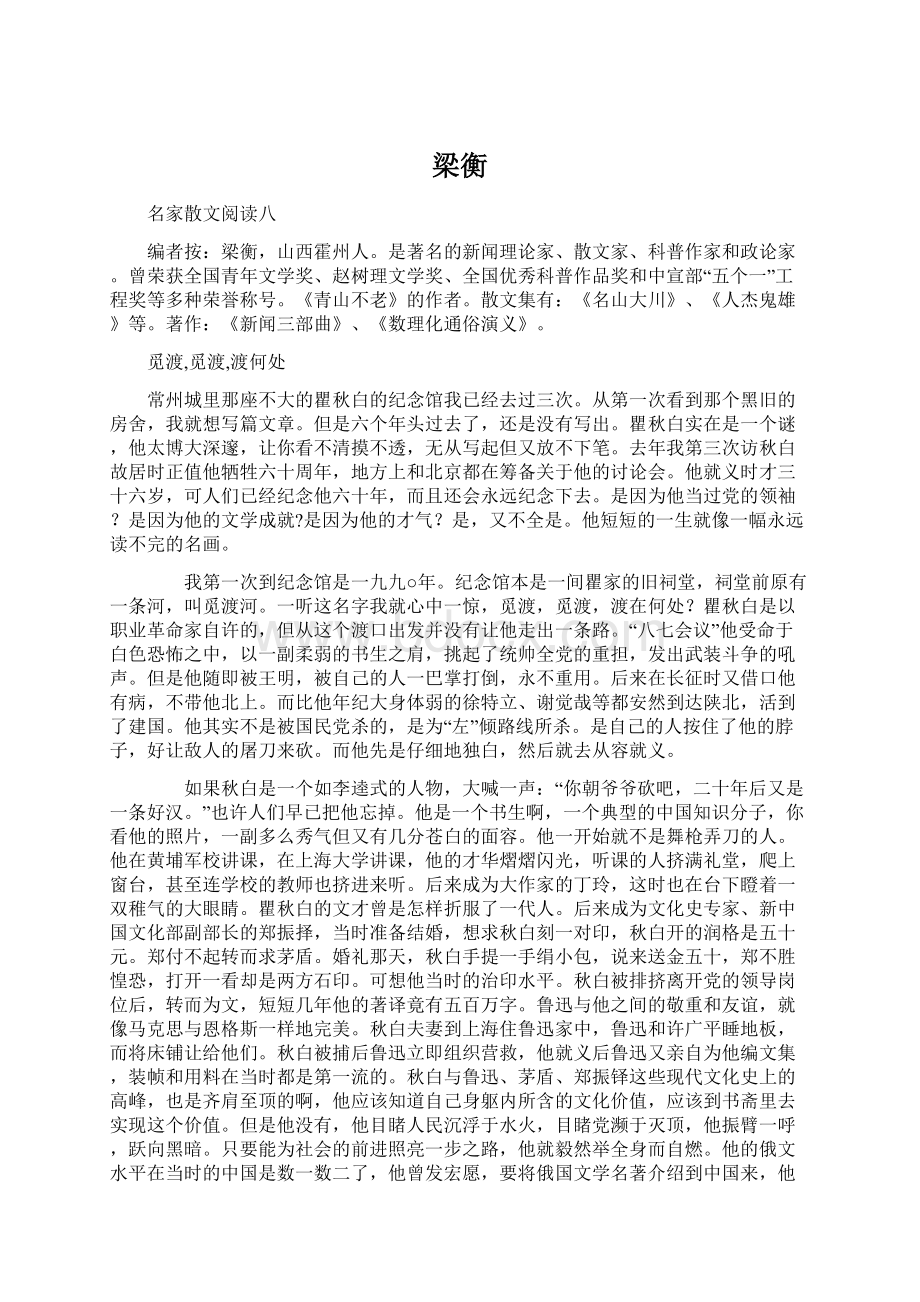
梁衡
名家散文阅读八
编者按:
梁衡,山西霍州人。
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
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青山不老》的作者。
散文集有:
《名山大川》、《人杰鬼雄》等。
著作:
《新闻三部曲》、《数理化通俗演义》。
觅渡,觅渡,渡何处
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
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
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
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
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六十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
他就义时才三十六岁,可人们已经纪念他六十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
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
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
是因为他的才气?
是,又不全是。
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一九九○年。
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觅渡河。
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觅渡,觅渡,渡在何处?
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许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
“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
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
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
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
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
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
而他先是仔细地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
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大喊一声:
“你朝爷爷砍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
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
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
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
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
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
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
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
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可想他当时的治印水平。
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著译竟有五百万字。
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
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
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
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
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
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
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了,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译是最合适的。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
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人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
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
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
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作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
但是他没有。
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
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
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
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
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
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
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
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
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
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
“瞿秋白!
”他却木然无应。
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
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
“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
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
”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
他死意已决,说:
“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
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
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唯求一死。
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
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粉。
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达到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
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
刑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
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
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
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
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
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
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
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
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
不必了。
他将生命看得很淡。
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
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
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
他说过:
“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
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
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
而他却不肯。
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
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
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
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
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地来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
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起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
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
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
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
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
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
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
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
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
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
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
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
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儿男子偏不肯去打球。
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获,甚至被人误会。
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
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而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
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
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
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返观人生。
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
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
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
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
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
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秋白不朽。
追求一个境界(代序)
——谈梁衡的散文
季羡林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看法:
在中国散文坛上有两个流派。
一个流派主张(或许是大声地主张),散文之妙就在一个“散”字上,信笔写来,松松散散,随随便便,用不着讲什么结构,什么布局,我姑且称此派为“松散派”。
另一个正相反,他们的写作讲究谋篇布局,炼字铸句,我借用杜甫的一句话“意匠惨淡经营中”,称此派为“经营派”,都是杜撰的名词。
我还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大家的传世名篇无一不是惨淡经营的结果。
我窃附于“经营派”。
我认为,梁衡也属于“经营派”,而且他的经营还非同寻常。
即以他的写人物的散文来说,一般都认为,写人物能写到形似,已属不易,而能写到神似者则不啻为上乘。
可是梁衡却不以神似为满足,他追求一种更高的水平,异常执著地追求。
但是他追求什么呢?
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名词。
我曾想用“境地”,觉得不够。
又曾想用“意境”,也觉得不够。
也曾想用“意韵”、“韵味”等等,都觉得不够。
想来想去,我突然想到王国维的“境界”,自认得之矣。
“境界说”是王国维论词的新发展。
《人间词话》有很多地方讲到“境界”:
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境界”,同“性灵”、“神韵”等一些文艺理论名词一样,是有一定的模糊性的,颇难以严格界定其含义,但是统而观之,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这是一个富有启迪性、暗示性、涵盖性的名词,上举《人间词话》最后几句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
现在从梁衡散文中举出一个例子来。
他的名作《觅渡,觅渡,渡何处?
》是写瞿秋白的。
瞿秋白这个人才华横溢,性格中和行动中有不少矛盾,梁衡想写这样一个人,构思了六年,三访瞿秋白纪念馆,迟迟不敢下笔。
他忽然抓住了“觅渡”这个概念,于是境界立出,运笔如风,写成了这篇名作。
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
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
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
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把栏杆拍遍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
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我看到的资料里,辛弃疾至少是快刀利剑地杀过几次人的。
他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
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岁时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并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
一次义军中出了叛徒,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
辛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提回一颗人头。
为了光复大业,他又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
不想就这几天之内又变生肘腋,当他完成任务返回时,部将叛变,耿京被杀。
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
说来,他干这场壮举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
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也再没有机会奔走沙场,血溅战袍,而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
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像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
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
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
虽然杜甫也写过: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
“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
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
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
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
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
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
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
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
我曾专门到南京寻找过这个辛公拍栏杆处,但人去楼毁,早已了无痕迹,唯有江水悠悠,似词人的长叹,东流不息。
辛词比其它文人更深一层的不同,是他的词不是用墨来写,而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
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像。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这样不为朝廷喜欢呢?
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
“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
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
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
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
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
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
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
本来有碗饭吃便不该再多事,可是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
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
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
他任湖南安抚使,这本是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却在任上创办了一支2500人的“飞虎军”,铁甲烈马,威风凛凛,雄镇江南。
建军之初,造营房,恰逢连日阴雨,无法烧制屋瓦。
他就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全部筹足。
其施政的干练作风可见一斑。
后来他到福建任地方官,又在那里招兵买马。
闽南与漠北相隔何远,但还是隔不断他的忧民情、复国志。
他这个书生,这个工作狂,实在太过了,“过则成灾”,终于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独裁、犯上。
皇帝对他也就时用时弃。
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
别看他饱读诗书,在词中到处用典,甚至被后人讥为“掉书袋”。
但他至死,也没有弄懂南宋小朝廷为什么只图苟安而不愿去收复失地。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
他只有一块心病:
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这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就读过的那首著名的《菩萨蛮》。
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
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
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
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酸辛苦。
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永遇乐》)
你看“艰辛”、“酸辛”、“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
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
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地被调动。
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
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
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
算只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
休去依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
梁启超评曰:
“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
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
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
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
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
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
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
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
“君恩重,且教种芙蓉!
”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
“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
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
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
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
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
白鹤在何处,尝试与谐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
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
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
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
(《水调歌头》)
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
“稼轩”,要回乡种地了。
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作一个词人。
郭沫若说陈毅:
“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
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
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
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
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
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
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
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
他亲自组练过军队,上书过《美芹十论》这样著名的治国方略。
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
他像一块铁,时而被烧红锤打,时而又被扔到冷水中淬火。
有人说他是豪放派,继承了苏东坡,但苏的豪放仅止于“大江东去”,山水之阔。
苏正当北宋太平盛世,还没有民族仇、复国志来炼其词魂,也没有胡尘飞、金戈鸣来壮其词威。
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包括社会、民族、军事等矛盾)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
诗歌,也只有在政治之风的鼓荡下,才能飞翔,才能燃烧,才能炸响,才能振聋发聩。
学诗功夫在诗外,诗歌之效在诗外。
我们承认艺术本身的魅力,更承认艺术加上思想的爆发力。
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
谁解相怜?
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
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
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
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
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
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
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
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
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
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
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
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
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草。
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
诗,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写的吗?
诗人,能在历史上留下名的诗人,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吗?
“一将成名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还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
那么,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
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
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梁衡《读柳永》
柳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并不大的人物。
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碰到过又很快忘了他。
但是近年来这根柳丝却紧紧地系着我,倒不是为了他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为那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只为他那人,他那身不由己的经历和那歪打正着的成就,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的道理。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生平记载,以至于现在也不知道他确切的生卒年月。
那年到闽北去,我曾想打听一下他的家世,找一点可凭吊的实物,但一川绿风,山水寂寂,没有一点音讯。
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大约在30岁时便告别家乡,到京城求功名去了。
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
其实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