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docx
《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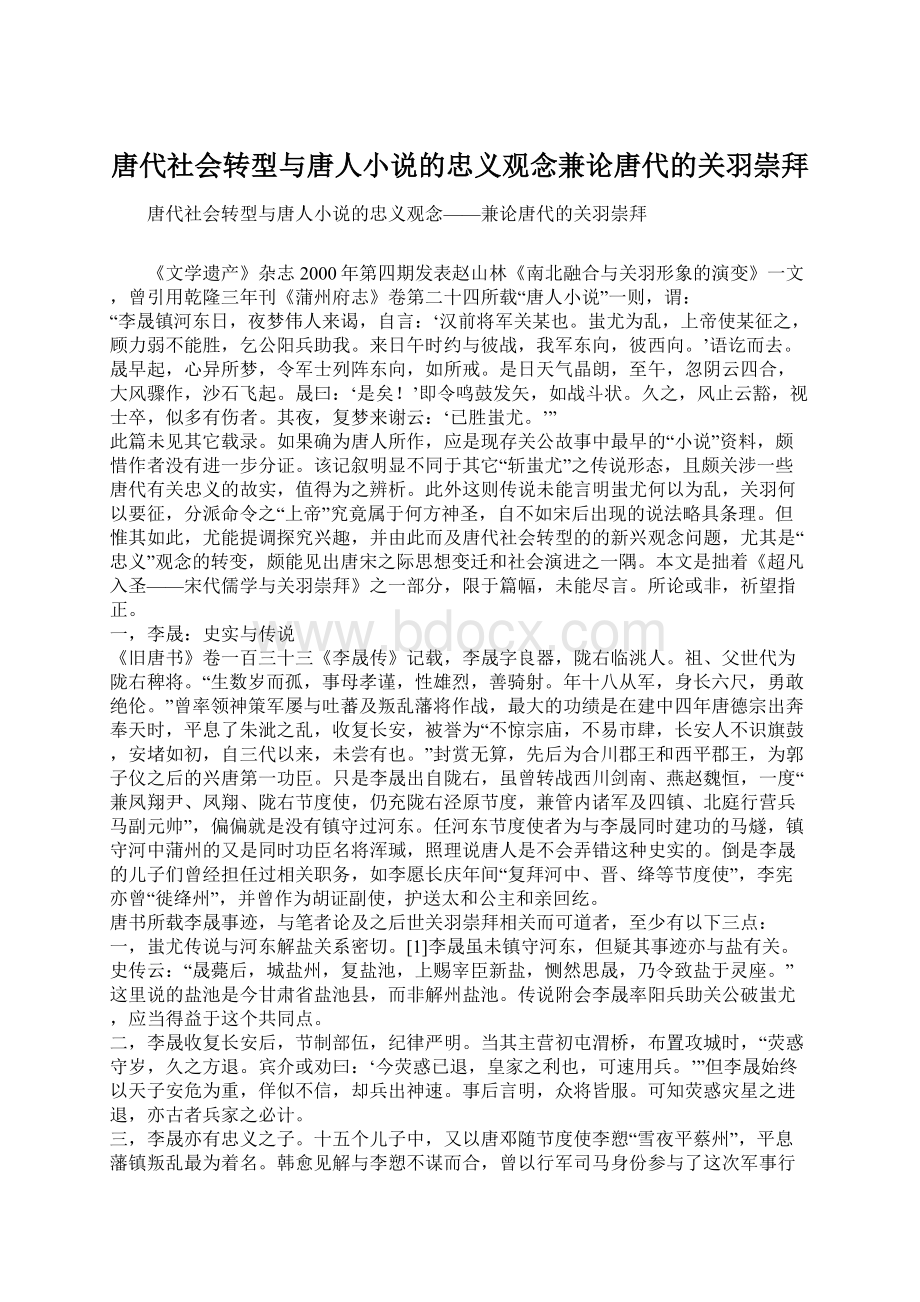
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
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
《文学遗产》杂志2000年第四期发表赵山林《南北融合与关羽形象的演变》一文,曾引用乾隆三年刊《蒲州府志》卷第二十四所载“唐人小说”一则,谓:
“李晟镇河东日,夜梦伟人来谒,自言:
‘汉前将军关某也。
蚩尤为乱,上帝使某征之,顾力弱不能胜,乞公阳兵助我。
来日午时约与彼战,我军东向,彼西向。
’语讫而去。
晟早起,心异所梦,令军士列阵东向,如所戒。
是日天气晶朗,至午,忽阴云四合,大风骤作,沙石飞起。
晟曰:
‘是矣!
’即令鸣鼓发矢,如战斗状。
久之,风止云豁,视士卒,似多有伤者。
其夜,复梦来谢云:
‘已胜蚩尤。
’”
此篇未见其它载录。
如果确为唐人所作,应是现存关公故事中最早的“小说”资料,颇惜作者没有进一步分证。
该记叙明显不同于其它“斩蚩尤”之传说形态,且颇关涉一些唐代有关忠义的故实,值得为之辨析。
此外这则传说未能言明蚩尤何以为乱,关羽何以要征,分派命令之“上帝”究竟属于何方神圣,自不如宋后出现的说法略具条理。
但惟其如此,尤能提调探究兴趣,并由此而及唐代社会转型的的新兴观念问题,尤其是“忠义”观念的转变,颇能见出唐宋之际思想变迁和社会演进之一隅。
本文是拙着《超凡入圣——宋代儒学与关羽崇拜》之一部分,限于篇幅,未能尽言。
所论或非,祈望指正。
一,李晟:
史实与传说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三《李晟传》记载,李晟字良器,陇右临洮人。
祖、父世代为陇右稗将。
“生数岁而孤,事母孝谨,性雄烈,善骑射。
年十八从军,身长六尺,勇敢绝伦。
”曾率领神策军屡与吐蕃及叛乱藩将作战,最大的功绩是在建中四年唐德宗出奔奉天时,平息了朱泚之乱,收复长安,被誉为“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来,未尝有也。
”封赏无算,先后为合川郡王和西平郡王,为郭子仪之后的兴唐第一功臣。
只是李晟出自陇右,虽曾转战西川剑南、燕赵魏恒,一度“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仍充陇右泾原节度,兼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偏偏就是没有镇守过河东。
任河东节度使者为与李晟同时建功的马燧,镇守河中蒲州的又是同时功臣名将浑瑊,照理说唐人是不会弄错这种史实的。
倒是李晟的儿子们曾经担任过相关职务,如李愿长庆年间“复拜河中、晋、绛等节度使”,李宪亦曾“徙绛州”,并曾作为胡证副使,护送太和公主和亲回纥。
唐书所载李晟事迹,与笔者论及之后世关羽崇拜相关而可道者,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蚩尤传说与河东解盐关系密切。
[1]李晟虽未镇守河东,但疑其事迹亦与盐有关。
史传云:
“晟薨后,城盐州,复盐池,上赐宰臣新盐,恻然思晟,乃令致盐于灵座。
”这里说的盐池是今甘肃省盐池县,而非解州盐池。
传说附会李晟率阳兵助关公破蚩尤,应当得益于这个共同点。
二,李晟收复长安后,节制部伍,纪律严明。
当其主营初屯渭桥,布置攻城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
宾介或劝曰:
‘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
’”但李晟始终以天子安危为重,佯似不信,却兵出神速。
事后言明,众将皆服。
可知荧惑灾星之进退,亦古者兵家之必计。
三,李晟亦有忠义之子。
十五个儿子中,又以唐邓随节度使李愬“雪夜平蔡州”,平息藩镇叛乱最为着名。
韩愈见解与李愬不谋而合,曾以行军司马身份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
《旧唐书·李晟传》附《李愬传》赞云:
“始,晟克复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复踵其美。
父子仍建大勋,虽昆仲皆领兵马,而功业不侔于愬,近代无以比伦。
”这与关羽、关平父子勤劳王事,亦有可通。
唯一的差别,就是李氏父子都功成业就,而关氏父子却功亏一篑。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关羽需要向李晟借力的原因吧。
中晚唐为唐人小说传奇的“黄金时代”。
除了铺陈前代前人故事之作,如《虬髯客传》、《东城父老传》、《长恨歌传》、《太真外传》等以外,与李晟同时之事亦复不少,如《无双传》即以“泾原兵士反,姚令言领兵入含元殿,天子出北苑北门,百官奔赴行在”,作为结撰全篇的大背景,而这正是唐德宗建中四年冬十月“朱泚之乱”的开始。
後世着名戏剧《西厢记》的母本《莺莺传》,不但发生在解盐所在的河东蒲州,而且以“是岁,浑瑊薨于蒲。
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
”作为张生、莺莺得以许婚的大关目。
这些小说的历史背景,陈寅恪曾在批注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中有所考论,不妨参看。
唐人小说向以传奇性着称,假托神仙鬼怪,亦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这一则李晟助关公战蚩尤的故事,究竟是否出于唐人之手,尚不能骤断。
唯文中关羽之自称但言“关某”而不称名,应该是明清关公崇拜大兴以後,由戏曲小说引发出来的习俗。
但至迟在元代,李晟亦被道教列为传奇人物。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有“先知死罪”条言:
“桑道茂祖为供奉,李晟为神策小将。
道茂曰:
‘足下即贵,某之数,性命当在公手。
能赦之否?
’晟笑曰:
‘供奉见侮乎?
’道茂怀中取一纸,大书其官衔姓名,云:
‘所犯罪衍,乃是逼迫,伏乞恩慈,性命全宥。
’晟笑曰:
‘遣某道何语?
’道茂乞曰:
‘准状特放。
’晟为书之。
後朱泚反,道茂复旧职。
晟往京城,收逆徒数百人,置旗下就戮。
道茂大呼曰:
‘某有状!
’取视之,乃昔年所书也。
晟惊悟,释放道茂,以为上客。
”
案《新唐书·方伎传》有桑道茂事迹,略谓道茂善太一遁甲术。
曾数次预言唐师胜败及宰相休咎事,“德宗素验其数”。
“及朱泚反,帝蒙难奉天,赖以济。
李晟为右金吾大将军,道茂赍一缣见晟,再拜曰:
‘公贵盛无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见赦否?
’晟大惊,不领其言。
道茂出怀中一书,自具姓名,署其左曰:
‘为贼逼胁。
’固请晟判,晟笑曰:
‘欲我何语?
’道茂曰:
‘弟言准状赦之。
’晟勉从。
已又以缣愿易晟衫,请题衿膺曰:
‘它日为信。
’再拜去。
道茂果污伪官。
晟收长安,与逆徒缚旗下,将就刑,出晟衫及书以示。
晟为奏,原其死。
”则道茂能望气,作预言,盖亦神仙者流,唐人已异其能。
其中“李晟救道茂”故事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涉及到中晚唐臣僚的两难处境。
中晚唐政局反复多变,皇帝动辄就仓皇出逃,确实会令留在京城,无力随“狩”的臣下无所是其从。
钱锺书论及杜甫《哀江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望城南望城北”句时,以为“杜诗尤凄警”:
“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有若张衡《西京赋》所谓‘丧精亡魄,失归忘趋’。
”欧阳修记叙桑道茂向李晟预请赦书的故事,正表示着对于这种两难处境的“同情之理解”。
其实,既然桑道茂善于预言,理应预见并避免自己身陷这种两难处境。
“缣帛”之类道具,“书具”预赦,“衿膺”题免等等表演,明显为“想当然”之增饰,此亦当时说话人,后世小说家之惯技,无非表达出了修史者的微妙情感。
[1]拙着《“关帝斩蚩尤”考——关羽崇拜与宋代道教》曾探及此,香港《岭南大学学报》新三期。
《旧唐书》列传第八十三《李晟传》。
《“关帝斩蚩尤”考》第八节《“黄帝”“蚩尤”与宋元律历星占》论及此。
巴蜀书社《藏外道书》《关帝灵籖》别本第六十二籖籖题,即为“李愬雪夜入蔡州”,可谓暗合。
《〈唐人小说〉批注》,《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後集》卷1〈道教门〉,170-171页。
该书元刊本题为“江阴薛证汝节刊”或“江阴薛诩汝节刊”,可知曾多次覆刻。
所辑以宋金元间神怪仙道之事为主。
奇怪的是,《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桑道茂传》却说:
“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及朱泚之乱,帝仓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
时道茂已卒,命祭之。
”欧史于此传增益甚多,其中包括《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四《应徵十·温造》、卷第二百二十三《相三·桑道茂》、赵元一《奉天录》卷一记桑道茂事等。
赵元一《奉天录》为唐人实录。
曾说道茂本为卫士云云。
其他则耳食之谈,小说家言。
参《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版,988-989页。
且说唐代虽然素以盛大夸耀于史,亦为后人艳称,却始终没有能够树立起一套保障官僚体制忠诚李唐皇室的价值系统来。
短短一百一十四年间,紧接着“贞观之治”的便是“武周代唐”,紧接着“开元盛世”的便是“天宝之乱”,一方面“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建立了“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1]另一方面宫廷内部管理极为不力,庞大的官僚系统不堪一击。
不但容易造成政局的大幅度振荡,就是至亲骨肉的皇子王孙,也不是引颈受戮于皇家刑场,就是铁骑践踏于京城天街,以致杜甫在《哀王孙》里充满感情的吟道: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
韦庄《秦中吟》述唐王朝灭亡之惨状更为淋漓。
《十国春秋·韦庄传》:
“应举时,遇黄巢犯阙,着《秦妇吟》云: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人称为‘秦妇吟秀才’。
”韦庄“杜陵人。
唐臣见素之後也。
”韦、杜两氏本为与李唐王朝同气连枝的高门大姓,故对其衰落灭亡更有切肤之痛。
唐德宗李适在《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的开首感喟道:
“天有柱以正其倾,地有维以钮其绝,皇王有辅佐以济其艰难。
非命历所归,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大勋;非暴乱宏多,不足表忠节;非奸猾炽焰,不克展雄才。
天与事肆会,然后臣功着而王业兴焉。
”
这场由唐德宗一厢情愿开始的“忠节”标立,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和理学的阐发,逐渐成为“五伦”之一。
而后世关羽故事中的“义不降曹”、“辞曹归汉”,以致败走麦城,舍身全忠的故事,也都成为后世鼓励臣僚效忠社稷的好教材,但唐人对待关羽史迹的态度,却还不那么明晰。
这表现在武庙配祀的变化上。
古人云:
“国家之事,唯祀与戎。
”以为君主的基本职责,就在于运用祭祀来宣示文化政策和价值导向,运用战争来表达的领土主权和统治意志。
除了例行敬天法祖的“岳渎”、“祖先”崇拜之外,唐王朝的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就是宣布以国家大典,来祭祀孔子和姜尚,以明示价值体系的取向。
据《新唐书》卷十五《礼乐五》,唐以关羽配祀姜尚凡有三变:
依据安史之乱后的形势变化,唐肃宗首先配飨了志在“兴复汉室”,且为唐太宗盛赞过的诸葛亮;第二变是在礼仪使颜真卿的倡议下,大幅度增加了武成王庙祀,尤其是兴唐保唐诸将的配飨,反映出颜真卿的孤旨苦心。
他意图奖掖历史上功臣名将,用榜样的力量引导握有实权的各路藩镇节度忠心保国。
结果是魏蜀吴并立,而且吴人占据了半数,不知是否与唐室“仰食东南漕粮”,而当时叛乱藩镇多出于河北的情势有关,关羽也在这时和张飞、邓艾一同进入了庙祀。
颇疑李商隐《骄儿诗》描述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元和间唐人说话,亦与这次配飨不无关联。
可惜事与愿违,这项诏令颁布的次年,即发生了李希烈、朱泚等人的大规模叛乱,唐德宗逃难唯恐不及,就连提出这个设计的颜真卿也命丧强藩骄镇之手。
事后武庙配飨也跟着吃了挂落,被毫不客气地撤去祀位,请出武庙。
儒士大夫意犹未尽,还想再接再厉,撤去武成王庙封号,降格为“齐太公庙”。
其实文智武勇,缺一不能安邦定国。
但是作为价值体系的榜样,姜尚代表的更多是“兵家”的谋略及勇于反抗暴政的精神,这在后世小说从《武王伐纣平话》到《封神演义》中有清楚的阐释,而对于中唐这样亟需树立为巩固中央政权奋勇立功之将帅的现实,却多少有点文不对题,从大臣的嚼嚅中,分明已视姜尚为殷之“叛臣”,这正是当时之莫大忌讳。
此外,儒臣还对《孙子兵法》所言之“兵者,诡道也”抱有偏见,以为不足以表率后世,所以极力推崇孔子的政教礼制精神,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以正名分而挽颓世。
中唐文臣武将在庙祀上的对峙,还表现为儒臣多热心于文宣庙的重修。
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双方争执也日益表面化。
上世纪陆续发现的敦煌俗曲率真晓畅,向以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真情实感而乐为学人征引。
其中有两首《定风波》针锋相对,颇像酒桌上武士儒生的斗性使气:
“功【攻】书学剑能几何?
争如沙塞骋偻罗。
手执六寻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剑】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满【谩】夸儒士德能康。
四塞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