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docx
《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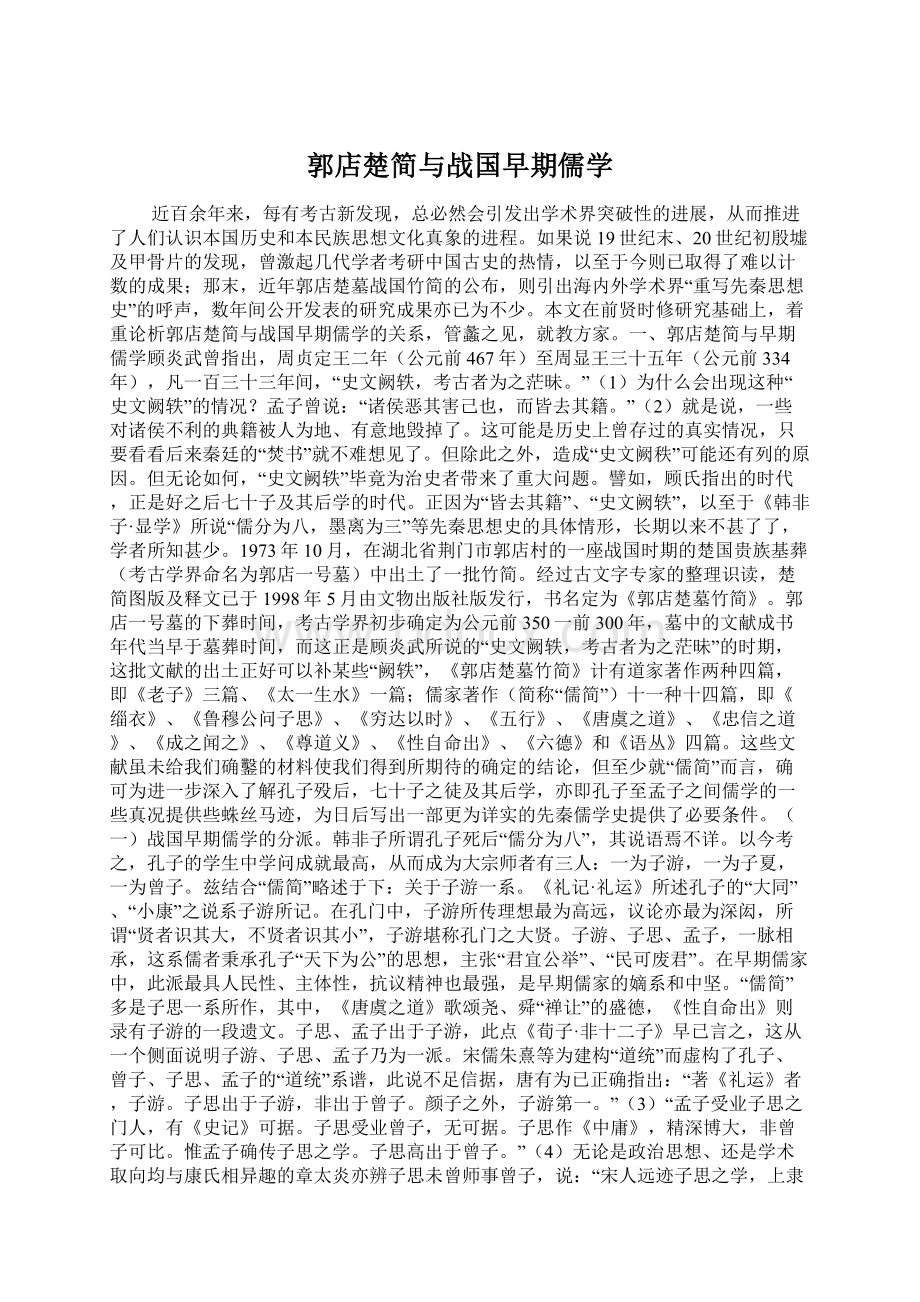
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近百余年来,每有考古新发现,总必然会引发出学术界突破性的进展,从而推进了人们认识本国历史和本民族思想文化真象的进程。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及甲骨片的发现,曾激起几代学者考研中国古史的热情,以至于今则已取得了难以计数的成果;那末,近年郭店楚墓战国竹简的公布,则引出海内外学术界“重写先秦思想史”的呼声,数年间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亦已为不少。
本文在前贤时修研究基础上,着重论析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的关系,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一、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
”
(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史文阙轶”的情况?
孟子曾说:
“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
(2)就是说,一些对诸侯不利的典籍被人为地、有意地毁掉了。
这可能是历史上曾存过的真实情况,只要看看后来秦廷的“焚书”就不难想见了。
但除此之外,造成“史文阙秩”可能还有列的原因。
但无论如何,“史文阙轶”毕竟为治史者带来了重大问题。
譬如,顾氏指出的时代,正是好之后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时代。
正因为“皆去其籍”、“史文阙轶”,以至于《韩非子·显学》所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等先秦思想史的具体情形,长期以来不甚了了,学者所知甚少。
197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基葬(考古学界命名为郭店一号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
经过古文字专家的整理识读,楚简图版及释文已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版发行,书名定为《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时间,考古学界初步确定为公元前350一前300年,墓中的文献成书年代当早于墓葬时间,而这正是顾炎武所说的“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的时期,这批文献的出土正好可以补某些“阙轶”,《郭店楚墓竹简》计有道家著作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篇、《太一生水》一篇;儒家著作(简称“儒简”)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道义》、《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四篇。
这些文献虽未给我们确鑿的材料使我们得到所期待的确定的结论,但至少就“儒简”而言,确可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孔子殁后,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亦即孔子至孟子之间儒学的一些真况提供些蛛丝马迹,为日后写出一部更为详实的先秦儒学史提供了必要条件。
(一)战国早期儒学的分派。
韩非子所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说语焉不详。
以今考之,孔子的学生中学问成就最高,从而成为大宗师者有三人:
一为子游,一为子夏,一为曾子。
兹结合“儒简”略述于下:
关于子游一系。
《礼记·礼运》所述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系子游所记。
在孔门中,子游所传理想最为高远,议论亦最为深闳,所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子游堪称孔门之大贤。
子游、子思、孟子,一脉相承,这系儒者秉承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君宜公举”、“民可废君”。
在早期儒家中,此派最具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也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
“儒简”多是子思一系所作,其中,《唐虞之道》歌颂尧、舜“禅让”的盛德,《性自命出》则录有子游的一段遗文。
子思、孟子出于子游,此点《荀子·非十二子》早已言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子游、子思、孟子乃为一派。
宋儒朱熹等为建构“道统”而虚构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系谱,此说不足信据,唐有为已正确指出:
“著《礼运》者,子游。
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
颜子之外,子游第一。
”(3)“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有《史记》可据。
子思受业曾子,无可据。
子思作《中庸》,精深博大,非曾子可比。
惟孟子确传子思之学。
子思高出于曾子。
”(4)无论是政治思想、还是学术取向均与康氏相异趣的章太炎亦辨子思未曾师事曾子,说:
“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
寻《制言》、《天圆》诸篇,于子思所论述殊矣。
《檀弓》篇记曾子呼伋,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征也。
《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
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
足明其非弟子也。
”(5)[!
--empirenews.page--]关于子夏一系。
子游、子夏,在孔门中均以通晓文献典籍著称,但子游教育学生颇重“上达”功夫,而子夏教育学生则以“下学”之功为重。
子夏一派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原典的传承和研习有很大贡献。
后来的荀子除继承子弓一系外,对子夏一系的学说也有所继承,成为传经之儒。
汉以后儒家经学的发展,主要是这一派的推动。
这系儒者比较注意与统治者的合作,因而较少思孟之儒那样的批判和抗议精神。
康有为说:
“传经之学,子夏为多。
”(6)“传经之功,荀子为多。
”(7)“孟子之后无传经,……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
”(8)关于曾子一系。
此派儒者主要有曾参及其子申(在《礼记》中,曾申有时亦被称为曾子)及参之弟子乐正子春等。
这派儒者重孝道之践履,其基点落左家庭父子关系上。
他们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如曾参认为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甚至不以时伐山林、杀禽兽等,都会绘父母带来恶名,皆不可谓孝。
这一派也讲阴阳问题,可能是儒家最早重视阴阳问题的学派。
康有为《论语注》谓:
曾子之学守约,治身笃谨,然其弟子宗旨学识狭隘。
但他又说:
“曾子得成就为游大派,结弘毅之功,力宣饲孔道为己任也。
……曾子盖能行而后言者,虽守约,亦可法矣。
”“儒简”中,《尊德义》有孔子语而未称引引孔子:
“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此在《孟子·公孙丑上》则明确称引孔子。
其所以有孔子语而未称引孔子,有学者认为此篇乃孔子自作,此说确否?
备考。
同理,《穷达时命》中有一段话亦未说明是何人所说,而《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均称为“孔子曰”,认为是孔子所言。
《性自命出》中有“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
舞,喜之终也。
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舞,舞斯踊。
踊,愠之终也。
”这段话亦见之于《礼记·檀弓下》,称子游所说(北宋刘敞疑其中有阙文)。
此外,《鲁穆公问子思》、《缁衣》、《五行》等篇则显当与子思有关。
《荀子·非十二子》已隐言子思之学由子游而上溯孔子,这乃是当时儒者较为普遍的看法。
而孔子、子游、子思的思想作品同存于这批楚简中,是否可以说明这批“儒简”主要是子游、子思一派的作品呢?
倘若于此可得肯定性结论,则“儒简”的问世为我们比较真实地了解子游以至思孟之儒的全貌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二)早期儒学的经典。
儒家原典为“六经”。
关于“六经”一词的最早出处,人们常常举出两条材料:
一是《庄子·天运》记好对老聃之言: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
”二是《礼记·经解》依次论列《诗》、《书》、《礼》、《乐》、《春秋》的教化功能,虽未径称这六部书为“经”,然既以“经解”名篇,则亿洂以此六书为“六经”了。
这两条材料,一则明言“六经”、一则隐言“六经”,但学者于此总未能安,原因在于对《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的年代问题不能作出确切考订。
《庄子》“寓言十九”,其说未必可信,且书中各篇亦未必其自著,《天运》篇或系晚出(9),故而“六经”之称自然也就不一定出于庄子了(10)。
不过,这并不足以证明先秦一定不能出现“六经”字样。
[!
--empirenews.page--]《郭店楚墓竹简》中提供了两条新资料,对解决“六经”一词出处问题很有帮助:
其一,《语丛一》说: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1][2][3][4][5][6][7]下一页《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其二,《六德》说:
“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犹犴亡由作也。
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据此两则资料,可以认定至迟在战国初中叶(孟子以前),《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书已为儒者所研习了,并且,这六部书虽然体裁不一,但还是有其共同思想倾向的,即都重视父子、夫妇、兄弟、君臣的伦常关系,故而其时儒者将之称为“经”,是很有可能的。
此外,由这两则资料看,先秦确有《乐经》存在,至于其至汉代亡失,当以古文经学家毁于秦火之说是,而今文经学家关于“乐”只是与《礼》、《诗》相配合的曲而本无文字的说法,似不可取,因为“乐”若只有曲而无文字,如何从中“观”夫妇、父子、君臣的伦常关系?
又何以会有释“乐”的说记一一《礼记·乐记》?
所以,古文经学认为先秦本有《乐记》的看法更为接近历史真实。
“儒简”中《缁衣》一篇除了引用孔子的话之外,例皆引用《诗》、《书》之语。
其中,引用《伊诰》一次、《君牙》一次、《吕刑》三次、《君陈》二次、《祭公之顾命》次、《康诰》一次、《君奭》一次,这些篇名及其内容无疑都应归属于《尚书》原典。
这对了解《尚书》真貌并进而深化《尚书》的研究,显然很有帮助。
譬如,《祭公》篇或称《祭公之顾命》篇,不见于传世今本、古文《尚书》,而见于《逸周书》。
《尚书》本可分“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按《缁衣》引《书》之例,《祭公之顾命》似应属“周书”部分。
祭公,字谋父,为周公之孙,周穆王时以老臣当国。
此篇乃其将死时告诫穆王之辞,是篇很重要的政治文献。
原本列于《尚书》之中,为什么历代学者不将之作为《尚书》的内容呢?
这主要是因为传世本《礼记·缁衣》误将“祭公之顾命”的“祭”隶定为“叶”,变成了“叶公之顾命”;自汉代郑玄至唐代孔颖达,皆因错就错,以“叶”为本字,误注为叶公子高,而叶公子高是春秋末期人,这样就不仅时代相差大远,而且人物的分量亦远远不够,也就有人会去想此篇可能非《尚书》原典的内容了。
又如,仍以《缁衣》引《书》之例,篇中有引《伊诰》之语云:
“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
”《伊诰》本是《尚书》原典中的一篇,应是伊尹结太甲之言。
但传世本《尚书》将“诰”误为“吉”,似乎好像是一位姓伊名吉者所说的话。
大约汉儒发现古文《尚书》有“尹诰”一篇,当时可能并无篇题,汉人见其中有“咸有一德”一语,遂用以篇名;后此篇失传,造作伪《古文尚书》者便从传世《缁衣》中抄撮“惟尹躬及汤,咸肖一德”之语,敷行成篇,这就成了伪《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篇了,盖不知《尚书》原典中“咸有一德”语本出自《伊诰》中。
汉儒已误,造作伪《古文尚书》者误信其说而造假,正露出了造假的破绽。
[!
--empirenews.page--](三)早期儒学的精髓。
由“儒简”来看,早期儒学最富有价值的主要有三端:
一是“大同”说。
此说见于《礼记·礼运》中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孔子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作,是谓大同。
宋儒关于此“大同”说,曾有过番议论。
南宋经学家胡安国著《春秋传》,屡引《礼记·礼运》“天下为公”,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
吕祖谦写信给朱熹表示不同意见,认为《礼运》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自昔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
”(11)此语不仅表明吕氏缺乏见识,而且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弄错了,因为《礼运》篇并未以尧、舜时代为“小康”,而是将之归为“大同”之世,属于“小康”之世的是禹、汤、文、武、周公时代,以今日观之,禹夏时代是私有制的文明国家产生之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分界,此前的“大同”之世是原始公产制时代,以“天下为公”为准则,所以“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选贤与能”。
这曾是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先秦诸子所述不一,但都没有怀疑过。
吕祖谦因见老子、墨子称述尧、舜之世,便认为《礼运》“大同”说是“老聃、点之论”,显然失当。
还是朱熹多少有些识见,他在回复吕氏的信中指出,《礼运》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的“大同”时代、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不仅合乎史实,而且乃孔子本意;并认为“小康”之世像禹、汤、文、武、周公那样的“大贤”即可达到,至于“大同”则如无尧、舜那样具有更大政治智慧的“圣人”出世就难以企及了。
当然,朱子虽有此识见,却并未把“大同”说作为儒学“道统”的内容。
二是“禅让”及“汤武革命”说。
康有为曾揭示“禅让”的意义道:
“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大平大同之民主也。
”(12)“孔子最重禅让,故特托尧、舜。
”(13)“禅让”说是儒家以尧、舜禅让为模式的政治权力转移的主张。
“儒简”中的《唐虞之道》开篇即云:
唐虞之道,(擅)而不传。
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
(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故昔贤仁圣者如此。
“禅让”说在孟子那里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孟子说舜有天下是“天与之,人与之”,又指出:
“天视自我民视,夫听自我民听。
”(14)此处“天”乃虚悬一格,归根到底实则“人与之”,亦即君主的权力是民众给予的,民众具有着选择君主的权力。
这当为中国古代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
此外,儒家又盛称“汤武革命”,认为君主“德不称位”,甚至残虐臣民,臣民即可“革命”,重择新君。
如果说“儒简”中《语丛三》还只是提出臣之于君,“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那末,《孟子·梁惠王下》则记载道:
[!
--empirenews.page--]齐宣王问曰:
“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对曰:
“于传有之。
”曰:
“臣弑其君,可乎?
”曰: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贱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珠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还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15)荀子的看法与之相类,他说:
“世俗之为说者曰:
‘桀、纣之有天下也,汤、武篡而夺之。
’是不然。
……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
桀、纣非失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仪之分,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
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汤、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纣者,民之怨贼也!
”(16)三是贵“情”说。
“儒简”中有《性自命出》一篇。
此篇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精致的心性理论,指出人有自由意志,这与天地间所有生物都有着不同的特点:
“凡人虽有性,心无莫志。
”而此自由意志又自有其特点:
“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
”人的个性在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引物引诱、内心嗜好、时势变迁、传习沿袭、友朋榜样、道义激励、信念策勉等等,因此个性的形成也就会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人毕竟是一种群体性的生物,在群体生活中,要做到共存共生,人类社会便需要一种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此即儒家所说的“道”和“礼”。
但怎样的“道”和“礼”才最能人性,最能使人悦诚服呢?
《性自命出》提出贵“情”说,谓:
道始于情,情合于性。
礼作于情。
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
凡至乐必悲上一页[1][2][3][4][5][6][7]下一页,哭亦悲,皆至其情也。
信,情之方也。
情出于性。
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
凡人,情为可悦也。
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
未言而信,有美有情者也。
在此篇作者看来,合乎“情”的“道”和“礼”就是群体的价值取向,这也便是教育的内容,而教育可以引导个性的健康发展,由自然的可能性走向必然的合理性。
人类社会的政治建立在“情”的基础上,人们自然乐于接受;只要以“情”为基础,即使有失误,也会得到人们的谅解。
反之,不以“情”为基础,即便做出多么了不起的事业,人们也不会觉得如何可贵。
总之,不能离“情”而谈社会政治和社会规范的“道”与“礼”。
这样,“情”就成了衡量是非善恶的展度。
这种思想同后世宋明理学家的“性善情恶”观显然是完全相反的。
上述“大同”说、“禅让”和“汤武革命”说、贵“情”说正是以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等为代表的早期懦学之“道”。
“大同”说的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理想,“禅让”和“汤武革命”说反映了他们的政冶思想,贵“情”说则他们的人生哲学。
这是儒学精髓所在;宋以来儒者不察,妄以出自伪《古文尚书》的“人心惟危,道人下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奉为儒家“道统”的“十六字心传”,又列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二程、朱熹的所谓“道统”授受谱系,实际将儒学精义丧失殆尽。
[!
--empirenews.page--]二、“儒简”与《中庸》自宋儒大力表彰“四书”以来,《中庸》一直在儒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此书究竟成于何时?
是否为子思所作?
其内容究竟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有无后人增饰的成分?
这些至今都还是学者们聚讼不已的问题,而“儒简”的问世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十四篇“儒简”中,目前可以确定并且学界意见对比较一致的子思作品有《缁衣》、《五行》两篇。
《缁衣》出于《子思子》,这在史书上本有明确记载,如《隋书·音乐志上》引沈约之言曰:
“《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
”按:
《子思子》一书,《隋书·经籍志》、《新唐书》、《旧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可见其至少隋唐时尚存。
正因为隋唐时还流传于世,所以唐马总《意林》引《子思子》十余条,其中见于《表记》者一条、见于《缁衣》者两条;《太平御览》引《子思子》,见于《表记》者一条;《文选注》引《子思子》,见于《缁衣》者两条。
“儒简”中《缁衣》既本为《子思子》中之一篇,则《表记》、《坊记》等似亦可判定为出于子思之手。
至于《五行》篇,早在二十余年前马王堆汉墓中就已被发现达,所见者“经”之外还有“说”。
魏启鹏先生曾根据其思想特点定为“战国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庞朴先生则指出文中“仁义礼智圣”即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五行”,揭开了思孟之儒五行说之谜。
(17)但由于马王堆汉墓年代较晚,又缺少更多材料可以分别说明“经”和“说”的年代,故而当时学者往往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多认为是孟子后学的作品,其年代约在战国后期,甚或在西汉初期。
这次出土的楚简《五行》,与帛书《五行》相比,有“经”无“说”,此可见《五行》“经”的部分成书年代更早,很可能是子思的作品。
若将“儒简”中《缁衣》、《表记》、《坊记》与《五行》均看作是子思的作品,则不难发现这两类作品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别:
《缁衣》、《表记》、《坊记》三篇右形式上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论,每章均冠以“子曰”或“子言之”,体例类似《论语》;每篇除了一个基本主题外,往往还涉及较广泛的内容,当属杂记性质。
如《缁衣》篇,依郑玄《礼记目录》:
“名曰《缁衣》者,善其好贤者也。
《缁衣》,郑诗也。
”然其内容实际以讨论君臣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君民关系、交友之道、言行之要等等,“好贤”仅为其中一小部分;《坊记》主要讨论礼、刑对人们鸻的防范,同时涉及祭祀、交往之道等;《表记》主要记录了有关“仁”的议论,还涉及君子持身之道、言行之要、卜筮等。
此外,这论多引《诗》、《书》、《易》、《春秋》,尤以引《诗》为多,其情形与《论语》颇相类。
而《五行》与这三篇有别,主要阐发和论证作者自己的思想观点,当为一篇独立的哲学论文。
全文主要围绕仁义礼智圣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步步展开,层层递进,各段之间具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很少有脱离主题的议论,更无引用“子曰”之处,间或引《诗》也仅限于个别章节,与《缁衣》等动辄“子曰”、且几乎每章多次称引《诗》《书》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五行》更有极高的理论思辨色彩,这与《缁衣》等篇文句简单,多为警句格言形成鲜明反差。
《五行》与《缁衣》等三篇的这种不同,绝非偶然,大约表明子思的思想曾经历过前、后期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前期,他主要祖述孔子之言,这在文献上也有所反映,如《孔丛子·公仪》载:
[!
--empirenews.page--]穆公谓子思曰:
“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
”子思曰:
“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
且君之所疑者何?
”可见,在这阶段,子思常常把自己的言论同乃祖之言混同起来,以致引起人们的怀疑。
而在后期,他则明确而又系统地阐述着自己的思想观点,与前此相比具有很高的理论思辨色彩,这反映出子思的学说思想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耐人寻味的是,《缁衣》等三篇和《五行》篇的不同以及由此透射出来的子思学说思想岁展变化的轨迹,在今本《中庸》中也有着反映。
今本《中庸》上、下部分在文体、内容、思想等方面均有差异,表现出不同的旨趣,极当考究。
其上半部分包括弟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段“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一部分主要记述孔子的言论;除了第十二章外,每章均有“子曰”出现,与《缁衣》等三篇体例相类,属于记言体。
除第二至九章论“中庸”外,第十章记孔子答“子路问强”,第十一至十五章论“君子之道”,第十六至十九章论“鬼神之为德”及舜、文王、武王、周公祭祀宗庙之事,第二十章记孔子答“哀公问政”,可见这部分涉及内容较为广泛,应属于杂记性质,这与《缁衣》等三篇也基本相同。
如果这样的比较性分析可以成立,那末,我们完全有理由将《缁衣》等三篇和今本《中庸》的这上半部分视为子思学说思想发展过程中前一阶段的作品,或者可以说是出于学说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时的子思之手。
今本《中庸》下半部分包括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以下,这部分主要记述的是作者自己的议论,与《五行》篇体例接近,其内容则主要围绕“诚明”思想层层展开,从“天命之谓性”开始,经过“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由“天命”而至“性”、由“尽性”复回至“天道”,俨然是篇内容完整、逻辑谨严的议论文。
除了第二十八章有两处“子曰”外,其余部分均未有“子曰”出现,可见这部分是以直接阐述作者自己学说思想为主。
但第二十八章有“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及“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等文字,这显系后人增入,或许第二十八章本即错简,似可排除不记。
总之,今本《中庸》内部存在着文体上的差异,而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组织在一起整合而为一文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先秦古籍中鲜见其例。
前人性疑今本《中庸》包含两个部分,并非毫无道理。
(18)以上结合“儒简”着重从文本角度略析了今本《中庸》存在着上、下两个部分的差异。
其实,如再从思想内容上做稍有点深度的分析,这种差异依然存在。
今本《中庸》上半部分着力讨论“中庸”,故而不妨即以“中庸”名篇。
关于上一页[1][2][3][4][5][6][7]下一页“中庸”,前人解说不一。
郑玄《礼记目录》曰:
“名为‘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
‘庸’,用也。
”朱喜《中庸章句》引二程语云: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郑玄认为“中庸”即《中庸》第一章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与“已发”的“中和”,而二程则以为“中庸”乃是一种方法;两相比较,郑氏把原来并无直接关系的两个概念硬联系了起来,并不足取,而二程的看法亦多少违背了《中庸》的本义。
那末,“中庸”的本义究竟是什么?
许慎《说文》:
“中,内也;从口、l,上下通。
”这“口、1”,应指礼器一类,有学者释之为“徽帜”、“册簿”或“旗鼓”(19),其说颇通。
古时每逢大事,君主需要祭天,执“中”以通上下,表示“君命神授”,“受命于天”,故而“中”之本义当为沟通天人的礼仪、礼器一类。
由于“礼”在古代社会有神圣崇高的地位,具有无限威力,且又渗透到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思想以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思想、生活、思维与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而在文献中“中”就具有此一含义。
《礼记·仲尼燕居》载:
[!
--empirenews.page--]子贡越席而对曰:
“敢问何以为此‘中’者也?
”子曰:
“礼乎礼!
夫礼所以制中也。
”《荀子·儒效》记: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
曷谓‘中’?
曰:
礼义是也。
”又,《周礼·地官·大司徒》谓:
“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此处“教之中”的“中”指的就是“礼”。
盖君王祭天,民众必自四方而至,久而久之,引申出中心的“中”,象征君位所在,所谓“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
”(20)又引申出“正”义,所谓“允执厥中”(21)、“允执其中”(22)的“中”字,皆表“正”意。
二程以“不偏之谓中”,有一定道理,但“偏”与“不偏”要有个标准,这标准就是“礼”。
至于“庸”,有“常”的意思,《尔雅·释诂上》:
“庸,常也。
”具体指常行、常道。
所以,“中庸”的本义应为“中道”和“常道”,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