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首同归两心知试论刘禹锡与白居易的际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docx
《皓首同归两心知试论刘禹锡与白居易的际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皓首同归两心知试论刘禹锡与白居易的际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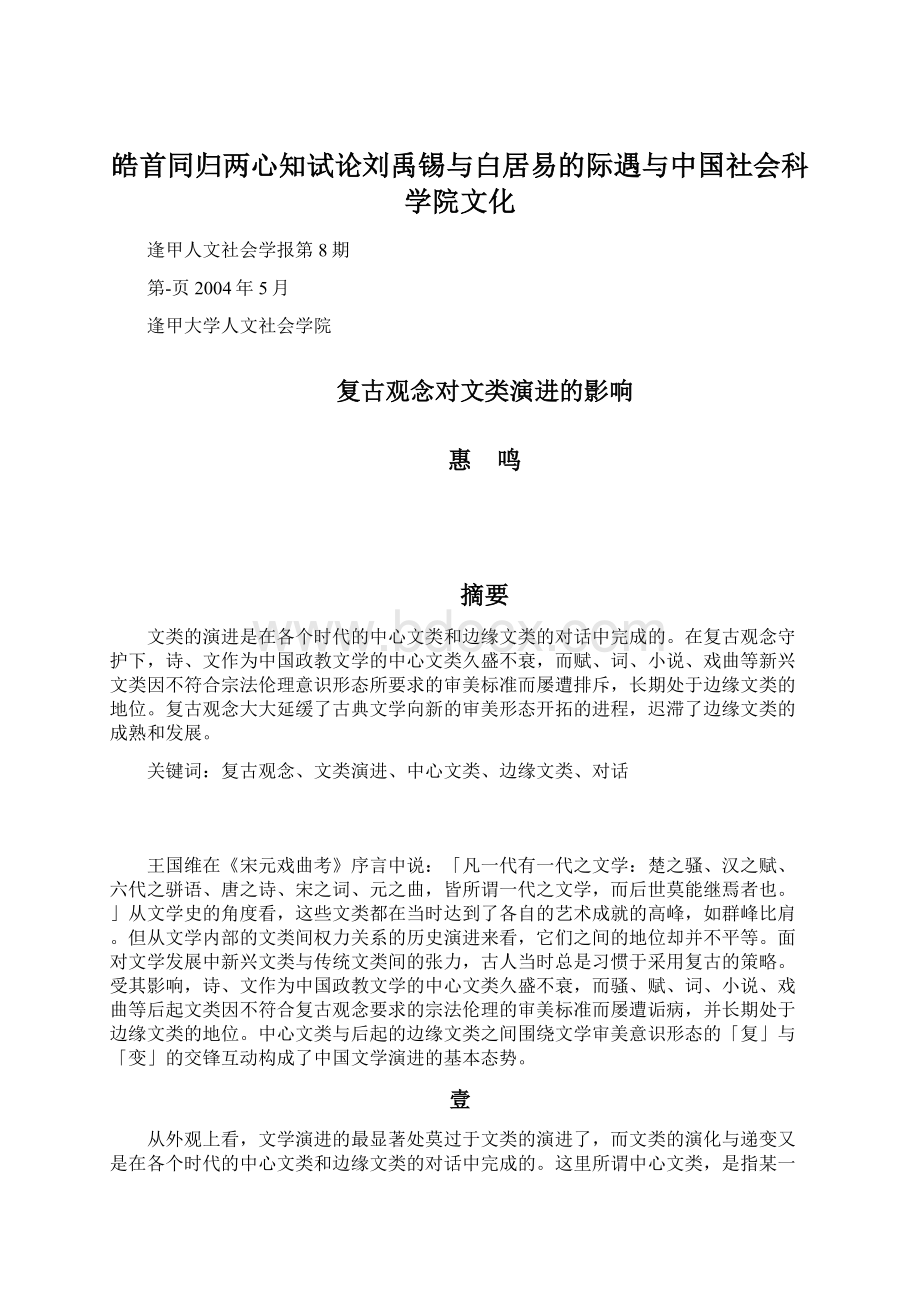
皓首同归两心知试论刘禹锡与白居易的际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
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8期
第-页2004年5月
逢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复古观念对文类演进的影响
惠 鸣
摘要
文类的演进是在各个时代的中心文类和边缘文类的对话中完成的。
在复古观念守护下,诗、文作为中国政教文学的中心文类久盛不衰,而赋、词、小说、戏曲等新兴文类因不符合宗法伦理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审美标准而屡遭排斥,长期处于边缘文类的地位。
复古观念大大延缓了古典文学向新的审美形态开拓的进程,迟滞了边缘文类的成熟和发展。
关键词:
复古观念、文类演进、中心文类、边缘文类、对话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言中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些文类都在当时达到了各自的艺术成就的高峰,如群峰比肩。
但从文学内部的文类间权力关系的历史演进来看,它们之间的地位却并不平等。
面对文学发展中新兴文类与传统文类间的张力,古人当时总是习惯于采用复古的策略。
受其影响,诗、文作为中国政教文学的中心文类久盛不衰,而骚、赋、词、小说、戏曲等后起文类因不符合复古观念要求的宗法伦理的审美标准而屡遭诟病,并长期处于边缘文类的地位。
中心文类与后起的边缘文类之间围绕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复」与「变」的交锋互动构成了中国文学演进的基本态势。
壹
从外观上看,文学演进的最显著处莫过于文类的演进了,而文类的演化与递变又是在各个时代的中心文类和边缘文类的对话中完成的。
这里所谓中心文类,是指某一时期中那些文体己获独立,具有被主流意识形态接受或倡导的相对稳定的审美要素系统,并在创作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文类。
相对于中心文类,边缘文类则是指某一时期那些文体尚未独立,审美要素系统尚未定型,或文体审美观念虽然相对成熟但却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文类,以及那些创作上已经式微的文类。
从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来看,源远流长而又并驾齐驱的诗、文无疑是文学传统中的中心文类。
此处的诗,并非指文学史上某种独立的诗体,而是指肇自《诗经》,下迄唐宋明清的各类古体、律、绝体的这样一种诗的历史流传物;而文则指始于《尚书》、《春秋》、《左传》、先秦诸子,下及唐宋明清的种种骈文、散体文的这样一种文的历史流传物。
诗、文的中心文类地位源于尊经。
《礼记·经解》中关于《诗》教使人「温柔敦厚而不愚」以及《春秋》教使人「属词比事而不乱」的思想奠定了诗、文在中国政教文学中的并尊地位。
由此出发,对诗的要求是「感天地,动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
而对文的要求则逐渐集中于传达圣人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传统文论中所谓「主文而谲谏」、「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种种主张,不过是这种要求的换个说法而已。
诗、文要承担如此神圣的使命,就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诗因而被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文则被要求「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
诗、文的这些美学特征,既是确立自身中心文类地位的依据,又是诗、文与其它边缘文类对话的「话语」特权。
树立诗、文的中心文类地位的「话语」模式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其根据则是封建宗法等级伦理的意识形态。
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断语,奠定了传统政教文学观念以儒家宗法伦理情感作为对诗、文的基本美学要求的根基。
清人黄宗羲说:
「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
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
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情也。
」诗、文作为中心文类,它们的审美标准是排斥个体意识以及个性情感张扬的。
但艺术发展自有内在规律,随着审美意识在艺术——实践活动中的日益自觉与社会生活中个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张扬的个性情感必然要求在中心文类的语言形式、审美观念和新兴边缘文类中表现出来。
这种趋势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心文类的话语权力就会受到来自内部的话语颠覆力量和来自外部的边缘文类的双重挑战。
就中心文类的内部挑战而言,它可以表现为社会风气对中心文类传统审美价值的侵消,如齐梁宫体诗的淫丽对的「思无邪」与「美刺」观念的挑战;可以表现为审美时尚对中心文类话语传统的悖离,如北宋「太学体」僻涩怪诞的文风对「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传统的颠覆;也可以表现为个体意识与宗法伦理意识形态的对峙,如晚明笔记、小品文中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个性展露对中庸品格的反动。
就边缘文类的挑战而言,一方面,文学史上新兴的边缘文类往往起源于民间,带有鲜明的市井俚俗特色,它们通俗率真的乡土气息,大胆无忌的抒情表白,浓艳直白的俚语特色,传奇魔幻的自由想象都与中心文类力求含蓄典雅、浑朴自然的文人化追求相对立。
另一方面,随着新兴边缘文类的审美特征与艺术风格上与时迁变、不断发展,它们不仅会在话语风格和意识形态层面与中心文类相抗衡,而且会在创作上和接受上挑战中心文类的地位。
所有这些都在动摇着《诗》教、《春秋》教的地位。
对于抱持着坚定《诗》教信念的复古家们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复古家们无法忍看诗、文沦落到边缘文类的地位,他们一次次祭起复古大旗,以摧陷清廓、横制颓波的豪情来为诗、文找回失落的位置。
虽然不同时代的复古观念在动机、意向、目标、影响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于维护诗、文的正统地位这点上却并无二致。
抛开复古家们奉为至尊却又各衷其是的诗、文典范,我们将看到,从唐代古文复兴、北宋诗文革新、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到有清一代绵绵不绝的复古思潮,复古家们种种努力的旨归大体不出于恢复与守护诗、文话语的质简与典雅的话语品格这一范畴。
也正是这种质简与典雅的话语品格一次次成功地捍卫了诗、文作为中心文类历久弥坚的「合法」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学史上长期以诗、文为中心文类的基本格局。
然而,这只是复古观念对文类演进的一种影响。
贰
复古观念对中国传统文类演进最显著的影响,是它固执地坚持诗、文所代表的「正统」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迟滞了边缘文类的成熟和发展。
在文学演进中,来自诗、文的审美意识形态压力往往迫使边缘文类修正乃至放弃作为自身审美品格的「本色」话语,转而接受中心文类的审美「话语」。
对于深受传统政教文学观念浸熏的文学家们,是否符合中心文类的话语要求是决定他们对边缘文类的态度的根本标准。
这在赋、词、小说和戏曲的发展中都有体现。
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类,自出现以来,就与其它文类不断渗合,在历史上经历了骚赋、辞赋、骈赋、律赋、文赋的种种文体演变。
两汉四百年间,赋体文学风靡天下,作家众多,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文类。
班固《两都赋·序》中描述西汉后期赋体创作盛况时说:
「故言语待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使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肖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着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锺嵘《诗品·总序》里也说:
「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
从李都尉(陵)迄班婕妤(姬),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失。
」
从文学审美特征而言,汉大赋无疑是汉赋的突出代表,而排铺摛文或可视为汉大赋最为突出的艺术标志。
但终两汉之世,赋体这一艺术标志始终身处「诗」、「骚」以来讽誎传统以及美剌观念的阴影之下。
班固曾言:
「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于《诗》之风谏何异?
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音,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赋家意在讽誎,但排铺摛文的苦心以及正言反出的无奈却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
扬雄对大赋欲「讽」却「劝」的效果分析正体现出赋家的自觉担忧。
在经学思想的影响下,自汉代以来,对赋体的批评就持续不断。
班固对屈原「扬才露已」、「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的责难,扬雄「辞人之赋丽以淫」的指斥,王充对司马相如、扬雄之流「文丽而务巨,言眇趋深」、「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的诘难,王符对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的不屑,刘勰对汉大赋「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规,莫益劝戒」的总结,都体现了正统文学家对诗、文话语权力的自觉捍卫。
可以说,在两汉的大多数时段中,赋体文学风头健盛,从创作与接受的角度而言,都堪称当时的中心文类。
但在两汉强大的经学传统压力下,赋体文学并未取得对其他文类支配性的话语权力。
相反,在经学思想绝对统治下,赋体文学始终处在铺排文采与讽谕规谏的两难选择之中,中心文类的话语权力依然属于先秦以来就已形成的诗、文传统。
在诗、文中心文类立场的支配下,对赋体文学的傲慢与偏见一直传承到清代。
清人程廷祚论骚赋之别时说「且骚之近于诗者,能具恻隐,含风谕。
故观其述谗邪之言,则庸主为之动色;叙流离之苦,则悼夫为之改容;伤公正之陵迟,则义士莫不于邑。
至于赋家,则专于侈丽闳衍之词,不必裁以正道,有助于淫靡之思,无益于劝戒之旨,以其所以短也。
」
词起源于民间,是随着唐五代以来流行于宦家酒宴和青楼歌肆之中的燕乐的兴盛而流行的合乐歌词,本以通俗抒情为特征。
经过词人们长期创作实践,词作为一种新兴文类已在艺术上取得了高度成就,但却不为正统的文学观念认可,被认为是「浪谑游戏之作」,只配做「诗之余」。
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
「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倾刻释卷也。
」词的地位如此,词人的处境也可堪相怜。
著名词人柳永的遭际即为例证:
「虽然他的词为广大市民所喜爱,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可是当时从皇帝、宰相到一般文人学士都以为他是『多游狎邪』的浪子,轻视他『无行』,鄙视他的词俚俗。
宋仁宗申斥过他『浮艳虚华』,不取他为进士;晏殊曾责备他作『彩线慵拈伴伊坐』一类的情词;张先曾讥诮他的早行词『语意颠倒』;苏轼曾责怪秦观沾染柳词作风;李清照曾笑他『语词尘下』;此外,如王灼、黄升、沈伯时等无不诋毁他的词俚俗,王灼甚至说他是『野狐涎之毒』」。
「奉旨填词柳三变」道出的正是这位职业词人的无限悲酸。
从词在宋代发展的轨迹看,由俗趋雅是其基本定式。
苏轼不满柳词的俚俗浅艳,他「以诗入词」的作法固然引来了不少不「协音律」的之类的指责,但却将诗、文言志传统引入历来被正统文人视为「小技」、「末道」、「艳科」的词中,是开拓之举。
这无疑是诗、文中心文类对词的一种「雅化」。
苏轼之后,北宋周邦彦等大晟词人,在创作上明确以去俗求雅为指向。
周邦彦作词,不仅注重制腔造谱,播诸管弦,还讲究文字声律的清浊轻重,力求和谐于口舌。
《四库全书》编者为南宋方千里《和清真词》所作提要说:
「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
所制诸调,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
所谓分刌节度,深契微芒。
」大晟词人万俟咏曾自删词集,以正其「雅」。
南宋一代,词坛虽有东坡遗韵,辛词强音,但词作尚雅,蔚成风气,这从时人词集取名中可见一斑。
施蛰存先生曾指出:
「词既以雅为最高标准,于是周邦彦就成为雅词的典范作家。
《乐府指迷》、《词源》、《词旨》诸书,一致地以『清空雅正』为词的标准风格。
梦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诸词家,皆力避俚俗,务求典雅。
」南宋词人中,姜夔、吴文英是致力「雅词」的突出代表。
姜夔的词历来被公认重音律,崇典雅,情深韵胜,褪尽铅华。
吴文英的词烹练精绽,密丽幽邃,奇思壮彩,令人雕缋满眼。
南宋张炎的《词源》力倡雅正与清空,是周邦彦、姜夔一派词学的重要总结。
就词而言,愈是「雅正」,则取词愈严;愈是「清空」则取径愈窄。
在一味求雅正、崇尚清空的背景下,词的境界难免愈进愈狭,其最终衰落不可避免。
清代「常州词派」首领张惠言在其《词选·序》中主张词和诗一样,要讲求比兴、要有寄托,「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他认为宋亡以后「四百余年」的词家,都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这些看法固然与其经学家的身份有莫大关系,但宋词一味求雅的弊端,亦可从中得到反证。
从宋至清,词的艳俗本色既不能为诗、文中心文类所见容,一味求雅的努力又导致境界局促、失却生机,倒是诗、文本身比兴寄托的传统不时对词进行着渗透。
这就是诗、文中心文类话语权力对于词的影响。
小说作为一种文类,自唐人有意创作传奇就已取得文体独立地位,经过宋代话本的发展,至元代已开始兴盛,在到明清时代,小说从形态和审美情趣上已日趋成熟,不光产生了「三言」「二拍」,「四大小说」这样的不朽之作,而且对自身的艺术特征也有了深刻的认识。
明代绿天馆主人对此有一段妙论:
「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
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尽管如此,但却小说被视为不登大雅。
清末的黄人(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说:
「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明不列于四部。
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
」这正是明清时正统文人与小说间关系的真实写状。
同时,来自诗文中心文类的压力使小说在言情感人的同时也大力宣扬伦常报应、忠孝节义等内容,人们在对小说的接受中普遍也存在着求实心理。
夏志清先生说:
「《三言》中没有一个故事的重要人物没有来历,作者还特地要交代清楚他们是何时何地人,以保证其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他们对虚构的故事不信任表明,他们相信故事和小说不能仅仅作为艺术品而存在:
不论怎样加上寓言的伪装,它们都只有作为真事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它们得负像史书一样教化民众的责任。
」「真事」和「教化民众」正体现了明清人最常用的「补史」和「道德」两种小说接受观念的要旨。
明清小说接受上的「补史」观念的渊源可上溯到汉代。
班固对「小说家」的看法中已流露出对「小说」的「补史」之用的认识。
成书于西晋的《西京杂记》收录西汉流传的逸闻传说、掌故琐事,编辑者葛洪在跋文中明确声称其目的是「以裨《汉书》之阙」。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更将小说看作史乘的分支,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明清人置班、刘之「小说」观念及《西京杂记》与明清白话通俗小说的形态差异于不顾,几乎将求实的「补史」观念看作小说存在的依据。
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把极摹市井人情世故之态,备写闾巷悲欢离合之事的小说称作「正史之余」。
绿天馆主人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
「史统散而小说兴」。
明人胡应麟说:
「小说,子书流也。
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类志传者。
」在这种观念主导下,他认为《柳毅传》这样的传奇「极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
清代蔡元放从「通俗补史」的原则出发,要求小说内容「件件都从经史中来」,「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并认为:
「子弟读了(东周列国志),便如将一部《春秋》、《左传》、《国语》、《国策》都读熟了,岂非快事!
」《四库全书》编纂主持者纪昀沿袭班固以来的「补史」观念,把「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辍辑琐语三类。
他在编录「小说家类」时,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其原则仍为「实录」。
明清人如此看重小说的「补史」功能,其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让小说承当起「言志」的诗,「载道」的文及「通鉴」的史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价值范导作用。
这一点,在风行明清的另一种立足于「道德」教化的小说接受模式中体现尤为突出。
明代「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序》申明小说具有「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的功用,《警世通言》一篇小说的「入话」则说:
「语必通俗方远传,语必关风始动人」,简洁明快地道出了「道德」批评模式的全部旨趣。
「道德」批评的观念如此深厚,以致以思想激进而名的李贽在点评小说时也离不开这一思维模式。
李贽明确表示,自己点评《水浒传》的全部目的,在于给「有国者」、「贤宰相」、「兵部」、「督府」们指出一条扭转当时社会「小德投大德,小贤役大贤」的不合理秩序的道路。
「补史」和「道德」的小说接受观念固然为古典小说中写实品格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但它们共同的反「造作」、「添造」特色却使小说发展悖离了早期的「传奇」色彩,向史退化,成为道德宣教的工具,更有不少小说因道德教化的关系屡屡遭禁。
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古典小说文类演进的特色。
晚清维新人士在「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下,发出了以革新小说来革新国民精神的呐喊: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虽然维新派对小说「新民」的期望值未免过高,但其与封建正统文学的小说观念彻底决裂的决心正反映出他们的深恶痛绝。
戏曲的命运并不比小说好。
元杂剧本以俚俗为本色,但最后走入宫廷,一味迎合风雅,归于消亡。
在元杂剧兴起的同时,统治者曾颁布了一系列有针对的禁令,尽管此后禁令由严厉趋向宽松,但戏曲始终是被当作有可能产生有害作用而须加防范的娱乐活动看待的。
明洪武三年,诏天下立学,明经取士,明确将出身倡优之家者排除于科考生员之外。
明初的亲王朱权热衷于杂剧,但也只将其视为一项娱乐,认为杂剧之作是「良家之子,有通于音律者,又生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
」文人也把戏曲看作「小技末道」。
明人何良俊说:
「祖宗开国,尊崇儒术。
士大夫耻留心曲词。
杂剧与旧戏文本皆不传,世人不得尽见。
」即便到了「临川四梦」享誉天下的时候,还有人对汤显祖表示惋惜:
「张新建相国偿语汤临川曰:
‘以君之辩才,推尘而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
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
’」虽然戏曲受到如此歧视,但其自身「感人也速」的特点却使它和小说一样,被迫担起成俗化教的作用。
清代梁清远《雕丘杂录》载: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
或亦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洪武三十年律令规定:
「几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粉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朱元璋曾对以「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为创作原则的《琵琶记》大加赞赏:
「《五经》、《四书》在民间譬诸五谷,不可无;此传乃珍馐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也」。
在这种情况下,明清虽有像《西厢记》、《牡丹亭》等不少为至情至真而发的作品,但主流却附比风化,出现《五伦全备记》、《香囊记》这样毫无趣味的道学说教戏也并不足怪了。
探讨戏曲的发展,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便是关于「本色」的争论。
这场贯穿明清,几乎所有知名剧作家与剧论家都卷入其中的关于曲词风格的讨论冲击了笼罩剧坛的浓烈的八股时文气息,力图使戏曲语言向舞台性和通俗性靠拢,但最终却在对非「雅」亦非「俗」的「俊语」的追求中走上了文人化方向。
这一点,只要看到明清人对本色的讨论无一不从文人剧作中寻求规范就足以明了:
明清人对本色的讨论南戏取《琵琶记》、杂剧标《西厢记》,皆为文人气质浓郁的作品,而对真正的民间草根戏作,却鄙薄视之。
从比附教化到文人化品格的追求,中心文类巧妙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追求转嫁给一种本是要体现新的审美追求的艺术形式,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成为舞台的主角时,当忠孝节义化风成俗成为戏曲的唯一使命时,中国古典戏曲实质上已沦为一种最为行之有效的愚民工具。
事实上,元明以来,戏曲已是目不识丁的黎民百姓接受伦理教化最的直接途径之一。
晚清维新派一味寄厚望于「新小说」去「新一国之民」,而对更为效果更显见的「新戏曲」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就显得实在不够高明了。
参
从最初的「诗言志」至清代,古典政教诗学的审美观念历经了「吟咏性情」(诗大序),「诗缘情而绮靡」(陆机),「干之以风以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锺嵘),「诗有三境」(王昌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王士桢)等不同认识过程,其演化轨迹正是通向「诗情饱满」的审美自觉之途。
但是由于被复古家们竭力守护的政教文学观念始终占据着诗学话语的中心地位,诗学观念的审美自觉只有作为道德价值的补充才能取得主流观念的认可,这样,诗学观念的最终定位自然只能是正统诗教与审美自觉两种观念妥协的产物。
清代诗学堪当古典诗学理论的总结,其代表性观念,如情景说(王夫之)、格调说(沈德潜)、神韵说(王士祯)和肌理说(翁方纲)等,所追求的淡泊中和、清远幽深、心物融一、主「理」重「法」的诗境的本质上乃是封建文士所向往的心性宁静的文人情怀。
这种优雅情怀的背后是代表正统文化的儒家审美教化观念与代表个性解放的新兴世俗化个人情感的「雅」「俗」对峙,是中心文类以自己固执的审美态度、审美标准以「雅」压「俗」、以「雅」化「俗」,对边缘文类中个性解放精神和平民文艺观念进行压抑和匡裁的话语霸权。
晚明浪漫思潮中出现的李贽「童心说」对个性情感的追求在清代的一度销声匿迹、公安三袁「性灵说」主「露」尚「俗」的凌锐之气在清代继承者那里的退化、清代的文化高压都体现了传统的中心文类审美意识形态的自闭与保守。
清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新质对传统文化视域的浸渐,传统文类的审美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变革要求,但由于中心文类的审美观念依然保持着强大的自闭力量,导致文体变革的尝试表现出鼠首两端的格局:
既要追求古人之技法、格调与神韵,又要表现对时代精神的关注。
然而这种类似「阐旧邦」与「辅新命」之间的调和是可能的吗?
我们只要看看各种文类努力通变的结果就不难得出结论。
晚清诗歌中本善于抒情的「江西诗派」、「南社派」以及词中的「常州词派」,力图用传统的话语系统和表现技巧来表现外来文明冲击之下危机四起的时代生活,但其原有的表现手法与语言模式已无法准确表达出复杂而新鲜的时代感受,最终只有步入衰亡。
「诗界革命派」欲「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将大量新事物、新名词、新思想纳入诗句,但由于不能打破五、七言句式,终于未能开一代新风。
文中的「桐城派」散文,戏曲中的「北剧派」、「传奇剧派」,其没落也是同样的原因。
二十世纪文论中,俄国形式主义曾深入研究文类交叉渗透现象,尤其强调通俗文类对高雅文类的冲击、渗透与取代。
托马舍夫斯基认为,通俗文艺冲击高雅文艺产生两种结果:
一是高雅体裁完全消失,如颂诗消失于十八世纪,史诗消失于十九世纪;二是低俗体裁向高雅体裁渗透,促成了自身体裁的规范。
中国文学演进中,各种文类围绕「俗」与「雅」、「情」与「理」的交锋正体现了边缘文类对中心文类高雅的话语格调与审美趣味的反复冲击以及中心文类对边缘文类的文体规范化的影响。
虽然新兴的小说、戏曲等边缘文类对传统中心文类诗、文的冲击一再因复古观念的压制而受阻,但在个性解放和民间世俗文化兴起的历史趋势面前,尤其是在异质文明猛烈对撞和社会精神急剧转型的清末,这种压制只会导致边更为剧烈的反弹。
因而,我们看到,在传统中心文类力图保持自身话语风格与审美形态的努力走向失败的同时,一些开拓性的文体创新纷纷抛弃中心文类传统的审美规范与话语要求,为传统文类间权力格局的革命性颠覆进行着切实准备。
晚清兴起的「新文体派」散文,以其语言之自由不拘、情感之放纵不检、语体之明朗活泼,彻底与传统的文的语言风格与审美形态决裂,最终过渡为五四白话散文文体。
此外,「鸳鸯蝴蝶派」小说对近代西方小说观念和表现技巧的借鉴与初步运用,「谴责小说派」对白话的广泛运用,「文明戏派」对西洋近代话剧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移植等,都为五四新文体的创造准备了条件。
在中西文化的急剧磨撞中,传统的中心文类与文学观念最终遭到强烈的质疑与颠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有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王国维以「境界」说修订意境说,其意旨正在使表现喜怒哀乐的「真感情」成为诗歌艺术情感的主体。
五四前夕(1917年),陈独秀明确提出以「三大主义」对传统政教文学进行「革命」: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更以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为楷模,要求新文学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
只有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