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之研究.docx
《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之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之研究.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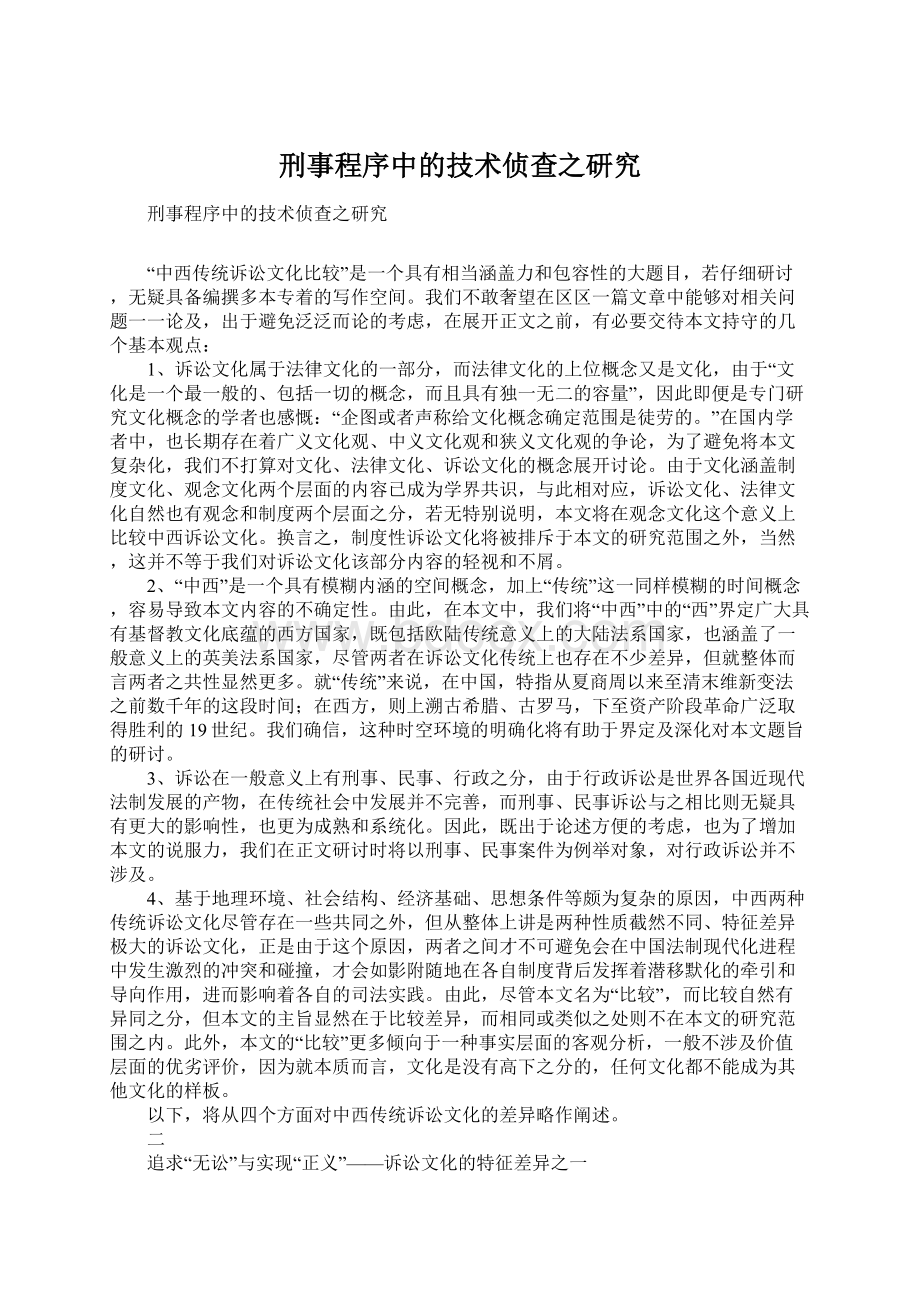
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之研究
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之研究
“中西传统诉讼文化比较”是一个具有相当涵盖力和包容性的大题目,若仔细研讨,无疑具备编撰多本专着的写作空间。
我们不敢奢望在区区一篇文章中能够对相关问题一一论及,出于避免泛泛而论的考虑,在展开正文之前,有必要交待本文持守的几个基本观点:
1、诉讼文化属于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而法律文化的上位概念又是文化,由于“文化是一个最一般的、包括一切的概念,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容量”,因此即便是专门研究文化概念的学者也感慨:
“企图或者声称给文化概念确定范围是徒劳的。
”在国内学者中,也长期存在着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的争论,为了避免将本文复杂化,我们不打算对文化、法律文化、诉讼文化的概念展开讨论。
由于文化涵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两个层面的内容已成为学界共识,与此相对应,诉讼文化、法律文化自然也有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之分,若无特别说明,本文将在观念文化这个意义上比较中西诉讼文化。
换言之,制度性诉讼文化将被排斥于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外,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对诉讼文化该部分内容的轻视和不屑。
2、“中西”是一个具有模糊内涵的空间概念,加上“传统”这一同样模糊的时间概念,容易导致本文内容的不确定性。
由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中西”中的“西”界定广大具有基督教文化底蕴的西方国家,既包括欧陆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涵盖了一般意义上的英美法系国家,尽管两者在诉讼文化传统上也存在不少差异,但就整体而言两者之共性显然更多。
就“传统”来说,在中国,特指从夏商周以来至清末维新变法之前数千年的这段时间;在西方,则上溯古希腊、古罗马,下至资产阶段革命广泛取得胜利的19世纪。
我们确信,这种时空环境的明确化将有助于界定及深化对本文题旨的研讨。
3、诉讼在一般意义上有刑事、民事、行政之分,由于行政诉讼是世界各国近现代法制发展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发展并不完善,而刑事、民事诉讼与之相比则无疑具有更大的影响性,也更为成熟和系统化。
因此,既出于论述方便的考虑,也为了增加本文的说服力,我们在正文研讨时将以刑事、民事案件为例举对象,对行政诉讼并不涉及。
4、基于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思想条件等颇为复杂的原因,中西两种传统诉讼文化尽管存在一些共同之外,但从整体上讲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特征差异极大的诉讼文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者之间才不可避免会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才会如影附随地在各自制度背后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牵引和导向作用,进而影响着各自的司法实践。
由此,尽管本文名为“比较”,而比较自然有异同之分,但本文的主旨显然在于比较差异,而相同或类似之处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此外,本文的“比较”更多倾向于一种事实层面的客观分析,一般不涉及价值层面的优劣评价,因为就本质而言,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任何文化都不能成为其他文化的样板。
以下,将从四个方面对中西传统诉讼文化的差异略作阐述。
二
追求“无讼”与实现“正义”——诉讼文化的特征差异之一
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诉讼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深深影响和制约着司法实践的运作机制和决策程序,比较中西传统诉讼文化的差异首先由此展开。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一言以盖之,即“无讼”。
这一语汇直接来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教诲:
“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
”所谓“无讼”,即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
申言之,诉讼的终极目标或根本出发点在于消灭争诉,其隐含的观念基础在于,争诉是社会的一种恶和不道德行为,理应越少越好。
如《周易。
讼卦》就说:
“讼,终凶”,因此“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无讼”的社会才能理想中的大同世界。
“听讼”是实现“无讼”的一种手段,“无讼”才是“听讼”的最终目的。
儒家创始人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基本诉讼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方面,普通民众普遍养成了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遇到争讼特别是民事争讼,大多依家族家规、风俗习惯由长辈裁断,或通过亲友族邻出面调解说理,不愿告之官府,通过诉讼解决,以致许多巨族大户都以几十年“无字纸入官府”自誉自励,同时还将息讼、无讼的思想记入祖训家法,以规后人。
如安徽黔县南屏叶氏《祖训家风》就明白告之后人:
“族内偶有争端,必先凭劝谕处理,毋得遽兴词讼。
前此我族无一字入公门者,历有年,……族中士庶以舞弄刀笔、出入公门为耻,非公事不见官长。
或语入呈词、讼事则忸怩而不安,诚恐开罪祖先,有忝家风。
”另一方面,劝讼、止讼、息讼也成为中国历代官府、吏史的重要使命和断案宗旨,力图以此实现“完赋役、无讼事”的“天堂世界”,与此相对应诉讼多则常被视为官吏德化不足和政绩不好的表现。
如东汉时吴祜为胶东相时,即“民有争讼者,必先闭合自责,然后断讼,以道譬训喻之,或亲到闾里重相和解。
自是争讼省息,吏人怀而不欺。
”而陈宠则把诉讼的增多看作是吏治败坏的结果,他说:
“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
”隋朝的刘旷在任职期间,“人有争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去”.更有甚者,不少清官循吏还以地方诏告的方式来劝阻诉讼,以实现“无讼”的目的。
如明代的王守仁在《禁省词讼告谕》中明确指出:
“一应小事,各宜念忍,不得辄兴词讼。
……若剖断不公,或有亏枉,方诉申诉,敢有故违,仍前告扰者,定行痛责,仍照例枷号问发,决不轻贷。
”既便是海瑞这样的清官,尽管因断案而出名并因此深受百姓拥戴,但内心深处仍洋溢着“化有讼为无讼”的理想,其在《兴革条例。
吏属》中就写道:
“各衙门日日听讼,迄不能止讼者何?
失其本也。
……今日风俗健讼,若圣贤当于其间,当必须止讼之方,而不徒听讼之为尚也。
”
与中国古代不同,西方传统诉讼文化中诉讼的价值取向在于通过适用法律实现正义。
早在古希腊时期,“法”就与“正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柏拉图的着作《理想国》有一副标题即为“论正义”,主要围绕正义来阐述其法律、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更是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
”到了古罗马时期,自然法思想得以萌芽并发展起来,正义开始被明确视为法的目的和衡量标准。
西塞马就明确指出:
“法是正义与非正义事物之间的界限,是自然与一切最原始的和最古老的事物之间达成的一种契约;它与自然的标准相符并构成了对邪恶予以惩罚,对善良予以扞卫和保障的那些人类法。
”《阿伯特:
犹太智慧书》中更是记载说:
“世界立于三块基石之上:
至理、公正的审判及和睦。
”此时,适用法律的诉讼活动开始被认为是寻求和培植自然正义的活动,法官也被视为正义的传播者。
《学说汇篡》中,对司法官的职责是这样定位的:
“人们有理由称我们为法的司铎,因为我们是在培植正义,并传播善良和公正的知识;区分公正与不公正,区别合法与非法;我们希望在教导人们行善时不仅借助刑罚的威吓,而且也利用奖赏的鼓励;我们追求的是真正的哲理,而不是虚伪的哲理。
”
到了中世纪时期,神学思想统揽一切,法学也成为神学体系的一个分支,被奥古斯丁、伊西多、托马斯。
阿奎那等神学政治家以上帝的名义重新加以检视。
此时,正义成了上帝的一种意志,它通过永恒法、自然法和神法所体现出的理性为人定法的制定和执行指明了方向。
正如休斯勒指出的那样,翻开中世纪日尔曼的法律典籍,其同篇驰骋的观点是:
法——“人们对上帝所创造的公正和整理的一种追求。
”与此相对应,法官的职责就是依据理心和良心原则作出的裁判,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客观真实性。
由此,不论是宗教法庭,还是世俗法庭,适用法律的诉讼活动仍然被视为寻求正义的活动,只不过此时的“正义”已打上了神的烙印,成为上帝意志的体现。
到16世纪的时候,罗马法复兴运动带来了法律的重新世俗化,以格劳秀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摆脱了“神示正义”的束缚,赋予“法”以新的涵义,将其与公平、正义、人的理性等联系起来。
如格劳秀斯就将法定义为:
“一种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必要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
”继古典自然法学派之后兴起的历史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同样将正义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是前者视正义为民族传统和习惯中体现出的人民意志,后者一般以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诠释正义。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法治国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诉讼作为人民实现正义的方法和手段也逐渐被广泛认可,上至政治更迭、官员选举,下至财产纠纷、交通肇事等,人们都愿意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以此求得一个“说法”。
“程序化”与“非程序化”——诉讼文化的特征差异之二
立法和诉讼实践中对程序的认识与看法构成传统诉讼文化的重要内容,正是这一点上,中西方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中国古代社会法典中,不仅“民刑不分”,而且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没有截然的区别,由此导致了人们诉讼程序观的淡漠及司法实践中对程序的肆意违反和粗暴践踏。
这种传统诉讼文化非程序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人们对诉讼的认识带有非程序化的特点。
如前所述,由于深受儒家“非讼”思想的影响,诉讼在本质上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自然应当越少越好,由此导致了家族内部裁判、民间调解等非讼争端解决方式在中国古代的盛行,以致于成为传统社会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
其次,表现为中国古代诉讼程序的非体系化、单一化。
中国传统法律的法典化起源于战国时期魏司寇李悝“集诸国刑典”而作的《法经》。
《法经》共六篇:
《盗》、《贼》、《囚》、《捕》、《杂》、《具》。
其中《囚》、《捕》两篇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
这种编制体例,“既以刑法为主,又包含了诉讼法、行政法的内容,可以说开了后世‘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典体例的先河”。
此后,从秦汉直至唐汉元明清,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都是较为零散地分布于历朝各代的法典,这种“诉讼断狱附见刑律”的结构不仅未与以刑法为主的实体法区分开来,单成体系,而且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混为一体,殊难区别。
再次,表现为中国古代诉讼实践中从未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职业阶层。
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从未出现过与“行政”相对应的“司法”,“司法”只是“行政”的诸多职能之一,因而传统社会中既不存在专门化的司法系统,也没有形成职业化的司法队伍。
在历代统治者看来,审理案件,裁断纠纷只是行政长官治理社会的方式之一,诉讼运作更多讲究情、礼、法的统一,不需要专门的技能,自然也排斥一个与行政长官分享权力的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
因此,尽管早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世代相传专习法律的人才,也有不少熟谙注释的律学大家,且这种现象历朝历代都不罕见,但终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即便是明清两代相当盛行的“刑名幕友”,也始终只能藏在幕后为人作嫁衣,无法名正言顺地主持诉讼;至于当时与之齐名的“诉师”,则地位更加悲惨,不仅为世人所贱视和不屑,而且由于法律的严加限制,难以正常参加诉讼,当然也谈不上形成制衡国家权力的法律共同体了。
这种法律职业阶层阙如是中国古代诉讼非程序化的重要表象之一。
最后,表现为中国古代诉讼运作的非程序化。
由于中国古代诉讼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加之系统化程序规则的缺乏与粗糙化,导致司法实践中诉讼运作的个别化色彩浓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同朝代的官吏,断案方式与审判程序是不大一样的,既便是同一朝代,不同的官吏常常在审理案件时也具有不同的风格与特点。
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共通的,即历代官吏在裁断案件时往往不重视程序的规范性与正当性,非程序化现象严重。
如清代康熙年间,陆陇其任某地知县时,有兄弟二人因财产争讼状至县衙。
这位知县开庭时既不询问案件,也不调查证据,更“不言其产之如何分配,及谁曲谁直”,“但令兄弟相呼”,结果“此唤弟弟,彼唤哥哥,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自愿息讼”。
由此可见,在“息讼”“无讼”的价值取向下,司法官员关心的只是如何以宗法伦理来劝诱当事人,以减少或消除诉讼,此时程序本身自然已没有多大的价值了。
与中国古代不同,西方国家在古代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一直比较重视程序的价值和作用,由此形成了自己传统诉讼文化特色。
首先,如前所述,在西方,诉讼被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一种手段。
由此,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人们对于生活中发生的矛盾和纠纷,愿意求助于诉讼加以解决,这就客观上导致对程序的重视及程序立法的发达化。
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诉讼就已区分为公诉与私诉两种。
古罗马时的公诉是指任何人都有权告发,对有关损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查,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个人案件的审查,这种分类已经具备了现代诉讼形态中公诉与自诉的雏形。
此外,在古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私诉程序还先后呈现出法定诉讼,程式诉讼、特别诉讼等三种不同的形态。
古希腊也根据案件性质不同,形成了由不同陪审法庭审理的诉讼制度。
这种细密精致的分工既显示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立法技术的高超,也反映了当时对诉讼程序规范化的重视。
公元533年颁布施行的《法学阶梯》是当时古罗马的钦定教科书,并具有法律效力,该书在“人法”、“物法”后单列“诉讼法”的目次,由此可见当时诉讼程序的发达程度。
到了中世纪教会立法时,诉讼程序已经非常严密发达,如证人必须进行宣誓、允许代理人参加诉讼、诉讼程序分为“庄重的和正式”的与“简易的和衡平”的两种、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原则断案等为现代诉讼制度所广泛采用的做法已经程序化、规范化了。
其次,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中独立的法律职业阶层已经形成并得以延续。
考察西方法制史,我们会发现,与中国古代不同,西方很早就形成了特定的法律职业阶层,且数千年来延绵不断,持续至今。
早在古罗马时期,便活跃着一群职业法学家,他们通过解答法律问题、指导诉讼、撰写契据、注释与编辑罗马法的各种渊源、着书立说,极大地推动和影响着罗马法的发展。
特别指出的是,许多法学家还通过担任“辩护士”或“辩论家”这一类似现代律师的角色参加诉讼,推动着古罗马诉讼程序的精密化与发达化。
基督教出现并盛行后,僧侣由于受教育程度高,逐渐掌握并垄断了对法律的解释与传播,开始形成新的法律职业阶层,这一法律群体对教会法的发展与完善功不可没,他们通过召开宗教会议、诠释《圣经》与教皇的敕令、编撰教会法典、着书立说、传习法律,极大地推动了教会法的发展。
此外,中世纪法学高等教育的盛行也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从最早成立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开始,法学就是与神学并列的大学必修课程之一,许多法律学家在此授课、开展研究,丰富与发展了包括诉讼法在内的法学体系。
如中世纪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并被广泛适用的《格拉蒂安教令集》就是由波伦亚大学教师约翰。
格拉蒂安于1139年——1141年间编撰的,该法典即包含了大量有关诉讼法的内容。
再次,西方古代诉讼运作很早就有了程序化、正规化的特点。
如上已述,早在古罗马期,便出现了辩护士,诉讼运作依案件性质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程序,表现出很高的规范性。
古希腊也是如此,着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因“渎神罪”被判处死刑,就是通过当时盛行的陪审法庭投票裁决完成的,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不仅有辩论权,而且还可以与有关证人进行对质,这些都显示了当时诉讼程序已经相当严密、发达。
即便是进入中世纪,教会法庭审理案件也比较重视诉讼的规范化运作。
事实上,按照龙宗智教授的观点,《圣经》本身就是一部刑事诉讼法的教科书,而从摩西十诫中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到《旧约。
申命记》中的“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单凭一个人的口作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才可定案”,无一不折射出现代诉讼文明的理性之光。
即便是过于呆板、机械而备受后人诟病的证据法定主义,在当时对限制法官的司法专断、促进事实真相的查明、统一办案规格、保证程序的规范运作无疑也具有相当积极的价值。
在较少受到教会法影响的中世纪英格兰法律体系与司法实践中,也比较重视程序的规范运作。
早在亨利六世时代,大法官福蒂斯丘爵士即主张应赋予法律职业以神秘性,主张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的特殊科学。
中世纪时,司法权当时尽管依然受制于国王,但国王往往只能在特殊的场合“因要人和大案”才行使司法职能。
即便这样,国王对司法的干预也往往受到法官以专业为由的反对,如在1612年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争论中,柯克便指出,法律是一门“人为理性”,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时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由此,尽管国王在普通法上被视为“一国之父”,但其权力仍应受普通法基本原则和法定程序的限制,以防止其剥夺或侵害任何人的天赋人权。
伦理性与宗教性——诉讼文化的特征差异之三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而西方传统诉讼文化又深深打上了宗教性的烙印,这是两大诉讼文化的又一重要区别。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伦理性,也有学者称之为“诉讼的道德化”,是指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指导思想,同时人们对诉讼的认识又深深渗透着儒家的伦理精神。
在中国古代的青铜时代,法与宗教、伦理不分,“天罚神判”成为统治者进行诉讼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进入周朝,“神明裁判”逐渐退出诉讼领域,法律与宗教开始分离,法律有了独立的发展。
到了秦统天下后,法家思想成了诉讼的指导原则。
中国传统法律包括诉讼法律伦理化的进程,按照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大致始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在家、独尊儒术”,完成于唐律的诞生,前后长达七个半世纪,其间可以粗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汉代,这是伦理化的初始阶段,此时儒家伦理对法律与诉讼实践的影响和改造只能通过“引经决狱”和研习律学、解释法律这种侧面迂回的方式来实现。
第二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立法和诉讼实践伦理化不断深入的阶段,此时众多儒家伦理道德直接全面地贯彻、渗透到法律中去。
第三阶段是隋唐时期,立法与司法的伦理化全面完成,儒家的宗法伦理已全面渗透进法律之中。
就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伦理性的表征来说,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表现在对“诉讼”的认识上。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无论是普遍民众,还是清官廉吏,从观念上都视“诉讼”为一种恶,一种不道德、不光彩的行为,因此诉讼的目的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裁断纠纷,而是为了实现“无讼”,为了“明刑弼教”,这种在诉讼正式开始之前已久久萦绕在司法官员和各方当事人心头的道德观念从根本上决定了诉讼运作的伦理化倾向。
二是法典的伦理化。
早在曹魏时期,“八议”开始入律,到《晋律》时确立了“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北魏律》将“官当”制度法律化,《北齐律》又明确规定了“重罪十条”,至《唐律》“一准乎礼”时,法典的儒家化、伦理化已经完成,宋元明清诸律基本上都以“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的《唐律》为蓝本,同时还结合各自实际对其中的伦理化精神作了弘扬,特别是宋明理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法典伦理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和扩张,在有关家庭、婚姻、两性关系等领域达到了十分极端的地步。
三是诉讼实践的伦理化。
《礼记。
王制》很早就指出: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
”东汉初年,大儒董仲舒便创设了“引经决狱”的断案方式,深深影响着当时的诉讼实践,以致于出现了“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年有政议,数遣延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的情况。
此后,这种诉讼运作引经据典的泛道德化现象在中国古代司法中屡见不鲜,已成为常态,以至于有人说,古代司法官办案的第一原则就是:
“人有争讼,必谕以理,启其良心,俾悟而上。
”因为历代统治者均奉信“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与中国传统世俗政权的强大和占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对佛、道等宗教思想的强烈排斥而导致中国传统诉讼文化非宗教性不同,西方各国由于其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导致其诉讼文化呈现出较强的宗教色彩。
在基督教产生以前,西方法律与原始宗教紧密相联,人们对诉讼的认识也打上了强烈的宗教烙印。
博登海默指出:
“在古希腊的早期,法律和宗教没有多大区别。
……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中,祭司在司法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认为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及权力是宙斯亲自赐予的。
”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罗马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就是一部带着浓厚宗教色彩的法典,除了第十表是“宗教法”外,该法典对诉讼活动的规定许多地方充斥着神明裁判的内容,泰格就此评价道,《十二铜表法》“其特征均在于信赖巫术和宗礼仪,以之作为法律诉讼程序的主要部分和产生义务的手段”.此后,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法中的原始宗教因素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
公元4世纪左右,基督教为罗马皇帝所承认并被立为国教,此后,基督教的思想和理念开始渗透入法,影响着人们对法的认识及诉讼实践活动。
如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学者普遍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法,一种是永恒的自然法,另一种是人定的制定法。
但是,一旦上帝至高无上的观点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来后,便出现了高于人定法、自然法的上帝法。
到了公元5世纪的时候,开始出现了各类教会、宗教会议的教令、教规汇编,较着名的有《罗马的礼仪》、《西斯帕那教会观点汇编》等。
而“《查士丁尼法典》的诞生,标志着基督教在罗马法体系中已占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位置”.此时,在诉讼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宗教机构开始在民事领域获得管辖权,出现了宗教人士担任法官的主教审。
从公元5世纪末期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6世纪初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前,基督教教权及教会法的地位不断上升,直至凌架于世俗法及世俗政权之上,由此开始了神学一统天下的格局。
此时,诉讼实践中一方面“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
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
《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教会中出现了以主教法庭,大主教法庭和教皇法庭为主体的独立的审判机构体系,形成了完整的诉讼程序。
就案件的管辖范围来看,凡涉及教会利益的案件或涉及宗教信仰的民事案件,诸如违反誓言、亵渎神灵、侵犯教会经济利益以及家庭和婚姻案件,甚至一般的刑事和民事契约案件,教会都有管辖权。
至于臭名昭着的宗教裁判所则是专门审理异端案件的教会法庭,它更是建立了一套包括法官任命、案件告发、侦讯、审问、刑讯、判决在内的严密制度,成为人类诉讼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在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时期,教规教义不仅与法律融为一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凌架于世俗法律之上,此时,无论是人们对诉讼活动的认识,还是司法实践,都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16世纪后,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的兴起,教会及教会法逐渐丧失了其显赫地位,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宗教对世俗法律及司法实践的直接干预日益减少。
但是,这并不等于终止了基督教及其教会法对西方法文化的继续影响,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
“被结束的是天主教会的政治和法律统治,而不是作为文化精神现象的基督教;被摧毁和被唾弃的是宗教裁判所,而不是教会法的全部。
因此,基督教和教会法不仅对中世纪而且对近代以后的西方法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表现在诉讼实践中就是诸如法官应当依“理性”和“良心”断案、证人宣誓制度等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做法得以继续沿用。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于一次宗教革命。
封闭性与开放性——诉讼文化的特性差异之四
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诉讼文化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和稳定性,而西方传统诉讼文化则呈现出开放性和不稳定性,这是两者在特征方面的重大差异之一。
封闭性,是指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主流思想与核心内容皆生自本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术语、概念、命题、内容及观念体系,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内发的渐进式特点,受外界的冲击和影响较小。
一方面,这种封闭性表现在诉讼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上。
自从东汉初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孟儒家思想就成为统治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其中蕴含的“无讼”“德主刑辅”“引礼入法”等观念成为千百年来司法活动和诉讼实践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几乎历朝各代都奉为“圭臬”而遵守之,没有太大的变动。
另一方面,作为观念文化对应物的诉讼制度,起于《法经》,形成于秦汉,到唐代《唐律疏议》而臻于完备,以后无论是《宋刑统》、《大元通制》,还是《大明律集解附例》、《大清律例》,几乎没有因朝代更替而发生太大的变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稳定性和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