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docx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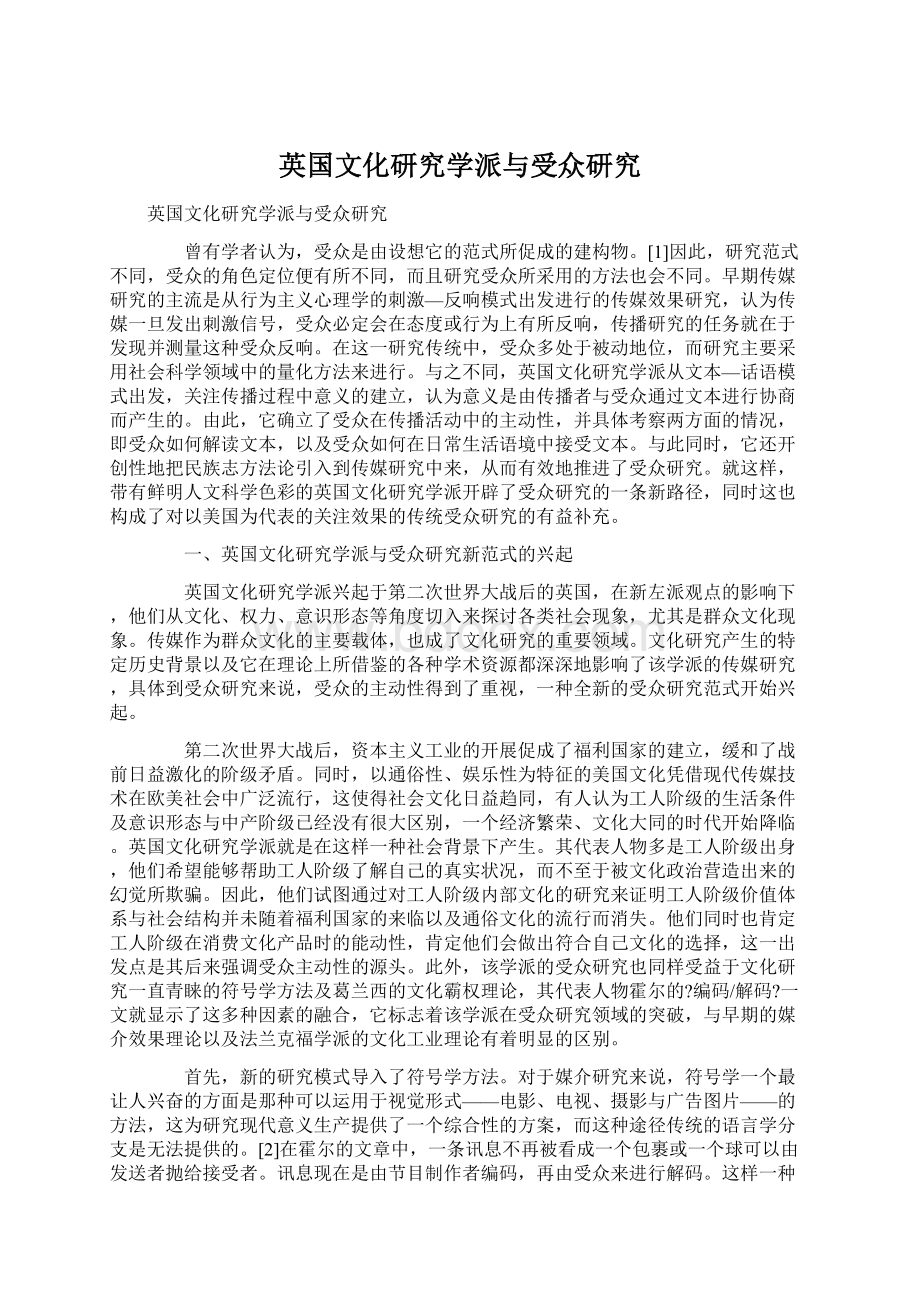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
曾有学者认为,受众是由设想它的范式所促成的建构物。
[1]因此,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会不同。
早期传媒研究的主流是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响模式出发进行的传媒效果研究,认为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响,传播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响。
在这一研究传统中,受众多处于被动地位,而研究主要采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量化方法来进行。
与之不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认为意义是由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文本进行协商而产生的。
由此,它确立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并具体考察两方面的情况,即受众如何解读文本,以及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接受文本。
与此同时,它还开创性地把民族志方法论引入到传媒研究中来,从而有效地推进了受众研究。
就这样,带有鲜明人文科学色彩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开辟了受众研究的一条新路径,同时这也构成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关注效果的传统受众研究的有益补充。
一、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范式的兴起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在新左派观点的影响下,他们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群众文化现象。
传媒作为群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
文化研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它在理论上所借鉴的各种学术资源都深深地影响了该学派的传媒研究,具体到受众研究来说,受众的主动性得到了重视,一种全新的受众研究范式开始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开展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建立,缓和了战前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
同时,以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美国文化凭借现代传媒技术在欧美社会中广泛流行,这使得社会文化日益趋同,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意识形态与中产阶级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大同的时代开始降临。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
其代表人物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真实状况,而不至于被文化政治营造出来的幻觉所欺骗。
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工人阶级价值体系与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福利国家的来临以及通俗文化的流行而消失。
他们同时也肯定工人阶级在消费文化产品时的能动性,肯定他们会做出符合自己文化的选择,这一出发点是其后来强调受众主动性的源头。
此外,该学派的受众研究也同样受益于文化研究一直青睐的符号学方法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代表人物霍尔的?
编码/解码?
一文就显示了这多种因素的融合,它标志着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的突破,与早期的媒介效果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新的研究模式导入了符号学方法。
对于媒介研究来说,符号学一个最让人兴奋的方面是那种可以运用于视觉形式——电影、电视、摄影与广告图片——的方法,这为研究现代意义生产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方案,而这种途径传统的语言学分支是无法提供的。
[2]在霍尔的文章中,一条讯息不再被看成一个包裹或一个球可以由发送者抛给接受者。
讯息现在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再由受众来进行解码。
这样一种观念就意味着发送的讯息和接收的讯息并不一定是同一的,不同的受众可能对节目有不同的解码。
[3]于是,讯息的效果就不再是根据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响模式发生,而是要依赖于受众的解读过程。
由此,霍尔肯定了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它们并不是效果研究所认为的那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
此外,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其所能生产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也就绝对无法化减至一个“最终的〞或“真实的〞意义。
[4]这样,霍尔指出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的解读方式不止一个,并提出受众可以有三种解读立场:
统治—霸权立尝协商立场与对抗立常后两种立场的提出也使得文化研究敞开了受众主动性研究的大门。
其次,对于霍尔来说,该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广泛讨论的一局部,它标志着从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的多元决定论转向了由葛兰西霸权模式所提出的更为复杂的观点。
[5]在此之前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援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暗示,意识形态力量用适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构造主体几乎是无法抵御的。
所以他们认为在以传媒为主要场所的文化工业的操纵下,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入到群众的意识之中,人们成为“文化傀儡〞,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毒害人民的鸦片〞的受害者。
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充分关注受众的诠释活动。
这样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
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
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在霍尔的三种解读模式提出之后,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
20世纪80年代,莫利出版了?
〈全国〉观众?
与?
家庭电视?
,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而伊恩·昂、拉德威以及费斯克也分别对美国肥皂剧?
达拉斯?
的观众、浪漫小说的读者以及群众文化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从这些新型受众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受众的主动性是其最根本的理论观点。
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做的研究都试图反对单向片面的意识形态控制论,希望证明受众的接收活动存在着协商与对抗的创造性空间。
尤其是费斯克,他不仅提出了“语意斗争〞、“文化民主〞等概念,认为受众是才是真正的意义生产者,进而他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开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制造与流通意义和快感的过程。
〞[6]
除此之外,这种新范式还有一些其他特点,据此我们能够把它与强调受众主动性的另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它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认为受众接触媒介后参与了意义的建构;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的使用是一种功能性选择的结果,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传播现象。
其次,它认为解读是支配性意识形态与受众的替代性、对抗性意义之间的斗争,不是受众个人的随机活动,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传媒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博弈的真实情况。
而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是“受众使用媒介而非被媒介所使用。
这种使用有助于产生一种个人身份的认同感,收集信息;此外还能满足休闲的需要并协助社会互动〞。
[7]这样,它高估了受众的主动性、讯息的开放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媒体数量,并不认可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存在。
再次,它借鉴了社会学,把个人看作社会结构的一局部,是包含了许屡次团体与亚文化的复杂类型,这些因素以及解读活动的具体情境会影响人们的解码方式。
而使用与满足理论从考察个人的心理需求出发,从心理层次来解释人们对媒介和讯息的使用。
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在具体操作时又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其一是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其二是将受众置于日常生活语境之中的接受分析。
二、作为文本解读者的受众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将受众作为文本解读者的文本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针对新闻时事类节目,分析受众透过哪些特定的话语来解读文本;二是针对群众文化产品,如肥皂剧等,分析受众如何从文本中获得快感或者是自行建构意义来抵抗原有的社会体系。
1、受众对新闻文本之解读
对于新闻时事类节目,研究者们认定,从一开始它们就扮演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角色,编码者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文本的意义,预设了一个处于优势的或主流的意义。
而这种意义能否成功传播,取决于受众所持有的文化符码是否与节目的符码相一致。
这样,受众到底持什么样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研究者努力想解开的谜团。
最初是霍尔受到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发,将受众视为阶级的产物。
帕金认为西方社会有着三个主要“意义体系〞:
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臣服的价值体系,剧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
[8]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分别拥有不同的“意义体系〞。
霍尔将这一模式引入到传播领域,根据受众的阶级变项推导出对新闻文本的三种解码方式。
在这种观点下,我们甚至可以推断,由于传媒往往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效劳的,这样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一般对文本进行倾向式解读,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往往会因为利益受损而进行对抗式解读。
随后,莫利对BB的晚间新闻节目?
全国?
的观众进行研究,试图对霍尔模式进行经验性的验证并探讨还有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受众的解读活动。
在该研究中,莫利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尽可能的考察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对解码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了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也包括“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附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那么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包括较难设计却十清楚显的个人特质。
二是他不再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而是提出“话语〞的说法,他认为“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该词台湾多译成论述〕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
[9]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
[10]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
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如果说霍尔从统治/协商/对抗模式来理解受众还略显粗糙,那么莫利那么是从话语入手,对它进行了精细化的处理。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莫利也感到困惑,因为形成话语的社会因素过于繁多且不确定,要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无疑是相当困难的。
于是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不再执着于将受众作为多种话语的构建物,不再致力于深究受众话语的组成,而是开始关注受众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游击队员从通俗文化中所获得的快感。
2、受众对通俗文化文本之解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主要参照系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也渐渐脱离阿尔都塞式及葛兰西式的理论话语,开始接受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有着开放、自由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破除了权威话语,颠覆了传统,对许多约定俗成的概念提出质疑。
这为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此时较有特色的是费斯克对群众文化的研究。
费斯克对群众文化的理解受德塞图抵抗理论的影响颇深,后者强调群众作为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可以利用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力机构对他们的限制,自行创造出行为空间。
所以,费斯克认为群众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能够在统治性体制所提供的有限资源中,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用文化商品。
比方,他研究了麦当娜这一流行文化现象。
尽管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为形象根底,处处暴露自己的性征,但是费斯克认为她并不是父系霸权的代言人,并没有教会那些女性崇拜者像男人观看她们那样去看她们自己,并没有怂恿她们作父权制内的女性主体。
他认为在麦当娜的形象中有某些间隙或空缝逃脱了意识形态控制,比方她对宗教象征物〔十字架、念珠〕的随意享用,涂抹过艳的口红,佩戴过量的首饰,都使她从主导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利用其能指而拒绝其所指,并且这也向其歌迷展示了她们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意义。
麦当娜的形象制造让女孩们看到,女性性征能被置于她们的控制之下,能按她们的利益来制造,她们的主体性不必完全由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来决定。
因此,麦当娜的流行是权力与抵抗、意义与反意义、快乐与争夺控制权的复合体。
[11]
总之,在通俗文化研究者那儿,文化是复杂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容易被使用者经常改造,这些使用者在其本性上是文化素材料主动的操纵者。
[12]因此,受众是具有策略的意义生产者,他们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总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述关于新闻时事节目与通俗文化产品的受众研究,是以媒介文本为中心,以受众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