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哈穆德和他的糖萝卜.docx
《麦哈穆德和他的糖萝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麦哈穆德和他的糖萝卜.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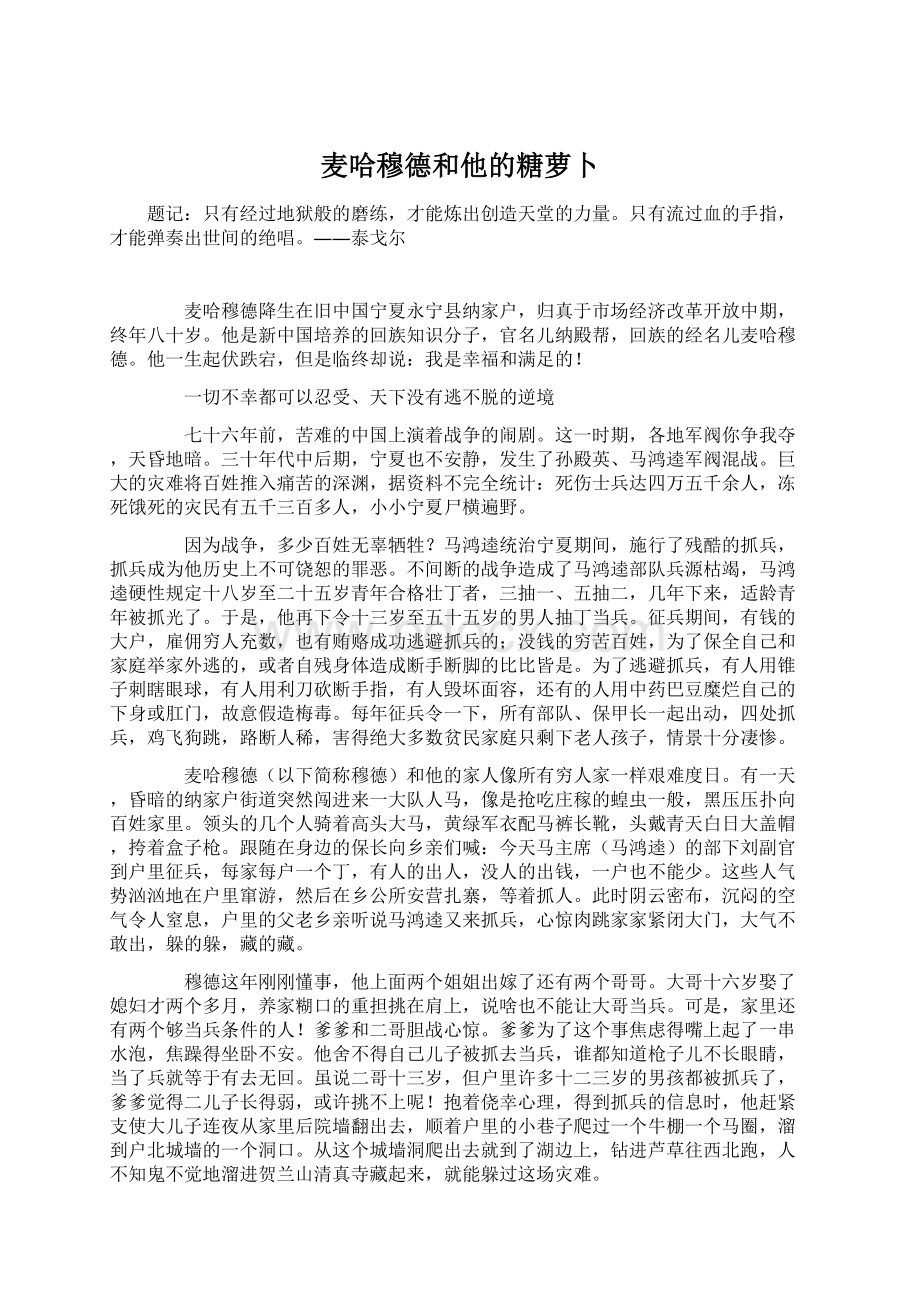
麦哈穆德和他的糖萝卜
题记:
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奏出世间的绝唱。
――泰戈尔
麦哈穆德降生在旧中国宁夏永宁县纳家户,归真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中期,终年八十岁。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回族知识分子,官名儿纳殿帮,回族的经名儿麦哈穆德。
他一生起伏跌宕,但是临终却说:
我是幸福和满足的!
一切不幸都可以忍受、天下没有逃不脱的逆境
七十六年前,苦难的中国上演着战争的闹剧。
这一时期,各地军阀你争我夺,天昏地暗。
三十年代中后期,宁夏也不安静,发生了孙殿英、马鸿逵军阀混战。
巨大的灾难将百姓推入痛苦的深渊,据资料不完全统计:
死伤士兵达四万五千余人,冻死饿死的灾民有五千三百多人,小小宁夏尸横遍野。
因为战争,多少百姓无辜牺牲?
马鸿逵统治宁夏期间,施行了残酷的抓兵,抓兵成为他历史上不可饶恕的罪恶。
不间断的战争造成了马鸿逵部队兵源枯竭,马鸿逵硬性规定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青年合格壮丁者,三抽一、五抽二,几年下来,适龄青年被抓光了。
于是,他再下令十三岁至五十五岁的男人抽丁当兵。
征兵期间,有钱的大户,雇佣穷人充数,也有贿赂成功逃避抓兵的;没钱的穷苦百姓,为了保全自己和家庭举家外逃的,或者自残身体造成断手断脚的比比皆是。
为了逃避抓兵,有人用锥子刺瞎眼球,有人用利刀砍断手指,有人毁坏面容,还有的人用中药巴豆糜烂自己的下身或肛门,故意假造梅毒。
每年征兵令一下,所有部队、保甲长一起出动,四处抓兵,鸡飞狗跳,路断人稀,害得绝大多数贫民家庭只剩下老人孩子,情景十分凄惨。
麦哈穆德(以下简称穆德)和他的家人像所有穷人家一样艰难度日。
有一天,昏暗的纳家户街道突然闯进来一大队人马,像是抢吃庄稼的蝗虫一般,黑压压扑向百姓家里。
领头的几个人骑着高头大马,黄绿军衣配马裤长靴,头戴青天白日大盖帽,挎着盒子枪。
跟随在身边的保长向乡亲们喊:
今天马主席(马鸿逵)的部下刘副官到户里征兵,每家每户一个丁,有人的出人,没人的出钱,一户也不能少。
这些人气势汹汹地在户里窜游,然后在乡公所安营扎寨,等着抓人。
此时阴云密布,沉闷的空气令人窒息,户里的父老乡亲听说马鸿逵又来抓兵,心惊肉跳家家紧闭大门,大气不敢出,躲的躲,藏的藏。
穆德这年刚刚懂事,他上面两个姐姐出嫁了还有两个哥哥。
大哥十六岁娶了媳妇才两个多月,养家糊口的重担挑在肩上,说啥也不能让大哥当兵。
可是,家里还有两个够当兵条件的人!
爹爹和二哥胆战心惊。
爹爹为了这个事焦虑得嘴上起了一串水泡,焦躁得坐卧不安。
他舍不得自己儿子被抓去当兵,谁都知道枪子儿不长眼睛,当了兵就等于有去无回。
虽说二哥十三岁,但户里许多十二三岁的男孩都被抓兵了,爹爹觉得二儿子长得弱,或许挑不上呢!
抱着侥幸心理,得到抓兵的信息时,他赶紧支使大儿子连夜从家里后院墙翻出去,顺着户里的小巷子爬过一个牛棚一个马圈,溜到户北城墙的一个洞口。
从这个城墙洞爬出去就到了湖边上,钻进芦草往西北跑,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进贺兰山清真寺藏起来,就能躲过这场灾难。
很快,保甲长带着马匪兵进屋了,没有抓到穆德的大哥,扑了空,气急败坏地将穆德爹一顿暴打命他顶兵,粗暴地连推带搡押他往乡公所走。
穆德爹目睹老老少少不少乡邻被抓来押往一个方向,想找机会溜掉,可到处是马匪兵的岗哨,怎么也溜不掉。
走着走着,他突然看见一个小满拉左手提刀右手提鸡对面走来,他奋力挣开马匪兵的手,抢到小满拉跟前夺过菜刀,马匪兵以为他想杀人,呼叫着吓得四散躲在墙角边,准备开枪射击。
说时迟那时快,穆德爹大喊一声蹲在地上:
狗日的,老子就是不当兵!
话起刀落,咔嚓一声,将自己右手两个指头剁下来,顿时鲜血流淌。
马匪兵们惊呆了,过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扑上去把他摁住。
穆德爹半卧在地上抱着自己的手,疼得面色苍白,衰弱不支。
马匪兵连提带拉把他带到乡公所骂道:
囊孙日的,想找死没那么便宜!
老子今天必须从你家带走一个人!
这时,他的二儿子跑进来,见到父亲滴血的手,立即嚎哭道:
爹呀爹!
咋剁手呀,儿子替你当兵就行啦!
在场一个副官抽着烟咪斜着眼盯住瘦弱的少年问:
不是家有三个男儿吗?
把大的呼来就饶了你。
说着命人把少年捆绑起来,放了残废的穆德爹。
几个马匪兵跟保长逼着少年敲开了家门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了更小的穆德。
显然,这家抓不到第二个人了。
这时乡公所里已抓了不少年轻人。
有几家交不出人的,爹妈都被抓来捆绑在树上,马匪兵们用皮鞭挨个打他们,衣服打破了,肉被打烂了,马匪逼着他们交人。
几天后,纳家户能抓的人都被抓走了,总算平静了下来,各家各户仍然惊恐地闭门不出。
大部分男人包括男孩子被抓走了,户里的人家为失去亲人哀哀地痛哭,再也听不见年轻人嬉笑声了。
傍晚,家家户户早早熄灭了油灯,被黑暗和悲愤凄惨笼罩着。
夜,死一样寂静,只有乌鸦不时地拍打着翅膀,哇哇地叫唤,野猫发出像孩子般的惨哭。
穆德二哥被抓兵后,大哥始终没有音讯,爹爹又气又急,手伤越来越重,兵荒马乱得不到及时治疗,手指感染化脓整条胳膊都变得肿胀溃烂,没过几天活活痛死了,终年五十四岁。
穆德爹无常后,穆德妈伤心绝望,十分想念不知死活的两个儿子,他无法找到大儿子,便千方百计打听到了二儿子的当兵地址,背上馍步行三十里路赶到军营看儿子。
军营不让她进去,她痴痴地等了大半天,终于等到儿子军训出现在操场上。
人群里她很快认出了穿着军服的儿子,隔着铁丝网大喊儿子的名字,儿子仿佛听见了掉回头寻她,被带兵的狠狠踢了几脚。
她这一来回六十里路,仅仅远远地看了儿子几眼。
回来的时候她走得费劲,走得无比辛苦,又冻又饿过于劳累,到家后发烧打摆子,半个月撇下幼小的穆德和十五岁的儿媳咽下最后一口气。
当穆德的大哥为躲避抓兵藏了一段日子跑回家来,刚刚上了纳闸桥已经有人告知他父母双亡的噩耗,他失魂落魄地往回跑,推开破旧的柴门,看见媳妇和不到十岁的穆德蜷缩于灰暗的炉灶旁瑟瑟发抖。
穆德大哥不到十七岁,可此刻,算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必须承担养家的重任。
日子极为贫困。
穆德和哥嫂每天只能吃一顿主粮,多是赊借来的,那是杂米和萝卜做的稀饭,干重活需要加一个高粱面或麸子面馍馍增加耐性。
麸子吃时间长了肚胀拉不下屎,人很痛苦。
每到春季,青黄不接,用野菜当主食。
荠菜、马齿苋、灰灰菜、扫帚苗……每天是一锅绿水。
嫂子把几种野菜和在一起撒把盐放一把粗面粉,已经是最好的饭食了!
不吃粮食容易饿,外面风一吹,腿软得打颤。
太阳出来时,嫂子带着穆德找野菜,附近的野菜都被挖光了!
旷野上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
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变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叔嫂便跑到很远的地方采野菜。
苦苦菜、甜苦菜、车前草、娃娃菜,见什么挖什么。
苦难像乌云,远望墨黑一片,身临其境不过是灰色
苦难的年景慢慢有了改变,二哥把当兵积攒的一点军晌钱寄来补贴家用。
土灶里的柴火又闹腾起来,柴火噼啪噼啪地脆响,铁锅里飘出饭香气,有粮食吃了,宅院里还养了鸡。
大哥家添丁加人了,两个小侄子呱呱落地。
穆德十二岁,考入马鸿逵在八里桥办的全公费职业学校。
学校每周安排时间上山打收马莲草、让学生跟着教师实习造币、造麦芽菌、制作酱油、醋等,学校还培训学生做农产品加工方面的事情,做工增强了穆德的工业制造意识。
穆德十四岁那年,大哥把他送到吴忠清真大寺当满拉,读阿文,做礼拜,吃住在清真寺里。
孤苦伶仃的穆德生活在寺里,眼前常常出现父母的身影,有一天做完礼拜,他忧郁的眼神盯着窗外翻飞的燕子自言自语:
燕子在唱歌
有人在播种
那是我爹爹
一个心里只有安拉和庄稼的人
他不分昼夜挥动铁锹、锄头、镰刀
祈求你带来一个好天气
一个适宜播种、抽穗、杨花、收获的好天气
让我爹爹心想事成
萤火虫在飞着
有人在念经
那是我爹爹
天天跪在拜毯上用汤?
j洗涤眼眶尘埃的人
他虔诚地诵读《古兰经》信仰执著
祈求你照亮每一个洁净的时辰
让我爹爹心想事成
穆德蜷缩着瘦弱饥肠辘辘的身体,微闭双眼再次合掌默念,爹妈想得我愁肠,请真主慈悯有信仰的人,带我找到父母藏身的地方。
汲取着来自父母的温暖,穆德心里宽敞了。
其实现实更加阴郁,日本人占领了内蒙包头市,日机隔三差五轰炸兰州和银川。
马鸿逵开始了新一轮的抓兵行动扩充兵力。
又要抽丁了!
穆德和大哥谁去当兵?
大哥的两个孩子幼小,只有穆德去当兵。
少年穆德穿着肥肥的军装在炮火下穿梭。
空气是沉闷的,环境十分险恶。
每遇打仗,同龄孩子死伤无数,穆德不知道是否活到明天?
心里时常充满恐怖,有时候他跟着部队行军,看见那些熟悉的田熟悉的树,树叶虽然是碧绿的,但是院墙弹痕累累。
触目惊心的死人,死马横七竖八躺在路边水边,肿得胖胖的,空气里飘着烂肉,屎尿的臭味,令人掩鼻恶心。
此情此景,穆德总会微闭双眼念一句清真言。
一天太阳下山了,前边吵吵嚷嚷,尘土飞扬,部队还在行进,穆德清楚地感觉自己是苦痛的厌倦的,而此刻他听到一声断喝,穆德,营长叫你快去!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惊慌失措地跑步到营长面前,营长并不说什么,拉他上马一阵疾驰。
待进入一个古老的宅院,院子青砖铺地,瓦房连接,一排六间瓦房四周群厢环抱形成四合院。
穿过三个院子,院子里都是树,树上结着果实,似乎是梨树,枝头沉甸甸地垂下头。
树下栽种着野菊。
进了屋,方砖的地面铺着地毯,似乎是个客屋,两头卷曲锃光瓦亮的案上摆着一色的古董,一面墙挂着古画,一张雕漆方桌两侧的太师椅铺着白色的狐皮。
穆德站在宽大阔绰的屋里发呆,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耀得他眼花头晕。
猛然他又听见一声喝叫:
小子!
把这个盆端出去倒了!
他顺着喝叫跑去,弯腰端盆,一股骚气直冲脑门,满满一盆骚尿。
接着他被使唤着从前院跑到后院,早已经不见了营长的影子,他明白是营长抓差让他干家务的。
他见天给小姐太太端茶倒尿跑杂,早晚铺床叠被,挑水扫院。
穆德不怕干活,他人机灵嘴皮子甜,几天下来营长家眷们喜欢上他,把他留在家里跑腿。
如此一来,反让穆德侥幸躲过战火,避过灾难和饥饿保全了性命。
1945年国共开战,军长马步芳的81军调到固原(驻军在中宁)穆德所在的部队驻扎平凉一带,营长带着家眷调到别处驻扎了。
把穆德交到81军202团特务排。
春天的时候,这个团奉命攻打延安,穆德随部队到达大水坑当夜,弃枪逃跑。
没过半年,穆德糊里糊涂又被抓了兵,这次是接受甘肃团管局训练。
他毕竟当过兵,比招来的其他学员熟悉军队操练那一套,结业后,被提升为上士班长,每月两块银元。
从军不久,他所在连队奉命到甘肃静远征收新兵。
从平凉出发,步行七天到达静远县。
他们前脚一到,当地的乡保长后脚就来了,鞠躬哈腰一脸堆笑围着征兵的班排长转悠,整天像苍蝇一样盯住长官请客送礼笼络关系,无非是为自己亲属开脱抓兵。
征兵的长官不管谁来当兵,只要有钱拿,有肉吃,乡保长抓谁来都行,只要把人头凑够数便大功告成了。
所以,那些当官的,趁着征兵中饱私囊贪婪腐化,找妓女,吸鸦片司空见惯。
到了穆德这帮底层兵士,他们必须完成上司交代的新兵训练任务。
静远收兵后,休整几天,穆德所在部队奉命到甘肃宁定县征兵。
从平凉出发,身背30多斤的行装和枪支,步行20多天到达宁定县(今天的甘肃广河县),住在县里一家车马大店。
走到了马鸿逵、马步芳的根据地,穆德一无所知,却意外认识了一位宁夏金积县小伙马效芳。
老乡相见十分投机,经过马效芳介绍,穆德认识了他的母亲。
老太太四十几岁,白皙干净的脸庞上一双眼睛和蔼而安静,见到穆德宽大的额头刀削似的眉锋高挺的鼻子,身材俊拔,即刻喜欢地眉开眼笑,抓着穆德的手絮叨起来。
穆德获悉老太太16岁嫁入马家,30年未回宁夏了。
在老太太家吃过饭,老太太提议儿子马效芳和穆德结拜为兄弟。
在宁定驻军三个月期间,穆德成了老太太家离不开的客人。
当团管局征兵任务完成开拔的时候,穆德忽然找不见了。
其实,穆德的逃离是老太太的主意,穆德向老太太透露过自己的心思,部队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他对国民党部队深感失望,老太太把穆德悄悄转移到东乡村藏身。
30里路外,穆德藏在老太太的亲戚家住了十天,每天土豆、馓饭、玉米面窝窝头吃得饱饱的。
日子飞快,住在马家两个多月,前方还在打仗,华东的战事吃紧,拜把儿兄弟马效芳应征去青海军事学校培训,接着服役。
穆德被老太太送到青海昆仑中学读书。
次年,临夏和宁定三县十分需要师资,穆德被派去到世那努中心小学当教员。
1949年3月份,共产党在平陕一带战事接连胜利,宁定县时局很乱。
学校基本停课。
兰州解放后,王震的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路过宁定,恶战一天一夜,解放了宁定县,接管了政权。
穆德随着局势的急速变化,成为一个身份混杂的人。
他心情动荡,担心自己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许些年混在旧军阀家里,干妈视他如同己出,他从心里认了她。
可是,共产党来了,他一夜间变成了共产党那边的坏人?
因此胆战心惊的捱日子。
让他没想到的是,穆德一类教职人员被共产党政府整顿一番便重新编制派往各学校任职,穆德还被任了世那努中心小学的校长,他疑惑是共产党政府考验他,即刻召集旧学校的老师们开会,休整教室,通知学生到校上课。
过了两个月,穆德把新学校办得十分出色,获得了新政府的表彰。
很快,他被调回县府教育科工作。
期间,青海省尚未解放,马步芳尚在和共产党顽抗。
当地贵族官僚,有钱的大地主,煽动不明真相的百姓闹事,土匪时隐时现。
1949年9月,宁定县的土匪围困了县城,打了7天的硬仗,被王震一骑兵团从临夏赶来剿灭。
有一天,干妈寻到他,透露土匪要抓他,整一整给共产党办事的人,催促他保命逃往宁夏。
对着困难摇头,就无权在胜利面前点头微笑
1949年10月1日深夜,穆德匆忙整理了行装,骑了一匹快马,揣着干妈做的干粮,趁着月色告别了干妈离开宁定县,跑了一天一夜到达兰州,卖了马儿,他搭乘一辆到宁夏的军车,回到纳家户。
他没有想到,匆匆这一别,他与干妈成为永诀。
穆德历经磨难回到纳家户,二哥已经娶媳妇独门立户。
家乡依然穷困,大哥种田闲暇沿村卖烧馍,有时给驻军磨面。
二哥挑了一个小百货担子,走街串户卖辣面子酿醋过日子。
1950年,穆德考入农校进入中专学习。
学校是省政府办的半工半读学校,吃大锅饭,国家发衣服。
一年的工读生活度过后,他被分配到农研所当练习生,享受供给制,每月发35元津贴费。
1952年农业厅选择根红苗正的青年干部到大学深造,穆德被保送西北大学财务系深造。
大学有助学金,吃小灶,每日四菜一汤,1954年穆德学习期满毕业回原单位工作。
1954年7月穆德回到农研所,被定为技术员,每月工资63元。
这年他与贫农的女儿索福亚结了婚,小日子十分幸福。
每月63元工资养着妻子也资助着妻子的爹妈,一元钱买50个鸡蛋,五毛钱吃一碗羊肉泡馍,穆德感觉富得不得了。
早在农校学习时,穆德学过农产品加工制造,实习过制糖,到农研所工作后,他十分崇拜所长,因为所长是土糖制造专家。
1954年冬天,农研所建起了一个小型制糖作坊,集中所里技术力量制糖。
穆德黑糖做到白糖又试着做冰糖。
1958年是大跃进之年,祖国各地轰轰烈烈办工业。
宁夏糖厂开始筹建。
说起制糖,历史表明,解放前美国人在永宁杨和镇办过糖厂熬过糖满足过回族群众喝糖茶的需要。
因为宁夏的气候干旱,光照充足,土壤松软肥沃,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积累,又是一种在沙地、盐碱地种植的糖原料,所以,甜菜十分适合在宁夏的土地里生长。
正因为上述优良的原料条件,糖厂作为大型企业,于1958年底成立了,可是技术人才非常短缺!
穆德便被推荐上来。
穆德在农化所几年已成长为技术骨干,企业调他来不是让他当官来了,更不是享受!
而是筹建糖厂原料实验站。
穆德招收了第一批工人,开着拖拉机赶着毛驴拉着行李到平吉堡筹建甜菜试验站,即种植糖萝卜。
什么都需要从头做起。
买土地,盖房子,招聘人员,面临的困难比想象得还多。
当穆德带着大队人马站到无边无际的野地里,平吉堡呈现的是无尽的荒凉和凄黯。
荒野散发出清新、潮湿的泥土气息,除了望不穿的莽荡荒凉外,就是叫不破的寂静。
没有房子,先打地窝子铺了麦草住人。
安顿下锅灶解决吃饭,再打草翻整荒地,加班加点脱坯盖房子。
房子墙砌了一半,呼呼的西北风一场接着一场刮,狂风带过一堆堆枯草和干树枝,瞬间,席卷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愤怒,带着沙土迅速掩埋了地铺和锅灶,摧毁了生活的一切。
穆德叫苦不迭,啥他妈的鬼地方!
他诅咒着天气,鼓动工人们勒紧裤带与天斗一斗,不与天斗就被压垮了,难道逃跑吗?
上级交代的任务怎么办?
穆德的煽动像是一声进军号,瞬时铁锹挥舞杈子爬动,车拉人扛忙碌不停,天色由黄变成银灰又变成乳白,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东方吐出了一缕霞光,每人的脸上都挂着汗珠子,蜗居厨房整整齐齐更加稳固地排列到眼前时,穆德开心地笑了。
到平吉堡农场后,生活条件的艰苦超乎穆德想象,为了有效指挥出工收工,穆德在树上绑个喇叭,定点放起床号。
出工是东方红太阳升、收工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天天这两首歌,听得工人们提意见了,要求每周看场电影。
平吉堡距银川较远,不方便放电影,穆德为此跑回去跟厂长恳求,由厂里联系放映队下来每周为大家放电影鼓干劲。
果然,工人情绪大涨。
周末的时候,空气里流动着喜悦的成份。
下午收工,全队人马早早坐在草场上等着观看露天电影。
放什么内容的片子?
职工们竟然头一天就议论不休,有说科教片、打仗片的、也有说故事片、科幻片。
放电影当天,职工们兴奋不已,饭也不做了,啃几口馍,炒了黄豆装进衣袋,早早占了位置等电影。
电影开始了,放《刘巧儿》和《小二黑结婚》那天,银幕的两面全坐着人,有许多抢不到正面的位置只好坐在银幕的反面,人和景都是倒着的,他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边看电影边嘎嘣嘎嘣嚼黄豆,沉浸在电影故事和音乐里。
夜深了,不知不觉蚊子摸来了,平吉堡的蚊子又大又猛,嗡嗡地如同小飞机。
蚊子借着黑夜和空气煽动翅膀攻击人,悄悄俯冲下来对准人的肉皮猛刺一剑,锐利的剑锋透过人的衣服进入毛细管,蚊子贪婪地吸血,吸得飞不动了人还感觉不到,电影把人吸引得忘记了一切。
所以,每看完电影,大多数人都被叮得满身青包红疙瘩,又痒又痛。
但下次看电影,大家已经好了伤疤忘了疼,早把蚊虫叮人那档子事丢到脑后,依然兴趣十足提着板凳看露天电影。
一天中午,穆德一伙人吃过饭去打柴,走到一片草滩,草丛密集高挑,他们看好地方挥刀,不大会儿工夫割了一捆,大约七八十斤。
烧饭取暖全靠柴禾,穆德动员大家再砍点,砍着砍着穆德的刀突然碰上一个东西,以为是块石头,他拨开草一看竟然是个大土蜂窝,说时迟那时快,黑压压的土蜂一下子炸开,嗡的一声朝大家飞来。
穆德忽然意识到什么,大喊快跑!
他下意识用双手护住眼睛,只觉脸和胳膊被铁钉扫过一样剧痛,眼泪立即奔泻而下。
蜂群过后,穆德手上、鼻上、胳膊、嘴上,都被土蜂叮过,其他人也遭到程度不同的袭击。
穆德捂着脸往回跑,途中遇见几位同样中午出来打草的职工,见此状,说被这么多土蜂蜇脸马上肿成面包了,尽快用肥皂水反复冲洗被蜇处。
回屋后他用肥皂洗,头、脸、胳膊到处是泡泡。
蜂蜇过的地方特别疼,那种钻心的痛,尤其鼻子傍边的软骨更痛,火辣辣的,他坐立不安。
奇怪的是一直未肿,一直到吃晚餐,蜂蜇过的地方奇痛无比,饭也不想吃了,头晕眼花,晚上睡觉略感轻些。
由于劳累的挺不住了,他合衣躺下不知不觉睡着了。
笫二天起床痛感顿消,感觉昨晚睡得香、睡得踏实。
一问被蜂蜇过的人,都说怪了!
原来腿疼脖子疼的人都不疼了,全身仿佛有种轻松的感觉。
拿镜子一瞧,被叮的部位,黑色的蜂针深深地扎在里面,听说蜂叮人,可以给人治病消毒,而失去蜂针的蜂也会死,穆德庆幸遇到了神医,他的关节痛从此被治好了。
刚来时,水利条件极差,穆德带着工人打井抽水灌田,人吃的水暂时到附近部队去拉,米面油盐菜所需生活用品从城里往过运。
配置简陋落后,新房砌好时,是两排土坯平房,没等干透,大家就搬了进去。
深秋的时候,100亩荒地下籽种的甜菜即糖萝卜,如纺锤般壮实,大的重约7斤左右,小的也有3斤上下。
糖萝卜三分之二卧在土里,三分之一露于土上,叶簇半直立叶子直径约10厘米,如伞如盖。
田野里,大片大片深绿色的叶子遮盖着的萝卜和地面,就像深海里一只只小帆船。
这是一件足够轰动足够新鲜的话题,原料使糖厂的未来忽然辉煌起来,刺激着建设者们的神经,也鼓励着建设者们的积极性。
糖原料战役初步告捷后,穆德有些得意,他在生产讨论会上慷慨陈词,从制糖讲到糖萝卜的利用价值。
他拉出4000年前国外利用甜菜做饲料的事例,描绘抽取糖汁的糖萝卜,含有牲畜所需的一般营养物质外,还含有胡萝卜素,能补充饲料中的甲种维生素。
他又补充了几个事例,什么古西方利用甜菜做药用,古罗马帝国用甜菜叶子治疗便秘和发烧,用甜菜叶子包裹治疗外伤等等。
他讲得忘乎所以,把生产会变成了演讲堂!
他的宗旨是尽快上马一个饲料加工车间!
与制糖车间平行开工。
他有点书生气也太超前,不知道自己的讲解正刺痛着一个人的耳朵和神经,那人忽然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是生产科长范大胡子。
穆德一直把他理解成多疑而谨小慎微的人。
此刻,范大胡子的脸上充满憎恶,抬起的胳膊颤动了一下,指着穆德吼,喂!
你―你收起你那套!
给谁演戏呢?
这是生产会,不是表功会,说有用的!
旁边有人低声附和着,对,对呀。
穆德忽然受到了当众批评,尊严受到侵犯,脸上一阵由衷的惊愕,他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想起范胡子一贯对自己横挑竖捡看不惯,便像弹簧般跳起来,厉声反击范胡子,小人!
欺人太甚,老子在平吉堡受苦受累种甜菜,你还睡大觉呢!
话音未落,他手中握的茶缸已经投向范胡子,他想让他知道他不是绵羊,他也会发威!
范胡子的肩膀被砸中了,忽地跳起来,毫不示弱推翻了身下的桌子,一阵稀里哗啦,会场不欢而散。
尽管两人都受到了批评做了自我检讨,但此后彼此躲避着对方,心里已经结了梁子。
按照生产计划,各车间进入试生产阶段,小火车从厂部穿过,满载糖萝卜的车皮开进洗涤车间。
糖萝卜被卸进宽大的水沟里,像水车一样的车轮搅动起来,清洗刮擦着糖萝卜粗糙带泥的部位。
一个多小时,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相貌丑陋泥巴裹身的糖萝卜,经过清洗整容,齐齐整整挤在皮带运输机上时,已洁白无瑕。
糖萝卜经过切丝搅轧进入恒温糖罐蒸沸提汁,过滤后的糖渣被送出车间扔在空地上,而灌装的糖汁与糖蜜分离后,糖蜜进入管道流进酒精车间,成为制作工业酒精的原料,糖汁则经过熬制结晶干燥程序变成了白砂糖。
制糖生产试验成功了,正式生产即将开始。
重中之重依然是甜菜问题,平吉堡原料基地的糖原料源源不断供应上来,可是远远不能满足制糖生产周期的需要,糖厂急切需要广大农民种植甜菜来满足糖厂对原料需求。
一个人自以为走向绝路,殊不知光明正要开始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划定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成为头等重要任务。
第一批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穆德的师长,他最敬佩的教授,学识渊博的农研所所长被打成右派。
教授成了阶级敌人,穆德心里震动很大,愤愤不平。
1960年8月,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有指向地进行,定了指标在各部门抓捕回民干部,特别是技术干部。
平时喜欢钻牛角尖,喜欢给组织给领导提意见,爱出风头的回族知识分子,一概被拉进黑名单。
穆德和其他几位回民干部,不幸被圈进了黑名单。
运动一开始,矛头已经瞄准他们,尤其是穆德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的臭脾气,成为范大胡子一伙人的抨击对象,遭到了小揪斗和大批判。
群众运动面前,不讲原则政策,编造,诽谤,胡言乱语,乱扣帽子成为普遍现象。
穆德看不到自己的险境,忙着找领导为农研所所长据理力争。
他公开包庇右派!
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国庆节前夕,他和几个干部被扣了坏分子帽子,其中一个因为饥饿偷了食堂一个馒头而已,也被打成坏分子。
这天傍晚,穆德几个从办公室被推上一辆军用卡车,汽车沿西干渠西边土路向北开,到达目的地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他们被集中一间大房子里,坐在稻草上等处理。
不一会儿进来个人,穆德朝那人请求,渴死了给杯水喝吧?
那人气咻咻走到穆德面前,是个威武的男人,不由分说左右开弓抽了穆德两个大耳光,他的鼻子开始流血。
那男人骂道:
喝水吗?
你以为到家了?
他手指一扫,你们这些龟孙子,以为住店来了?
以为请客吃饭来了?
不剥皮抽筋还不反上天了?
边骂着手里举起钢丝绳做的鞭子,照着刚刚拉来的几十个人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