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docx
《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根.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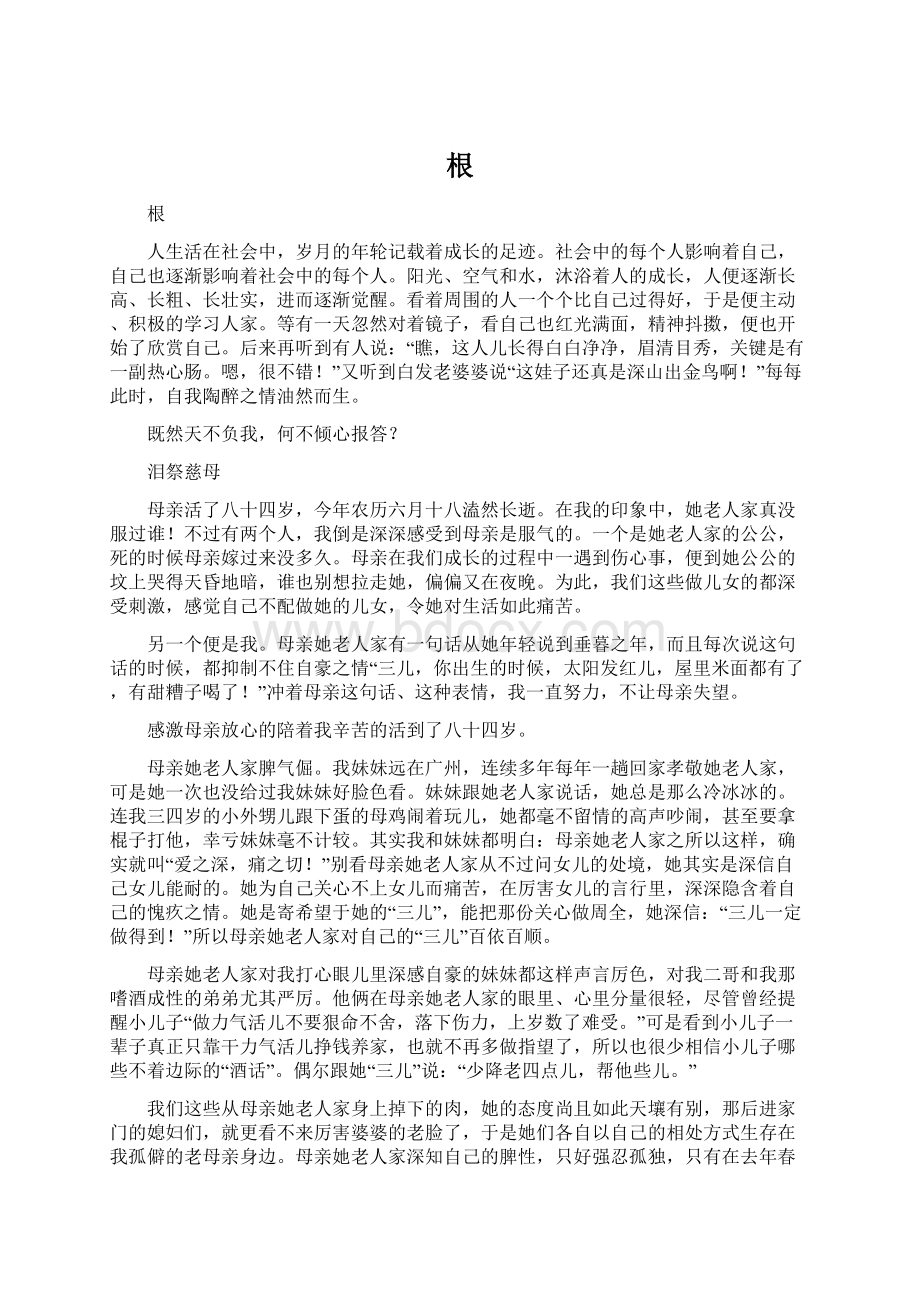
根
根
人生活在社会中,岁月的年轮记载着成长的足迹。
社会中的每个人影响着自己,自己也逐渐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个人。
阳光、空气和水,沐浴着人的成长,人便逐渐长高、长粗、长壮实,进而逐渐觉醒。
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比自己过得好,于是便主动、积极的学习人家。
等有一天忽然对着镜子,看自己也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便也开始了欣赏自己。
后来再听到有人说:
“瞧,这人儿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关键是有一副热心肠。
嗯,很不错!
”又听到白发老婆婆说“这娃子还真是深山出金鸟啊!
”每每此时,自我陶醉之情油然而生。
既然天不负我,何不倾心报答?
泪祭慈母
母亲活了八十四岁,今年农历六月十八溘然长逝。
在我的印象中,她老人家真没服过谁!
不过有两个人,我倒是深深感受到母亲是服气的。
一个是她老人家的公公,死的时候母亲嫁过来没多久。
母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遇到伤心事,便到她公公的坟上哭得天昏地暗,谁也别想拉走她,偏偏又在夜晚。
为此,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都深受刺激,感觉自己不配做她的儿女,令她对生活如此痛苦。
另一个便是我。
母亲她老人家有一句话从她年轻说到垂暮之年,而且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抑制不住自豪之情“三儿,你出生的时候,太阳发红儿,屋里米面都有了,有甜糟子喝了!
”冲着母亲这句话、这种表情,我一直努力,不让母亲失望。
感激母亲放心的陪着我辛苦的活到了八十四岁。
母亲她老人家脾气倔。
我妹妹远在广州,连续多年每年一趟回家孝敬她老人家,可是她一次也没给过我妹妹好脸色看。
妹妹跟她老人家说话,她总是那么冷冰冰的。
连我三四岁的小外甥儿跟下蛋的母鸡闹着玩儿,她都毫不留情的高声吵闹,甚至要拿棍子打他,幸亏妹妹毫不计较。
其实我和妹妹都明白:
母亲她老人家之所以这样,确实就叫“爱之深,痛之切!
”别看母亲她老人家从不过问女儿的处境,她其实是深信自己女儿能耐的。
她为自己关心不上女儿而痛苦,在厉害女儿的言行里,深深隐含着自己的愧疚之情。
她是寄希望于她的“三儿”,能把那份关心做周全,她深信:
“三儿一定做得到!
”所以母亲她老人家对自己的“三儿”百依百顺。
母亲她老人家对我打心眼儿里深感自豪的妹妹都这样声言厉色,对我二哥和我那嗜酒成性的弟弟尤其严厉。
他俩在母亲她老人家的眼里、心里分量很轻,尽管曾经提醒小儿子“做力气活儿不要狠命不舍,落下伤力,上岁数了难受。
”可是看到小儿子一辈子真正只靠干力气活儿挣钱养家,也就不再多做指望了,所以也很少相信小儿子哪些不着边际的“酒话”。
偶尔跟她“三儿”说:
“少降老四点儿,帮他些儿。
”
我们这些从母亲她老人家身上掉下的肉,她的态度尚且如此天壤有别,那后进家门的媳妇们,就更看不来厉害婆婆的老脸了,于是她们各自以自己的相处方式生存在我孤僻的老母亲身边。
母亲她老人家深知自己的脾性,只好强忍孤独,只有在去年春节前感觉自己已不能再做饭给自己吃的时候,才扶着门框,努力直直已经再也伸不直的腰,凄苦无限地说:
“谁来管管我呀!
”苍天没有回音,大地没有回答……
我妹妹从河边找儿子回来,离老远听母亲她老人家这声呼喊,无限的酸楚骤然涌上心头,她停下脚步,许久没有挪动。
当真正让我听妹妹说出母亲她老人家这句话的时候,我那倔强的老母亲已经陪我慈祥的父亲去了。
我终究还是让母亲失望了。
母亲她老人家终究还是忍受不了我给她上“政治课”,在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摔伤自己,痛痛快快的去和我的慈父闹吵去了。
尴尬童年
我长到两岁半,有了弟弟祥满。
为了不致让我受罪挨饿,伯伯和妈把我送到小姨和外公身边,让小姨养活我。
小姨二十出头年纪,生活能力很强,有点文化,个性活泼,做事有主见,虽是姑娘家,却能够为大队的事儿忘我工作,天天早出晚归,所以我每天和外公相处。
在柳牌儿老屋院儿,二舅和大舅两家的房子一正一横,外公的房子在二舅房子后面,走出外公的家二十来步,便是坟园包,坟早已不见,绕着圆形坟包,生长着三棵老槐树,每棵都有两个大人合抱那么粗,每年春天槐花一开,老香了。
一到夏天,挨着外公房屋正面的老槐树前种着的苦瓜,很是茂盛,爬上架的苦瓜藤儿开满了黄色的小花儿,温热的夏风送上一阵阵花香,给我幼小的印象留下深深的记忆。
外公爱喝酒,爱吃苦瓜,爱抽烟,会用直径二十来公分的小篾簸箩端鱼,上十个小篾簸箩,一到春、夏、秋天,都被外公蒙上粗纱布,在中心挖个小孩儿拳头大小的圆洞洞儿,外公再把用羊油拌麦麸子做的鱼饵抹在鱼簸箩底儿,很有目的的放在水里端鱼,端一回要吃上好多天。
天热的时候,外公把鱼挤得干干净净,放在太阳下晾晒成鱼干儿,每顿饭煎几条下酒,日子过得比较滋润,我是从外公的神色看出来的。
二舅两个儿子,祥龙和祥虎儿,和我的年龄相仿,祥龙1964年生,属龙。
大舅的三儿子名叫“社会”,跟我年龄也相仿,我们四个小伙伴玩的贴心。
特别是祥龙,我俩几乎形影不离,逮着空儿就到河里扎猛子,摸着水底的石子啊、虾米啊、水草啊,十里开外不把头伸出水面,外公端鱼一找不见我就急。
他不舍得打我,向小姨告发我,小姨会拿细树条子抽我。
我拿小姨没办法,小姨不在身边时,我便爬到外公怀里,伸出小手,狠劲捋他的山羊胡子,疼的外公“啊,啊”叫,我才撒手。
尽管这样,外公还是舍不得打我,哪怕是轻轻地弹一下。
偶尔,小姨也会把我带上街,带进会场,让我认识不少大人。
小姨和外公教我了不少待人接物的礼仪,我试着去做,大人们很欣赏我。
小姨和外公也因此格外看好我,我是他们的快乐。
他们给我取名“祥青”,后来上一年级,依着二舅家的儿女,给我取了学名儿------刘祥青。
小姨还没结婚,就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儿子了,足见小姨对我的深爱。
外公打心眼儿里信服我小姨的“足智多谋”,看小姨如此深爱我,也爱屋及乌,从心底里接受我。
小姨不在家,他给我在包谷糁儿里放糖,生怕我饿着了。
眼巴巴看我吃好了,就撩开他那蓝色家机布长袍子,把我揽在怀里,念叨起《增广贤文》“从小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
早知书中黄金贵,夜点明灯读五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亲不亲,一乡人;贵不贵,家乡水”等等,有时教我《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再就是《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对于这些他不光教我念,还手把手教我写。
不管我懂不懂,他教的时候,目光注视着我,我的眼光盯着他,特好奇,就一边注视他一撅一撅的山羊胡,一边跟着他像模像样的念。
时间一长,便不自觉地我自己也念叨起来。
后来外公告诉我,他念叨这些,从不在意我到底听还是不听,他认为:
念叨得多了,必然我会放在心上的。
于是,只要我在他身边,他老人家不是念叨《增广贤文》,就是念叨《论语》、《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弟子规》,那么不厌其烦,那么津津有味,那么乐在其中。
时日一久,我一想伯伯和妈而又见不到他们、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模样的时候,便趴在外公的怀里,捋着他的山羊胡儿,一任他有节奏的拍着我抑扬顿挫的念叨这些古代经典文化。
而奇怪的是每当外公念叨这些的时候,我便把对伯伯和妈的想念随风消散。
外公和小姨都说我三岁多了才开始说话,他们那个着急呀!
“咋这么乖的娃子,老是不会说话,可别是哑巴呀!
”他们哪里知道:
我身不在父母身边,看同伴儿们跟他们的爹妈那么亲热,纵情撒娇,我幼小的心智,无限羡慕之余,无所适从,急也无用,又怎么能憋出话来呢?
而且我在这些伙伴们眼里是没妈的、是深山里的、是没有依靠的,所以得不到他们应有的尊重。
如此,我更急,急迫里就更不知说什么,所以只好“哑巴”。
当然这其中多次,我那白发苍苍的大外婆一遇到我被那些顽皮的小伙伴围攻时,就红光满面的呵斥他们,用“山里娃子咋的?
深山出金鸟,平川出些恶老雕。
你们长大不会比他有出息!
”这类的话为我解围、救急。
我永远忘不了大外婆这样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加感激大外婆对我的鼓励和欣赏。
我不敢设想,如果没有大外婆这句鼓励和欣赏的话,我后来会不会当上老师,会不会常怀感恩的心,会不会一直自我鞭策,还真是说不好。
总之我终身都记着我的大外婆,终身都记着那些发自内心激励我、欣赏我的人。
1967年,我小姨的家里住进了一位阿姨,她姓什么,我忘记了,阿姨的丈夫姓陈,小姨让我叫他陈叔叔,我叫得很亲热,他们没孩子,对我也很亲热。
阿姨做得一手好茶饭。
每次做饭的时候,只要我在她身边,总要让我尝尝菜的味道,还把做好的菜肴让我吃,小姨在不在家都一样。
小姨告诉我,他们是为建二汽,从祖国五湖四海来的。
的确,陈叔叔他们来后,火车路修通了,火车来了,楼房有了,厂房连成一片片,明显的,人也比过去多多了。
终于有一天,外公送我上学,路上遇着我外公房后的小舅儿,我正挎着书包、抱着四条腿的小板凳一蹦一跳地走在外公的前面。
外公拄着他那根长烟袋杆子,穿着那件蓝布长袍子,很精神的走在我后面,离不多远,大概一丈以内的样子。
忽然,外公让我停下,我发现小舅在外公跟前,我走上去,外公竟让小舅“把祥青背上!
”小舅迟疑了一下,顶了一句“我是老师,为啥要背他?
”外公不容分说,把那大烟袋哨子砸在小舅头上。
到底是小伙子,小舅没哭;到底是晚辈,小舅没还手;到底是外公够威风,小舅还真就把我背起来往学校走去。
外公接过小板凳,跟在后面。
学校不远,穿过小桥就到了。
学校是干打垒平房,坐东迎西,操场边有棵两个人合抱的拐枣树,操场不够平整,学生也不算多,一下课同学们大多都在拐枣树下游戏。
我也是由于玩得还算快乐,所以那颗拐枣树留给我的印象颇深,直到八十年末,我才再没见到它。
外公因我打了小舅,我那和我不太亲近的远房大外婆,搬凳子坐在外公门前的大坟园包上和外公对骂了三天。
毕竟不是外公的亲大嫂,我的亲大外婆,所以外公到底还是镇住了大外婆。
此事我后来当老师,阴差阳错和小舅同在一个学校,小舅乐呵呵的和我提及当年的事,还把外公用烟袋勺子打他,留在脑袋上的凹坑儿,指给我看,我多少还是有些歉疚,说不上为谁。
只是我当老师是经常背学生的,那是老师必须的。
上学不久,我伯伯又来外公家了。
趁外公和伯伯不注意,我提前藏在学校旁边河道的芦苇丛后,伯伯往前,我也往前,双眼始终没有离开伯伯,生怕他又顾自离开,把我丢在小姨家。
等看不见外公了,离外公的家也比较远了。
我终于不再藏下去,扑在伯伯怀里,表示无论如何也要跟着伯伯回家。
伯伯没再坚持,爱抚的背上我,走进深山沟里,回到了我日思夜盼的家,见到了我妈,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当然不再是祥满弟弟,而是祥平弟弟。
偶尔我问妈“祥满去哪儿了?
”“丢了。
”我察觉到妈凄楚的表情,没再追问下去。
不久我就融入了自己这个家大口阔、吃不饱穿不暖但整天有说有笑的穷家庭里,诀别了尴尬的童年。
苦涩少年
将近八岁的样子,我回到了自己已经破落的四合院,厅房已不复存在,东西厢房连着我家的正房。
西厢房住着我四爹一家五口人,东厢房住着我二爹一家五口人。
不管是厢房还是正房,屋子开间和进深都只有一丈开外,墙壁都熏得老黑了。
二爹家住的东厢房后檐墙都快要倒了。
虽说多出了一间,其实毫不宽绰。
四爹住的西厢房仅仅两间,幸好一间厨房紧还连着我家的正房,要不然更促狭。
我家的正房是完整的三间,两排列架,用桦栎木板装饰,那些装饰板儿里红外黑,接地的木地槽已经腐朽。
这是一座典型的明清风格四合院,早年间是草房,到我曾祖父杨继宗时代,因为开桐油坊发迹,才把草房换成了瓦房。
可见曾祖父是我们这个家族既往开来者,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开创一番家业,是很不简单的,这当然得感谢他有一位虽然双目失明但却特别能干的奶奶了。
听我伯伯说:
杨继宗的奶奶“口答算儿”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一位,这边儿报着桐油的斤数,老奶奶那边儿就把该付的钱数响亮的喊出口了!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感受到了自强的力量。
我十岁之前和伯伯睡一头儿,弟弟和妈睡一头儿,四个人挤一张板床,两个哥哥在堂屋另搭一张特别简易的床。
后檐墙放一个烂柜,全身木板已经腐朽,虽然有盖儿,柜里面却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一张八仙桌儿,其中一角被松亮子烧了老大一个黑窝,靠在装饰板儿上还一摇三晃的。
家里少得可怜的米面,放在东间房屋的木柜瓦缸里,木柜紧挨着我和伯伯的床头儿,过道儿仅容一人。
计划经济年代,靠挣工分吃饭。
妈身体不好,伯伯一人上工,挣够三十个劳动日,还要扣除妈那一部分,月月所剩无几。
一到春上,我们全家不是老吃谷面糊儿,就是萌花叶、香椿叶、苦蒿子、干红薯叶、佛爷儿指甲(一种野菜)等等煮一大锅,里面撒一点儿包谷糁儿啦或者是米糁啦,总之从没有吃过纯粹的米、面,连过年也是这样。
由于经常吃上顿无下顿,我饿的读书都没了声音。
四年级那会儿搞演出唱歌儿,因为没声音,刘老师把她那份儿炒馒头干儿端给我。
我宁愿不演出、回家饿肚子,也拒绝了老师的关心,弄的老师又心疼又欣赏。
偏偏那两年我老犯灾星,出麻疹搞得一个星期都双目失明,把伯伯和妈心疼、着急得连话都不敢在我面前说,就是说话,那喉咙也都哽咽着。
我倒是很乐观,把老师教给我的歌儿唱给他们听,这样越发叫他们伤心。
麻疹出的厉害时,我什么都吃不下,伯伯省出全家的口粮,给我擀又白又细又薄的面条儿,放进鸡蛋娑儿、浇上香油,一勺一勺的喂我。
白天上一天工,晚上还要在坡上弄一大挑子柴火,回家都半夜了,有一次由于用力过猛,树皮把伯伯的中指勒的明显看见骨头,用桑树皮缠着,回家又忙着给我们做饭吃。
饭做好以后,先把我抱起来喂好了,放床上。
再去把我哥哥叫醒,把我弟弟抱起来看他吃。
有了伯伯和妈的精心伺候,我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又给他们唱歌听了,跳舞看了,或许是我的开心感染了伯伯吧,伯伯也拿出一根泛红的竹箫,连凳子都不坐,蹲下来,靠着西边儿那扇柴门,十分专注的吹起来。
那声音很动听,悠扬、清亮、婉转……这是伯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让我听到的心灵之声。
谁知麻疹刚刚好利索,我大腿根部又开始生疮,前次出麻疹因为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妈找了好多单方。
这次生疮,又得想办法找单方治,一个疮还没好,紧挨着又来一个,简直把伯伯和妈都快愁死了。
十几天之后,脓流出来了,妈用自己头上的银簪,及其小心翼翼的刮呀,刮呀,生怕弄疼了我。
我慢慢好转,渐渐痊愈,伯伯和妈的眉头也随之缓缓舒展。
我这两次生灾,可害苦了我的伯伯和妈。
我伯伯是准五尺的汉子,粗胳膊粗腿,肩挑三百来斤重东西,简直太寻常,而这次人整个瘦了一圈儿,本来就满脸胡子,现在更浓更密,但依然精神得很,从没听他叫一声苦。
原本就很清瘦的妈,这次显得又瘦又虚弱,和伯伯一样,也没在我面前叫过苦。
我很感激自己有如此刚强的父母。
为了检验我身体恢复的程度,也为了让我开开眼界,伯伯第一次带我出了一趟远门儿------与我们临近的房县风水岭儿我小舅爷家。
一踏上风水岭儿,站在桫椤树下,伯伯就跟我讲:
风水岭儿一脚踏三县,往东是均县(今丹江口市),往北是郧县,往西是房县;娑罗树是从月亮上掉下的种子长出来的,祖祖辈辈从这棵桫椤树下走过的人,都看它这么高大,这么粗壮,给谁都乘凉。
啊!
伯伯的脑子里也有这么浪漫的故事,胸中也有这么浪漫的情怀。
十一岁那年,我有了妹妹。
妹妹的出世,带来了全家的喜庆和幸福。
日子虽然依旧糠糠菜菜,但一家人在妹妹出生后很少生疮害病。
特别是我的两个哥哥,一回到家,都争着抢着要背她、要抱她。
那神态、那劲头,似乎只要抱着妹妹就不饿了,也不累了。
当妹妹说出第一句话“十六行”时,笑声弥漫了满屋。
那是因为包谷熟了,伯伯给我们烧包谷穗儿吃,我教妹妹数数,谁都没有想到妹妹真的会说话了,而且还会数出“十六行”这个数量词来。
在妹妹出世的欢喜中,我们兄弟四个睡到了一张简易的床上,这意味着我和弟弟也长大了。
在妹妹出世的欢喜中,我开始像二哥一样,试着给伯伯和妈分忧解愁。
二哥去卖柴换钱,我也跟着他去;二哥翻山越岭砍竹娃儿,扛到五零厂,卖给蔬菜队换钱,我也跟着一起。
我俩用换来的钱给妹妹买藕粉、奶粉、给家买米、面,日子慢慢地好起来。
但是因为人穷,受气也很自然。
记得跟二爹一起翻山驾岭百十里到彭家坡砍竹娃儿,回来的路上我实在又饿又累,扛不动了,二爹把我的一捆竹娃儿绑到他一起扛了回来,把我感动了好几天,等星期天我准备去扛着跟二哥去换钱时候,二爹眼珠子一翻:
“那是我扛回来的,就是我的了,你凭啥子要?
”我顿时无语,心中窝满了气,从此觉得二爹不是那么亲近了,一直疏远到我当老师以后才在心里原谅他。
为了换钱贴补家用,我和二哥不止一次上山砍竹娃儿,有一次家里实在太急用钱,我跟二哥又去砍竹娃儿,旷课了。
刚进课堂,年轻气盛的老师揪住衣领,把我俩先后拎上讲台,很快又敲着我俩后脑勺,使劲把我俩推到教室外操场上。
那教室的门槛很高,出了门槛不足一米的走廊,又是离地一米多高,才是操场。
若不是我兄弟俩双腿利落,老师那使劲的推搡,非把我俩刺破鼻子、跌掉牙齿不可。
连老师也不同情穷学生啊!
越是这样,我越是努力学习,每天中午二哥回家给我拿饭,我就在学校里帮推搡我的老师批改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尽管老师从不给我笑脸,也丝毫不感谢我为他付出的劳动。
那时学校搞复式教学,老师教一到五年级语文和算术,我一个三年级学生连四年级、五年级的语文、算术作业都给批改了,这让我语文、算术成绩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我得感谢老师。
由于从小受到外公的语言熏陶,我对语文特别情有所衷,对文字也特别敏感。
三年级写了一篇自己拔黄豆的记叙文,终于感动了老师,他给我这篇作文的批语是“写的详细,有体会。
”我捧读着老师的批语,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为自己的争气加油:
知识一定能改变命运!
四年级我跟着二哥一起转了学,那是因为妈要让二哥无论走到哪儿都必须带着我,不能让我受人欺负。
转到新学校不到一个月,我便遇上了后来能彻底改变我贫穷命运的刘思荣老师。
她给了我很多的照顾,大雪天给我缝了崭新的棉衣、棉裤;课堂上给我很多的表达机会;课堂外给我很多语言的鼓励;跟她一起经过小卖店,还舍得花钱买糖给我吃。
那次吃糖太稀罕了,我还是幼年时外公在饭碗里给我放糖呢,直到现在整整九年没有尝过糖滋味儿了。
刘老师的细心呵护,激励我萌动了长大当老师的梦想,我一冲动,把梦想写进了作文里,刘老师读了我的作文,更加欣赏我,鼓励我,帮助我。
还把我因为贫穷而辍学后,亲自上门接回学校。
有妹妹真好!
妹妹带给我太多进步的动力,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在妹妹出世的欢喜中,我开开心心的结束了初中学习生活,以特别优秀的语文成绩考上了高中。
要知道:
人家都是考了五门都没考上,我只考了两门!
我们班三十多名同学,我是五人中的一人。
我明白:
妹妹出生的喜气,加上伯伯和妈的勤劳精神,再加上我的勤奋意志,成就了自己的高中生梦想。
我也爱自己的妹妹。
1978年末,高一寒假临近的星期五,上完晚自习已经六点半过,我急着要回家看到妹妹,也不顾天上正下着零星小雪,公交车也已收班,便下定决心步行回家。
从白浪中学到家那是要走将近八十里,我一个人抹黑上路,越往前走雪下的越大,渐渐的风卷雪花,直往眼里钻。
刚爬上黄宝山,雪已经覆盖了原野,大地一片白,根本分不清哪是坑哪是路。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凭着自己的印象照平处走,所幸没有摔多少跤。
爬上王家垭子,坡快下完了,脚底一打滑,人整个摔在光滑的石壁上,一直仰面朝天滑进水底。
好在这是茅塔河水库尾巴,我从水底站起来,把手伸得老高,却没有探到水面。
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清醒,知道今年雨水多,库里的水一直满满的,但是这里并不宽,我从水底忘乎所以的朝前走,很快走上对岸,继续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家走,争取尽快赶回家。
好不容易回家了,伯伯和妈还在火炉旁等我,松亮子“噗噜噗噜”扑闪,我推开柴门,伯伯和妈不约而同的扑向我,一摸浑身水淋淋的,妈赶紧去找衣服,伯伯脱下我的湿衣服,让我站火边烤着,他去给我张罗吃的。
妈找来里里外外干衣服,帮着我换好不多会儿,伯伯就把热腾腾的面条端到我面前,我双手接过来津津有味的吃起来。
火炉里的火很红,因为烧的时间长,没有一根冒烟的柴头子。
两个哥哥、弟弟、妹妹都睡熟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回来了。
我吃完饭躺下,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
辛酸青年
两年高中,由于得黄疸型肝炎耽误了半学期,高考仅以零点五分的差距,与南京师范大学无缘。
这当然还是怪我逆怼数学、物理、化学,更糟糕的是高一开学没上到一个月的课,我就把英语书搞丢了。
只是高考七门课,还是只考了语文和政治两门。
尤其悲哀的是八零年还在批判“白卷先生张铁生”,我理科考试全没有参加,完全撞到了枪口上。
十岁开始做起的教师梦,这一下更加遥遥无期了。
回乡后,我狠命的干活,天天下死力气。
有一个夜晚,终于来到了沟口的水塘边,纵身一跃,往水塘里跳去,结果衣服被伯伯紧紧拉住了,他把我一把拉进怀里,紧紧抱住,久久没有出声。
我依偎在伯伯怀里,渐渐感受到温暖:
再努力吧,会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
天快亮了,我对伯伯说:
“走,伯伯,我们回吧!
”伯伯放开我,爷儿俩拉着手,一前一后回到了家。
为了报答伯伯,我又恢复了少年时的活泼、开朗,全家人因为有了我,几乎每天都有说有笑,不管多苦多累。
我都十八岁了,那老旧的四合院正房早已容纳不了我们一家七口人。
于是我跟伯伯一起上山放房料、扛房料。
第一次扛椽楯,那一百多斤压在肩上,我双腿筛糠似的迈不动步子,更兼山路崎岖,高高低低,好似羊肠。
刚刚放倒、截断的松树橦子,湿漉漉的,粗櫴櫴的树皮和我细嫩的肉皮接触在一起,有说不出的难受。
可我忍住了,把它给扛走了,一根儿,两根儿,三根儿……终于我把它们给制服了!
两年多的准备,房料齐了,屋基批下来了,屋基砌平了,打土墙的师傅凑齐了,一年之内,三间干打垒平房拔地而起,一家人欢欢喜喜搬进了宽敞的新屋。
住进新屋后,一家老小都把我当成了全家的顶梁柱,伯伯尤其开心。
因为在这之前的1980年,我就经过考试,当上了民办老师。
八三年新房子盖起,我已经当了三年的老师,伯伯和妈都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自豪感。
我更是有浑身使不完的力气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有鼓动性,我拥有了和伯伯与妈一样自强不息的精神劲儿。
1984年冬天,我在阴湾口公路边帮姨父收柴,由于怕被其他司机拉走,我一连几个晚上露宿在柴堆旁边的岩壳儿下。
夜里很冷,一床棉被紧紧裹着还是冻得直哆嗦。
柴没拉走,我不能擅自离开,偏偏这天晚上又下起雪来。
我回家吃完饭,照常下来看守。
雪越下越大,铺天盖地,纷纷扬扬,没一会儿工夫,岩壳儿里就堆起雪来。
四周很静,只听见北风“呜呜”地尖叫,雪片砸树叶的声音也比较清晰,此时一个黑影出现在我面前。
“三儿,被褥放这儿,我们回。
”我没有坚持,这个时候,是不会有人把柴拉走的。
我和伯伯互相紧紧的搀扶着,十分艰难的往回走。
雪一直下个不停,而且盖得眼一直无法睁开,钻进脖子的雪丝毫来不及融化。
还没有走出10米距离,远远近近一片白。
我们父子俩并排行进在不到一米宽的田埂上,路是白的,田是白的,连几十米深的河道都白的分不出来了。
幸好我们走得极慢,配合的极默契,脚底稍一打滑,其中一个马上把另一个扶住,站稳了再迈步,最终安全回家。
这次雪中行,父子俩都深深的欣赏对方、敬爱对方、信赖对方。
尤其是我从中深深感受到努力用知识改变家庭困境、改变亲人和个人命运的深远意义。
我爱读书,可是家里没有书。
我当民办老师的津贴要贴补家用,一年到头发一次薪水才几百元钱,我还要还父母在我们小时候养我们的贷款。
我只好靠星期天扛松树橦子卖给五零厂工人换钱,积攒多次才能买一本、两本书回来读。
有一次卖松树橦子遇上了好人,他慷慨的付给我75元钱,这么多钱,在当时可是不啻于天文数字,还送我10斤粮票。
我临走时,阿姨深情地说:
“好好教书,看你这细皮嫩肉、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一定是有志气的。
书教好了,作为更大。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对都姓李而且养育了七个子女的父母,他们跟我父母一样善良,一样辛苦,一样能干。
我捧着李阿姨给我的钱,兴冲冲的坐公交车来到位于五堰的郧阳地区新华书店,一次性花掉10元钱买了满满两挎包书。
其中的《唐诗三百首》、《宋元明诗三百首》、《南行记》、《蒙古民间故事》、《呼兰河传》直到现在我依然视如珍宝。
我清晰的记得当初买好这些书,小心翼翼的装进黄色军用挎包后,留下其中的一本,旋身挤进公交车,细心的品读起来。
到站下车后,我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边走边看,既没有顾着买饭吃,也没有顾着看脚下的路,全神贯注于书中。
回家后,伯伯问我“咋没装壶酒”,我才醒悟过来,赶紧拿上酒壶,一溜烟跑出门来到离家八里开外的小卖店,装了酒,还给伯伯和妈买了烟。
一口气跑回家去的时候,已经是月挂中天,星星闪亮了,此时我才想起自己还是凌晨吃的饭,还真是有些饿了。
我急匆匆吃完饭,趁大家吃饭的功夫,又捧起那本没有看完的书,接着往下看。
等大家都吃完饭,我洗好碗筷,又在灯光下忘情的往下读。
那几天一有时间,我的眼光全都集中在书本里。
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