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则西汉早期铜镜铭文所折射的汉人精神世界.docx
《关于一则西汉早期铜镜铭文所折射的汉人精神世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一则西汉早期铜镜铭文所折射的汉人精神世界.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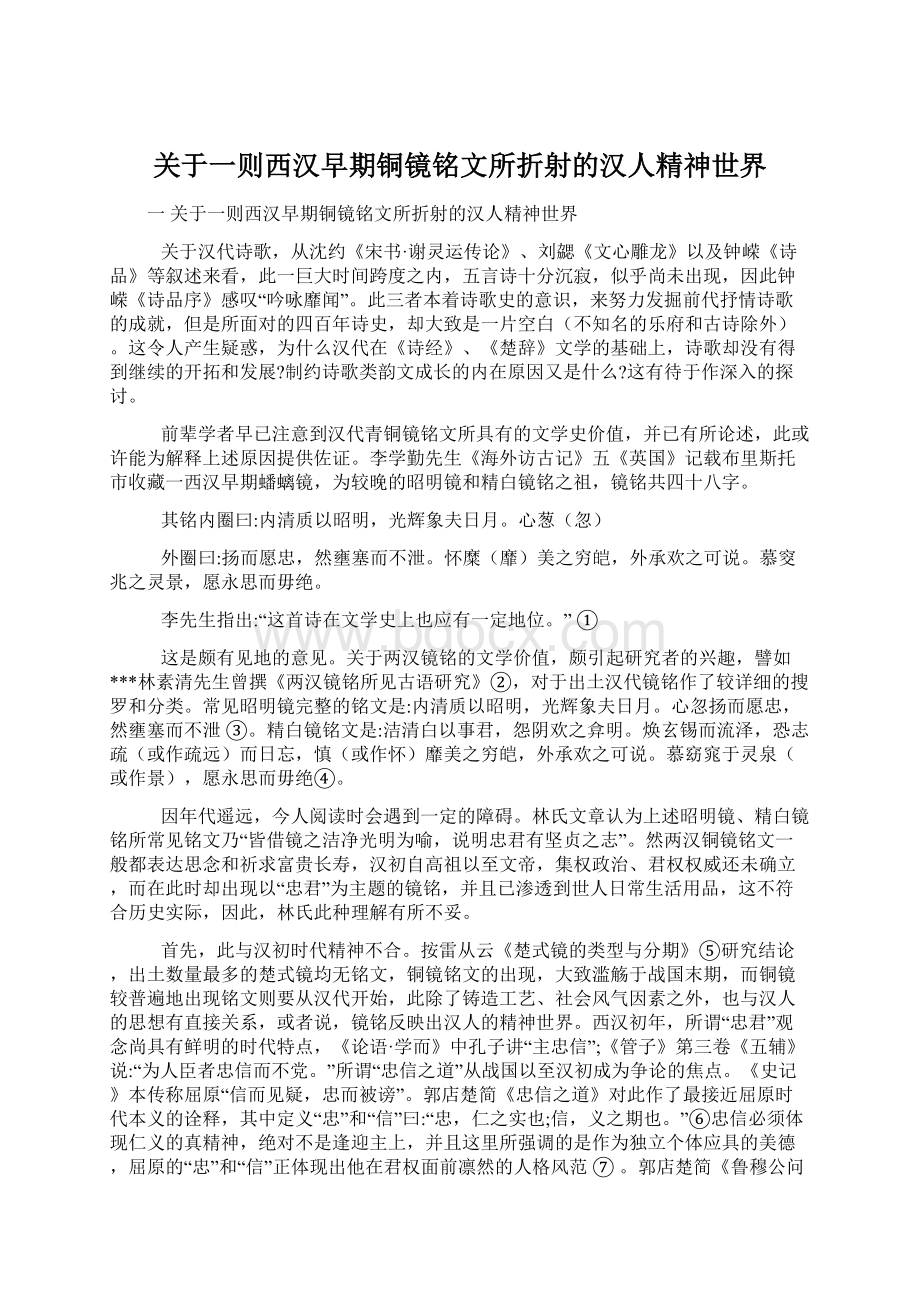
关于一则西汉早期铜镜铭文所折射的汉人精神世界
一关于一则西汉早期铜镜铭文所折射的汉人精神世界
关于汉代诗歌,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以及钟嵘《诗品》等叙述来看,此一巨大时间跨度之内,五言诗十分沉寂,似乎尚未出现,因此钟嵘《诗品序》感叹“吟咏靡闻”。
此三者本着诗歌史的意识,来努力发掘前代抒情诗歌的成就,但是所面对的四百年诗史,却大致是一片空白(不知名的乐府和古诗除外)。
这令人产生疑惑,为什么汉代在《诗经》、《楚辞》文学的基础上,诗歌却没有得到继续的开拓和发展?
制约诗歌类韵文成长的内在原因又是什么?
这有待于作深入的探讨。
前辈学者早已注意到汉代青铜镜铭文所具有的文学史价值,并已有所论述,此或许能为解释上述原因提供佐证。
李学勤先生《海外访古记》五《英国》记载布里斯托市收藏一西汉早期蟠螭镜,为较晚的昭明镜和精白镜铭之祖,镜铭共四十八字。
其铭内圈曰: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
心葱(忽)
外圈曰:
扬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
怀糜(靡)美之穷皑,外承欢之可说。
慕窔兆之灵景,愿永思而毋绝。
李先生指出:
“这首诗在文学史上也应有一定地位。
”①
这是颇有见地的意见。
关于两汉镜铭的文学价值,颇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譬如***林素清先生曾撰《两汉镜铭所见古语研究》②,对于出土汉代镜铭作了较详细的搜罗和分类。
常见昭明镜完整的铭文是: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
心忽扬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③。
精白镜铭文是:
洁清白以事君,怨阴欢之弇明。
焕玄锡而流泽,恐志疏(或作疏远)而日忘,慎(或作怀)靡美之穷皑,外承欢之可说。
慕窈窕于灵泉(或作景),愿永思而毋绝④。
因年代遥远,今人阅读时会遇到一定的障碍。
林氏文章认为上述昭明镜、精白镜铭所常见铭文乃“皆借镜之洁净光明为喻,说明忠君有坚贞之志”。
然两汉铜镜铭文一般都表达思念和祈求富贵长寿,汉初自高祖以至文帝,集权政治、君权权威还未确立,而在此时却出现以“忠君”为主题的镜铭,并且已渗透到世人日常生活用品,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因此,林氏此种理解有所不妥。
首先,此与汉初时代精神不合。
按雷从云《楚式镜的类型与分期》⑤研究结论,出土数量最多的楚式镜均无铭文,铜镜铭文的出现,大致滥觞于战国末期,而铜镜较普遍地出现铭文则要从汉代开始,此除了铸造工艺、社会风气因素之外,也与汉人的思想有直接关系,或者说,镜铭反映出汉人的精神世界。
西汉初年,所谓“忠君”观念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论语·学而》中孔子讲“主忠信”;《管子》第三卷《五辅》说:
“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
”所谓“忠信之道”从战国以至汉初成为争论的焦点。
《史记》本传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对此作了最接近屈原时代本义的诠释,其中定义“忠”和“信”曰:
“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
”⑥忠信必须体现仁义的真精神,绝对不是逢迎主上,并且这里所强调的是作为独立个体应具的美德,屈原的“忠”和“信”正体现出他在君权面前凛然的人格风范⑦。
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说: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
‘何如而可谓忠臣?
’子思曰:
‘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在汉初,激烈的反秦、反法家思潮是主旋律,青铜镜当时属于私人用品,它是否可能出现以忠君为题旨的铭文,实在令人怀疑。
其次,青铜镜的使用,在汉人具有吉祥辟邪的意味,其祈愿一般表达出既企慕天国的永生、又希望得到俗世满足的心理,譬如日光镜铭有一则曰:
“镜气清明,服者君卿。
延年益寿,安乐未央。
”⑧
显然“镜气清明”与“延年益寿”有直接的关联。
根据孔祥星、刘一曼著《中国古代铜镜》介绍上世纪出土的一些铜镜常置于人骨架的腰部或胸部⑨;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叁《二号墓》二《出土器物》介绍三件铜镜,分别出于主室漆盒、棺内漆奁和墓主窦绾玉衣左手中,而且棺内漆奁中的蟠螭纹规矩镜还有十五字铭文曰:
“大乐富贵,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
”⑩此实质上与先秦两汉人佩玉的风习十分相类,表达出世人对于富贵长寿的渴求。
此对于理解上述昭明镜、精白镜铭颇有启发,其铭文是以明镜来比拟持镜者,或寄寓以明镜降福持镜者之意。
按《国语·周语》说:
“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则,礼也;制义庶孚,信也。
然则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
”此是内史过对于周襄王的告诫之辞,其中“精、忠、礼、信”四者,作为周襄王乃是向内的道德修养,其中“精”又是第一位的,“忠”、“礼”与“信”只是从属于“精”,个体惟反身有“精”,才能够焕发出“忠”、“礼”与“信”种种美德,所以对照上述镜铭“内清质以昭明”,联系“昭明物则,礼也”,也必然需以内在的“精”为前提。
汉文帝时的贾谊《新书》是与此镜铭差不多同时期的文献,作为参照,可有助于对此镜铭的理解。
《新书》卷第八《道德说》说:
德有六理。
何谓六理?
曰:
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
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象人者,独玉也。
……神者,道、德、神、气发于性也,康若泺流不可物效也。
变化无所不为,物理及诸变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泺流谓之神”,“神生变,通之以化”。
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知,明则有辉于外矣。
外内通一,则写得失,事理是非,皆职于知,故曰“光辉谓之明”,“明生识,通之以知”……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故曰“忠者,德之厚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书》者,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故曰“《书》者,此之著者也”。
《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
《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
《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事师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纪者也”。
《礼》者,体德礼而为之节文,成人事,故曰“《礼》者,此之体者也”。
《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
合则欢然大乐矣,故曰“《乐》者,此之乐者也”。
人能修德之理,则安利之谓福……德毕施物,物虽有之,微细难识。
夫玉者,真德写也。
六理在玉,明而易见也。
是以举玉以谕,物之所受于德者,与玉一体也。
11
其中“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知,明则有辉于外矣。
外内通一,则写得失,事理是非,皆职于知,故曰‘光辉谓之明’,‘明生识,通之以知’……物所道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故曰‘忠者,德之厚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史记·五帝本纪》之张守节《正义》有曰:
“又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
”《尚书大传略说》“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12,两者或有渊源关系。
对照昭明镜铭文说所谓“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显然“明”和“光辉”是指一种人的心理及生理状态,而以玉作比喻,诚如《礼记·玉藻》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此在先秦成为传统,正表明在此种状态下,非但生命力饱满,而且智慧优裕。
紧接对于“明”和“光辉”的诠释,又曰“明生识,通之以知”,《新书》卷第八《道术》说:
“爱利出中谓之忠,反忠为倍……期果言当谓之信,反信为慢……深知祸福谓之知,反知为愚。
”可见“忠”、“信”分别是德之“厚”与“固”,而所谓“知”,在贾谊思想中侧重于个体独立的修养,尤其“深知祸福谓之知”,隐约透露出《老子》的祸福观,足见对于个体自我生命价值的珍惜,远要凌驾于他者之上,故“心忽扬而愿忠”实际上与后世所理解的效忠君主无涉。
李学勤先生《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一文,已经谈及“贾谊《新书》的《六术》篇曾引据《五行》,这是马王堆帛书整理者已经指出的。
《六术》和与之连接的《道德说》也引据了见于郭店简的《六德》。
看来《五行》、《六德》实同出一源”13。
郭店楚简《五行》讲“仁”、“义”、“礼”、“智”、“圣”,然其具体呈现为“玉色”和“玉音”,确实与贾谊以玉象人德之“六理”具有相同的渊源,而且与先秦时期的“精气”养生说有直接的关联。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二《玉府》曾对玉在古代社会生活里的重大意义作了赅博的阐释14,在人类生死两界,玉都被视作具有神奇作用的器物。
《史记·孝武本纪》之《索隐》引《三辅故事》说:
“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
”但是古人是否真的食玉,孙诒让则表示怀疑。
《管子》第十二卷《侈靡》说:
“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
”《庄子·外物》中有“儒以诗礼发冢”的讽刺,述及墓主口中含珠;按《荀子·正论》说:
“若是,则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
”两者恰好可以互相印证。
贵人重厚葬,金缕玉衣则是最高规格的葬仪,按《说文解字·玉部》,颇反映此种葬俗,如解释“琀”谓“送死口中玉也”,《汉书·杨王孙传》杨王孙说尸体“口含玉石,欲化不得”;又如解释“珥”谓“以玉充耳”,《荀子·礼论》说:
“充耳而设……反生术也。
”这充分证明玉不仅关乎人的养生,并且在给死者送葬器物中,玉也凸现着其重要的作用15。
这正说明贾谊以玉比喻德之“六理”,也隐含着精气说的意思,此为将上述镜铭置于精气说语境来领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至于镜铭“然壅塞而不泄”,今人比较难以理解。
林素清先生上述论文引《楚辞·九辩》所说“路壅塞而不通”来作解释,认为是屈、宋感喟奸人当道,自己忠心不得上达16。
然而按照这样的理解,此镜铭似乎具有某种社会政治批评的意味,士人将其现实中“不遇”的愤懑抒发于镜铭之上,如此泛政治化,政治似乎已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然作如此解读的镜铭内容,与铜镜纹饰所流露的尚美求仙意识不谐和,在汉初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这里“壅塞”与“不泄”似是意近之词,可理解成像“壅塞”一样“不泄”。
按《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记载“(周)仁为人阴重不泄”。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说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
《索隐》曰:
“案:
孔文祥云‘谓质重少言,胆气在中也。
周仁“阴重不泄”,其行亦同也’。
”“不泄”就并没有贬义词的意味。
泄,大致有两个意思,一则,贾谊《新书》卷第九《大政下》说:
“故曰刑罚不可以慈民,简泄不可以得士。
”注释者以“简泄”为“简慢”,引《荀子·荣辱》注说:
“泄,与媟同,嫚也。
”另则,《管子》第四卷《宙合》说:
“故曰:
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菑极。
”则指无形的计谋借言语泄露出去,《管子》第十三卷《心术下》说:
“气者身之充也。
”而气之泄,其意正与“谋泄”之“泄”意近。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曰:
“人生于清(精),不智(知)爱其气,故多病而易死。
人之所以善蹶,蚤(早)衰于阴,以其不能节其气也。
能善节其气而实其阴,则利其身矣。
”17
所谓“节其气”也就是不泄的意思。
汉初陆贾《新语》卷下《怀虑》第九说:
“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延寿命者,则志不流于外。
”《怀虑》又说:
“心佚情散,虽高必崩,气泄生疾,寿命不长,颠倒无端,失道不行。
故气感之符,清洁明光,情素之表,恬畅和良,调密者固,安静者详,志定心平,血脉乃强。
”18
《淮南子·原道》说:
“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处之则废,气不当其所充而用之则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则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疾病都是由于“气泄”所引发,而若要长寿,必须防止“气泄”,《管子》第十四卷《四时》甚至认为人若顺乎四时节律,“地乃不泄”,意指地气不致跑泄,此与养生意同,这是当时一般卫生健体的共识,反映于镜铭,正是所谓“壅塞而不泄”的意思。
李学勤先生所述镜铭下半节文字:
“怀糜(靡)美之穷皑,外承欢之可说。
慕窔兆之灵景,愿永思而毋绝。
”联系常见昭明镜完整的铭文之下半段:
“洁清白以事君,怨阴欢之弇明。
焕玄锡而流泽,恐志疏(或作疏远)而日忘,慎(或作怀)靡美之穷皑,外承欢之可说。
慕窈窕于灵泉(或作景),愿永思而毋绝。
”显然上边铭文是下边铭文的简写,其发端“洁清白以事君”,此存在两种情形,假使持镜者是女子,则其主语显然就指镜子的女主人,而女子与镜子则可以是一体同功者,在社会生活里,女子与镜子都可扮演“事君”的角色,在男性主导的社会,其主语理解作为人之妻妾,也是顺理成章的;假如持镜者是男子,因为这里不存在王权政治的君臣关系,其主语也不可能是为人臣者,而是“铜镜”,“铜镜”又比拟持镜之人——“君”,铜镜不经常擦拭,就会蒙上阴影,就如人情欲失去节制,也会掩却人心之“明”,人鉴于镜,则会生“洁清白”自己心灵的启示。
《管子》第十三卷《心术下》说:
“镜大清者,视乎大明。
”这里的“镜”字不管作动词或名词,总之,镜之清和视之明,两者是对应关系,而其“清”和“明”在此篇中的语境不外乎“精气”说;《淮南子·俶真》说:
“夫鉴明者,尘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不能乱。
”《管子》第十三卷《心术上》说:
“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故曰‘不伐’。
洁其宫,阙其门,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
洁之者,去好过也。
”房玄龄注“去好过也”曰“去欲好之过也”,甚为精当。
关于铭文,按照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说:
“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
”此种铭文所蕴涵的人生警示,倒正保存了“铭”这类文体的古意。
下文“慎”或“怀”均与“外”相对,虚静大明之心灵,若应对世事,必然游刃有余。
关于“承欢之可说”,按上述贾谊《新书》卷第八《道德说》的论述,人的欢乐并非仅止于口体之奉,乃由道德修养既深,内心所能体会到的一种真正的愉悦,《书》、《诗》、《易》、《春秋》、《礼》及《乐》等儒家的经典被纳入到其道德学说之中,他认为《五经》融于血肉,则与德相合,“合则欢然大乐矣……夫玉者,真德写也。
六理在玉,明而易见也。
是以举玉以谕,物之所受于德者,与玉一体也”。
稷下道家精气说的形成,应比《五经》概念出现得更早,道家和儒家关于如何感悟或建立道德的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在君子比德于玉这点上,却“殊途而同归”。
由于汉初学术继续着各学派融合的趋势,贾谊“颇通诸家之书”,按照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赞赏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贾谊大致反映了此种学术大势,因此,他认为只有具备《五经》之道,才合乎德,才进乎“欢然大乐”之境地。
显然他把精气养生说儒家化了,而作为心理体验,令人理解起来则比较抽象,假使要以具体物象来表达,则按《礼记·聘义》中孔子所说: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诗》云: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故君子贵之也。
”当然,汉初铜镜铭文未必已具有了贾谊这样的儒家意思,然而所谓“承欢之可乐”,却与道家精气说则更有着较近的渊源,惟有固精,才能恬静欢乐。
关于“窈窕”一词,郑玄笺《毛诗·关雎》之“窈窕淑女”云:
“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
”《正义》进一步解释说:
“此雎鸠之鸟虽雌雄情至,犹能自别,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随也。
兴情至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说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
”19
所以“窈窕”有着自持节制的意味,尤其在“兴情”问题上,能够保持高度的人性尊严,不致沦为禽兽,这是先秦时期人性的自觉,铜镜铭文向往此种境界,仍然与精其气、玉其德的语境前后一致。
二固精意识对汉代诗学的影响
固精意识根深蒂固,它对于汉代诗学的影响,除了要探讨在士人思想、学术中其所居地位之外,还须看到,因经学的作用,关于固精意识,民间与精英之间,逐渐产生了距离,主流思想下的士人,对于心的活动和作用,因排斥情欲,从而使经自觉清理之后所存留心底者,并非空白,而即是所谓的志,这造成了情与志的分离,此正是建筑汉代诗学的重要基础。
首先,固精养生思想在汉代精英文化层面具有深刻的影响。
按李学勤先生《海外访古记》十《瑞典》,李先生还记载了一面西汉早期的蟠螭纹镜。
其铭文曰:
道深辽远,中有关梁,鉴不胜请(情),修毋相忘。
铜镜铭文中一般包含有六言、四言及三言等句式,且有押韵的意识,李先生认为此“镜铭情溢于辞,甚为优美,很可宝贵”,初步具备着诗歌的特征。
王昆吾先生《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揭示出两汉铜镜铭文和汉乐府之间的关系20。
然而,为何两汉韵文还是局限于民谣体式,抒情韵文却未曾在士人阶层流播开来,发人深省。
汉代诗学就乐府以及士人创作而言,其成就不可藐视,然此时的诗崇尚实用,以致抒情诗(尤其在士人范围内)未能在《诗经》等基础上,在汉代继续发展,此与汉代人接受精气说影响有关。
《管子》第十三卷《白心》说:
“故曰:
欲爱吾身,先知吾情,君亲六合,以考内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养生。
”行情与养生有直接的联系,使得士人对于“情”格外重视,甚至备加警惕。
古人谈论政治时,如《毛诗序》的思维方式是“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而一人之本由“身”及“心”,典型地以《周易·系辞下》为例,往往以身及物,循微见著,由近至远,由内至外,这是古人的共识,先秦以至汉代,诸子百家莫不因循这样的思维模式。
《老子》十三章曰: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管子·牧民》说:
“天下之本者国也,国之本者家也,家之本者人也,人之本者身也,身者治之本也。
”《孟子·离娄上》说:
“孟子曰: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各家的说法完全相同,意指政治家之“身”主导国家的命运,要使“身”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则必须重视养生,养生主要是调适人内心的平衡。
《庄子·让王》说: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提出“内圣外王”说。
《荀子·强国》有曰: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
”则是从人贵生乐安天性引申到礼义建设,而此一切的起点正是“固精”说。
《吕氏春秋》对修身与治国关系论之极详,其《审分》一言以蔽之曰:
“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
”21对此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通国身》22
祖述此种思想,认为治国与治身,并无二致。
这样个体延伸至家、国以至天下,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孤立的存在。
这样的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修身或养生基础之上,对于如何处置“情”的问题,必然被凸现出来。
因此反映于上述铜镜铭文的精气说,降及汉代仍然影响着民间信仰以至精英阶层,并且凸现了像贾谊那样将民间意识精英化的趋向。
汉代以前,按《庄子·在宥》说:
“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
”人苦心焦思辛勤操劳也是养生之大敌。
《韩非子·扬权》说:
“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
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
”沉溺于情感的愉悦,同样有害于养生。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将人生命过程描述为“精”由盛至衰的几个变化阶段,若充分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精神恬愉,人就可以长命百岁。
这种养生说依《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在秦汉时期有较完整的承传。
《吕氏春秋·先己》说: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精气日新。
”《淮南子·原道》承袭《庄子》所谓喜怒忧悲好憎嗜欲都有害于道德心性的思想;汉代最讲天人之际,汉末高诱注《淮南子·原道》“故圣人不以人滑天”说:
“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乱其身也,不以欲乱其清净之性者也。
”从非后天因素来讲,身应属于天的范畴,而如何防遏它为“人”所滑乱,那就必须戒备欲望所带来的淆乱。
可见保精养气说,在汉代依然影响深广。
汉初尚黄老,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属于汉初文献,所谓“精”的概念,在其中也寻觅得到,其第一篇《经法》之六《论》说:
“强生威,威生惠,惠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
至神之极,见知不惑,帝王者,执此道也,是以守天地之极。
”23
又初河上公注《老》说:
“甚爱色,费精神;甚爱财,遇祸患。
所爱者少,所费者多,故言大费。
”又曰:
“自知己之得失,不自显见德美于外,藏之于内,自爱其身以保精气。
”24
上述陆贾《新语·怀虑》所谓“养气治性,思通精神,延寿命者,则志不流于外”。
“志”在贾谊观念里几乎与固精是同义词;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堪称是齐学养气说之要义,他说:
“故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
”《汉书·王吉传》载王吉习《齐诗》,他曾上疏谏昌邑王说:
“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
”治齐学者特别重视固精与寿命的关系,董仲舒《春秋繁露·通国身》说“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概括了齐学养生要义。
而汉代经学,以齐学一派势大,养生作为齐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借主流思想深入人心。
《汉书·东方朔传》说:
“臣闻乐太甚则阳溢,哀太甚则阴损,阴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气及。
”汉宣帝《报丙吉》说:
“……君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
”按饶宗颐先生《老子想尔注校证》一书25,东汉张鲁纯以固精说解《老》,固精养生之道终汉世未绝,于此可见一斑。
在汉代士人心目中,“固精养生”在政治、家庭和个人各个层面,均是一向往的境界,虽“穷则独善其身”时,要讲究“固精”,若“达则兼济天下”之日,有时更须为天下人的性命得以安养而“舍生取义”,这就表现为士人应具之“志”,个体与群体利益常常会产生矛盾,为了理想社会的建设,具有汉儒意识者勇于舍弃一己的私利,故有汉代坚持直谏的所谓“骨鲠之臣”,其所维护的是天下祥和的社会环境。
按《管子·心术下》强调人内心情绪的过度反应,于固精有害,亦必危及生命。
《管子·内业》说:
“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
”认为人的忧悲喜怒干扰了人心的“平正”,而葆养“精”或“道”或“灵气”,是“人之生”的第一要义,过激的心理感动,会与“精”发生冲突,两者不能相容,而若要固精,则唯有守静。
它指出《诗》与礼乐对养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或者说,《诗》或礼乐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养生的需要。
《论语·泰伯》中孔子提出人的修养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后人殊不知《诗》与礼乐的修养作用,在《管子》中均是附庸于“固精”层面而论的,因此孔子所言,其所依托的前提实与此相类。
《庄子》等先秦诸子都有“固精”养生思想,反对喜怒哀乐过激的情绪反应,此必然反映到文学领域,《汉书·翼奉传》中翼奉治《齐诗》,他说:
“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
”而“固精”说排斥情感,应视作在专制政治之外,对于中国抒情文学另一层面的影响。
其次,固精养生思想与诗学“言志”观的确立有直接的关系。
屈原在《楚辞·远游》中也抒发过向往“登仙”的意趣,曰:
“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
”宋玉《九辩》说:
“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
”足证屈子也熟悉当时流行的精气养生说,但是一旦舍身以救国,就不能顾及养生。
故此西汉末年扬雄《反离骚》说“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乎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屈《骚》中的琼靡与秋菊等具有养生延年的功用,扬雄因此质疑屈原对生命的放弃,此疑问颇具代表性,隐含着两种诗学观的对立,此阻断了《风》、《骚》精神在汉代的延续和光大,汉人对于屈原的批评往往缘此而发,此将固精观引入了诗学领域,对于理解汉代诗学很有意义。
《毛诗》在两汉地位并不显赫,而《毛诗大序》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诗学文献,关于其作者,《汉书》之《儒林传》和《艺文志》记载是“赵人毛公”。
《礼记·乐记》颇有与《毛诗序》交光互影者,两者关系密切,《礼记·乐记》曰: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
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
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
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孔疏引郑注《月令》云:
“宫属土,土居中央,总四方,君之象也。
”《史记·乐书》的“太史公曰”也以五行来牵合君臣、五脏、五常等五者,有与上述《乐记》相似的记述,均有思孟学派的影子。
《孟子·尽心上》说:
“孟子曰:
‘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刘向《说苑·君道》引河间献王说:
“……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26
与《乐记》相对看,在五行所对应的五音、五事中,“怨”与“哀”总是和民之烦役辛劳联系在一起。
《毛诗序》说: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也是把“音”与“民”之“怨”、“哀”结合起来看,同时参照产生于西汉成、哀以后的《诗纬含神雾》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