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交换.docx
《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交换.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交换.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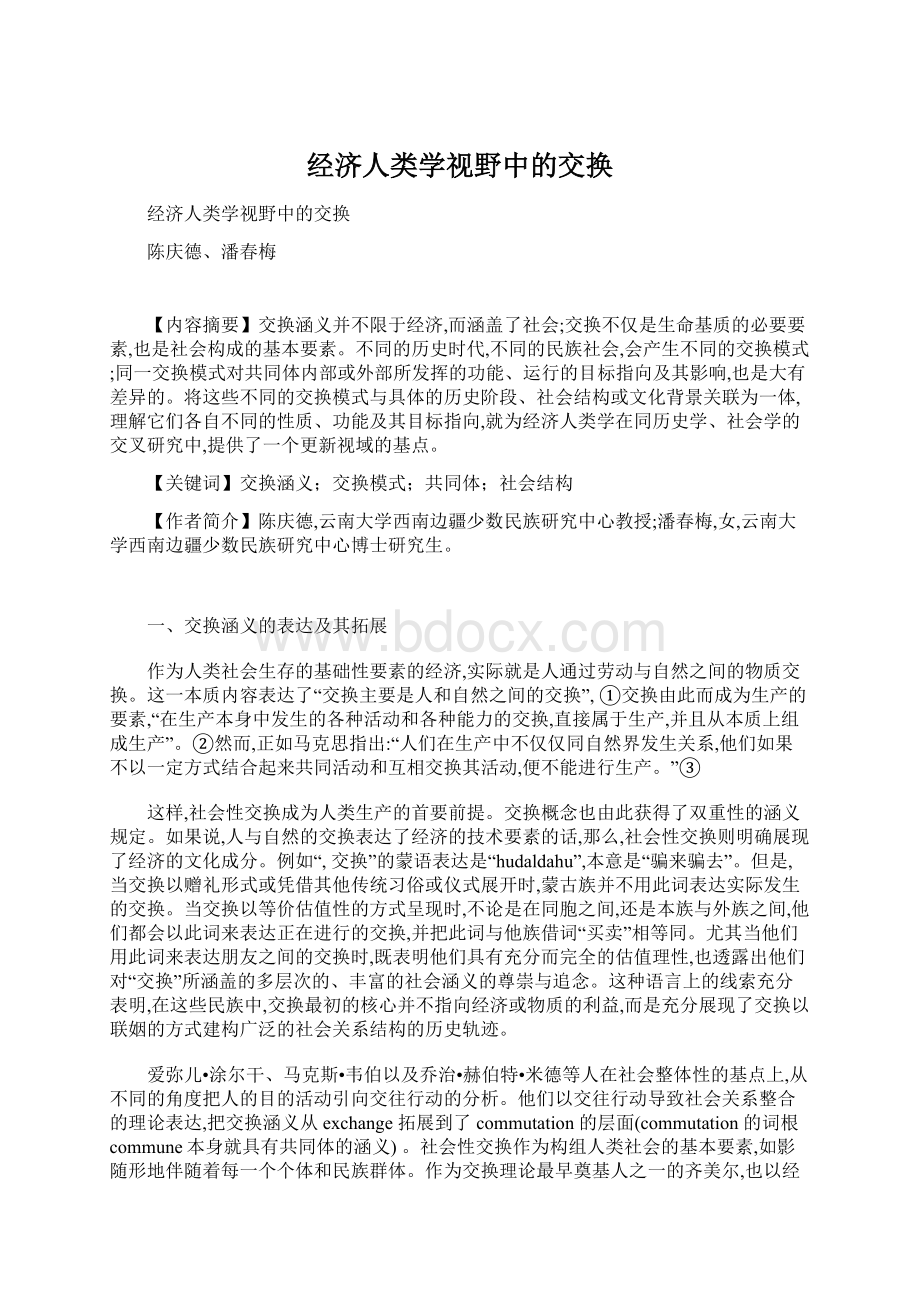
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交换
经济人类学视野中的交换
陈庆德、潘春梅
【内容摘要】交换涵义并不限于经济,而涵盖了社会;交换不仅是生命基质的必要要素,也是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
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民族社会,会产生不同的交换模式;同一交换模式对共同体内部或外部所发挥的功能、运行的目标指向及其影响,也是大有差异的。
将这些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理解它们各自不同的性质、功能及其目标指向,就为经济人类学在同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中,提供了一个更新视域的基点。
【关键词】交换涵义;交换模式;共同体;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陈庆德,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潘春梅,女,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交换涵义的表达及其拓展
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性要素的经济,实际就是人通过劳动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这一本质内容表达了“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①交换由此而成为生产的要素,“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
②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
”③
这样,社会性交换成为人类生产的首要前提。
交换概念也由此获得了双重性的涵义规定。
如果说,人与自然的交换表达了经济的技术要素的话,那么,社会性交换则明确展现了经济的文化成分。
例如“,交换”的蒙语表达是“hudaldahu”,本意是“骗来骗去”。
但是,当交换以赠礼形式或凭借其他传统习俗或仪式展开时,蒙古族并不用此词表达实际发生的交换。
当交换以等价估值性的方式呈现时,不论是在同胞之间,还是本族与外族之间,他们都会以此词来表达正在进行的交换,并把此词与他族借词“买卖”相等同。
尤其当他们用此词来表达朋友之间的交换时,既表明他们具有充分而完全的估值理性,也透露出他们对“交换”所涵盖的多层次的、丰富的社会涵义的尊崇与追念。
这种语言上的线索充分表明,在这些民族中,交换最初的核心并不指向经济或物质的利益,而是充分展现了交换以联姻的方式建构广泛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历史轨迹。
爱弥儿•涂尔干、马克斯•韦伯以及乔治•赫伯特•米德等人在社会整体性的基点上,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的目的活动引向交往行动的分析。
他们以交往行动导致社会关系整合的理论表达,把交换涵义从exchange拓展到了commutation的层面(commutation的词根commune本身就具有共同体的涵义)。
社会性交换作为构组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一个个体和民族群体。
作为交换理论最早奠基人之一的齐美尔,也以经济交换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典型模式,指出交换概念“仅仅预示了相关主体之间的一种情形或变化,而非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某个对象”,进而指出“每一种交流都必须被看作是一种交换”。
④彼德•布劳则从“社会吸引导致交换过程产生”出发,强调了社会互动作为一个整体总是采取交换的形式而得到表达。
⑤
这种理论视野的拓展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依据交换内容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物质性交换(如商品等)、社会性交换(如和亲、权力等)和符号象征交换(如仪式等);从交换所赖以立足的社会关系基点看,有直接交换、间接交换以及内部性和外部性交换;从交换主体的角度看,有主动性、被动性交换以及支配性、依附性交换;从交换结果上看,则有等价性和非等价性交换以及破坏性和建设性交换,等等。
不同的社会或文化系统中,交换可以借助经济的形式得到直接表达,可以借助权力体系得到隐含表达,可以借助仪式符号得到象征性表达,也可以借助和亲联姻得到社会表达,甚或可以通过战争形式进行极端表达。
不论从形式类型还是从功能特征上讲,交换具有多样化的存在。
它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影响着整个人类和自然界。
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假定,以及将生产划分为创造使用性的单一性生产和交换性生产之后,交往也就限定成一种为获取不能直接得到的财物而采取的间接手段,从而形成交换一词的局限性描述。
这种描述假定,在一个无分层的社会共同体中,生产所赖以进行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无需通过交易的形式来获得,而是表现为一个直接得到的既定存在。
因此,交换只表现为共同体的一种外部性活动。
这一逻辑进程的最终结果,就是把交换的涵义狭隘地限定在市场交换上。
交换的根源被追溯于两方面:
交换物品与交换者。
对于交换物品,使用价值的差异性或稀缺性,是交换得以产生的基础;而对于交换者,无论是追求物质的需要与享受,还是追求交换价值的利益所得,都是交换实现的推动力,其聚焦的核心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支配了社会,这就为经济学理论的普泛化奠下了深厚基础,导致经济学对交换概念狭隘化理解的普遍流行。
对这一主流偏见的扭转,应归功于马塞尔•莫斯。
他收集了散见于不同人类学文献中有关赠礼的民族志个案资料,以《赠礼:
古代社会交换的形式和功能》(1925)第一次对这些民族社会中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
莫斯认为,用我们所熟知的“馈赠”、“礼物”或“赠礼”等词汇来描述这些交换行为“本身并不十分确切”,这些交换行为所涉及到的观念,是一个能够引发所有那些经济行为的复杂观念“,它既不是纯粹自愿和完全白送的呈献,也不是指生产或单纯意在功利的交换。
它是在这个社会中盛行的一种杂糅的观念”。
⑥莫斯把这些活动视为一种“经济市场”的存在,只不过其“交换制度”与现代社会大相径庭罢了。
这样,市场先于商业制度,也先于货币。
⑦基于这些基本事实,他认为:
“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之前,还是在原始或低等的名义下被混为一谈的种种社会之中,似乎从未存在过所谓的自然经济。
”⑧由此揭穿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一个理论神话的骗局。
莫斯以其哲学底蕴对“赠礼”概念的总结,使之成为人类学唯一试图以哲学方式去界定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特质的概念,并将其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研究的一个基本范畴。
在由财物的禁忌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约束”的支配下,人们在进行物质交换的同时,也进行着精神的交换;交换从经济扩大到政治、宗教和社会的范围。
这些古老的交换方式既是一种物质的循环,也是人和权利的循环。
这个循环不是由市场、价值或经济效用来维持,而是由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赠予、接受和回报的义务关系来维持。
这就拓宽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推动人们去探问当市场既不具有我们所说的现代契约形式或销售形式,而又没有记名货币,甚或交换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极为不同的时候,市场是怎样运作的问题;使人们把交换与特定的经济体系、法律规范、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等关联起来分析。
一句话,开启了把交换置于社会整体性中进行分析的理论路径。
继之于莫斯,波拉尼以“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三个交换模式的提出,统合了人类社会形式纷繁的交换行为。
波拉尼这一理论性的概括,把对交换进行社会关联性的总体分析,进一步推向了结构分析的层面。
二、交换类型与社会结构的差异
把交换关联于社会进行总体性和结构性的分析路径,在不同学科中激发出深刻的洞见。
布罗代尔指出:
在人类历史实存中“,存在过许多种社会-经济交换形式,它们的多样性不妨碍它们的共存,或者正是由于它们的多样性,它们才能共存”。
⑨就是最初从区分商品与礼物出发的克里斯•格雷戈里后来也提出了修正看法:
“不存在纯粹的礼物或商品经济活动,有的只是处在相同经济领域的人们在不同情景中建构的与他人关系的不同模式。
”⑩
(一)互惠交换模式
波拉尼把互惠称为“在对称群体关联点之间的运动”。
[11]在这一模式下,交换主要是以赠礼的形式表达的。
如在萨摩亚人中,无论是贸易,还是诸如婚姻、丧葬等人生礼仪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伴有赠礼的发生。
这种赠礼制度有两大基本要素:
“一是荣誉、威望和财富所赋予的‘吗纳’;二是回礼的绝对义务,如不回礼便会导致‘吗纳’、权威、法宝以及本身便是权威的财富之源的丧失。
”[12]又如,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库拉交易圈不仅涵盖了全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把所有部落包容其中,甚至伸展到广泛的族际之间。
它首先以称为“库拉”的礼仪性物品——臂镯和项链——把各共同体的首领联合为特定的交易伙伴。
库拉物品的价值既不以其物质基质,也不以其生产耗费的劳动来衡量,而取决于其交易的次数和交易者的贪求;任何其他产品都不能与库拉物品等价。
每一次交换都在开头或启动时的赠礼和结束时的回礼的仪式形式中进行,库拉就这样以赠礼的仪式带来了称之为“gimwali”的日常生活用品交换的时机。
附属交易的货物被使用和消耗,而库拉却永远在库拉圈中循环,处于永恒的流通过程中。
[13]持有库拉物品者得到了贸易安全的保护并结成交易伙伴,使货物像涓涓细流一样不断在一个村的内部流动,并从一个部落流向另一个部落,从一个岛流向另一个岛,[14]也“使农业部落与沿海部落确立了常规的、义务性的交换”。
[15]
由此可见,互惠交换模式展现了经济交换的另一种体系和结构的存在。
首先,它明显标识出了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的结构属性。
这种根本性的结构属性不仅使经济交换“首先要交流的是礼节、宴会、仪式、军事、妇女、儿童、舞蹈、节日和集市”,而且,不论是以共同体为直接基点,还是以共同体首领为中介,交换总是在“集体之间互设义务、互相交换和互订契约”的基础上得以进行。
[16]即,交换只在人们的直接性社会关系的框架中产生。
在此意义上,可把这种交换类型称之为直接交换。
格雷戈里也曾从“商品交换建立起被交换的客体之间的关系,而礼物交换则是建立起主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指出“礼物交换是一种在拥有互相依赖性地位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不可异化物品的交换,交易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定性的关系”。
[17]值得强调的是,它并非是一种偶然的、不稳定的交换形式,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稳定的,甚至是建立在交易双方终身关系基点上的交换形式,并且“有神话的背景,有传统法规的支持,有巫术仪式的伴随”。
[18]这一结构性的根本制约,使交换乃至其他不同的经济行为也总是表现为一个社会的“总体性”行为。
有如在特罗布里恩群岛所展现的事实:
“部落生活的整体渗透着不断的给予和索取;每一个仪式、每一项传统规定和风俗都存在相关的物质上的赠礼与回礼;财富的给出和接受是社会赖以组织、酋长的权力赖以显示、亲属关系赖以维持、法定关系赖以体现的主要手段。
”[19]同样,在西北太平洋海岸的波特拉赤,作为确认的一种基本行径“,这种认可既是军事的、法律的、经济的,也是宗教的;而且在每一方面均兼有该词的种种含义”。
[20]礼物的“意义在于它们背后的传统和风俗所赋予的社会力量,它给这些物品以特别的价值,使它们笼罩着浪漫的光环”。
[21]这样,礼物成为了社会话语的织线。
又如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所指出的:
“礼品在构成社会的同时使文化从人的生物性中解放出来。
”[22]从而使赠礼并非物品的纯粹传递,而是“带有确定意义的社会行为”。
[23]赠礼的意义是表达或确立交换者之间的社会联结。
赠礼与回报赋予参与者一种信赖、团结、互助的合作语言。
其次,这种交换的动机和目的并非纯经济的或物质利益的,而是社会总体性的,甚至更主要的动机与目的是聚焦于道德、感情、义务等等的社会性要求上。
如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各个家庭都同样生产甘薯,但他们种的甘薯和吃的甘薯是不同的:
在收获季节,男人把收获的甘薯,送到他的姐妹家,而他这个家庭所食用的甘薯,则由其妻的兄弟供给。
这种交换不产生获利性或差额累积性的事实,对经济学有关相同的使用价值不交换的定律提出了最尖锐的根本性挑战。
这一挑战表明,经济交换是可以借助不同形式而得以表达的;交换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可以各有千秋的。
在特罗布里恩群岛被称为大远航(Uvalaku)的“这种最完整、最庄严、最高贵、最富竞争性的库拉中”,[24]其主要目的是确认不同部落群岛之间“固定和永久的身份”,固化各群岛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延伸成大规模的关系网。
正是基于这种社会性的目标,在种种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其附属交易的经济机制“,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形式,意味着高度的相互信赖和商业声誉”。
[25]“在商品和礼物交换系统中,人们都试图实现最大化:
礼物经济活动中的人们尽可能多的送出物品,是为了实现社会关系的最大化;商品交换中的人们则是力图实现货币财富和占有物的最大化”。
[26]
最后,互惠交换模式在赠礼的表达中,在直观的表象上,虽然表现为自愿的形式,但在上述特质的规约下,实质上却是极为严格的义务性的,“甚至极易引发私下或公开的冲突”。
[27]这就使得该交换模式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获得一个极富弹性的生存空间。
它既可广泛地存在于无分层的共同体中,成为连接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纽带,也可以在分层社会中获得表达。
如上述的库拉、波特拉赤等等的交换制度,就深深地纠缠在声望等级中。
它们在发挥带动日常用品交易的经济功能的同时,亦在增强和保护着已出现的阶级结构,发挥着巩固阶层等级制的功能。
正是基于此,萨林斯以“概化互惠”(generalizedreciprocity)、“平衡互惠”(balancedreciprocity)和“负性互惠”(negativereciprocity)的细化,展现了这一交换模式在不同社会结构中可能的存在与可能的功能趋向。
尽管礼物交换的重心不在于等价“,它不能是讨价还价和算计之后的即时等价交换”;[28]也不能把它简约为物物交换。
但是,当它存活于等级社会中时,以赠礼形式而表达的交换也会加入计量因素,这样,在互惠交换中出现了两种情况:
一是用等量物品偿还礼物,或以为对方的服务来抵偿礼物;一是赠礼的一方利用他人的劳动,达到抵偿礼物的目的。
当受礼者不能用物品偿还,而只有用为对方服务的方式来偿还礼物时,受礼者往往就会成为赠礼者的依附者或追随者,或者是赠礼者赠送多得使对方回不了的礼物来羞辱受礼者,或是以不等的物质交换,来获取权力秩序或政治声望上的回报。
这就可能使礼物的交换成为竞争与抗衡的特殊语言,使互惠交换蕴含了不平等交换的趋向。
(二)再分配交换模式
波拉尼认为此交换模式标识了“敛集于一个中心而再次分发的运动”。
[29]它意指一种“支付”与“返还”的连锁系统,即共同体成员向某个政治性或宗教性的权力中心进行财物与服务的义务支付(税收、贡租等等),然后由这个权力中心依其某种目标重新分配给共同体成员。
这种集中化的交换模式展现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
如部落共同体成员向部落酋长的呈献;部落联盟中各加盟部落向盟主的缴纳;依附农民对封建领主的贡赋;以及古代世界范围内一切帝制国家或王国的“国家礼仪”和“贡租大祭”等等。
从总体上说,这种交换模式的直接立足点,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身份属性。
所以,仍然可以把它视为经济交换的直接交换类型。
但是,对任何一个规模得到迅速扩展的社会来说,这一模式内含的直接交换性质的局限性,使其不能总体上囊括全社会,因而,这一交换模式大体上呈现出与其他多种不同交换形式共存的格局。
时至近代,在容纳着傣、布朗、拉祜、德昂、基诺、哈尼等若干民族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傣族最高首领“召片领”成为这一广阔区域土地的最终所有者。
在此区域所有的不同民族群体,均以村寨为单位向“召片领”以及各级首领缴纳贡赋,而纳入了再分配的交换体系中,而与此共存的还有众多形式各异的交换类型。
在以家族、氏族或村寨等不同的公有框架及其所组成的多种形式的共耕关系中,就广泛存在着直接融入生产,并在本质上组成生产的多重的交换形式和内容。
这些交换的目标指向,是对小共同体公有经济运行的维系,同时还有村寨内部、村寨之间个体或群体的赠礼交换和商品交换,甚至凭借于“茶马古道”的开辟而进入了跨区域商品交换的体系,等等。
[30]
再分配交换模式与多种交换形式共存的格局,常常使它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社会实施社会控制的基本系统,这在中央集权的社会中表现尤为突出,也使得它在不同的时代或社会中,表现出主导性或辅助性的存在状态。
如在中国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帝国时代,在国家编户下的各类小生产者、商人、地主与皇权之间,以实物形态为主的直接交纳,构筑起一个有效的再分配交换模式。
一方面,皇权统治机制的运转,也先决性地要求藉市场的运行,把其所攫取到的经济剩余转化为各级官吏的俸禄,并支撑各级政府机构的运转,充分展现了这一再分配交换模式对市场交换的倚重。
另一方面,与此并存而共同构筑社会总体交换体系的,不仅有施坚雅所归纳的,即由标准集市、中间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大城市、区域城市、区域中心、中心都会所构成的8个等级结构的市场交换体系,[31]而且有浸淫于城乡日常生活中的,旨在确认和加强各种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的赠礼交换,以及以“蕃贡继路,商贾交入”[32]为基本形式的各种外部性交换。
即便在现代社会中,再分配交换模式仍然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得到展现:
或者作为对市场经济的一种修正,成为实施所谓“福利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或者服务于某个权力中心特定的政策目标,成为削弱或扶持某一社会阶层或经济集团的有效手段。
(三)市场交换模式
波拉尼把市场交换称为在特定生产体系下“人手”之间所发生的反向运动。
[33]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是使私人劳动或个别劳动获得社会承认,实现其内含的社会劳动性质的基本途径。
它是由直接交换到间接交换的一种形式变换,也是以价格构建起的一个自我调节系统。
从而,它把具有不同经济贡献的地区、进行不同专业生产的人们联结为一个统一整体。
它依凭价格这一共同语言“,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使商品所有者的行为“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
[34]可以说,市场交换模式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奠定了一个深厚的外部基础;也可以说,市场交换模式无论是其存在的扩展,还是其功能的发挥,在现代社会都得到了极致化的表达。
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在资本主导下的市场交换,只是市场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以此作为界定市场交换模式的唯一标准,也是有所偏颇的。
市场交换作为商品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而产生出货币形式后,这一经济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某种社会的制度性要素合力参与的结果。
但是,在交换关系的发展中,每一更高层次上已完善起来的价值表现或流通形式,并不排斥原来低层次上旧有生产所提供的商品,而是把各个不同层次的生产方式所提供的商品,融会在已进一步完善了的流通形式中。
不论商品源出于奴隶之手,还是由农民、公社或国家生产的产品,甚或是渔猎-采集共同体提供的产品,都可以交错在一起,构成一个总的商品流通或商品运动。
这种运动既不要求生产者一定要隶属于某种特定的经济成分或要素(如资本),也不要求这种要素对生产过程进行直接的支配。
市场交
换的这种总体流通运动“,按它的性质来说,包括一切生产方式的商品”。
[35]交易、货币和市场在本质上各有其独立的起源,即便有市场的地方,“需求-供给”机制也未必就是联动的;以“需求—供给”的价格基质为基点的市场,是在晚近的社会中才发展起来的。
齐美尔曾指出:
“人们甚至往往忽视,经济交往中的很多东西也还有某些不能用货币来表达的方面……对于农民来说,土地里面不仅仅蕴藏着单纯的财富价值,而且还有某些别的东西。
对他来说,土地是有益劳动的可能性,是一种利益的中心,是一种指明方向的生活内容,一旦农民不是占有土地,而仅仅是占有它的以货币形式折算的价值,他就失去了这种生活内容。
”[36]
可以看到,所谓市场,无非是一种创造交换环境的制度复合体。
由于人们的交往关系各自依附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关系和结构在起源上是互不相关的),因此市场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系统,不可避免地要与特定的社会产生结构性关联。
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明确指出:
“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
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
”[37]因此,认识市场交换与社会的结构性关联,理解市场不同的生存基础、作用及其发展的历史差异,是更为贴切地阐释不同民族共同体经济实存关系的关键问题。
在土地私有的产权关系和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结构与局限性的自然差异结合中,整个社会的生产从一开始,便只有在对某种资源和手艺的独占关系下进行。
这种局限性的片面生产,与个体生产者不断发展的全面性需求相冲突,客观上使市场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必要组成。
尤其是当资源和个体生产者自身能力的极限约束,使原来的某种主体性生产出现短缺时(这种短缺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这种原有的主要生产不足以吸收现实的劳动力资源;一是这种生产之产出不足以供给生产者的基本需要),就会加速促进生产者超越自身的直接需求,而进行其他副业或专门性生产,并藉市场的运行来实现自身再生产过程的供求平衡。
因此,小农经济固然具有强烈的自给性质,但当小农个体家庭独立为基本的生产单位时,却没有同时成为经济自给的基本单位。
小农虽然以个体家庭组织起独立的生产,但其经济全过程的运行并不限于家庭,甚至也不为村庄狭小的范围所制约,而是扩及到了由一定市场联结起来的村社聚落。
这种被称之为“标准集市”[38]的市场形式,成为小农经济实现其自给性质的枢纽,它不仅是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市场存在,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可以说,用“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取代的话语,虽简便易行,却无济于事。
用此话语来解说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的理论错位,抹杀了市场交换这一形式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
如果说,英国市场交换的经济运行形式是以各种分散的专为市场而生产的小生产者逐渐聚拢于商业资本活动的中心的方式,走上了以都市为基点的商品经济集中化的发展道路,并由此直接导致了近代工业化变革的革命性结果。
那么,在同一时期,当这一经济运行形式在英、法、荷兰等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时,在德国、波兰以及斯拉夫地区,大规模的粮食商品化生产却直接推动了“再版农奴制”的复活。
在此之前的欧洲的香槟集市,也曾以大规模商品交换,一度繁荣了佛兰德尔地区的庄园经济。
从世界范围来看,阿拉伯民族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商业集团而出现于历史中的,远距离贸易在这个民族中起了格外重要的作用,阿拉伯文化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形态始终表现出了商业性质。
同样,在17世纪以前的长时期中,非洲也已和旧世界的其余部分建立了交换关系,它的商业活动跨越了撒哈拉沙漠,从横亘达喀尔与红海之间的热带大草原一直伸展到地中海。
这一商业活动成为热带非洲社会组织的重要基础之一,并成为整个旧世界(地中海、阿拉伯地区和欧洲)在美洲发现以前,获取黄金的主要产地。
虽然大规模商业活动的这两个实例极为突出,但它在“和比较贫困的公社制或贡纳制社会形态”[39]的联系中“,大规模贸易并不产生资本主义,而且大规模贸易本身也不是资本主义的”。
[40]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
对某个特定的共同体来说,当市场交换这种经济运行形式只表现为一种外部性的存在时,它并不能把整个的社会经济整合为一体,共同体内部的不同生产方式与共同体外部的商品交换,只是拼接成了相对分割的并存状态。
市场交换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产生于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的、新的经济结构的产物。
它可以存活于各种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亦可以由不同因素促成其发展并导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由千家万户零星分散的小生产的简单集合,可以凑集成庞大的社会商品运动,但它只表现为许多同质而不凝结的国内细胞。
同样,如果说它的发展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么,相反的,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
[41]可见,市场交换模式在特定民族中的一个具体发展实例,是不足以成为其世界性发展的一般标准和特征规定的。
事实上,在市场中关联着两种有区别的现实的交织,即社会关系的生产和产品生产过程流通的社会形式。
现实的这两个方面并不处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