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湟水流域历史文化追忆之八乐都篇下.docx
《青海湟水流域历史文化追忆之八乐都篇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青海湟水流域历史文化追忆之八乐都篇下.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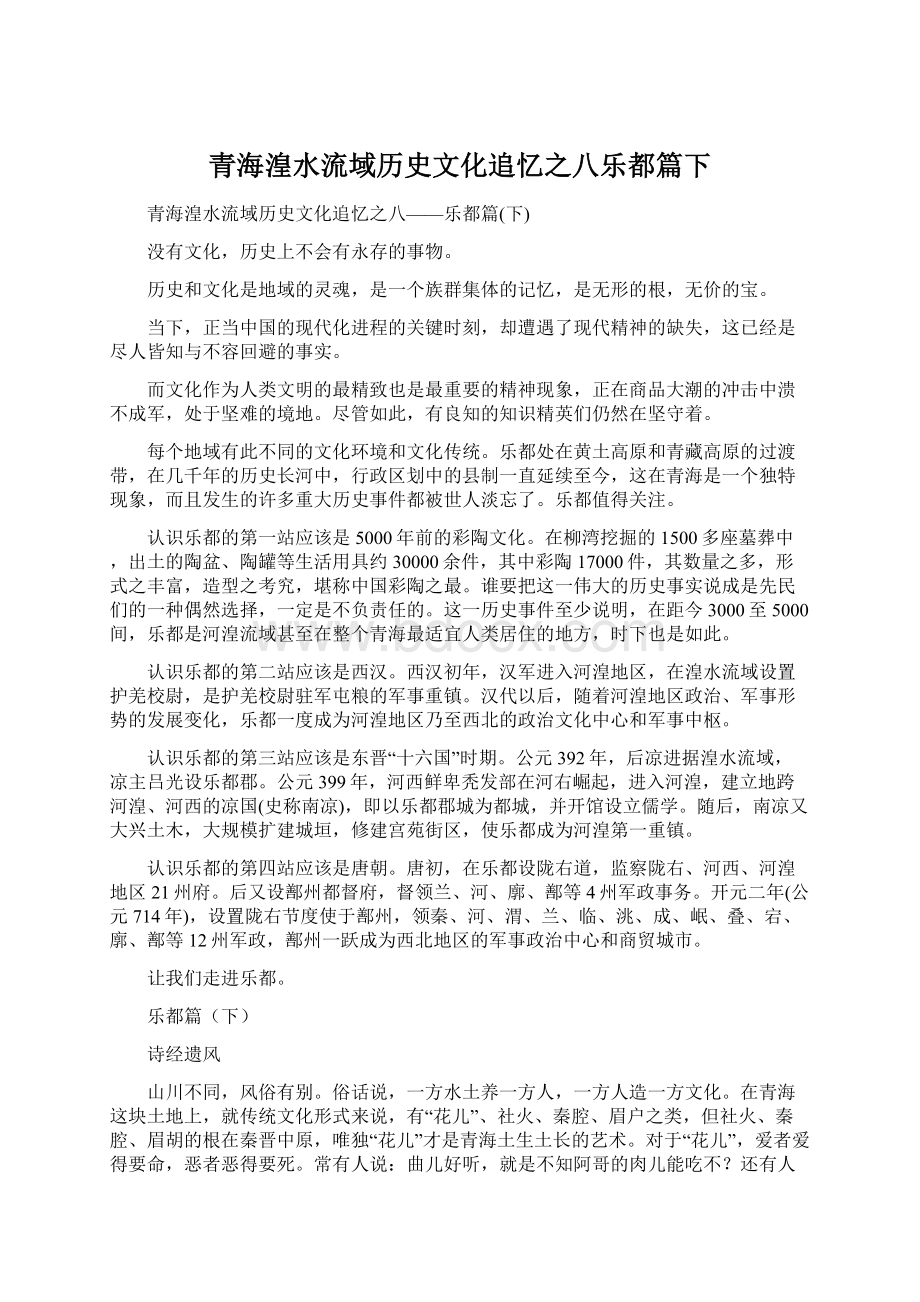
青海湟水流域历史文化追忆之八乐都篇下
青海湟水流域历史文化追忆之八——乐都篇(下)
没有文化,历史上不会有永存的事物。
历史和文化是地域的灵魂,是一个族群集体的记忆,是无形的根,无价的宝。
当下,正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却遭遇了现代精神的缺失,这已经是尽人皆知与不容回避的事实。
而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最精致也是最重要的精神现象,正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中溃不成军,处于坚难的境地。
尽管如此,有良知的知识精英们仍然在坚守着。
每个地域有此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
乐都处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行政区划中的县制一直延续至今,这在青海是一个独特现象,而且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被世人淡忘了。
乐都值得关注。
认识乐都的第一站应该是5000年前的彩陶文化。
在柳湾挖掘的1500多座墓葬中,出土的陶盆、陶罐等生活用具约30000余件,其中彩陶17000件,其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造型之考究,堪称中国彩陶之最。
谁要把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说成是先民们的一种偶然选择,一定是不负责任的。
这一历史事件至少说明,在距今3000至5000间,乐都是河湟流域甚至在整个青海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时下也是如此。
认识乐都的第二站应该是西汉。
西汉初年,汉军进入河湟地区,在湟水流域设置护羌校尉,是护羌校尉驻军屯粮的军事重镇。
汉代以后,随着河湟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乐都一度成为河湟地区乃至西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中枢。
认识乐都的第三站应该是东晋“十六国”时期。
公元392年,后凉进据湟水流域,凉主吕光设乐都郡。
公元399年,河西鲜卑秃发部在河右崛起,进入河湟,建立地跨河湟、河西的凉国(史称南凉),即以乐都郡城为都城,并开馆设立儒学。
随后,南凉又大兴土木,大规模扩建城垣,修建宫苑街区,使乐都成为河湟第一重镇。
认识乐都的第四站应该是唐朝。
唐初,在乐都设陇右道,监察陇右、河西、河湟地区21州府。
后又设鄯州都督府,督领兰、河、廓、鄯等4州军政事务。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设置陇右节度使于鄯州,领秦、河、渭、兰、临、洮、成、岷、叠、宕、廓、鄯等12州军政,鄯州一跃成为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和商贸城市。
让我们走进乐都。
乐都篇(下)
诗经遗风
山川不同,风俗有别。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一方文化。
在青海这块土地上,就传统文化形式来说,有“花儿”、社火、秦腔、眉户之类,但社火、秦腔、眉胡的根在秦晋中原,唯独“花儿”才是青海土生土长的艺术。
对于“花儿”,爱者爱得要命,恶者恶得要死。
常有人说:
曲儿好听,就是不知阿哥的肉儿能吃不?
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说:
扯着嗓门大喊大叫,让人怪痒的。
于是,便有女人在“花儿”会上,见而不视,听而不闻;也有老人骂那些唱“花儿”和“少年”的把式们不正经。
所以别的歌唱艺术可以走向世界,唱红五大洲、四大洋,唯“花儿”则如西北人一样,厚厚道道,恋山恋水,恪守泥土。
多么顽固的乡土观念啊!
“花儿”几经变腔走调,让朱仲录、苏平、马俊们精心经营,也有过打出国门的辉煌,但毕竟是小打小闹。
她的市场在西北,确切地说,应该在青海。
几百年来,“花儿”没有被淘汰,而且越唱越红,这使多少人疑惑。
其实,只要你了解了这里的人文景观,就不难理解。
先不说南方北方之别,只要你乘陇海铁路线走一趟,西行的列车过了宝鸡,自然景观就会突变。
辽阔的地平线,褐黄的山梁,在这大背景下,远远横着黄泥土庄廓,古老的像长城;冲天而起的白杨,粗而壮,骨中有肉,肉中见骨,而它的绿叶却小似铜钱,在西风中翻翻覆覆,张扬着生命。
这时候或许你在想:
生命,在这里是多么艰难;活下来,又是多么辉煌。
并且能细细地体验出生存与生活的准确概念。
你甚至在这一瞬间明白了这里的地理景观与“花儿”粗犷的音律是多么和谐统一。
先去接触这一方人吧,活脱脱一群龙的传人:
个高眉浓,膀大腰圆,粗大的手脚,完全是一幅力的造型。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物质文明日新月异,中西方文化相互渗透的大环境下,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轻薄这些天底下的老实人,更没有资格嘲笑这些老实人用劳动创造的“粗野”的“花儿”艺术。
黄昏,残阳如血;芨芨草在山梁上化成了孤独的惆怅。
你听,山梁上“花儿”传递着一种古朴而悠远的情思,蕴含着对生命的啸吼、对命运对爱情的挑战,这山与那山的拖腔互相交织、冲撞。
这心上的“花儿”,原来是青海的天籁地鸣啊。
在干旱时或许就是汩汩流动的雨水;在阴雨连日不开时,或许就是一轮沙沙的黎明声和一轮嫩嫩的骄阳。
就这样,老老少少唱,男男女女唱,唱生活唱爱情。
生活在这里的乡下人,要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和聪明才华,除了正月的社火,不唱“花儿”还有什么呢?
尤其是青海浅脑山地区,屋前是山,屋后是山,生是黄土炕,死是黄土堆,“花儿”成了唯一能充分发泄情感的艺术。
天无限遥远,地无限空旷。
就这样,“花儿”便成了大苦中的大乐。
当太阳西斜,田野累得精疲力尽,人跟老牛软绵柔和地躺倒在夕阳下,卷一支老黄烟,对着青天厚土喊一首“花儿”,那满身的皮肉之困、心头之乏,便烟消雾散。
此时此刻,“花儿”便成了他们心目中的一方青草地,就那样在他们的意念中疯长着。
“花儿”与他们,要和五谷杂粮、互助青稞酒、乐都沙果,以至循化花椒一样,成为生命的能量和调味品。
席无酒不热,生活没了“花儿”,便少了情趣。
他们高兴时喊破天,嗓门像烈性炸药爆响一样,一腔一音,要把整个身心空荡荡粉碎在空中,洋溢着一种震憾人心的生命强音;痛苦了,唱“惆怅”,拖腔悠悠长长,一头山南,一头地北,让你意会到一种揪心裂肺的生离死别。
但拖腔末时,往往让你看见一朵“牡丹”,说透了,是一种对美的向往。
在“四月八”、“端午节”、“六月六”,那种难以想象的狂喜、激动和雄壮,如黄河解冻,如雪山崩裂,那力度,那气势,胜过任何歌唱场面。
1980年,十六岁的我第一次去赶瞿昙寺的六月十五“花儿会”。
一进岗沟峡,男男女女的人们打着伞赶会场,从沟口到罗汉山下,人们把“花儿”唱成了一条彩河。
在瞿昙寺会场,从黎明到子夜,直唱得流云含情,云雀唱秋,以至瞿昙寺的雄伟只成了“花儿会”的陪衬。
树林间、草丛中,一头是男,一头是女,冗长的拖腔叩击着对方的胸膛。
此时此地,我猛然觉得自己心中一股强硬的气魄随同着“花儿”的节奏,在胳膊上暴起了肌肉疙瘩。
“花儿”啊,你是如此激动着人们的心!
我始终捉摸不透那次胳膊上暴起的肌肉疙瘩,直到一九八六年“花儿”皇后苏平来乐都进行首次“花儿”专场演唱,说她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唱得泣不成声,还说有人曾请教“阿哥的肉儿”如何理解才对时,她寻思了好一会儿找不出合适的答案,只好用了“深不可测,只能意会”来解释。
其实苏平的回答是有道理的。
三十岁以前我对“花儿”只处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三十岁后我对“花儿”和十六岁那年莫名其妙的肌肉疙瘩,才有了一点理性的认识。
“花儿”,不仅仅是表现一些男男女女之事,她以无限广阔的背景包容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生活、对美的一种永恒的追求和向往,是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对生命历程的一种浓缩,是青海这片土地上孕育的《诗经》。
《诗经》是殷、商、周五百年间的“花儿”和“少年”。
随便拣几首瞿昙寺庙会上的“花儿”和“少年”,在《诗经》里就可以找到类似的《风》,比如:
高山上拉雾(者)下雨哩,
四山上响雷着哩。
早期晚夕(者)想你哩,
你心里想谁(者)哩。
(《诗经·卫风·伯兮》)曰:
……其雨,
其雨,
杲杲日出。
愿言思伯,
甘心首疾。
说成“少年”则是:
盼望(之)雨点儿不下了,
又出了红红的太阳。
一心把我(之)阿哥想,
甘心头昏儿脑胀。
又如:
白绸子染成宝蓝了,
蓝绸子擦了(个)汗了。
尕手里抓住(者)哭憨了,
终久是我俩儿见了。
(《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曰:
野有蔓草,
零露溥兮。
有美一人,
清扬婉兮;
邂遁相遇,
适我愿兮。
说成“花儿”则是:
地上(之)草儿青又青,
露珠儿滚圆着哩。
尕妹儿生就(者)大眼睛,
今儿碰上(之)巧,
我(之)想心上到了。
我甚至认为,青海的“花儿”和“少年”如此绝妙的比兴艺术是明朝官方诗人们的创作流传到青海来的,至少进行过艺术加工,那种炉火纯青的比兴,那种精巧别致的押韵,无不闪耀着艺术的光芒。
有一次,我去瞿昙寺六月十五“花儿”会采风,一对妇女在聊天,居然没有一句是口语化的散文,所有的对话都是押韵的。
我惊奇这一对妇女的语言天赋了,问及这一对妇女都没有进过一天学堂。
然而,让我更加吃惊的是在一个娘娘庙里一个女人求子的祷告,她郑重地跪在王母娘娘的神像前,不是叙说求子的心愿,而是唱出来的,你听:
去年我来了,
你就给我答应着哪,
今年我来了,
我是跟你老要着哪,
明年我来了,
我是手里抱着哪,
咯咯嘎嘎地笑着哪!
这是我听到的最美的祷告词。
我甚至认为,一个乡土作家不读民歌,成不了一个好的乡土作家的。
欣慰的是,“瞿昙寺花儿会”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了保护。
在青海这片土地、这片环境、这片气氛中,面对着这天底下最忠厚老实的人,“花儿”是最逞能的,她的艺术和魅力是同生活和生命并存的,客居的文人无论如何是创作不了的。
人老珠黄,没有盼头了,生命终止了,“花儿”也便枯了。
“花儿”,人们心目中的“花儿”啊!
惊世名片
早在5000年前,乐都,就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而叩开这湟水谷地千年文明之门的现场,就是一个叫柳湾的村子。
柳湾啊柳湾,你是点燃文明的火炬,在美丽的疤痕上还在闪烁灿烂的火焰。
这些在地下沉睡了5000多年的绚丽多姿的彩陶,把一个史前农耕文明高度成熟的高原古都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挖掘的1500多座墓葬中,出土的陶盆、陶罐等生活用具约30000余件,其中彩陶17000件,其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造型之考究,堪称中国彩陶之最。
尽管这种远古文明在历史进程的某个时期发生了断裂,许多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还在艰难地寻找这个链条,但这个文明的存在和曾经的辉煌是不可置疑的。
这正好引证了人类社会进程中,人们傍水而居、缘水而兴的必然选择。
古代两河流域、古希腊、古印度都无一例外。
日月天华,天籁中的先族们,用一双农耕的茧手,摸捏出一个灿烂辉煌的彩陶世界,留下一串无法破译的千年之谜,让后人望而生叹,以致在著名作家张承志的笔下,将湟水破译成一条彩陶流成的河。
款款地,款款地步入柳湾彩陶博物馆的展厅,这里充满了庄严肃穆和让人猜测、探究的气氛,喧嚣的尘世对这里来说是一个不太和谐的音符。
轻轻地,轻轻地步入展馆,生怕踩痛了历史,冲撞了祖宗,因为就在我们脚踩的黄土深处,还有我们许多沉睡的宗亲。
这里很静,静得就像中华民族的沉毅性格,静得也一如智者多思,倩女凝神。
以其精巧的布局、翔实的图文、逼真的模型、精选那些能够重塑昨日的原料,向世人诚实地展示了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齐家文化,辛店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距今约五千年的漫长历史时光里先祖们稼穑的文化果实;揭开了我国黄河上游最大的一处氏族社会公共墓地的神秘面纱;重现了已经成为典故的古代先民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多彩的精神世界的原版,同时也隐透着人类在沸腾起的一种原始冲动里所蕴含着的伟大的渴望与追求。
让我们虔诚地走进泱泱彩陶的王国吧。
马家窑文化,造型多样,构图精美,风格独特。
这一时期的制陶业十分发达,以精美的彩陶著称于世。
器形有壶、罐、瓶、钵、盆等,多为细泥橙黄色陶质,表面打磨十分光滑,陶质坚硬,造型匀称,上下和谐,别致优美。
纹饰长见的有弦文、波纹、旋涡纹、圆圈纹等,多饰于陶的腹部。
通体绘彩,在盆内施内外彩,口沿繁彩是其陶的特点。
色彩单纯明快,在细腻光亮的橙色陶胎上,绘以各种花纹,用笔飞动流畅,多以优美的弧线来往翻回,勾连往复,图案布局和谐严谨,具有流线性韵律和强烈的动感。
这一时期的彩陶已进入鼎盛时期,是对自然和劳动的形象模拟。
5000年的历史是漫长而悠远的,但人类文化的脉血是有源可寻的,而且永远充满着旺盛的生命。
那些用黄泥巴摸捏而成的彩陶的幽幽泛青的层面上,虽然有上百种的纹样,但万变不离其宗,透过黄土深埋过的斑斑痕迹和天长日久虫蛀的穴孔,我们不难看出,人类文化的结晶深埋于厚土之中,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同样也要承受苦难的锻造,关于这一点,让我越来越怀疑“人死如灯灭”的真理。
让我们细细品味这上百种纹样,万变之中的宗多么酷似于一种叫青蛙的物种,而且这些蛙的变体纹和神人纹,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原始人最原始最朴素的“美观”和“装饰”而已,并无具体的含义和内容,如果我们对先祖们精心创造的这些彩陶和彩陶上繁多的蛙纹,仅仅理解成一种对均衡对称的最初快感,那是远远不够的。
人类的文化不论处在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只要他以一种生命的形式存活下来,就一定有其复杂的意念和想象的意义在内。
我们不妨走进生物学的领域,亲近青蛙吧。
青蛙是水陆两栖动物,但曾被奉为水神。
青蛙肺小而薄,需要依靠皮肤帮助呼吸,天气的阴晴变化对青蛙是特别敏感的,因此蛙鸣变化可预知天气的变化,于是便有了青蛙兆雨的经验。
居住在湟水谷地高台上的原始先民,受来自自然界各种灾难的压迫,误以为青蛙有某种神秘而伟大的力量在支配雨水的降临,致使大自然的种属和谐共处、风调雨顺,便产生了以蛙为对象的水神崇拜。
当稻谷丰收的时候,他们以超度先祖的心情生旺窑中的柴火,除了生活的需要,把自己复杂的意念和想象融化在一个个的彩陶之中,也许这便是最早的彩陶文明,说穿了是一种水神崇拜。
其实柳湾文明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彩陶文明和水神崇拜,说到底是一种林牧农耕相间以农耕为主的湟水文明。
从出土的独木棺(一段圆木,中间凿成船舱状,形似木舟),足见当时植被林木的繁茂(这为我们研究湟水流域的土地和植被退化提供了信息);从出土的舞蹈花纹彩陶盆来看,三五人连臂踏歌的图案,我们不难想象先民们劳动之余在柳阴下或小河边载歌载舞的欢乐情景。
农耕文明的前提取决于自然环境。
乐都东有老鸦峡,西有小峡,春夏秋冬四季风都无堵挡,吹得畅快自在,稼禾长得也自在,加之湟水千年沉积的沃土,形成了平坦富饶的狭长谷地,沉淀悠久的农业文明是很自然的。
沿湟水一线东西长六十四公里的川水六镇高店、雨润、碾伯、岗沟、洪水、高庙,古来就有发展农业的良好基础。
以川水为核心的“一村一品”农业经济逐步向沟岔辐射,规模型经济在东部农业区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这是—块养人的地方。
日月经天,往来升降,纳黄土之精气,吸湟水之脉血,尽万物之情态,乐都成了三百里湟川的“瓜果之乡”,说乐都的沙果子比西宁的鸡蛋大,有点言过其实,但从中透露的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