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docx
《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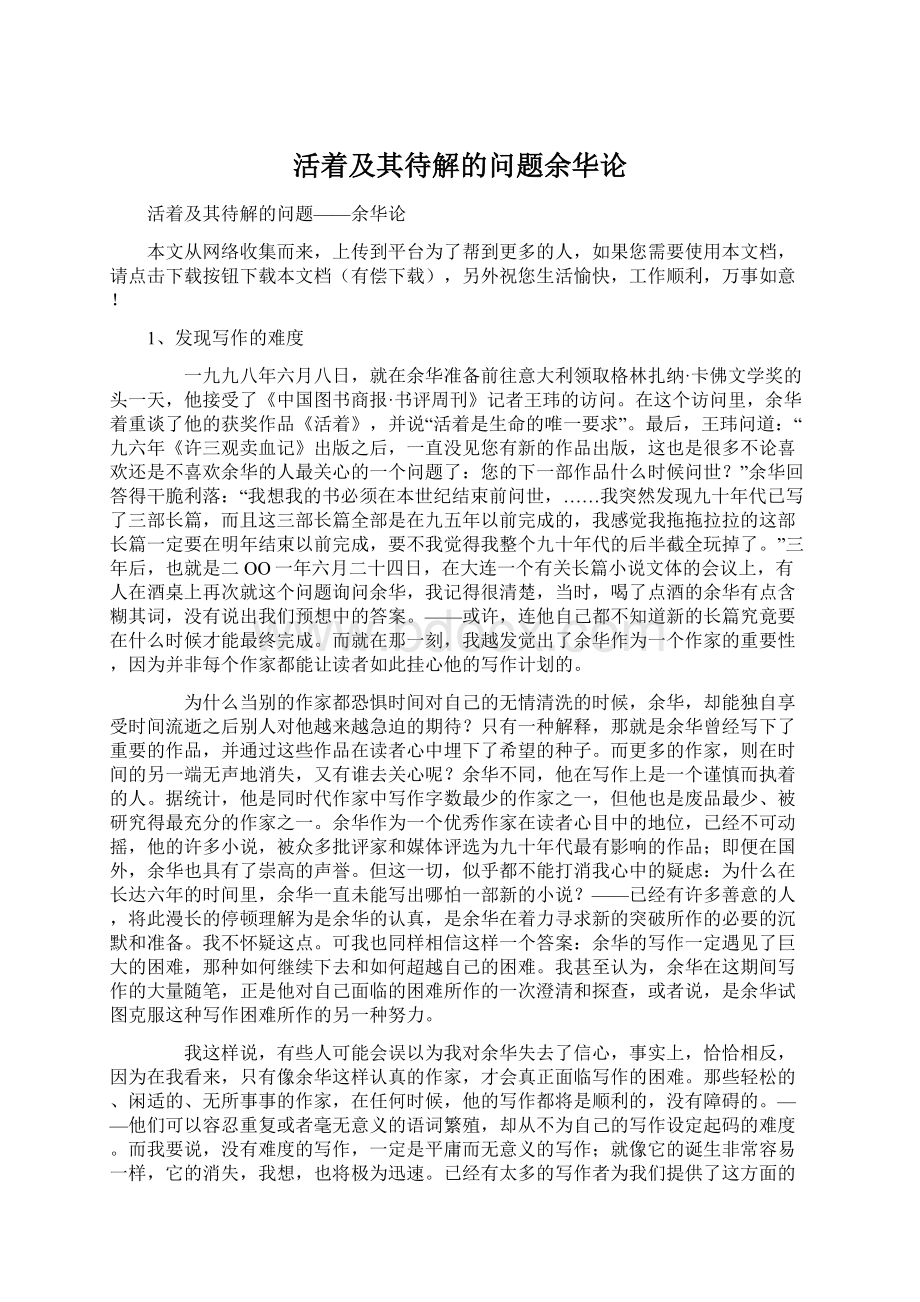
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
活着及其待解的问题——余华论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发现写作的难度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就在余华准备前往意大利领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的头一天,他接受了《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记者王玮的访问。
在这个访问里,余华着重谈了他的获奖作品《活着》,并说“活着是生命的唯一要求”。
最后,王玮问道:
“九六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之后,一直没见您有新的作品出版,这也是很多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余华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您的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问世?
”余华回答得干脆利落:
“我想我的书必须在本世纪结束前问世,……我突然发现九十年代已写了三部长篇,而且这三部长篇全部是在九五年以前完成的,我感觉我拖拖拉拉的这部长篇一定要在明年结束以前完成,要不我觉得我整个九十年代的后半截全玩掉了。
”三年后,也就是二ΟО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大连一个有关长篇小说文体的会议上,有人在酒桌上再次就这个问题询问余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喝了点酒的余华有点含糊其词,没有说出我们预想中的答案。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新的长篇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才能最终完成。
而就在那一刻,我越发觉出了余华作为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因为并非每个作家都能让读者如此挂心他的写作计划的。
为什么当别的作家都恐惧时间对自己的无情清洗的时候,余华,却能独自享受时间流逝之后别人对他越来越急迫的期待?
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余华曾经写下了重要的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在读者心中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而更多的作家,则在时间的另一端无声地消失,又有谁去关心呢?
余华不同,他在写作上是一个谨慎而执着的人。
据统计,他是同时代作家中写作字数最少的作家之一,但他也是废品最少、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
余华作为一个优秀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他的许多小说,被众多批评家和媒体评选为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即便在国外,余华也具有了崇高的声誉。
但这一切,似乎都不能打消我心中的疑虑:
为什么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余华一直未能写出哪怕一部新的小说?
——已经有许多善意的人,将此漫长的停顿理解为是余华的认真,是余华在着力寻求新的突破所作的必要的沉默和准备。
我不怀疑这点。
可我也同样相信这样一个答案:
余华的写作一定遇见了巨大的困难,那种如何继续下去和如何超越自己的困难。
我甚至认为,余华在这期间写作的大量随笔,正是他对自己面临的困难所作的一次澄清和探查,或者说,是余华试图克服这种写作困难所作的另一种努力。
我这样说,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我对余华失去了信心,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像余华这样认真的作家,才会真正面临写作的困难。
那些轻松的、闲适的、无所事事的作家,在任何时候,他的写作都将是顺利的,没有障碍的。
——他们可以容忍重复或者毫无意义的语词繁殖,却从不为自己的写作设定起码的难度。
而我要说,没有难度的写作,一定是平庸而无意义的写作;就像它的诞生非常容易一样,它的消失,我想,也将极为迅速。
已经有太多的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生动例证。
但余华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作家,所以,他为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异乎寻常的难度:
他的每一部重要作品出现,几乎都是一次腾跳,一次逾越,一次精神和艺术的攀援。
《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是这样,《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也是这样。
我相信,正是因为余华对于写作难度的智慧警觉,才使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了先锋作家的角色,并成功地实现了写作上的几次转型;我也相信,正是出于对这种写作难度的畏惧,余华才迟迟不肯出版他一生中的第四部长篇小说。
似乎可以这样说,写作的难度,正越来越深刻地折磨着那些有责任感、有艺术追求并渴望探查人类精神真相的作家们。
余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早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他便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地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的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
为什么几年前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
是时代在变?
还是我们在变?
这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
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
很清楚,“使自己始终置身于发现之中”,这就是余华的写作难度,他力图拒斥的是“一成不变”。
余华后来的写作实践证明,他说这个话并不是为了搪塞读者。
只是,在时代的微妙变化面前,许多作家并不像余华那样,具有在写作难度中孤独前行的勇气,而是毅然从这种难度面前起身离去,转而寻求商业和市场的成功。
有些人的确成功了,也有些人因此提前就开始从文学舞台上退场。
这个事实,我认为与当代文学的兴衰密切相关。
我不想回忆历代以来,有多少作家由于满足于短暂的成功,如何被时代和读者迅速抛弃。
我不想回忆。
我愿意进一步设想的是,如果要使当代文学从低迷的光景中走出来,走向真正广阔、高远的境界,惟有吁请作家们都找回自己写作的难度,并以这个新的难度为起点,带着自己全部的勇气、智慧、决心和天才上路,最终才有可能重新企及那个理想中的文学目标。
我们知道,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写作,都是一个超越已有的难度并建立新的难度的过程;他的创造性,体现在对这种难度的制造和克服上;而他逾越难度时所走过的路途,就构成了他在作品中留下的美妙的艺术曲线。
比如,卡夫卡为自己的写作所设立的难度是:
人性的道路被腐蚀之后,天堂何以成为可能?
在这个问题没有获得解决以前,卡夫卡的写作一直是绝望而惶恐不安的,他的写作方法,也只能是寓言式的;还有普鲁斯特,当他对机械的东西、盲目而失去了记忆的世界感到不满时,他也开始为自己的写作建立新的难度:
他经过耐心的观察和他那能使事物生辉的能力,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内向的、只忠实于自己记忆的写作方式,从而有效地复活了记忆,并幻想自己在一种封闭的完美中找到了永恒。
普鲁斯特把失落的记忆、含混的现实与幸福的日子结合在一起,成功地抵抗了遗忘的力量。
你可以想象,卡夫卡和普鲁斯特这些人的写作之于巴尔扎克等人,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革命,而他们为自己所设立的难度又是多么的惊人!
他们被称为大师,是因为文学在他们的身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人和世界的悲剧处境
余华也是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真正变化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
这种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他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我当然没有忘记余华小说在结构、语言和叙述上的探索,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创造性,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作家一定是先有了对人和世界的不同理解,他才开始寻求新的艺术方式的。
也就是说,当旧有的话语方式不能再穷尽作家的内心图景时,他就会起来寻找新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新的精神和内心。
——艺术革命从来就不是单独进行的,它总是伴随着精神的内在变化。
如同余华自己所说,“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段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
”然而,“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其结构已经放弃了对事实框架的模仿。
表面上看为了表现更多的事实,使其世界能够尽可能呈现纷繁的状态,我采用了并置、错位的结构方式。
但实质上,我有关世界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并开始脱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自觉,我认为,余华的写作才开始获得广阔的自由。
而余华的智慧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种自由当作在语言和结构上放纵自己的借口,而是及时地通过这种自由深入到人和世界的内部,把它们从过去那种陈旧的结论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余华的作品之所以比他同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的原因。
余华一直以来握住的都是人和世界的基本母题,他从来没有轻易地被某个形式问题转移注意力。
他握住的其实是文学中恒常的部分,而不像一些作家,在语言和形式革命上用力过猛,以致当革命的大潮退去,最终却露出空洞而贫乏的面貌,徒剩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
因此,了解余华小说中的人学立场,是进入他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解码口,它甚至比叙述问题还更重要。
我一直认为,余华写作上的致命困境,从来不是来自于技术问题,而是来自他对人性的体验和开掘。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余华前后的艺术变化上看出来。
在写作《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和《鲜血梅花》等作品的时候,余华是一个在叙述、结构上繁复多变的作家;到《在细雨中呼喊》,虽然艺术线条开始变得简朴、晓畅而清晰,但余华还是喜欢时间的折叠、弯曲和循环,喜欢叙述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
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所有这些在形式上带有装饰意味的东西突然消失了,叙述的重心倾斜到了人物的命运上。
这个时候的余华,看起来像是一个诚实的现实主义者,似乎丧失了叙述实验的热情;尤其是中篇版的《活着》,无论是叙述结构还是叙述语气,都与肖洛霍夫的一个中篇过于相像,并无多少的新意。
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敛去了叙述装饰性的余华,他作品中人的命运和精神问题再一次被尖锐地标示了出来。
这何尝不是一个形式内在化的过程呢?
因为命运的内部也是有形式感的。
余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对人的悲剧处境的体验过程。
他的叙述,完全随着他对人的体验和理解的变化而变化。
最初的时候,余华眼中的人大多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是冷漠的看客,是在无常的命运中随波逐流的人,那时的余华尽管在叙述上表现出了罕见的冷静,但文字间还是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寒冷和血腥气息;到《在细雨中呼喊》,因着追忆而有的温情,如同闪光的话语链条不断地在小说中闪烁,余华的叙述也随之变得舒缓、忧伤而跳跃;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由于善良、高尚、温和、悲悯、宽容等一系列品质,成了这两部小说主要的精神底色,余华的叙述也就变得老实而含情脉脉起来。
探查这种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的里面,也许蕴含着余华写作上的全部秘密。
为什么余华在早期的时候会那么迷恋残酷和暴力?
这决非偶然。
一次,余华谈到在潮湿的阴雨绵绵的南方,自己如何将暴力、恐惧、死亡,还有血迹写在一张张像布一样柔软的受潮的稿纸上时,特别提到了他的童年记忆:
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
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我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
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
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
这显然不是余华后来迷恋血腥和暴力叙事的全部原因,因为在他的小说里,死亡、暴力和血并不仅仅是一种记忆,而是经由余华的叙述,被指证为这个世界的基本现实,或者说,是这个世界内在的本质。
这一指证,对当代文学是意义非凡的。
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对人的关注,还多是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人的文化属性等方面,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则几乎是一个空洞。
这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很显然,前者笔下的人所遇到的困境,可以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存在中的人不同,他的困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你只能在存在论上为他寻找答案。
因此,余华的出现,决非像他以前的作家那样,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真实的书写,而是用了极端而残酷的暴力作为其叙述的根本指向,以彻底改写人的欲望、精神、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结构。
余华说:
“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
”而一个作家,如果从欲望结构开始对人类的存在旅程的探查,他首先要面对的一定是人类内部那些难以阻遏的暴力景象。
“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
确实,再没有比暴力这个词更能概括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现实了。
回望中国的历史,无边无际的苦难,以及对权力没完没了的渴望,可以说,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内容。
而苦难和权力,恰恰是生产暴力的根源。
在一个专断的权力社会,你如果要想远离生活的苦难,那你就必须拥有权力,而权力的夺取必须通过暴力,权力的维持依靠的也是暴力;而一旦暴力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试图用一种更强大的暴力来征服它,所谓以暴抗暴、以牙还牙,这一直以来都是人类遵循的基本的生存原则。
于是,暴力就在这种循环中,获得了生长和蔓延的广阔土壤。
3、暴力的内在结构
暴力是余华对这个世界之本质的基本指证,它也是贯穿余华小说始终的一个主词。
早期如《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作品,写的多是一种纯粹的肉体暴力,并用肉体暴力这个寓言作为精神暴力和思想暴力的一个转喻,以完成对一种内在真实的书写。
后期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了暴力和血腥的场面,但它的主题其实依然和暴力有关。
这个时候的余华,通过书写命运的残忍,苦难的无以复加,进一步指证的是生活的暴力——一种更潜在、更强大、更难以抗拒的暴力形式。
所不同的,不过是人物在面对暴力时不一样的精神反应机制而已。
暴力在余华小说中也分成人世界的暴力和孩童世界的暴力,二者的并置,使暴力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完整的形式。
成人世界的暴力,呈现的是暴力和权力、欲望、历史阴影相混杂后的复杂面貌;孩童世界的暴力,则是对成人世界之暴力的模仿,它表明暴力在人类中间得以延续和生长。
《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和《河边的错误》这几篇小说,是最能说明余华那冷酷的暴力美学的。
这里面不仅有最为阴郁、冷酷的血腥场面,更重要的是,余华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如何被暴力挟持着往前走,最终又成为暴力的制造者和牺牲者的。
以《现实一种》为例,暴力的起源是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
他只是个孩子,可他已经开始学会使用暴力来获取快乐——堂弟的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异常激动”,“他就这样不断地去卡堂弟的喉咙又不断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
他最初“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无意识的,其实是孩子对成人世界的模仿,因为“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
接着,他抱着堂弟到屋外看太阳,似乎是出于本能,当他觉得手上的孩子越来越沉重时,就松开了手,那一刻,他并没有去注意堂弟摔下去后会怎么样,而是“感到轻松自在”。
就这样,暴力的漩涡在孩子一次无意识的罪恶行动中形成了。
山岗和山峰两兄弟及其妻子,都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暴力的漩涡中。
成人世界的暴力一旦展开,可绝不像孩童世界那样是非理性的,它是有计划、有安排、有目标的,它要求每一个人都用暴力来还击暴力,否则你就无法继续获得做人的尊严。
比如,山岗开始时对自己儿子的死有点漠然,但他立刻受到了妻子的谴责:
“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
”这个世界似乎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对暴力坐视不管,他必须反击,可是,除了暴力本身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制止和惩罚暴力呢?
于是,报复性的暴力活动就在山岗和山峰一家展开了,它像一阵暴风,将每一个人都席卷了进来,结果,每个人都具有了双重角色:
他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
而暴力作为一种力量,一旦在人的内心启动,似乎就无法停下来了,直到把所有人都带进毁灭之中。
这也说明,暴力不是一种外在的手段,它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一有机会,它就会奔泻而出,甚至最终主宰一个人的意志和精神。
《一九八六年》中那个曾经做过中学历史教师的疯子,实际上就是一个被暴力主宰而最终成为暴力的代言人的。
他把各种酷刑实施在自己身上,通过这种残酷的自戕和由此展示的周围的看客心理,余华进一步地向我们证实,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尤其是疯子本身的暴力幻想,以及余华在暴力叙事上的极度渲染,更是加深了暴力的穿透力量。
他嘴里大喊一声:
“劓!
”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鼻子。
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了起来,像是在笑。
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拚命地喊上一声:
“劓!
”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
于是黑乎乎的嘴唇开始红润了。
不一会钢锯锯在了鼻骨上,发出沙沙的轻微摩擦声。
于是他不像刚才那样喊叫,而是微微地摇头晃脑,嘴里相应地发出沙沙的声音。
那锯子锯着鼻骨时的样子,让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乐地吹着口琴。
然而不久后他又一声一声狂喊起来,刚才那短暂的麻木过去之后,更沉重的疼痛来到了。
他的脸开始歪了过去。
锯了一会,他实在疼痛难熬,便将锯子取下来搁在腿上。
然后仰着头大口大口地喘气。
鲜血此刻畅流而下了,不一会工夫整个嘴唇和下巴都染得通红,胸膛上出现了无数歪曲交叉的血流,有几道流到了头发上,顺着发丝爬行而下,然后滴在水泥地上,像溅开来的火星。
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
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入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里闪烁着红光。
他的动作非常仔细,又非常迟钝。
抠了一阵后,他又认认真真检查了一阵。
随后用手将鼻子往外拉,另一只手把钢锯放了进去。
但这次他的双手没再摆动,只是虚张声势地狂喊了一阵。
接着就将钢锯取了出来,再用手去摇摇鼻子,于是那鼻子秋千般地在脸上荡了起来。
疯子的暴力书写,含示着作者对暴力的控诉。
这个时候,肉体暴力已经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伸越到了历史文化的内部,它指向的是历史文化中那些精神和思想暴力的死结。
疯子的疯狂,以及他那血淋淋的自戕,这些肉体的暴力行为,其实都是精神和思想暴力作用后的结果。
这一点,即便撇开《一九八六年》中的“文革”背景,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疯子身后那条长长的历史阴影。
但是,并不是任何暴力行为都可以得到历史的清算的,相反,历史还经常为暴力提供合法的理由,比如《河边的错误》里面也有一个疯子,他被马哲枪杀了,这本来是不容置疑的暴力行为,但由于马哲的行为带有为民除害的特点,所以获得了人们的理解,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觉得枪杀疯子是一种犯罪;等法律的制裁要临及他的时候,他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疯子,以逃避制裁。
整个过程中,马哲枪杀一个人这个暴力行为的事实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发生了变化的只是文化、权力和科学对暴力的不同解释。
难怪连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都曾经为某些暴力行为辩解:
“由于暴力在本质是具有工具性,因此在它有效地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目的的范围内都是理性的。
”——这其实是使暴力和非暴力的界限彻底模糊。
又比如,《现实一种》这篇小说的最后,详细地写到了医生解剖尸体的整个过程,如果单从文字和场面的血腥效果而言,这种解剖所蕴含的暴力色彩,一点都不亚于山岗和山峰兄弟间的残杀,也不亚于《一九八六年》中那个疯子的自戕,但它并不能算暴力,原因在于人类现有的文化、道德和科学反对把它列为暴力。
还有,《一九八六年》中疯子的自戕行为,算不算暴力,该不该受到谴责呢?
这同样是一个在现有的标准里难以判断的事情。
这样,暴力就开始显露出它复杂的面貌。
它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一整套属于它自己、并充满矛盾的逻辑链条,而余华之所以花那么多的笔墨来描摹暴力,不仅是要揭示暴力的黑暗品质,更重要的是,他对有关暴力的评价系统也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下去,就会发现,暴力的后面总是隐藏着权力的威严和人类对权力的渴望。
“权力和暴力虽是不同现象,却通常一同出现。
”“如果我们看看文学里对权力现象的描写,就立刻会发现从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暴力不过是权力最肆虐最无耻的表现。
C·莱特·米尔斯这样写到:
‘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权力的终极就是暴力。
’”这当然是从政治方面来说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余华的小说证实了这一点。
在《河边的错误》中,权力对马哲杀人性质的篡改,就表明暴力一旦与权力合谋,制造的只会是更大、更隐蔽的暴力。
《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在家里的权力的获得,靠的也是暴力,以致家中没有人敢反抗他。
甚至连小孩都知道,该如何通过暴力来获得权力。
比如,当孙光平用镰刀划破了弟弟孙光林的脑袋,为了逃避父亲的惩罚,孙光平又强行划破另一个弟弟孙光明的脸,然后伙同他一起诬告孙光林,结果受到惩罚的不仅不是施暴的哥哥孙光平,反而是受害者孙光林。
而孙光林也在成长过程中,多次用威胁的方式打败了国庆和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
……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却是另一种美好。
”是暴力征用了权力,而权力又反过来证明了暴力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于是,一个人性的囚牢、世界的深渊就在暴力和权力的交织中建立了起来。
余华笔下的人物多数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从中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明,有的只是一片人性的晦暗,个人在其中无助的挣扎,以及大面积的死亡。
难怪在当时,有人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余华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渣子。
4、苦难及其缓解方式
这还远不是暴力的全部。
如果你看到《一九八六年》里那个疯子自戕时的暴力幻想,是把自己当作了施虐者,把自己的身体假想成了另一个被虐者的身体,你就会知道,疯子的自戕玩的其实也是施虐和受虐的游戏,可见,暴力已经内在成了人的本能,以致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了施暴的倾向;如果你还看到余华在进行这种暴力叙事时,多少有津津乐道和过于迷恋之嫌,甚至由此还多少有了话语暴力的迹象,那你就更会知道,暴力的发生绝不是一些个案,它其实渗透到了每一个人的思维之中,即便是暴力的批判者,也未必能够幸免。
因此,肉体暴力的实质,最终一定指向它背后的精神暴力。
余华警觉地看到这一点,并用与之相称的残酷话语为内心中的暴力划定了一个边界,应该说,余华是清醒而深刻的。
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个将人置于本能和形而下的层面进行观照,通过对肉体暴力的残酷书写,极端地揭示出人和世界的黑暗景象。
余华所发现的,是一个卓越的人性限度,它为丰富当代文学对人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参照。
同时,余华所敞开的世界,也是一个令人恐惧、不安而绝望的世界。
他通过这些密不透风的暴力话语,触及到了新的真实,并把人类阴暗的内心解放了出来,从而让他们在黑暗的沉浮中享受恐惧和绝望的滋味。
这个时候的余华,在叙述上是冷漠的,也是坚强的。
他为了最大限度地将人性的深渊景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甚至一度拒绝描摹符合事实框架的日常生活,以致我们在他的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常态的生活,一切都是非常态的。
——《现实一种》里的家庭杀戮,《一九八六年》里的疯子自戕,《世事如烟》里飘忽的人物关系和宿命的人物命运,《古典爱情》里的吃人场面,《鲜血梅花》里的江湖恩怨,等等,这些在叙述上,从一开始就是虚拟的,也是极端的,你很难找到相似的现实与之相对应。
很显然,余华会在这个时期决绝地离开当代生活的外表,转而奔向那些虚拟的现实场景,肯定是因为他的内心蕴藏着更重要的精神问题需要追问。
这些精神问题又如此的尖锐,好像只有把它置于非常态的现实中,才能更好地将它里面的黑暗细节有效地逼示出来。
在这点上,余华显得迫不及待,他仿佛与现实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只要一进入叙述,就急切地要将现实撕开,以露出它狰狞的面目。
往往就在这个时候,余华的叙述也变得紧张起来,在这个紧张下面,余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暴躁的现实,以及他那颗面对现实时暴躁的心。
真正让余华稍微平静下来的作品是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
这部小说一改余华以前那种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节奏变得舒缓、忧伤起来,如同题目中的两个意象,“细雨”和“呼喊”,前者是温和的,后者是尖锐的。
余华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一直纠缠在这两套话语系统之中,叙述者“我”的恐惧和战栗,也在这两套话语的隙缝中生长出来,中间还混杂着悲哀、绝望,以及因回忆而有的温馨。
尽管这部小说仍旧延续了余华惯有的恐惧、绝望和人性险恶等主题,但过于激烈的血腥场面却已清理干净,小说的外表也不再是虚拟的非常态社会,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小镇上。
之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小说外表的真实性就更加明显。
余华在叙述上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早期的叙述态度上——“对事实框架的模仿”,但同时多了简洁、质朴和沉着。
为什么《在细雨中呼喊》之后,余华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我想,最根本的,是余华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暴力、血腥和死亡的阴影,他的叙述中,多出了请求慰藉和渴想希望的维度。
《在细雨中呼喊》里,是开头那个女人孤独而无依无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