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古诗复习汇编.docx
《大学语文古诗复习汇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学语文古诗复习汇编.docx(5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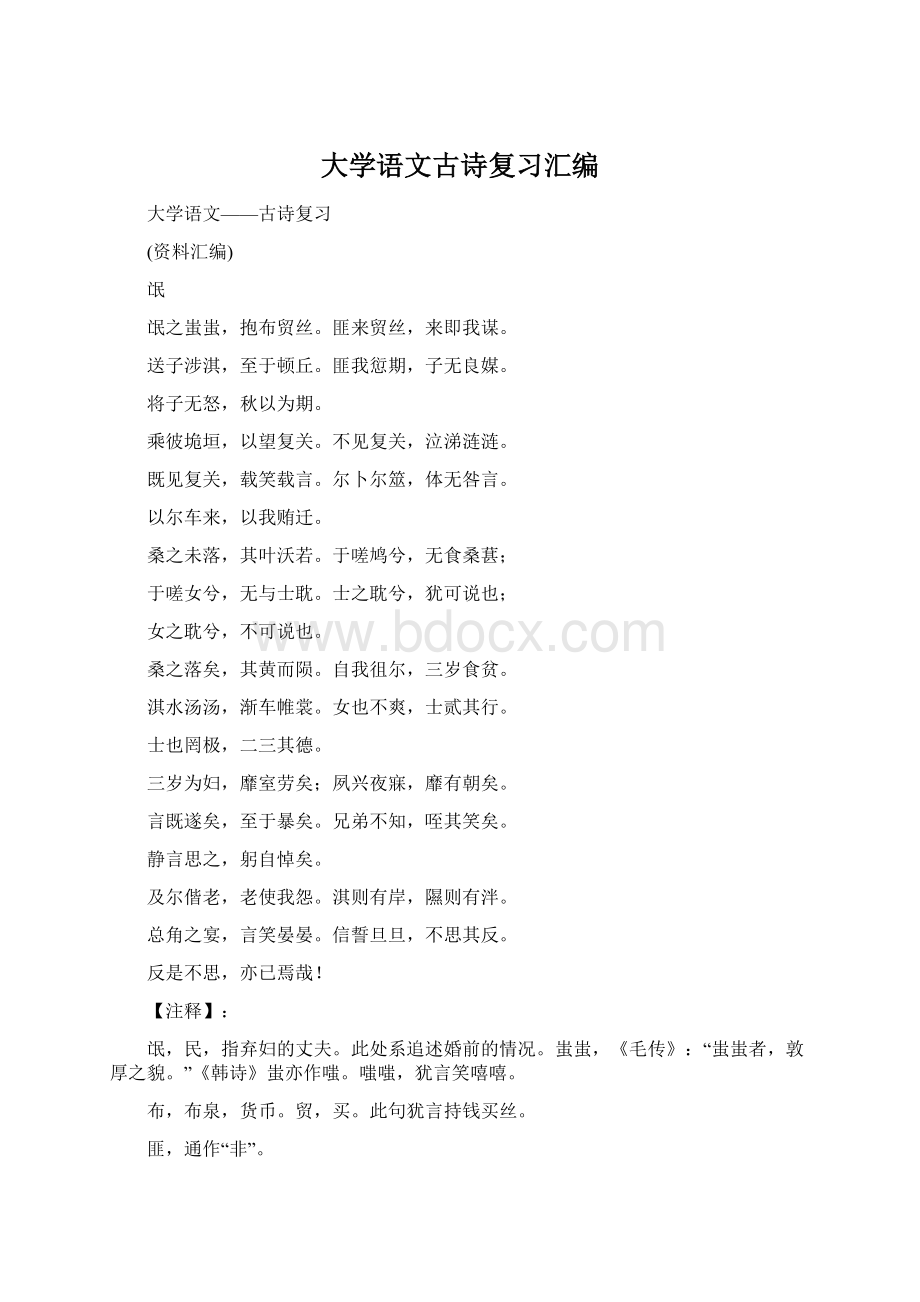
大学语文古诗复习汇编
大学语文——古诗复习
(资料汇编)
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
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注释】:
氓,民,指弃妇的丈夫。
此处系追述婚前的情况。
蚩蚩,《毛传》:
“蚩蚩者,敦厚之貌。
”《韩诗》蚩亦作嗤。
嗤嗤,犹言笑嘻嘻。
布,布泉,货币。
贸,买。
此句犹言持钱买丝。
匪,通作“非”。
即,就。
这句说,来就我商量婚事。
淇,淇水,卫国的河流。
顿丘,本为高堆的通称,后转为地名。
在淇水南。
淇水又曲折流经其西方。
愆(qian,阴平)期,过期。
愆,过。
将(qiang,阴平),愿、请。
秋以为期,以秋为期。
期,谓约定的婚期。
乘,登上。
垝(gui,上声)垣,已坏的墙。
复关,为此男子所居之地。
一说,关,车厢。
复关,指返回的车子。
涟涟,泪流貌。
载,犹言则。
尔,你。
卜,用龟甲卜卦。
筮,用蓍草占卦。
体,卦体、卦象。
咎言,犹凶辞。
犹言卜筮结果,幸无凶辞。
车,指迎妇的车。
贿,财物。
指陪嫁。
沃若,沃然,肥泽貌。
这句以桑叶肥泽,喻女子正在年轻美貌之时。
一说,喻男子情意浓厚的时候。
于嗟两句:
于嗟,即吁嗟,叹词。
鸠,鸟名。
《毛传》:
“鸠,鹘鸠也。
食桑葚过,则醉而伤其性。
”此以鸠鸟卜可贪食桑葚,喻女子不可为爱情所迷。
耽,乐,欢爱。
黄,谓叶黄。
陨,堕,落下。
这句以桑叶黄落喻女子颜色已衰。
一说,喻男子情意已衰。
徂尔,嫁往你家。
徂,往。
三岁,泛指多年,不是实数。
食贫,犹言过着贫苦的日子。
汤汤(读若shang,阴平),水盛貌。
渐,渍,浸湿。
帏裳,女子车上的布幔。
爽,过失,差错。
贰,即“忒”的假借字。
忒,差失,过错。
行,行为。
这句连上句说,女子并无过失,是男子自己的行为有差忒。
罔极,犹今言没准儿,反复无常。
罔,无。
极,中。
二三其德,言其行为再三反复。
靡室劳矣,言不以操持家务为劳苦。
靡,无,不。
室,指室家之事,犹今所谓家务。
夙兴夜寐,起早睡晚。
夙,早。
兴,起,指起身。
靡有朝矣,言不止一日,日日如此。
言,句首语词。
遂,犹久。
这两句说,我在你家既已久了,你就对我粗暴,虐待我了。
咥(xi,去声)然,大笑貌。
静言思之,静而思之。
言,句中语词。
躬,身。
悼,伤。
此句犹言独自悲伤。
隰(xi,阳平),低湿之地。
泮,同“畔”,边沿。
这句连上句说,淇尚有岸,隰尚有泮,而其夫却行为放荡,没有拘束。
总角,结发,谓男女未成年时。
宴,安乐,欢乐。
此女子当在未成年时即与男子相识。
晏晏,和柔貌。
旦旦,即怛怛,诚恳貌。
旦为“怛”的假借字。
不思其反,不要设想这些誓言会被违反。
此为当时男子表示自己始终不渝之词。
反,指违反誓言的事。
是,则。
已,止,指爱情终止,婚姻生活结束。
这两句大意说,我是没有想悼你会违反誓言,但我们的爱情却就这样地完了呀!
《氓》与《邶风·谷风》,都可以算作“弃妇词”,但这两位弃妇的“品格”大有不同。
《谷风》之女,乃所谓“品格贞一”者,故历来博得经学家的同情。
《氓》之女,则所谓“被诱失身”也,因此虽遭弃的身世与《谷风》同,而同情的一票却颇难得。
如今自然不必再存迂腐之见。
两诗都是写情、写怨,这情与怨乃各依附了自己的故事,或曰“境遇”,且凭借了这境遇而沉潜浮荡,于是它可以从那么邈远的地方,递送过来触手可温的情思。
就诗的艺术而言,不好断然说它曾经怎样谋篇布局的功夫,但并不很长的篇幅里,讲一个曲曲折折的故事,而每一个情节都站在一个极妥帖的位置,论“三百篇”之“赋”,《氓》总可以归人上乘。
氓,毛传曰“民”。
蚩蚩,毛曰“敦厚之貌”,据韩诗义,则“蚩蚩”者,乃笑之痴也。
毛、韩虽义异却不妨互相发明。
“抱布贸丝”,而“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范处义曰:
“从我贸丝,其意非为丝也,即欲谋我为室家耳。
是时必有谋昏之言,诗之所不及,不然安得已有从之之意,遂送其去涉淇水之外,至于一成之顿丘。
是时必有迫促之言,亦诗之所不及,不然安得遽有‘无良媒’、‘无我怒’、‘秋以为期’之约。
”邓翔曰:
“‘送子’二句,将落矣,‘匪我’句忽又颺开,笔乃不直;藏过负约一段情事,此为省笔。
‘涉淇’而忽变卦,恐氓生怒,故又慰之、约之。
”可知这里多用了省略之笔,而又省略得恰好,正是以说出来的,照应那未说出来的。
刘义庆《幽明录》中有故事曰《买粉儿》,略云: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
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
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
明日复来,问曰:
‘君买此粉,将欲何施?
’答曰:
‘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
’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
”后来《聊斋志异》的《阿绣》,开头儿也有相似的情节,乃买扇也。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此中自然藏了故事,虽然没有细节,但八个字已尽曲折_时间的,还有起伏在时间中的喜嗔怨怒。
“乘彼诡垣”之乘,特有神。
王先谦引《说文》“乘,覆也”,曰“凡物相覆谓之乘。
《易·屯卦》郑注‘马牝牡曰乘’,是也。
人在垣上,若覆之者,故亦曰乘”。
其实“乘彼垝垣”,意思很清楚,而形象却模糊,但是此处偏偏正是需要这样的效果。
王解乘为覆,并没有使形象变得清晰,却由这一注,而见得由“乘”字牵出的许多情味来。
亦正如下面的“泣涕涟涟”,王应麟《诗考》引王逸注《楚辞》引诗作“波涕涟涟”,张慎仪曰此“波”乃讹字也,丁晏则以为是诗云涕下如流泉波涕。
推敲起来,“波”字实可存,丁解亦好,好像因此而带出一点儿俏皮,而此节叙事本来是带着俏皮的,这也正是见出性情的地方。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也,其黄而陨”,多解作女用来比喻自己色衰爱弛,但欧阳修说:
“‘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时可爱;至‘黄而陨’,又喻男意易得衰落尔。
”此解似较诸说为胜,如此,沃若、黄陨之喻,乃是扣合“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来说,而这也正是一个伤心故事的开端和终结。
郑笺“用心专者怨必深”,最是觑得伤心处,而“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正好可以用着“爱情于女是生命之全书”的意思_倒不是特意引来西人为我说法,只是于此格外感慨古今中外人情之相通。
屈原——九歌·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音“航”],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音“老”],援玉枹[音“扶”]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音“墅”];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遥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音“从”];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音“隆”];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简析】:
此篇是祭祀保卫国土战死的将士的祭歌。
手执吴戈锐呵身披犀甲坚,
在车毂交错中与敌人开战。
旌旗蔽日呵敌寇蜂拥如云,
箭雨纷坠呵将士奋勇向前。
敌寇凌犯我军阵呵践踏队列,
左骖倒毙呵右骖伤于刀剑。
埋定车轮呵拉住战马,
拿过玉槌呵擂动鼓点。
战气萧杀呵苍天含怒,
被残杀的将士呵散弃荒原。
既已出征呵就没想过要回返,
家山邈远呵去路漫漫。
带上长剑呵操起秦弓,
纵使首身异处呵无悔无怨。
真是英勇无畏呵武艺超凡,
你永远刚强呵不可凌犯。
既已身死呵将成神显灵,
你是鬼中的英雄呵魂魄毅然。
①戈:
平头戟。
吴戈:
吴国所制的戈。
当时这种戈最锋利。
被:
同披。
犀甲:
犀牛皮制的甲。
②错:
交错。
毂(gu3):
车轮中间横贯车轴的部件。
古时常以之代指车轮。
短兵:
短兵器。
③凌:
侵犯。
阵:
军阵,阵地。
躐(lie4猎):
践踏。
行:
行列。
④骖:
驾在战车两旁的马。
殪(yi4义):
死,杀死。
刃伤:
被刀剑砍伤。
⑤霾(mai2埋):
同“埋”。
絷(zhi2植):
用绳子拴住。
⑥援:
拿起。
枹(fu2福):
鼓槌。
鸣鼓:
声音很响的鼓。
⑦天时:
犹言天象。
怼(dui4对):
怨愤。
威灵:
神灵。
⑧严杀:
犹言“肃杀”,指战场上的肃杀之气。
壄(ye3野):
古“野”字。
⑨忽:
渺茫而萧索。
超远:
即遥远。
⑩带:
佩在身上。
挟:
夹在腋下。
⑾心不惩:
心不悔。
⑿诚:
果然是。
勇:
指精神上的气势。
武:
指孔武有力。
⒀终:
到底。
不可凌:
指志不可夺。
⒁神以灵:
指为国捐躯的将士死后成神,神灵显赫。
意谓他们精神不死。
⒂此句一作“魂魄毅兮为鬼雄”,意较佳。
【赏析】
《国殇》是屈原为祭祀神鬼所作的一组乐歌——《九歌》中的一首,内容是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
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
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
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
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他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
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
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
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
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
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
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本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
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
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我们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
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
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本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
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
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
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的《国殇》,包括其他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作者小传】:
屈原(前335?
—前296),名平,字原。
是楚国王族同姓。
早年得楚怀王信任,官左徒,不久,因受到贵族政治集团的诋毁,被怀王疏远,放逐汉北。
顷襄王时又被流放到沅、湘流域。
当他走到湘水附近的汩罗江时就自沉而死。
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作品充满着政治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不朽典范。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绡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怒怨,但坐看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
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
使君一何愚。
使君自有妇,
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
夫婿居上头。
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
黄金络马头。
腰中鹿卢剑,
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吏,
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
四十专城居。
为人结白皙,
鬑鬑颇有须。
盈盈公府步,
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
皆言夫婿殊。
这诗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属《相和歌辞》,写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一“使君”即太守之类官员调戏的故事,歌颂她的美貌与坚贞的情操。
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名《艳歌罗敷行》,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日出东南隅行》。
不过更早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已经提到这首诗,称之为《陌上桑》。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沿用了《古今注》的题名,以后便成为习惯。
“陌上桑”,意即大路边的桑林,这是故事发生的场所。
因为女主人公是在路边采桑,才引起一连串的戏性情节。
《陌上桑》故事很简单,语言也相当浅近,但有个关键的问题却不容易解释:
诗中的秦罗敷到底是什么身份?
按照诗歌开场的交代是一个采桑女,然而其衣着打扮,却是华贵无比;按照最后一段罗敷自述,她是一位太守夫人,但这位夫人怎会跑到路边来采桑?
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这样看的:
“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
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去其夫已四十,知必无是事也。
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列不必严词拒绝。
”以后有人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认为罗敷是一位劳动妇女,诗中关于她的衣饰的描写,纯出于夸张;最后一段,则是罗敷的计谋,以此来吓退对方。
这已经成为通行的观点。
但这些其实都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之辞,诗歌本身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根据。
以二十不足之女子嫁年已四十之丈夫,即在今日亦不足为奇,何以“必无是事”?
况且文学本是虚构的产物,又何必“泥定看杀”其断然不可?
至于
后一种引申之说,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其实仍是矛盾重重:
既然作者可以夸张地描写罗敷的衣饰,而不认为这破坏了她的身分,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她安排一个做官的丈夫?
这是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同样的情况,而曲成已说。
其实《陌上桑》并不是一篇孤立的作品,以上的问题,要从产生这一作品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来解释。
我们先从诗题《陌上桑》所设定的故事场所说起。
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分工。
“女织”从广义上说,也包括采桑养蚕。
桑林在野外,活动比较自由,桑叶茂盛,又容易隐蔽,所以在男女之大防还不很严厉的时代,桑林实是极好的幽会场所。
在这里,谁知道发生过多少浪漫的故事?
自然而然,桑林便不断出现于爱情诗篇中。
这在《诗以》中已经很普遍。
《汾沮洳》是写一个女子在采桑时爱上了一个男子: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彼其之子,美如英。
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桑中》是写男女的幽会: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乎上官,送我乎淇上矣!
”可以说,在《诗以》的时代,桑林已经有了特殊的象征意味,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文学的“桑林”。
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的男女情爱遭到了否定。
上述诗篇,也被儒家的经师解释为讥刺“淫奔”的作品。
于是,在文学的“桑林”中,开始产生完全不同的故事。
最有名的,便是秋胡戏妻故事。
西汉刘向《列女传》记载:
鲁国人秋胡,娶妻五日,离家游宦,身致高位,五年乃归。
将至家,见一美妇人采桑于路旁,便下车调戏,说是“力桑不如逢国卿”(采桑养蚕不如遇上个做大官的),遭到采桑女的断然拒绝。
回家后,与妻相见,发现原来就是那采桑女。
其妻鄙夷丈夫的为人,竟投河死。
乐府中有《秋胡行》一题,就是后人有感于这一传说而作。
古辞佚,今存有西晋传玄之拟作,内容与《列女传》所载大体相同。
可以到,“桑林”中的故事,原来大多是男女相诱相亲,而现在变成了女子拒绝子的引诱。
当然,人们也可以说,秋胡是一个“坏人”,这种故事与《诗经》所歌唱的纯真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不要忘记:
在民间传说文学故事中,虚设一个反面角色是很容易的。
关键在于,通过虚设的人物活动,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审美理想。
这样我们能得出结论:
汉代的“桑林”,已经不同于《诗经》时代的“桑林”,文学中的道德主题,开始压倒了爱情主题。
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已经失传《秋胡行》古辞与《列女传》所载故事并无大异。
而《陌上桑》显然是这一故事或直接从《秋胡行》演化而来的。
试看两个故事的基本结构:
场所:
大路边的桑林;主人公:
一位采桑的美妇人;主要情节:
路过的大官调戏采桑女,遭到拒绝。
所不同的是,在秋胡故事中,调戏者是采桑女之夫,故事最终以悲剧结束;在《陌上桑》中,采桑女另有一位做官的好丈夫,她拒绝了“使君”的调允,并以自己丈夫压倒对方,故事以喜剧结束。
实际上,《陌上桑》是把《秋胡行》中的秋胡一劈为二:
一个是过路的恶太守,一个是值得夸耀的好丈夫。
但尽管《陌上桑》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秋胡行》的故事,却也作了重要改变,从而使诗的重心发生转移。
秋胡戏妻的故事,主旨是宣扬儒家道德,采桑女即秋胡妻的形象,也完全是一个道德形象。
她即使是令人感动的,恐怕也很难说怎么可爱。
故事中也提到她长得很美,但作为一个结构万分,这只是导致秋胡产生不良企图的原因。
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除了拒绝太过的调戏这一表现德性的情节外,作者还花了大量篇幅,描摹她的美貌,以及周围人对她的爱幕。
这一部分,实际是全诗中最精彩的。
这尽管同《诗经》所写男女相诱相亲之情不同,但两者具有共同的基点:
即人类的普遍的爱美之心,和对理想的异性的向往,所以说,罗敷的形象,是美和情感的因素,同时代所要求的德性的因素的结合;换言之,是《诗经》的“桑林”精神与《秋胡行》的“桑林”精神的结合。
也正是因为罗敷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道德形象,所以作者也没有必要为她安排一个强烈的悲剧下场,而让她在轻松的喜剧气氛中变得更为可爱。
由此可见,《陌上桑》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生活中具体事件的记载或改写,而是漫长的文化变迁的产物罗敷这个人物,也是综合了各种因素才形成的。
她年轻、美丽、高贵、富有、幸福、坚贞、纯洁,寄托着那些民间无名作者的人生理想。
也因为她是理想化的,所以她并不严格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
她既是一个贵妇人,又是一个采桑女。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那些公主、王子,实际是代表着普通民众的心愿。
一定要拿后世僵化得莫名其妙的政治观念去穿凿附会,反而是荒廖混乱的。
然后回到诗歌本身。
这诗原来按音乐分为三解,其文字内容,也相应地分为三段。
第一段着重写罗敷的美貌和人们对她的喜爱。
起首四句,从大处说到小外,从虚处说到实处,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式的开场白。
同时,这四句也奠了全诗的气氛:
明郎的阳光照耀着绚丽的楼阁,楼阁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色鲜明,光彩流溢,好像中国年画的味道。
“照我秦氏楼”,既是亲切的口气,也表明诗人是站在罗敷的立场上说话,并由此把读者引入到这种关系中去。
而后罗敷就正式登场了:
她提着一只精美的桑篮,络绳是用青丝编成,提把是用挂树枝做就。
这里器物的精致华美,是为了衬托人物的高贵和美好。
再看她的打扮,头上梳的是斜倚一侧、似堕非堕的“倭堕髻”(东汉时一种流行发式),耳朵上挂着晶莹闪亮、价值连城的明月珠,上身穿一件紫红绫子短袄,下身围一条杏黄色绮罗裙。
一切都是鲜艳的、明丽的、珍贵的、动人的。
这好像是一个采桑的农妇,其实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女。
照说,接下来应该写罗敷的身体与面目之美。
但这很困难。
因为诗人所要表的,是绝对的、最高的美,而这种美无法加以具体的描绘。
谁能说出什么样的身材、体态、眉目、唇齿算是达到了完善无缺的程度?
作者也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各具标准的审美要求。
于是笔势一荡,作者不直接写罗敷本身,而去用周围的人为罗敷所吸引的神态:
过路人放下了担子,伫立凝视。
他好像年岁较大,性格也沉稳些,所以只是手捋着胡须,流露出赞叹的神气。
那一帮小伙子便沉住气,有的脱下帽子,整理着头巾,像是在卖弄,又像是在逗引;至少赚得美人流波一转,便可得意民多时。
种田的农人更糟,看得失了神,活也不干了;回家还故意找碴,摔盆砸碗。
-因为看了罗敷,嫌老婆长得丑。
这些都是诙谐的夸张之笔,令人读来不禁失笑,好像拿不准自己在那场合会是什么模样。
其效果,一是增添了诗歌的戏剧性,使得场面、气氛都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从虚处落笔,无中生有,表达了不可描摹完美。
反正,你爱怎么想像就怎么想像,罗敷总是天下最美的。
这实在是绝妙之笔。
观罗敷的一节,也最近于“桑林”文学的本来面目。
它所表现的,是异性间的吸引,是人类爱美的天性。
但它又不同于《诗经》中的作品,而是有分寸有限制的。
那些观者,都只是远远地伸长了头颈看罗敷,却不敢走近搭话,更不敢有越规之举;而罗敷好像同他们并不发生关系,旁若无人。
这就在男女双方之间,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墙。
这便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
”同时也有另一种分寸:
尽管有那么多人在围观,那些小伙子几乎就在冲破防线,作者也没有让罗敷给他们来一通义正辞严的斥责。
要不然,就太教人扫兴,太没有味道了。
因为这诗原有双重的主题,作者都要照顾到。
当然,整个第一段,是为了完成美和情感的主题,只是限制它,不让它破坏道德的主题。
下面第二段,就开始转向了。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好大气派!
“使君”是太守、刺史一类官员的尊称,他们执掌一个地区的全权,汉人比之于古代的诸侯。
官做得大,气派自然大,胆子跟着大。
别人见了罗敷,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位使君就不甘心于此了。
于是派了手下人去问:
这是谁家的漂亮女子?
多少年纪了?
罗敷不动声色,一一作答。
这都是为了充分地展开情节,使矛冲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
若是一上来就剑拔弩张,文学趣味就少了。
顺带,又写出罗敷的年纪:
十五至二十之间。
中国古人认为这是女子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
而后进入矛盾冲突的高潮。
使君问道:
你可愿意坐上我的车,跟我回去?
罗敷的回答犹如当头一棒:
“使君一何愚!
”有了“一何”二字,语气十分强烈。
理由是很简单:
你有你的妻,我有我的夫。
各安其家室,乃是礼教之大义,岂可逾越?
这一节是从秋胡戏妻故事中继承来的,表现了诗歌的道德主题。
而道德主题,总是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才能表现得鲜明强烈。
第三段紧接上一段的未句“罗敷自有夫”,由主人公全面铺展地夸耀丈夫。
罗敷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丈夫?
这问题本来很简单:
诗中说有,我们只好承认有。
尽管在一般读者的心理中,都不喜欢文学作品里的漂亮女子早早嫁人,那也无奈何。
这问题还可从二方面来证明:
其一,《陌上桑》的故事来源于秋胡戏妻故事,秋胡妻本是出嫁了的美妇人;其二,作者在这里是要彰扬忠贞的道德,总得先有丈夫才有忠贞。
但第三段也并不完全是从道德主题着眼的。
不然,完全可以让罗敷来一通说教。
但如果真是那样,就糟糕了,这个美女马上就变得干巴巴的,教人喜欢不起来。
所以作者也是适可而止,道德大义在第二段用结末二句话点明之后,到第三段就转向一层富有喜剧色彩、诙谐的情节,使读者依然能够享受到文学的趣味。
罗敷夸婿,完全是有针对性的。
使君出巡,自然很有威势,于是她先夸丈夫的威势:
丈夫骑马出门,后面跟着上千人的僚属、差役;他骑一匹大白马,随人都骑黑色小马,更显得出众超群;他的剑,他的马匹,全都装饰得华贵无比。
使君官做得大,她就再夸丈夫的权位:
丈夫官运亨通,十五岁做小吏,二十岁就入朝作大夫,三十岁成了天子的亲随侍中郎,如今四十岁,已经做到专权一方的太守。
言下之意,目前他和你使君虽然是同等官职位,将来的前程,恐怕是难以相提并论了!
最后是夸丈夫的相貌风采:
丈夫皮肤洁白,长着稀稀的美髯,走起路来气度非凡,用这些来反衬使君的委琐丑陋。
这么一层层下来,罗敷越说越神气,越说越得意,使君却是越听越晦气,终了必然是灰溜溜逃之夭夭。
读自然也跟着高兴,直到故事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罗敷的这位丈夫,也是童话中白马王子式的人物,不可拿生活的逻辑去查考。
萧涤先生说,对这一节不可泥定看杀,不可求其句句实在,原是说得很对,但这个人物在故事里却是合理的存在,这是要注意到的。
前面说了,《陌上桑》其实有双重主题,但作者处理得很好,并没有彼此分离。
从道德主题来说,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