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docx
《随遇而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随遇而安.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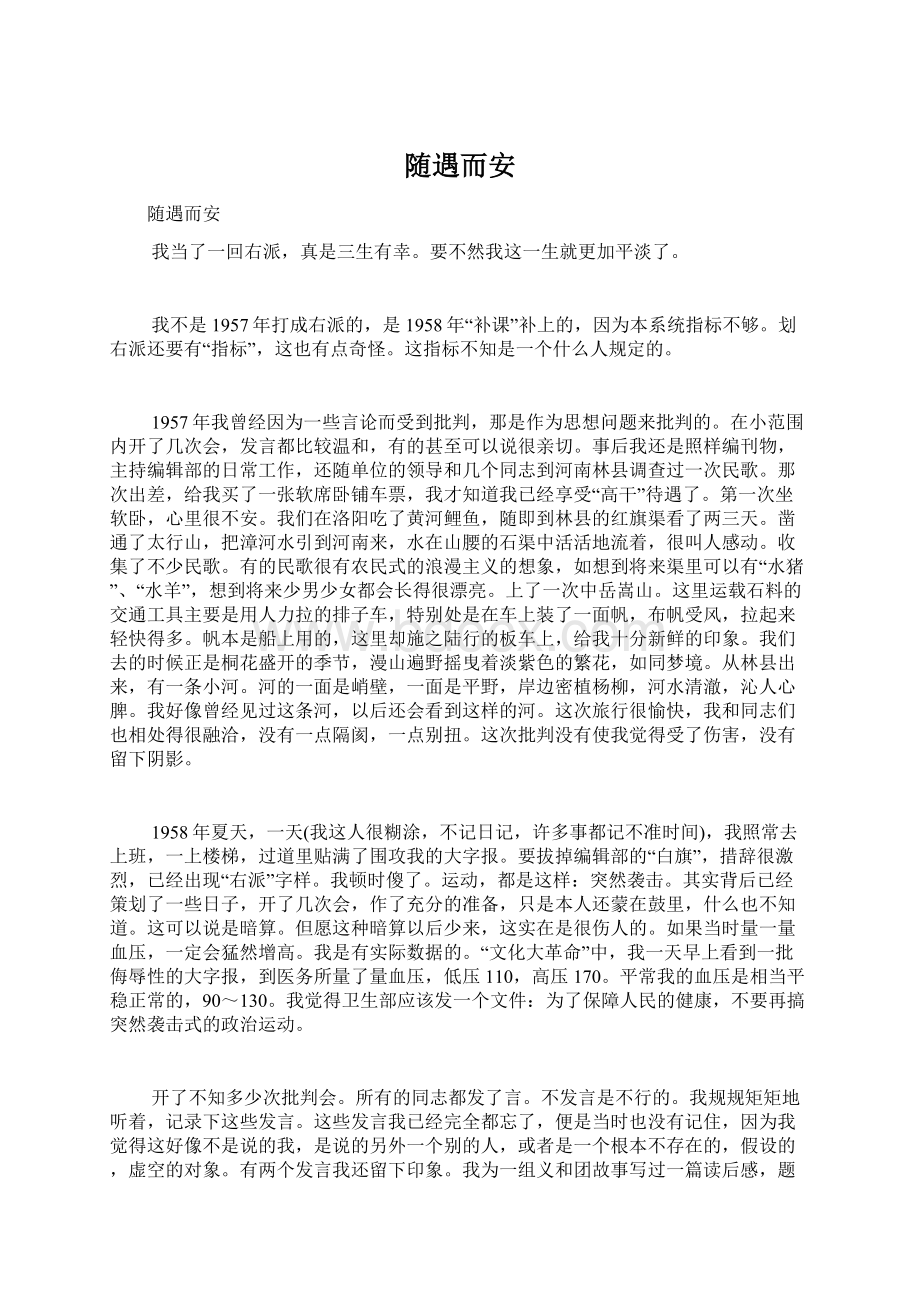
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
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补课”补上的,因为本系统指标不够。
划右派还要有“指标”,这也有点奇怪。
这指标不知是一个什么人规定的。
1957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
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
事后我还是照样编刊物,主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还随单位的领导和几个同志到河南林县调查过一次民歌。
那次出差,给我买了一张软席卧铺车票,我才知道我已经享受“高干”待遇了。
第一次坐软卧,心里很不安。
我们在洛阳吃了黄河鲤鱼,随即到林县的红旗渠看了两三天。
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来,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着,很叫人感动。
收集了不少民歌。
有的民歌很有农民式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如想到将来渠里可以有“水猪”、“水羊”,想到将来少男少女都会长得很漂亮。
上了一次中岳嵩山。
这里运载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车,特别处是在车上装了一面帆,布帆受风,拉起来轻快得多。
帆本是船上用的,这里却施之陆行的板车上,给我十分新鲜的印象。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桐花盛开的季节,漫山遍野摇曳着淡紫色的繁花,如同梦境。
从林县出来,有一条小河。
河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平野,岸边密植杨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
我好像曾经见过这条河,以后还会看到这样的河。
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志们也相处得很融洽,没有一点隔阂,一点别扭。
这次批判没有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没有留下阴影。
1958年夏天,一天(我这人很糊涂,不记日记,许多事都记不准时间),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
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
我顿时傻了。
运动,都是这样:
突然袭击。
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这可以说是暗算。
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
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会猛然增高。
我是有实际数据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报,到医务所量了量血压,低压110,高压170。
平常我的血压是相当平稳正常的,90~130。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
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
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
不发言是不行的。
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
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
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
这位同志说:
“你对谁仇恨?
轻蔑谁?
自豪什么?
”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
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
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
我想辩解两句,行么?
当时我想:
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
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
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辩认”,他辩你认。
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
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
问题是问题,态度是态度,问题大小是客观存在,怎么能因为态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缩呢?
许多错案都是因为本人为了态度好而屈认,而造成的。
假如再有运动(阿弥陀佛,但愿真的不再有了),对实事求是、据理力争的同志应予表扬。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
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
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伸解释的。
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
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
他们也并不好受。
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
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
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
我在一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过:
“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
她想:
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
”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其实,问题只是那一些,只要写一次检查,开一次会,甚至一次会不开,就可以定案。
但是不,非得开够了“数”不可。
原来运动是一种疲劳战术,非得把人搞得极度疲劳,身心交瘁,丧失、切意志,瘫软在地上不可。
我写了多次检查,一次比一次更没有内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场了,因为大家都累了。
结论下来了:
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
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在那篇写右派的小说里写道:
“……她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
”我那天回到家里,见到爱人说,“定成右派了”,脸上就是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笑。
我想起金圣叹。
金圣叹在临刑前给人写信,说:
“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亦奇。
”有人说这不可靠。
金圣叹给儿子的信中说:
“字谕大儿知悉,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说这更不可靠。
我以前也不大相信,临刑之前,怎能开这种玩笑?
现在,我相信这是真实的。
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鲁迅说金圣叹“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鲁迅没有被杀过头,也没有当过右派,他没有这种体验。
另一方面,我又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我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
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
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
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
”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
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
所里有不少技师、技术员,所领导对知识分子是了解的,只是在干部和农业工人的组长一级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和我同时下放到这里的还有另外几个人),并没有在全体职工面前宣布我们的问题。
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
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
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
真够一呛。
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
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
我当时想:
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来,不死掉,我就得拼命地干。
大部分的农活我都干过,力气也增长了,能够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样陡的高坡。
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
果园的活比较轻松,也比‘大田”有意思。
最常干的活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
硫酸铜加石灰,兑上适量的水,便是波尔多液,颜色浅蓝如晴空,很好看,喷波尔多液是为了防治果树病害,是常年要喷的。
喷波尔多液是个细致活。
不能喷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树叶子挂不住,流了。
叶面、叶背都得喷到。
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
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
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
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
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
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在下面也有文娱活动。
这里兴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里不少都会唱两句。
我去给他们化妆。
原来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妆,──鹅蛋粉、服脂、黑锅烟子描眉。
我改成用戏剧油彩,这比粉妆要漂亮得多。
我勾的脸谱比张家口专业剧团的“黑”(山西梆子谓花脸为“黑”)还要干净讲究。
遇春节,沙岭子堡(镇)闹社火,几个年轻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浅妆把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如花似玉,轰动一堡,几个女工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和几个职工还合演过戏,我记得演过的有小歌剧《三月三》、崔巍的独幕话剧《十六条枪》。
一年除夕,在“堡”里演话剧,海报上特别标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这里的老乡还没有见过布景。
这布景是我们指导着一个木工做的。
演完戏,我还要赶火车回北京。
我连妆都没卸干净,就上了车。
1959年底给我们几个人作鉴定,参加的有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
工人组长一致认为:
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
所领导考虑,才下来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
这样,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个思想总结后,经所领导宣布:
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
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画画。
我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我用多种土农药在展览牌上粘贴出一幅很大的松鹤图,色调古雅,这里的美术中专的一位教员曾特别带着学生来观摩);我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超声波”怎样用图像表现?
声波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我就画了农林牧副渔多种产品,上面一律用圆规蘸白粉画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圆)。
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
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
为什么设在沽源?
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沾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
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
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
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
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带了在沙岭子新华书店买得的《癸已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和两册《容斋随笔》(沙岭子新华书店进了这几种书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买,大概永远也卖不出去),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8月下旬。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
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
我曾经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叙述我的生活。
全诗已忘,只记得两句:
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
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
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沽源是绝塞孤城。
这本来是一个军台。
清代制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发往军台效力”,这处分比充军要轻一些(名曰“效力”,实际上大臣自己并不去,只是闲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一个人去军台充数)。
我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
效力军台
白天画画,晚上就看我带去的几本书。
1962年初,我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
“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
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该人是摘瑁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
“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
我不知道我们的人事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
“文革”期间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
“汪曾棋可以控制使用”。
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
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1979年给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别。
我到原单位去交材料,并向经办我的专案的同志道谢:
“为了我的问题的平反,你们做了很多工作,麻烦你们了,谢谢!
”那几位同志说:
“别说这些了吧!
20年了!
”
有人间我: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们大概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凭仗什么力量支持过来的。
我回答:
“随遇而安。
”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
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
“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
不“安”,又怎么着呢?
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
如北京人所说:
“哄自己玩儿”。
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
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
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
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
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
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
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
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
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
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
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199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