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姓之婚.docx
《同姓之婚.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同姓之婚.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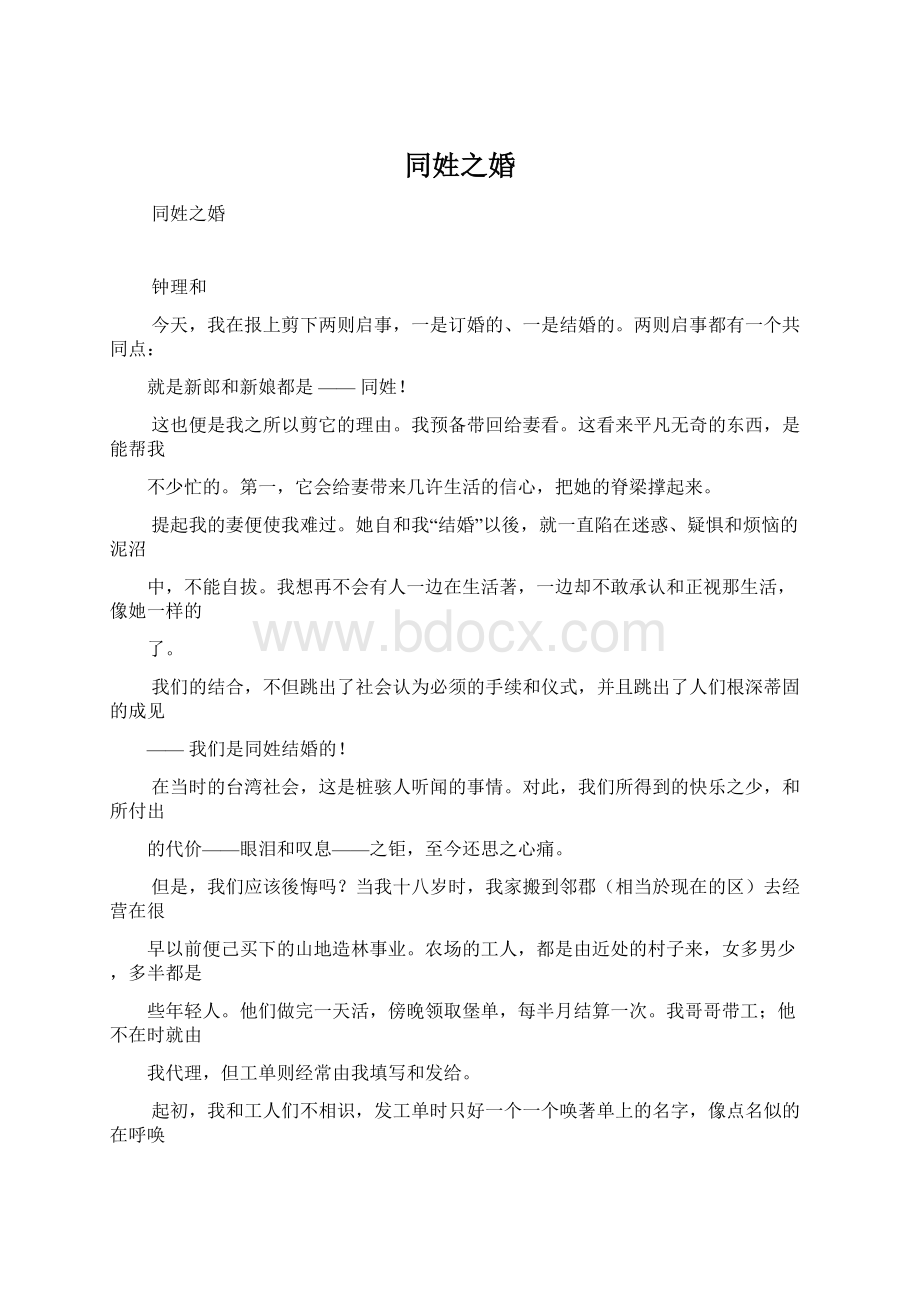
同姓之婚
同姓之婚
钟理和
今天,我在报上剪下两则启事,一是订婚的、一是结婚的。
两则启事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新郎和新娘都是——同姓!
这也便是我之所以剪它的理由。
我预备带回给妻看。
这看来平凡无奇的东西,是能帮我
不少忙的。
第一,它会给妻带来几许生活的信心,把她的脊梁撑起来。
提起我的妻便使我难过。
她自和我“结婚”以後,就一直陷在迷惑、疑惧和烦恼的泥沼
中,不能自拔。
我想再不会有人一边在生活著,一边却不敢承认和正视那生活,像她一样的
了。
我们的结合,不但跳出了社会认为必须的手续和仪式,并且跳出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
——我们是同姓结婚的!
在当时的台湾社会,这是桩骇人听闻的事情。
对此,我们所得到的快乐之少,和所付出
的代价——眼泪和叹息——之钜,至今还思之心痛。
但是,我们应该後悔吗?
当我十八岁时,我家搬到邻郡(相当於现在的区)去经营在很
早以前便己买下的山地造林事业。
农场的工人,都是由近处的村子来,女多男少,多半都是
些年轻人。
他们做完一天活,傍晚领取堡单,每半月结算一次。
我哥哥带工;他不在时就由
我代理,但工单则经常由我填写和发给。
起初,我和工人们不相识,发工单时只好一个一个唤著单上的名字,像点名似的在呼唤
时,我在男工名下加个“哥”,女工名下加个“姐”。
随即我就发觉这办法给我带来了意想
不到的好结果。
每个人听了之後,脸上都挂著和谐与融洽的喜气,似乎我们之间亲热了许
多。
“阿福哥、玉英姐、贞妹姐、新喜哥、桂香姐……”
随著我的呼唤声,工人一个个分开扰嚷的人群,出来把自己的单子接去。
男工活泼大
力,女工柔静□腆,羞人答答。
对於我附加的称呼,男工还无所谓,,有些女人则含笑提出
抗议,彷佛是蒙受了冤曲。
“哟,你看这人,”她们尖叫著:
“也不怕雷打呢!
”
但是我不理,继续喊下去:
“瑞金姐□□”
工人群中扬起一阵喧笑,接著我发现自己面前走出一个小泵娘来。
看上去,她的年龄至
多不会超过十七岁。
“你这人真讨厌,没老没少的!
”小泵娘含羞地说,噘著小嘴把单子领去。
我看著她那稚气的脸孔,也不禁好笑。
“平妹姐□□”我又喊,一边还浸在快乐的气氛中。
蓦的由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来,抢去了我手裹的那张单子。
我大吃一惊,定神细看,原来
是一个苗条身段的女人,这时已转过身子,坚定地走了。
她那傲慢不逊的举措,使我大大地
感到意外,因而在第二天发工单时,我便特别关心她。
“平妹姐□□!
”我著重语气叫,并把尾音拖长。
平妹出现在我面前了:
约莫二十左右的年纪,瓜子脸儿,直直的鼻梁上星见的眼睛,眉
宇间有著一份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慨。
我奇怪自己为何昨天竟没有留心到如此标致的一个女人。
“平妹姐,”我说,一边把单子交给她:
“不要再抢了,我会给你的。
”
平妹嫣然,露出一排洁白好看的牙齿。
“平妹姐,”我又说,无话找话:
“□家在村头?
村尾?
改天过路时,我可不可以进去
喝杯茶呢!
”
“水是有的,”平妹笑笑说道:
“就请你进来喝杯水。
”
工单发完,我小立庭边,目送工人们走下小坡。
在一群女工之中,我觉得平妹的後姿特
别的娉婷而优美。
内心不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轻微的骚动。
以後我每天特别关心她,发工单时总设法和她聊上几句话。
有时我们的眼睛互视一下,
她就向我静静地笑笑,那细碎的牙齿闪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鼓动。
我发觉自己是在爱著她了。
但也就在这时,我发觉她和我是同姓。
这事最初使我很失望。
就如一个小孩在街上看见
心爱的东西,而被父母强制拉开时的感到不满和不乐。
随後的一段时间,我陷在从未有过的傍徨和迷惘中,不知如何是好。
虽然这时候我还没
有明白的打算,但是同姓的意识苦苦缠著我不放。
当我和平妹说得高兴时,它会像一条蛇,
不声不响地爬进我的知觉中,使我在瞬间由快乐的顶点一下跌进苦闷的深渊。
有时我非常生
气。
但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向谁生气。
有时烦恼而懊丧,彷佛生命失去了最
珍贵的一部分。
有时我又满不在乎,以为谁也阻挠不了我的意志。
然而这一切顾虑都是多馀的,经不起平妹的一笑一聋,便去得无影无踪。
她那娟秀苗条
的容姿,已整个的占据了我的心。
那裹面除开对她的爱恋和渴望以外,便不再有什麽疑惧
了。
我发觉平妹对我也有好感,并且这好感随著日子正在渐渐变成别种性质的东西。
我还不
知道这某种东西应不应该称之为“爱”。
然而无论如何,这发现使我欢喜若狂,因而对她也
就更大胆更热烈了。
当时,我的双亲正在为我的婚事张罗,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议亲,每天我都去“看女
人”。
我是抱著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应酬这些而。
我一口气看了不下一二十个女人,但每次母
亲来徵求我的意见时,我只有微笑。
“难道说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吗?
”母亲不乐地问我。
我歉然地摇摇头。
有时一种奇异的冲动,使我几乎把自己的心事和盘说出。
我看著母亲
的脸在想:
如果让她知道我中意的人是谁将怎样呢?
母亲是不是要大大地吃惊?
或者骂我是
发疯了?
但是我和平妹相爱的事情,终於吹进父亲的耳中。
父亲大发雷霆;他说他不愿意自己有
这麽个羞辱门第的儿子,在盛怒之下把我赶出家庭□□一次、二次、三次。
我就像游魂般在
朋友亲戚家飘来荡去。
但是母亲舍不得。
每次都由她作好作歹的领我回去。
母亲的慈爱愁叹和哀诉虽也使我难过得、心裹有如刀割,可是我却出奇的冷酷、倔强。
好像在心裹面另有一个人在支使我,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母亲眼看说我不动,於是迁怒到
平妹身上去。
她骂她是淫邪无耻的女人,,是一个专会迷惑男人的狐狸精,将一切过错统统
往她身上推,显得自己的儿子是无辜受骗的牺牲者。
这实在是冤枉的。
然而我又不能替她分
说。
由是以後,平妹便给我负起了十字架。
她是赔了多少眼泪的呵!
我常常看见她那咬紧下
唇,泪流满面地忍受著一切的绝望的姿影。
平妹劝我离开她,回到父母身边去安分守己的做一个好儿子。
但我只能冷冷地听著,一
种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意识,使我在自己的行为中甚至感到无限骄傲和快慰。
它作成了我的意
志力的最大泉源。
“求你做做好事,离开我吧!
”有一天,平妹又如此向我哀求,一半也是为了可怜我像
丧家之犬的四处□徨。
“我求你,”她又说:
“你听他们的话去娶个媳妇,他们还是会喜欢你的,我也可以少
受点儿骂!
”
“□呢?
”我反问。
“你就不要管我!
”
“□也嫁人吗?
”
“请你放心,我是不会嫁人的,”她带著讽刺和自暴的口气说:
“不嫁人,也照样可以活下去的!
”
“我不娶!
”我说得很坚决。
“你不娶,我也不嫁给你!
”平妹也说得很坚决,彷佛我们在赌气似的。
但是像线一样
的眼泪却由她的双颊流下来了。
我们坐在溪旁,溪水幽咽,像伴她哭。
紫色的布□花,低低的垂覆在水面上,静静地。
我拿起她的手来抚摸著,心像飞到一千里以外去了一般感到空虚、寂寞和怅惘。
我凝视
著流动的溪水,有很大的功夫,在心裹盘算著一件事情,最後,我开口对她说:
“我到一个地方去,□在家裹等我,只一二年的工夫,我就回来领□走,远远的离开这
裹!
”
“你到哪裹去?
”她抬起头来,泪眼盈盈地望著我。
“满洲!
”
实际在很久以前,我便计划著这件事了,但总踌躇不决。
到了此际,我才充分觉悟到我
必须这样做,除此别无他途可循。
我想:
假使我们要结婚,便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一,
离开家庭;第二,经济自立!
其後不久,我便只身跑到东北渖阳去。
第一年,我弄了一份汽车驾驶执照,,努力建设
起一个小小的立足点来。
第三年,我回来领她走,如此结束了我们那坎坷不平,艰难悲苦的
恋爱。
那是民国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八月三日的事。
在外面,虽然不再有人来干涉和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可以完全领有我们的日子和
我们自身,而舒展一下数年来郁结的胸怀和紧张的神经了。
然而妻总还忘不了对世人的顾
忌。
彷佛随时随地可能由那一个角落伸出一只可怕的手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关系随时都
有被破坏和拆散的可能。
她那过分踌躇与疑虑,使我做丈夫的非常苦恼。
然而,那一段时间,在我们却还是最平静、最幸福、最甜蜜的。
台湾光复的翌年夏初,我们敌不过乡心的引诱,於是回到久别的台湾,起初依照预定计
划留在高雄□□那时我一个最小的兄弟便住在那裹。
然後,又搬到我做事的任所去。
但是多
麽不幸,不到一年,我生病了。
为了以後的生活著想,我们只好硬著头皮,回到故乡家裹
去。
那裹有我一份应得的产业,可资一家四口人的生计。
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料到的一著。
我
们怀著受难者的心情,登上火车。
家裹,父亲已於前几年病笔,兄弟也分散了,只有大兄一房人守著老屋。
家人,包括母
亲在内,对平妹的态度,是颇微妙的。
他们虽说过去已曾相识,然而却有如对一个外国人似
的处处表示应酬。
在他们的言语和仪态中都带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成分。
□□但是大致说来,大家尚能平静相处,不快的事件还是由外面来的。
不多几天,光复後的第一次户口总检查届临,乡公所来了几个人预查户口。
我们的户
籍,在接收时不知为何竟给脱漏了,不消说孩子的出生,就是我们的结婚手续都需重新申
报。
他们问我妻的姓名。
“锺平妹。
”我说。
其实,他们都认识我和平妹,特别其中之一,过去有一段时间和我玩得不错。
何况我和
平妹的事,周围几十里都哄传过,因此,他们是应该一切都很明白的了。
不过我以为人家既
然是公事公办,那麽我也只好照实说出。
“什麽?
”他们重问了一遍。
“锺平妹!
”我又重说了一遍;心裹有点不耐烦。
“锺?
”他们彷佛吃惊的样子,眼睛向我注视:
“同姓呀?
”
我非常生气;我认为他们存心与我为难,我粗暴地反问道:
“同姓又怎麽样?
”
此时,一直就坐在我旁边的大兄,似乎感到场面有点僵,连忙站出来给我们圆场:
“是的,是的,锺平妹!
”他说。
他们冷冷的看著我,却也不再多问什麽了。
为了这事,一整天我都不好过。
这些人的卑劣和虚伪,令我愤懑。
从这件事,我清楚地看出世人还未能忘怀於我和平妹的事情,这是一个警告,我们此後
的日子,不会是很平静的。
我很为平妹担心。
她是否经得起来自周围的歧视和指摘呢?
她从
前的朋友,即使是最亲密的,现在都远远的避开她了。
彷佛我们已经变成了毒蛇,不可亲近
和不可触摸了。
我为怕平妹伤心,曾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去邀请,甚至哀求她的朋友到
我家来游玩;但没有成功过一次。
有一天,找到附近一个山寺去散步,不期遇到妻的一位旧日的好友。
我欢欣而雀跃,如
获至宝。
这次无论如何总得把她留住,请到家裹去。
□□我这样想;我打算让平妹高兴高
兴。
经过我一番歪缠和坚请,於是她和我约定;只需再耽搁一会儿就去,叫我先行。
我飞奔
回家把这消息告诉妻。
她此时正在预备午膳,听了满心欢喜。
她请我给她找找家裹所能找到
的可口的东西,她准备留她的朋友吃午饭。
我给她翻出几只鸡蛋和两尾鱿鱼。
夫妻两个兴奋
得在家裹转来转去,等待贵宾驾临。
饭菜已经烧好了,而她□□妻的朋友,还不见到来。
妻开始不安起来,殷切的问我是否
真的看见她?
她问她在寺裹?
於是我不得不将方才的邂逅,从头再说一遍。
我们等了再等,桌上的菜肴在慢慢的凉下来。
妻万分焦急,吩咐我在家看著,她自己则
匆匆的向寺裹跑去。
我也有点动摇,不时由窗口往外张望。
不大的工夫,我看见那条通往山
寺去的,有著茂密的龙眼树的小径上,有人影在幌动。
妻回来了,可是只有她一个人!
由她的失望而沮丧的表情,我察知事情已经出了岔子。
我迎上去,忍不住问她:
“她不来吗?
”
“她走了!
”她答得很低,红著眼圈,就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她走了?
”
我好像挨了一个重重的耳光。
可是我能说什麽呢?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并且拿好话安慰
妻,像哄小孩子。
我觉得她是够可怜的。
“我想是临时有什麽急事先回去了,”我说:
“大概过一两天就会来的!
”
“不!
”妻摇摇头:
“她讨厌我们!
”
讨厌我们。
平妹说得丝毫不差。
这一句话道破了周围和我们的关系,使我无话可说。
外
边,明晃晃的太阳照亮了每个角落。
我意识了这是强有力的世界,虽然它是不理想的世界。
我茫然站著,感到自己是这样孤独无援。
而事情还不止此,还有更难堪的侮辱,□□更高的试□,在等候我们,需要我们更大的
忍耐。
在很早以前,我就发觉我们的孩子也成为人们取笑和寻开心的对象了。
我已无数次听到
过他们指著我们的孩子说:
“牛,畜牲养的。
”这样的话了。
我只希望这些话不会落到平妹
的耳朵才好。
我想像她听见这话後的痛苦,而感到寒心。
有一天,傍晚时分,平妹在猪栏□猪,两个孩子在庭院前玩著,这时来了几个女人□□
来坡下做活的,她们常常到这裹来歇息,在凉亭下聊天。
其中一个女人忽然叫著我们的孩子说:
“小孩子,你有几条腿?
四条是不是?
四条腿?
”
另一个女人马上加了进来。
她给孩子指著系在庭边一棵树下的牛,说:
“小孩子,那是你爸爸,是吧?
你爸爸是牛公,你妈妈是牛母,你是小牛子!
”
宪儿□□我们的大儿子,不解其意,莫名其妙的看看她们,又看看牛。
她们都大声哄笑
起来。
“你看,你爸爸在倒草(反刍)哪!
”
她们说著又大笑起来。
我□□在屋裹,恰似被兜头冲了盆凉水,浑身毛骨悚然,我往猪栏那边望去;,在苍茫
的暮色中,只见平妹靠著齐腰高的竹栏立著,脸向著那边。
我不知道妻是否也已听见,我祷
天祷地,希望那话声不致送进她的耳朵,或者猪的咀嚼声大些,把话声压下去。
但是,她已经听见了!
她挑著两只空水桶,一进入屋裹,眼泪便潸潸地流下来。
当晚她哭得很悲惨。
她告诉
我,外边人们是怎样的在奚落我们的孩子。
我想不起适当的话来向她劝解,只好让她尽情哭去。
我觉得很对不起她,这些都是我的
不好。
我们是不应该回来的。
我想想找们以後的生活,不禁迷惘起来。
日子在烦恼中滚流著、转瞬间,半年过去了,而我的病,却没有丝毫进展。
长此下去,
何时痊愈,颇难预料。
因此,我打算入院治疗,平妹也同意我这样做。
半个多月前,我曾给
台北的朋友去信,请他打听医院的状况,和办理登记手续。
而今,朋友的回信到了,说是一
切都已弄妥,叫我即可动身北上。
可是教我如何忍心抛下她们母子呢?
我把朋友来信的事情
搁下来,不向平妹提起。
我怀著烦闷的心情走到埤头去。
近来我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裹去坐一会儿的,那裹有绝
好的眺望。
我在一块眠床大小的石板上,枕著掌心仰卧著,潺潺的流水声,只在头下,我看著异常
辽阔的天空,徐缓地移动著、舒展著的流云,哀愁像石块似的压在心上。
我想起我们自从回家,一直到今天所遭遇到的种种事情,实在不能放心走路。
自己走
後,她们□□平妹母子会安静的活下去吗?
人们不会像历来那样残忍的对待她们吗?
如果再
遇到横逆,她们能够安稳地度过吗?
我这样一层一层地想下去,这些思想使我忐忑不安,黯
然心痛。
但是次一瞬间,我又打消了这些念头。
也许她们会活得更好些!
□□我如此安慰自己,
於是站起身来:
我不该想得太多!
我很晚才回家。
在屋角边,我碰见了正由大兄那边出来的两三个农夫模样的年轻男子。
闪身而过时,他们全用了那种令人不快的眼光向我扫视。
妻的口角边,噙著久已不见的微笑,并且频频向我眨。
我发觉这眼睛有异样的光芒。
我
怔怔的看著她,有点纳闷,也有点惶惑。
待孩子都睡定了,我们相对喝茶。
平妹开口了:
“他们说起我们的孩子□□”
我微微一颤;又是他们!
而且又是我们的孩子!
然而妻却一本正经的说下去:
“他们说,我们同姓结婚,怎麽会生出这样好的孩子呢?
”
“哦!
”
“他们说,”她又说:
“我们的孩子生得又聪明、又好看□□”
原来如此!
我不禁愕然;继而又苦笑起来。
这和自己的预料是相差得太远了。
我们久已不敢有这样的期待、这样的恭维。
偶一听
著,反而觉得有些生疏,而且刺耳。
妻说著,十分得意。
她是最乐意听人家称赞她的孩子的。
她像十四五岁的少女那样,笑
得天真、娇憨;眼睛在幽暗的煤油灯下,更觉迷人了。
於是我不觉的也高兴起来。
我们夫妻头一次这样欢喜。
前此,特别是这半年来,我们原只有眼泪和叹息的。
我忽然想起朋友的信。
而也就在这时候,平妹静静地仰首看我,脸上的笑容,已经是收
起来了。
“阿铮,”她轻轻地说:
“台北还没有来信吗?
那天来的那一封,不是呀?
”
“来了,”我说:
“就是那封!
朋友说,一切都办要了,叫我接信就□□”
“就去吗?
那你为什麽还不走?
你不放心,是不是?
”
“□能住下去?
”
“能!
”
“□哭过呢?
”
“哭过!
那是因为有你在著,心裹有委屈,哭哭,有人心疼。
你尽管放心走;我能哭,
也能不哭!
你不在家,我守著两个孩子过日子□□宏儿也会跟我笑了。
”
“□不怕日子会更难过?
”
“我知道!
我能忍耐!
只要你病好,我吃点苦,值得!
”
“我这一去,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来呢?
”
“都不要紧;我等著你!
我说过了:
我能忍耐!
反正他们不能把我宰了。
他们理我,陪
他们说几句;不理我,我逗宏儿笑!
只要你病好回家,我们母子还是一样快快乐乐的,要
不……!
那你早点儿走吧,只管放心,我会过得很好的!
”
第三天,我离别了他们母子,来到北部。
当天清晨,他们伫立在庭前龙眼树下;妻怀中
抱著刚满周岁的宏儿,宪儿则紧紧偎依在她脚边。
三对依依难舍的眼睛,送著我走下斜坡,
将到坡尽处时,我回过头去,只见妻在向我微笑,那比哭还要使人难受的藏著泪水的笑。
我
一气走完坡坎,转入田珑。
再回头过去,但这回我仅能看见在空中摇曳著的一段龙眼树梢,
在□□的向我挥别。
..................
现在,三年了,就一直没有回去过。
天天,她们母子那冷冷清清相依为命的影子,不断
地在我跟前浮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