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docx
《解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解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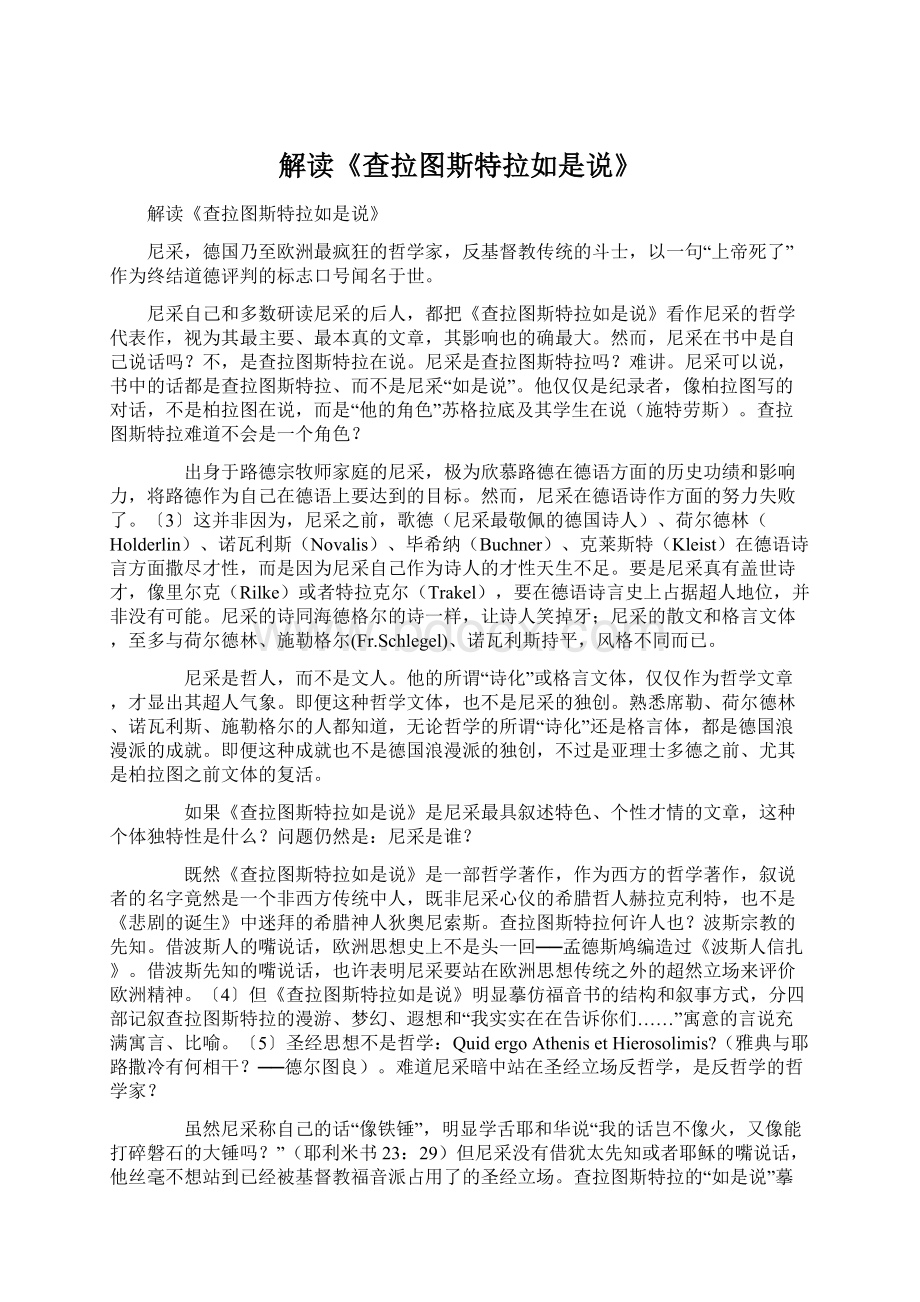
解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解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德国乃至欧洲最疯狂的哲学家,反基督教传统的斗士,以一句“上帝死了”作为终结道德评判的标志口号闻名于世。
尼采自己和多数研读尼采的后人,都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作尼采的哲学代表作,视为其最主要、最本真的文章,其影响也的确最大。
然而,尼采在书中是自己说话吗?
不,是查拉图斯特拉在说。
尼采是查拉图斯特拉吗?
难讲。
尼采可以说,书中的话都是查拉图斯特拉、而不是尼采“如是说”。
他仅仅是纪录者,像柏拉图写的对话,不是柏拉图在说,而是“他的角色”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在说(施特劳斯)。
查拉图斯特拉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
出身于路德宗牧师家庭的尼采,极为欣慕路德在德语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影响力,将路德作为自己在德语上要达到的目标。
然而,尼采在德语诗作方面的努力失败了。
〔3〕这并非因为,尼采之前,歌德(尼采最敬佩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毕希纳(Buchner)、克莱斯特(Kleist)在德语诗言方面撒尽才性,而是因为尼采自己作为诗人的才性天生不足。
要是尼采真有盖世诗才,像里尔克(Rilke)或者特拉克尔(Trakel),要在德语诗言史上占据超人地位,并非没有可能。
尼采的诗同海德格尔的诗一样,让诗人笑掉牙;尼采的散文和格言文体,至多与荷尔德林、施勒格尔(Fr.Schlegel)、诺瓦利斯持平,风格不同而已。
尼采是哲人,而不是文人。
他的所谓“诗化”或格言文体,仅仅作为哲学文章,才显出其超人气象。
即便这种哲学文体,也不是尼采的独创。
熟悉席勒、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施勒格尔的人都知道,无论哲学的所谓“诗化”还是格言体,都是德国浪漫派的成就。
即便这种成就也不是德国浪漫派的独创,不过是亚理士多德之前、尤其是柏拉图之前文体的复活。
如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具叙述特色、个性才情的文章,这种个体独特性是什么?
问题仍然是:
尼采是谁?
既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作为西方的哲学著作,叙说者的名字竟然是一个非西方传统中人,既非尼采心仪的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也不是《悲剧的诞生》中迷拜的希腊神人狄奥尼索斯。
查拉图斯特拉何许人也?
波斯宗教的先知。
借波斯人的嘴说话,欧洲思想史上不是头一回──孟德斯鸠编造过《波斯人信扎》。
借波斯先知的嘴说话,也许表明尼采要站在欧洲思想传统之外的超然立场来评价欧洲精神。
〔4〕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明显摹仿福音书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分四部记叙查拉图斯特拉的漫游、梦幻、遐想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寓意的言说充满寓言、比喻。
〔5〕圣经思想不是哲学:
QuidergoAthenisetHierosolimis?
(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
──德尔图良)。
难道尼采暗中站在圣经立场反哲学,是反哲学的哲学家?
虽然尼采称自己的话“像铁锤”,明显学舌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
”(耶利米书23:
29)但尼采没有借犹太先知或者耶稣的嘴说话,他丝毫不想站到已经被基督教福音派占用了的圣经立场。
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摹仿福音书的叙事和教诲口气,不过为了与耶稣基督作对,其“如是说”言必反福音书中的耶稣之言。
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尼采站到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这两个西方思想源头之外,他还能算哲人?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可以算哲学书?
也许查拉图斯特拉的角色是狄奥尼索斯的化身,代表悲剧诗人反哲学的传统。
可是,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激情洋溢中”和他站立的“高山绝顶之上”,歌德、莎士比亚这些悲剧诗人的后代“可能会喘不过气来,但丁同查拉图斯特拉相比,不过是个皈依者而已”(这个人6)。
比较文学或者跨文化学者兴奋起来:
看啊,尼采多么靠近东方、热爱东方……然而,尼采说,那帮编纂《吠陀经》的教士们“连给查拉图斯特拉脱鞋的资格都没有”。
与耶稣主要对门徒“如是说”不同,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经常对自己说。
查拉图斯特拉重新“成人”之前说的第一句话是对太阳说的。
太阳就是查拉图斯特拉自己,对太阳说,就是对自己说。
“这样一个人,假如他自言自语,将用什么语言?
纵酒狂歌的语言”(这个人7)。
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否就是尼采的自言自语呢?
就算是罢。
“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也可以是一种隐身(sichzuverbergen)手段”(善恶169)。
尼采在自传中明白说过,自己是“这种纵酒狂歌的发明者”(这个人7)。
尼采还说过:
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哲人是“真正真实的”(善恶177)。
倘若如此,尼采就仍然是一个哲人。
只不过我们切不可轻率地把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当作尼采的真言,查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是谎言──偶而夹杂几句实话。
是的,我劝你们离开我,并且抵制查拉图斯特拉!
最好因他而羞愧!
也许他欺骗了你们。
(如是说:
《论馈赠的道德》)
查拉图斯特拉的这句“如是说”仅仅随便说说?
没有真理,只有解释?
暂时先放下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满纸谎话这一问题。
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究竟说的什么?
是否有可以称为查拉图斯特拉学说的东西?
尼采自己告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宗旨是永恒复返思想,也就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这个人1)。
依据这一告白,洛维特以为,“永恒复返”不仅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主题,而且是尼采思想的基本学说。
“无论愚蠢还是睿智,永恒复返说都是理解尼采哲学的钥匙,并且说明了尼采哲学的历史意义,因为它重新复活了早期基督教与古典异教的争执。
”〔6〕海德格尔对自己昔日的学生的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
是谁?
”的演讲勾消了这一说法:
“永恒复返”说的确出现在、而且主要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然而,这种学说既无法说明、也无可反驳,仅仅在带出值得思议的、“面相之迷般的”问题。
〔7〕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永恒复返”可能是大假话,至少暗示不是尼采的真言。
谜底在于“权力意志”的提法。
“永恒复返”与“权力意志”具有“最为内在的关联”,是重估价值思想的一体两面,似乎“永恒复返”是显白表达(不等于谎言),“权力意志”是隐微表达。
海德格尔断言,如果没有把握到这两种表达“最为内在的关联”,并“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基本设问,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
〔8〕权力意志论是尼采的真言,亦是尼采思想的历史功绩,它颠倒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学说——对于存在的理解。
沿着这条可以称为本体—认识论的解构之路,海德格尔开始解释尼采解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革命性”行动:
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最后一人,以摧毁这一传统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精髓。
权力意志论不过是在谢林那里达到顶点的唯意志本体论的结果,因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表达,预示了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
〔9〕
某些后现代思想家并不理会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谱系论,但也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思想入迷,以为其中隐藏着“生肌权力”(biopower)的启示。
福科钟情的既非《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非《权力意志》,而是《道德的谱系》。
然而,“为什么尼采要对追求起源提出挑战?
”回答是:
“为了揭示通体打满历史印记的身体,并揭示历史摧毁这个身体的过程。
”〔10〕“权力意志”不是柏拉图主义存在论的痕迹,而是显露身体的标记。
通过“权力意志”的提法,尼采展露出生命的本原现象。
德娄茨由此得到启示:
凡考虑到生命的思想都分享了其对象的权力(power),因而必然会面对权力的策略。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成了德娄茨最后的思想,《什么是哲学》的结尾透露,尼采教德娄茨把生命定义为绝对的直接性、“无需知识的纯粹沉思”、绝对的内在性,是福科临终都还在思考的“生肌权力”。
“永恒复返”既是宇宙论的,更是“生理学说”,是“生肌权力”的生成论。
〔11〕尽管撇开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史的尼采解释,德娄茨的尼采解释仍然进入了现代哲学中超验论与内在论的对立,试图接续由斯宾诺莎发端、尼采彻底推进的内在论谱系。
对于海德格尔,理解“权力意志”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事关“未来的世纪”,同样,生肌权力的“生命”概念据说“作为福科和德娄茨思想的遗产,肯定将构成未来哲学的主题”。
〔12〕
对如此发微尼采的“纵酒狂歌”,将歌词阐发为“存在学说”或“生肌权力”学说,德里达给予了尼采式的摧毁:
尼采文章根本没有隐含什么确定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最终含义。
发微或阐发尼采学说的人都忘了尼采的启示:
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参善恶34)。
要从尼采“纵酒狂歌的语言”中找出某种学说,就像大白天打着灯笼在街市上找上帝。
尼采文章总用两种、甚至多种声音说话,因为他对世界的肯定是一种思想游戏,要求风格的多声道。
风格成为思想本身,没有尼采,只有theNietzsches(尼采们)。
尼采善用短小语句,如果将这些语句与其总体风格分开,根本不可理解、而且经常自相矛盾。
尼采文章因此有无限制的解释可能性,哲学在他那里成了无限的解释。
〔13〕德里达不仅挑战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也瓦解了福科—德娄茨的尼采解释。
这些尼采读法仍然受传统的真理问题支配,依附于某种形而上学幽灵,难怪他们看不到尼采文章的多样性。
话虽如此,德里达的尼采解释依然得自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恰如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方式恰恰来自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
把尼采看成彻底摧毁形而上学逻各斯的先驱,而不是看成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式解释学行动的继承、发扬?
〔14〕再说,与内在论对立的超验论谱系从康德经胡塞尔传到列维纳(Levinas),海德格尔恰恰站在两个谱系的转换关节点——胡塞尔与尼采交汇的地方。
的确,尼采文章大都不像“学术”论文,这使得人们很难从其论述形式中找到其思想主张的内在理路。
即便可以归结出所谓“权力意志”、“重估价值”、“超人哲学”、“永恒复返”一类学说,实际上都依赖于重新组织尼采的话。
解读尼采,解释者不得不明确摆出自己的解释框架,不能像解释其他思想家比如康德、黑格尔那样,躲在他们的思想框架中作出自己的解释。
海德格尔、福科、德娄茨、德里达的尼采解释,哪个不是以自己的哲学框框为基础?
洛维特可能没有看错: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的革命性,并不在于接着尼采摧毁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在于不理会尼采文章自身,自己说自己的。
〔15〕
勾消尼采书写的内在实质,代之以多声风格,尼采就不在了。
然而,真的再不可能找到尼采?
尼采是谁,真的没有可能回答?
即便多声风格,也非尼采的发明。
柏拉图的对话充满了不同声音,能肯定苏格拉底的声音一定是柏拉图的声音?
基尔克果用过一打笔名,哪一个是他自己的声音?
柏拉图或基尔克果并非在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中不在了,仍然可以肯定有可以叫做柏拉图或基尔克果的思想。
角色或笔名都很可能是“隐身手段”,正因为有“身”要隐,才发明了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
尼采这个人在“风格”中隐藏自身,而不是根本没有尼采之“身”。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本打算写自传。
“自传”就是谈论自己。
如果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尼采“自言自语”,何需再写自传?
写自传的愿望,表明尼采在“隐身手段”中说话感到憋气不能畅言。
然而,尼采放弃了写自传,代之以《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然后才作了自述(《瞧这个人!
》),然后才“惨死在思想的十字架上”(托马斯·曼)。
从《善恶的彼岸》开始,尼采越来越多自我引证——引证自己的作品,《瞧这个人!
》更是大段抄录。
德里达很可能被尼采“没有真理,只有解释”的话骗了。
并非没有一个尼采,“尼采们”不过是尼采的身影——就像他一本书的书名“漫游者和他的影子”。
尼采不是后现代的非逻各斯论者,他追求真理,只不过不直言真理。
德里达没有去问为什么尼采不直言真理,反而以为尼采的言说证明根本没有真理,实乃典型的后现代的自以为是。
查拉图斯特拉口中的“蟒蛇”
姑且不谈尼采公开发表的论著,尼采从来没有打算发表的书信、明信片可以证明,“永恒复返”、“权力意志”、“重估价值”的确是尼采想要说的“学说”,它们是否就是尼采想说的真理,倒一时难以确定。
在据尼采自己说宗旨为“永恒复返思想”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权力意志”已经出现了。
查拉图斯特拉说: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智者,一种是民众。
智者身上的热情是“求真意志”,其实质是要“所有的存在应当顺从”自己,如此意志就是权力意志:
“你们意欲创造一个你们可以屈尊崇拜的世界;这就是你们终极的希冀和陶醉。
”可是,民众也有自己的“权力意志”——他们所相信的善恶分明的伦理。
这里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意志”,如果我们要谈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究竟该说哪一种“权力意志”?
查拉图斯特拉接下来的“如是说”马上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善用比喻的查拉图斯特拉继续说:
“不智者自然是民众——他们犹如一条河川,河上有一小舟向前漂流,小舟上载有种种庄重的、隐匿着的价值评估。
”(如是说:
论超越自我)这段“如是说”让我想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政治古训,民众为河川、智者为小舟,明明说的是统治关系,如此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以价值评估为基础的。
为什么?
两种“权力意志”是什么关系?
谁求真?
不是君王,也非民众,只有哲人。
“求真意志”是智者(哲人)的权力意志,它与民众的权力意志(善善恶恶)处于支配性关系,这里的哲人看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而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谓的哲人—王。
在世上谁应该统治?
有求真意志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求真意志才能排列价值秩序的高低,统治的正当性就基于这种高低有序的价值秩序。
既然更高的权力来自更高的价值,而不是恰恰相反,智者(哲人)就应该展示出自己求得的价值,为什么查拉图斯特拉又说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
查拉图斯特拉教诲了智者的“权力意志”就是权力者“要当主子的意志”后,马上说到:
你们,价值评估者啊,你们用自己有关善恶的价值和言行行使你们的权力;这就是你们隐而不彰的爱和你们惊魂的光辉、颤栗和激奋。
然而,从你们的评价中产生了一种更强的权力,一种新的征服:
因它之故,蛋和蛋壳都破碎了。
(如是说:
论超越自我)
是否为了不让“蛋和蛋壳都破碎”,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
在这段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中,权力意志与重估价值的确显出内在的紧密关联。
尽管没有用到“永恒复返”的字眼,但河川不能自己流动,是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在使它动,这就是“永恒复返”。
然而,相当明显的是,这段“如是说”的经脉不在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学“最内在的关联”,而在智者与民众的政治关系──两种“权力意志”无法公开共存。
查拉图斯特拉当时大谈“求真意志”,越说越忘乎所以,几乎就要把“隐匿的”真理讲穿,兴奋得忘了这真理本来说不得,必须隐藏:
“你们聪慧绝伦的人啊,让我们对此谈个够罢,尽管这不大好;但沉默更不好,真理一旦被隐瞒就会变得有毒。
”(如是说:
论超越自我)所谓
“超越自我”,听起来是一个道德哲学论题,实际上事关向民众隐藏真理,“超越自我”就是哲人克服想向世人宣讲真理的冲动。
那些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中去沉思形而上学残余或者发微身体权力的人,看来被尼采的其它话蒙骗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为什么尼采没有写自传?
现在可以有把握这样讲:
尼采感到还不到把“隐匿着的”真理说穿的时候。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语言上说是真正的壮举”,“也许只有《善恶的彼岸》的行业工匠歌手序幕中的精湛分析能与之比肩”。
〔16〕果然,《善恶的彼岸》开篇讨论了哲学家(智者)的“偏见”后,接下来就谈到智者“权力意志的权利”──杀死道德的上帝、也就是杀死民众赖以为生的善善恶恶伦理的权力。
尼采最后还斩钉截铁宣称:
(哲人的)权力意志之外,“一切皆无”(善恶36)。
这无异于说,只有智者(哲人)的“求真意志”才应该有绝对的、至高的主权。
紧接着,尼采讲了一句奇诡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大白话么:
上帝受到了驳斥,魔鬼却没有?
”恰恰相反!
相反,我的朋友们哪!
真该死,谁强迫你们说大白话(popularzureden)来着!
(善恶37)
尼采在生前未刊的笔记中曾谈到堪称伟人的三项条件:
除了“有能力从自己生命的巨大平面出发修炼自己的意志力”和不怕舆论、敢于蔑视“群畜道德”外,最重要的是“不能泄露自己的天机”,像《道德经》上说的,“知我者希,则我贵矣。
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假如有人识破了自己的真面目,他认为是不寻常的。
当他不对自己说话时,他就要戴上面具。
他宁肯撒谎,而不想讲实话。
因为,撒谎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
(意志962)
有一回,查拉图斯特拉与一个“来自幸福岛的人”出海航行,在船上的头两天,查拉图斯特拉一直没有说话,船上大多是侏儒,而他是“远游者和冒险家的朋友”,与侏儒没有共同语言。
实在闷得慌,查拉图斯特拉忍不住给侏儒宣讲起“永恒复返”教义,不料突然被狗吠打断了:
“我如是说着,声音压得越来越低,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思想和隐念。
蓦然,我听见一只狗在附近狂吠。
”接下来,查拉图斯特拉做了一个怪异得可怕的白日梦,梦见自己“突然置身乱石丛中,孤独、凄凉,沐浴在萧疏的月光里”,眼见一颤抖、哽咽的年轻牧人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如是说:
论相貌和谜)
中国民间有一种“黄道秘术”,据说修得这秘术可以赶鬼和施魔(最起码可以让打你的人痛而挨打的你自己不痛)。
修炼此功必须在僻静处,尤其不能听见狗叫或被女人撞见,否则前功尽弃(为何非得避女人?
也许《书》上说过:
“牝鸡不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修得这秘术的基本功,就是练习对自己知道的真相守口如瓶。
查拉图斯特拉做的那个白日梦,分明是他泄露天机后产生的恐惧——想想“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一生中唯一一次明目张胆戴上一副脸谱面具说话,而不像在其它场合,用种种隐形面具。
从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此惊恐,可见尼采何等在意说还是不说自己的真实世界观。
早在青年时期,尼采就被真理与谎言的关系问题搞得精疲力尽。
《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这篇文章,尼采生前没有公之于世。
文章头三节写得规规矩矩,语言没有丝毫夸张、浮躁、反讽,随后十来节草率得像题纲,似乎没有耐心把这个题目再想下去。
第一节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就个人希望保护自己反对其他人而言,他的智力一般多用来作假。
但就在同时,由于无聊,也因为必要性,他又希望社会合群。
他不得不和好,并从他的王国尽可能消除至少最明目张胆的“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这一和平协议带来的影响似乎是通向获得那令人困惑的真理冲动的第一步,从此就有了“真理”一说。
(笔记,页102)
查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显然没有解除真理与谎言的紧张,尼采还处于说还是不说的两难中。
等到《敌基督者》解除说还是不说的紧张,写自传的时刻到来,尼采的日子也满了。
这样的结局,其实查拉图斯特拉早就晓得:
“真的,哪里有毁灭,哪里有树叶飘落,哪里就有生命的牺牲——为了权力!
”(如是说:
论超越自我)。
尼采思想中看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紧张——真实与谎言或者哲人与民众的紧张,这是否才是真正需要沉思的尼采呢?
无论发微尼采的基本学说,还是沉浸在“尼采们”之中,都可能是尼采所谓“劣等哲学家的偏见”。
是否可以也像海德格尔那样说,如果没有把握到尼采说还是不说的紧张,“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
“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康有为直到仙逝都没有刊印《大同书》十部(合柏拉图《理想国》卷数!
),其弟子曾在《不忍》月刊连载头两部,当时,康子仍在海外流亡。
数月后康子返国,马上阻止继续刊登。
康子早已演成“大同之义”,为什么在世时不愿公之于世?
若说康子自感还不圆满,从《不忍》月刊连载到他仙逝,有十几年时间,足以修润。
当然,“大同之义”与康子一向讲的“虚君共和”改制论明显有矛盾:
改制仍然要维系传统伦理,并不是达至大同境界的步骤。
“虚君共和”是现世的政治法理,“大同之义”是理想的万世大法,根本是不同的政治原则。
但这一矛盾会影响到公布《大同书》吗?
有的思想史家(如萧公权)以为,这一矛盾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用西学对康子的影响就可以圆通。
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告诫,面对大思想者明显的矛盾必须慎微,留心此处可能有难言之隐。
朱维铮教授就有这种审慎,以为康子不公布《大同书》可能“别有缘故”。
〔17〕不过,康子最终“不能言”自己为万世开太平之义,究竟是因为康子“秉性之奇诡”(梁启超),抑或因为康子还没有为乌托邦找到历史“实例”(朱维铮)?
康子自己称“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难道是随便说说?
公羊家有大义微言之说,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所谓“隐微不显之言”、“精微要妙之言”。
“大义”与“微言”不同是否仅深浅之别,微言较大义隐深而已?
非也!
大义微言之辩,小康大同之辩也!
百姓自有百姓的生涯,不能承受圣贤人的大同世,小康世已是最高的社会理想。
春秋大义明是非、别善恶、诛暴乱,此“封建”大义专为小康世而设,中材之人已经可以得大凡。
但“封建,势也,非孔子本意”(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王制》)。
孔子微言所寓,非中材以上不能知。
小康世平庸之极,圣贤人会活得百无聊奈。
百姓与圣贤人的生活理想扦格难通,圣贤人心知肚明,却又不得明言要实现大同理想:
“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康子内外篇·阖辟篇》)。
究竟为什么不能言?
“言”就是要变成社会现实。
要是真搞大同世,像宋儒或毛泽东那样把微言转变成大义,就会“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
”(《大同书》)康子说“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就像查拉图斯特拉说“蛋和蛋壳都破碎了”,绝非随便说说。
“虚君共和”论乃“大义”,“大同之义”是“微言”。
梁子谓康子“始终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可能深得师心。
康子虽不晓得柏拉图氏有“高贵的谎言”术,却谙“道心惟微”(《古文尚书》)、“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管子·心术上》)等古训,懂得“言不必信”,所以才“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不忍白”不等于不说,微言并非不言。
微言是已经说出来的话,不过隐而难明而已。
公羊家坚持微言是口说,口口秘传,口传的才是真言。
但口说的意思是不形诸文字吗?
孔子微言在《春秋》,《春秋》已是文字,只不过后人不得望文生义,要懂得区分字面上说的和其中隐藏着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说”。
康子所谓孔子本意靠口说相传,到董子才形诸文字,意思并非指孔子本意通过子夏、公羊子等口传到《春秋繁露》才写成文字。
“《春秋》之意,全在口说,口说莫如《公羊》,《公羊》莫如董子”(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孔子王制二》)。
《春秋》、《公羊》、董氏《春秋》都是文字的东西。
形诸文字的含义因此是,用时人可以明白的话来写,但微言本来就不得用时人明白的话显白地说出来,所以董子之言仍然“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与口说没有什么分别。
口说与形诸文字之辩,有如大同、小康之辩,两种不同的书写——隐微的和大义的书写隐含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原则。
所以,《礼运》说小康世,“天下为家,言礼多而言仁少”,大同世“天下为公,言仁多而言礼少”(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
《礼运》与《春秋》都是文字的东西,却有“言”与“不言”、文字与口说的不同。
为什么非要分别口说与笔写?
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讨论过这一问题。
苏格拉底也说,文章有口说和笔写两种,笔写的文章要面对民众的信仰——民众以为正义、善和美的,这样一来,写文章的智者就无法把自己的真正看法讲出来,除非假定民众在德性和智性上与智者相同。
笔写的文章有说服效果,但“说服的效果是从民众的看法、而不是从真理来的”。
立法者(就是智者)为了让民众信服,就得顺着民众的心意说,笔写的文章就无异于欺骗或迷惑民众。
欺骗或迷惑民众是必须的,因为
“说到正义和善”,立法者与民众“各自有各自的看法”,而且“相互冲突”(斐德诺篇,页141—148)。
〔18〕
做文章必得讲究修辞术,修辞术不是简单的文章做法技巧。
习修辞术,关节点并不在于学会笔写文章的做法之类,而在于掌握民众的信仰和心意,“想做修辞家的人必须知道心灵有哪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