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docx
《第六章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六章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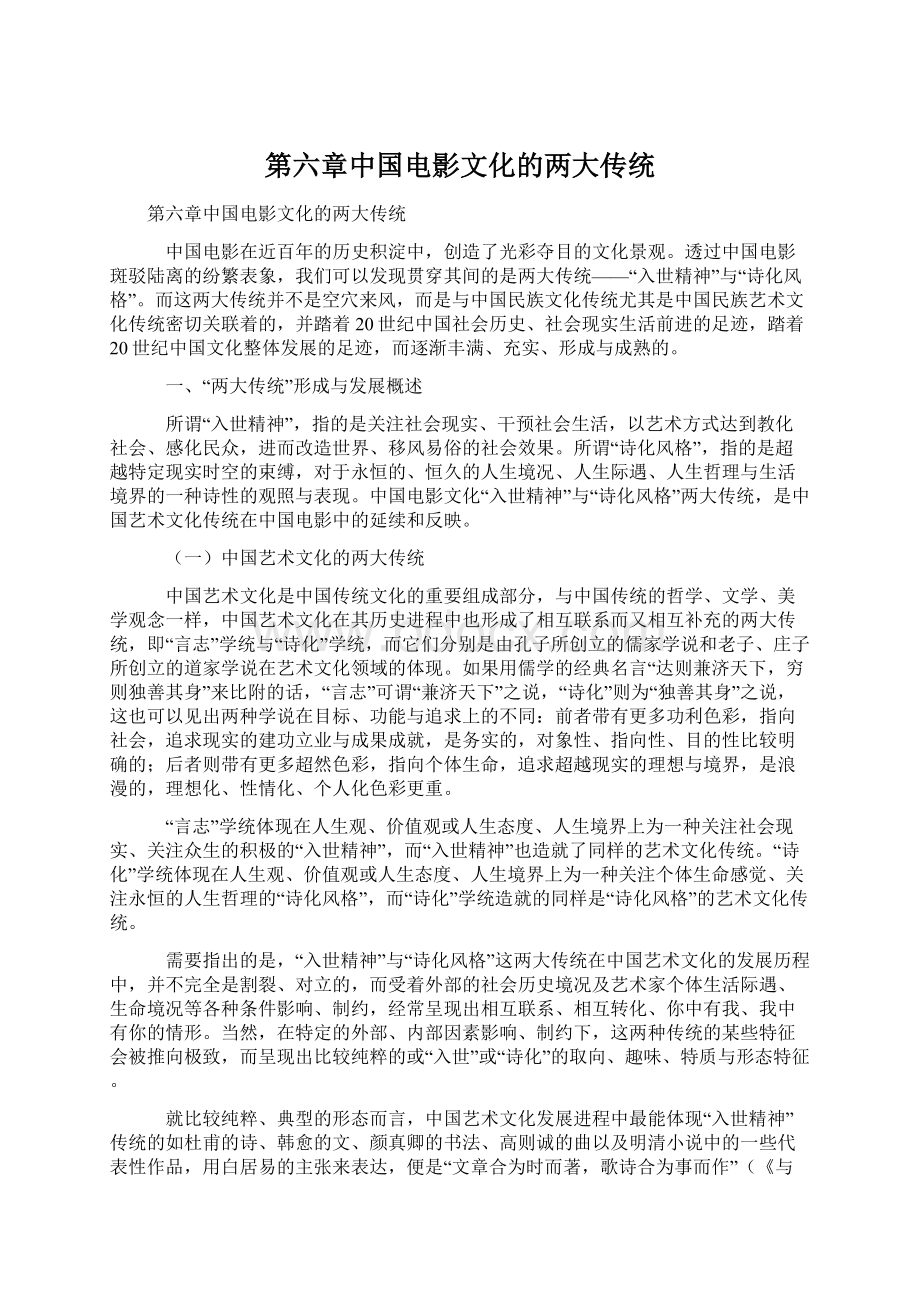
第六章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
第六章中国电影文化的两大传统
中国电影在近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创造了光彩夺目的文化景观。
透过中国电影斑驳陆离的纷繁表象,我们可以发现贯穿其间的是两大传统——“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
而这两大传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着的,并踏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社会现实生活前进的足迹,踏着20世纪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足迹,而逐渐丰满、充实、形成与成熟的。
一、“两大传统”形成与发展概述
所谓“入世精神”,指的是关注社会现实、干预社会生活,以艺术方式达到教化社会、感化民众,进而改造世界、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
所谓“诗化风格”,指的是超越特定现实时空的束缚,对于永恒的、恒久的人生境况、人生际遇、人生哲理与生活境界的一种诗性的观照与表现。
中国电影文化“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两大传统,是中国艺术文化传统在中国电影中的延续和反映。
(一)中国艺术文化的两大传统
中国艺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美学观念一样,中国艺术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也形成了相互联系而又相互补充的两大传统,即“言志”学统与“诗化”学统,而它们分别是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和老子、庄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在艺术文化领域的体现。
如果用儒学的经典名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比附的话,“言志”可谓“兼济天下”之说,“诗化”则为“独善其身”之说,这也可以见出两种学说在目标、功能与追求上的不同:
前者带有更多功利色彩,指向社会,追求现实的建功立业与成果成就,是务实的,对象性、指向性、目的性比较明确的;后者则带有更多超然色彩,指向个体生命,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与境界,是浪漫的,理想化、性情化、个人化色彩更重。
“言志”学统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上为一种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众生的积极的“入世精神”,而“入世精神”也造就了同样的艺术文化传统。
“诗化”学统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或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上为一种关注个体生命感觉、关注永恒的人生哲理的“诗化风格”,而“诗化”学统造就的同样是“诗化风格”的艺术文化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这两大传统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并不完全是割裂、对立的,而受着外部的社会历史境况及艺术家个体生活际遇、生命境况等各种条件影响、制约,经常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
当然,在特定的外部、内部因素影响、制约下,这两种传统的某些特征会被推向极致,而呈现出比较纯粹的或“入世”或“诗化”的取向、趣味、特质与形态特征。
就比较纯粹、典型的形态而言,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进程中最能体现“入世精神”传统的如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高则诚的曲以及明清小说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用白居易的主张来表达,便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这一“入世”传统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价值,尤其是对现实的伦理规范进而对现实的伦理政治的直接的实用性功能。
白居易将“入世精神”的精髓概括得最为清晰明了:
“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可以播於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
白居易的讽谕诗可以说将“入世精神”的实用功能价值推到了极致。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为之争论的“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等中国艺术传统的一些具体内涵与思想。
而最能体现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进程中“诗化风格”传统的则是具有浓郁文人、艺术家个人色彩的艺术创作,如田园诗、山水画、词曲小品等,陶渊明、王维、李清照、马致远、李贽、汤显祖、孔尚任等都有此一方面的传世之作。
当文人、艺术家因遭遇不幸、仕途不顺或退隐江湖、寄情山水之时,常常生发出关于宇宙、生命的某些富于哲思和才情的感喟、咏叹。
其表象常常是远离尘嚣的自然景观、景象、景物,如风花雪月、云烟雾雨、江河湖溪等,其“情节”与“细节”则常常是表现主人公思想情感情绪的某些行为,如独钓、品茗、孤眠、归牧、坐忘及抚弄把玩琴、棋、书、画等。
而渗透其间的哲思与情绪则常常与家国兴衰、人生无常、离愁别恨、无名感伤等联系在一起。
自然景观、景物之“象”,与文人、艺术家的上述诸多情思、情绪之“意”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个“意象”,进而升华为一个个具有内在力量的“意境”。
源自文人、艺术家内心的感悟、感怀、感伤,外化于宇宙自然的万事万物,形成富于禅意的种种意境,是“诗化风格”的显著特征。
有关“诗化风格”的理论学说众多,这里我们不妨取其几个典型去感受、感知:
“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当然这样两大传统的划分并不能表明二者泾渭分明,互不搭界。
正如一生图求建功立业的杜甫一方面有“安有广厦千万间”的社会关怀,一方面也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人生感喟。
一生与“婉约”相伴相随的李清照既有“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感怀感伤,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进取。
至于李白、苏轼、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等更是兼备两种传统之魂魄,将“金戈铁马”、“大江东去”的“入世精神”与“人生如梦”、“欲说还休”的“诗化风格”浑然一体地凝结起来,构筑起巍巍壮观的中国古典艺术大厦,以独具东方神韵、气魄的艺术文化品格,代代相传,源远流长。
“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这两大传统,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此消彼长,相互补充。
从总体上看,“入世精神”的追求使其与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紧密,不论是正面的维护还是负面的批判,其指向导致了其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之间保持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即“入世精神”的传统总是力求以伦理道德规范为起点与落点,以此牵连起文人、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种种思考、情感,牵连起他们的或感性或理性的感受、体验、判断与认识。
因此,“入世精神”传统成为中国艺术文化传统的主导潮流。
“诗化风格”的追求使其与文人、艺术家的个人化、心灵化的情感、状态紧密相联。
这其中有飘逸、放达、闲适,有感喟、感怀、感伤,情调不尽一致,但宗旨、意趣与取向则大致相近。
“诗化风格”的追求使其力图脱离某种特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而达到个性化的情感、情绪、生命状态的某种解放与超越。
正因此,不少学者把“诗化风格”传统视为最具东方情调、神韵,最能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传统。
“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这两大传统,在其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历史境况的变化以及文人、艺术家个体生命状态的变动,而呈现出时代、社会与个体的差异,打上了各具特色的内蕴、内涵与样式、形式的烙印。
但当新的时代来临之时,这两大传统并未从根本上消失,而是结合了新的时代、社会与个体生命的特征,呈现出新的形态、风貌。
(二)中国电影文化两大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诞生于中国土壤之上的中国电影,尽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从“西洋”“舶来”的,但却无法脱离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
近百年的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历程充分昭示了其与中国艺术文化传统,其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的深刻联系。
从这个意义与视角来看,中国电影文化依然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在20世纪的延续,中国电影文化因此依然可分为“入世精神”与“诗化风格”两大传统。
只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现实生活的改变,而在具体内涵、内容与样式、形式上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质与特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生活情状,紧张激烈的民族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使得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艺术文化领域同样充满了各种思潮派别的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新兴的电影文化感应着诸多的思潮,顺应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以其独特的方式、手段与语言描摹着、反映着、体现着社会生活与人生境况,逐渐形成了自己别具特色的两大传统。
中国电影文化“入世精神”的传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以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导倾向的革命斗争精神;二是以反对旧礼教、旧习俗、旧道德并针砭社会现实生活中种种丑恶行径为主导倾向的伦理化的社会批判。
1、“入世精神”之一——革命斗争精神
最早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体现出进步政治倾向的是新闻纪录片。
纪录辛亥革命成功的新闻短片《武汉战争》、纪录二次革命的新闻短片《上海战争》是迄今可查的宝贵影片。
此后《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及反映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影片都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轨迹清晰地纪录在电影之中。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革命电影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一批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人加盟左翼文化运动,使现代中国电影文化格局得到根本的调整与改变。
1931年9月,左翼“剧联”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通过了《最近行动纲领》,明确提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方向与任务。
这个《纲领》提出:
“除演剧而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
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员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组织电影研究会,吸收进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材,以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基础”;“同时,为准备并发动中国电影界的‘普罗·机诺’(即无产阶级电影)运动与布尔乔亚及封建的倾向斗争,对于现阶段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加以批判与清算的必要。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于1931年9月通过,旋于同年10月23日出版的《文学导所》第1卷第6、7期合刊号上公布。
——转引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第177~178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第2版。
)
自此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开始以高昂的革命斗争精神,加入到左翼文化的大阵营中,并逐渐发展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文化武器,革命的、战斗的、进步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文化的主导构成部分,并进而形成了自觉配合进步的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需要的重要传统。
田汉、夏衍、阿英、阳翰笙与聂耳、孙瑜、沈西苓、蔡楚生等一批革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在黑沉沉的旧中国推出了一批洋溢着时代激情、民族激情与政治激情的优秀影片。
这些影片将笔触伸到了工人、农民、妇女与知识分子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与斗争领域,在银幕上展现了一幅幅生动逼真而广阔深远的近世中国社会生活画卷。
体现“左翼”电影运动革命斗争精神的重要影片有《狂流》、《春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压迫》、《盐潮》、《脂粉市场》、《时代的儿女》、《共赴国难》、《城市之夜》、《母性之光》、《都会的早晨》、《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新女性》、《大路》、《桃李劫》、《自由神》等。
抗战前夕又有一批电影艺术家加盟左翼电影运动阵营,并在“革命斗争”精神的感召下,将创作视野进一步打开,推出了《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压岁钱》、《生死同心》、《青年进行曲》、《壮志凌云》等优秀影片。
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们克服种种困难,以极其饱满的革命热情创作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青年中国》、《塞上风云》、《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影片,极大鼓舞了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岁月里,革命的、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们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与迫害,顽强、机智地斗智斗勇,创作了《遥远的爱》、《天堂春梦》、《圣城记》、《乘龙快婿》、《幸福狂想曲》、《松花江上》、《新闺怨》、《三毛流浪记》、《假凤虚凰》、《丽人行》等优秀影片,尤其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影片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成熟而辉煌的阶段。
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电影纪录片在炮火硝烟中也锻炼成长起来,这些纪录着中国人民可歌可泣英雄壮举、纪录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生活的宝贵胶片,成为中国电影文化革命斗争精神传统的有力证明。
我们不会忘记,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电影事业,从1938年“延安电影团”建立开始,在艰苦卓绝的生活环境中,拍摄了彪柄史册的一些光辉的人物与光荣的生活。
如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白求恩大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还有《边区劳动英雄》等故事片。
与国统区进步电影一样,解放区电影更是直接在自己的拍摄、创作中传达、体现了革命斗争精神。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电影的革命斗争精神成为最主导、最主要的一种传统,贯穿于电影创作生产的方方面面。
以近百年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爱国救亡、奋斗进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可歌可泣的故事为素材,以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创作了一大批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的优秀影片,如《中华女儿》、《白毛女》、《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董存瑞》、《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柳堡的故事》、《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战火中的青春》、《风暴》、《聂耳》、《林则徐》、《青春之歌》、《老兵新传》、《万水千山》、《甲午风云》、《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兵临城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
从现当代文学名著改编而来的一些作品如《祝福》、《林家铺子》、《红旗谱》、《红日》搬上银幕也同样加大了其革命斗争的力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抗美援朝战争,也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上甘岭》、《英雄儿女》等影片中充溢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观众。
甚至一些类型片如歌舞片、戏曲片、儿童片、喜剧片及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不少影片,也同样被赋予了鲜明的革命斗争色彩与品格。
2、“入世精神”之二——伦理化的社会批判
“入世精神”在中国电影中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以伦理道德判断为主旨的伦理化的社会批判,即通过电影张扬“善”,鞭挞“恶”;通过“善”、“恶”的伦理道德判断,批判社会不公,展现人间的悲欢离合;通过伦理情感的宣泄,引发观众的同情与共鸣。
中国是一个最依赖伦理道德体系维护社会关系的国度,小至个人修养,大至国家统治,都有一整套严密、完整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维系,而且这些伦理道德规范、原则已成为中国人认识、判断、把握世界不可替代的方式。
从伦理道德规范的视角表现世事人生,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艺术文化中“入世精神”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期的中国电影人谙熟这一规则,他们懂得要抓住观众,必须从伦理道德视角与层面入手。
所以中国电影“入世精神”中社会批判精神的贯彻,常常是通过伦理道德层面的铺展来实现的。
简而言之,从伦理道德规范层面认识、判断与表现“善”与“恶”的对立(为达到感人至深的效果,常常表现“恶”对“善”的残忍与压迫,所以通常为“苦情戏”),进而展开社会批判。
郑正秋的《孤儿救祖记》(1923年),无疑为伦理化社会批判电影的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的一系列影片如《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挂名的夫妻》直到《姊妹花》等,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封建制度(尤其是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特别是对广大受压迫妇女的凌辱),抨击了封建婚姻的寡妇守节、养媳招婿、蓄婢营娼等不合理制度,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种种社会不公与社会罪恶。
蔡楚生在郑正秋开辟的电影创作道路上继续拓展。
《渔光曲》(1935年)讲述的是贫苦渔民家庭因破产而带来凄惨遭遇的故事。
善良而勤劳的社会下层劳动人民在冷酷而无情的社会恶势力欺压、盘剥下难逃噩运。
该片通过一个家庭的悲剧将笔触延伸到社会,探寻造成这悲剧的社会根源,上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走出国门,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完成于1948年的巨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亲情恩怨的伦理故事,将整个抗日战争八年的丰富历史内容纳入其中,将身陷敌占区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痛苦与大后方国统区上层社会的腐败,进行了力透纸背的对比,将巨大而深厚的历史内容作了伦理化处理,产生了空前的社会影响,将伦理化社会批判影片推向一个极致,也在中国电影史上竖起一座经典性里程碑。
伦理化的社会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学中的许多因素,也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一方面,透过亲情或友情等伦理情感的起伏跌宕,来判断是非曲直,来展示社会生活的风云变幻,来展开善恶美丑的社会批判,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的延续、延伸;另一方面,伦理化的社会批判,符合中国普通百姓的观赏习惯和审美趣味,在“悲情”、“苦情”中可以通过“煽情”引发观众们的伦理化情感的共鸣,满足他们对于社会矛盾、情感矛盾的焦虑的排泄,实现他们自我情感、心理的抚慰。
因此,伦理化的社会批判成为中国电影“入世精神”传统中不可或缺的、极富民族特征的一个部分。
尽管在五、六十年代伦理化的社会批判受到相当的抑制,但在谢晋的《舞台姐妹》等影片中依然延续了这个传统。
当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创作空间再一次得以打开的时候,此类影片又一次得到观众们的青睐。
3、“诗化风格”
中国电影的“诗化风格”传统,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
实际上“诗化风格”与“入世精神”在题材上并无二致,其差异更多体现在“落点”和艺术品格上。
从“落点”上看,同样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内容,“入世精神”传统往往更注重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展现,注重内涵的政治性、革命性与社会批判色彩,而“诗化风格”传统则更注重揭示相对普遍的人生问题、人的普遍的生存问题、人的情感和心灵深处潜在内蕴的感喟、感叹与感怀。
从艺术品格上看,“入世精神”传统追求实际的社会功能的实现,追求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干预、判断与触动,追求对于现存伦理法则与社会现象的反思与批判,追求对于积极进取的社会力量的肯定、讴歌与赞美。
“诗化风格”传统则未必追求对于现实社会存在的伦理性判断,而更关注着普遍的人性、人的情感与命运的存在。
在情感基调上,“入世精神”往往是激昂的、悲愤的,而“诗化风格”则往往是抒缓的、忧伤的。
“入世精神”传统更注重社会性功效,而“诗化风格”传统则更注重个人化特征。
孙瑜、吴永刚等是“诗化风格”传统第一代的代表人物。
孙瑜的《故都春梦》(1930年)透过主人公从底层爬到上层,从飞黄腾达跌落到潦倒沉沦的命运遭际,引发出对于“宦海浮沉,前尘如梦”的人的命运的感叹。
孙瑜的《野草闲花》(1930年)讲述了一个有钱少爷与卖花少女之间曲曲折折的爱情故事,套路近似《茶花女》,只是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这两部影片充溢着小资情调,浪漫、多情而忧郁、感伤。
许多镜头虚实相间,产生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吴永刚的《神女》(1934年)堪称这一时期“诗化风格”的典范之作。
一个为了自己的孩子忍辱含垢出卖肉体的妓女,为了自己的尊严而与社会不懈地抗争,但社会却不能容她。
在《神女》里,人性的种种复杂内涵都有机地被揉在故事中,被压迫、被污辱的人们的生存与命运长久为观众所牵挂与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部影片的女主角都是由阮玲玉饰演的。
一代名伶阮玲玉以她非凡的气质与才华,在银幕上塑造了一系列外表柔美、内心坚强、受尽屈辱又不懈抗争的美丽动人的中国女性形象。
这些形象既高贵典雅又朴实自然,既神韵飞动又端庄稳重,既张扬华丽又收敛含蓄。
阮玲玉精致绝纶的演绎给了中国电影“诗化风格”传统以最直接、最明了的阐释。
20世纪30~40年代狂风暴雨的民族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给中国电影“诗化风格”传统留下的空间日渐狭小。
在40年代极为罕见的此类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小城之春》。
这部由费穆导演的电影名片长期遭受电影业内外的冷遇。
但在中国电影“诗化风格”传统形成、发展进程中,《小城之春》无疑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是一个发生在女主人公与其丈夫和其昔日情人(突然出现)间的情感纠葛和缠绵不尽的故事。
在情感与理智、欲望与道德、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爱的理念与爱的行为之间所发生的重重矛盾,复杂又微妙地纠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人性的痛苦、生命的困惑、存在的尴尬。
尽管该片最后采取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选择,但激荡在每个观众心灵深处的波澜却难以挥之即去,而将长久地纠缠和萦绕着。
抒缓的节奏、淡淡的忧伤,不尽的余音,笼罩着全片,给予人们的是关于情感、欲望、爱等永恒而普遍的感受、体验与感悟、感怀。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电影“诗化风格”传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夏衍改编的《祝福》(桑弧导演)、《林家铺子》(水华导演)、王苹导演的《柳堡的故事》及表现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五朵金花》、《刘三姐》等影片,虽然不能称之为纯粹的“诗化风格”,但其中精美的画面造型、淡雅的情感基调、抒情化、写意化的风格韵味等与“诗化风格”传统是相传承的。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谢铁骊的《早春二月》。
该片从柔石小说原作《二月》改编而来,除保留原作的基本故事、人物、情节外,导演更在此片中融入了个性化、风格化的感受、体验、思考与表现。
在极富江南水乡特色的场景——小桥、溪水、小船、荷塘、柳林营造的氛围中,主人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爱欲与责任之间的痛苦,以及谣言、嫉妒等无所不在而又无影无踪的无形压力带来的困惑与尴尬,都超越了那个时代具体的历史内容给予我们的震憾,而在我们心灵深处长久地激荡起层层波澜。
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电影不可能摆脱当时整体的文化律令的制约。
即使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盛行的年代,我们在王苹的《闪闪的红星》,谢铁骊的《海霞》等影片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丝清新、淡雅而浪漫、多情的“诗化风格”的韵味。
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个以追寻人生况味的感受、感怀为主旨、以淡雅而浪漫情致为特征的“诗化风格”传统得到了较好的拓展。
吴贻弓、胡柄榴、黄建中等都为此做出过重要贡献。
二、“入世精神”的当代体现——谢晋与他的影片
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入世精神”传统与新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风尚与精神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具有新中国独特风采的新的精神境界。
而谢晋及其创作的一系列影片就是这种精神传统的最好的体现。
史诗手笔·时代激情·伦理视角
严格地讲,谢晋并不是靠他的哪一部电影而或闻名或传世的,从他50年代独立导演电影以来,迄今共有27部影片问世,其中大多数荣获了国内、国际各类大奖,在国际影坛产生了广泛影响,更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卓然独立,构成了谢晋式电影的一个完整的系列。
而《芙蓉镇》就是这个系列中较为典型、具有代表性的影片之一。
《芙蓉镇》先后曾荣获1987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故事片奖;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大奖——水晶球奖;第28届瓦亚多利德(西班牙)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人民奖和西班牙国家电台听众奖;第5届蒙比利埃尔国际电影节(法国)金熊猫奖;捷克第40届劳动人民电影节荣誉奖;民主德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的民主德国1989年发行的最佳外国故事片评论奖。
1、影片内容。
湘西山区有一个芙蓉镇,镇上有一位叫胡玉音的年轻女性,与丈夫黎桂桂开了一家米豆腐小摊,胡玉音漂亮、热情、聪明,同时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引得全镇老老少少趋之若鹜,也招致了对面国营粮店经理李国香的恼火和嫉妒。
胡玉音与丈夫黎桂桂辛辛苦苦,攒钱盖了一幢新房。
落成之日,镇党支书黎满庚、粮店主任谷燕山和众乡亲纷纷前来贺喜。
不到一年“四清”运动就开始了(1964年)。
李国香靠着当县委书记的舅舅的支持、提拔,当上了工作组组长,到芙蓉镇上抓阶级斗争。
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王秋赦,因家里一贫如洗而作为“土改根子”,成为了李国香依靠的对象。
王秋赦趁机将买去他土改分得的宅基地的胡玉音、黎桂桂“供”了出来。
李国香前来胡玉音家“调查”情况,将王秋赦提供的情况“通报”给胡玉音,令黎桂桂惊恐万分。
为了躲避阶级斗争引火烧身,胡玉音将小两口积攒的1500元钱交给黎满庚代为保管,胡玉音则跑到外地远亲家避风。
黎满庚曾是胡玉音青梅竹马的恋人,但因胡玉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