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docx
《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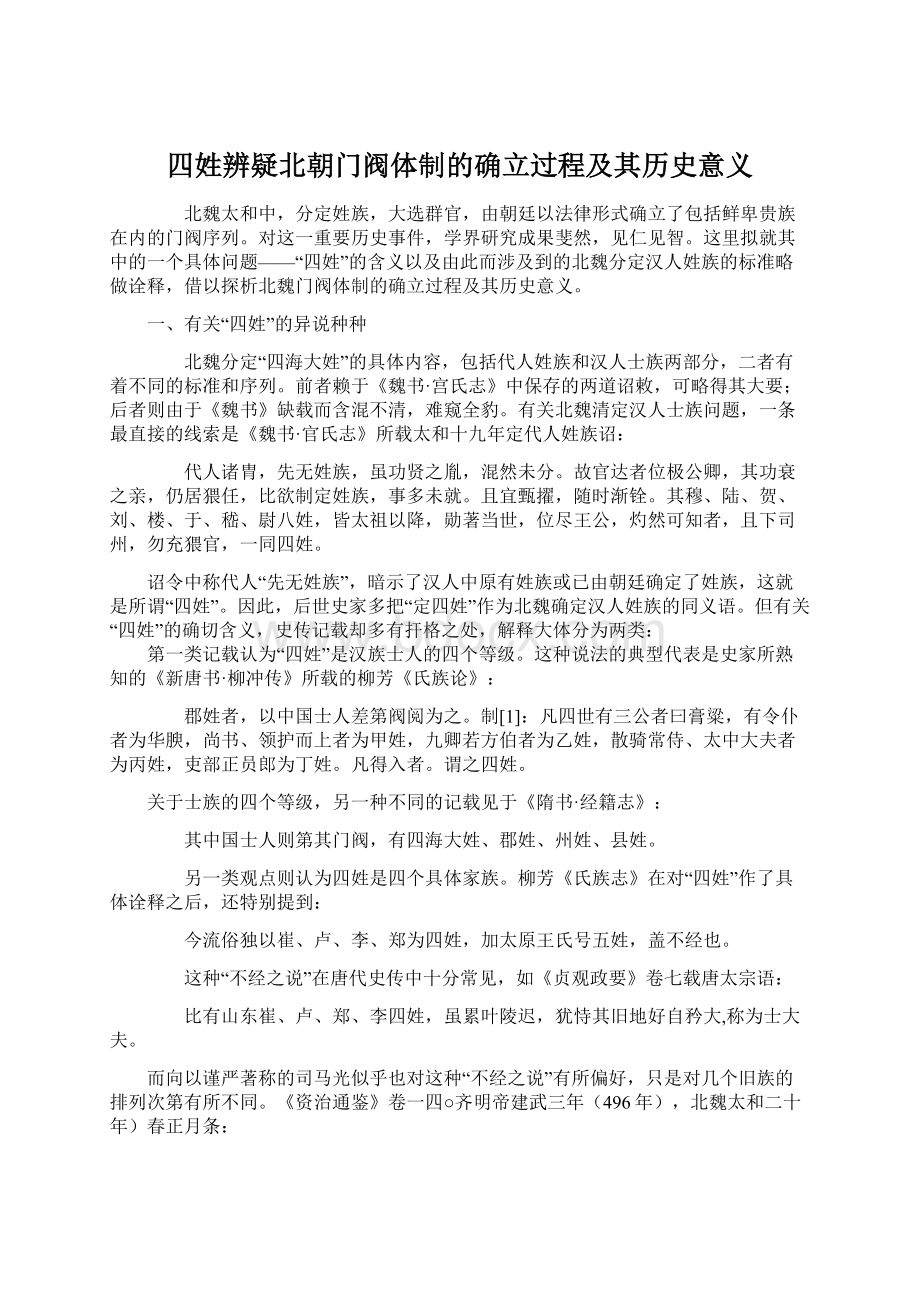
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北魏太和中,分定姓族,大选群官,由朝廷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包括鲜卑贵族在内的门阀序列。
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学界研究成果斐然,见仁见智。
这里拟就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四姓”的含义以及由此而涉及到的北魏分定汉人姓族的标准略做诠释,借以探析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一、有关“四姓”的异说种种
北魏分定“四海大姓”的具体内容,包括代人姓族和汉人士族两部分,二者有着不同的标准和序列。
前者赖于《魏书·宫氏志》中保存的两道诏敕,可略得其大要;后者则由于《魏书》缺载而含混不清,难窥全豹。
有关北魏清定汉人士族问题,一条最直接的线索是《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十九年定代人姓族诏:
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
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
且宜甄擢,随时渐铨。
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以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诏令中称代人“先无姓族”,暗示了汉人中原有姓族或已由朝廷确定了姓族,这就是所谓“四姓”。
因此,后世史家多把“定四姓”作为北魏确定汉人姓族的同义语。
但有关“四姓”的确切含义,史传记载却多有扞格之处,解释大体分为两类:
第一类记载认为“四姓”是汉族士人的四个等级。
这种说法的典型代表是史家所熟知的《新唐书·柳冲传》所载的柳芳《氏族论》:
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
制[1]:
凡四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为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
凡得入者。
谓之四姓。
关于士族的四个等级,另一种不同的记载见于《隋书·经籍志》:
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四姓是四个具体家族。
柳芳《氏族志》在对“四姓”作了具体诠释之后,还特别提到:
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
这种“不经之说”在唐代史传中十分常见,如《贞观政要》卷七载唐太宗语:
比有山东崔、卢、郑、李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而向以谨严著称的司马光似乎也对这种“不经之说”有所偏好,只是对几个旧族的排列次第有所不同。
《资治通鉴》卷一四○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年),北魏太和二十年)春正月条:
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连,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
(胡注:
四姓,卢、崔、郑、王也)……时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胜家风,故世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胡注:
卢、崔、郑、王,并赵李为五姓)。
如上所见,关于北魏“四姓”,计有二类四说,虽各有所据,却都属唐以后晚出材料。
长期以来,史家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多径取所需,未予详考。
直至唐长孺先生发表《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2]一文,才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探究:
他根据入姓入族以官爵为唯一标准为线索,推测柳芳《氏族论》所述之四姓即本太和十八年定四海士族之规定,认为汉人门阀可能也分先朝官爵和入魏后官爵,《氏族论》只保留了入魏后的官爵,而无魏晋旧籍的记载。
对于《隋书·经籍志》的歧异之处,唐先生认为柳芳所论“四姓”即为高门,亦即四海大姓、右姓。
隋志把它从郡姓中提出来,名之为“四海大姓”,但仍有非“四姓”的郡姓。
其中较高者为州姓,卑者为县姓。
唐先生的分析精辟入理,又以大量金石、文献为佐证,使北魏汉人门第这一原本模糊错乱的内容,得以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近年来,杨德炳先生和黄惠贤先生先后发表《四姓试释》和《〈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两篇重要文章,对相关资料条分缕析,极大地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3]。
唐先生的研究,统一了四姓异说中第一类两种不同说法的矛盾,对于第二类记载则没有直接涉及,只是笼统地提到唐代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家获得北朝一流高门地位即在太和之时。
那么,为什么这种“不经”的“四姓”(五姓)之说在唐代广为流布,而正宗的“四姓”之制却只有极少数谙熟谱牒的士大夫才能通晓呢?
代人先无族姓,因而分族定氏一以官爵为断;而铨定素有门第传统的汉人士族的标准,又多了一个“魏晋旧籍”。
那么入魏官爵和“魏晋旧籍”两重标准问题的矛盾如何协调统一起来呢?
除此之外,是否还包括其它一些因素?
孝文帝分定代人姓族,雷厉风行。
代人竟起辞讼,至魏末仍纷争不息[4];那么以法令的形式确定汉人姓族,同样是一桩空前的盛事,理应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和震动。
但就史传所见,北方汉族士人的反应却十分冷淡,被后人讥为高门家谱的《魏书》,甚至对此阙而不载[5];在北朝和隋唐的大量碑志中,也见不到某家族在太和中被定为某姓的任何记述,这不能不使人对这一法令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意义产生某种怀疑。
唐长孺先生曾敏锐地指出:
北魏分定姓族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种政治势力,使之成为巩固拓跋氏政权的积极因素。
新标准的精神,不妨说是传统惯例的具体化和制度化。
遵循这一思路,重新理解“四姓”的确切含义,成为认识北魏分定姓族的标准与意义的关键所在。
二、柳芳“四姓说”献疑
柳芳的《氏族论》,属于唐以后的晚出材料。
文中所提到的汉人士族以官爵划分的诸等级,与《魏书·官氏志》所载的太和职品完全相同,丝丝入扣[6],因而可以视为太和诏令的概略。
在没有新证出现的情况下,不应盲目怀疑其可靠性。
但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论,柳芳不是专论太和之制,《新唐书》所引又必多删节,那么这段话的最后两句“凡得入者,谓之四姓”,究竟是诏令的原文,还是柳芳个人的理解,就有值得探讨的余地了。
在《魏书》等有关北魏的第一手材料中,找不到把这种等级序列称为“四姓”的直接证据。
唐长孺先生所举的两条材料:
《魏书·崔玄伯附崔僧渊传》载僧渊与崔惠(慧)景书中的“料甲乙之科”和《通鉴》卷一四○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年)正月条薛宗起与孝文帝争入郡姓事,都只能理解为门第高下的一种泛指,并不能全面印证《氏族论》中的等级序列。
探讨“四姓”最直接的线索是《魏书·官氏志》所载定代人姓族诏中的“勿充猥官,一同四姓”一语,而这里的“四姓”如按柳芳的解释,语义却十分含混,前后不能贯通。
“定代人姓族诏”第一条的核心是确定鲜卑八姓,即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个“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的家族,他们在北魏王朝中的地位仅次于皇族,与汉人中的华腴、膏粱属于同一层次。
如按柳芳的解释,诏令中前一个“八姓”是指“位尽王公”,地位相互平行八个具体的代人姓族,而后文的“四姓”却又泛指官位高下有别、地位悬殊的不同品级的众多汉人士族,二者在“勿充猬官”这一点上究竟怎样等同起来呢?
在国家正式诏令中似乎不应出现这种语义不明、概念模糊的失误。
[7]
《氏族论》所载的“四姓”之制,是一个在制度上整齐划一的理想模式,而著于法令的制度与社会实际状况往往有相当距离。
太和门品之令与职品之令是相互配合,互为表里的,而北魏前期的官职却以紊乱、杂芜著称,如何把先世官爵与当朝的官品统一起来,颇费周折。
更为棘手的是,与“先无姓族”的代人不同,北方汉族士人素有自己的门第传统和习惯,这就是所谓的“魏晋旧族”。
由于长期的战乱和频繁的迁徙,许多士族谱系已无从稽考,检校“旧籍”势必引起社会的极大骚乱,而如何把“魏晋旧籍”与当世官爵统一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正因为如此,定四海士族的举措似乎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阻力。
《魏书·宋弁传》:
时大选群官,并定四海士族。
弁专叁铨量之任,事多称旨。
然好言人阴短,高门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毁之;至于旧族沦滞,人非可忌者,又申达之。
弁又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颇为时人所怨。
在这种情况下铨定士族的工作似乎没有取得多大成效,最终连专参铨量之任的宋弁自身,门户高低也难以确证。
《魏书·宋弁传》:
弁性好矜伐,自许膏腴。
高祖以郭祚魏晋名门,从容谓弁曰:
“卿固当推郭祚之门也。
”弁笑曰:
“臣家未肯推祚。
”高祖曰:
“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
”弁曰:
“臣清素自立,要尔不推。
”侍臣出后,高祖谓彭城王勰曰:
“弁人身良自不恶,乃复欲以门户自矜,殊为可怪。
”
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是雅重门族的孝文帝,还是专参铨量之任的宋弁,似乎都没有提及北魏王朝曾对士族的官爵与品第作出过十分明确和详尽的法律规定,可见这一诏令即使确曾颁布,最终也已成为一纸具文。
另据《魏书·李彪传》: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之交,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议,犹以地寒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
……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颜色,时论以此讥祚。
出身寒微的李彪,在孝文一朝虽位历显要,在旧族的心目中仍不入士流,他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为由替子求官当是援引北魏对汉人姓族的有关规定,这与代人于忠之子“援例求进”的性质相同[8]。
于忠之子最终得以顺利登朝,而李彪却“备尽辛酸”,含羞蒙辱,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说明终孝文一世,衡量汉人门第的标准主要仍是传统和习惯,而非制度或法律。
成于北齐的《魏书》中,显系伪托或被魏收怀疑为伪冒的士族,仍占有相当数量,似乎北魏王朝从来就没有象稽核代人姓族那样认真检校过汉人的旧籍。
近世出土的大量北朝碑志中,似乎也找不到某一家族在太和年间被法定为甲姓或乙姓的任何记载,这多少反映了铨定四海士族之举的实际执行效果。
也许正是出于徒具其文这一原因,如此重要的定汉人姓族诏甚至为《魏书》所忽略不载(当然,也不排除《魏书》散佚缺失这一原因)。
三.“四姓”之称的历史渊源
如上所述,柳芳《氏族论》既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又包含诸多疑点,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太和改制前后北方汉人士族门第的变化情况。
于是,重新认识北魏四姓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
在此,有必要对“四姓”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作一番历史的追溯。
“四姓”一词,始见于东汉初年。
《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九年)是岁,大有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李贤注引袁宏《汉纪》:
永平中,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经。
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号四姓小侯,置五经师。
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礼记》曰“庶方小侯”,亦其义也。
钱大昭《后汉书辨疑》卷二:
但言四姓者,特举后族耳。
所谓“四姓小侯”,意指光武帝之妻樊氏、皇后郭圣远、阴丽华,以及汉明帝之后马氏所属的四个外戚家族。
这一制度大致形成于汉明帝永平初年[9],其内容主要包括封爵、礼遇及子弟教育等方面,从表面上看,属优宠外戚之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不大。
但联系到四后的家族背景以及东汉初年的政治格局,这一制度又有某种特殊的政治意味[10]。
豪强大族是东汉政权建立的基础,南阳、颍川、河北诸豪更是统治集团的核心所在。
“四姓”诸族多非元从功臣,却在地方拥有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与西汉众多起自布衣的后妃之家迥然有别,从而使他们与帝室的联姻具备了更多的政治色彩。
正因为如此,马援以外戚不入云台二十八将而为世人所称羡,而马氏悄然得到“小侯”之封,子弟布列朝廷。
从这个意义上看,四姓之制中世袭封爵,参与朝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四姓”家族政治地位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别立学官”则使“四姓”子弟获得了与功臣子弟同等的入仕途径,是东汉王朝调整权力结构、巩固统治基础的有效手段。
明帝以后,“四姓小侯”之称屡见于东汉史传,或称为“四姓末属”,或简称为“四姓”[11]。
终东汉一世,“四姓”或“四姓小侯”都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专称。
魏晋之际,“四姓”的含义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指地方上正在逐渐形成的、获得社会普遍承认的地方大姓。
《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引《魏略·薛夏传》:
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推于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所屈。
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避,东诣京师。
《晋书·刘颂传》:
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
“雷、蒋、谷、鲁,刘最为祖。
”
《世说新语·赏誉》:
吴《四姓旧目》云:
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
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
《世说新语·赏誉》:
会稽孔沈、魏、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
《华阳国志·蜀志》:
新都县:
又有四姓,马、许、史、郑者也。
德阳县:
康、古、袁氏为四姓,大族之甲者也。
江阳县:
王、董、张、赵为四姓。
各地多以四为单位划定士望,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汉末清议兴起之后人物品评、比方的习惯有关,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汉一朝外戚尽为累世公卿的名家望族,“四姓”逐渐演化成为名家望族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汉魏以来,“四姓”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和概念,前后虽有差别,但一直是指某些具体的姓氏或家族。
考察北魏四姓问题不能不考虑这一历史传统。
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以《通鉴》为代表的另一类“四姓说”,便会发现这一“不经之论”在许多方面确有所本:
纳卢、崔、郑、李之女以充后宫,以四家为“四姓”,这一概念无论用东汉以外戚家族为“四姓”,还是魏晋间以地方名家大族为“四姓”,从哪种含义来衡量,都与传统上的习惯称谓相合。
以汉人的卢、崔、郑、王为“四姓”,与鲜卑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门第相当,地位相同。
采用这种解释,使《魏书》所载“定代人姓族诏”前后对应分明,语义豁然贯通,不象柳芳说那样牵强。
关于以“八族”同“四姓”,在《元和姓纂》卷十《一屋》中曾出现过这样的解释:
穆……代为部落大人,为北人八族之首。
后魏以穆、陆、奚、于比汉金、张、许、史。
以代人“八族”方汉朝“四姓”,解释固然欠妥,但如果理解为以代人“八族”方当朝汉人“四姓”,则于史有征。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汉安县:
四姓,程、姚、郭、石;八族:
张、季、赵、李辈。
江阳县:
四姓,王、孙、程、郭;八族:
又有赵、魏、先、周也。
《文选》卷二四陆士衡《吴趋行》:
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
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
李善注引张勃《吴录》:
八族:
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
朱、张、顾、陆也。
[12]
以“四姓”与“八族”对举,是汉魏以来人物比方的习惯,这种传统又为北魏王朝所沿袭,只不过内容变成了以汉人“四姓”与鲜卑“勋臣八姓”的对举。
《通鉴》所称孝文帝纳五姓之女以充后宫之事,无一例外地在《魏书》诸传中得到了印证,这至少说明《通鉴》所述历史事实是清晰准确的。
《通鉴》的“四姓说”在北朝史传中虽亦无明文,但仍有个别痕迹可寻。
据《朝野佥载》卷一:
后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
时四姓已定迄,故今谓之“驼李”焉。
这里的四姓,很明显不是指柳芳所说的“四姓”,否则以当时陇西李氏的政治权势和社会声望断无“恐不入”的道理,因而只能是指崔、卢、郑、王四个具体姓族。
这一传说似乎还暗示陇西李氏最初未得入“四姓”,这与《通鉴》的记载基本合拍。
北魏以后,直至唐初,传统的“四姓”概念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
《新唐书·高俭传》载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诏:
以四后姓、 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
唐代官修谱谍所列各郡士望中,以四姓所占的比例很多[13]。
这说明汉魏以来以“四姓”指代后族或地方大族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代,在北朝应不会有例外,因而《通鉴》之说基本上可以成立。
四、《通鉴》“四姓”说辨证
在确认《通鉴》“四姓说”为信史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对其所记载的史实进行重新梳理。
在《通鉴》齐明帝建武三年(496)春正月丁卯条下,记述了如下内容:
1、诏改拓跋为元氏,改鲜卑姓氏为汉姓。
2、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
3、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
4、诏宋弁定诸州士族。
5、颁代人姓族诏。
6、孝文帝诏命诸弟改纳“八族及清修之门”。
7、赵郡李氏人物尤多,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
8、蜀薛入郡姓之争。
9、孝文帝与群臣论取士标准。
凡此种种,均属“分定姓族”的具体内容,《通鉴》作者将上述诸事并入一条,意在说明“分定姓族”的前因后果,并不意味着所有史事均发生在同一时间,于是便产生了如下问题:
代人“八族”的制定与汉人“四姓”的确立是否是在同时进行的,宋弁主持制定的“诸州士族”中,是否包括了作为“四海通望”的“四姓”;“四姓”中是否包括陇西李氏,赵郡李氏与“四姓”家族是什么关系。
“代人姓族诏”中“一同四姓”一语,表明汉人“四姓”的出现早于代人“八族”,具体时间史籍无征,我们只有依据《通鉴》中“纳其女以充后宫”一语进行探寻。
《魏书·崔休传》:
高祖纳休妹为嫔,以为尚书主客郎(时在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
《魏书·卢玄附卢敏传》
高祖纳其女为嫔(时间无考)。
《魏书·郑羲传》:
文明太后为高祖纳其女为嫔,征为秘书监(时在太和十五年冯太后卒以前)。
《魏书·王慧龙附王琼传》:
太和十六年,降侯为伯。
高祖纳其女为嫔,拜前军将军,并州大中正。
由此可见,孝文帝纳“四姓”女为嫔一事,大致发生在太和十六年(492)前后,而不是在太和二十年(496)颁定代人姓族之时。
关于汉人“四姓”地位确立的另一个重要线索是孝文帝为诸弟娉“四姓”女为妃一事,《通鉴》亦将其系入齐明帝建武三年(496)春正月丁卯条中,而此事的发生远远早于这一时间。
《魏书·咸阳王禧传》
于时,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禧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
诏曰:
“……将以此年为六弟娉室。
长弟咸阳王禧可娉故颖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次弟河南王干可娉故中散代郡穆明乐女,次弟广陵王羽可娉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次弟颍川王雍可娉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懿女。
”
诏令中诸王的封号,与太和二十年的情况显然不符。
《魏书·赵郡王干传》:
太和九年,封河南王。
……迁洛,改封赵郡王。
《魏书·高阳王雍传》:
太和九年,封颍川王。
……改封高阳,奉迁七庙神主于洛阳。
《魏书·高祖纪》:
(太和十八年二月丙申)河南王干徙封赵郡,颍川王雍徙封高阳 (《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二月丙申条胡注:
将以河南颍川为畿甸,故二王徙封)。
《魏书·彭城王勰传》:
太和九年,封始平王。
……开建五等……改封彭城王。
诏令中所提及李冲当时的官位,值得特别注意,《魏书·李冲传》:
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拜廷尉卿。
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
从李冲担任廷尉卿的短暂时间推断,孝文帝为诸王娉高门女一事,当发生在太和十七年“改降五等”前后,这说明早在迁都洛阳之前,“四姓”作为北方一流高门大姓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
孝文帝汉文化修养之高,连南朝史家也无法否认[14]。
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左右近臣又多文儒之士,奏疏中曾多次援引马后、阴后之典[15]。
北魏“四姓”与东汉的“四姓小侯”有许多相似之处:
同属地方大族,同以后族称“四姓”,同是累世贵显,同与王室累世联姻。
这究竟是无意的巧合,还是“参稽古式”的结果,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
那么,陇西李氏是否列于“四姓”之中呢?
从历史的传统看,尽管“四姓”这一概念一直指称某些具体的姓氏或家族,但数目并不一定以“四”为限。
东汉四姓小侯之制并不限于樊、阴、郭、马四个家族,如秦彭于永平七年“以彭贵人兄,随四姓小侯擢为开阳城门侯”[16],桓帝建和二年“赐四姓及梁、邓小侯各有差”[17],似乎所有的外戚家族都可以援此制获得特殊的礼遇。
魏晋时期,以“四姓”相称的地方大族也不尽是“四”族。
《华阳国志·蜀志》:
德阳县:
康、古、袁氏为四姓。
成都县:
四姓,有柳、杜、张、赵、郭、杨氏。
《华阳国志·南中志》:
(诸葛亮南征,平南中四郡)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
前引诸例,或多于四,或少于四,但都被称为“四姓”,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即是“大姓”之意。
陇西李氏本属关中大族,自李宝之世才东迁入魏,其门第渊源和家世背景与崔、卢、郑、王等中原大姓有一定差别。
与后者相比,陇西李氏缺乏显赫的魏晋“世资”,但当朝的仕途官宦又较崔、卢、郑、王为优。
为弥补自身在门第上的缺陷,李冲等人利用政治上的优势,与中原大族结成了广泛的婚姻关系。
“驼李”的传说暗示出陇西李氏最初未能入选“四姓”,同时也反映了陇西李氏对“四姓”地位的渴求之态。
不久之后,在李冲的苦心经营之下,孝文帝“亦纳其女为夫人”,使这一家族最终进入了“四姓”的行列。
或许正是基于这番周折,《通鉴》记载中把陇西李氏单独排列于崔、卢、郑、王之后,并特别强调其结姻帝室的原因是“当朝贵重”和“所结姻连,莫非清望”。
问题似乎并没有就此完结,如果承认陇西李氏在“四姓”之中,那么赵郡李氏以及博陵崔氏是否也在这一行列中呢?
唐代禁婚诏中,把这两个家族与上述“五姓”同列于“七姓”当中,唐人中也有以太和中“七姓”为中原首望的说法。
《新唐书·李义府传》:
后魏太和中,定姓族七望,子孙迭为婚姻。
这种说法似乎与《通鉴》中“世言高华者,以五姓(此处当指五姓七望)为首”的记载相吻合,这样一来,太和“四姓”的实际内涵就变为“七姓”了。
稽诸史传,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两个家族与“四姓”问题都有一些若隐若现的联系。
《魏书·崔挺传》:
尚书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为嫔。
《通鉴》“四姓”文后,以赵郡李氏“人物尤多”,与崔、卢、郑、王并称“五姓”。
但孝文纳崔挺女一事不载于《通鉴》,而史集中亦不见孝文纳赵李之女,当不是编排失次的缘故。
在唐代的禁婚诏中,其他五姓的始祖都只追溯到北魏,而这两姓却一直追溯到前燕的崔懿和西晋的李楷,其中亦有原委。
如果仅以家族在北魏的官宦和宗族势力而论,两家与“四姓”的差距不大;但其历史渊源,特别是家族在魏晋时期的显赫程度,较之崔、卢、郑、王四家则等而下之,因而在士人的观念中有“博崔赵李”的贬称。
北魏铨定汉人门第的过程中,“汉魏旧籍”仍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按照这一标准,博崔、赵李最初很有可能不在四姓之内。
《魏书·高阳王雍传》:
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
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
关于博崔、赵李,还有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是《通鉴》记载中“咸纳其女以充后宫”一语,是进入“四姓”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识,但并不是唯一“标准”。
孝文帝纳高门女之事,史籍中还有一例,《魏书·韦阆附韦崇传》:
高祖纳其女为充华嫔。
由此可证,女入后宫者,并不一定就得入“四姓”;《魏书·皇后列传序》:
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
可见后宫之内也有一定的等级划分,崔挺之女与崔休之女的地位不一定相同。
关于博崔、赵李与崔、卢、郑、王“四姓”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后世进入“五姓”婚姻集团的过程,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
简言之,就实际范围和时间顺序而言,“太和四姓”的形成过程是由崔、卢、郑、王“四姓”到崔、卢、李、郑、王“五姓”,又加“博崔”、“赵李”,最终形成“五姓七望”。
综上所述,北魏太和中,对汉人姓族曾经进行过两次清定:
第一次是在太和十六年前后的“定四姓”,其目的主要是确定“四海通望”或“四海大姓”,《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后魏定氏族,佥以太原王为天下首姓,故古今时谚有“鼎盖”之名,盖谓盖海内甲族著姓也。
而北魏太和二十年的“分定姓族”,主要是确定代人姓族和汉人中的“诸州姓族”,这是作为“四海通望”的“四姓”家族的地位已经确立,因而在当时的诏令中才会出现“一同四姓”之语。
由此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