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中的女同性之爱.docx
《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中的女同性之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中的女同性之爱.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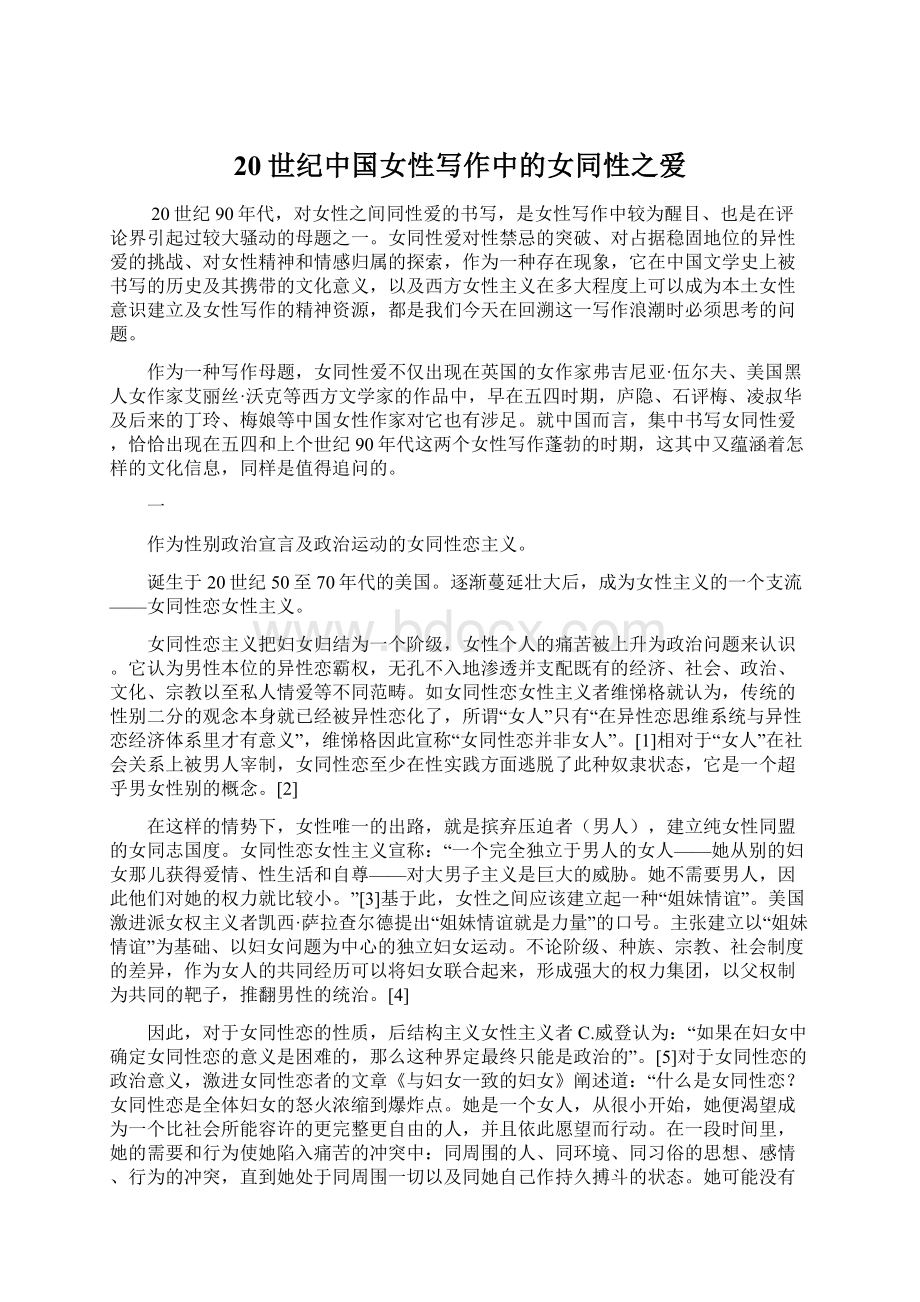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中的女同性之爱
20世纪90年代,对女性之间同性爱的书写,是女性写作中较为醒目、也是在评论界引起过较大骚动的母题之一。
女同性爱对性禁忌的突破、对占据稳固地位的异性爱的挑战、对女性精神和情感归属的探索,作为一种存在现象,它在中国文学史上被书写的历史及其携带的文化意义,以及西方女性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本土女性意识建立及女性写作的精神资源,都是我们今天在回溯这一写作浪潮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种写作母题,女同性爱不仅出现在英国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等西方文学家的作品中,早在五四时期,庐隐、石评梅、凌叔华及后来的丁玲、梅娘等中国女性作家对它也有涉足。
就中国而言,集中书写女同性爱,恰恰出现在五四和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两个女性写作蓬勃的时期,这其中又蕴涵着怎样的文化信息,同样是值得追问的。
一
作为性别政治宣言及政治运动的女同性恋主义。
诞生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
逐渐蔓延壮大后,成为女性主义的一个支流——女同性恋女性主义。
女同性恋主义把妇女归结为一个阶级,女性个人的痛苦被上升为政治问题来认识。
它认为男性本位的异性恋霸权,无孔不入地渗透并支配既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以至私人情爱等不同范畴。
如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维悌格就认为,传统的性别二分的观念本身就已经被异性恋化了,所谓“女人”只有“在异性恋思维系统与异性恋经济体系里才有意义”,维悌格因此宣称“女同性恋并非女人”。
[1]相对于“女人”在社会关系上被男人宰制,女同性恋至少在性实践方面逃脱了此种奴隶状态,它是一个超乎男女性别的概念。
[2]
在这样的情势下,女性唯一的出路,就是摈弃压迫者(男人),建立纯女性同盟的女同志国度。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宣称:
“一个完全独立于男人的女人——她从别的妇女那儿获得爱情、性生活和自尊——对大男子主义是巨大的威胁。
她不需要男人,因此他们对她的权力就比较小。
”[3]基于此,女性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姐妹情谊”。
美国激进派女权主义者凯西·萨拉查尔德提出“姐妹情谊就是力量”的口号。
主张建立以“姐妹情谊”为基础、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的独立妇女运动。
不论阶级、种族、宗教、社会制度的差异,作为女人的共同经历可以将妇女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权力集团,以父权制为共同的靶子,推翻男性的统治。
[4]
因此,对于女同性恋的性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C.威登认为:
“如果在妇女中确定女同性恋的意义是困难的,那么这种界定最终只能是政治的”。
[5]对于女同性恋的政治意义,激进女同性恋者的文章《与妇女一致的妇女》阐述道:
“什么是女同性恋?
女同性恋是全体妇女的怒火浓缩到爆炸点。
她是一个女人,从很小开始,她便渴望成为一个比社会所能容许的更完整更自由的人,并且依此愿望而行动。
在一段时间里,她的需要和行为使她陷入痛苦的冲突中:
同周围的人、同环境、同习俗的思想、感情、行为的冲突,直到她处于同周围一切以及同她自己作持久搏斗的状态。
她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她所认为的个人私事的政治含义,但是,在某种层次上她不能接受由这个社会强加给她的最基本角色——女性角色——所造成的限制和压迫。
”[6]
发表在1972年女同性恋刊物《狂怒》上的文章,阐述了作为反抗男权中心策略的“与妇女一致的妇女”,其目的是:
“致力于从其他妇女那儿寻求政治、感情、身体和经济上的支持……这不仅是取代压迫性的男女关系的一种选择,更主要的是她爱妇女。
……女同性恋者认识到,把爱情和支持给予男子而不给妇女,实际上巩固了那个压迫她的制度。
”[7]
“女性同性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把女性角色局限于消极、伪善和采取间接行动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男性性欲的野蛮性和机械性的一种摒弃。
”[8]将女同性恋视为追求目标,和将异性恋主义视为摈斥对象,表达了同样的政治意义:
反对菲勒斯专制,改变女性在社会文化和生活中的“第二性”处境。
同时,女同性恋也是建构女性自我、继而实现性别平等的途径。
“必须创造一个只有透过女性互相建立才能实现的自我观。
此身份只能由自我建立,不可依靠男人……我们的精力能量必须流向姐妹,不可倒转给我们的压迫者……女人彼此联系并创造女人新意识,这是解放女人的关键,也是文化革命的基础。
”[9]
女性同性恋被认为是女性在同性中寻找中心的尝试,它不同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性选择的男同性恋,它是对传统秩序的批判,因而它首先是一种反抗父权制(patriarchy)的女性主义立场。
美国女性主义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Rich)在1978年发表的《强迫的异性爱和女同性恋的存在》里说:
“我说的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是指一个贯穿每个妇女的生活、贯穿整个历史的女性生活范畴,而不是简单地指一名妇女与另一名妇女有性的体验或自觉地希望跟她有性往来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扩展其含义,包括更多形式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部的原有的强烈感情,如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结合起来反抗男性暴力,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反对男人侵占女人的权力。
”[10]她用“女同性恋连续统一体”(Lesbiancontinuum)这个概念,使女同性恋成为贯穿于妇女生活始终和整个妇女历史的一种反抗性生活方式,它不专指女性间的性关系。
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打破禁忌、反抗父权制和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它提倡的“姐妹情谊”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性别压迫下女性的悲凉,也为抗衡男权世界的女性提供了有限的精神援助,因而成为女性主义写作策略之一。
女同性爱,不再是传统眼里的“邪恶”(sin)与“病态”(sickness)。
事实上,早在西方女性主义前驱伍尔夫那里,女同性恋就被反复书写过。
1913年完成、1915年出版的《启航》里,女主角瑞奇""温里斯对男性世界的暴力与歧视感到恐惧、厌恶。
她的同性恋倾向,显示了女性的独立与自我盈足。
她的死,象征了女性自我追求的夭折。
1925年出版的《达罗卫夫人》中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与女友萨莉·赛顿、1927年出版的《到灯塔去》里的拉姆齐夫人和女画家莉莉·布里斯科之间,都存在着同性爱。
女性之间因为精神相通而产生的同性爱,与作品表现出的对婚姻的恐惧形成鲜明对比。
小说中贯穿着的有关异性爱与婚姻缺陷的声音,是作者内心焦虑的写照。
1928年,英国女作家拉德克利芙·霍尔发表的《孤独的井》,因为展露了“妇女对妇女的爱的真相”,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11]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1973年发表的《苏拉》,描写了苏拉和内尔之间炽热的同性情谊。
在艾丽丝"沃克(AliceWalker)的《紫色》里,受尽男性摧残的女主人公黑人西利亚,是在另一名黑人妇女萨格那里,才体验到人间温情和爱情,并产生了反抗男人的觉悟和勇气。
女作家对女性同性恋问题的书写,引起了美国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注意。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者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Smith)在其《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中,追溯了黑人女作家对女同性爱的书写传统。
邦尼·齐默尔曼(BonnieZimmerman)的《前所未有:
女性同性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面面观》(WhatHasNeverBeen:
AnOverviewofLesbianFeministLiteraryCriticism),是女同性爱书写在文学批评界的回应。
至20世纪70年代,“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Lesbian-feministliterarycriticism)理论得以建立,文学中对女同性爱这一题材的表现也成为自觉。
文学创作与批评和实践领域的女同性恋运动相互激荡,女同性恋运动作为激进女权主义的一支,在西方社会迅速蔓延起来。
二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其论文《作为妇女的阅读》中指出,在菲勒斯中心主义影响下的“男性批评家们把女性之间的关系看作是邪恶和不自然的”,对这种关系,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女人的团结威胁着男性统治和男性特征”。
[12]
在中国文学史上男性叙事者那里,女性之间的情谊被悬置。
“在男性历史(history-hisstory)沉迷于编织‘英雄惜英雄’的男性神话的同时,女性却一再地被书写为互相妒忌和排斥的分裂群体,以使她完成被要求和限定了的‘镜子’作用——‘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
’——反照出男性的宽阔胸襟和非凡力量。
……女性之间呈现出来的,是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互相提防,彼此算计,‘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历代文人更是大肆渲染后宫之争(这种津津乐道多少带点阴暗心理);直到《金瓶梅》,可谓登峰造极:
众多女性为获得一个男人的欢心,用尽心机,争得你死我活,结果两败俱伤,还蒙上了淫荡下贱的罪名,受人唾骂——这样一则男性叙事文本,居高临下,嘲讽女性的咎由自取。
各类报纸、小说、传记等似乎也在反复印证和加深这种印象:
‘女人对女人是很严酷的,女人不喜欢女人。
”[13]几千年文学史上可供记载的女作家寥若星辰,即便是在她们笔下,女人之间的同性爱也绝少被提及。
20世纪初,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女性作家群,具有描写性别意识的女性书写因此产生。
在五四时期,女性与子一辈的男性结为同盟,一起摈弃和颠覆封建礼教,做封建“礼教的叛徒”。
恋爱婚姻自由是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基本。
对女作家而言,历史的局限,使她们一时还不可能获得更多寄托自己才情和自由的空间,恋爱婚姻自由就成为她们最近(一定意义上也是最远)的反抗地。
因此,五四女作家多把笔墨集中在婚恋领域。
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不可能是象牙塔,历史文化在这里有太多的沉淀。
从“父”之家逃离和叛逆出来的“娜拉”很快发现,获得了恋爱自由的她,进入的是又一个写满男权中心陋习的“夫”的家。
原本和她们并列一行反抗父权和礼教的异性伴侣,其自身携带着父权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遗传密码,“他”成为“娜拉”精神痛苦的渊薮。
对异性爱失望甚至绝望后,一些女性作家将女同性爱作为自己漂泊灵魂的寄居地。
因为,“女同性爱的存在包括打破禁忌和反对强迫的生活方式,它还直接或间接地反对男人侵占女人的权力。
”[14]尽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姐妹情谊’,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逃离,是女性对自我尊严和独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守护,也是觉醒了的性爱要求的替代,尽管这种逃离和守护是短暂的,这种替代是残缺的和脆弱的。
”[15]但在无路可走时,逃向女同性爱,在同性那里寻求精神援助,遂成了自我放逐、失去家园的女性可以就近获得的庇荫。
现代文学史上的庐隐、石评梅、凌叔华、丁玲、梅娘等现代女作家对女同性爱都有表现。
对它的书写统一在一个主题之下:
对男性权威和以此为基石构成的女性处境的回避。
庐隐堪称中国文学史上较早致力于女性写作的作家,在其代表作《海滨故人》中,弥漫着浓浓的同性情谊,“海滨故人”是一群女同性爱的崇信者。
庐隐希望通过建立“女儿国”、“姐妹邦”来对抗人间束缚,拯救异性爱带来的伤害。
然而这只是乌托邦的假想,脆弱而虚幻,“海滨故人”后来纷纷陷入异性爱的旋涡。
《丽石的日记》记述了丽石与沅青之间的相互依恋,丽石宣称:
“我从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因为和他们的交接总觉得不自由。
沅青她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
”
“一个女儿国的理想,最多也只是对封建秩序的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不可能构成否定与摧毁性的力量。
”[16]在传统文化有着超稳固结构的中国,坚如磐石的异性爱对同性爱有坚壁清野的占领力和摧解力。
起先,沅青对丽石的爱有过回应,后来还是畏于社会舆论退缩了。
她被迫听从父母之命远嫁,丽石最终以身殉爱。
与庐隐有着深厚“姐妹情谊”的石评梅,也钟情于对女同性爱的表现。
《惆怅》采用独白的调子抒写了女性间的柔情,展现了一个年轻女性对另一个女人的情欲,没有结果的收尾意味深长。
其它如《漱玉》、《玉薇》等作品,也涉及到这一主题。
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写了女校里的两个女性——云罗与影曼,因为演出《罗米欧与朱丽叶》产生了爱情。
云罗的哥哥要她嫁给他的科长,她和影曼则结成同盟,反抗母亲、兄弟包办婚姻。
然而,云罗后来还是顶不住压力出嫁了,她试图依赖的同性之爱的大厦,也随之哗然倒塌。
有意味的是作者在这里对叙述空间,即人物生活的环境背景的建构。
在这所女校里,普遍存在着同性情谊,她们手拉手、肩并肩地学习生活。
大家对云罗与影曼的恋情也不以为怪。
甚至她们在校园散步时,同学们看见了,还含笑为她们让道。
这里仿佛是女同性恋提倡者所谓的“女同志国度”,是外面充满性别歧视和压迫世界的对比。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者把同性情谊安排在相对独立、逼仄的空间,也反映了女儿社会天空的低矮和有限。
其它一些反映女同性爱的作品,其叙事空间也相对封闭,对此都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丁玲的《岁暮》写了两个知识女性之间的友谊,因为一方有了男友而产生纠葛。
《暑假中》描写的同性爱,产生于隔绝状态,是环境压抑的产物。
它是为了摆脱孤独而产生的,它的存在又将人物推向了更孤独的境地,因为这是没有合理土壤的感情。
丁玲藉女校女子间近乎“游戏”的同性爱,实质表现了一群知识女性对爱情的向往,以及爱情匮乏在她们心理上投下的暗影。
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北平沦陷区文坛上的梅娘,12岁在女校住读时,“在那些大姐姐的关心和爱护下,我的寒冷的小心灵苏生过来,我知道了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浓厚的感情,我的小脸上开始有了笑意。
甚至礼拜日我都不愿意回家去。
”[17]幼年时代的生命亲历及其烙印在梅娘心中对女性悲凉命运的创伤性记忆,或许正是她推重女性之间情谊的原因之一。
面对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社会,她主张女性之间建立同盟,以抗衡力量强大的男性社会。
《动手术之前》中的女主人公宣称:
“我要联合一切不幸的女人来和你们男人格斗。
”《蟹》里的贵族女儿玲玲和家佣的女儿小翠之间超越阶层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性别命运的基础上。
《蚌》里的梅丽、雯姐、秀文、贞、兰,有着相似的感情困惑和伤害,她们在一起互相安慰,排解心里的郁闷。
“我们有一个能感到苦闷的心,若是所有的女人都感到这样苦闷,那我们就有救了”。
梅丽把女性处境的改良,寄希望于女性的集体觉醒和反抗。
她想,她要做出点什么来的,使“身边的女人们明白,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联合起来才能自救。
”在《小妇人》(未完成,1944年)里,当凤凰陷入恋人袁良情感背叛的痛苦时,是情同姐妹的李莹给了她许多抚慰。
如同其她一些女作家一样,在感受到男性中心社会强大与坚硬的内核时,梅娘以“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浓厚的感情”,揭示了存在于妇女生活中的不幸和人世的不平,进而把关注的眼神,延伸到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关心与爱护上。
[18]对女性情谊的倚重和呼吁,袒露了作家对女性获得社会权力途径的理性思考。
正像里奇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现代女作家在书写女同性爱时,性的需要和身体行为是微乎其微的。
女同性爱者与男同性恋者不同,她们彼此之间的精神支持和情感需求越过了身体需求。
或许对于这些筚路蓝缕开拓新的书写领域的女作家而言,传统惯性所形成的性禁忌是坚固的。
因此,现代文学史上,女性写作对女同性爱者美丽的身体虽有涉笔和唯美展现,但其身体萌动却被有意无意地删减了。
祛除了身体欲望的表现,女作家专力于书写女性之间的精神契合。
“对女伴身体美与精神美的发现与欣赏,实际上是自我发现自我欣赏的一面反光镜,女人们在这种相互发现与相互欣赏中共享美的愉悦,分享自恋与互恋的乐趣。
她们以这种同性结盟的方式筑起一道防范、回避异性侵入、伤害的围墙,一个精神的和审美的‘女儿国’。
这种现象本身,就已经折射出封建父权制婚姻的先天性缺陷,折射出被终身围困其中的男人和女人都是不幸福的和快乐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距离平等的、自然的、和谐的人的关系还相当遥远。
”[19]
三
与上半个世纪相比,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女作家对女同性爱的书写更加普遍,姿态更加大胆。
她们以女同性爱反抗男性中心社会的态度更加激进,对女同性爱可能走向的探索也趋向多维。
张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女性意识觉醒比较早的一位作家。
和其她同时代女作家相似,她也是在对社会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夹缝里植入其女性话语的。
《爱,是不能忘记的》尽管在当时引起了评论界的哗然惊叹,但其性别意识并不显彰。
对钟雨和恋人之间刻骨铭心爱情的禁欲表现,反射了作者对两性情感理解上的偏失。
从对钟雨柏拉图式的爱情的礼赞里,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两性爱情的温馨理解。
到了《方舟》中,张洁开始揭开异性爱的温情面纱,暴露了两性关系中女性举步维艰的情感困境。
与早期创作比,《方舟》的叙述声音是“激忿的、撕破的、外扬的、反叛的、犀利的也是凄厉的,是发自心底的也是与自身生命处境紧密相连的。
”[20]罹受着来自异性情感折磨的三个女性,组成了一个女性联盟,互相鼓励互相扶助,共同抵御外界流言的侵袭。
以女同性爱为女性苦难的救赎之径和庇护之所,是小说标题“方舟”象征意义之所在。
然而,张洁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作为主流的异性爱。
三个女性的愤激和失望,均源自于理想异性爱的阙如。
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自己的天空》放逐了男性和对异性爱的执守。
“昔日女性意义归宿的异性爱降平为女性自我选择对象物,曾是女性意义盲区的同性爱升起了女性自我认同价值标向。
以对于传统文学异性爱话语的消解式避弃,刘西鸿以轻松自如的女同性爱话语扰乱了父权社会那最蛊惑人心的悬置的虚拟,从而使男性权威消失神光而形同虚设。
”[21]刘西鸿潇洒地放开了曾经紧紧牵着男性的那只手,“颠覆了女性以男性中心价值归属的传统爱情神话——异性爱梦想本体。
”[22]“神女峰”的传说、“过尽千帆皆不是”的词句铸造的传统女性,她们的不幸,正来自于她们苦苦等候的男性。
她们被教化为把爱情婚姻、男子看作自己的终身归属,结果却发现,她们进入的是没有天日的深井。
异性爱的谎言和实质,被“巫女”犀利的目光看穿。
在刘西鸿笔下,由于女性之间同性爱的建立,对异性爱的失望得到稀释。
到了更年轻一代的女作家这里,发生了更剧烈的变化。
女同性爱在陈染那里被多次书写,她认为:
“女人之间的沟通,比起与男人的沟通障碍要小一些,她们的性别立场、角度以及思维方式、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更为贴近。
”[23]
《与往事干杯》是“我”写给女友乔琳的信。
乔琳是“我”的挚友,也是“我”的故事的读者和倾诉对象。
这种结构,使陈染的故事成为同性间亲密而抒情的私语,也是一份“无处告白”的自我剖析。
《空心人的诞生》里,女主人公不堪丈夫的虐待,带着孩子出走。
在独居生活中,与同在镇政府做播音员的女同事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同性间的温情缓释了噩梦般的异性压迫。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写了黛二与伊堕人之间的同性精神爱。
伊堕人对黛二说:
“没有男人肯于要你,因为你的内心与我一样,同他们一样强大有力,他们恐惧我们,避之惟恐不及。
若我们不在一起,你将永远孤独,你的心将永无对手……”。
洞穿了深存于男子内心和男权文化深处的“厌女症”(misogyny),女人开始建立面向女性的同盟。
《破开》里的“我”和殒楠紧紧依偎。
“我”觉得女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生命力潜能”,它被荒废了。
梦中的老女人(殒楠死去的母亲)预言般地宣称:
“你们要齐心协力对付这个世界,像姐妹一样亲密,像嘴唇和牙齿,头发和梳子,像鞋子与脚,枪膛与子弹。
因为只有女人最懂得女人,最怜惜女人……”她交给“我”那串有象征意味的珠子是女人之间一脉相传的某种精神牵系、是女性集合的隐喻表达。
“谨给女人”题记,标示着陈染在《破开》中试图将男权文化与她意欲建构的女性文化“破开”为二的理念:
“将男人和女人这一半与另一半合成的一个整体破开”,“女人和女人的相依相亲和‘抱成团’”[24]才能实现。
或许正是有感于广泛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的“性沟”,陈染慨叹:
“如果繁衍不是人类结合的唯一目的,亚当也许会觉得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更容易沟通和默契,夏娃也许会觉得与她的姐妹们在一起更能相互体贴理解。
人类的第一个早晨倘若是这种排除功利目的开端,那么沿袭到今天的世界将是另外一番样子”。
在为同性爱辩护时,叙述主体克服了文明对同性爱的禁忌和罪恶感,认同了同性间的亲密关系:
“我不再在乎男女性别,不在乎身处‘少数’,而且并不认为‘异常’。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它其实也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力潜能。
”
陈染对同性爱的认同里,也有对人与人之间隔绝与孤独状态的克服。
在人类——男性和女性反抗孤独的同一命题下,陈染认同了这种关系。
既然两性之间由性别及性别文化造成的“性沟”难以填补,相同的生活境遇便成为同性之间情感沟通的现实基础。
不同于新时期之初张洁笔下温馨中透着凄凉的“姐妹情谊”,也不同于世纪之初庐隐笔下仅仅指涉精神支撑的女同性爱。
世纪末的女作家从西方女性主义那里获得理论支持,借着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多元化带来的文化空隙和话语自由,她们对女同性爱的表现是自觉的、也是多侧面的。
在前辈作家那里空缺了的身体及其隐约的欲望,被她们坦然推出。
徐小斌《羽蛇》(《花城》1998年第5期)里的金乌是羽钟爱的大朋友,羽和金乌在布满鲜花的浴池里相互抚摩,彼此欣赏。
如诗如画的场面,是对女性之间情谊和身体愉悦的审美化描写。
陈染在《私人生活》里,表现了倪拗拗和禾寡妇身体的亲吻和触摸。
在林白《回廊之椅》里,朱凉和七叶主仆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及她们相互欣赏对方身体的情景,被作者以充满诗意的笔触细致写出。
《瓶中之水》中,二帕和意萍两个女性之间的情谊美伦美焕,她们彼此依恋,一种不能抑制的激情在她们之间蔓延着。
“很难想象有哪两个女人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这使我们很容易想到某个在西方通行的合法的词汇”——闪烁其词中,作者林白有些急迫地提示读者她们之间的关系。
只有在强大了自己内心力量、克服了对禁忌的罪恶感后,女作家才可能对女人之间的爱抚和欲望作如此放逸的描写。
在评论勃兴于台湾20世纪90年代女同性恋小说创作现象时,梅家玲指出,对女同性恋的描写,体现的“不只是性倾向身份与性别认同之间的多元衍异;更是在直接或间接批判主流体制的同时,意图开发新生的情欲空间,为多样化的性别论述,寻求各种可能出路。
”[25]这个评论可以移植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女同性爱书写。
世纪初到世纪末,女作家对这一题材表现内容和层次的变化,不仅折射出了文学环境的改变,更泄露了女性在性别关系认识上的辗转变迁。
论及女作家对女同性爱的描写,盛英感慨:
“基于文化、生理缘由,她们的同性恋倾向属西方女权主义所讲的:
是对女性生命力的一种呼唤,对女性性权利的一种自由选择。
我想,陈染等对女同性恋形象的塑造,确实呈露了某些现代女性心灵的秘史,具一定社会学和美学意义,不必予以非议”。
[26]
张扬女同性爱在建构女性主体方面积极意义的同时,女作家没有回避对它的局限的勘探。
“一些描写女性同性恋的作品,也总是以女人的相依相恋开始,而以相恨相斥告终。
这类作品在呈现女人们微妙心路和深层对其进行测定,因而它们颇具文化意味而催人思索”。
[27]在陈染的《饥饿的口袋》里,麦弋与“密不可分的心灵伙伴”意馨最终还是分手了,原因是意馨隐瞒真情,弃麦弋而去,选择了前夫。
麦弋“对男人失望的同时,对女人也感到失望”。
《破开》里那串有象征意义的石珠最终还是断裂开来,滚落了一地。
这既是女性实现自我解放道路艰巨曲折的预言,也是对女人同盟脆弱性的写照。
“瓶中之水”也许是女性情谊的象喻:
纯洁晶莹,又因为缺少坚实的护卫随时面临流溢四散的结局。
“女人与女人之间总是因为社会角色,包括地位、身份、名声的悬殊而彼此拉远距离;女人与女人之间还会因为女人自我心理、气度、才智的偏狭而彼此轻视。
新时期女性文学这种人性的探索和测量,无疑为女性文化建设孕育着新的生机”。
[28]当代女作家在对女同性爱可能与局限的表现中,表达了这样的思考:
女性情谊的联结纽带是什么,它的牢靠性和边界在哪里?
这些疑问,显示了她们在女同性爱认识上的理性心态。
在当代众多表现女同性爱的作品中,王安忆创作于80年代末的《弟兄们》值得特别一提。
小说记叙了单身宿舍里三位女子之间的情谊。
她们年纪都不小了,但相互之间难舍难分。
对于感情的出路,她们怀着美好的想象,希望在未来的岁月中,她们的友谊能像男人间的兄弟情谊那样绵长。
然而女人之间的关系经过生存的不断耗损,在母性和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