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docx
《女性写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女性写作.docx(3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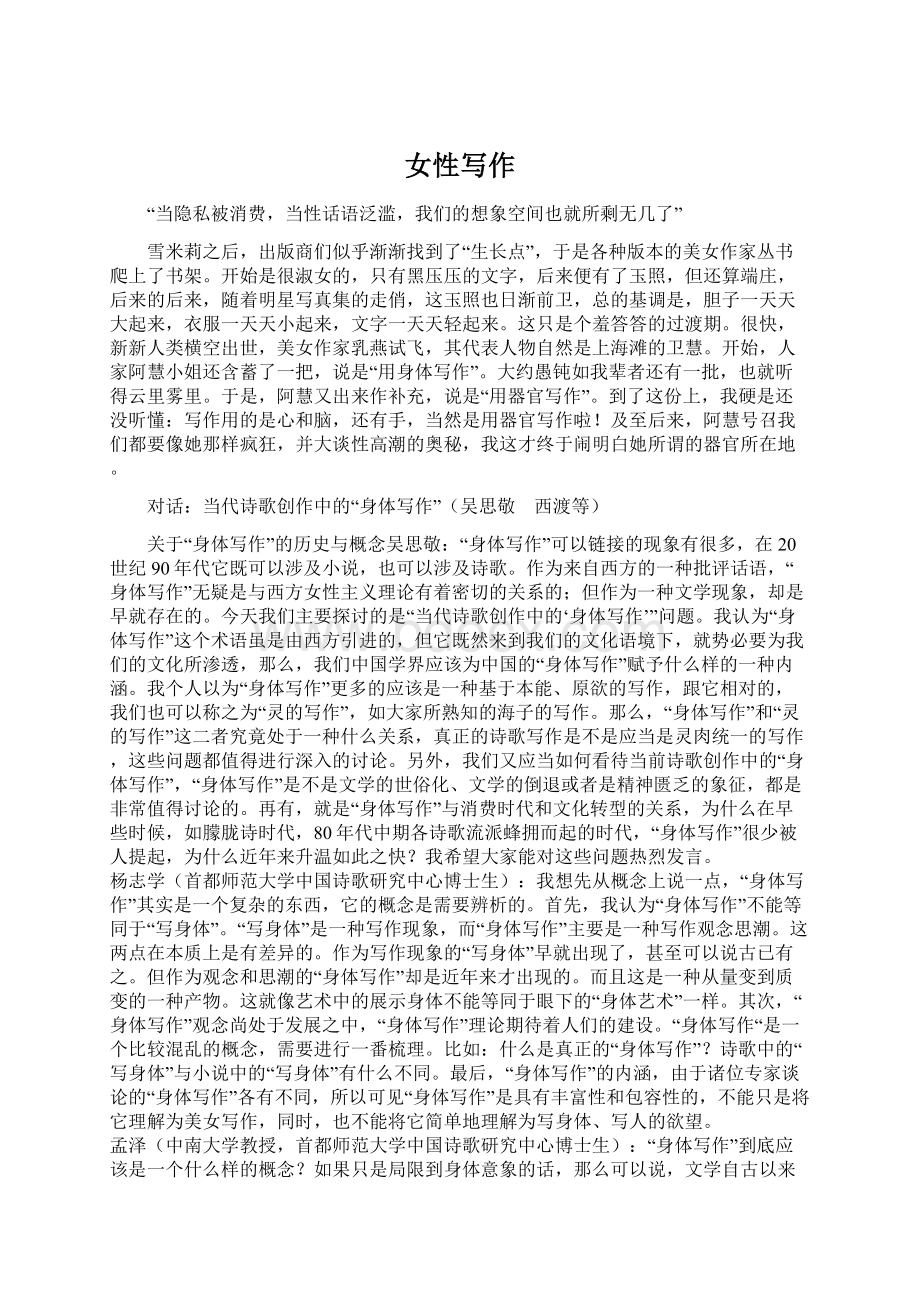
女性写作
“当隐私被消费,当性话语泛滥,我们的想象空间也就所剩无几了”
雪米莉之后,出版商们似乎渐渐找到了“生长点”,于是各种版本的美女作家丛书爬上了书架。
开始是很淑女的,只有黑压压的文字,后来便有了玉照,但还算端庄,后来的后来,随着明星写真集的走俏,这玉照也日渐前卫,总的基调是,胆子一天天大起来,衣服一天天小起来,文字一天天轻起来。
这只是个羞答答的过渡期。
很快,新新人类横空出世,美女作家乳燕试飞,其代表人物自然是上海滩的卫慧。
开始,人家阿慧小姐还含蓄了一把,说是“用身体写作”。
大约愚钝如我辈者还有一批,也就听得云里雾里。
于是,阿慧又出来作补充,说是“用器官写作”。
到了这份上,我硬是还没听懂:
写作用的是心和脑,还有手,当然是用器官写作啦!
及至后来,阿慧号召我们都要像她那样疯狂,并大谈性高潮的奥秘,我这才终于闹明白她所谓的器官所在地。
对话:
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吴思敬 西渡等)
关于“身体写作”的历史与概念吴思敬:
“身体写作”可以链接的现象有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它既可以涉及小说,也可以涉及诗歌。
作为来自西方的一种批评话语,“身体写作”无疑是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却是早就存在的。
今天我们主要探讨的是“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问题。
我认为“身体写作”这个术语虽是由西方引进的,但它既然来到我们的文化语境下,就势必要为我们的文化所渗透,那么,我们中国学界应该为中国的“身体写作”赋予什么样的一种内涵。
我个人以为“身体写作”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基于本能、原欲的写作,跟它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灵的写作”,如大家所熟知的海子的写作。
那么,“身体写作”和“灵的写作”这二者究竟处于一种什么关系,真正的诗歌写作是不是应当是灵肉统一的写作,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的讨论。
另外,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当前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身体写作”是不是文学的世俗化、文学的倒退或者是精神匮乏的象征,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再有,就是“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和文化转型的关系,为什么在早些时候,如朦胧诗时代,80年代中期各诗歌流派蜂拥而起的时代,“身体写作”很少被人提起,为什么近年来升温如此之快?
我希望大家能对这些问题热烈发言。
杨志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
我想先从概念上说一点,“身体写作”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它的概念是需要辨析的。
首先,我认为“身体写作”不能等同于“写身体”。
“写身体”是一种写作现象,而“身体写作”主要是一种写作观念思潮。
这两点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
作为写作现象的“写身体”早就出现了,甚至可以说古已有之。
但作为观念和思潮的“身体写作”却是近年来才出现的。
而且这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一种产物。
这就像艺术中的展示身体不能等同于眼下的“身体艺术”一样。
其次,“身体写作”观念尚处于发展之中,“身体写作”理论期待着人们的建设。
“身体写作“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概念,需要进行一番梳理。
比如:
什么是真正的“身体写作”?
诗歌中的“写身体”与小说中的“写身体”有什么不同。
最后,“身体写作”的内涵,由于诸位专家谈论的“身体写作”各有不同,所以可见“身体写作”是具有丰富性和包容性的,不能只是将它理解为美女写作,同时,也不能将它简单地理解为写身体、写人的欲望。
孟泽(中南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
“身体写作”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如果只是局限到身体意象的话,那么可以说,文学自古以来就没有离开过身体,这一点即使在原始艺术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关于身体感受的正面描述在宋朝以后似乎是越来越缺乏的。
废名曾经说过,中国人对于身体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写不好。
他认为中国人对于身体或性只有两种态度,要么是下流,要么是正经。
我个人感觉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人在描述身体的时候还一直在这个范围里打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身体写作”无论达到什么程度,只要保证一定的界限如不下流,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身体写作”是不是就是女性写作,现在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起来,女性在文学中越来越活跃,大致在90年代以后,“身体写作”就一直是由女性在踏“雷区”。
但这是否就是女性写作要等同于“身体写作”的一个前提,这个问题无疑是值得商讨的。
徐虹(中国美术馆理论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由于我主要是搞美术批评的,所以我只想就美术界的一些现象来谈论这个问题。
在美术界里,“身体写作”这个词汇也有所出现,而且往往在批评女性艺术家的时候更会多次出现。
但在美术界更多是强调生理意义上的,不是写作。
当然这又往往与许多批评家特别是男性批评家不理解女性作品进而发展到结论武断有关。
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懂得一点美术史的人都知道,无论在中西方用身体作为载体来表达女性情态的作品是非常多的,古希腊的许多作品都清楚地表现了这种现象。
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传统艺术中,描绘身体的权力都在男性的手中,这一点在历史流传下来的著名作品中都十分清楚地得到了表现。
这里,我们应该感谢西方女性主义者以身体作为载体表达思想意识的视角和方式,因为在某种层面上她们的努力使我们扭转了以往女性身体只能作为欲望对象的传统。
同时,我们在这种比较中也充分看到了“身体写作”在当代的意义。
从古代希腊描绘女性裸体的雕像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
男性在其中所体现的观念就是男性是英雄,即使他们在痛苦之中;而女性作为一种等待救赎的对象,是男性渴望征服的,或者是母亲形象,或者是大地母神的形象。
我曾对女性画家和男性画家描写裸体的作品进行过比较,女性艺术家在这个时候所描绘的总不是按照男性的标准进行的。
女性在描绘菩萨形象的时候,总是把她当成救苦救难的形象来描绘的,她们希望得到圣洁,得到不为男性和社会所污染的境地,这一点与男性往往将菩萨作为母亲的形象有所不同。
联系西方的绘画,我认为,“身体写作”在中国男性与女性之间是有区别的。
对于“身体写作”,我们不能轻易排斥它们,关键看里面隐含着什么,它对人类发展和社会平等到底带来了什么,只有到具体作品具体分析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明它们的意义何在。
吴思敬:
徐虹老师从当代美术学的范畴为我们解说了“身体写作”,这对我们了解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写作”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徐虹还写过一篇论文,题为《我的感觉、我的身体、我的方式———解读20世纪90年代女性艺术》,里面涉及她今天所讲的观点,还附有若干幅作品的照片,发表在《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大家可以参看。
王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后):
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诗歌中的“身体写作”与小说的是不一样的。
小说可以通过商业行为如封皮包装等使自己的创作成为“卖点”,但诗歌不能。
写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挣钱的。
小说文体与诗歌文体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决定了诗歌与小说中的“身体写作”是不同的。
“身体写作”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观念,这里含有的问题是非常多的。
我个人认为诗歌中的“身体写作”应当是近期出现的、对欲望过分专注的一种写作。
“身体写作”的最终浮出历史的地表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它的出现对我们的诗歌写作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不是什么新的崛起。
但我们在看待他们的时候应当客观公正,不要先入为主。
这种写作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会越来越多,但我不希望它大规模的发展,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它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身体写作”与当代诗歌的问题张立群(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
“身体写作”或“躯体写作”是90年代以来批评界对“女性写作”的一种特殊提法,其中又交叉涵盖诗歌、小说等多种文本写作上的种种理解以及诸多歧义。
当然,如果只是就字面理解的话,那么古今中外作品中具有描写身体的场景是不乏可陈的。
但作为一种理论术语,它最早却是来自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特别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如西苏、伊利格瑞等的一些理论文章。
之所以使用“身体写作”对90年代许多文学现象进行批评主要是与其传入的时间有关。
当然,这里也不能完全排除我们一些学者误读的因素。
我个人以为,“身体写作”虽然就其来源来看,它是西方的术语,但它一旦进入中国之后,就势必要逐渐成为一种“中国话语场”内的东西。
关于西方女性与中国女性在各自生存状况上存有差异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中国女性诗歌来说,虽然没有西方女性诗歌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容易导致对虚假的封建文化传统的麻木和认同,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女性不会为生存、选举等权利担忧乃至斗争的现实生活境遇,也常常使中国女性诗人又多了一份坦然的心态,她们可以从容地面对世界、走进诗歌,而不像许多西方女诗人那样时时不忘女权,以至丢掉了作为女性的更宽阔的主体意识。
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身体写作”这个词汇来对中国的诗歌写作特别是女性诗歌写作进行批评,但完全采取西方的视角则势必会产生偏差。
同时,就新时期以来诗歌写作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单把“身体写作”放在女性诗歌写作也未免显得视野狭窄。
当然,“身体写作”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对于“文革”那种将个人的身体压制成群体符号式的公众身体来说,“身体写作”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80年代中期,虽然“身体写作”这个词语我们许多人还并未知晓,但像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的一些作品如《女人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的部分以及《黑色沙漠》等却都是可以用“身体写作”来进行考察的。
进入90年代以来,当这些女性诗人改变策略之后,即逐步走向“超性别意识”之后,由于一些男性作家提出的“下半身”又在世纪末出现了。
如果将从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人的写作到世纪末部分男性诗人的创作联系起来的话,我们是否得到这样的结论:
第一,“身体写作”的概念需要我们重新去界定;第二,在“身体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无法排除类似关于市场、权利、反叛等种种逻辑,那么,我们是否不必轻易下结论,而只是仔细梳理这种现象,并努力将这些现象说明,进而上升为理论话语特别是诗学理论话语;第三,是应该解决好“身体写作”与灵魂牵手的问题。
霍俊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
我觉得今天的讨论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身体性”和“下半身”之间,或者说和简单的“肉体”应当区别开来。
记得梅洛·庞蒂曾经说过一句话:
“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
”身体不单是一个个体的问题,它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觉得在中国20世纪由于长期重视一种简单的形而上甚至是宗教教义式的行为倾向,已经将身体符号化了,因此,我们可以谈论身体就变成了一件很有意义,同时也是很困惑的一个问题。
身体其实并非简单赋予一种肉体的快感,它与社会、与文化都是分不开的。
诗歌中的“身体写作”和简单地以“下半身”为代表的诗歌写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把身体分为五种类型:
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只有最后一个即当身体作为生理学或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的时候,才是最低级的一个层次,“下半身”往往只关注最后一个层次,因而其创作和理论往往会误导许多读者。
我觉得,新时期诗歌中的“身体写作”并不是起源于“下半身”,也不是起源于80年代的一些女性诗人,早在诗歌的“白洋淀”时期,芒克、多多等就已经开始了身体中的书写。
当然,“身体写作”出现的意义是明显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身体性写作突破了诗歌素材“洁癖”神话,对长期的禁忌进行了可贵的消解和规避,打破了纯粹形而上精神乌托邦的一定意义上的虚幻和无依感,在对生存现场的经验表述中,生活细部的纹理和对身体性的张扬成为一个时代进步和诗歌进步的声音。
王珂: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所理解的“身体写作”。
我们往往一提到“下半身”就联想到了性,但我认为他们其实更多是在强调一种行动。
我觉得“下半身”出现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包括在“下半身”之前的一些论争中就已经出现了类似“要说人话”、“反贵族”的口号,“身体写作”是不宜用一些预定之言进行论断的。
我个人是为“个人化写作”进行辩护的,“身体写作”作为一种“个人化写作”理应得到大家认可,我个人是不主张用权力压制某一种写作的,因为写作可以有不同的层面。
对于“身体写作”特别是以“下半身”为例,我们究竟有几个人真正地去仔细读过他们的作品,而没有认真阅读人家的作品就批评人家的作品无疑是非常苍白无力甚至是武断的。
为什么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选择“下半身”?
恐怕只是使用单纯的道德批判可能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实质的。
在20世纪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女性诗歌中很早就有了“身体写作”的倾向,从石评梅、郑敏到今天的女性诗歌写作中,它大致经历了从最早的圣女、贞女、母亲、女人的阶段,而到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命名都似乎显得不够确切。
我认为“身体写作”以及“下半身”写作的出现原因大致有九点:
第一是政治问题,这里有明显地追求话语权利的问题;第二是商业目的,因为身体在这个时代是可以作为另类进行炒作的;第三是诗歌界的沿革;第四是个性解放问题;第五是社会的发展;第六点就是女权主义运动;第七就是文化大转型问题;第八就是传统文化的问题;第九就是诗教功利化问题。
最后,我还想讲一句,今天的诗歌写作到底应该是重视留下作品,还是强调写作的过程?
对于“身体写作”而言,我们到底是应该注意他们写什么,还是怎样写的问题?
张立群:
我对王珂刚才说的话有一点质疑。
对于他刚才将“身体写作”所定的范围,我是不能认同的。
由于我们无法对中国的“身体写作”进行界定,所以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就难免会在实际中遇到一系列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身体写作”首先应当是强调一种意识和观念,而选择身体作为其外部表象只是一种写作上的策略方法。
“身体写作”肯定无法与“写身体”等同起来,同时,“身体写作”也往往由于小说、诗歌文体间的差异而在语言表现上有所差异。
但“身体写作”的核心在于它的内部存在的东西。
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把《废都》这样描绘一个知识分子名人身处边缘境地的作品看成是“身体写作”,而始终坚持从翟永明等开始的写作是“身体写作”,何况80年代以前我们的身体一直是处于符号化的状态。
当然,对“身体写作”又是不宜轻易下结论的,如果我们事先就把一切尺度都定好的话,那么,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
我们更多应该做的应是在关注的前提下进而发现其本质,然后才是学理上的思索。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由于我近两年主要从事近现代的文学研究,所以可能距离“身体写作”有点远,我只简单讲几点自己的认识。
我在前两天一次宴会上偶然听到了“下半身”这个名字,当时,在座的一位朋友还朗诵了一首他们的诗《再舒服一些》。
我非常本能地感觉这与90年代初的一些女性作家如林白、陈染的写作不一样。
但“身体写作”无疑是一种大的趋势。
因为中国几十年来对“身体”、“性文化”的禁锢,最终能有这样一个开端是非常正常的,这是走向健康的一个必须过程。
我们不必对此大惊小怪甚至要禁锢与查禁,但是,我们在对这样的写作进行一种文化层面的分析的时候,尤其我们是处于一种女权主义立场的时候,问题似乎又不那么简单。
我们的许多作家一直呼吁要回归自然与原欲,我本人其实对此很怀疑。
“身体写作”并不仅仅反映欲望,它是与社会生活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的。
周亚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前几年我在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的时候,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小说研究者在谈论“下半身”,而且是以一种批判的口吻在谈,我当时心里是比较反感的。
我认识一些“下半身”的诗人,也读过他们的作品,我承认他们的作品是有一定问题的,但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他们其中的一些比较好的作品。
而且,对他们的评价应该是属于专业的,但这些研究者为什么只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呢?
我觉得他们在很多的情况下是望文生义,而不考虑具体的作家作品。
我觉得对于“身体写作”这个概念的提出首先应当进行一个学理上的梳理,它即使作为一个论文题目也是可以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它主要是针对小说的。
因而,“下半身”作为一种观念其实并不新鲜。
如果我们看一看《下半身》创刊号的宣言,就不难发现其实在“下半身”当中,每一位诗人对这个词语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他们的写作也必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
80年代中期“两报大展”的时候,那时出现了许多流派,也有许多宣言,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如《他们》、《非非》等。
但对于诗歌研究者来说,宣言往往是不可信的,诗人的写作也往往和他们的宣言是脱节的,自然也往往是不能互相印证的。
另外,对于“身体写作”这个概念,也可以从理论上进行复原,可以追溯到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批评家,这里比较值得关注的应该是西苏、伊利格瑞等的理论主张。
当代的理论界特别是批评界当时是有明显借用倾向的,只不过他们似乎没有更好地进行实践的融合,这也是中国理论界存在的一个问题。
女性诗歌中有没有明确的“身体写作”的说法?
是不是只是从“下半身”中以及后来的追随者得出的?
当代女性诗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大致有两个主要的流向,其中一条也许有描绘身体的倾向。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没有做太多准备,所以也不能轻易下结论。
吴思敬:
你这个问题其实就与刚才张立群和王珂的争论有关,他们两个就在“身体写作”的起源上有所差异。
张立群认为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的写作是当代诗歌中的“身体写作”的开端,而王珂则不这样认为;而你也在发言中将女性诗歌分为两个主要流向。
“身体写作”在90年代诗歌写作中是存在的,那么,翟永明这部分诗歌到底是不是“身体写作”?
这正是分歧的所在,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你也可以发表你的看法。
周亚琴:
我认为“下半身”在提倡身体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将身体和知识、历史,还有一些观念进行了二元对立。
“下半身”或性本身果真像他们所写的那样,还是与他们漏洞百出的理论相对应?
身体和性都是每一代人观念上的东西,它们不是纯粹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身体写作”在中国可能是被狭隘化了。
在西方女性主义者那里,“身体”是具有历史性。
“身体写作”是观念上的,如果要联系到诗歌文本上,那么,它必将与诗歌文体联系在一起,而单就“下半身”来说,他们对诗歌文体是没有什么建设的。
我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对他们的写作进行概括:
“观念上的写身体,艺术上的口语化。
”但他们在文体上没有什么建设,而女性诗歌可能会在将来在文体建设上有所突破。
吴思敬:
那么,女性诗歌将会在文体上有哪些突破呢?
周亚琴:
女性诗歌在文体上的建设我目前还没有完全想好,所以无法妄下结论,但是,回顾以往女性的诗歌创作,我们是不难发现她们的写作是非常有特点的。
霍俊明:
我觉得“身体写作”尤其是“下半身”对中国诗歌写作的负面影响还是太大了,因为他们要“拒绝抒情、拒绝思想”,而只是找到了“身体”。
他们带来的是新一轮的暴力,即使肉体乌托邦成为一种话语权利,因为他们拒绝了意义上的追求。
“身体”应当是诗歌描写的一个对象,但关键是在写作中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我对女性诗歌会为诗歌文体带来突破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的,因为女性诗歌不但要面对诗歌写作,还要面对诗歌外部的一些问题,这实质是“他者化”的一个问题。
文化与男权长期对女性诗歌进行了桎梏,这往往使女性诗歌举步维艰。
西渡(诗人、中国计划出版社副编审):
我觉得今天大家主要是从文化、社会这个角度来谈,但在具体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还是应当将“身体写作”的概念予以澄清。
是不是写“身体”就是“身体写作”,不写“身体”就不是“身体写作”。
这里我强调一个误区,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写作应当是一种语言的行为,它应当是自己意识的一种体现,而不是王珂所说的是一种“行动”。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我进行的才是“身体写作”,因为我写的是我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些不是身体最深处的东西吗?
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这种描写“身体”能不能给诗歌、给文学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刚才许多老师、同学都提出身体不是简单的一个问题,其实无论何种身体到最后都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文化。
方才周亚琴提到“下半身”他们要以自己的的写作与身体相对立,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们往往被自己的观念给束缚住了,我不觉得通过纯自然意义上的身体能够进入人的本质。
身体是一种综合性的、复杂性的存在,混同了很多关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观念在里面,要想充分表达附着在身体上的东西,就必须从一种批判的眼光开始,然后才能对它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这才是一种建设性的写作。
否则,像“下半身”这样描绘身体不是提高了身体的地位,恰恰是对身体的一种贬低。
我认为诗歌是对生命的一种体悟,诗歌应该去解放身体,而不是靠身体去解放诗歌。
胡兴(加拿大温哥华驻京高级软件工程师、文学硕士):
刚才西渡的话很有启发性。
不是写身体的就是“身体写作”,“身体写作”的内涵应当是比较宽泛的。
美国有一位著名诗人强调诗歌不应当用脑袋去写,而要下去,下到肚子的位置,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身体写作”,它的实质是要求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后):
我们包括西渡、臧棣曾经做了一个关于“身体写作”的对话,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发表出来。
但是,当时谈论的还是比较宽泛,而且也比较深入。
后来,吴老师说有这样一个会,所以,我个人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
我总体有这样一个印象,“身体写作”这个概念目前还处于含混的阶段,大家的观点还都不太一致,要么泛化,要么狭窄化。
有人把身体直接压缩为“下半身”或者是单纯的性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狭窄化的趋向。
脑袋是不是身体?
脑袋的思考是不是属于身体?
这都是可以提出疑问的方面。
同时,刚才像徐虹老师所说的女性身体,因为一般描绘身体总是以女性的为主,但是,男性身体需不需要在“身体写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一个男性写自己的身体,甚至是一个女性来写男性的身体,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算做是“身体写作”。
80年代杨炼曾经有一首诗叫《诺日朗》,这首诗曾经遭到了批判,因为它有强烈的男权意识,但这是不是“身体写作”?
所以,“身体写作”首先应当进行一番概念上的清理,当然,如果要深入讨论下去,还要对身体本身包含的比较复杂的东西进行研究。
身体在某些时候是非常感性的、在场的东西,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又是与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道成肉身”中的身体就是身份复杂的,这里还隐含着宗教的问题。
另外,具体到诗歌上的“身体写作”,它对于诗歌的影响我觉得有一个界限的问题,这就像性感和色情之间会存在一个界限一样。
比如穆旦的一些诗歌,后来唐在评价的时候说成是“肉感”。
这个“肉感”的评价是身体介入诗歌之后的一种效应。
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诗歌中的“身体写作”的时候,应该将视野放开,避免将它简单化和狭窄化。
关于“身体写作”的文化内涵及其批评
刘玮(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硕士生):
我只想谈谈“身体写作”的进步意义,当然这里必须首先要抵制那种无聊甚至肮脏不堪的描写。
身体究竟应该是什么,是形体还是躯体或者肉体?
当“身体写作”的概念被掷入文坛并掀起一股轩然大波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顺理成章的、注定要发生的一件事。
在过去的写作中我们的身体已经被压抑得太久,它需要找到一个地方来进行安身,而有关这一点,不但是生理机制的作用和历史规律的限定,更是人类思维模式、自我意识、社会道德标准转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大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生):
文化现象总是无法从个体经验的角度去解读的。
“身体写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只是从个体来进行说明,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
对于今天的文化现象,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一个“类”的基础之上去探究。
女权主义在许多现象上的解读可能由于极端化而显得很可笑,但它是一种观念上的表达,这作为理论上的表达是可以的,这就像海德格尔解读荷尔德林的诗一样,海德格尔在解读的过程中无疑是存在着大量自己的主观因素,但没有人会说他解读的不好。
我觉得“身体写作”应当从一种文化症候的视角去解读,我们不应该将其本质化,也不应该将其妖魔化了。
“身体写作”其实表明一种现象,即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身体是匮乏的或残缺不全的。
作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一种产物,身体一方面是文化上的东西,自然意义上的身体已经是不存在了,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讲,它又是一种无经验的经验,这是一种症候,虽然它是一个匮乏的症候。
因而,下定义对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需要以一种理论的态度去看待它,既不回避,也不就是简单归结为一个结论。
“身体写作”不能只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代名词,因为描述身体并不仅仅是女性所独有的。
俞菁慧(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