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枯荣.docx
《万物枯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万物枯荣.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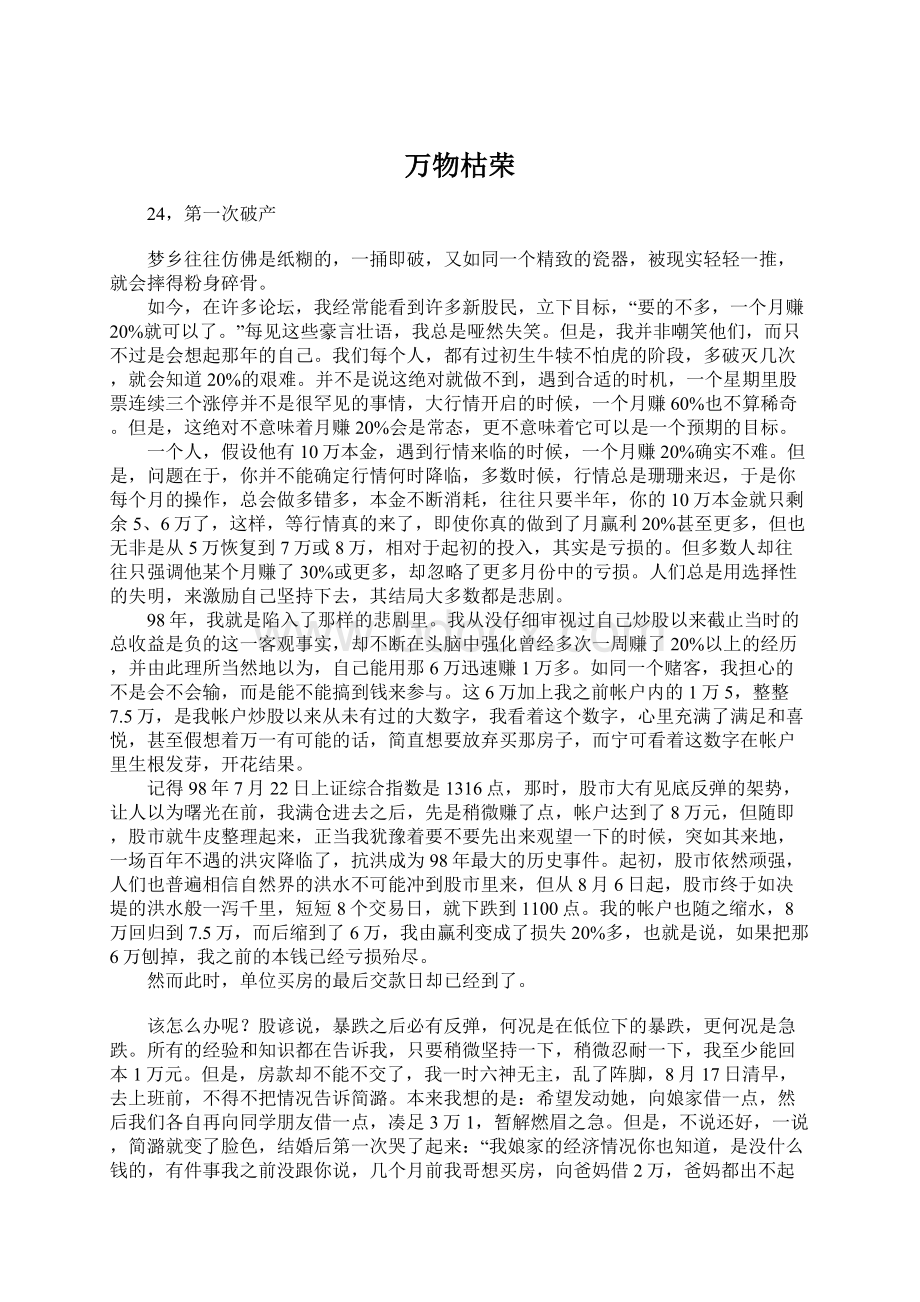
万物枯荣
24,第一次破产
梦乡往往仿佛是纸糊的,一捅即破,又如同一个精致的瓷器,被现实轻轻一推,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如今,在许多论坛,我经常能看到许多新股民,立下目标,“要的不多,一个月赚20%就可以了。
”每见这些豪言壮语,我总是哑然失笑。
但是,我并非嘲笑他们,而只不过是会想起那年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阶段,多破灭几次,就会知道20%的艰难。
并不是说这绝对就做不到,遇到合适的时机,一个星期里股票连续三个涨停并不是很罕见的事情,大行情开启的时候,一个月赚60%也不算稀奇。
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月赚20%会是常态,更不意味着它可以是一个预期的目标。
一个人,假设他有10万本金,遇到行情来临的时候,一个月赚20%确实不难。
但是,问题在于,你并不能确定行情何时降临,多数时候,行情总是珊珊来迟,于是你每个月的操作,总会做多错多,本金不断消耗,往往只要半年,你的10万本金就只剩余5、6万了,这样,等行情真的来了,即使你真的做到了月赢利20%甚至更多,但也无非是从5万恢复到7万或8万,相对于起初的投入,其实是亏损的。
但多数人却往往只强调他某个月赚了30%或更多,却忽略了更多月份中的亏损。
人们总是用选择性的失明,来激励自己坚持下去,其结局大多数都是悲剧。
98年,我就是陷入了那样的悲剧里。
我从没仔细审视过自己炒股以来截止当时的总收益是负的这一客观事实,却不断在头脑中强化曾经多次一周赚了20%以上的经历,并由此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能用那6万迅速赚1万多。
如同一个赌客,我担心的不是会不会输,而是能不能搞到钱来参与。
这6万加上我之前帐户内的1万5,整整7.5万,是我帐户炒股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数字,我看着这个数字,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喜悦,甚至假想着万一有可能的话,简直想要放弃买那房子,而宁可看着这数字在帐户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记得98年7月22日上证综合指数是1316点,那时,股市大有见底反弹的架势,让人以为曙光在前,我满仓进去之后,先是稍微赚了点,帐户达到了8万元,但随即,股市就牛皮整理起来,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先出来观望一下的时候,突如其来地,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降临了,抗洪成为98年最大的历史事件。
起初,股市依然顽强,人们也普遍相信自然界的洪水不可能冲到股市里来,但从8月6日起,股市终于如决堤的洪水般一泻千里,短短8个交易日,就下跌到1100点。
我的帐户也随之缩水,8万回归到7.5万,而后缩到了6万,我由赢利变成了损失20%多,也就是说,如果把那6万刨掉,我之前的本钱已经亏损殆尽。
然而此时,单位买房的最后交款日却已经到了。
该怎么办呢?
股谚说,暴跌之后必有反弹,何况是在低位下的暴跌,更何况是急跌。
所有的经验和知识都在告诉我,只要稍微坚持一下,稍微忍耐一下,我至少能回本1万元。
但是,房款却不能不交了,我一时六神无主,乱了阵脚,8月17日清早,去上班前,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简潞。
本来我想的是:
希望发动她,向娘家借一点,然后我们各自再向同学朋友借一点,凑足3万1,暂解燃眉之急。
但是,不说还好,一说,简潞就变了脸色,结婚后第一次哭了起来:
“我娘家的经济情况你也知道,是没什么钱的,有件事我之前没跟你说,几个月前我哥想买房,向爸妈借2万,爸妈都出不起,悄悄问我能不能从咱们这先凑2万帮一下哥哥,可我刚工作手里哪有余钱?
至于你,炒股以来哪还舍得把钱从股市里往外掏?
所以,我没把这事告诉你,就悄悄回绝了我爸妈……为这事,我爸失望极了,在电话里说,女儿嫁出去了就真的是泼出去的水了,每想起他这话,我都忍不住偷偷流泪,只不过一直没让你晓得……而现在,你居然还倒过来想让我帮着借钱继续炒股,我跟你说,绝对不可能,咱既然手里的钱还够,为什么要借?
而且不仅不借,装修的钱也得马上取出来,免得继续在股市里亏个精光!
”
在那一刻,我竟然没为简潞的泪水而内疚,却抓耳挠腮,为连装修的钱也要提前取出来而愤懑。
8月17日上午,我割肉卖出了足够交3万1房款的股票,却依然没舍得将装修的钱也提前卖出来。
晚上,很晚我才回到简潞的宿舍,隔着窗户,我看到屋里黑黑的,没有开灯,还以为简潞不在,但打开门,走进去,却发现简潞蜷缩在床上。
月光从窗户洒进来,虚无地摇曳在简潞清丽的脸上,简潞的眼角有着泪痕,眼神空空的,她望着头上空空如也的单身宿舍房顶,仿佛灵魂已经游离出了躯体。
我心里突然涌起巨大的悲怅,紧紧将简潞抱在怀里,喃喃地说:
“3万1已经卖出来了,明天一大早,我保证把装修和买家具的钱也卖出来,股票不炒了……”
简潞听我这么说,仿佛看着一个戒赌的浪子,眼角终于燃起了希望的光芒。
“你一直在炒股,我知道这里面有你的梦想,所以我尽管从一开始就反对,但一直在忍耐,不过现在我真的再不能忍了,你是当局者迷啊,股票其实不是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能炒的,再炒,这个家就完了,所以,我必须阻拦你了。
”她用手掌轻轻拂摸着我的脸,说,“我知道你心高气傲,不甘平庸,不让你炒了,你肯定难受,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自己,我们只是普通人,输不起啊,我们不能连普通人的平安日子都输没了啊。
”
我点了点头,吻着简潞,心想,这么好的女人,她从未要求过我太多,如果我连一个起码的家都不能给她,如果住进了旧房子连墙壁地板都不重新装修一下,连起码的家电家具都没有,我如何对得住她。
于是,那个夜晚,我暗暗在心里与深爱的股市道别,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惆怅。
第二天是1998年8月18日,很吉利的数字,但并没给我带来吉利。
上午9点多,我向蒋处长请假,说把股票割肉卖了,去取钱交房款,以后可能不打算炒股了。
蒋处长站起来,拍了拍我,说:
“小雷啊,这样做就对了,你去吧。
”我骑着车,到证券公司将3万1从股票帐户取出来,那时还没有第三方存管,取钱必须去券商柜台。
取出钱后,我看了看散户大厅的屏幕,绿绿的一片,我心里长叹一声,将剩余的股票也全部清仓,资金又缩了点水,还剩2万7,也就是说,我之前的股市资金,已经彻底归零了。
这是我在股市第一次破产,奇怪的是我却似乎并没什么痛苦,我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单位蹬,有一点莫名其妙的轻松感:
以后不用再随时想着股票了,仿佛放下了一块石头。
但同时,一种巨大的空虚吞噬了我,使我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激情,股市如同一个窃贼,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洗劫了我的心,偷去了我的热情,而后冷漠地将我推在门外,仿佛它从来不曾在乎过我。
而这,莫非就是我作为一个小人物,所必须承受的命运?
25,远离股票的日子
从那以后,我过了接近两年远离股票的日子。
98年9月初,我拿到了房子钥匙。
虽然只是一套旧房,依然让我那些大学同学们羡慕不已。
毕业仅仅两年时间,就能在成都市内环路以内的中心地段,拥有一套全产权的住房,这对于同年毕业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我的那些大学同学,有的进了外资企业,有的进了律师行,月薪比起我们小公务员,要高不少,但是,他们都没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拥有一套住房。
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恩。
随后就是装修,都说装修是个无底洞,投再多的钱进去也冒不了一个泡,即使在98年,花个十万八万,也不是稀奇事儿。
所以我预算中这一万,装得不可能豪华。
但是,我和简潞都是很有审美眼光的人,基本做到了“花钱少,装修好”。
先是做木工活儿,能将就着用的就将就着用,比如说,房里的门,多数人都是重新做新的门,加上门套,一扇门就得400元。
简潞主动提议,就用以前的门,重新刷一次漆就可以了;另外,书柜不用去买,而是自己做,让木工直接钉在书房墙上,既省木料,也可以把一面墙也顺便装修了……当然,有些必须换的还是得换,老房子原来的窗户很旧,我们换成了铝合金窗,房间立即就显得焕然一新了。
装修过程中,我越发觉得简潞的贤惠。
简潞原本一直想安木地板,但我心里嫌木地板比瓷砖地板贵,于是买什么地板,就一直悬而未决。
一次,我们一起去买木料的时候,经过一个仓库,偶然发现里面有很多陈旧的地砖,尽管积了灰,抹开后却很雅致,关键是,价格便宜得惊人。
简潞当即决定,就买这地砖。
我们花很少的钱,就买够了铺完整套房子的地砖,俩人都为这意外的好事欣喜不已。
我们装修总共只花了9000元,这样,2万7就还剩余出了1万8,可以用来买家具家电。
对于家具,以前也不是没看过,但都没仔细瞧,如今仔细看了,才吓了一跳。
一套沙发,即便是布艺或者猪皮的,稍微时尚一点的,也得三四千元。
衣柜、书柜、双人床……哪样不得两千来元?
这还没算家用电器。
在98年,空调还是奢侈品,我是不打算买的,但是,彩电总得买吧?
冰箱总得买吧?
洗衣机总得买吧,所有这些,没有两万来块,不大可能置得完。
国庆节那天,简潞很高兴,大清早就拉着我去了电器商城。
原来,简潞看报纸,得知电器商城正在推出彩电特价,29吋的大彩电,在96年要卖6000多元,到了98年,降到了3800元。
如今搞国庆特价,一台29吋的康佳,只要3200元。
机会难得,简潞生怕国庆一过便恢复原价,欢天喜地地选了一台,因为是特价,商场不包送,我们在高兴之下却丝毫不介意,说,“也好,你们送,我们还不放心呢,而且,你们要明天才送得到,我们可是今天就想把它搬回自己家里去。
”
我和简潞租了个三轮车,将彩电运回了新家。
这是我们小窝里的第一样东西,让我俩兴奋不已。
高兴之余,我俩就关了门,亲昵起来,开始只打算接接吻,吻着吻着我就吻到简潞的雪白细长的脖子上去了,手也不规矩起来,简潞叹了口气,说:
“你就是这么不老实,假如你在工作上也这么进取,早就脱颖而出了。
”我嘻皮笑脸地说:
“我才不在乎工作上脱颖而出呢,我只想在你这里脱颖而出。
”简潞掰了掰我的手,没掰开,只好任我继续“脱颖而出”,脱着脱着,简潞的脖子就红透了,眼睛也水波流动,白了我一眼说:
“你真要在这里做啊?
”我说:
“当然是真的。
”由于房子里再没别的东西,地板又还没清理,简潞只能趴在新买的大彩电纸箱上,一再地问,“这彩电承得住吗?
可别把咱们最大的财产给压坏了啊。
”我说,“你没看箱子上写的吗?
最多可以叠加四台,你比一台彩电重不了多少,怕什么承不住呢?
”一边说,一边开始用劲,简潞似乎放心了,开始闭上眼睛,伊伊呀呀地低声**起来。
尽管彩电纸箱终究是小了些,但因为是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家里做,俩人都心情特别舒畅,做了一次,又做了第二次。
做完之后,竟然都中午了,我们没吃早饭,肚子早就有些咕咕叫起来,于是一起到家门附近街上的小馆子里,简单吃了顿饭,两人坐得近近的,时不时用手握一下对方的手,都感到恩爱无尽,仿佛回到了刚开始相恋的时候。
之后的那几天,我们四处寻觅打折的家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寻找价廉物美的家具如同淘宝一样,倒也是一件乐事。
很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先是买到了一套合意的浅绿色沙发,虽然是猪皮的,但款式新颖,质地优良,最重要的是,居然只要2100元;还买了一个很大的衣柜,大到可以装完简潞所有的衣服还绰绰有余,衣柜色调很好,柜门一半是咖啡色,一半是**白色,中间是一面镜子,和杂志上看到的“宜家”的某一款衣柜颇为神似,价格却只有1800元;再一个是床,98年在成都,对咱们普通市民来说“青田家俬”就算不错的了,我发现里面尽管多数商品都比一般家俬城贵不少,但偶尔也有特价商品,反而比其他地方便宜。
比如我们在青田买的床,原价2800,特惠价1600,标得清清楚楚,青田里的商品不会故意乱标价,这说明它确实以前曾经卖到过2800,如此一来,相对于以前买这床的人,我们无疑白捡了1200元,类似于28元的股票跌到了12元,此等好事,怎能错过,于是连忙将床买回了我们的新家。
此外,我们还花2千多元买了个海尔小王子冰箱,1千多元买了个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以上这些大件,一共花了1万3千来元,屋里其他一些小东小西,大致花了3千来元,总共1万6千元,我们便把小家布置得舒舒服服。
而我从股市里取出的钱,这么一来,也就只剩下2千元了,这2000元便是我和简潞全部的积蓄,如此之少,以至于连拿来炒股都显得毫无意义,现实的拮据,使我彻底地与股票越隔越远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似乎是老天对我的怜悯。
98年下半年直到99年5月,接近一年的时间里,股市经历了严酷的下跌,无数百万富翁破产消逝,无数千万富翁敛羽而归。
资金投入得越多,损失越惨烈。
我幸运地在98年并无多少资金,且为了买房与装修不得不清仓离场,所以固然亏光本金,损失的也无非是一万多元。
而老童,在搬进新居后,观察股市良久,认为自己耐心等待了一年多,终于等到了底部,于是再次倾力入市,想要一举扭亏。
然而他没想到,自己却抄在了半山腰上,将他最后的养老钱亏了个精光。
每一轮熊市,新手总是倒在山顶,因为新手往往乐观看多,难免在山顶被套;老手则是倒在山腰,因为老手喜欢抄底,却又普遍把山腰当成了山脚;而所谓高手,他们躲过了山顶,也躲过了山腰,却往往倒在了山脚的剧烈震荡中,在山脚过于频繁的追涨杀跌里元气大伤。
熊市是一个无底洞,不管你是身家千万还是仅仅万元,在上苍眼里,一律只是刍狗,一视同仁地用巨大无边的熊掌,将你扑杀。
所以,在熊市里,资金越少的小股民越幸运,因为上天垂怜,即便亏光也并非一个无法翻身的大数字。
我在懵懂之中远离了股市,侥幸躲过熊市末期的杀跌,不至于身负债务,这种后怕,使我对股市突然产生了严重的厌恶,连看也不想再看股市行情。
我的生活变得平静起来,98年11月,我们告别简潞的单身宿舍,开开心心地搬进自己的小家,我和简潞感到十分满足。
我们从93年开始相恋,5年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容易啊。
我们房子的窗外是一棵很大的法国梧桐,正式入住后的第一个早晨,是个周末,醒来的时候,居然听到了鸟叫。
我们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并且也不想**,只是紧紧地互相依隈在一起,感到心比蜜甜。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到小馆子里喝点小酒,庆祝乔迁。
我拉着简潞的手,突然有些哽噎,说:
“我今生今世运气真好,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
”简潞说:
“少抒情了,你工作努力一些,积极进取一些,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
我想想也是,自己毕业这两年半,激情都放在了炒股上,在单位里越混越差,越来越不受重视,要怪还是怪自己啊,有这么好的老婆,为了我们的未来,我怎么可以不积极工作呢?
恰在这时,新一批下派工作开始了,我们单位需要三名干部下派到偏远的巴中挂职工作一年,为了扭转自己进单位以来的颓势,好好挣点表现,我报了名。
26,与“五一九”擦肩而过
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早期,下派是件美差,就像21世纪里的公务员出国进修一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镀金方式。
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下派过的人越来越多,不可能都提拔,很多人下派了也就下派了,回来还是原地踏步。
机关里的人渐渐就明白一个道理:
想提拔你,没下派过照样提拔,不想提拔你,下派了照样不提拔。
既然如此,谁还愿意去吃那个苦?
所以,到了98年前后,已经很少有主动要求下派的了,甚至不少人私下说,这下派制度,形式主义,没有多少实际作用,不如取消了还好些。
但是,沿袭多年的制度不是说改就改的,每个省委省府的厅级单位,每年照样得安排干部定点下派扶贫。
不知不觉中,下派对各方面而言,都成了个鸡肋般的东西。
我们单位定点下派扶贫的地方是巴中市巴朗县。
巴中是全省最边远的地区之一,巴朗是这个边远地区里最边远的县份之一,出了名的“老少边穷”,离省城成都很远,坐汽车要十多个钟头。
所以巴朗实在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下派点。
我们单位的人经常抱怨说,你看人家XX厅,下派的那个县也叫“贫困县”,但离成都才八十公里,下派就跟度假一样,多好。
所以,当98年底单位再度要完成下派任务时,我是唯一一个主动报名的,自然而然就成了下派三人之一。
另外两个,一个是XX处的副处长钱小群,下派到巴朗当县委副书记;一个是XX处的主任科员小贺,下派到巴朗县广电局当副局长;至于我,还只是科员,下派到巴朗县委XX部,当了个办公室副主任。
确定下派之后,还有半个月才正式下去,这半个来月,主要做一些工作移交的事情。
我本想将内务趁机移交给小贾,这样一年后我回来,或许就有希望不再做内务。
可是,小贾很有心计,为了避免全部接受内务,他以协助蒋处长写材料很忙为借口,只接收了内务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蒋处长让老童代理,这个小小的安排上的技巧,意味着我下派回来之后,只要不另换处室,依然不得不继续干内务。
我心里完全明白小贾的手段,却又无可奈何,不禁感到有些消极,还没下去就这样了,回来之后又能如何?
但是,我还能不去吗?
在人生的路途中,许多时候总是身不由己,一旦出发,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99年1月,元旦过后没几天,单位派了辆车,送我们三人到下派点去。
因为巴朗实在太远,出发时间定得很早,六点半就得在省委大门口碰头。
我专门定了闹钟,五点半就早早起床。
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主要是换洗的衣服和必要的日常用品,还有几本书,据说下派期间比较无聊,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书打发时间。
就这么一些东西,居然也有一大皮箱。
我重新把皮箱打开,最后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才又把皮箱锁好。
这时候,六点了,我得出门了,本来想跟简潞打个招呼,但简潞昨晚也是很晚才睡着,五点半钟被闹钟闹醒时嘟哝了两句,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我不忍心又把简潞推醒,用唇轻轻在简潞额头上触了一下,就小心地带上门出去了。
走到楼下,我突然听到简潞的声音,“雷子,雷子”,我抬起头,看到简潞正从卧室窗户里探出来半个头,我心里一热,说:
“你快休息,天冷,别冻着了。
”然后狠狠心,头也不回地向宿舍大院门口走去。
临出院门时,我突然想起还一直没有给窗户安防护栏,微微有些酸楚。
安防护栏得近两千元,我心底下希望将这笔钱省了,所以一直拖着没安,如今,看着光秃秃的窗户,我忽然觉得挺对不住简潞。
到了巴朗之后,起初有些新鲜,但渐渐也就麻木了。
我们一般两个月才回成都一次,十分孤单,下面的同事并不见得非常热情,彬彬有礼地和我们保持着适度的距离。
虽然都是省上来的干部,但下派干部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享受的待遇是大不一样的。
从省上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基层的干部对省上干部的称呼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不知道具体职务,就一律称“领导”,我记得当初刚上班不久跟随蒋处长到巴中开过一次会,被当地干部左一句“领导”右一句“领导”地叫得很是顺耳;如果知道职务,部长自然还是喊部长,处长自然还是喊处长,但普通干部的喊法,却颇有讲究,假比说,你是个主任科员,他们喊你时,就特意把后面的“科员”二字省略,简称“主任”,假比你只是个小科员,他们也有办法,就是在姓后面只加一个“科”字,“王科”、“张科”地喊,给人感觉是“王科长”、“张科长”,自然让“王科”“张科”们心中暗喜了。
但是,下派干部一般是享受不到这种礼遇的,一来你不是来视察的,是来接受基层锻炼的。
二来你不是只在下面呆几天就走,如果是呆几天就走,场面上奉承你两句,即便没有好处也无妨,反正拍几天马屁也累不死人,但你是呆上一年,谁愿意拍一年劳而无功的马屁呢?
当然,他们也不会待你太差,就那么尊重而客气地维持着一种和和气气的关系,久而久之令人感到十分乏味,让我颇有些后悔报名下派。
但更令我在后来的日子久久遗憾的是,下派期间,资讯的封闭使我更为疏离了股市,而边远县城投资氛围的极度稀薄,则使我完全觉察不到股市一个巨大的机会突如其来的降临:
1999年5月19日,股市忽然否极泰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由1047点迅速涨到了1700点,如此之快,让人根本措手不及。
在那如火如荼的行情里,如果我是在成都,无论如何都会跟风追进,而在遥远的巴朗,仿佛这是一块与投机完全绝缘的飞地,我们仿佛置身在一个没有股市的时代。
我呆在这个被“五一九”彻底遗忘的角落,再次与股市的一次大机会擦肩而过。
这是命运吗?
或许我注定就会一生清贫?
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连我自己也不能。
1999年6月底,我回成都休假时,听到周围的人又都在谈论股票了,然而那时点位已高,我显然已经错过介入的好时机。
看着由10元涨到28的广电信息,看着由15元涨到40的东方明珠,我既惆怅,又迷惘,体会到一种比熊市里更难受的痛楚。
从那一刻起,我发现对我们小股民来说,踏空比套牢更沮丧,因为即使套牢,心中始终还是拥有着希望,有希望就会有快乐;而一旦踏空,最大的打击是发现希望像肥皂泡一般被戳破了,没了希望,人就象被抽去了主心骨的皮囊,陡然就疲软了。
27,新千年
就这样,一年时间渐渐也便过去了,1999年12月底,我们开始张罗着准备返回省上。
一天,我正在百无聊赖,突然司机老孙头问我:
“雷主任,我要进一趟市里,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原来,部长嫌以前用的手机不够时尚,决定换一部,让老孙头到市里去买个新手机来。
巴朗虽然穷,但领导们的手机却是从不落伍的,即便与省城的成功人士随身携带的手机相比,也够得上档次。
据说部长本来是不想换新手机的,但是,为了不在与外地同志洽谈工作时给巴朗丢脸,只好勉为其难地换了。
巴朗是一座历史只有二十多年的新城,在大山中间一小块空地里,由于是贫困县,小小的县城没有几条街道,半小时便可逛完。
商场也没有几个,一到天黑就关门闭户,黑灯瞎火。
我老呆那里,平时连市里也难得一去,作为省城来的年轻人,难免会十分无聊,老孙头显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去市里,往往主动载着我去。
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坐老孙头的车去市里了。
一路上,我感到他似乎欲言又止,有什么话想说。
我有些小小的不安,素来最怕别人无缘无故对自己好,总担心当对方有所求时,我却帮不上忙。
这老孙头,自从我来后,就对我格外好,因此,我很想知道老孙头究竟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但是,这话又不好主动问出口,着实让我有些心急。
好在,车快到市里的时候,老孙头突然说,自己一家三口,迄今在巴朗没有房子住,只能租附近农民的住房,既要交租金,又很不方便。
他希望我离开巴朗时,将所住的那间房子的钥匙,直接交给他。
“现在等着那房子的人不少,基层就是这样,谁先实际占着谁就能成事儿,用你们干部们的话说,叫‘造成既成事实’,你到时候把钥匙给我,部长那里,我会去说,他帮我找县委办公室通融通融,这房子就是我的了……”
我听了,心里好一阵感慨。
作为下派干部,我一来就住进了县委单身宿舍楼里的一个单间,屋里连被褥、床单、脸帕及脸盆,都为我准备齐全了。
我起初还有些嫌那房间简陋,完全没想到许多县委的工作人员,却连那样的单身宿舍也住不上,还得在外面租房,并紧张地注视着每一间可能空出来的宿舍……多少人,在为更好的前程费尽心机,而另有多少人,在为一些起码的待遇碾转反侧。
想起那句话——许多人奋斗一生获得的,就是另外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拥有的——人啊,在这苍茫世间,是如此不平等,而又是如此雷同——不平等的是人与人追求的东西相差万里,雷同的,是不管他们追求的东西如何不同,但追求过程中的情感和心态,却是千篇一律,难分伯仲。
几天后,我的下派工作就顺利结束了,临走前,我把钥匙私自给了老孙,这对我来说只是小小的越权,对他来说却是巨大的收获,因此我愿意帮他这个忙。
回到单位,果然发现,我的返回几乎没任何人在意,连内务工作也顺理成章地立即移交回来,仿佛我不是离开了一年,而仅仅是离开几天。
机关就象一片表面波澜不兴的巨大湖面,而我则如同一滴小小的水珠,当小水珠重回湖面时,连一个水花都渐不起。
1999年即将过去,翻过元旦便是新千年了。
相对于社会上普遍的对“新世纪”这个概念的关注,机关里显得平淡得多,没有人特别在意2000年的到来。
我一向是个对新生事物比较敏感的人,可是,在我的周围,没有谁和我谈论未来,更没有人会思考1999年与2000年有何不同,的确,在多数人眼里,这两个数字是没有差别的,人们关心的只是切身的利益和视野可及的生活,而这些,的确不会因年月数字的微小改变而有太大不同。
甚至,在这样的氛围里,谁去思考这些不切实际的问题,也会被视为笑柄。
我们这个民族是不擅长抽象思维的民族,太过现实,太过追求经世致用。
或许,是因为几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于艰辛,使“活下去”与“活得体面一点”始终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心思去思考那些遥远的问题。
而我,却那么不合时宜地喜欢去想玄而又玄的东西。
只不过,在如此的环境里,我即使有心去想,却也难以真正静下心来想清楚什么。
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坐在自家窗前,看着窗外寒冬中的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