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赵树理《套不住的手》之欧阳术创编.docx
《短篇小说赵树理《套不住的手》之欧阳术创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短篇小说赵树理《套不住的手》之欧阳术创编.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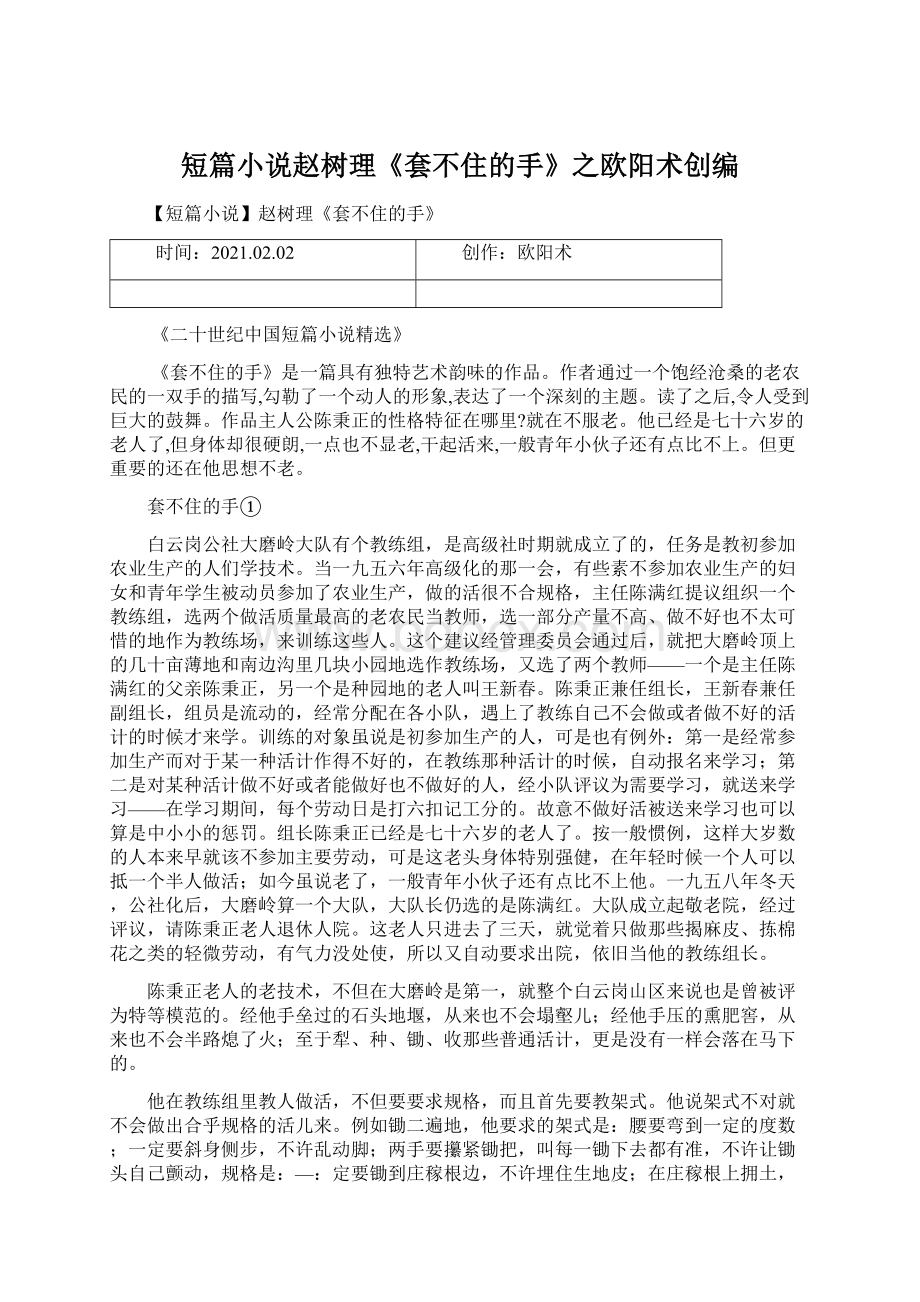
短篇小说赵树理《套不住的手》之欧阳术创编
【短篇小说】赵树理《套不住的手》
时间:
2021.02.02
创作:
欧阳术
《二十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精选》
《套不住的手》是一篇具有独特艺术韵味的作品。
作者通过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农民的一双手的描写,勾勒了一个动人的形象,表达了一个深刻的主题。
读了之后,令人受到巨大的鼓舞。
作品主人公陈秉正的性格特征在哪里?
就在不服老。
他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但身体却很硬朗,一点也不显老,干起活来,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
但更重要的还在他思想不老。
套不住的手①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是高级社时期就成立了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们学技术。
当一九五六年高级化的那一会,有些素不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和青年学生被动员参加了农业生产,做的活很不合规格,主任陈满红提议组织一个教练组,选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选一部分产量不高、做不好也不太可惜的地作为教练场,来训练这些人。
这个建议经管理委员会通过后,就把大磨岭顶上的几十亩薄地和南边沟里几块小园地选作教练场,又选了两个教师——一个是主任陈满红的父亲陈秉正,另一个是种园地的老人叫王新春。
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分配在各小队,遇上了教练自己不会做或者做不好的活计的时候才来学。
训练的对象虽说是初参加生产的人,可是也有例外:
第一是经常参加生产而对于某一种活计作得不好的,在教练那种活计的时候,自动报名来学习;第二是对某种活计做不好或者能做好也不做好的人,经小队评议为需要学习,就送来学习——在学习期间,每个劳动日是打六扣记工分的。
故意不做好活被送来学习也可以算是中小小的惩罚。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
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
一九五八年冬天,公社化后,大磨岭算一个大队,大队长仍选的是陈满红。
大队成立起敬老院,经过评议,请陈秉正老人退休人院。
这老人只进去了三天,就觉着只做那些揭麻皮、拣棉花之类的轻微劳动,有气力没处使,所以又自动要求出院,依旧当他的教练组长。
陈秉正老人的老技术,不但在大磨岭是第一,就整个白云岗山区来说也是曾被评为特等模范的。
经他手垒过的石头地堰,从来也不会塌壑儿;经他手压的熏肥窖,从来也不会半路熄了火;至于犁、种、锄、收那些普通活计,更是没有一样会落在马下的。
他在教练组里教人做活,不但要要求规格,而且首先要教架式。
他说架式不对就不会做出合乎规格的活儿来。
例如锄二遍地,他要求的架式是:
腰要弯到一定的度数;一定要斜身侧步,不许乱动脚;两手要攥紧锄把,叫每一锄下去都有准,不许让锄头自己颤动,规格是:
—:
定要锄到庄稼根边,不许埋住生地皮;在庄稼根上拥土,尽可能做到整整肃肃三锄拥一个堆,要平顶不要尖顶。
在开始教的时候,他先做榜样,让徒弟们在一边跟着看。
他一边做一边讲,往往要重复讲十几遍,然后才让大家动手他跟着看。
因为格律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腰太亘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该是一下就能办的事却几下不得解决问题……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往往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有个人叫郝和合,半辈子常是直着腰锄地,锄一锄,锄头蹦三蹦,锄头蹦到草上就锄了草、蹦到苗上就伤了苗。
教练组成立以后,小队里评议让他到组里受训。
他来的时候,老组长陈秉正照例教给他锄地的架式,只是这个人外号“哈哈哈”,带几分懒汉性,弯下腰去锄不了几锄就又直起腰来。
陈秉正这老人也有点创造性,第二天回去把自己家里闲着的一个锄头,安了三尺来长一个短把子给郝和合说:
“你这弯不下腰去的习惯,只有用这短把子锄头,才能彻底改正。
”郝和合一换锄头果然改正了——因为三尺来长的锄把,要不弯腰,根本探不着地皮。
后来各小队知道了这个办法,都准备了几张短把锄头,专门叫给那些没有弯腰习惯的人用。
徒弟们练架式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和他们休息一阵子。
相隔八九段梯田下边的沟岸上,有副组长王新春领着另一批徒弟在那里教练种园地。
在休息时候,上下常好打个招呼,两个老人好到一块吸着旱烟闲谈一会;徒弟们也好凑在一处读一读小报,或者说说笑笑。
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
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一被他握住像被钳子挟住那样疼。
有一次休息时候,陈秉正叫王新春上去吸烟。
陈秉正是用火镰子打火的,王新春说:
“烧一堆柴火吸着多痛快!
”一个新参加学习的中学生听说,忙帮他们在就近拣柴,却找不到什么东西,只拣了二寸来长两段干柿树枝。
王新春笑了笑说:
“不用找!
你陈家爷爷有柴厂那个学生看了看,没有看到什么柴。
陈秉正老人也说了个“有柴”,不慌不忙放下火镰子,连看也不看,用两只手在身边左右的土里抓了一阵,不知道是些什么树皮皮、禾根根抓了两大把;王新春老人擦着洋火点着,陈老人就又抓了两把盖在上面。
那个学生看了说:
“这个办法倒不错!
”说着自己就也去抓。
陈老人说:
“慢慢慢!
你可不要抓!
”可是这一拦拦得慢了点,那个学生的中指已经被什么东西刺破了,马上缩回手去。
王新春说:
“你这孩子!
你是什么手,他是什么手?
他的手跟铁耙一样,什么棘针蒺藜都刺不破它!
”
那个学生,一边揉着自己的中指,一边看着陈老人的手,只见那两只手确实和一般人的手不同:
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
不过他对这一双手,并不是欣赏而是有点鄙视,好像说“那怎么能算‘手’哩”。
学生的神情,两个老人都看出来了。
陈秉正老人没有理他,只是自豪地笑了一下就拿起自己的旱烟袋来去吸烟,王新春老人点着烟之后却教训起这个青年人来。
他说:
“小伙子!
你不要看不起那两只手!
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教练场恐怕还是荒坡哩!
这山是地主王子裕的,山顶上这十几段地,听老人们说从光绪三年就荒了,一直荒到宣统三年。
当年间我们两家都没有寸垅田地,他给王子裕家当长工、我给王子裕家放牛。
后来他来这里开荒,我长大了从放牛孩子升成长工,跟着老领工在大河滩学着种园地。
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他们父子俩一钁头一钁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没有那两只手,这里还不是一片荒坡吗?
”
那个学生虽然对他自己那种鄙视的表示有点后悔,可是他除了不愿当面认错,反而还自我解嘲地说:
“怨不得我们学习得慢,原来就没有那样的手!
”
陈秉正老人一本正经地教训他说:
“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
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
他这双手不但坚硬,而且灵巧。
他爱编织,常用荆条编成各色各样的生产用具,也会用高梁秆子编成各色各样的儿童玩具。
当他编生产用具的时候,破荆条不用那个牛角塞子,只用把荆条分作三股,把食指塞在中间当塞子,吱吱吱……就破开了,而他的手皮一点也磨不伤;可是他做起细活计来,细得真想不到是用这两只手作成的。
他用高粱秆子扎成的“叫哥哥”①笼子,是有门有窗又分楼上楼下的小楼房,二寸见方的小窗户上,窗格子还能做成好多不同角度的图案,图案中间的小窟窿,连个蜜蜂也钻不过去。
土改以后,经过互助、合作一直到公社化了,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
他接过来一看说:
“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
”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子。
儿子陈满红说:
“慢慢用着就合适了!
”老人带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
“还好!
”说罢,卸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
“暂且给我放过去吧!
”满红媳妇说:
“爹!
你就带上走吧!
到地里手不冷?
”老人说:
“在沟里闸谷坊,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
”说着就放下走了。
以后谷坊闸完了,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
满红媳妇劝老人说:
“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你教多少技术,你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会吧!
”老人答应了。
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
满红媳妇说:
“这回可带上你的手套吧!
”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带上走了。
大磨岭村子小,没有供销分社。
老人穿着新衣服、戴着手套打街上走过,村里人见他要到白云岗去,就有些入托他捎买东西,东家三两油、西家二斤盐,凑起来两只手就拿不了,借了邻家一个小篮子提着。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走到供销社门口,把给别人捎买的日用品买全了又向前走,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忙着正往车下搬。
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
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
他自己身上没有带钱,想起满红在公社开会也许有带的钱。
他跑到公社向满红一说,满红说:
“噢!
哟!
那可是宝贝,赶快买!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来递给他。
老人拿上钱就到山货部来挑桑杈。
老人对农具很讲究,从来见不得有毛病的。
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拿起一柄来把杈头放在地上试看三股子平不平、有力没力、头正不正、把弯不弯。
他连一柄还没有看完,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转眼工夫,买杈的越来越多,连在公社开会的大队长们也暂时休了会出来买杈。
这些人也不挑三拣四,问明了价钱就拿。
陈秉正老人见情况紧张起来,也不敢再按自己的规格挑选,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
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提起小篮子来挤出山货部,因为东西够拿了,他也无心再逛那半条街,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
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
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搜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
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
他想:
“丢就丢了吧!
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
”于是他又束好了腰、扛起桑杈、提起小篮子继续往家走;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
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
这自然又该是他带一次手套的时候。
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带上。
大磨岭离县城四十里,冬天的白天又短,陈秉正老汉从吃过早饭起程,直走到太阳快落山才到。
这一天只是报到的日期。
老人到县后,先找着报到处报了名、领了出席证,然后就去找晚上住宿的招待所。
他半年没有进县城,县城里已经大变了样——街道改宽了,马路也压光了,他们往年来开会住的破破烂烂的招待所,已经彻底改修成一排一排崭新的砖瓦房了。
他进入招待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后边几排房子靠甬道两旁的窗户里都闪出灯光,一看就知道里边已经住下了人。
前三排的窗户,也有明的、也有黑的。
他到传达室登记了名字,招待员领他往西二排五号去。
他走到西二排,见只有最西边的六号房间窗上有灯光,其余都还是黑的;脚底下踩着些软一块硬一块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些什么。
招待员向他说:
“小心点老人家!
这房子刚修好,交了工还不到一礼拜,院子还没有清理完哩!
——这边些,那里是个石灰池!
——靠墙走,那里还有两截木料……”走到五号门口,招待员开了门先进去开了灯,才把老人让进去。
老人一看,房子里挺干净,火炉子也燃得很旺,靠窗前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条板凳,后边靠东西墙一边排着两张床,门窗还不曾油漆过,墙好像才粉刷了,经火炉子一熏还有点湿味儿。
老人看了看床位说:
“一个房间住四个人吗?
”招待员说:
“四个人!
”“这次会议住得满住不满?
”“都来了差不多住满了!
路远的还没有赶到哩!
你休息一下吧!
我给你打水来洗洗脸!
”一会,招待员打来了水,老人洗着脸,路远的人也陆续来着,西二排的房子就也都住满了。
五号房间除了老人以外,又住了三位青年,老人和他们彼此作了自我介绍。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了,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
下午,离县城近一点的就都回村去了,路远的就得再住一宿。
陈秉正老人离家四十里,说远也不算远,说近可也不近,要是青年人,赶一赶也可以在天黑赶到,老人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不想摸黑,也就准备多住这半天了。
吃过了午饭,住下来的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
老人回到西二排五号房间里,见和自己同住的三个青年,陪着四号一个人打扑克玩。
老人问:
“你们不上街去?
”一个青年回答说:
“你先去吧老爷爷!
我们过一会去!
”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便走出房间。
因为院里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走过四号门口,便得擦着三号的墙根走,他总觉着太不顺当。
他想:
“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
可是转到什么地方好呢?
”他蹲在四号门边来看空子,觉着只有转到石灰池的南边好一点,看准了,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
这一截木料是截去两头、中间留来的一段盘节,又粗又短又弯又扁,很不好转动。
老人很费了点气力才掀起来,转了一个过就又跌死了。
老人想找个帮手,敲了敲四号的门,四号的人都出去了,这才又回到五号来向那几个青年说:
“同志们!
你们帮一下,咱们把院里那两截木头转到一边让走路痛快点好不好?
”
“好!
我昨天还试了一下,没有转动了!
”一个青年答应着,放下手里的牌,其他三个也都同声答应看站起来往外走。
老人趁空子解了腰带脱下他的新棉袄来放在床上,就跟着走出来了。
老人和青年们一同去转动木料,一个青年拦住他说:
“你歇歇吧!
不够我们转!
”短短一截木头,四个人就护满了,老人插不上手,只好让他们转,而自己去搬动另一截。
青年们把那一截粗而短的转过去,回头看见老人搬动另一截,一个青年又拦住他说:
“老爷爷你歇歇吧!
这一截可以抬起来走!
”另一个青年就走过来和这个青年抬。
这一截比那一截长一点,可是一头粗一头细,抬细头的抬起来了,抬粗头的吃劲一托没有动,连声说:
“不行不行”就放了手。
抬细头的见他抬不起来,正要往下放,老人说:
“我来!
”说着弯下腰去两手托住,两腿摆成骑马架式,两肩一耸,利利落落抬起来。
起先来抬的那个青年,看着另外一个青年竖了竖大拇指头,然后两个人一齐抢过来接住说:
“老爷爷真行!
你上年纪了,还是我们来吧!
”
一个招待员提着茶壶来送水,见他们抬木料,忙说:
“谢谢你们!
我们来吧!
”“算不了什么!
”“在开会以前,我们只剩前三排院子没有赶上清理完,开会期间又顾不上做它,等明天早晨你们一走,我们几个人用不了两天就清理完了!
”陈秉正老人说:
“为什么要等到我们走了才做呢?
我们的会开完了,现在不是正好帮你们清理院子吗?
”招待员说“不便劳驾”,陈老人和青年们说“完全可以”,其他房间里还没有上街的同志们听见谈到帮助招待员清理院子,大家都从房间里走出来表示同意。
招待员见这情况,赶忙去问经理,大家不等他回来,就去找清理院子的工具。
前三排还没有清理,工具就放在东西排的院子里,被他们找来铁锹、扫帚、筐子、抬杆一大堆,马上就动起手来。
陈老人要抬筐子,大家看见他的长白胡须,说死说活不让他抬,他也只得拿起扫帚跟着大家扫院子。
劳模总是劳模,前三排没有走掉的人见西二排这样做,大家也都仿照着做起来。
不大一会,招待员把招待所经理找来了。
经理劝大家休息劝不下去,也就只好号召事务员、会计和每个招待员全体总动员和劳模们一齐参加劳动。
大家用铁锨拢着院里的残砖、破瓦、树皮、锯屑等类的零乱东西,陈老人跟在后边扫地。
老人从西二排院子的西南墙角落上扫起,面朝北一帚沿一帚排过来,扫到六号窗下,看见窗台上还有泥块、刨花,把扫帚伸上去,因为地方小扫不着,就放下扫帚用他那两只磨不破的手往下扒拉。
他又顺东看去,只见每个窗台上都有。
他沿着六号、五号、四号……把每一个窗台都先扒拉干净,然后返回西头来继续扫院子。
人多好做活,不过个把钟头就把六个院子都清理完了,垃圾都堆在大甬道的两旁,成材的东西都抬到存剩余材料的后门外,只等夜间有卡车来装载。
老人对这成绩欣赏了一阵,觉着这样一清理,走步路也痛快得多。
经理、事务员、会计、招待员们一齐给劳模打水洗手脸。
大家洗过之后有些人就上了街,陈老人重新穿起新棉袄,束住了腰,伸手去戴手套,才发现又把手套丢了。
他顺口问那几个青年说:
“你们打扫时候可见过一副手套吗?
”有一个答应说:
“没有见!
你放在哪里来?
”“放在四号门口的阶台上!
”另一个青年说:
“有来!
我们拢着拢着,看见一团刨花里好像有一只手套沾满了泥土。
我还当是谁扔了的一只破手套哩!
”“对!
可能是我把四号窗台上的刨花扒拉下来埋住了它,你们没有看见,给拢到泥土里去了!
”老人跑到甬道旁边的垃圾堆里来找,可是光西二排的垃圾就抬了几十筐,马上怎么会找到呢?
一个招待员看见了就问:
“老爷爷你找什么?
”“我的一副手套拢到这里边去了!
”“准在吗?
”“准在!
”“准在你上街逛去吧,我们给你找!
”“不要找它了吧!
手套给我没有多大用处!
”老人干脆放弃了。
老人逛了几道街,除看了看半年以前还没有的一些新建筑外,别的东西也无心多看。
他想:
“我也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净在这些店铺门口转什么?
”想到这里,也就回招待所来了。
他回到招待所,天还不黑,同房间的青年们都还没有回来。
一个招待员给他开了门,告他说手套找到’了。
他到房间里一看,静静的火炉子依旧很旺,招待员已经给他把手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搭在靠近火炉的一个椅背上,都快烘干了。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满红媳妇说:
“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
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
————————————————————————————————————————-
[转]“套不住的手”简析
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是一篇内容切实,文字朴素的短篇小说。
它通过一双闲不住的手的真切描绘,创造了勤劳质朴的陈秉正这样一个形象鲜明的人物。
全篇情节单纯,只是选择了日常劳动中的几个片断表达了一个重大的主题:
劳动是崇高而光荣的。
小说中的陈秉正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从年龄来说,他巳年过古稀,按通常惯例早就可以不参加主要劳动了,从经济情况来看,他的家庭收入在中国农村也较富裕,完全用不着他操心了。
“可是这老头儿身体特别强们共产主义劳动的深刻的美学意义”,写出了
“这个红色老人的共产主义高尚情操”(见一九六O年十二月十六日《广州日报>:
师东
《慈眼识英雄—读赵树理<套不住的手》书后>一文)。
这也许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共产主
义的“美学意义”和“高尚情操”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其特色是否仅指爱劳动这点,这还需作深入的研究。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陈策正老汉身上,巳经出现了全新的因素,这就是真心实意为集体,劳动巳成为自觉的习惯,例如买桑叉、带头在招待所劳动,当教练组长等等,这就决不是旧时代的个体农民所能做到的。
这种热爱集体、高度自觉的美德,是崇高的、可贵的、值得称颂的。
时间:
2021.02.02
创作:
欧阳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