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上海摩登与格调 读王安忆小说.docx
《文革时期的上海摩登与格调 读王安忆小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革时期的上海摩登与格调 读王安忆小说.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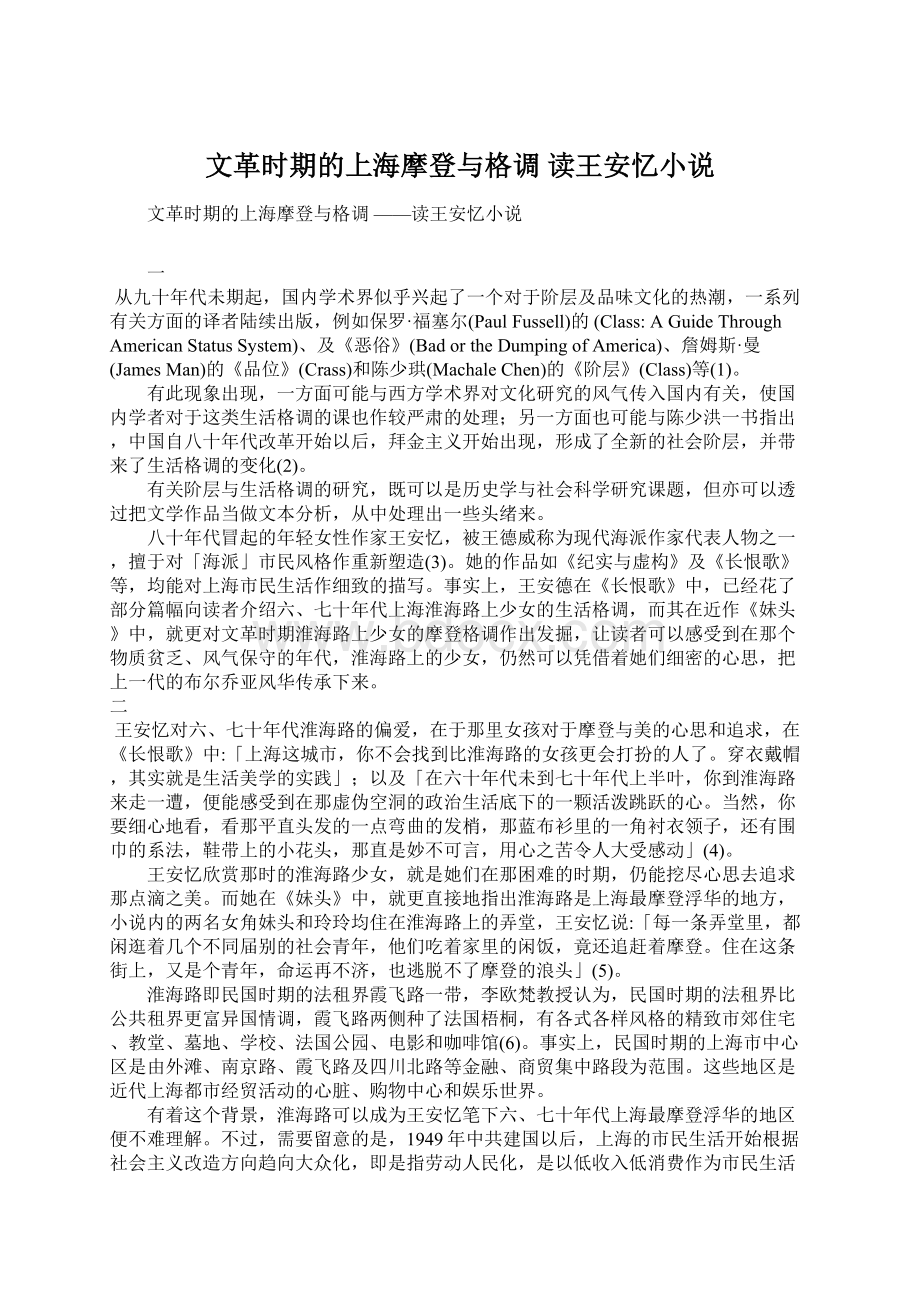
文革时期的上海摩登与格调读王安忆小说
文革时期的上海摩登与格调——读王安忆小说
一
从九十年代未期起,国内学术界似乎兴起了一个对于阶层及品味文化的热潮,一系列有关方面的译者陆续出版,例如保罗·福塞尔(PaulFussell)的(Class:
AGuideThroughAmericanStatusSystem)、及《恶俗》(BadortheDumpingofAmerica)、詹姆斯·曼(JamesMan)的《品位》(Crass)和陈少珙(MachaleChen)的《阶层》(Class)等
(1)。
有此现象出现,一方面可能与西方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风气传入国内有关,使国内学者对于这类生活格调的课也作较严肃的处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陈少洪一书指出,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始以后,拜金主义开始出现,形成了全新的社会阶层,并带来了生活格调的变化
(2)。
有关阶层与生活格调的研究,既可以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但亦可以透过把文学作品当做文本分析,从中处理出一些头绪来。
八十年代冒起的年轻女性作家王安忆,被王德威称为现代海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擅于对「海派」市民风格作重新塑造(3)。
她的作品如《纪实与虚构》及《长恨歌》等,均能对上海市民生活作细致的描写。
事实上,王安德在《长恨歌》中,已经花了部分篇幅向读者介绍六、七十年代上海淮海路上少女的生活格调,而其在近作《妹头》中,就更对文革时期淮海路上少女的摩登格调作出发掘,让读者可以感受到在那个物质贫乏、风气保守的年代,淮海路上的少女,仍然可以凭借着她们细密的心思,把上一代的布尔乔亚风华传承下来。
二
王安忆对六、七十年代淮海路的偏爱,在于那里女孩对于摩登与美的心思和追求,在《长恨歌》中:
「上海这城市,你不会找到比淮海路的女孩更会打扮的人了。
穿衣戴帽,其实就是生活美学的实践」;以及「在六十年代未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
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直是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4)。
王安忆欣赏那时的淮海路少女,就是她们在那困难的时期,仍能挖尽心思去追求那点滴之美。
而她在《妹头》中,就更直接地指出淮海路是上海最摩登浮华的地方,小说内的两名女角妹头和玲玲均住在淮海路上的弄堂,王安忆说:
「每一条弄堂里,都闲逛着几个不同届别的社会青年,他们吃着家里的闲饭,竟还追赶着摩登。
住在这条街上,又是个青年,命运再不济,也逃脱不了摩登的浪头」(5)。
淮海路即民国时期的法租界霞飞路一带,李欧梵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法租界比公共租界更富异国情调,霞飞路两侧种了法国梧桐,有各式各样风格的精致市郊住宅、教堂、墓地、学校、法国公园、电影和咖啡馆(6)。
事实上,民国时期的上海市中心区是由外滩、南京路、霞飞路及四川北路等金融、商贸集中路段为范围。
这些地区是近代上海都市经贸活动的心脏、购物中心和娱乐世界。
有着这个背景,淮海路可以成为王安忆笔下六、七十年代上海最摩登浮华的地区便不难理解。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上海的市民生活开始根据社会主义改造方向趋向大众化,即是指劳动人民化,是以低收入低消费作为市民生活。
至六十年代初因资源缺乏而形成上海市民的困难生活时期。
至七十年代未期开始改革开放后的上海社会逐步走向生活改善,上海人开始追求「吃好穿好」(8)。
但对于王安忆来说,六、七十年代的上海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却比文化大革命以后追求「吃好穿好」的上海来得有格调。
在《长恨歌》中,主角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成长于文革以后,王安忆对于那个年代的女孩,评价却低了很多:
「薇薇她们的时代,照王琦瑶看来,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读。
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
说是甚么都在恢复,甚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只可辨个依稀大概的」(9)。
王安忆所谓的「恢复」和「回来」,相信就是指昔日上海霞飞路(即淮海路)的摩登与繁华,不过,王安忆所见文革以后回来的却是虚有其表的摩登与繁华,因为,王安忆在《妹头》中就透过男角小白眼里的八、九十年代上海街头的少女模样来与六、七十年代的来相比,所见的都是令她失望的模样:
「现在,他走在熙攘的街道上,迎面而来,最触目的,是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
她们一律穿着最为时尚的衣着。
由于时尚,她们的面目彼此就是有些相像,而不是以往那样,每条马路的女孩子都有每条马路的风范」(10)。
看上来,王安忆似乎有点怀旧的倾向,总觉得新不如旧,七十年代未期以后,上海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人都可以追随潮流,倒使她觉得街头上每位少女的面貌有如复制一般,没有性格,亦失去了当年淮海路上摩登少女的风采。
王安忆有着如此感觉,主要是因为她在上海生活得太久,她对上海的观察,已经是从感性上出发,而不是从知性上着手,她在《寻找上海》一文中指出:
「现在生活却是如此的绵密,甚至是纠缠的,它渗透了我们的感官。
感性接纳了大量的散漫的细节,使人无法下手去整理、组织、归纳、得出结论,这就是生活得太近的障碍。
听凭外乡人评论上海,也觉得不对,却不知不对在那里。
它对于我们实在是太具体了,具体到有时候只是一种脸型,一种乡音,一种口味。
……脸型是感性最初摄取的印象,它直接为视觉接受。
而在略为成年以后,感官发育得更为深入,便被另一些较为抽象的事物所吸引。
这些事物,往往是含混的,模糊的形骸,边缘渗入在空气里,于是,这里和那里,就连成了一片,它们形成了一种叫氛围的东西」(11)。
王安忆所说的「氛围」,意思较为模糊,未能作出明确的了解,或许是她认为以前上海每条街的人都有着他们不同的生活格调,由于格调的不同,自然也形成了每条街的人都有着不同的面貌,以至是有着不同的气质。
事实上,王安忆是认为人的气质是需要经过培养出来的,而培养气质的方法,就需要由日常生活格调来培养的。
在这方面,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薇薇的面貌及气质作描写时,已道出了她在这方面的观点:
「薇薇称不上是好看,虽然继承了王琦瑶的眉眼,可那类眉眼是要有风韵和情味作底蕴,否则便是平淡无趣了。
而薇薇生长的那个年头,是最无法为人提供这两项的学习和培养」(12)。
薇薇出生于1961年,成长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如前所述。
王安忆认为那个年代成长的少女变得粗鲁了,亦是因为缺乏学习和培养风韵与情味机会的源故。
至于《妹头》中的女角妹头和玲玲则是成长于六十年代,在王安忆笔下,她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例如妹头,她自小便经常受到家人的责打,但这责打却使妹头学习了做中等人家的教养,这教养综合了仪表、审美、做人、持家、谋生、处世等经验和成规。
故妹头成长后便成为一个聪明、能干、有风度、又有人缘的小女人(13)。
妹头的相貌是瓜子口面、杏眼、薄唇、和尖下巴,王安忆指出:
「妹头的长相称得上完美,没甚么可挑的。
但妹头的好看不是风头很健的好看,因为缺少了一点光彩和气度,也是和她的聪明才智一样,在小圈子里算头挑。
不过,妹头好看不好看,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不人云亦云」(14)。
这正是因为妹头自小便受到中等阶层的生活学习与训练,建立了一套生活格调,故此能有自我的生活美学及办事能力,在整部《妹头》,王安忆在很多细节中都向读者介绍了妹头在这方面的能力。
这亦正是王安忆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格调,并不是后来上海的少女人人都像复制一样追赶潮流。
玲玲亦是在文革时期成长于淮海路,在那个时期,玲玲闲在家里没事干,便把心思全都花在打扮之上。
在文革未期的玲玲,在久经钻研之下,已经甚为懂得装扮之道。
文革未期,女性在服饰上的风气还很保守,但玲玲却是懂得在稳中求变,比如?
衣做成男式的领子,袖子的克褔比通常延长一倍,一列三个扣子,腰身窄长,衭子却较阔,还有灯芯绒外套以条纹组成图案,有些类似猎装(15)。
衣着当然是显现一个人个性和风韵的最佳途径,玲玲一身稳中求变的装扮,正好显出她是花过心思的,王安忆最爱看见的,就是这类淮海路上的女性。
同样地,在《妹头》中其中一个甚为值得留意的女角「七O届的拉三」同样是住在淮海路上的弄堂,她的外型是平肩、高腰、长腿的身型、面型似欧洲人、肤色偏深,总要穿紫红色调的衣服,是学校里的风头人物,在淮海路的弄堂里,七O届的拉三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但她的日常生活却能比其它人显得优雅,王安忆认为,淮海路上的少女总是有着能把浮华与家常调和起来的素养(16)。
继承着民国时期霞飞路上的摩登与浮华,六、七十年代的淮海路上少女仍然有着以往的风华,正如王安忆在<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一文中所说:
「这是我家弄堂前的淮海路上,特有的情景,所有的摩登一应都有落后腐朽的征兆。
这是一种亮丽的腐朽征兆,它显得既新又旧。
这些亮丽的男女,走过淮海路,似乎是去赶赴上个世纪的约」(17)。
如此看来,王安忆似乎很喜爱怀旧,在她眼中,淮海路上凡落后和腐朽都是亮丽。
但更有趣的是,王安忆是用落后腐朽来形容「摩登」这两个字。
李欧梵教授曾经说过:
「在风行一时的五四用语中,变得『摩登』首先意味着要变得『新』(18)。
在民国时期,最新的人和事都称为摩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些摩登已成为落后与腐朽,不过,王安忆却认为它仍然亮丽,这就是为何她喜爱怀旧的原因,亦是为何她特别喜爱淮海路的原因,因为在上海,只有淮海路才能把这些摩登停留下来。
三.
王安忆特别喜爱淮海路上的人(特别是女孩),就是因这些人与其它地区不同。
在《妹头》中。
王安忆就花了很多篇幅来比较淮海路与其它地区的女孩之间的分别。
妹头在毕业后,分配到一家中型国营羊毛衫厂里当质检工,她的师傅是一个美丽的苏北女人,肌肤丰腴,面若桃花。
不过,苏北人在民国时期早已被上海人歧视为次等居民,苏北人在上海人眼中一般都较穷、较蠢、操低贱的工作(19)。
妹头师傅虽然长得美,但到底都不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因此,她的行为与生活与妹头都不同。
就以饮食习惯为例,师傅吃的一律都是红烧的食物,上着浓浓的酱色,并且烧得烂熟,这与妹头家里吃惯清淡的食物有所不同。
师傅爱吃那类食物,也烧给妹头吃,虽然与妹头日常吃惯的不同,但因为妹头在羊毛衫厂经过体力劳动工作,出力出汗,这样厚味食物倒使她胃口大开,再加上是敬爱的师傅做的菜,所以妹头亦爱吃(20)。
虽然说到妹头亦爱上了吃那类厚味食物,但小说亦说出了妹头那类淮海路上的中等人家的饮食品味是较清淡,与出卖劳力阶层的人爱吃厚味食物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阶层与生活格调有着密切关系,淮海路上的中等人家,生活与其它地区自然不同,王安忆在《妹头》中,就有着与<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一文中类似的说法:
「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多少是有些旧式的。
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面,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在某一面上,甚至是相当封闭。
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
它们就是依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
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之后,淮海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就和这封闭有关」(21)。
就是有着这样的背景,妹头有很多地方都比师傅显得保守。
例如师傅在研究妹头乳房的大小与她有否和男性发生过关系等问题时,就令妹头感到非常羞窘;此外,师傅教妹头如何拿免费避孕药,但妹头却不肯干,最后还是由师傅替她拿(22)。
凡此种种,足可看见妹头在对于性这方面的态度比师傅保守得多。
师傅比妹头大胆开放,一方面可以说淮海路上的人比其它地区保守,另一方面也可了解作是师傅比她年长,生活经验丰富,故此对性方面的认识没有妹头般没头没脑,不过,当王安忆再写道妹头与姊姊薜雅琴时,就可以再一次看出妹头在这方面的保守一面。
薜雅琴是生活在曹家渡的女孩,她非常祟拜妹头,有如妹头的奴仆一般,就连她的男朋友都是妹头介绍的。
当薜雅琴有了男朋友阿川的骨肉时,向妹头求救,那时妹头对于男女之事已早有经历,但当好听到薜雅琴既内行又露骨地在她面前谈性事时,妹头仍不免红了脸(23)。
这些细节就显示了在王安忆笔下淮海路女孩与其它地区女孩的分别。
谈到妹头与薜雅琴的从属关系,主要是因为薜雅琴对淮海路的仰慕。
在王安忆笔下,薜雅琴的五官、身材,都称得上端正和均称,只是肤色有些焦黄,人就显得暗,而她的衣着较保守,并不像淮海路上的少女懂得从保守中寻突破。
因此,薜雅琴要追求摩登,就得向妹头学习,例如向妹头学习造衣服的方法,甚至是借她的衣服来穿(24)。
除了学习妹头的品味外,薜雅琴喜爱淮海路的生活更显现于她常在假日跑到妹头帮着做家务,及后当薜雅琴交上了阿川,就少到了妹头家做家务,不过,好只是改到阿川家,阿川与妹头是住在同一条弄堂的,亦是淮海路上的人(25)。
但更有趣的是,当薜雅琴嫁了阿川,搬到淮海路后,人也出现了转变,王安忆写道:
「在淮海路上生活了这些年,耳濡目染,不说学,熏也熏出来了。
她现在做了一个极短的发型,后面看起来完全是男式,但前面留了较长的额发,烫过后翻卷上去,特别配她的有梭有角的方脸型和大眼睛,有一种越剧小生的妩媚。
衣服呢,常是宽肩窄身,齐膝的一步裙。
看上去很正式,好象随时准备出席礼宾场合,也是和她形体相貌配合的。
她也学会了化妆,本来暗淡的肤色便焕发了。
总之,她看上去很亮,甚至有些过于艳丽了」。
王安忆花了很多文字来描写改变了的薜雅琴,不过,她始终不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因此,王安忆仍然很不客气地说薜雅琴「就稍稍乡气了一些」、「总是有一种」来形容她(26)。
从这些描写,就可以看出王安忆是如何把淮海路的中心性突显出来。
不过,淮海路在王安忆心目中的中心性也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转变。
事实上,王安忆是认为淮海路上的生活正因为是保守,才能把昔日霞飞路上的摩登停留下来。
但是伴随着淮海路上的摩登是因为六、七十年代的贫困物质生活背景,因为贫困,就需要更加花上心思才能达到摩登的效果。
而这种情况,就在七十年代未期开始转变。
文革未期,管制开始放松,淮海路上的摩登格调开始在这个时期出现转变。
王安忆在《妹头》中,写道阿川在这个时期经营服装生意,从南边购买廉价衣服到上海转售,王安忆在这段描述中,已铺排了形势的转变:
「这些来自南边的衣服,大都是轻薄透明的化纤尼龙质料,色彩鲜艳,镶着繁复的蕾丝,式样相当跨张,做工且十分粗糙。
它们散发出一股不是不洁净,也不是洁净的气味。
很暧昧不明的。
好象包含着一些来历,却又无从寻查,确证。
但是,这些衣服带来了一股开放的气息,它以它的粗鲁和新颖,冲击着这个城市的傲慢偏见,打破了成规」(27)。
从这短短的描述中,王安忆已经带出了七十年代未期开始冲击上海残留民国时期的摩登气息的根源之一,就是这一批批廉价而又粗糙的衣服。
怪不得王安忆会在《长恨歌》中说七十年代未期以后成长的上海少女是变得粗鲁了,故她说:
「如今满街的想穿好又没穿好的奇装异服,还不如文化革命中清一色的蓝布衫,单调是单调,至少还有点朴素的文雅」(28)。
不单是变得粗鲁,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个性,不像从前的每条街上的人均有不同面貌,王安忆在<服装一二三>一文中,就有着如此说法:
「如今的姹紫嫣红万种风流,也是磨灭个性,总归是花如海,人如潮,分不出个你我他」(29)。
就因为人人的面貌与装扮有如复制一样,故此,文革以后,淮海路作为上海的摩登中心地位亦随之而失去。
四.
王安忆爱怀旧,她所爱的正是昔日淮海路上残留的摩登(或许更可进一步说是民国霞飞路上的摩登),这些摩登,都是因为淮海路的人家的保守生活,再加上淮海路上女孩的点点心思得以留存下后。
不过,这一切却被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鲁莽地摧毁。
这新一代不再讲究心思,只是跟着潮流的趋势,一窝蜂的追上,淮海路上的女孩如是,其它地区的女孩亦如是,因此,文革以后,淮海路上的女孩已失去了昔日的摩登,昔日的格调,或许这就是「后摩登」(post-modern)了。
其实,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指出在五、六十年代有一类名为「老克腊」(OldColour)的人物,这类人物保持着昔日上海的旧时尚,以固守为激进。
但这类人物到了八十年代几乎已绝了迹,不过,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又悄悄地生长起一代年轻的老克腊,他们要比旧时代的老克腊更甘于寂寞,面目上也比较随和,不作哗众取宠之势(30)。
或许,王安忆就是当时其中一个老克腊,迷恋着昔日的繁华,亦透过小说把昔日的繁华梦重构出来。
阅读有关文革时期的社会史,大都只会看到当时负面的生活部分,但在黑暗与负面的背后,或许仍然寻找到一点格调的足迹,亦可能从中发掘出一些社会阶层(当时不是以财富来划分,而是以生活格调来划分)的迹象来。
而王安忆的小说,就可以给予我们一点的启发。
【注释】
(1)保罗·福塞尔着,梁丽真、乐涛、石涛译:
《格调:
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保罗·福塞尔着,何纵译:
《恶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詹姆斯·曼等着,李雨、力安编译:
《品位:
文明尺度与生存品位》,(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1999),陈少珙:
《阶层:
中国人的格调与阶层品味分析》,(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2)见陈少珙:
《阶层:
中国人的格调与阶层品味分析》,第一章。
(3)王德武:
<海派文学,又见传人-------王安忆的小说>,见氏着:
《如何现代,怎样文学?
------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1998),。
(4)王安忆:
《长恨歌》,(香港,天地,1996),;282。
(5)王安忆:
《妹头》,(海口,南海出版社,2000),。
(6)LeoOu-fanLee,ShanghaiModern:
TheFloweringofANewUrbanCultureinChina1930-1945,(Cambridge,Mass: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
(7)《上海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8)《上海通史》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8章。
(9)王安忆:
《长恨歌》,289。
(10)王安忆:
《妹头》,。
(11)王安忆:
<寻找上海>,收入《妹头》,p184及。
(12)王安忆:
《长恨歌》,。
(13)王安忆:
《妹头》,。
(14)王安忆:
《妹头》,pp17,18。
(15)王安忆:
《妹头》,及。
(16)王安忆:
《妹头》,。
(17)王安忆: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见《妹头》,。
(18)LeoOu-fan,"InSearchofModernity:
SomeReflectionsonaNewModeofConsciousnessinTwentieth-CenturyChineseHistoryandLiterature",inIdealAcrossCultures:
EssaysonChineseThoughtinHonorofBenjaminI.Schwartz,ed.PaulCohenandGoldman(Cambridge,Mass: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
(19)详可见EmilyHonig,CreatingChineseEthnicity:
SubeiPeopleinShanghai,1850-1980,(NewHe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2)。
(20)王安忆:
《妹头》,。
(21)王安忆:
《妹头》,、32。
(22)王安忆:
《妹头》,、、。
(23)王安忆:
《妹头》,。
(24)王安忆:
《妹头》,。
(25)王安忆:
《妹头》,,。
(26)王安忆:
《妹头》,,126。
(27)王安忆:
《妹头》,。
(28)王安忆:
《长恨歌》,。
(29)王安忆:
<服装一二三>,见氏着《重建象牙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30)王安忆:
《长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