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docx
《课外阅读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课外阅读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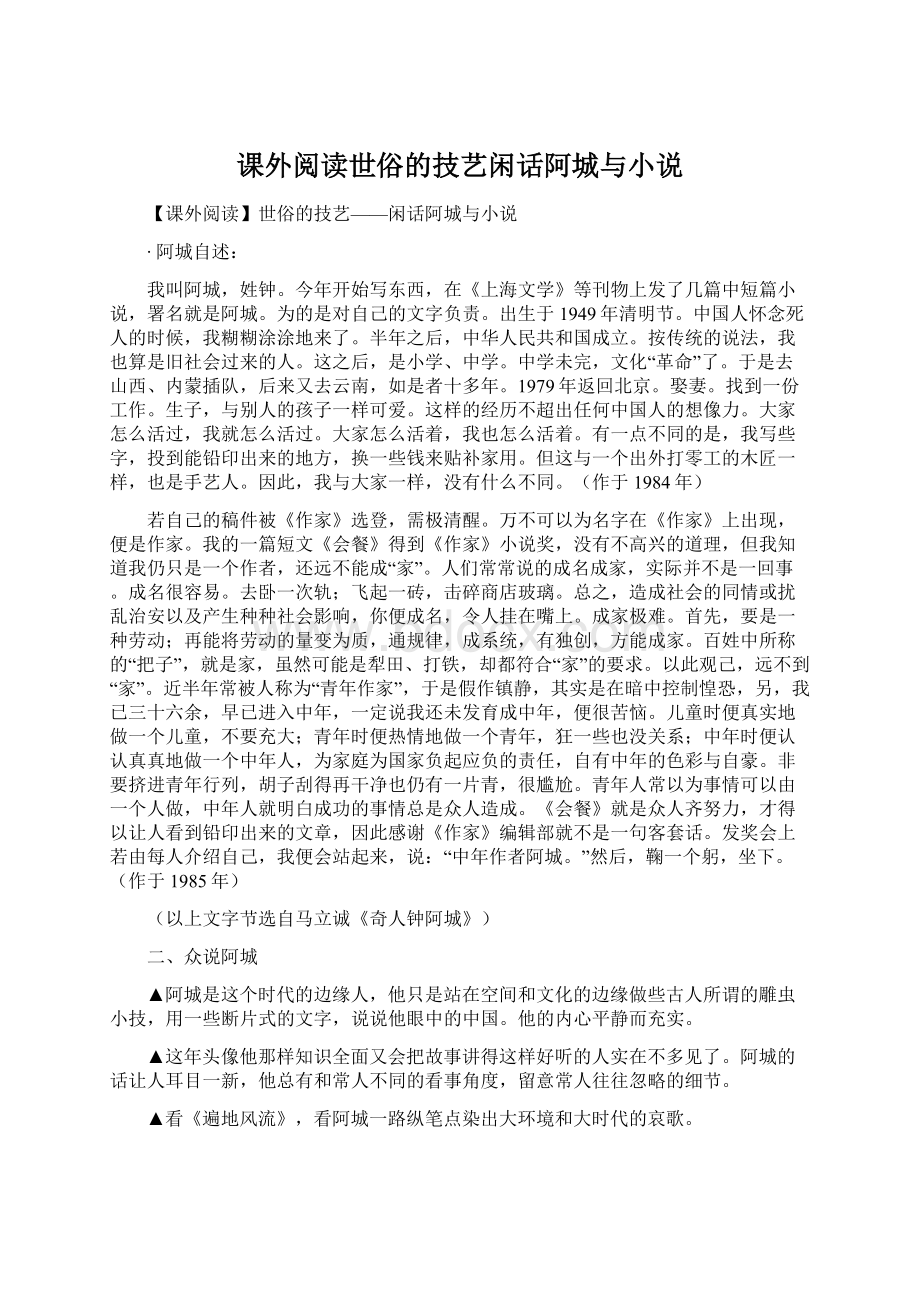
课外阅读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
【课外阅读】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
∙阿城自述:
我叫阿城,姓钟。
今年开始写东西,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了几篇中短篇小说,署名就是阿城。
为的是对自己的文字负责。
出生于1949年清明节。
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
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
这之后,是小学、中学。
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
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
1979年返回北京。
娶妻。
找到一份工作。
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
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像力。
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
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
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
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
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作于1984年)
若自己的稿件被《作家》选登,需极清醒。
万不可以为名字在《作家》上出现,便是作家。
我的一篇短文《会餐》得到《作家》小说奖,没有不高兴的道理,但我知道我仍只是一个作者,还远不能成“家”。
人们常常说的成名成家,实际并不是一回事。
成名很容易。
去卧一次轨;飞起一砖,击碎商店玻璃。
总之,造成社会的同情或扰乱治安以及产生种种社会影响,你便成名,令人挂在嘴上。
成家极难。
首先,要是一种劳动;再能将劳动的量变为质,通规律,成系统,有独创,方能成家。
百姓中所称的“把子”,就是家,虽然可能是犁田、打铁,却都符合“家”的要求。
以此观己,远不到“家”。
近半年常被人称为“青年作家”,于是假作镇静,其实是在暗中控制惶恐,另,我已三十六余,早已进入中年,一定说我还未发育成中年,便很苦恼。
儿童时便真实地做一个儿童,不要充大;青年时便热情地做一个青年,狂一些也没关系;中年时便认认真真地做一个中年人,为家庭为国家负起应负的责任,自有中年的色彩与自豪。
非要挤进青年行列,胡子刮得再干净也仍有一片青,很尴尬。
青年人常以为事情可以由一个人做,中年人就明白成功的事情总是众人造成。
《会餐》就是众人齐努力,才得以让人看到铅印出来的文章,因此感谢《作家》编辑部就不是一句客套话。
发奖会上若由每人介绍自己,我便会站起来,说:
“中年作者阿城。
”然后,鞠一个躬,坐下。
(作于1985年)
(以上文字节选自马立诚《奇人钟阿城》)
二、众说阿城
▲阿城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人,他只是站在空间和文化的边缘做些古人所谓的雕虫小技,用一些断片式的文字,说说他眼中的中国。
他的内心平静而充实。
▲这年头像他那样知识全面又会把故事讲得这样好听的人实在不多见了。
阿城的话让人耳目一新,他总有和常人不同的看事角度,留意常人往往忽略的细节。
▲看《遍地风流》,看阿城一路纵笔点染出大环境和大时代的哀歌。
▲也许是他为人一贯的随意,他喜欢随意,喜欢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感觉,喜欢一路的见意外之人遇意外之事,以丰足他那本已十分丰足的人生。
▲阿城是个想得明白也活得明白的人。
▲阿城的文字始终在奔跑,像几乎不带形容词的那部小说《棋王》。
这种奔跑并不忙乱,匀速行进,到了冲线的地方就双手一撒,然后我们就看见前方豁然开朗。
▲读阿城的随笔就如同坐在一个高高的山头上看山下的风景,城镇上空缭绕着淡淡的炊烟,街道上的红男绿女都变得很小,狗叫马嘶声也变得模模糊糊,你会暂时地忘掉人世间的纷乱争斗,即便想起来也会感到很淡漠。
▲陈凯歌曾说起他和阿城同在云南农场时的生后。
他说在那愿始森林里,他和阿城都用利斧砍倒过合抱在一起的大树,然后在旱季里点起漫山的大火。
“当几百年的生命嘶叫着化为灰烬,我们却在望着自己的握斧过后的血手笑,自豪地挺起胸膛。
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杀戮。
后来,我从树想到了人。
”陈凯歌参军以后,阿城还留在农场,一呆就是十一年。
陈凯歌钦服阿城极少谈起十一年间的生活,他说,“这有点像一些不愿挂出勋章的军人。
因为将亲历的战争换成闪闪的勋章,那光亮似乎是对艰难岁月的亵渎。
吃苦而不言苦,这大约是唯恐苦难蒙上时间的光环,严酷变成追怀的美梦,水在臆想中变成了酒,沾沾自喜中贻误了下一代。
血依然是血,水仍旧是水,这就是阿城在小说中做的。
但是他却口气平缓,只在呼吸之间便道出了真的性命和真的人生。
”
▲卡尔维诺在《为了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过轻逸、迅速、确切、易见、繁复这五个创作概念,中文作家中能做到这些的我看当首推阿城。
他几乎所有发表的文章我都找来看过,越翻越有趣。
阿城对自己早期的小说谦逊的很,常常自贬的一文不值。
"三王"中《棋王》最好,《孩子王》次之,《树王》再次之。
不过我也相当喜欢《孩子王》,而《遍地风流》中有些短篇本是不输“三王”,但有些败笔,盖因一个“腔”字。
∙阿诚简介:
原名钟阿城。
原籍四川江津,1949年生于北京。
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
1979年回北京。
1979年后,阿城曾协助父亲钟惦棐先生(著名导演)撰写《电影美学》。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到中国的《易经》、儒学、道家、禅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阿城在与父亲的切磋研讨、耳濡目染中,博古通今,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
1984年发表处女作《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7期),引起广泛关注,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据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记载,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
《棋王》所以惊世骇俗的,除了文字,还有他的哲学:
“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
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
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
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此后又有小说《树王》、《孩子王》相继问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
这些作品以及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寻根”的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使他成为当时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在海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90年代后定居美国,仍有不少杂感和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
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三王”——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随笔集《遍地风流》、《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
四、阿诚谈《遍地风流》:
当下好看的书不少,这本书翻开来,却是三十年前的事,实在令人犹豫要不要翻一本旧帐。
于是来作个自序,免得别人碍于情面说些好话,转过来读者鄙薄的是我。
《遍地风流》《彼时正年轻》,及《杂色》里的一些,是我在乡下时无事所写。
当时正年轻,真的是年轻,日间再累,一觉睡过来,又是一条好汉。
年轻气盛,年轻自然气盛元气足。
元气足,不免就狂。
年轻的时候狂起来还算好看,二十五岁以后再狂,没人理了。
孔子晚年有狂的时候,但他处的时代年轻。
文章是状态的流露,年轻的时候当然就流露出年轻的状态。
状态一过,就再也写不到了。
所以现在来改那时的文章,难下笔,越描越枯,不如不改。
状态原来是不可以欺负的,它任性之极,就是丑,也丑得有志气,不得不敬它。
年轻有一个自觉处,就是学生腔,文艺腔。
学生和文艺,都不讨厌,讨厌在套进腔里,以为有了腔就有了文艺。
我是中学时从《学生范文选》里觉得这一套的,当时气盛,认为文章不该这样写。
那文章应该怎样写呢?
不知道。
教的又不愿学,学校好像白上了。
我永远要感谢的是旧书店。
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便宜,但还是没有一本买得起,就站着看。
我想我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我与我的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
有了这个构成启蒙,心里才有点底。
心里有底就会痒,上手一写,又泄气了。
我就是带着这种又痒又泄气的状态去插队的。
先是去山西雁北,同去者有黄其煦、龚继遂等五六个人。
黄基煦是我的小学同学,又是邻居,龚继遂则是一起去时认识的,这两个朋友现在都在美国而有成就。
在桑乾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里先来的是北京男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的知青,算得是北京中学里的精英吧。
不过让我受益的是一个叫来运的高三学生,面容很像关云长,少言。
离开山西前请教于他,他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是刺”。
这个意思我受用到现在。
继之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同去的还是黄、龚等人,不过这次还有章立凡、刑红远、李恒久等十来个人。
章立凡身长高大,面如脂玉,观之正是所谓玉树临风,我父亲有一次从干校回家碰到立凡,将我叫到另外的屋里问“哪里冒出来的”,一脸的又惧又喜。
再去的就是云南了。
这次朋友中只有黄其煦,其他则是新朋友孙良华、杨铁刚、张刚。
我在这里写到昔日的青春同路人,想想当时都才十多岁,额头都是透明放光的。
在云南一呆就是十年,北京来的朋友们陆续回去北京。
我因为父亲的问题,连个昆明艺校都考不进去,大学恢复高考,亦不动心,闲时写写画画。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过世,四月,我在外国电台里听到“四五”的消息。
每日还是上山干活,风雨如故,地老天荒。
六月,唐山大地震,我探亲回北京,火车进站,一个工人一路摇着一柄锤敲打车轮,忽听得他不知为何大骂“我他姥姥的”,很多年没有听到如此纯正的乡音了。
九月,毛泽东过世,当天街巷皆有肃杀之气,我替父亲送点东西到前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先生家去,在巷口见他坐在矮凳上如老僧入定,说是居委会命他在此观察阶级敌人的活动,我说您自己不就是阶级敌人吗?
老人不出声音地笑到眼泪流出来。
回云南到昆明的时候,正遇上王张江姚所谓“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激动。
我在朋友家借宿,坐下来写《宠物》,写好了看看,再一次明确文学这件事情真不是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我习惯写短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是怕忘,反而现在不怕忘了。
忘了的东西一定是记不住的东西,这是废话,不过废话若由经验得来,就有废话的用处。
看消息说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三十周年,有要纪念的意思。
不过依我的经验,青春这件事,多的是恶。
这种恶,来源于青春的盲目。
盲目的恶,即本能的发散,好像老鼠的啃东西,好像猫发情时的搅扰,受扰者皆会有怒气。
如果有所谓“知青文学”,应该是青春文学的一类,若是这样,知青这个类,也只有芒克的《野事》一部写得恰当吧。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所谓“知青文学”,多是无奈,无奈是中年以后的事,与青春不搭边。
再往回看到一九四九年,一路来竟无一篇与青春有关,只是些年轻时与政治意义的关系,与政治意义无关的青春,是不能入小说的,“知青小说”的致命伤,也在于此。
而青春小说在中国,恕我直言,大概只有王朔的一篇《动物凶猛》,光是题目就已经够了。
青春难写,还在于写者要成熟到能感觉感觉。
理会到感觉,写出来的不是感觉,而是理会。
感觉到感觉,写出来才会是感觉。
这个意思不玄,只是难理会得。
编集旧东西,头皮要硬一些,硬着头皮才能将一些现在看来脸红的东西集在一起送去出版。
(以上文字节选自阿城《<遍地风流>和我的经历》)
五、《棋王》与“寻根文学”:
阿城原是一位画家,在1984年首次发表文学作品,处女作就是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的中篇小说《棋王》。
这部作品和阿城随后一气写下的《孩子王》、《树王》皆取材于他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无论在主题意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与通常的知青小说有很大不同。
阿城无意去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也避免了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风格模式,他在日常化的平和叙说中,传达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
《棋王》的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
这是一个在历史旋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这使他虽以一己的单薄存在,却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顽强精神和文化魅力。
小说中写王一生天性柔弱,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像他这种小人物好比狂风中的沙粒,要在不能自主的命运中获得意义和价值,唯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心,寻求自身精神的平衡和充实。
小说从知青离城的送别写起,首先就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之句来映衬王一生独坐一旁的内心宁静,而后通过写他对于“吃”的高度重视,暗示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在他那种处世不惊、怡然自得的性格刻画中,已经悄悄拉开了这个人物与时代规范下的知青形象的距离,成为知青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
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对他痴迷于棋道的描绘。
王一生从小竿迷恋下象棋,但把棋道与传统文化沟通,还是起因于一位神秘的拾垃圾的老头传授给他道家文化的精髓要义,这便是阴阳之气相游相交,“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
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
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
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
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
无为即是道……”这里讲的都是下棋的要领,但同时也是讲万事万物的造化之道,王一生以生命的本能领悟了这些道理,把棋道和人格融为一体,此后他的人生变成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
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却能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
小说中对王一生独特个性的描绘便集中在这个方面:
他看似阴柔孱弱,其实是在无所作为中静静地积蓄了内在的力量,一旦需要他有所作为时,内力鹊起,阴极而阳复,他便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
这仍体现在他的棋艺上,最突出的表现是王一生在同九个高手之间的“车轮大战”中,把全部潜能都发挥出来,取得大胜,作品中对这一场赴的描绘是极动人的: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
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
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在这九局连环大战中,王一生的生命之光和盘托出,与茫茫宇宙气息相贯通,实现了人格力量的充分展示,也完成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
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
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和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
但作家没有直接讲述这些“道理”,而是将其隐没于饶有风趣的故事和生动的艺术描写里而不彰。
这正是《棋王》作为“寻根文学”作品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以上文字节选自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
六、世俗的技艺
阿城生而有幸,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不幸的是,阿城的出身有欠纯正。
他的父亲钟惦棐是著名影人,因为执著一己艺术信念,早在50年代的运动中,即已中箭下马。
如阿城自谓,在他成长的年月里,早已体会因身份有别,前途殊异的道理。
文革期间,不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喽啰也沾不上边。
一俟“上山下乡”的口号展开,他早早打好行李,准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先去雁北,再到内蒙,最后落户云南,一待就是十年。
“四人帮”倒台后,各地知青摩拳擦掌,纷纷争取深造的机会,而阿城无动于衷。
原因无他,家庭背景有以致之。
然而十几年辗转南北,深入村野的经验,早已教给阿城太多学校以外的知识。
他逆来顺受,与其说是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因素,长怀自知之明,更不如说民间的一切让他了解到,生命驳杂的层面,有待更多的担待与包容。
他的“三王”作品写知青下乡,没有公子落难式的酸气,也不刻意夸张青春无悔式的天真。
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用心,这一姿态,似远实近,是阿城写作的一大特色。
更重要的是,阿城作品对世态人生的扫描,展现前所鲜见的大陆众生相,《棋王》中的拾荒老者,真人不露相,竟然深怀绝技。
《树王》中的萧疙瘩,舍身护树,令人肃然起敬。
《孩子王》中的山村男女,一颦一笑,如此质朴无文,而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开启了“文革”绝境中的一线生机。
礼失求诸野,阿城向往一种市井甚或山野文化,以作为对正统的批判,甚或对正统的救赎。
阿城笔下的系列人物,寒碜丑怪,但正是在这些畸人丑人里,阿城参看乱世中的生存智慧,颇有所得。
难怪“三王”小说一出,众家读者如获至宝,或曰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或曰禅道香火,劫后重生,好不热闹。
我以为阿城“三王”时期的作品,善则善矣,但仍然未脱微言大义的框架。
较之文革后的文学,他当然已走得太远,但比较《遍地风流》的作品,尤其“杂色”中诸篇,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转变。
如果“三王”小说仍执着“礼失求诸野”的乌托邦怀想,《遍地风流》所要标记的,应是“礼不下庶人”。
庶人所充斥的世俗社会,熙来攘往,啼笑之外,更多的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与平庸。
然而阿城看出其中自有一股生命力。
往好了说,这生命力是一股顽强的元气,总已蠢蠢欲动,饮食男女,莫不始于此。
但另一方面,这生命力也是一种坚韧的习气,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且战且走的日常生活策略。
阿城希望多写世俗社会中的元气,但笔下的人物每多显露得过且过的习气,两者都是生命力的表现,但所透露的差距何其之大。
这是阿城作品的尴尬所在,也是他的(有意无意泄露的)历史感所在。
阿城世俗观最系统化的呈现,是在他《闲话闲说》及《威尼斯日记》二书中。
前者收纳阿城1987年至1993年漫谈中国文化与小说的心得,后者则是他的世俗观的身体力行。
从甲骨文、老子、孔子到《教坊记》、《太平广记》、《武林旧事》,从散曲话本《金瓶》、《红楼》到张爱玲、王安忆。
千言万语,阿城的世俗可以归纳到一个“自为的空间”。
这是一个浮世的空间,容得下男耕女织,可想也难清除男盗女娼;这也是一个花样百出的空间,“就是活生生的多重实在,岂是好坏兴亡所能剔分的。
”而在《威尼斯日记》里,这一空间更可以是异国的、驿动的。
阿城认为世俗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总为礼乐教化提供额外的出路。
我以为这一自为的世俗空间,与其说是结结实实的存在,更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两者之间有相辅相成的时候,也有格格不入的时候。
阿城游走其间,未必完全说得清他的意向。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市井的匹夫匹妇也许充实了世俗的声光色相,但观察世俗并且指认其中的境界者,总少不了艺术工作者——或更广义的“生活家”——的慧眼与中介。
阿城于此,应有当仁不让的信念。
而他也必然得要面对其中的吊诡:
过分抬举世俗难免有刻意求工之嫌,过分牵就世俗也可能导致沆瀣一气的可能[6]。
于是他提出了“观”世俗的必要与限制。
世俗“其实是无观的自在”,总是超出观者的预料[7]。
但“观者”的存在又是体现世俗的要径。
如何静静旁观,而不制造世俗的大观奇观,是阿城的用心所在。
阿城小说的文字平淡隽永,即使偶见机锋,也是点到为止,决不强作解人。
“三王”小说中最动人的片段往往在于描写最委琐的生命时刻。
像《棋王》中写王一生的吃相,早为读者津津乐道;《孩子王》中的教学场景,娓娓述来,自是活生生的启蒙新解。
同样的乱世浮生,阿城与多数作家不同,总能别有所见,这些现象或是灵光乍现,或是荒谬突兀、或仅仅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即景,一经点染,立刻生动起来。
阿城抒情的极致处,不只在于容纳世俗欲望的千奇百怪,也更及于生命最凶险无情的时刻。
早期的“三王”系列,各以“文革”中一种艰难处境为着眼点。
知青下放的苦中作乐,山野村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卫树行动,或穷乡僻壤的朗朗书声,都是在现实环境的死角,化不可能为可能。
在《遍地风流》里,阿城更进一步直视他的素材。
《大门》里的红卫兵,肆意破坏一座古庙,好不得意;一年后“重回旧地,赫然发现一座庙门矗立在平野上,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块瓦一根木丝都不见了,只剩下这门,这个贴了封条的门”。
黄河边上的小村,莽莽天地间,惟有一门矗立。
这门开向文明的一晌繁华,还是文明的骤然劫毁?
《夜路》里的知青以不怕鬼出名,还因此得到女伴青睐。
未料女伴突然死去,知青自愿为她守尸。
“天气热,尸体就胀,先是大肠发酵,肚子凸得像怀胎十月……天黑后,凉下来,腹中气流窜,肚子里吱吱乱响,气出喉管,(死者)就发出呻吟,好像还活着忍受病痛。
”《火葬》里的干部暴毙,知青奉命烧尸,不得其法,死人“肚子爆了,油泼到知青的脸上,温温的”。
之后他们就着火堆,“花生黄豆慢慢的烤吃”。
花生黄豆原是用来助长火势,加速烧尸用的。
这真是些令人无言以对的时刻。
阿城写来俨然写来无动于衷。
我们不禁要问,在什么意义下,这样的情境也堪称抒情?
传统抒情文学讲究温柔敦厚、情景交融。
阿城却似乎要说在那些混沌岁月里,那里容得下这样的闲情逸致?
惟有出入粗鄙的丑陋的角色,而且仍能参得其“情”,才是真正的情景交融。
阿城的小说读来如行云流水,仿佛不着一力,细看则颇有讲究。
修辞遣字,是得实实在在造就出来的。
阿城对文字风格的要求,可以见诸《闲话闲说》中的篇章。
他对世俗文类如戏曲、小说的重视,对常情常理的刻画,已经可见尺度所在。
他又最忌小说有“腔”,不论是寻根腔或伤痕腔都“引人发怵”,而在散文集《威尼斯日记》中他写道:
“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
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
”作文章与做人,对阿城而言,都要懂得大巧若拙的道理。
这里的“巧”不意为机巧,而更近于技能。
与以往抒情美学言为心声、诚中形外的说法,这似乎有些距离。
但我以为阿城另有看法,他的自况身世,颇有“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感慨。
生活的历练,使他必须经营所能,趋吉避凶。
文章故为千古之事,但到底是种技艺,有它实在的因缘。
从阿城的立场来看,写作作为一种文字手艺,应与世俗的其他技艺等量齐观。
“三王”中的《棋王》是最明显的例子。
知青下乡学习,原是一个宏大的教育/政治策略。
然而深怀绝技的拾荒老人的出现,恰恰与国家鼓吹的政教体系唱出反调。
老人的棋艺旷世难逢,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是个捡破烂的。
以往对《棋王》的评论多朝它的博大精深发展,我独以为阿城的用心是在棋艺之为小道、之为易学难精却又无用的技能。
《树王》中的萧疙瘩以身殉树,不为别的宏观道理,只为他“知道”国家的自然政策。
而《孩子王》中的学生,从最简单的文字开蒙,大地洪荒,于是重有了意义,这意义却与上面交待的任务多么不同。
在《遍地风流》中,我们更可看到阿城对技艺的好奇与敬重。
他明白其中有一套庞大驳杂的知识体系,与正统格格不入。
他写抻面条师傅如何的不忘旧恩(《抻面》);跑江湖的老来如何说明“江湖”的要义(《江湖》);做豆腐的如何靠着豆腐手艺与民国史共相始末(《豆腐》);修补鞋的如何历经革命后仍然技痒难耐(《补鞋》)。
《纵火》里的吴顺德别无所好,只会搜集人家看不起的东西,“文革”来了,他为了一张有青天白日国徽的月份牌坐立难安,最后一把火烧了所有家当。
《唱片》里的赵衡生原来醉心京剧唱片,文革中搬运抄家物品,三搬两弄居然成了唱机专家,更不可思议的,你抄我捡,他对西洋音乐听出了门道。
《提琴》中的老侯原来是个乡下木匠,因缘际会,学会了为洋人修乐器。
文革中老侯可巧瞧见了他曾修过的一提琴,“琴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浆糊刷大字报。
”
对阿城而言,这些技艺妙手偶得,适足说明人间生活形式的自觉追求。
雕虫小技,却使得生命在粗糙中得细致,无明中见光彩。
也正因其没有实际的有效性,这类技艺为大叙述所忽视。
记录这些技艺的得与失,阿城很愿意看作是小说家的本份吧。
然而面对革命、国家、现代化大潮下的各种机械运作,techne注定即生即灭。
而阿城所作的,是遥想,搜集以往所闻所见的奇能异技;小说本身正是世俗技艺的传播者、集大成者。
阿城的惜墨如金到底要让我们觉得若有所失。
从上一本《棋王》在台湾问世,十五年已经过去了。
《遍地风流》的多数作品也是成于阿城序中所记“彼时正年轻”的日子。
阿城为何对写作如此散淡?
是见好就收,还是因为“世俗”左右,另有寄托?
还是蓄养元气,徐图大举?
这些年他的注意力早已转移到其他艺术媒体上。
在新世纪读阿城的作品,不禁使我们惊觉,好的文艺构想、创造,并不与时并进,日新又新。
文明高潮的转折,世俗智慧的隐现,也都不是如此。
也许对阿城而言,小说之为技艺,正有其该撒手就得撒手的时候吧?
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年他成名作的《棋王》。
身怀奇技的棋王不必总以绝招行走天下。
凭着拾荒者的身份,他人弃我捡,眼光八方。
他的绝技藏而不用,可能就此失传,但也可能一俟机会到了,才得传给有缘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