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docx
《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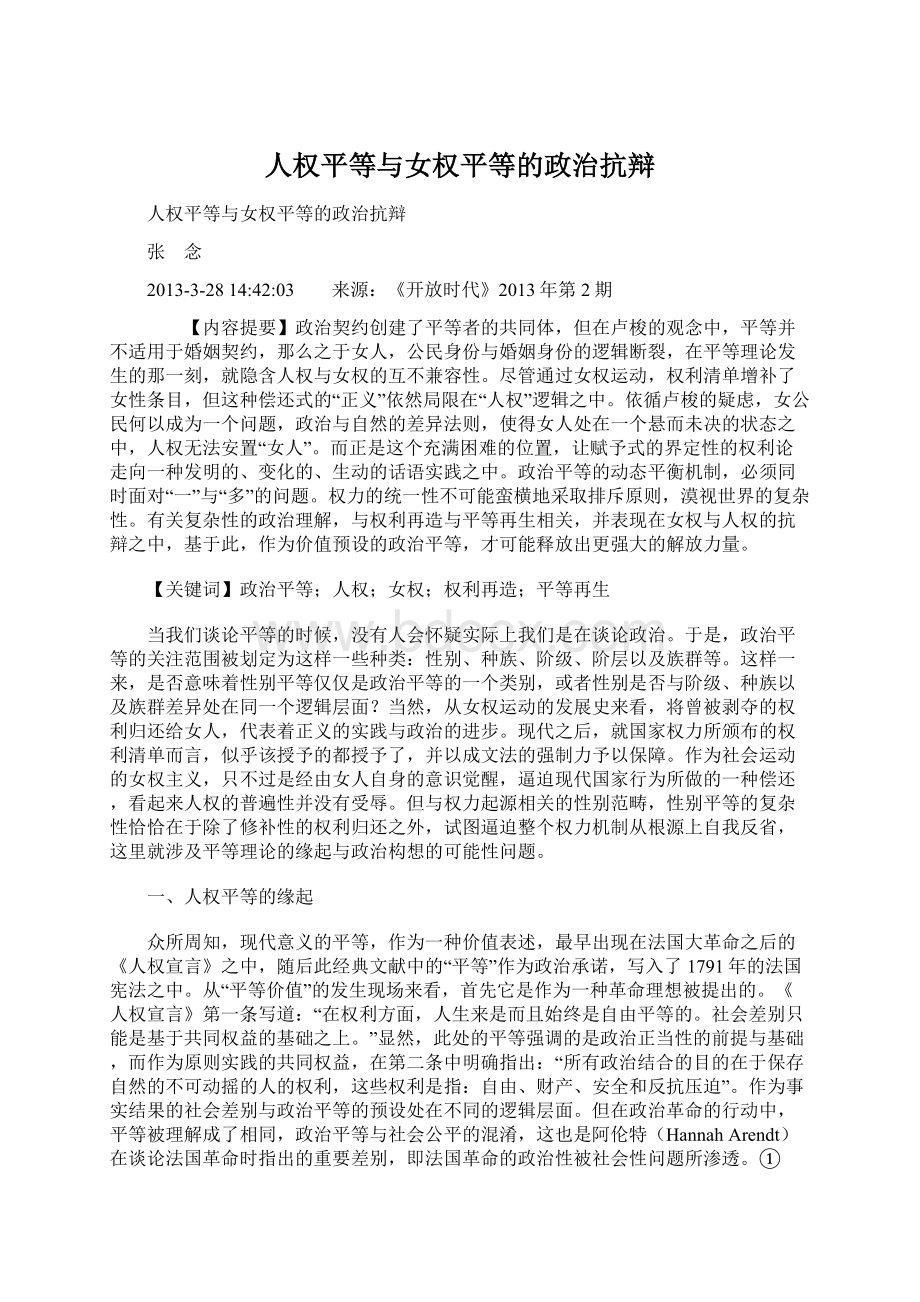
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人权平等与女权平等的政治抗辩
张 念
2013-3-2814:
42:
03 来源:
《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
【内容提要】政治契约创建了平等者的共同体,但在卢梭的观念中,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那么之于女人,公民身份与婚姻身份的逻辑断裂,在平等理论发生的那一刻,就隐含人权与女权的互不兼容性。
尽管通过女权运动,权利清单增补了女性条目,但这种偿还式的“正义”依然局限在“人权”逻辑之中。
依循卢梭的疑虑,女公民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政治与自然的差异法则,使得女人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之中,人权无法安置“女人”。
而正是这个充满困难的位置,让赋予式的界定性的权利论走向一种发明的、变化的、生动的话语实践之中。
政治平等的动态平衡机制,必须同时面对“一”与“多”的问题。
权力的统一性不可能蛮横地采取排斥原则,漠视世界的复杂性。
有关复杂性的政治理解,与权利再造与平等再生相关,并表现在女权与人权的抗辩之中,基于此,作为价值预设的政治平等,才可能释放出更强大的解放力量。
【关键词】政治平等;人权;女权;权利再造;平等再生
当我们谈论平等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政治。
于是,政治平等的关注范围被划定为这样一些种类:
性别、种族、阶级、阶层以及族群等。
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性别平等仅仅是政治平等的一个类别,或者性别是否与阶级、种族以及族群差异处在同一个逻辑层面?
当然,从女权运动的发展史来看,将曾被剥夺的权利归还给女人,代表着正义的实践与政治的进步。
现代之后,就国家权力所颁布的权利清单而言,似乎该授予的都授予了,并以成文法的强制力予以保障。
作为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只不过是经由女人自身的意识觉醒,逼迫现代国家行为所做的一种偿还,看起来人权的普遍性并没有受辱。
但与权力起源相关的性别范畴,性别平等的复杂性恰恰在于除了修补性的权利归还之外,试图逼迫整个权力机制从根源上自我反省,这里就涉及平等理论的缘起与政治构想的可能性问题。
一、人权平等的缘起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表述,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人权宣言》之中,随后此经典文献中的“平等”作为政治承诺,写入了1791年的法国宪法之中。
从“平等价值”的发生现场来看,首先它是作为一种革命理想被提出的。
《人权宣言》第一条写道:
“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社会差别只能是基于共同权益的基础之上。
”显然,此处的平等强调的是政治正当性的前提与基础,而作为原则实践的共同权益,在第二条中明确指出:
“所有政治结合的目的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动摇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指:
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作为事实结果的社会差别与政治平等的预设处在不同的逻辑层面。
但在政治革命的行动中,平等被理解成了相同,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混淆,这也是阿伦特(HannahArendt)在谈论法国革命时指出的重要差别,即法国革命的政治性被社会性问题所渗透。
①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开篇就指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不平等:
一种是自然的,比如力量和智力;一种是政治的,从约定而来的特权,是人为的。
②在此,先天的不同被卢梭理解为不平等,但这不是导致人之不幸的理由,而是政治的不平等妨碍了人的幸福。
人本来是生而平等的,自从私有制出现之后,不平等造成了这一自然事物的腐败。
需要注意的是卢梭无意废除私有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应该以平等的政治权利来限制私有的扩展,即平等意味着人根据国家意志所拥有的部分应该得到保护,从而可以克服先天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这就是说人总该拥有点什么,才是其权利平等的终极保障。
③卢梭的这一思想在《人权宣言》中有保留地得到继承,政治平等意味着平等自由地享有各项权利,而卢梭思想中混沌浪漫的“自然状况”被“社会差别”所修正。
政治平等与社会公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础和根据,后者是平等的事实与实践。
两者关涉的对象也不同,《社会契约论》旨在回答如何创建政治平等的基础,人们重新立约,推举公共权力。
在这一政治创建行动中,关涉的是立法、立法者、公共意志、个人意志以及被称为“人民”的政治集体。
在社会公平还没有到来之前,人们还需为政治平等的奠基,做出哪些艰苦的工作,去平等地赋予共同体成员以相同的权利,比如私有权的裁定,而至于贫穷与富有的差异,是基于这个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差异,是可容忍的,与平等与否没有关系。
这里存在一种有关平等的循环式论证:
赋予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权利,那么政治平等的内涵就是全体成员享有同等权利,而这个共同体就等于平等者的共同体。
这个由平等者所构成的共同体,实际上也造就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即任何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他们按照契约结盟、合作以及竞争。
契约论不仅回答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意味着立约行动是现代人格的发生现场,而独立个体与立约资格相辅相成,进而可见,赋权的对象正是这个公民个体,在理论上立约的发生先于赋权。
但是,我们发现人权平等并不适用于婚姻契约的状况,平等者的共同体因为性别而丧失其逻辑一致性。
卢梭在其另一部著作《爱弥尔》中认为,作为公民个体的女人并不存在,女人是通过对男人的服从,来践行个体公民对公共权力的维护。
就是说如何鉴定女人的政治属性,不能根据其公民身份,而是勘察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作为,她是否在自然基础之上维持着家庭的合理秩序。
④这样一来,公民个体就成了男性公民个体,而成为一个女公民,不是与社会一道从自然状态走向道德状态,之于女人,自然状态就等于道德状态。
这里的矛盾在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告诉我们的是追求平等的自然依据,并且卢梭还明确指出自然状态中,不存在女人之于男人的服从问题,而婚姻的出现则是一种转变,可见婚姻并非天然,那么婚姻契约与共同体的政治契约,就摆脱自然状况而言,两者都应该算是一种政治行为。
因为婚姻契约所形成的微型共同体,同样要处理的是两个个体结盟之后,其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可在《爱弥尔》中,卢梭提出婚姻是一种基于习俗的自然基础,那么,到底何为自然?
契约论缔造的难道仅仅是男性公民个体?
显然,女人还滞留在自然状态,但卢梭又提到,原始自然状态中没有谁服从谁的问题,那么“女人”是如何显现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女人问题”是伴随着政治现象而出现的,这也正是卢梭犹疑不定之处:
婚姻到底是自然的还是政治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篇,自然而然地将城邦的权力原型确认为家庭,即父权制。
如果说政治权力的原型是家庭,那么女权主义理论更关心的正是这原型的原型,即父权制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吉尔·罗宾(GeyleS.Rubin)认为:
外婚制伴随着针对女人的交换行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一般的剩余产品的交换。
而另一位女权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认为:
因为“女人”能产出生命,正是这种不同于物质生产的生产行为,其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异性婚制,而外婚制则是其性命攸关的政治配套。
⑤这样一来,性行为本身或者说异性性欲取向,即自然交配行为首先需满足于人类自身生产的目的,从而将这种带有目的性的异性婚制强化为对偶性的一男一女,然后才是女人的外嫁。
性别之别,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生理层面,其实并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
当我们说“性别”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明确其重要的含义,即人类必须先安排好自身的有关生殖活动的生产/权力制度,才有可能在交换女人的行为中,不断积累、沉淀并解析出其政治价值。
与原始时期就出现的奴隶交易不同的是,能够“生产”的女人无疑成了原始政治生命体的生产工具,就是女人不仅仅在产出生命,她还产出了政治关系,即基于联姻的政治联盟。
而她生产出的个体则作为政治构成的实在因素,即家庭成员的政治属性隶属于父权制,在此,这才有点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者,其劳动产品并不归她所有。
这在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解释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部落联盟之外的、缔约双方的第三类存在。
⑥
因此,“男人”这个概念如城邦的正义的整全性,是不可分的,但他们掌控并实施着划分的权力。
就两个部落而言,他们可以互为他者,于是我们发现建立在部落中心意义上的朦胧主体性意识,在主体与他者之间,才可找到女人的位置。
“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这个“她”什么都不是的同时,可以是任何东西,既是妻子、女儿、母亲,同时也与物件、贝壳以及牲畜类似,她们与它们共属于交换的客体。
在此我们依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路径就会发现,政治学中有关人/男人的定义之中,“女人”成了悬而未决的第三方,或者在场的缺席者。
《人权宣言》的法文全称是《人与公民权利的宣言》,此处,“人”与“公民”两个词的并列说明了什么?
人与公民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人在定义公民还是相反,人与公民之间的空隙暗示着什么?
可见,是“公民权”在扩展人之为人的普遍性,但公民权仅仅是在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规定人的平等状况,而在这个关系之外,平等一定会遭遇现实差异,激发并提升人们对于差异的敏感度,进而让权利与体验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更为幽微曲折的关系中去构造新的权利形象。
公民权之于人,并非是饱和与对等的,公民权是在人的现实状况中得到理解的,即,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践行公民权,并获得一种肯定的陈述,“生而平等”的天赋之权仅仅是一种预设和指令。
因此,从人权奠基而来的政治平等,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似乎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保证。
更进一步,当我们说平等的时候,实际是在根据人的自我完善性来想象生命的理想状态,而政治范畴之下的权利平等,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得到确认的,就是说在国家的眼里,所有的公民在权利层面都被同等对待,而其实践则体现在立法与司法行为中。
因此,人权平等只是针对抽象的全体公民,而对这个共同体的构成性问题予以悬置,并将生活世界的差异性排除在外,确立现代人格的第一原则,这就是公民身份。
女权平等恰恰是从这里出发,平等不是逻辑的终点而是起点,去诘问“人权”说的“人”是如何构成的,当我们说出“人”这个概念的时候,非人的存在是指哪些,因为“人”的总体性定义不可能自我指正,这个概念一定是在差异、关系与转换中被构造的,人权逻辑的辩证性就在于人的生成总是处在非确定性的绝境之中。
由此,“人”的概念不可能是一个封闭性的陈述,在卢梭那里,他必须借助一种自然人的自然状态来界定政治人,即从自然状态过渡到道德状态的“人”,保留了什么,并增添了什么,这个增添的部分就是国家意识及共同体的诞生。
于是人的自由不再是野蛮状态下,今天睡在这个树上,明天睡在另一棵树上的自由,而是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这种自由一定不是放任的结果,恰恰是理性指导之下的行为总和,这使得平等自由既具有自然正当性,而同时具有共同体所赋予的合法性,于是平等理念在其诞生的理论现场,就已经是在差异之中被构造出来的,就是说人来自自然但又不同于自然。
可见,人权叙事本身就是构造性的产物,作为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人权是在实践理性层面,将经验的多样性统一在抽象的平等形式之中,因此对于人权概念的再造与扩展在理论上就具有可行性。
人权作为中介项怎么可能只停留在自然/政治的单义的对立之中?
人权平等的起源提示我们差异如何作为原则,作为政治想象与政治创造的内在机制,去探究差异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既然现代政治的诞生刷新了人对自我的认识,为什么不可能发明更多?
二、作为问题的“女公民”
尽管从女权运动的历史来看,赋权仿佛是人权之于女性权利的一种滞后性的偿还,成文法的条例上添加了女人的工作权、投票权与教育权,这一切仿佛是在表明,权利说具有自身的修补能力,而在历史时间表上,滞后发生并得到国家承认的女性权利,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被历史不小心遗漏了的权利子项而已,在人权大框架之下,在人的概念中,男人和女人的集合作为整体性的表述,权利清单得到了扩充而已。
当权利清单的罗列与女人生存的体验格格不入的时候,女权才作为人权的悖论性存在被人们所意识到。
女人们发现自己通过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权利,恰恰是以丧失性别身份为代价而获得的,“像男人那样行事”反证出人权标准原来是有性别的,社会要求进一步指明,只有你必须把自己变成和男人一样的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是的,我享有了平等。
平等之于女人,除了是一项变性手术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已经偏离了卢梭平等理念的内核,即自然正当在女人这里成了一桩不可饶恕的罪。
现代人的自主性一目了然,而女人的自主性则成了伦理选择的困境:
在女人试图获得人格独立性的时候,性别差异显然与人权所暗含的变性资格相忤逆。
基于人权平等没有说出的东西,女权平等恰恰是在这个沉默的地方发声,去理解另外的不平等,这不平等伴随着文明或权力的起源,并内在于人们的习俗与文化之中。
要支撑这不平等的男性霸权,现代国家有时很会装聋作哑,因为人的概念与男人的概念往往是重叠的。
一个俗常的表达是:
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但前者是概念性的,后者是实存性的。
从不平等的另类起源中,我们发现启蒙之后的“人”之概念是一种预设前提,在此名义之下,可形成如下问题:
政治平等是如何被表征的,政治平等所蕴含的诸要素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联,是如何被连接起来的?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发生并得到解决的?
政治平等的创生原则,在卢梭那里有种模糊的社会主义意味,尽管卢梭并没有明确反对私有制,但他必须在理论上回答平等赋权的充分条件是什么?
他在《社会契约论》认为,当所有人将所有权利让渡给共同体,即每个单独的个体必须转变成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人才可从共同体中获得存在感,这个“存在感”当然与卢梭所珍爱的自由相关。
而让渡的目的不是霍布斯认为的那样,将自然权利托付给主权者获得照料与看护,而是为了形成一个普遍意志(公意)做好准备。
就是说,在平等共同体发生的那一刻,人与人的差异或不同是通过这种“让渡”被抹除,这有点类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这一始源的政治发生场景,只不过卢梭的这个共同体发生学更加的抽象化以及形式化。
在普遍意志被推举之后,个体与共同体血脉相连,服从自己与服从共同体也就没有对立与冲突了,反之,共同体受到伤害就等于每个个体受到伤害,每个个体的生命脉动与政治节律处在和谐共振的状态中。
卢梭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强调集体大于个人,而是说人要脱离低级放任的原始自由,就必须放弃强与弱的天然差别,当然此处的差别在原始状态中与等级秩序无关,而是说在立约的那一刻,抽象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必然是无差异之人的联合,道德状态下的限制并没有让自由有所损失,恰恰相反,这种联合保护了所有人的自由,就效果而言,实际上限制了强者的自由,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埋下伏笔,到了马克思那里,个人自由则被阶级解放置换。
当一种作为政治要素的制度即公有制,借用了卢梭的平等之名的时候,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就成了女权主义思想的一种路径。
但我们知道,性别平等正如卢梭思想一样,其困难在于探索有没有一种不损害个人自由的平等,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期许。
毕竟卢梭的普遍意志概念既不同于自然法,也不同于权力整体,其落点在于强迫所有人成为有道德的自由人,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
“放弃自由,就等于放弃做人的资格”。
⑦
基于契约论之上的现代国家建制,一个显在的成就是:
瓦解了任何阶层与利益集团的特权,这个最不平等的政治表征就是王权制,但赶走了国王就意味着平等的完全实现吗?
因为在逻辑上平等与任何形式的特权或霸权相对,而“平等”概念作为一种参照系,时刻检验现实中的不平等,在平等的承诺中去不平等地、非对称性地提出新的抗争议题。
这一切不可能在人之外去发现不平等的迷踪,恰恰是“人权”本身就是这种可疑的踪迹,因为人权不可能涵盖人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且在人权的面前,站立着的不可能是同质化的人。
人的造型与构成,最不可化约的所在就是男人/女人。
如果政治还是在基于统治/被统治的关系模式中得到理解,那么统治权的正当性一旦确立,所有的服从就无需质疑,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与成为一个好的男人或女人,在逻辑上显然是一致的。
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这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在既是公民,又是男人/女人的同一个主体身上,在人权平等语焉不详或沉默的地方,这奇异的部分究竟意味着什么?
平等原则至今依然是最为激进的人类理想,在其被刻写在现代国家的承诺之中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扩展并激活人们对于人权的理解。
显然人的历史比追求平等的历史更加久远,在平等政治的实践中,最为困难的就是平等的真在自然差异、社会差异、历史差异面前,既不可能向人道主义求助,也不可能站在反人道的方向上,将人们赖以维系的现存秩序全部冲毁。
但是,平等的真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激励话语,为建制化、制度化的现代政治提供了更甦的可能。
柏拉图的“女公民”依然是一个亘古的政治议题,并且是作为问题的“女公民”如何复现在现代视野之中——如著名的安提戈涅公案,⑧她们如果还是被作为会说话的财产充公,为城邦与男人所共有——城邦与男人在柏拉图那里是可互换的词汇,那么现代之后,“女公民”的称谓必须同时在国家与男人这两个向度上得到澄清。
于是,政治平等在女权主义的视野中,同时意味着与国家权力相对的公民权利,以及与男性权力相对的女性权利,前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之中,而后者则更多体现在被习俗惯性所拖拽的麻木之中。
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美好制度的安排最终都归结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女权是对公民权的再造与更新,并且很有可能背负着“反人性”的污名,在打破既定伦理秩序的平衡之时,迎来新生与作为新生之罪的政治图景,在女权平等的政治实践中,其悖论性形象尤其鲜明。
人权平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价值预设,而不是人们要去追求的目标,就好像现代国家作为一部精良的装置,平等就是设定在装置中的危险程序,她时刻扰乱装置运行的稳定性,如果不是在宗教或者共产主义的系统内来观察,那么平等就是现代政治建制及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漏洞。
而这个漏洞,或者这个可疑的类似病毒的程序作为前提,使得不平等得到了更为深广的辨识与理解。
三、“兄弟联盟”之中的人权话语
就18世纪的启蒙逻辑而言,思想家们只是解决了一种纵向意义上的平等,即贯穿在人身上的自然秩序包括性别秩序,来强调自由与原始放任的区别,自由与限制相关,是通过将自然秩序转换成道德秩序而实现的;再者,除了历史的维度之外,还在个人与主权的纵向关系中规范了共同体的自由。
人的本来面目——如卢梭所描述的浑然天成的自由状态,无法推导出一个自然而然的性别状态。
按照卢梭的逻辑,如果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强者的权力,也不存在弱者的反抗,那么也就无所谓平等与否,那么平等恰恰是与政治社会一同诞生的,内在于统治正当性逻辑的一个反题。
因此,在同等享有权利的现代政治平等的陈述之外,女权平等是作为被遮蔽的问题而出现的,即平等者的共同体为什么实际上是摆脱父权的儿子—兄弟的共同体,⑨那么女儿—姐妹们的位置到底是自然给定的,还是应该处在一个人为的政治状态并在其中被塑造为什么?
“自然状态”一词使用,之于卢梭,最为关键的是独立人格保留,并且针对政治性以及社会联合而言,这种独立是自由的根本前提。
列奥·斯特劳斯认为,“自然状态”在卢梭那里,更多的是一种有关自由的“积极标准”⑩,这也正是卢梭与其他18世纪的契约论者的区别所在,霍布斯与洛克的“自然”或“自然权利”是政治规则演绎的前提与基础,而卢梭则以“共同意志”取代自然法。
政治哲学史家谢尔登·沃林(SheldonS.Wolin)认为,这个“共同意志”尽管极度抽象,但为了避免主观性的并不自然的个人判断,“共同意志”旨在取得普遍的利益,这样一来,“共同意志”其实是在模仿自然的支配作用。
11因此,遵循沃林的解释理路,我们发现卢梭为了避免他深恶痛绝的不平等,企图以“共同意志”的一般化来取代特殊性的差异化,这种无差异性类似于原始状态的混沌无知,并将自由转运到共同体成员与共同体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或者说平等就是强意义的自由,是人基于天性所发明的一种新生事物。
尽管列奥·斯特劳斯与沃林都准确地捕捉到了“共同意志”这诡异的自由属性,但是他们似乎都遗漏了“意志”。
沃林所言的“模仿自然”,而不是自然法演绎,更像是卢梭有违理性主义的惯常轨道,将“意志”这危险的事物缝合在政治理想之中,而不是以规则体系来降伏它。
意志是近乎生命本能的存在,这比自然权利更加自然的生命属性,是哲学经常避讳的不祥之物,但人类的政治生活却常常与它照面,且必须与之照面,卢梭较之同时代的思想家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地方也在于此,不仅其“自然”概念最早开启了现代性问题,而且就政治理论而言,“共同意志”更像一个先知的预言,将某种无限的眷望带入政治生活之中,由此想象力与即将来临的事物超越了霍布斯的政治体系,为历史终结说划下了一道口子。
更多的时候人们用公共理性来取消意志所携带的任意性,并将意志这极端个人化的因素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而人们之所以能够共同生活,那是因为在此之前达成了一些共识。
“共识”(commonsense)显然比卢梭的“共同意志”(commonwill)更简明,就启蒙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被广泛接受而言,“共识”作为人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性标准是一目了然的。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列奥·斯特劳斯进一步阐明:
卢梭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艺术家生活”,因为卢梭始终认为比自我持存更强烈而根本的欲望是人对存在感的发现与体验。
12另一位思想家阿伦特将人类的精神生活分包括意志、思维与判断,而判断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最近,她认为“意志”属于精神活动一个绝对起点,类似于神学中“创世论”,“意志”是从“无”到“有”的第一现场,由此展开一种新的系列行为和状态。
13而在《人的境况》一书中,阿伦特将政治定义为经由新生命的降生才有可能开启的行动,14可见,尽管“意志”并非政治因素,但它先于政治生活,并在其起源处,与传统的选择性自由不同的是,意志自由与创生发明密切相关。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卢梭为什么要把“意志”这一非政治的因素引入他的权利学说了。
如果我们将“意志”与卢梭所说的“存在感”相联系,就会发现“艺术家”的生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而想象力与创造某种不可预测的新事物相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等的极度抽象性可还原为某种创造行为,是在无限的否定性之中,从逻辑的背面将政治平等的显/隐运作铺陈开来。
为了追求平等,就必须不断地去发现不平等,并在事物的差异之中,重返权利的发生现场。
正如当代思想家朗西埃(JacquesRanciere)所指出的那样:
平等不仅是政治得以成立的一种预设,这预设需要不断地被提出,并致力于平等实践的持续创造。
15在政治理论方面,经典意义的权力统一体与卢梭的平等共同体构成了一种永恒的抗辩关系,在此,抽象与具体、原则与实践不再是政治质询的唯一路径,经由这种抗辩关系,实际上是同一与差异的逻辑在支撑着政治的操演,更多的统一性只能伴随着更多的差异性并行不悖。
所以,平等与差异成了一组对立的矛盾体,经典意义的政治自由并不关心事物的差异性,那么平等之于女人在逻辑上就可表述为:
要么针对女人实施“变性”手术,如柏拉图的做法,要么你继续滞留在自然状态,继续做女人,而成为女公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可见,恰恰是女人的僵局在逼迫政治难题显形:
如果不是从统治秩序层面,执意在人权框架中去争取所谓的权利,而是从秩序的非稳定性出发,争取权利就可表述为发明权利,因为自我赋权总是先于法理赋权,正如共同意志既催生了权力/权利,又在一个不断生成的状态下,在此时此刻把意志(will)的将来时镌刻成一种眷望的姿态,因此,女性权利不再以人权为参照系,而是在女权主义(feminism)内部的理论辨析之中,使得女人的意志携带着生产性的本能,先于知识理性来到人群之中,一如政治创生的始源场景,阿伦特将这场景描述为:
“一个孩子降生在我们中间”。
16
尽管卢梭的“共同体”没有给差异性留有任何余地,而他的“公民”概念并没有被净化成一个宪法意义上的抽象个体,他更多是在伙伴关系中来使用“公民”一词,这就将一种纵向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