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考古.docx
《现实考古.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实考古.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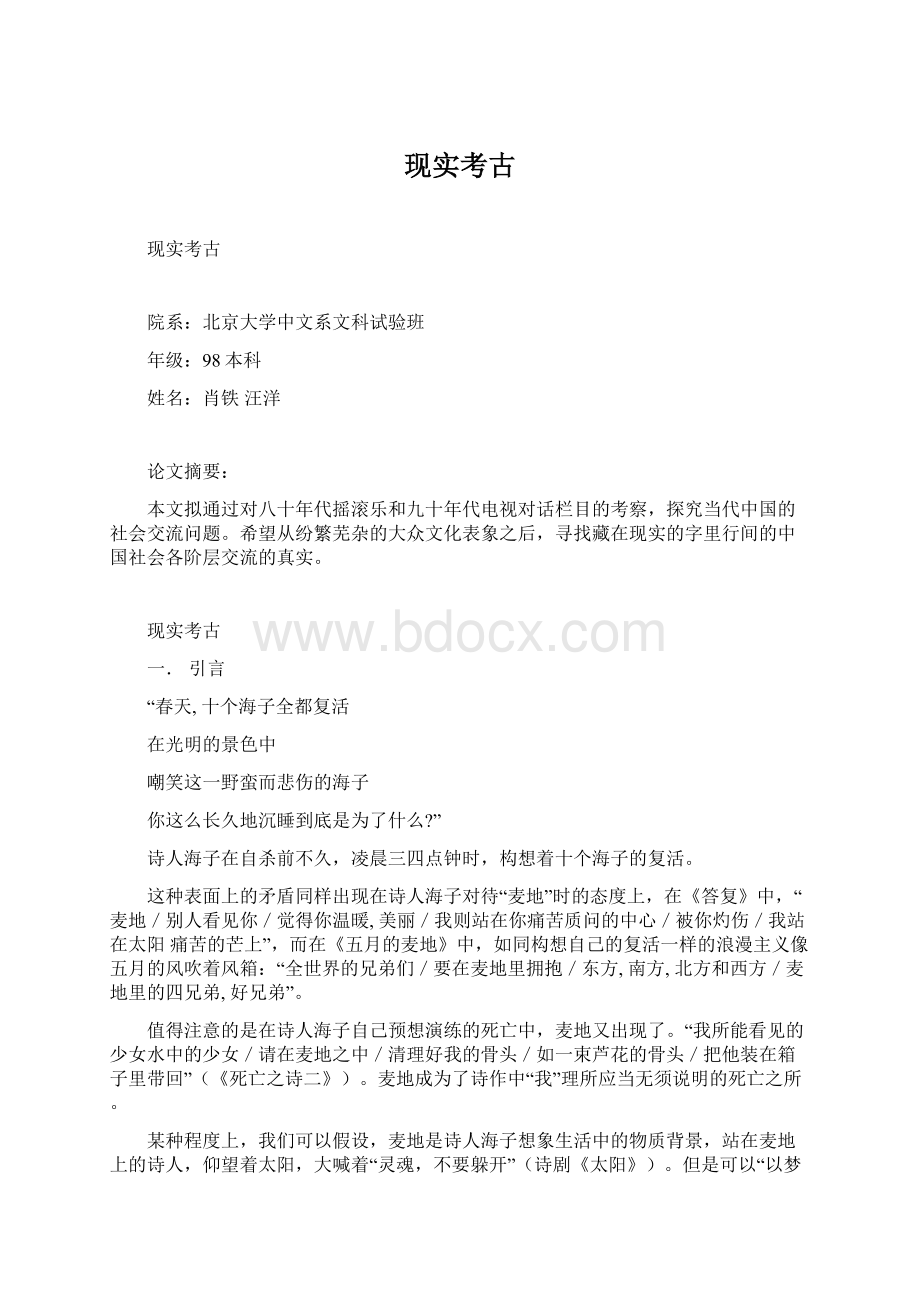
现实考古
现实考古
院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科试验班
年级:
98本科
姓名:
肖铁汪洋
论文摘要:
本文拟通过对八十年代摇滚乐和九十年代电视对话栏目的考察,探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交流问题。
希望从纷繁芜杂的大众文化表象之后,寻找藏在现实的字里行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交流的真实。
现实考古
一.引言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
诗人海子在自杀前不久,凌晨三四点钟时,构想着十个海子的复活。
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同样出现在诗人海子对待“麦地”时的态度上,在《答复》中,“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而在《五月的麦地》中,如同构想自己的复活一样的浪漫主义像五月的风吹着风箱:
“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东方,南方,北方和西方/麦地里的四兄弟,好兄弟”。
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海子自己预想演练的死亡中,麦地又出现了。
“我所能看见的少女水中的少女/请在麦地之中/清理好我的骨头/如一束芦花的骨头/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死亡之诗二》)。
麦地成为了诗作中“我”理所应当无须说明的死亡之所。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假设,麦地是诗人海子想象生活中的物质背景,站在麦地上的诗人,仰望着太阳,大喊着“灵魂,不要躲开”(诗剧《太阳》)。
但是可以“以梦为马”的海子在梦醒后的现实中,对待自己的生命却如同对待麦地一样,显示出了战栗与留恋间的迷茫。
那麦地中孤独的诗人的影子像个幽灵一样注视着聚在一起的“四面八方的兄弟”,渴望着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甚至暗想着那在麦地中阳光下的就是十个自己。
诗人在自杀前的最后的诗作中才把话说明,十个海子还在问着“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
假如我们相信海子的诗可以像他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一样是“一旦出现便永在的东西”,那么海子个人的死和他的私生活对于我们对他的这些诗句的解读就不再是必需的了。
它们在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隐喻笼罩在八十年代过去后的九十年代之上。
在得知自己会在春天复活后,诗人于1989年3月的一天自杀了,留下了麦地中悲伤的海子和春天里的十个自己,像“镜象”般面面相觑,暗示了孤独中“对话”的唯一可能:
自我复制!
二.交流的幻象
——从广场到演播室
广场和演播室根本的不同就在于:
一切精致的掩饰和委婉的言辞仿佛都会在进入广场的瞬间传上人群的躁动而立时真诚而无所畏惧地偏离事先的逻辑;而所有凌乱的思绪和微妙的个体差异又都会在主持人迷人的微笑中,驯顺地整和在策划的主题中。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一个明显而又有趣的文化现象便是几乎所有公开场合的交流都成为了演播室里的talkshow;而自“五·四”以来,人们在北京的广场上寻求“交流”的艰辛努力一时间似乎又都仅仅成为了历史书中可以演说或者有所禁忌的过去存在着。
在那个“对话”的要求和着崔健的歌声高频率地激荡在北京广场上空的夏天过去之后,诗人欧阳江河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态写道:
傍晚,我穿过广场
在死亡的氛围(傍晚)里,公共的政治生活(广场)在私人立场(我)中被毫无留恋地放逐(穿过)了。
①这种放逐不仅仅意味着九十年代个体对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疏离,它同时也标志着一种异质性对话的终结——广场不再上演权威和异端之间对抗、妥协与寻求“他者”理解的努力。
对于这种追求交流的努力,海子曾经满怀希望地恐惧过。
而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中期兴起的一系列发生在演播室中的对话,却似乎竭力通过兜售一种温文尔雅的交流方式来让社会忘却选择不久之前还令人兴奋不已的“广场”式言说的可能。
然而就在这温文尔雅构筑的“一团和气”的景象里,却常常闪烁着广场上威胁、恐吓的影子。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东方时空》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如果我们对中国“老百姓”在社会话语圈里低下的地位怀有一丝起码的愤怒,那么在为诸多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人文关怀”之外,这句台词或许听来就更像是一种“莫谈国事”式的威胁与劝诱。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自然意味着这个节目主要的叙事对象是那些普通人,普通事;当然“普通”就意味着这些人和事也是永远和严肃的“国事”扯不上任何干系的。
于是在我们的电台充分“尊重”了老百姓言说的权力之后,这看起来更像是“恩赐”的“人文关怀”又顺理成章地把老百姓放到了“国事”之外,放到了他们本来应该待着的地方。
并且,因为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话语圈几乎从来就没有给予老百姓言说的空间,所以当王刚借着二锅头的酒力娓娓说道“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这句广告词更是潜在地向公众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中国的老百姓没有理由不沉醉在这些普通的故事里。
广告的诱惑力越强,它的诱惑也更容易成为一种强制——究竟在任意一个给定的时段里,老百姓选择的电视节目只有一个。
于是,如果当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投入到“自己的故事”中去时,我们的媒体是否正在以劝诱或者以另外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剥夺普通人参与到那些不属于“老百姓的故事”中去的权力呢?
而这不正是一种变相的“莫谈国事”式的警告吗?
或许正是对这种温和劝诱与警告的需要才促成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众多电视对话节目的兴起、繁荣。
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将这些繁荣的对话节目看作是九十年代对于八十年代困扰全社会的“不满”情绪的一种新的疏导对策。
而这种疏导,更因为九十年代诸多对话节目日益明确的“分工合作”而显得更富成效——就像将洪水导向了不同的方向。
关于中央电视台那许多冠以,或者不曾冠以“对话”之名的对话节目,《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就曾谈到:
我们(《实话实说》)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是一家,同在新闻评论部。
所以选题上有分工。
②
“分工合作”恰恰是广场式交流和演播室里对话的本质不同之一。
“分工合作”意味着言说者并非是要整和所有异议者的不满,在抽象的“不满”和“愤怒”推动下,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去广场上做一个真或假的主义之争;它更多地像是一个小心翼翼地解决问题的过程。
但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中,所有和具体问题关系不大的人群很可能事先就被排除在栏目策划的考虑之外,例如那些不属于“老百姓”的人群,就不大会是《生活空间》竭力要讨好的构成收视率的对象。
于是,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那些在八十年代触动全社会神经的问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入各有专攻的演播室,每一个节目在获得为数众多的稳定的观众群的同时,因为其他节目的存在而失去更多原先的观众:
腐败的吏治大多由《焦点访谈》来加以揭露;经济改革的前途则由《对话》栏目里诸多工商界巨擘的智慧来照亮;而最底层琐屑的痛苦和不满也可以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得到发泄。
于是,我们发现八十年代促使人们走上广场的社会性的“不满”并没有在九十年代消失,只是在九十年代媒体技术化的分割下被肢解了。
每一个对话栏目或许真地提供了关于某个问题的充分交流,然而它却有意无意地阻隔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
人们开始为不同的演播室吸引,而不再为同一个广场而疯狂。
今天,对于电视屏幕上的“真实”保有一种警惕似乎成为了所有揭露大众传媒幽灵的批评所必然提及的东西。
然而,人们并非都如所有敏锐的批评家所预言的那样,迟钝到对那些可能被“事先安排好”或“时后经过处理”的影像全无防备的地步。
事实上,如果说,大量对话节目的科层化肢解并遮掩了社会的不满,制造出一个“一团和气”的假象,那么这个假象的制造可能是处于统治的需要,而假象的维持则有赖于受众的默许。
对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为数众多的对话节目而言,真正的“实话实说”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倒并不在于这只是国营电视台操纵舆论的方式,而在于“我们不再是观众,而是有成就的演员,并且越来越融入演出的过程。
”③如果说,在电视影像的呈现中真地存在一种对“现实”的谋杀,那么这种谋杀并非是因为影像对现实模仿的偏差和扭曲造成的,而是因为影像所模拟的现实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虚构,成为一种公认的,为大众所接受的谎言。
在央视《对话》栏目的周年总结中,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案例:
当主持人总结了爱立信总裁柯瑞川的表述之后,柯先生带着老外特有的幽默说道:
“我昨天跟他(主持人)说好了一定要这样说。
”在随后表达现场观众情绪反映的括号内,则顺理成章地写着:
“观众大笑”。
④
——我们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大都也会同样地大笑。
观众的笑声毫无疑问地暗示了观众对于后台操作的宽容。
而这种宽容无疑也是对那些为批评家所乐道的没有被“事先安排好的”,“没有经过事后加工的”真实的漠视。
漠视似乎意味着“真实”问题的消逝,然而事实上在这里,“真实”问题转化为了一个知情权的问题。
观众之所以会对人工制作对于真实的侵犯发出宽容的笑声,那是因为观众事先充分的了解到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事先安排”或“事后处理”对于电视的制作是一个不可豁缺的内容。
因此,当敏锐的批评家们痛斥“虚幻的拟像”时,“不真实”的问题或许存在,但是这时候“不真实”已经不再构成一种欺骗,一种道德的罪行,知情的观众往往更乐意带着一种洞见的狡黠参与到“拟像”的演出中去。
今天,人为的操作似乎不再成为影像令人无法容忍的缺陷,反倒可能是影像“真实”不可缺少的部分:
一个严格拷贝现实的影像叙述或许会因为现实本身的凌乱而让观众无法接受——就像八十年代广场上的言说总是很难让人把握一样;而将所有的现实碎片贯穿以一个主题的做法,或许反而会因为它一以贯之的逻辑而更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九十年代演播室里的对话不再是八十年代广场上享有全部知情权的一方和毫无知情权一方之间的交流。
交流的规则和其中可能的吊诡在参与之前就已经充分的为双方所知。
因此,如果影视形象真的负有“虚构”的罪责,那么这一罪行无疑是观众一同参与的,而人们对于这一指控的宽容和坦然,或许正是八十年代广场对话悲剧式的结尾所留下的一份遗产。
这种交流双方的“合谋”可以说更像是一种镜像两边的人和自己的影,在默许的状态下,交流成为了自我复制。
九十年代繁荣的对话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坐在家中安全地参与对话的闲适,然而所有的幸福似乎都是要有所付出的。
全民族对于电视对话节目的热衷,和对于广场的冷漠,常常让我们想起这么一个故事:
有个学生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王,魔王则让影子扮成那个学生活生生的复制品到处行走,而那个学生却仅仅成为该复制品的替身。
⑤
三.反叛下的共谋
——从崔健的张楚
如果说大众传媒中的对话节目建构了一种一团和气的“拟像”的话,那么有意思的是摇滚乐从一出现就似乎被安排在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位置上,代表着某种主流媒体不愿公开的反叛。
当崔健挽着裤管跳到舞台上时,大家就以他在舞台装束上的反叛确认了他的思想的反叛。
摇滚乐的产生在世界范围内看,应该说是音乐民主化进程中的产物,就我国而言,还有一个意识形态民主化的背景,这是我们谈论摇滚乐的前提。
如果我们不再一相情愿地喊着摇滚是反抗,念叨着崔健眼睛上的红布,而是回到历史和歌声的细微之处的话,我们会发现:
无论是批判摇滚乐,还是欲图使之合法化,都是建立在对其解读的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的,而摇滚最初一代的成功正是在两代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和没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对话的“合谋”下出现的:
对一部分有文革经历的人来说,崔健的音乐尤其是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满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与记忆的消费”(戴锦华语)的欲望。
而在一种隐喻下,把“革命时代”性爱化(《花房姑娘》《假行僧》),又使得他的音乐有了被缺少历史体验的人们物恋和怀旧的可能。
如果说“我的坚强已不再是虚伪/我的愤怒已不再是忏悔”,还只是委婉地表达了他一种希望“闭上眼没有过去”的愿望;而“我的眼睛将不在看着你/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则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对过去的否定;如果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心说别着急”,以戏仿的题材,以不在乎的,身体感官式的,与主题的严肃神圣性相悖的表达方式,来“摆脱集体主旋律的种种重负”,来突破“强迫性的文化记忆”,开拓出新的根据地,代表着叛逆。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一无所有》吧。
《一无所有》“两面讨好”地受到关注,一方面他借着麦克风,正面大声面无愧色不再掩饰地道破了人们欲言又止不想说出口又怕说出口的一代人的自我定位,人们不想不敢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奋斗了半天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境遇”的现状,被崔健在以情歌为框架的歌曲里表现出来,便掩盖住了既然“一无所有”那么是否还要革命这个危险的话题,使得人们可以没有顾虑的“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一些论者也庆幸“只有在这首歌里,价值关注没有被彻底取消,歌声里仍有‘她’的位置,并且‘她’是这样执着地深情地被呼唤着,被恳求着啊!
”
更有意思的是在重复了许多遍“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似乎把“一无所有”放在了否定的位置上后,崔健突然唱出“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巧妙地为“一无所有”正了名,不动声色地为一代人正了名,歌曲里“一无所有”与“追求”的交替出现,又把“一无所有”的现状与某种正面的可能性联在了一起,赋予了这种现状以合法性,而就像在“笑我”转变到“爱我”中间缺少必要的解释一样,在这正名的过程中,崔健也像被遮住了“一块红布”似的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视而不见含糊过去,以一种“反思历史的姿态拒绝反思”⑥,就像伤痕文学把自我定位为受伤,把个人的责任推卸给历史而不管(至少是不着重写)历史是谁造成的,从而获得新时期中个人的“纯洁”一样,崔健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也是这样,他看似不经意的,舞步轻盈的一跳,达到历史的彼岸,用置之不理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完成了他与潜在反对者的一次合谋。
在这一点上,崔健表现出了与朦胧诗惊人的相似。
在迅速把苦难的历史记忆转化为符合时代目标的积极遗产的“新时代”要求下,崔健同“朦胧诗”,包括“归来者的歌”一样,通过展示“个人”的觉醒和承担而从对“历史”的伤痛追述过渡到对未来的追求的表白。
这一“我”的特征如果不说是政治化的,那也至少是群体化的。
甚至可以说“我”本身即是象征化的,代表了新的“群众前进方向”。
就像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这也是一切》,顾城的《一代人》,江河的《纪念碑》,杨炼《我们从自己的脚印上》、《自白》。
可以说《一无所有》就是顾城的《一代人》的回声,里面的内在逻辑是多么惊人的相似,“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一无所有”,但“你就爱我一无所有”。
这种心理上的自足和自信我们以为是崔健大部分歌曲的出发点或背景,所以崔健虽然说着“别怪我对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仍然可以大声唱着“我的自由也属于天和地/我的勇气也属于我自己”,他可以“攥着手只管往前走/张着口只管大声吼”。
而在下一张专辑《红旗下的蛋》里,崔健仍延续了这种逻辑。
在《最后的抱怨》中,他说“记得那一天我的心并不纯洁/我迎着风向前胸中充满抱怨/我不知何时曾经被伤害/可这伤害给我感觉”“那一天”和“曾经”构建起历史的跨度,用完全和《一无所有》一样的逻辑方式,点明是处于被伤害的地位,但通过一个巧妙的看似轻松的转折,在对历史的再描述中为历史的后果也就是现状(受伤)正了名(“给我感觉”),而再次对造成这种伤害的历史悄悄闪过,在把历史悬置后获得当下的片刻轻松。
而正是有了这种在怀疑和矛盾的阴云笼罩下残存的一点理直气壮,崔健才又有了在歌的末尾再次高呼“向前向前我迎着风向前/向前向前我迎着风向前”的理由和力量。
当崔健的歌像被放进了共鸣箱一样穿过八十年代传遍九十年代,那巨大的几乎无法辩驳的声音使得人们仿佛只有耳朵去听嘴巴去跟唱,而没有空暇仔细考虑一下崔健的宏大叙事的内在逻辑特征。
“别想把黑暗放在我的面前/太阳已生长在我心底”唐朝的这句歌可能是崔健得以自信地轻轻一跃,拒绝反思而否定过去肯定现状,为经历浩劫的个人正名,但同时又在自己眼睛上的红布上扎了两个窟窿。
张楚的《姐姐》是另一个有趣的例证。
谈论《姐姐》只是写情感,我想可能是人情味儿过浓了。
仅仅写我对姐姐的感情,没有必要扯上“我爸爸是个混球”,没有必要揭姐姐的伤疤,“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真的没有必要,除非张楚他想说的更多。
其实如果我们降低情感的温度,也先把姐姐放一放,就会发现张楚借着情感的“修辞”的掩护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三代人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我与姐姐,那个男人,混球父亲。
而无疑,上两代人都是处于被否定的地位,爸爸干脆就是“混球”,也即建构历史(侮辱?
强奸?
)的人被张楚作为被说的对象,没有反驳余地的被否定,而姐姐这个我的同代人则被确认为“曾经被伤害”而成为被呼喊的对象。
如果就是这样,历史与现状似乎便被各司其职的定位而相安无事了,个人便可以在被否定的历史的废墟上清洁地生活,但张楚最后反复声嘶力竭地唱着“姐姐,我想回家/姐姐,带我回家”则暴露了张楚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即使那个家里有自己混球的父亲,即使那个侮辱了自己姐姐的男人有可能还在家里,张楚也还是要回家了,也还是要“走在老路上”了。
张楚在为我们情理并重地建构了一个历史的逻辑后,一不小心便又自己冲破了它。
于理,张楚似乎能咬牙骂一句混球扭头走掉,于情,却狠不下心了。
如果说在突然感到过去的宏大叙事原来是一个“黑梦”而一脚踩空后,崔健凭着惯性思维和“心中的太阳”再次起飞,那么张楚可算是明知有地球吸引力,但仍想向上够到原来的高度,在两头之间“双腿夹着灵魂 赶路匆忙”(《冷暖自知》)了。
摇滚乐以一种个人叙事介入历史,像我国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殊途同归地变成了对丧失统一性后的社会的整合剂,在一套宏大叙事中把历史做为不容辩驳“被说者”,通过理想化的的诠释为历史与现状定位,使得从历史中走出的个人得以“一尘不染”的再次走入现实时,它已经变成了保罗·利科所谓的“意识形态”:
它作为“自塑自我形象,进行戏剧意义上的‘自我表演’,主动参与游戏和表演的社会群体的需要”,“使开创性事件的创始意义成为整个群体的信仰物”,它使得人们可以用它心安理得地把集体记忆与现实连结起来而不会脱臼。
⑦进一步说,这种整体地诠释全部历史的“意识形态”――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言――“就是要从我们可以感知的实在中解放出来”⑧,而把事实纳入一种绝对的逻辑中。
谈反叛,谈何容易?
小心落入合谋的陷阱呦!
当我们在进行这我们的“现实考古”时,现实总是呈现出比它表面更有趣的东西来,当“对话”节目与摇滚乐这两个似乎暗含了某种对立的文化现象像我们展示了一种私下的“和谐”时,我们才发现现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的多,识破它的狡猾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只是担心在我们得意的一刹那是否又中了它新的圈套呢?
十个海子就在我们的上方,抬头看一看,小心别就是十个自己!
致谢
感谢泰兆基金对本文写作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慷慨资助,本文的写作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感谢老师曹文轩教授对于本文的悉心指导。
曹老师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的写作遇到麻烦,行文产生逻辑上的紊乱时,是曹老师耐心细致的指导引领我们走出思想的误区。
感谢教务部试验班办公室王海欣老师对本文写作的支持。
去年,王老师热情地肯定了我们的申请计划。
在长长一年的时间里,王老师一直关心着我们的写作进展。
感谢张慧瑜同学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参考文献。
他对本文的意见,也使我们有所受益。
注释:
①一行:
《公共生活的个体立场》http:
//www.china—
②崔永元:
《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p318
③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商务出版社p30
④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对话》栏目组:
《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p432
⑤让·博德里亚尔《完美的罪行》商务出版社p36
⑥《摇滚“孤儿”》 何鲤 《今日先锋》5
⑦《从文本到行动》 保罗·利科 转引自《比较文学》 陈淳等编 高教版
⑧《极权主义的起源》 汉娜·阿伦特 转引自《伤花怒放》
作者简介:
肖铁:
1979年8月21日生人,北京人,现为北京大学98级文科实验班学生,自幼喜欢文学,勤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数本。
学习态度较认真,获汇凯奖学金和“创新奖”。
汪洋:
98级文科试验班学生。
性喜读书。
北大良好的求学氛围,促使本人向学术方面发展。
三年的学习磨练了我的逻辑思考能力。
为人尚不算庸懒,曾获得校“学习积极分子”荣誉称号和“五四”奖学金。
感悟与寄语:
在将近一年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课题本身的认识。
在一年的合作之中,我们互相之间的启发和辩难,砥砺了各自的思考和研究能力。
本文的写作使得我们对学术上的协作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加深了互相的友谊。
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本文得以最终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在此,衷心希望我们的写作能为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
也希望我们良好的合作关系能为以后受泰兆基金资助的写作者提供一丝借鉴。
指导老师简介
曹文轩:
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自80年代以来发表文学作品与学术作品百余万字。
现为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组主任。
小结
本文特点:
对现实的关注。
我们的研究没有离开身边的现实,文章中含着两个学生对现实的关心。
从看似不相关的摇滚乐和电视对话栏目入手,考察了八九十年代人们不同的表达个体不满情绪,寻求交流的努力。
收获体会:
我们的合作。
双方的交流使得我们各自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我们相信我们的交流不是镜子的两边,而是打开的书的两页。
投入时间:
课题的写作是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完成的。
我们无法说出具体的时间。
不过我们真诚的投入是我们完成作品最大的动力。
学生:
肖铁汪洋
2001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