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docx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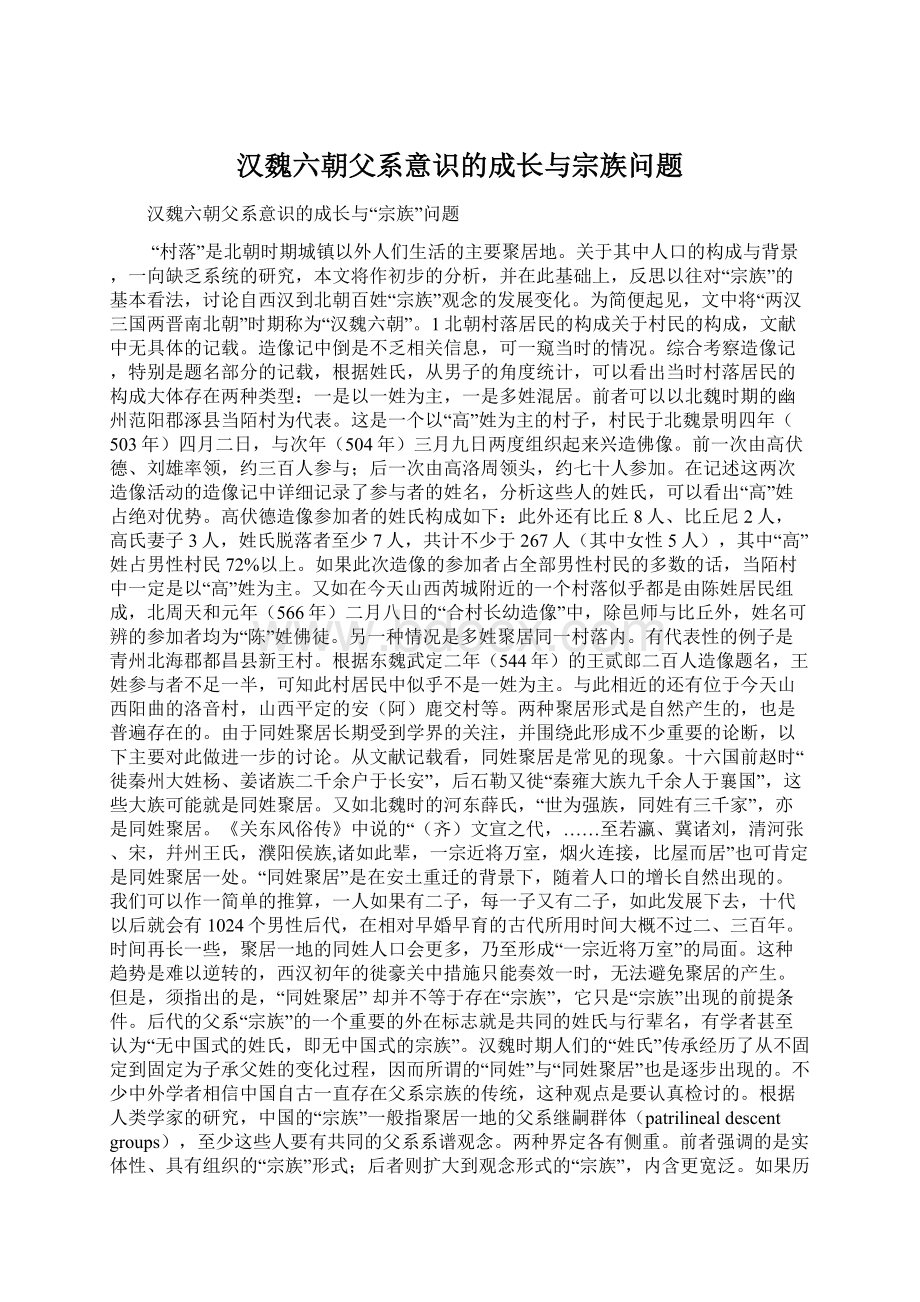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
“村落”是北朝时期城镇以外人们生活的主要聚居地。
关于其中人口的构成与背景,一向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将作初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以往对“宗族”的基本看法,讨论自西汉到北朝百姓“宗族”观念的发展变化。
为简便起见,文中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称为“汉魏六朝”。
1北朝村落居民的构成关于村民的构成,文献中无具体的记载。
造像记中倒是不乏相关信息,可一窥当时的情况。
综合考察造像记,特别是题名部分的记载,根据姓氏,从男子的角度统计,可以看出当时村落居民的构成大体存在两种类型:
一是以一姓为主,一是多姓混居。
前者可以以北魏时期的幽州范阳郡涿县当陌村为代表。
这是一个以“高”姓为主的村子,村民于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四月二日,与次年(504年)三月九日两度组织起来兴造佛像。
前一次由高伏德、刘雄率领,约三百人参与;后一次由高洛周领头,约七十人参加。
在记述这两次造像活动的造像记中详细记录了参与者的姓名,分析这些人的姓氏,可以看出“高”姓占绝对优势。
高伏德造像参加者的姓氏构成如下:
此外还有比丘8人、比丘尼2人,高氏妻子3人,姓氏脱落者至少7人,共计不少于267人(其中女性5人),其中“高”姓占男性村民72%以上。
如果此次造像的参加者占全部男性村民的多数的话,当陌村中一定是以“高”姓为主。
又如在今天山西芮城附近的一个村落似乎都是由陈姓居民组成,北周天和元年(566年)二月八日的“合村长幼造像”中,除邑师与比丘外,姓名可辨的参加者均为“陈”姓佛徒。
另一种情况是多姓聚居同一村落内。
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青州北海郡都昌县新王村。
根据东魏武定二年(544年)的王贰郎二百人造像题名,王姓参与者不足一半,可知此村居民中似乎不是一姓为主。
与此相近的还有位于今天山西阳曲的洛音村,山西平定的安(阿)鹿交村等。
两种聚居形式是自然产生的,也是普遍存在的。
由于同姓聚居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围绕此形成不少重要的论断,以下主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从文献记载看,同姓聚居是常见的现象。
十六国前赵时“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后石勒又徙“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这些大族可能就是同姓聚居。
又如北魏时的河东薛氏,“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亦是同姓聚居。
《关东风俗传》中说的“(齐)文宣之代,……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幷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也可肯定是同姓聚居一处。
“同姓聚居”是在安土重迁的背景下,随着人口的增长自然出现的。
我们可以作一简单的推算,一人如果有二子,每一子又有二子,如此发展下去,十代以后就会有1024个男性后代,在相对早婚早育的古代所用时间大概不过二、三百年。
时间再长一些,聚居一地的同姓人口会更多,乃至形成“一宗近将万室”的局面。
这种趋势是难以逆转的,西汉初年的徙豪关中措施只能奏效一时,无法避免聚居的产生。
但是,须指出的是,“同姓聚居”却并不等于存在“宗族”,它只是“宗族”出现的前提条件。
后代的父系“宗族”的一个重要的外在标志就是共同的姓氏与行辈名,有学者甚至认为“无中国式的姓氏,即无中国式的宗族”。
汉魏时期人们的“姓氏”传承经历了从不固定到固定为子承父姓的变化过程,因而所谓的“同姓”与“同姓聚居”也是逐步出现的。
不少中外学者相信中国自古一直存在父系宗族的传统,这种观点是要认真检讨的。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国的“宗族”一般指聚居一地的父系继嗣群体(patrilinealdescentgroups),至少这些人要有共同的父系系谱观念。
两种界定各有侧重。
前者强调的是实体性、具有组织的“宗族”形式;后者则扩大到观念形式的“宗族”,内含更宽泛。
如果历时性地观察,观念形式的“宗族”应先于实体性的“宗族”而出现。
宋代以后,在这种观念“宗族”的影响下,于部分地区产生了实体性“宗族”。
本文以观念形式的“宗族”这种广义上的概念作为讨论的参照,针对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的“父系意识”做些分析。
这里的所谓“父系意识”与人类学家所说的“父系系谱观念”的含义大体相当,指的是强调沿父亲一方计算祖先与后代的亲属关系的观念。
如果这种意识淡漠,可以说,不太可能存在观念形态的“宗族”,建立起实体性的“宗族”的机率就更小了。
这种意识在成长,则意味着观念形态的“宗族”在发展,实体性“宗族”也就要浮出地平线了。
当然,上述概念是据近现代的材料得出的,反映的主要是宋以后的情况。
追溯到汉魏六朝时期,“宗族”一词屡见文献,但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仍是小家庭,不见有后代的族产、族长与宗祠,父系系谱观念也处在发展中。
西汉末王莽的叔伯都封为侯,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而莽父早死,未得封侯,莽“独孤贫”,各家经济上并不相互接济。
东汉末刘备与同宗刘德然一道从卢植问学,“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说“各自一家,何能常尔邪!
”表示不满。
其根据就是各家经济上相互独立。
曹操与其从弟曹洪家也是如此。
曹操为司空时令本县估算各家的资产,结果估得曹洪家与曹操家相等,曹操说“我家赀那得如子廉(曹洪字)耶!
”曹丕在东宫时曾经“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也证明家各自为计,并不通财。
动乱时期会强化聚居的各家庭间的关系,除了“宗族乡里”的集体行动以外,关于去向各家仍可自行其是。
这与当时父系意识发展的程度分不开。
《仪礼·丧服传》曾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
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
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认为因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在对父系祖先的记忆上参差不齐,即父系祖先意识的发育程度上高下不等。
这段话不是无根之谈。
这里有必要对“宗族”做一番追根溯源的研究。
大体说来,除了皇族以外,汉魏六朝时期作为实体组织的“宗族”可以说基本不存在,观念上的“宗族”也始见于士人。
这一点,需要深入到当时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才能捕捉到,仅仅留心有关“宗族”的记载是不够的。
汉魏六朝母方亲属的作用与九族、宗族的含义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汉魏六朝时期母方亲属(当时所谓的母党、外家或外亲)在法律上的地位与家庭生活中的影响。
《仪礼·丧服》规定母方亲属的丧服为小功五月和缌麻三月,具体说来,为外祖父母、从母(即母之姊妹)服小功,而为从母之长殇、从母昆弟、甥、舅、舅之子则服缌麻丧,属于丧服中最轻的两种。
如《丧服传》所归纳的“外亲之服皆缌也”,郑玄在注中亦说“外亲异姓,正服不过缌”。
而为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姑服齐衰期(一年),为姑适人者、从父昆弟服大功九月。
相比之下,外亲的丧服要比生物学意义上血缘关系相同的父系亲属轻得多。
这种安排通常被认为是突出父系的地位,用来证明父系宗族在当时的影响。
不过,还有另一种解释。
刘宋时人庾蔚之曾说“外亲以缌断者,抑异姓以敦己族也”,暗示曾经有过外亲影响颇大的情况,而《丧服》的设制也正是针对这一状况的。
此人精研《丧服》,所说并非无稽。
从《丧服》的影响看,《仪礼》自西汉起就列为官学,传诵不绝,但西汉长期未行“三年之丧”,也很少按照《丧服经》的规定行事,只是西汉末以后逐渐有人行之。
为《仪礼》作注也要到了东汉后期,首先由马融为《丧服》篇作注,世间开始有人重视它。
如此看来试图抑制外家影响也不是只存在于先秦时代。
求诸史实,外家影响大的情况的确不仅见于先秦,汉魏六朝时也广泛存在。
1.西汉初律令中的母、妻地位最近公布的张家山汉简中的西汉初年的律令有一些涉及到立后和服丧问题,其规定与后代颇有不同,值得重视。
先说立后。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专门的“置后律”。
其中有这样的规定:
简三七九—三八○:
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
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
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
律文中提到的“寡”据简三七六“死,其寡有遗腹者,须遗腹产,乃以律为置爵、户后”,指的是“寡妇”。
同墓出土的《奏谳书》所收“杜泸女子甲与人和奸”的案例中引“故律”云“死夫(?
)以男为后。
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为后。
”(简一八○)这一案例被认为是西汉初年的事,故律所指尚难确定。
不过它规定的为后顺序与“置后律”是一致的。
据这两条律文,为后的法定次序首先是死者的子、父母妻女,然后是孙、耳孙、大父母与同居的同产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初年,母亲、妻子与女儿尚可以被立为户主,尽管她们的位置排在同类男性亲属之后。
而父方的“孙”“耳孙”与“大父母”“同产子”则置于女儿后面。
这种立后法定次序所遵循的并不是单纯的父系男性继承原则,也包含了母亲、妻子与女儿,大体概括是男性优先,兼顾女性。
比较唐代的规定,这种差别可以看得更清楚。
《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立嫡违法”条的疏引“令”云“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
曾、玄以下准此。
无后者,为户绝”,唐代立嫡顺序严格按照父系继嗣与嫡庶原则排列,完全排除了母、妻与女儿的一席之地。
与此相若,《置后律》中关于死事者爵位继承的规定也不限于父方男性亲属。
律规定首先是子男袭爵,“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产,毋男同产以女同产,毋女同产以妻。
诸死事当置后,毋父母、妻子、同产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
”虽然父方男性亲属相对优先袭爵,女儿、母亲与妻子,乃至姊妹也都侧身其中。
关于丧亲归宁的规定也与后代大有不同。
“置后律”有这样一条:
“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产、大父母、大父母之同产十五日之官”,上面提到的《奏谳书》中的案例引据的“律”文也有“诸有县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归宁卅日;大父母、同产十五日”,两者涉及应是同一问题。
此时的规定中,丧妻与丧父母均归宁三十天,比丧子、祖父母及祖父母的兄弟要多一倍,与后来通行的《仪礼·丧服》中偏重父方男性亲属的规定有相当的距离。
家庭中母与妻的角色实际是相通的。
今日之母乃昨日之妻;今日之妻多半会成为明日之母。
上述律令的规定所承认的既是母亲的地位,也是妻子的地位,亦是相通的。
概括说来,是对联姻关系中女性一方地位的认可。
立后问题上,(父系)继嗣关系与联姻关系均得到尊重,只是在子—(本人)—父机会优先,而其它较远的父方亲属的机会则要排在母、妻与女的后面。
机会优先唯有限的直系父方亲属可以享受。
与后世只考虑父系关系的做法大相径庭。
如果相信法律规定不是远离生活的空中楼阁,西汉初年的律令中对母亲与妻子、女儿地位的表述也就不应视为无本之木,在现实生活中必有其根源。
汉初到唐初有关法律规定的变化的背景与动因需要结合生活实际作进一步的挖掘。
2.日常生活中的母方亲属这一时期母方亲属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下文所指出的若干方面。
而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同母关系受重视之上的。
上述汉初律令的规定与此背景不无联系。
这里先考察同母关系的情况。
1)同母关系受重视当时的同母关系似乎在某些情况下也比同父关系密切,至少与同父关系一样受到重视。
普通人家的情况史书中记载甚少,难得其详,皇室生活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
汉武帝即位后,封与其母王太后同母异父的田蚡、田胜为侯,又听说他有一同母异父的姐姐金俗,在民间,说“何为不早言?
”乃车驾自往迎之。
金俗家在长陵小市,武帝“直至其门,使左右入求之。
家人惊恐,女逃匿。
扶将出拜,帝下车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
’载至长乐宫。
与俱谒太后,……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武帝迫切与金俗相见的心情跃然纸上,他并未因非同父所生而有什么芥蒂。
宣帝即位后“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到地节三年(前67年),才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无故、无故弟武,其时距宣帝即位已经7年了,“求外家”之不易与周折,以及宣帝的锲而不舍可见一斑。
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在其子成帝即位后封她的兄弟为侯时,同父同母的封户比同父异母的要多许多。
王政君有兄弟八人,唯王凤、王崇与她同母。
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二月封侯时王凤已嗣其父为侯,又“益封五千户”,累计八千户,同母弟王崇则“食邑万户”。
而其它五个在世的异母兄弟仅赐爵关内侯,有“食邑”,但封户很少,五年以后的河平二年(前27年)他们被封为列侯时封户也只有二千到三千七百户。
最多的尚不足同母兄弟封户的一半,可见同不同母关系重大。
不仅亲疏有别,待遇也高下悬殊。
王政君另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苟参,她甚至想比照武帝时田蚡的先例,封苟参为侯,虽遭到成帝的拒绝,但也还授予他侍中水衡都尉的官职。
相形之下,王莽则没那么幸运。
莽父王曼虽也是王政君的异母弟弟,因早卒,没赶上成帝即位时的封侯,不仅王莽幼年生活贫苦,仕途亦不顺,在射声校尉这一闲职上沉滞很久,封侯要到永始元年(前16年),比诸叔晚了十余年,还是在叔父王商等人的一再要求下才得到的。
较之苟参,他的出仕经历要艰难得多,个中原委,恐怕亦与王莽非太后同母子侄有很大关系。
元帝的傅昭仪也是如此。
傅昭仪的父亲早死,母改嫁郑翁,生男郑恽。
汉哀帝即位后封傅氏外戚时,不仅封她的从兄弟三人为侯,因其同母异父的弟弟郑恽已死,封郑恽之子郑业为侯,并追尊郑恽为侯。
封户上其从弟傅商初封仅千户,郑业也是千户,并无区别。
江苏仪征胥浦汉墓中出土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的“先令券书”则反映了西汉末年普通百姓家庭在财产分配上母亲的作用与同母关系的重要性。
据“券书”,“券书”作者朱凌的母亲先后嫁与三夫,有子女六人。
与朱凌同父另有兄妹三人:
以君、子方与仙君;另一弟“公文”,其父为吴衰近君;一妹弱君,父曲阳病长宾。
其母在分产业时,先给了朱姓的二子,后又给了异父的仙君与弱君田地。
随后又因公文“贫无产业”,仙君与弱君把田让给了公文。
从此券书看,父亲去世后,产业均由母亲处置,同母的子女,不论父亲是谁,都有机会得到产业。
综合上面的分析,这类现象恐怕不是个别性的。
此外,这一时期个人在家庭乃至乡里中的地位也与母亲及其家庭的地位和影响密切相联。
东汉的著名思想家王符的家乡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他在乡里社会中的地位也受到影响,可见外家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
类似的事例还见于南朝齐梁时人到洽。
其父到坦“以洽无外家,乃求娶于羊玄保以为外氏”,所谓“洽无外家”并非真的没有外亲,据其兄《到溉传》载,实际是“所生母魏本寒家”,她为了让到洽、到溉兄弟为人所赏识,“悉越中之资,为二儿推奉(任)昉”,其亲生母亲当时并未过世,只不过出身低贱。
江左风气虽说“不讳庶孽”,但外家仍然是重要的依靠力量,所以到坦要为到洽联姻高门。
北齐时人崔廓,“少孤贫而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廓是博陵安平人,生活在北朝末年,与王符的时代相距四百余年,两地也相隔数千里,风尚却相近,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可以断定的。
又如曹魏时裴潜折节仕进的原因是“自感所生微贱,无舅氏”与“又为父所不礼”。
不少人因母贱“庶出”而遭到各种歧视,北方更常见一些。
这一现象若仅从嫡庶角度考虑,意犹未尽,它背后的观念基础是《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说的“子以母贵”,重视“母子”关系,包括母亲家庭的地位,突出它在确立子嗣在家内及乡里地位与身份上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根据前辈学者的研究,汉代,特别是西汉,上至皇室下至百姓还存在子从母姓的现象,这大概不是罕见的现象,因此,东汉的王符在分析周室衰微以来的姓氏变化时特别指出“亦有杂厝,变而相入,或从母姓,或避怨仇”的情况。
“子从母姓”当然也是重母方的重要表现。
另外,西汉初年,外戚亦称宗室,也不被视为“异姓”,均属重视母方关系的明证。
2)外家抚孤汉魏六朝时期外家仍然有责任抚养年幼的外甥或外甥女。
不少人年幼丧父后,转由母家抚养。
据《汉书·外戚传》,汉文帝之母薄姬,“早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颜师古注曰:
“言太后为外家所养也”,这是西汉初年的例子。
范升“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范升曾被王莽的大司空王邑辟为议曹史,其少年时代应在西汉末。
此外,像汉宣帝的玄孙刘般、南阳宛人朱祐与朱晖少年时都有过类似的由外家抚养的经历,时间也集中在西汉末年。
刘般父祖被封在楚,王莽篡位后移居彭城,基本生活在南方。
上述事例发生的地域较广,这一作法似乎不是某个地区所特有的。
魏晋以后这类事例仍时有所见。
魏晋时任城樊人(今山东济宁市东)魏舒“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久乃别居”,西晋重臣颍川荀勖,父早亡“勖依于舅氏”,“少长舅氏”。
西晋人庾衮在抚养孤兄女的同时,还养育孤甥郭秀,史称“比诸子侄,衣食而每先之”。
永嘉之乱时乡里生活困难,郗鉴的“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
……鉴之薨也,翼追抚育之恩,解职而归,席苫心丧三年”,宋齐时人萧景先“少孤,有至性,随母孔氏,为舅氏鞠养”,萧梁时人颜协“幼孤,养于舅氏”。
北方同样有这种习惯。
西魏贺兰祥“年十一而孤,……长于舅氏,特为太祖所爱”,皇甫绩“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北齐时房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之所鞠养”。
杨坚的从叔杨元孙,齐亡前一直生活在邺城,“少孤,随母郭氏养于舅族”等。
由外家养育孤幼似乎是因为本家无父系亲属,其实未必。
生活在两晋之际的范汪,父死但叔父范坚、范广犹在世,却不由叔父养育,仍由母亲带回外家新野庾氏抚养。
房彦谦虽然父亲早亡,但伯父房豹与叔父房子贞仍在世,却也由其母兄抚养。
其它人因史料记载不详,不能确知他们是否有叔伯之类父系近亲,但多数有父系亲属是可以肯定的。
据本传,魏舒有“从叔父魏衡”,曾任吏部郎。
荀勖是否有叔父,史无明文,不过,其曾祖荀爽兄弟众多,号称“八龙”,子孙成群,魏晋时更是名人辈出,稍远一些的父系亲属相当多。
像颜协、萧景先等同样不乏父系亲属。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由母家来抚养,很值得玩味。
有时甚至母死父在,孩子也要交给母家抚养。
史载,晋武帝元杨皇后:
母天水赵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爱,亲乳养后,遣他人乳其子。
及长,又随后母段氏,依其家。
史书称皇后之父“早卒”,不过,在其父杨文宗死去前,其母已先亡故,因而将皇后转交“舅家”抚养,不再同父亲生活在一起,其父续娶了段氏,不久故去,皇后又转由后母养育。
皇后与其舅家感情很深,司马炎即位后“后追怀舅氏之恩,显官赵俊,纳俊兄虞女粲于后宫为夫人”,以示报答。
其父死后,她又依后母家,其实她尚有至少三个叔父在世,即杨骏、杨济与杨珧。
杨皇后为东汉大儒名臣杨震之后,祖上四世三公,经学传家,这样一个家庭中犹保存这种习惯,其它家庭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例子是宋武帝刘裕。
他幼年母死,父在,也“养于舅氏”,并改名奇奴为寄奴。
其父后娶继母,他“事继母以孝谨称”。
史书中记载的这类事例不多,但它们的意义很值得思考。
家庭的一个基本职能是抚育后代,一旦父母一方或双方离世,最普遍的是由亲属来接替抚养。
具体由哪方亲属来接替抚养后代是衡量接替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的重要标准。
汉魏六朝时期存在不少由父方亲属抚育孤幼的事例,同样可以见到许多返诸母家,由外亲赡养的情况,后者表明当时母方亲属在家庭生活中同样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3)舅甥关系密切与母家关系密切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外甥与舅舅间存在着亲密联系。
舅虽为男性,但他与外甥的关系是沿着母方计算的,乃是体现母方关系的重要标尺。
汉代还有外甥为舅舅复仇的情况,《后汉书·翟酺传》记载,酺“以报舅仇,当徙日南,亡于长安”,翟酺为广汉雒人,这一带似乎保留不少母系的遗存,《华阳国志·蜀志》“汶山郡·汶山县”云(该县)“贵妇人,党母族”,或以为汶山与雒几相毗邻,风俗接近之故。
实际不然。
在其它地区还可找到类似的事例。
同书《郭泰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记述的太原界休人贾淑“为舅宋瑗报仇于县中,为吏所捕,系狱当死”,后赖郭泰活动才得免死。
当时太原郡北邻雁门,西接西河,常受少数族影响,太原则为汉族聚居区,贾淑的行为不是受外来影响所至,而是与母方亲属关系密切的自然表露。
文献记载中汉人为父亲及父系亲属(如从父、兄弟、儿子)报仇的较多,据统计有26例;为母亲复仇的有3例,加上上述2例,为母方亲属复仇的共5例。
后者偏少,或与史书作者有意安排有关,前述贾淑为舅复仇事就不见于范晔的《后汉书》,而载于谢承的《后汉书》,若非李贤作注引此书,后人无从知道此事,类似的情况恐怕不止这一例。
根据人类学家对原始法的研究,宗族部落衰落以后,只有其最近亲属才有复仇的责任,如此看来,当时舅甥应属十分密切的亲属。
另外,直到东汉末年,还可以见到以外甥为嗣子的现象。
东汉末广陵人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孙吴的大将朱然本姓“施”,是朱治姐姐的儿子,因朱治初未有子,便以施然为嗣子,并改姓“朱”。
实际上,直至民国初年,没有子嗣的情况下,由甥继舅的习惯在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陕西与甘肃的部分地区还存在,其原因不少是因为舅甥血缘关系密切。
4)外家亦称“骨肉”实际生活中的母子以及与外家的密切关系在称呼中也有所体现。
在汉代,人们常常用“骨肉”或“骨肉至亲”来比喻父系亲属间的密切关系,《史记·田叔列传》所附禇少孙补的关于田仁事说,卫太子起兵时仁为司直,他“以为太子骨肉之亲”,闭城门,使太子逃亡。
太史公曰: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刘向为汉高帝刘邦异母弟刘交之后,他在上封事中说“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实际刘向与当时的汉元帝间的亲属关系已经很疏远了。
《三国志·夏侯尚传》注引《魏书》载诏曰“(尚)虽云异姓,其犹骨肉”,可知“骨肉”用来形容亲密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人同样将母子以及舅甥关系喻为“骨肉”。
汉元帝在给其弟东平思王刘宇母亲的玺书中调解母子的矛盾,说“闺门之内,母子之间,同气异息,骨肉之恩,岂可忽哉!
岂可忽哉!
”便是视母子为“骨肉”。
汉哀帝即位不久,司隶校尉解光上奏揭露王根的不法举动,其中一条是“先帝弃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便置酒歌舞,批评的理由是“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王根乃成帝母后王政君的异母兄弟,是成帝的庶舅,而非嫡舅,尽管如此,两人的关系也被视为“骨肉至亲”,若是亲舅甥,更是“骨肉”了。
东汉顺帝永和年间(136-141年),魏郡人霍谞的舅舅宋光被诬告关押在洛阳诏狱,霍谞奏记于大将军梁商,为其舅申冤,说到“谞与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随后据理说明宋光如何不可能妄刊诏书,最终打动了梁商,免罪释放了宋光。
霍谞在申诉中挑明他与宋光的舅甥骨肉关系,并指出因这种关系“言其冤滥,未必可谅”,转而从宋光的经历入手证明罪名不实,得以说服权臣。
他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显然是因为“舅甥”如“骨肉”是当时的普遍观念,两人关系过于密切,需首先排除,否则,只会弄巧成拙。
为《仪礼》作疏的唐人贾公彦解释外亲丧服时说“云‘外亲之服皆缌也’者,以其异姓,故云外亲,以本非骨肉,情疏,故圣人制礼无过缌也”,贾氏谓外亲“本非骨肉,情疏,”并非实情。
他去古已远,不无隔膜,难以凭信。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汉魏六朝时期的婚姻习俗。
当时尚未形成妇女“从一而终”,夫死不得再嫁的局面,离婚也较常见。
尽管西汉后期以降朝廷开始倡导妇女守节不再醮,但多数情况下,夫死,妻返母家并多再嫁,与夫家联姻关系终止。
与前夫所生的孩子若年幼也随母回母家抚养。
孩子多年生活在母家,与母方亲属的关系自然密切。
在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不高的背景下,这种情形必不罕见。
上引“先令券书”中出现的“妪”就曾经结婚三次并分别有孩子,即是一例。
3.九族、宗族的多种含义由上述事例看,汉魏六朝,特别是汉代,人们生活中不仅依托父方亲属,同样也依靠母方亲属,有时后者更重要。
因而当时所谓的“九族”与宗族不会仅指父系亲属。
今古文经学对“九族”有不同的解释,今文经学家认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古文经学家则以为“九族”仅限于父宗,为上至高族,下至玄孙。
两说孰是孰非,长期聚讼纷纭,迄无定论。
“九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经学家们主要是在注经时产生的不同的理解,不过,当时,人们也常常使用“九族”一词,它既见于皇帝的诏令中,也出现在史书的描述中。
根据上文的讨论,如果不过多拘泥于数字的多寡,而关心亲属范围的话,今文经学的解释显然更切近汉代的实际。
细绎文意,文献中不少地方出现的“九族”,指的不仅是同姓。
《汉书·高帝本纪下》记载七年(前200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此条不见于《史记·高祖纪》,原因不详。
因西汉初年外戚亦称“宗室”,这里所谓的“九族”显然包括外戚,只有依今文经学家的理解才能说得通。
《后汉书·刘般传》记载西汉末“般数岁而孤,独与母居”,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