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士大夫精神横遭掩埋的历史悲悯.docx
《周作人与士大夫精神横遭掩埋的历史悲悯.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周作人与士大夫精神横遭掩埋的历史悲悯.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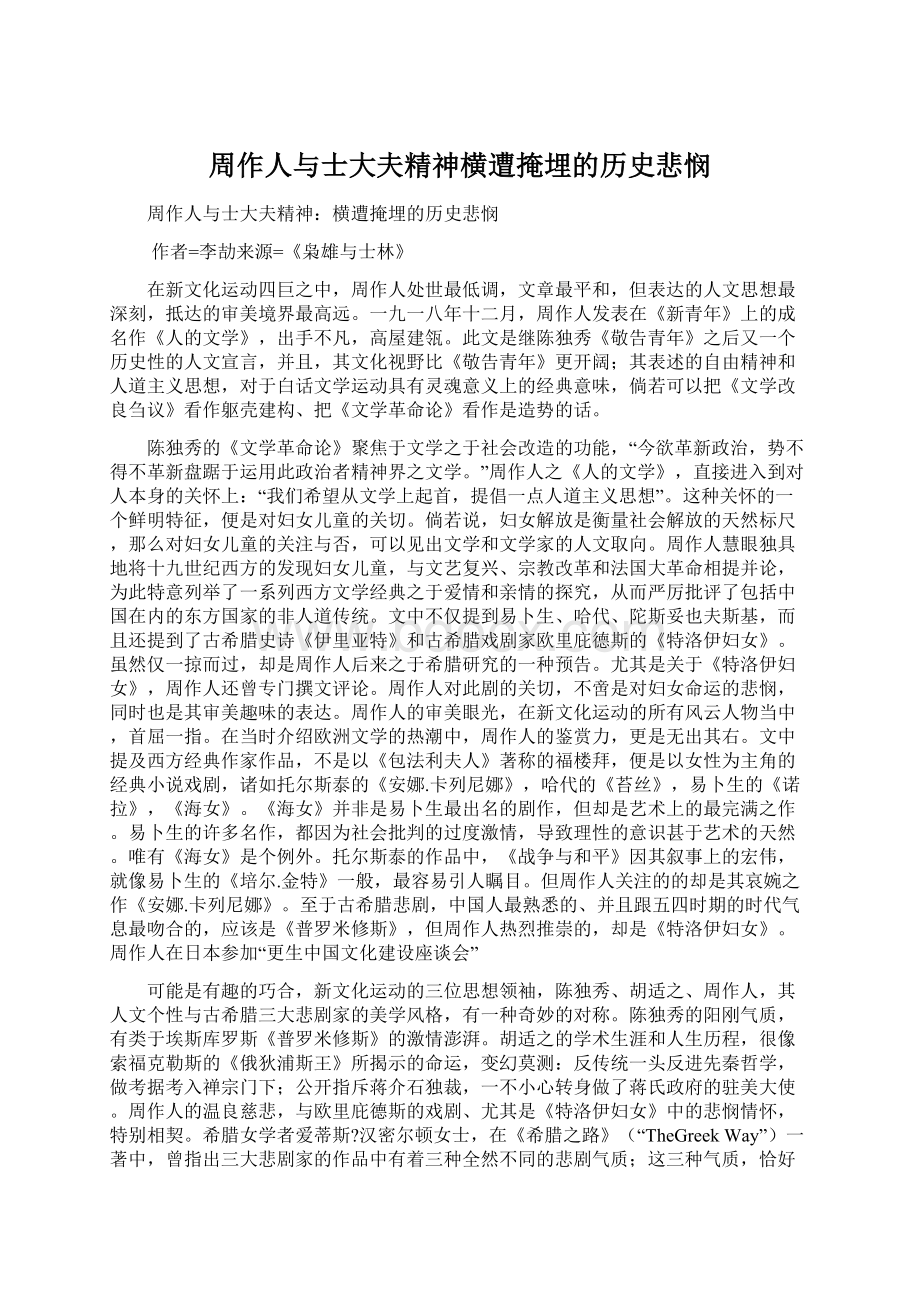
周作人与士大夫精神横遭掩埋的历史悲悯
周作人与士大夫精神:
横遭掩埋的历史悲悯
作者=李劼来源=《枭雄与士林》
在新文化运动四巨之中,周作人处世最低调,文章最平和,但表达的人文思想最深刻,抵达的审美境界最高远。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成名作《人的文学》,出手不凡,高屋建瓴。
此文是继陈独秀《敬告青年》之后又一个历史性的人文宣言,并且,其文化视野比《敬告青年》更开阔;其表述的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对于白话文学运动具有灵魂意义上的经典意味,倘若可以把《文学改良刍议》看作躯壳建构、把《文学革命论》看作是造势的话。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聚焦于文学之于社会改造的功能,“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周作人之《人的文学》,直接进入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上:
“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
这种关怀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对妇女儿童的关切。
倘若说,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标尺,那么对妇女儿童的关注与否,可以见出文学和文学家的人文取向。
周作人慧眼独具地将十九世纪西方的发现妇女儿童,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为此特意列举了一系列西方文学经典之于爱情和亲情的探究,从而严厉批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非人道传统。
文中不仅提到易卜生、哈代、陀斯妥也夫斯基,而且还提到了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
虽然仅一掠而过,却是周作人后来之于希腊研究的一种预告。
尤其是关于《特洛伊妇女》,周作人还曾专门撰文评论。
周作人对此剧的关切,不啻是对妇女命运的悲悯,同时也是其审美趣味的表达。
周作人的审美眼光,在新文化运动的所有风云人物当中,首屈一指。
在当时介绍欧洲文学的热潮中,周作人的鉴赏力,更是无出其右。
文中提及西方经典作家作品,不是以《包法利夫人》著称的福楼拜,便是以女性为主角的经典小说戏剧,诸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苔丝》,易卜生的《诺拉》,《海女》。
《海女》并非是易卜生最出名的剧作,但却是艺术上的最完满之作。
易卜生的许多名作,都因为社会批判的过度激情,导致理性的意识甚于艺术的天然。
唯有《海女》是个例外。
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因其叙事上的宏伟,就像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一般,最容易引人瞩目。
但周作人关注的的却是其哀婉之作《安娜.卡列尼娜》。
至于古希腊悲剧,中国人最熟悉的、并且跟五四时期的时代气息最吻合的,应该是《普罗米修斯》,但周作人热烈推崇的,却是《特洛伊妇女》。
周作人在日本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可能是有趣的巧合,新文化运动的三位思想领袖,陈独秀、胡适之、周作人,其人文个性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美学风格,有一种奇妙的对称。
陈独秀的阳刚气质,有类于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的激情澎湃。
胡适之的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很像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所揭示的命运,变幻莫测:
反传统一头反进先秦哲学,做考据考入禅宗门下;公开指斥蒋介石独裁,一不小心转身做了蒋氏政府的驻美大使。
周作人的温良慈悲,与欧里庇德斯的戏剧、尤其是《特洛伊妇女》中的悲悯情怀,特别相契。
希腊女学者爱蒂斯?
汉密尔顿女士,在《希腊之路》(“TheGreekWay”)一著中,曾指出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中有着三种全然不同的悲剧气质;这三种气质,恰好对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三位思想领袖的个性、人生和命运。
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乃是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一个失败城邦所遗留的孤儿寡母,如临深渊,却尊严犹在。
周作人的文学生涯,有如废墟下的弱草;早先体现在一篇篇著名文章里的人文关怀,全都被历史深深地掩埋。
极尽悲苦,却依然顽强。
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的革新文学、革新政治的救世倾向不同,周作人之《人的文学》旨在“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基于如此人道主义的立场,周作人在稍后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平民文学》一文中给新文学作出两个阐释:
“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情。
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 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
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
”其阐释所指出的四个要点:
人间的悲欢,人类的视野,真挚的文体,个人的视角;可以说,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点的文学精神所在。
比起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更具有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革新意味。
《文学革命论》中极其强烈的救世意识,潜伏着又一种文以载道倾向;而周作人所阐述的文学精神,既以人为基点,又以人为指归。
换句话说,周作人所说的文学精神,并没有必须承担救世义务的涵义在其中。
因此,周作人意味深长地指出,文学,“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
此语看似平淡,骨子里却石破天惊。
轻轻一下,便推倒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演义传统。
那个传统崇尚力气,崇尚拳头,崇尚杀人如麻,同时又崇尚效忠主子。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关羽崇拜,武松崇拜,黄天霸崇拜,诸如此类有人可杀、有主可忠的所谓好汉崇拜。
中国式的传统演义,可能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创伤最集中的流露。
虽然在艺术成就上有高低之分,但在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大同小异。
偌说二十四史基于视儒家为正统的历史观,那么从说书、评话及话本嬗变而成的演义小说,则是老百姓的喜闻乐见。
正史尚且难免篡改之嫌,演义更是杜撰到荒诞不经的地步。
惟有其间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纲常,倒是始终一脉相承。
比起正史,演义当然更加离谱,也更加赤裸裸:
该奴才时更奴才,该流氓时更流氓。
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文学和服务文学,实质上是因袭了演义的传统:
忠奸分明,好人与坏人的老套故事。
写来写去,无非是褒扬如何忠于党的奴才,讴歌以造反有理始、为主义献身终的愚夫愚妇。
从演义文学的这种绵绵不绝,可以看出周作人之于文学的人文主张,会遭到什么样的历史命运。
对英雄豪杰的拒绝意味着对日常人生的关注。
这样的关注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中国文学史上,及至晚明,蔚为风尚。
明末小品,由此成为继唐宋散文之后的又一文学大观。
既有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又有竟陵派旨在寄托心灵的“幽深孤峭”,更有张岱的梦寻梦忆、归有光的亭记亲情。
这两位小品大家的经典作品,既开李渔的《闲情偶寄》之先河,又启《红楼梦》的儿女世界之帷幕。
周作人之于明末小品的人文意蘊,可谓息息相通。
周作人不仅以其散文创作成为明末小品的集大成者,而且特意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明末小品与五四新文学从文学精神上作了明确的衔接。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匡正。
周作人藉此不仅在白话和文言的区别上,而且更在文学精神上,对新文学作出了历史性的定义:
文学乃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东西。
这样的定义无疑来自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
或者说,周作人是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所阐述的文学精神,勾勒从文言到白话的文学流变,区分言志和载道两种传统的差异所在,进而认定;诗可以言志,文亦可如是。
周作人后来解释说:
“不佞从前谈文章谓有言志载道两派,而以言志为是。
或疑诗言志,文以载道,二者本以诗文分,我所说有点缠夹,又或疑志与道并无若何殊异”。
周作人对文学独立性的如此强调,不仅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与鲁迅的听将令一说,泾渭分明。
周作人由此标举明末小品与新文学的渊源,并且在其散文写作中身体力行。
仅就文学的承继性而言,周作人无疑是张岱、归有光的白话文传人;必须指出的乃是,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人文气度上,皆远胜于明末诸子。
林语堂有评如是:
“周作人不知在哪里说过,适之似‘公安',平伯废名似‘竟陵',实在周作人才是公安、竟陵无异辞。
”其实,周作人小品岂止只是公安、竟陵?
史学世家出身的张岱,家风俨然,即便写作《西湖寻梦》、《陶庵忆梦》那么理当有些飘忽的小品文字,也遵循其“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宗旨,落笔实实在在,犹如刀削斧劈。
张岱的文学宗旨,与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提出的第二条文学主张,倒是不谋而合:
“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然而,彼此写出的小品,却迥异其趣。
张岱的两梦,固然能于简洁中抵达精致细腻,却过于实在,全然史志地理,至多也是游记笔法。
即便时时引用古人诗篇,也难以构成中国写意艺术通常具有的那种空白间的想像余地。
而事实上,张岱的两梦并非仅仅是写景状物,无所寄托。
“皇明无史乘,五凤属谁修?
九九藏《心史》,三三秘禹畴。
”以诗言志观之,张岱的寄托不小,而且心事苍茫,有道是:
“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故张岱在《陶庵忆梦》自序: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
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
”如此激越,足以道出张岱小品的心绪背景和忧国伤怀的人文底蕴。
只是后面两句,不无夸张:
“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感觉有点像抱着小皇帝蹈海自尽的陆秀夫。
被审判的周作人
张岱论说宋人名画,曾经透露心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
……嗟乎!
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
择端此图,即谓忠简请回鸾表可也。
”不才于异国他乡,华盛顿DC的国会图书馆,曾在此画的仿真卷跟前驻足良久,却怎么也感受不到张岱的如此一番深意。
同样,阅读张岱的《西湖寻梦》,感觉犹如旅游手册;《陶庵忆梦》中有些篇什,不时会冒出些许失意的心境,仿佛柳宗远被贬黜后的郁闷,却并不见国破山河在的苍凉,更无“请回鸾表”的殷切。
张岱的两梦,本当是性灵文字,却因为下意识里存有“请回鸾”念头,反而在境界上,失之局促。
且不说所谓深意写得过于隐晦,即便坦然道出,也不见得如何高远。
小品散文的凝炼,贵在神韵的有无;而神韵的有无,又取决于精神上的底气充沛和想像力的丰富与否。
面对山河的感慨,可以寄托历史的兴衰,也可以诉诸人世的沧桑,更可以表达内心的体悟,不必拘泥于王朝的消长起伏。
再说,将如此一番良苦用心深隐于字里行间,就算是同代人,都难以领会,更毋需说隔了好几代的后人。
张岱的苦心孤诣,虽然可以理解,但于性灵小品毕竟有些相隔。
人们完全有理由将张岱的《西湖寻梦》、《陶庵忆梦》,与李渔的《闲情偶寄》放在一起欣赏,而不必揣摸深隐于背后的家国兴亡。
张岱
相比之下,周作人的小品,同样的精致细腻,却有着张岱小品所缺乏的在精神上的凌空蹈逸。
比如《乌蓬船》,第二人称的书信体。
初读只见浓郁的乡情,及至细细回味,尤其是联想到此信乃是自己写给自己的自言自语,顿时,一股苍凉,尽在不言之中。
再如《故乡的野菜》,将采食野菜与清明扫墓浑写,融妇女儿童的日常画面与若续若断的悼亡习俗为一体。
短短的篇什,生命的情趣和死者的寂寥,却淋漓尽致,透出一种生死两茫茫的恢宏。
又如《北平的春天》,通篇看不出北平有什么动人的春天景致,作者不过是在寻找而已。
寻找良久,又似乎并没有找到:
“北平到底还是有他的春天,不过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叫人有时来不及尝他的味儿。
”最后轻轻一句:
“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
”掩卷之际,不由想起陈子昂的吟咏:
独怆然而涕下。
相对于张岱的寻梦忆梦,归有光的小品长于刻画日常亲情。
诸如《项脊轩记》的思念亡妻,《思子亭记》的痛失爱子,即便《寒花葬志》的追忆一个小丫环,寥寥几笔,活泼的人物和生动的想念,便跃然纸上。
常人常情,既是归有光小品所长,又是其短。
要而言之,情感真挚,悲悯无多。
这可能不啻是归有光小品的特征,也是明末小品共有的问题。
且不说其它,同样是小丫环形象,到了《红楼梦》的大观园里,栩栩如生之外,别有一种意蕴在其中。
文学境界的大观和小观,不在于文字的长短,也不在于是长篇巨作,还是精炼短制,而在于悲悯的有无,或者浓淡。
卡夫卡作品,短制如《变形记》,长篇如《城堡》,或者《审判》,无一例外地具有悲悯的力量。
悲悯,也同样是周作人小品的特色。
一如其谦卑的行文品质,与卡夫卡天然相通。
《济南道中》刻画以唱歌跳舞换蒲桃干吃的三岁山东小男孩;起先只是童趣盎然,突然跳出随口一句“不唱也给我罢”,令人心中不由一凌,具有竟无语凝噎的效果。
《若子的病》通篇是爱女得病后的一阵忙乱,至结尾处却猛然一静:
“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够写出这篇东西来,可见我的凌乱的头脑也略略静定了”。
亲情浓至极处,最后归于一下深深的吐纳;好比乱云飞渡之后一片蓝天白云的静谧,端得是,回味无穷。
《玄同纪念》似乎很不经意地留下如此细节:
“十日下午玄同来访,在苦雨斋西屋坐谈,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
”及至文章将尽,又以一句“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遥相对应,以此暗示玄同见之所见,避之所避。
通篇不提苦住一词,却让人尝尽苦住之味;从而使文中这联悼念亡友之词愈加触目惊心: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叮。
难怪不才向周作人当年日军侵占时期的北大学生、散文家邓云湘先生,问及苦住庵主,两鬓霜白的邓先生特意直直身子,清清嗓子,才肃然作答:
知堂老人,一生,没有做过坏事。
朱光潜曾在《论小品文》中说:
“我常觉得文章只有二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
”周作人的散文,无疑具有自言自语的品质,并且在审美上足以与《红楼梦》和卡夫卡小说相媲美。
在文学上抵达如此境界,新文学诸子当中,惟周作人而已。
究其原委,也许得归之于生命本身的底蕴。
周作人的小品意蕴,可以从他的二首《五十自寿诗》中得以读解。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玩骨董、种胡麻也罢,咬大蒜、拾芝麻也罢,最后全都归于苦茶的品味。
所谓“前世出家今在家”,既可读作在家的无奈,又可解为持出家心态、度在家人生。
“不将袍子换袈裟”的确切注解,乃是《红楼梦》的“枉入红尘若许年”。
当荷尔德林领悟人类诗意地居住在这地球上时,可能不知道东方哲人的存在,被诉诸什么样的诗意。
庄子与人激辩之际,内心有一种超然物外的轻松;老子骑着青牛西去,更是一派超凡出俗的潇洒。
及至周作人面对浊世的沉沦,若选择王国维式的绝决,无奈尘缘未断;如贾宝玉那般悬崖撒手,又放不下家累。
于是,惟苦住而已。
这与李叔同的遁入空门,殊途同归。
修持律宗,是寺庙里的苦住;闹市苦住,是尘世间的律宗。
正如王国维和贾宝玉可以参照着读解,周作人与李叔同乃是同一种修行的两种不同方式。
无庸置疑,周作人的有些小品,颇具李渔式的闲情逸志。
说竹,谈养鸟,论骨董,品点心,诸如此类。
有人把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与林语堂混为一谈,不太确切,但也事出有因。
这就好比说李渔的才学,并不在曹雪芹之下,不算妄语。
倘若李渔能够大彻大悟,文字间透出悲悯情怀,那么差不多就是曹雪芹了。
但李渔跨不过的,就是这道门坎。
林语堂与周作人的差距,也在于如此这般的相隔一层纸。
林语堂有接近周作人的文字根底,但林语堂捅不破人世间的那层纸。
因此,林语堂的《吾土吾民》之于中国历史文化介绍,虽然有趣,却失之浮光掠影。
就学术性而言,还不如其《苏东坡传》来得贴切。
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标题颇有以烟云之轻、反衬尘世之重的涵义在内。
然而,小说中呈现的凝重,却仅限于生存的艰辛,并无存在的低吟,更看不见萦绕不去的灵魂挣扎。
生存还是存在的微妙区别,轻轻划开了周作人与林语堂的界分,也标出了周作人小品与明末小品的泾渭。
顺便一句,林语堂的小品与归有光倒是十分相近。
分别在于,林文富态,有如王维的喜好空灵;归文清贫,一派郊寒岛瘦的简朴。
李渔的《闲情偶寄》,其经典足以与后人钱钟书的《管锥编》遥遥相望。
但李渔悟不出周作人在《生活的艺术》一文中所揭示的真谛:
“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
”这已然是荷尔德林的中国版。
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侧重古希腊文学中的崇高境界,周作人的审美情趣则在于东方式的柔婉如水。
尼采会从酒神引发悲剧的诞生,周作人谈论喝酒,却相当婉约:
“一口一口的吸,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
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
”酒神的酩酊大醉,固然阳刚气十足;然微醺,则是另一种饮酒的境界。
适可而止,浅尝辄止,点到为止,诸如此类的中国成语,确实含有中庸的意思。
但这又未尝不是一种意境。
周作人虽然反对祖先崇拜、厌恶三从四德之类的伦理纲常,却并不排斥适可而止的中庸之道。
这可能就是“半是儒家半释家”的意思所在。
周作人抨击礼教的同时,也有如此感叹:
“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
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
”倘若周作人知道历史正在滑入先禁欲后纵欲的唯物主义时代,或许应该为自己能够生在清末、长于民国,感到些许庆幸。
李渔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被人发表之后,和者甚众,轰动一时。
鲁迅因此发了一通感慨: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
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这番感慨的最后几句,着实深刻;但最好留给多年以后审判周作人的蒋介石政府悉心领会,与和诗的群公无多相干。
至于周作人的自寿诗,鲁迅也只读出其讽世之意,并不解其悲悯情怀。
悲悯是一种了悟,也是一种心胸,更是一种宽容。
这些境界,鲁迅都不曾抵达,遑论有所领略。
悲悯的境界,是周作人小品之灵魂,却是鲁迅文章之短缺。
周作人论及茶食点心时的精致,并非全然李渔式的闲适。
即便退一步论说,《闲情偶寄》中的津津乐道,也自有一番意蕴在其中。
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广东籍美国华侨,论及毛泽东时代,突然脱口而出:
中国人怎么会让一个只知道吃红烧肉的人统治了这么些年?
倘若周作人听见如此素朴的言谈,没准会,微微一笑。
文化的有无,根本不需要特意标榜;一如周作人的《关于苦茶》所言:
“口渴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
对于茶有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
这未必然。
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
这也未必然。
那么诗里为什么那么说,为什么又叫做庵名,岂不是假话么?
那也未必然。
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
”
明白了饮食中的文化意蕴,就能读懂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为何如此论说日本人:
“我们要规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
”仿佛是生怕人们听不懂,周作人又特意阐释道:
“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
”但把周作人视作汉奸的国人,依然没有听懂。
倒是有个叫做片冈铁兵的日本文人,听懂了周作人在文章中对文化的自信,把周作人叫做“反动的文坛老作家。
”因为在周作人心目中的国家,是以文化来定义的。
而只要中国文化不会被灭亡,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有亡国之虞。
蒙古人和满族人都先后入主中原,中国文化非但没有灭亡,入主者反而被同化了。
因此,所谓亡国论,通常是把王朝和国家混为一谈的蒙昧。
由此定罪汉奸,更是源自枭雄们角逐天下的需要。
中国式的定罪,通常是皇帝钦点,愚民欢呼。
蒋介石的没有文化,与其说是体现在读不懂胡适,不如说更是体现在无知于周作人是怎么回事。
周作人的命运,不仅鲁迅有所预感,就是周作人自己,也早就怀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奈。
对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了解和认知,周氏两兄弟的洞察力,不相上下。
早在《再谈油炸鬼》一文中,周作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古罪人。
故主和是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国人在战与和上面的思维定势和道德判断,归根结底在于思想的蒙昧。
周作人完全明白个中原委,在同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
“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
”“秦桧的案,我认为都应该翻一下,稍微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
”
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必定与不懂宽容的专制政府长年作伴。
而宽容的阙如,又必定不断地制造出愚昧的专横。
苦住在如此一个残破的文化空间,能够存活已经不易,更何况想要恪守思想的自由。
中国人的老于世故通常在于,要么做八面玲珑的奴才,要么做震摄天下的枭雄。
夹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心灵守护者,是最艰难,也是最尴尬的。
由此可以想见,周作人的苦住,是什么样的涵义。
由此也可以明白,周作人面对兄弟失和的难题时,向兄长表示了什么样的宽容。
不管周氏兄弟失和的个中原委如何,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周作人写给鲁迅的那封信,谦和温良,雍容大度。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愿你安心,自重。
以这样的心胸,论说他人作品,至少不会有失公允。
及至抵达至境,便是周作人于《志摩纪念》中这番话:
“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迎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
”如此审美意趣,虽说也可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或者严羽的《沧浪诗话》中见到,但其空灵,其高远,既逮及庄子境界,又暗合中国最始源的无言文化。
那种文化的审美方式,用高山流水般的相知,方可表达。
周作人的文学评论,虽非伯牙子期那样的绝响,却为一般评家难以比肩。
论及中国白话散文,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中如此写道:
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
用三种水果比喻三个流派,准确而隽永,清新又别致。
这样的笔法,与李叔同抄写佛经的墨迹,庶几相类:
柔柔地透出一种无言的空寂。
其中,青果之喻,既是俞平伯和废名散文的形容,又可看作周作人的夫子自道。
史家将俞平伯、废名和周作人归入同类,从风格上说是成立的。
但是在境界上,周作人更加深邃高远。
这就好比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群星灿烂,却又和而不同,并且还参差不齐。
从成就高低而言,俞平伯、废名有类于德加、修拉,周作人好比凡高,虽然一者似水,一者如火。
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有时还可以加上林语堂,这一派散文,以闲适概括,有失粗疏。
虽然林语堂本人倡言过“以闲适为格调”。
从人生姿态上说,这是一群与世无争的文人雅士。
从精神风貌上说,这是一群既不肯随波逐流又不愿争先恐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倘若说他们有所追求,那么无非追随自己的心境或自己的性情。
他们既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流派,又是民国时代的一道人文景观。
而周作人,是他们当中的灵魂人物。
周作人的文章,下笔远比鲁迅要轻淡,却比鲁迅更难真正读懂。
这就好比参禅,明白的人,不说也明白;不明白的,怎么说也不明白。
而周作人的苦住,比周作人的文章,更难领会。
相比之下,胡适的人生选择,总是最能让人看懂的。
日军进犯期间,胡适受命赴美,出任大使,极具抗日色彩从而无限风光;国共内战的结果行将揭晓之际,胡适毅然飞往台湾,避难。
这让后来许多吃尽苦头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得不羡慕胡适有先见之明。
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的苦住,每每与胡适的选择,反其道而行之。
若说胡适的选择是一种明智,那么周作人就有愚笨之嫌。
但要是周作人的苦住含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品质,那么,究竟谁更勇敢,就很难判断了。
这里不妨援引一九三八年八月,胡适从伦敦写给周作人的一首白话诗: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第二年九月,周作人也写了一首白话诗回复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