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化学的发展基团理论和一元论.docx
《有机化学的发展基团理论和一元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有机化学的发展基团理论和一元论.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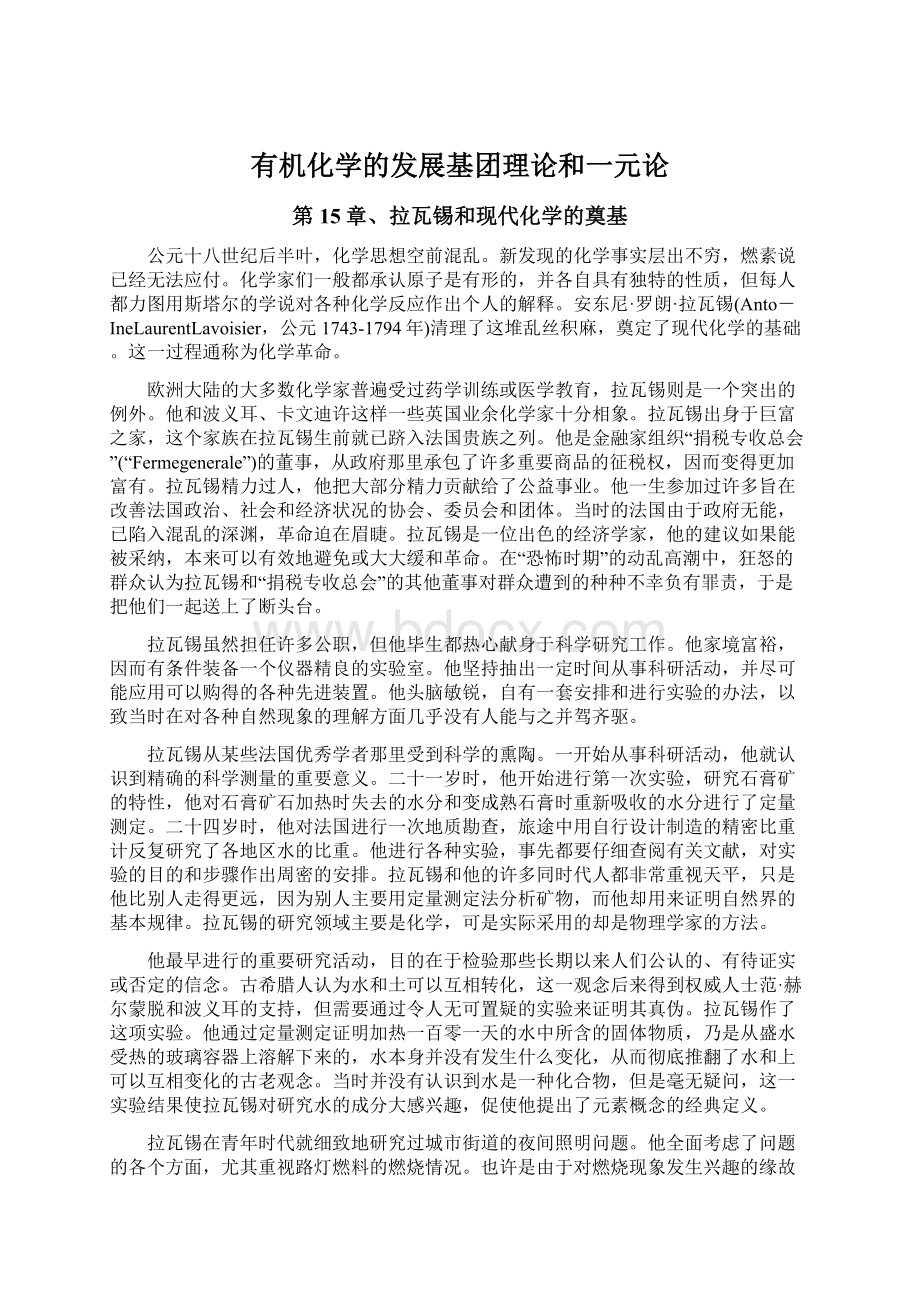
有机化学的发展基团理论和一元论
第15章、拉瓦锡和现代化学的奠基
公元十八世纪后半叶,化学思想空前混乱。
新发现的化学事实层出不穷,燃素说已经无法应付。
化学家们一般都承认原子是有形的,并各自具有独特的性质,但每人都力图用斯塔尔的学说对各种化学反应作出个人的解释。
安东尼·罗朗·拉瓦锡(Anto-IneLaurentLavoisier,公元1743-1794年)清理了这堆乱丝积麻,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
这一过程通称为化学革命。
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化学家普遍受过药学训练或医学教育,拉瓦锡则是一个突出的例外。
他和波义耳、卡文迪许这样一些英国业余化学家十分相象。
拉瓦锡出身于巨富之家,这个家族在拉瓦锡生前就已跻入法国贵族之列。
他是金融家组织“捐税专收总会”(“Fermegenerale”)的董事,从政府那里承包了许多重要商品的征税权,因而变得更加富有。
拉瓦锡精力过人,他把大部分精力贡献给了公益事业。
他一生参加过许多旨在改善法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协会、委员会和团体。
当时的法国由于政府无能,已陷入混乱的深渊,革命迫在眉睫。
拉瓦锡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他的建议如果能被采纳,本来可以有效地避免或大大缓和革命。
在“恐怖时期”的动乱高潮中,狂怒的群众认为拉瓦锡和“捐税专收总会”的其他董事对群众遭到的种种不幸负有罪责,于是把他们一起送上了断头台。
拉瓦锡虽然担任许多公职,但他毕生都热心献身于科学研究工作。
他家境富裕,因而有条件装备一个仪器精良的实验室。
他坚持抽出一定时间从事科研活动,并尽可能应用可以购得的各种先进装置。
他头脑敏锐,自有一套安排和进行实验的办法,以致当时在对各种自然现象的理解方面几乎没有人能与之并驾齐驱。
拉瓦锡从某些法国优秀学者那里受到科学的熏陶。
一开始从事科研活动,他就认识到精确的科学测量的重要意义。
二十一岁时,他开始进行第一次实验,研究石膏矿的特性,他对石膏矿石加热时失去的水分和变成熟石膏时重新吸收的水分进行了定量测定。
二十四岁时,他对法国进行一次地质勘查,旅途中用自行设计制造的精密比重计反复研究了各地区水的比重。
他进行各种实验,事先都要仔细查阅有关文献,对实验的目的和步骤作出周密的安排。
拉瓦锡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非常重视天平,只是他比别人走得更远,因为别人主要用定量测定法分析矿物,而他却用来证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
拉瓦锡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化学,可是实际采用的却是物理学家的方法。
他最早进行的重要研究活动,目的在于检验那些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有待证实或否定的信念。
古希腊人认为水和土可以互相转化,这一观念后来得到权威人士范·赫尔蒙脱和波义耳的支持,但需要通过令人无可置疑的实验来证明其真伪。
拉瓦锡作了这项实验。
他通过定量测定证明加热一百零一天的水中所含的固体物质,乃是从盛水受热的玻璃容器上溶解下来的,水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从而彻底推翻了水和上可以互相变化的古老观念。
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水是一种化合物,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实验结果使拉瓦锡对研究水的成分大感兴趣,促使他提出了元素概念的经典定义。
拉瓦锡在青年时代就细致地研究过城市街道的夜间照明问题。
他全面考虑了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重视路灯燃料的燃烧情况。
也许是由于对燃烧现象发生兴趣的缘故,他进入这一领域后,终生乐此不疲。
公元1772年,他开始研究燃烧和焙烧现象,进行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工作,最后直接导致了新化学的创立。
这一年,他和其他一些化学家证明,如果能获得足够的高温,金刚石也能在空气中燃烧。
大凸透镜是当时获取高温的最好器具。
利用这种工具,不论有无空气,都能在预定的位置上获得高温。
拉瓦锡在研究金刚石燃烧问题的同时,又去多方了解十八世纪化学家们花费大量时间对气体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他很熟悉黑尔斯的实验,实验表明气体可以包含在化学物质之中,并且可以从这些物质中释放出来。
拉瓦锡在早年所做的实验中,还使用过黑尔斯介绍的仪器。
不久以后,他读到布莱克的著作,感到非常敬佩。
他认识到布莱克实验相当重要,因而更加重视定量测定。
尤为重要的是,他从黑尔斯的研究工作和布莱克关于固定空气的实验中,认识到气体能够化合,又能通过化学反应从化合物中释放出来。
拉瓦锡也很熟悉英国的卡文迪许和普利斯特列的气体研究工作。
因此,他掌握有研究燃烧现象的丰富资料。
人们往往强调他没有发现过什么新化合物或新化学反应。
他的杰出天才主要表现在他能看到旧理论的主要弱点,并能把有用的事实和更正确、更全面的新理论结合起来。
继金刚石实验之后,拉瓦锡又转而研究磷和硫的燃烧生成物。
公元1772年底,他在向科学院提出的报告中指出,磷燃烧时与空气结合,生成“磷的酸精”(即磷酸),比原来的磷要重。
硫经过同样的反应可生成“硫酸”。
拉瓦锡用当时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将布莱克观测气体起化合作用的结果推进了一步。
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在开始工作的最初阶段就已认识到金属的煅烧是与磷和硫的燃烧十分类似的现象,金属煅烧后也和空气发生化合作用。
他紧接着用锡和铅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实验,首先证明波义耳关于金属煅烧后重量有所增加是由于吸收了火微粒的观点是错误的。
锡在密封容器中煅烧时,只有一部分变成了金属灰(即氧化锡),但在容器启封前,重量并没有增加。
启封时,可以听到空气冲进容器的声音。
毫无疑问,金属灰重量的增加是由于金属与空气发生化合的缘故。
拉瓦锡最初不能断定同金属发生化合的气体到底是布莱克所说的固定空气(即二氧化碳)还是普通空气,或者是空气中的一部分。
他非常倾向于后一种情况。
他注意到用木炭加热金属灰,能还原出金属,并且生成他断定是固定空气的某种气体。
公元1774年10月,普利斯特列来到巴黎与拉瓦锡会晤,他谈到自己研究了红色沉淀物,在加热这种沉淀物时得到一种奇怪的结果。
有人认为,拉瓦锡立即意识到这和他的工作密切相关。
看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两人当时都没有看清这种关系,只是后来人们才看出,普利斯特列做出的更加精确的实验是符合拉瓦锡的理论的。
拉瓦锡于公元1775年4月把贝扬和普利斯特列的实验重做了一遍,并且初步写成一份实验报告。
他指出,用木炭加热红色沉淀物,能还原为汞,并生成固定空气,可见红色沉淀物是一种真正的金属灰。
他后来又用凸透镜单独加热红色沉淀物,进一步证实了普利斯特列和贝扬的意见,反应生成物是汞和一种新气体,而不是固定空气。
由此可见,在煅烧过程中与金属化合的,可能是空气的“纯净部分”。
这些研究成果在公元1776年和1777年又有了新发展。
拉瓦锡于1774年送交科学院《院刊》的报告,直到1778年才被刊载。
这一刊物经常发生类似的拖延现象。
拉瓦锡乘机修改了报告,赶在刊物出版之前把他的新成果和新观点写了进去。
这时他确信普通空气中只有一部分与金属化合,可见他已认识到空气是两种物质的混合物。
呼吸和煅烧金属时消耗的是比较纯净的部分。
他把剩余部分称为摩凡陀(Mofette),后来又借用一个希腊词,改称为“氮”(Azote),也就是“无生命”的意思。
公元1790年,查普特尔(Chaptal)又把它命名为“Nitrogen”(氮)。
顺便提一下,卢瑟福最初曾把氮叫做臭气。
拉瓦锡接着用纯净的空气(他这时称之为“最宜于呼吸的空气”)来做实验,这些实验表明,把木炭和金属灰一起加热时,此种空气即与木炭化合,这样生成的固定空气只能是木炭和最宜于呼吸的空气的化合物。
差不多与此同时,对动物的种种实验研究使拉瓦锡确信,最宜于呼吸的空气在动物体中,特别是在肺中与碳化合,有热散发出来。
他觉得这和实验室里的情况完全一样。
动物体温的热源问题从而得到了解释,虽然当时还无法说明这种热的生成机制。
不过,这是生物化学在发展过程中迈出的最初一步。
磷和硫的燃烧已被看成是这些元素和最宜于呼吸的空气起化合作用的结果,而且拉瓦锡还认为各种酸里都含有这种气体。
公元1779年11月,他建议将这种气体命名为氧(PrincipeOxygine),该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可构成酸类”。
拉瓦锡准备向燃素说直接发起进攻。
公元1783年,他向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发表于1786年。
他在该文中指出燃素说的许多弱点。
这些弱点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是只要承认每一燃烧过程都是与氧发生化合作用、同时能发出热和光的过程,那么,这些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拉瓦锡理论走向完备的最后一步是弄清水的组成。
这一步是在英国迈出的。
公元1766年,卡文迪许就已发现他所说的“易燃空气”在普通空气中可以燃烧,但他没有对燃烧的生成物进行鉴定。
公元1781年,普利斯特列发现,这种气体燃烧时会在空气中凝成露珠。
卡文迪许重做了普利斯特列的实验,收集了燃烧时产生的露珠。
他指出,这是纯净的水,同时还发现用电火花将易燃气体和(含有氧的)普通空气的混合物引爆时,会生成某种酸。
他迟迟没有公布自己的实验结果,而是继续对这种反应进行研究。
他发现,普通空气和适量的易燃空气的混合物爆炸时,会消耗净尽,剩下的只有一个很小的气泡,并有硝酸生成。
公元1894年,小气泡被确认为氩。
对微量的惰性气体能做出这样出色的观测,全要归功于卡文迪许的高明精湛的实验技巧。
卡文迪许认为易燃空气几乎就是纯净的燃素,而氧则是脱燃素的空气,于是他把水的生成说成是这两种气体的化合,也就是脱燃素空气和燃素结合的结果。
实验结果虽说到公元1784年才正式公布,但拉瓦锡在公元1783年就已听说有这种实验。
他立即领悟到这种实验的重要意义,并做出了正确的解释:
水是易燃空气和氧的化合物。
他重新进行这个实验和提出上述结论是公元1783年的事,但他将实验的全部结果送往科学院的《院刊》发表反而是公元1781年,正式公布的时间则是公元1784年。
由于付印屡遭延宕以及某些刊物记载的时间有误,因而造成一片混乱,再加上普利斯特列、瓦特、卡文迪许、蒙日和拉瓦锡几乎是同时研究水的组成问题的,结果在谁是真正的最早发现者这个问题上引起了很大争执。
各地的科学家虽说就彼此的工作情况经常互通声气,但对解决这一争议仍然无济于事,他们往往拒不承认互通声气这一事实。
意见不同的人士各执一端,纷纷卷入这场所谓“水的争论”,唇枪舌剑的争吵时有所闻。
姑且不论真正的最先发现者究竟是谁,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对水的成分做出最出色的实验证明者是卡文迪许,第一个提出正确解释的是拉瓦锡。
戴莫维在新命名法中建议把易燃空气命名为氢(Hydrogen),也就是“能生成水”的意思。
拉瓦锡的工作为化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条理性和系统性,但化学物质的命名法依然紊乱不堪。
拉瓦锡所用的物质,一直沿用着与物质的实际成分毫不相干的炼金术符号。
学生只有靠死记硬背才能掌握住他所接触的物质的名称,而这些物质的种类正在不断增多。
吉顿·戴莫维(GuytonDeMorveau,公元1737——1816年)感到这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最初信仰燃素说,但很快就转而支持拉瓦锡的理论体系。
公元1782年,他发表了一篇论述统一化学命名法的论文。
拉瓦锡对于任何能使化学变得有条不紊的方案自然会大感兴趣,所以同戴莫维建立了合作关系。
另外,还有两位支持拉瓦锡学说的人,克罗德·路易斯·相托雷(ClaudeLouisBerthollet,公元1748-1822年)和戴·佛克罗伊(A.F.DeFourcroy,公元1755-1809年),也一同为创立新概念而努力。
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化学命名法》(MethodeDeNomenclatureChimique)一书,该书于公元1787年在巴黎出版。
这本书论述的化合物命名原则,基本上仍为我们所沿用。
每种物质必须有一个固定名称。
单质的名称必须尽可能表达出它们的特征,化合物的名称必须根据所含的单质表示出它们的组成。
书中建议,酸类和碱类用它们所含的元素命名,盐类用构成它们的酸和碱命名。
这个体系简单明了,各地的化学家都乐于采用。
这本书很快被译成了所有各主要国家的文字。
随着拉瓦锡化学理论体系的传播,这一新命名法甚至在当时还算是科学边远地区的美洲,也占有了牢固的地位。
这时,拉瓦锡的理论已经相当完备,而且有了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理论。
同拉瓦锡交往密切的一大批法国化学家接受了这些新思想,但科学界的其他许多人却仍在尽力弥补燃素说的种种缺陷。
因此,拉瓦锡决定根据新原理写出一部化学教科书。
它要和化学教科书的旧传统实行彻底决裂,为未来几代化学家的工作打下新的基础。
公元1778至1780年间,他写出了书的提纲。
公元1789年,该书在巴黎问世。
这就是著名的《化学纲要》(TraiteElementaireDeChimie)。
它对化学的贡献,完全可以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物理学做出的贡献比美。
在这本书中,拉瓦锡十分详尽地论述了推翻燃素说的各种实验依据和以氧为中心的新燃烧学说。
他的观点基本上也就是现代化学家的观点。
他曾经这样写道:
“化学以自然界的各种物体为实验对象,旨在分解出它们,以便对构成这些物体的各种物质进行单独的检验。
”他根据这种说法,终于列出一张“属于自然界各个领域的、可视为物体所含元素的单质一览表”。
他承认这只是一张凭经验列出的表格,还有待于用新发现的事实加以修正,但它的基础却是可靠的化学原理,因而被公认为第一张真正的化学元素表。
拉瓦锡对各种化学现象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物,因而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的一些思想的束缚。
微粒说最初被引进时,热是一种运动形式的观念曾经风靡一时,现在它又让位给热和光是物质实体的主张了。
陈旧的“越自然要素”被抛弃了,并进而把一切都看作是物质了。
拉瓦锡对这种主张表示赞同,因此,他在元素表的最前面列入了光和热,并把热称为“热质”(Caloric)。
他虽说抛弃了燃素这一陈旧名称,但实际上热质却保留有燃素的某些特性。
他认为氧气是氧元素和热质的化合物,当氧气和某种金属化合时,热质逸出,在反应中以热的形式出现。
对于热的性质的这种看法和认为各种酸类都含有氧的观点,是拉瓦锡化学理论体系中最严重的两大错误。
这两大错误给化学家们造成不少困难,影响所及直到下一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
如除开热质不谈,《化学纲要》一书中列出的元素表倒是正确无误的,它显示出对酸性氧化物和碱性氧化物的性质都有深刻的了解。
拉瓦锡甚至还看出不易蒸发的钾碱和苏打可能都是化合物,而组成这些化合物的基本元素还是未知的。
《化学纲要》一书包含有极为重要的深刻思想。
我们可以看出,十七世纪初期以来,许多化学家都曾经隐约提到物质不灭的思想。
罗蒙诺索夫甚至已讲得一清二楚,但西方对他的大部分著作不甚了解,因而他在这一方面对科学思想的进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拉瓦锡最早阐述了这一思想,并且指出在化学中应怎样应用这一思想。
他的论述产生了实际影响。
在论述糖变酒精的发酵过程时,他指出,“无论是人工的或是自然的作用都没有创造出什么东西。
物质在每一化学反应前的数量等于反应后的数量,这可以算是一个公理。
”根据这一原理,他终于能写出下面的式子,显而易见,这正是现代化学方程式的雏形:
“葡萄汁=碳酸+酒精”
他自己已经意识到这种表述方式的重要性,所以又写道:
我们可以设想,把参加发酵的物质和发酵后的生成物列成一个代数式,再逐个假定方程式中的每一项都是未知数,然后能逐个算出它们的值,这样一来,即可用计算来检验我们的实验,再用实验来验证我们的计算。
我经常卓有成效地用这种方法修正实验的初步结果,使我能通过正确的途径重新进行实验,直至获得成功。
《化学纲要》一书在化学史上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
它产生了迅速而又广泛的影响,很快被译成各主要国家的文字,并且多次再版。
除少数几人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普利斯特列),所有的化学家都转而拥护这种新思想,化学科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纪元,取得了令人几乎难以置信的进步。
拉瓦锡在这本巨著出版后仅仅活了五年,而且是社会政治剧烈动荡的五年,当时,人们从事科学活动相当困难,但他却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坚持化学研究工作。
他和数学家拉普拉斯(P.S.La-Place,公元1749-1827年)一起研究动物的呼吸过程,后来又和青年同事阿芒·塞魁恩(ArmandSeguin,公元1765-1835年)一起继续工作,结果证明碳的化合物和氧化合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是动物体温的真正来源,人在从事体力劳动时氧的消耗量会有所增大。
这项工作成为十九世纪末叶德国的沃特和鲁布纳的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也是现代营养学的基础。
拉瓦锡在这项工作中研究过各种碳化物,并设计出一套先在氧气中燃烧碳化物,然后测定生成的二氧化碳和水的方法,这一方法现在仍然是有机分析的基础,只是他测得的数据很不精确。
拉瓦锡还提出过一项建议,在化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公元1778年以前,没有一份专门的化学刊物。
各种化学研究成果必须送到同时刊载其它门类的科学资料的刊物上发表。
拉瓦锡的许多论文曾遭到科学院《院刊》的长期拖延,迟迟未予发表,足可表明撰稿人受害匪浅。
公元1778年,洛伦兹·范·克列尔(LorenzVonCrell,公元1744-1816年)创办了第一份专门的化学刊物《化学杂志》(ChemischesJournal),陆续印行到公元1781年。
公元1784年,该杂志再次复刊,改名为《化学年刊》(ChemischeAnnalen),通称“克列尔年刊”,以示与波根多夫(Poggendorf)和李比希后来创办的刊物相区别。
“克列尔年刊”一直出版到公元1803年,刊载过大批重要论文。
曾和拉瓦锡一同出版过《化学命名法》的比埃尔·奥古斯特·阿德特(PierieaugustAdet,公元1763-1832年),在公元1787年也打算创办一份法文化学杂志。
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在公元1789年4月间,拉瓦锡、戴莫维、蒙日、柏托雷、戴·迪特里希(DeDietrich)、哈森弗拉兹(Hassenfratz)和阿德特联合印行了第一期《化学年鉴》,该杂志直到现在仍在出版,其中刊载了化学史上最关重要的大量文献。
公元1794年5月8日,拉瓦锡被送上断头台,终年五十岁,他的化学研究活动从此终止。
如果让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还能取得什么成就,现在也只能凭空臆测,不过,他实际作出的贡献,已足以使法国在化学上多年居于领先地位,并且使化学走上了在很多方面都能大大发挥潜力的康庄大道,至于在这些方面究竟会取得什么成就,人们至今仍然无法充分估计。
第16章、原子结合定律
几百年来,许多化学家都在专心致志地研究燃烧现象,拉瓦锡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今人满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时,他还揭示出定量方法的作用,明确规定了化学的任务。
借助于这些新出现的远见卓识,化学家们方才有可能去研究他们关心的其它问题,并且满怀信心地认为,经过一番新的努力,这些问题也一定能迎刃而解。
十九世纪初叶,大家最关心的是纯化合物的结构和亲和力的性质。
人们不遗余力地钻研这些问题,很快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由于人们已理解到定量方法的重要性,所以这时竭力想在化学中应用数学方法,指望能象早些时候把数学用于物理学那样取得成功。
定量分析运用的数学方法极其简单,而且这一期间形成的大多数理论概念都不要求多么广博的数学知识。
因此,人们认为推算出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力和量的数值,不仅大有可能,而且很有必要,这种想法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前面已经提到,荷伯格、温策尔和柯尔万曾试图确定亲和力的数值,但是收效不大。
杰里米亚·本杰明·李希特(JeremiasBenjaminRichter,公元1762-1807年)重新进行了这类实验,于公元1792年在布雷斯劳发表了《化学计算法纲要》(AnfangsgrundederStochyometrie)第一卷,该书或译为《化学元素测量术》。
他和荷伯格、柯尔万一样,都认为只要能测定与一定数量的碱发生中和作用所需的各种酸的量,或是测定与一定数量的酸发生中和作用所需的各种碱的量,就可以得出亲和力的精确数值。
他把实验结果总结成一张表,标明中和一千份钾碱、苏打、挥发性碱(阿摩尼亚)、氧化钡、石灰、氧化镁和氧化铝所需要的硫酸、盐酸和硝酸的份量。
李希特进一步指出,两种中性盐进行复分解反应时,生成物也是中性的。
这就是说,如果AB和CD发生反应生成AC,那就会生成BD,如果知道AB和CD的成分,也就可以算出AC和BD的成分。
这自然是应用物质不灭定律的一个实例。
李希特创造了化学计算法(Stoichiometry)一词来表示他的研究领域,该词来自希腊语,含有测量某种不能分割之物的意思。
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定比定律:
各种元素在一种化合物中的比例不变,两个元素形成的任何化合物都有一个重量比,在含有其中一种元素的其它化合物中也可以遇到这一重量比。
李希特的中和表其实就是第一张当量表。
令人遗憾的是,李希特的表述方式极其繁复。
他过于偏重数学,总想用他测得的数据推导出各种难以成立的数学关系。
所以,他的著作不太受化学家们的欢迎,出版后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公元1802年,恩斯特·戈德弗雷·弗希尔(ErnstGottfriedFis-Cher,公元1754-1831年)把柏托雷论亲和力定律的一本法文著作译成了德文,书中附有李希特的亲和力表,不过已经简化成一张精确的当量表,至于“当量”一词,当时尚无人使用。
此表附后。
它列出了当时人们熟知的酸类和碱类。
表中数字皆为重量,每种酸后列出的数字表示这种酸与表中所列碱量中和时所需的重量。
碱类
酸类
氧化铝
525
氟酸
427
氧化镁
615
碳酸
577
阿摩尼亚
672
脂肪酸
706
石灰
793
盐酸
712
钠碱
859
草酸
755
氧化锶
1329
磷酸
979
钾碱
1605
蚁酸
988
氧化钡
2222
硫酸
1000
琥珀酸
1209
硝酸
1405
醋酸
1480
柠檬酸
1683
酒石酸
1694
一位在马德里担任教师的法国化学家约瑟夫·路易斯·普鲁斯特(JosephLouisProust,公元1754-1826年)提出了定比定律的实验证明。
公元1799年,普鲁斯特证实了:
不论碳酸铜的生成方式如何,亦即不论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合成,其组成都固定不变。
此后,他用了九年功夫提纯和分析各种化合物来验证定比定律。
这一期间,他和另一位法国学者柏托雷展开了一场著名争论,柏托雷就是和戴莫维、拉瓦锡合写过论述化学命名法著作的那个人。
柏托雷从分析亲和力入手,研究了化学组成的问题。
他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亲和力定律研究》(RecherchesSurLesLoisDel’Affinite,巴黎,公元1801年),另一本是更为著名的《化学静力学概论》(EssaiDeStatiqueChimique,巴黎,公元1803年)。
柏托雷指出,伯格曼在编纂有择亲和力(ElectiveAffinity)表时提出的假设并不完全正确。
亲和力不是绝无仅有的一种力,因为除亲和力在各种物质间起作用外,反应物的数量也能左右反应的方向。
他说过:
“当一种物质作用于某一化合过程时,进行化合实验的原反应物本身会发生分解,分别与其它两种物质化合,该过程不仅与这些物质相应的亲和能的大小有关,而且也和这些物质的数量多少有关。
”这实际上等于提出了质量作用定律;人们过了半个多世纪才认识到这一事实。
柏托雷指出了陈旧的有择亲和力观念的局限性,立下一大功劳,但又不适当地推广了他的理论,以致陷入严重的错误。
柏托雷深信化学亲和力是一种类似重力的力,并认为物质间任何类型的化合都是这种力的具体表现,溶解和化合并无本质不同,定比定律不过是亲和力这一普遍规律的特殊形式。
他认为,如果不是溶解度之类的特殊因素在起作用,化合物的成分就会发生变化。
在某种具有固定成分的化合物恰巧是溶解度最小的那种类型时,它往往会从溶液中沉淀出来,最后生成成分显然固定不变的物质。
不过,柏托雷认为这只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结果。
正是这种观点在普鲁斯特和柏托雷之间引起了一场争论,并且促使他们进行了大量分析工作。
普鲁斯特特别重视化合物的纯度问题。
他指出,柏托雷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引证的许多分析数据有误,因为他使用了含有杂质的化合物或混合物。
普鲁斯特还指出溶解和化学反应是两回事。
“在我看来,阿摩尼亚溶解于水和氢与氮生成阿摩尼亚毫无相似之处。
”
到公元1808年时,普鲁斯特的见解占了上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