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透视.docx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透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透视.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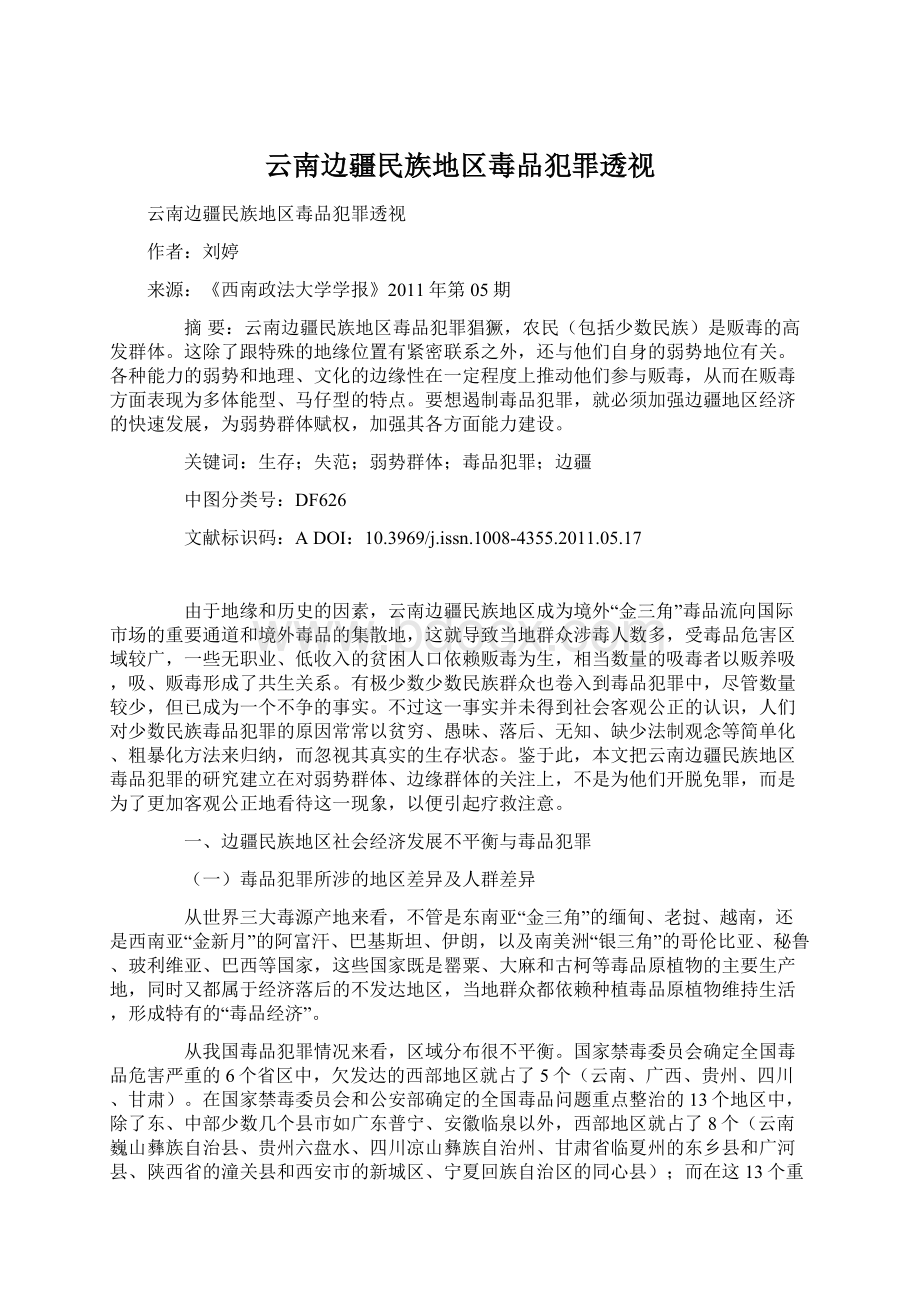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透视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透视
作者:
刘婷
来源: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05期
摘要: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猖獗,农民(包括少数民族)是贩毒的高发群体。
这除了跟特殊的地缘位置有紧密联系之外,还与他们自身的弱势地位有关。
各种能力的弱势和地理、文化的边缘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他们参与贩毒,从而在贩毒方面表现为多体能型、马仔型的特点。
要想遏制毒品犯罪,就必须加强边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弱势群体赋权,加强其各方面能力建设。
关键词:
生存;失范;弱势群体;毒品犯罪;边疆
中图分类号:
DF626
文献标识码:
ADOI:
10.3969/j.issn.1008-4355.2011.05.17
由于地缘和历史的因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成为境外“金三角”毒品流向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和境外毒品的集散地,这就导致当地群众涉毒人数多,受毒品危害区域较广,一些无职业、低收入的贫困人口依赖贩毒为生,相当数量的吸毒者以贩养吸,吸、贩毒形成了共生关系。
有极少数少数民族群众也卷入到毒品犯罪中,尽管数量较少,但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得到社会客观公正的认识,人们对少数民族毒品犯罪的原因常常以贫穷、愚昧、落后、无知、缺少法制观念等简单化、粗暴化方法来归纳,而忽视其真实的生存状态。
鉴于此,本文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的研究建立在对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关注上,不是为他们开脱免罪,而是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一现象,以便引起疗救注意。
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毒品犯罪
(一)毒品犯罪所涉的地区差异及人群差异
从世界三大毒源产地来看,不管是东南亚“金三角”的缅甸、老挝、越南,还是西南亚“金新月”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南美洲“银三角”的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巴西等国家,这些国家既是罂粟、大麻和古柯等毒品原植物的主要生产地,同时又都属于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地区,当地群众都依赖种植毒品原植物维持生活,形成特有的“毒品经济”。
从我国毒品犯罪情况来看,区域分布很不平衡。
国家禁毒委员会确定全国毒品危害严重的6个省区中,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就占了5个(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甘肃)。
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和公安部确定的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的13个地区中,除了东、中部少数几个县市如广东普宁、安徽临泉以外,西部地区就占了8个(云南巍山彝族自治县、贵州六盘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肃省临夏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陕西省的潼关县和西安市的新城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县);而在这13个重点县市中,甘肃广河县三甲集、宁夏同心县和安徽临泉被称为中国内地主要的三大毒品集散地。
这些地区历来是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离中心文化和核心政权较远,社会控制力一向较弱。
在这些不发达地区,低收入、低文化的农民和社会无业人员是贩毒的两大群体。
上世纪90年代,云南省公安机关破获的贩毒案件中,农民犯罪案件占了总数的65%左右,且呈上升趋势。
云南省1996年经检察机关批准共逮捕毒犯3505人,其中农民2604人,占74.3%;1997年上半年逮捕毒犯1916人,其中农民1521人,占79.4%[1]。
云南永德县1992-1997年查获的毒案中,农民作案222起,农民毒犯338名,分别是总数的72%、81%;农民毒犯居住于富裕地区6人,温饱地区61名,贫困地区271名,占总数的80%[2]。
在抓获的农民毒犯中,包括部分少数民族人民。
1996年兰州市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583名毒品犯罪嫌疑人中,有少数民族成员227名,占38.9%[3]。
近年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案件中,案犯多来自欠发达西部地区甘肃、青海、宁夏,72%的案犯为少数民族,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个别案犯甚至是文盲[4]。
根据1991年云南省劳改局对省第二监狱局在押1062名毒犯的分析,少数民族占总数的35.12%[5];到90年代末,云南在押少数民族毒犯,占全省毒犯总数的39.7%[6]。
这些少数民族毒犯涉及到23个民族,除了云南特有的傣族、景颇族、哈尼族、拉祜族、阿昌、佤族、傈僳族等16种少数民族外,内地的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四川凉山的彝族、甘肃临夏的东乡族、宁夏同心县的回族以及新疆维吾尔族等。
(二)毒品犯罪方式的差异与社会、政治经济作用
边疆民族地区的毒犯与我国内地、沿海地区相比,在犯罪的方式和手段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马仔型”、“山地型”居多
在毒品种植、加工、贩运、消费整个环节中,边疆民族地区的毒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很少参与毒品的加工和销售,主要受雇于他人充当马仔从事毒品运输的工作,俗称“骡子”。
他们运输毒品主要有两种形式:
(1)“离土不离乡”型。
主要发生在边境地区,当地边民多是跨境民族,因为人熟、地熟、情况熟而经常被境内外贩毒集团拉拢利用。
他们大多是山地民族,主要采取昼伏夜行,人背马驮,绕过关卡走山路的方式短途运输毒品,所以又被称为“山地型”。
(2)“离土又离乡”型。
主要指的是离开家乡外出到边境或到缅甸、老挝、越南境外打工的农民,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低,又无一技之长,很难即刻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加之携带的生活费用很少,生活难以为继,境内外毒贩就盯住他们,诱之以一、二千元的运费,雇用他们将毒品从境外长途运到昆明等大城市。
此类运毒方式风险较大,主要采用体内运毒的方式,毒品在体内一旦破裂很容易丧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刘婷: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透视
比起内地,边疆民族地区毒犯多体能型,少智能型;多马仔少毒枭;他们处于犯罪链条的末端,手段简单,主要靠出卖体力赚取运费,获利最小,却承担最大的风险,是低端线路者。
有学者指出:
“只消对那些把合法与非法的买卖联系到一起的网络仔细观察,就能将跨国毒品经济的微观因素与宏观因素、地方因素与全球因素联系起来。
在这种经济中,穷人当的是零售商,卖命推销毒品,而结果无非是给高层次的批发商保证巨额利润,毒品小贩冒着风险,拼着性命,养肥了那些批发商。
”[7]正如在皮艺军《犯罪学研究概要》中有国外学者指出“官方犯罪和被逮捕的犯罪者乃是由和其行为的损害性毫无关联的社会力量所产生。
最成功的犯罪人少被抓、少被起诉、亦少受惩罚。
这些是有权、有钱和聪明的人。
较不成功的犯罪人则较常被惩罚。
他们则是缺乏权力、贫穷和较笨拙的人。
”
2群体贩毒突出
少数民族很少单独作案,通常是二三人结伙作案,大都是由同籍贯、同乡、同村的人组成,或者是由同民族、同家支、家族或家属组成,浓厚的地域观、民族认同感、同宗、同族和交错的亲缘情感,使得他们形成相当的信任关系,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多走山路从事贩毒活动。
这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他们大多生活在山区或半山区封闭的环境里,见识短,阅历少,形成胆小的性格,不敢轻易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对外界存在陌生感和恐惧感,表现在贩毒的的过程中,通过集体贩毒的方式抵御对陌生世界的恐惧。
另一方面,从犯罪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少数民族的互动同化心理强于其他人群。
所谓互动同化心理是指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相互产生影响和作用,以至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因为这种影响和作用而逐渐趋向一致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犯罪中非常明显,当看到有人贩毒赚钱“衣锦还乡”、修房建屋,他们的心理会产生一种震动,贩毒致富的方法被认同和模仿,出现同一地方的人犯罪手法也趋同。
同时,群体贩毒使个体抱着责任分担的侥幸心理,加速了罪责感的弱化,罪责感弱化的结果就是无视法律的存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3主要是以贩养吸
内地毒贩牟利愿望很强烈,他们深知吸毒的危害性,故本身并不吸毒,主要是幻想贩毒一夜暴富。
而在边境地区,贩毒是吸毒的衍生物,因为吸食毒品而直接到境外参与贩毒帮助走私运输毒品的比较多,边民既是毒品犯罪的实施者,也是毒品最大的受害者。
他们无资金和固定收入,吸毒成瘾后,为了筹措吸毒资金,从毒贩手中购少量毒品采取自己吸一点,留一点,卖一点给其他吸毒者的方式从事零包销售。
现买现卖,小卖小赚,只是为了满足毒瘾,所以涉毒数量不大,较少涉及大宗案件。
在我国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吸毒人员占了60%以上。
由于身体羸弱、经济贫困,贩毒又成为他们惟一的生存办法,而被当地群众戏称为“具有合法执照”的吸贩毒者。
边疆民族地区的吸毒、贩毒、艾滋病问题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以至于已经严重威胁到某些民族的生存问题。
二、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原因分析
(一)“弱势群体”概念的引入
我国20多年的改革,形成了一种在相当多的竞争者中只有少数人有条件和机会获得巨额利润的机制,致使资源重新积聚,形成总体性资本和占人口比例极少的总体性精英,与此同时,由贫困的农民和进城谋生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下岗工人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共同构成弱势群体。
所谓“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或阶层,它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在现实生活中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状况之中,即物质生活贫困;二是由于能力的弱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三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也处于弱势地位,即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方面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我国抓获的毒贩来看,绝大多数是农民和无业人员这部分弱势群体,他们来自经济社会低下的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属于低收入、低文化、低生活水平的“三低人员”。
本文对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研究分析正是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之上。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的“结构性紧张理论”认为,所有文化都提出了作为普遍欲求的某些目标(如个人在金钱上获得成功)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或社会认可的手段(如努力工作、读书求学),但是在社会快速变化和社会不平等广泛存在的环境里,某些群体如农民可能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机会通过合法途径去实现文化上的成功,这就在目标和手段、社会和现实之间产生了紧张状态。
弱势群体在经济、能力、权力、机会等方面的弱势特征是影响他们成功的障碍,为了消除目标和现实之间的紧张,他们只好采取非法的方式去实现成功的目标,这就产生了犯罪。
(二)弱势群体与毒品犯罪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毒品问题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无必然的因果联系,主要是特定区域(边境、毗邻毒源地)的刑事犯罪问题。
云南边疆地区同时也是民族聚居区,毗邻世界毒源地“金三角”,4060公里的边境线无天然屏障,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是导致当地群众参与毒品贩运的主要原因,但其弱势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他们参与贩毒。
1经济的弱势与易涉毒性
按照发展的不同水平,中国有4个世界划分:
第一世界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二世界是中部较发达地区,第三世界是西部发展中的地区,第四世界就是发展中地区的少数民族。
居住在云南边境地区的边民58%是少数民族,他们大部分既是跨境民族,同时也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阶段的“直过”民族,社会发育程度低和封闭的地理环境构成的双重障碍,使得他们陷入了贫困与落后的状态,25个边境县中有17个是国家和省扶贫工作重点县,“大通道上车水马龙,大通道两侧刀耕火种”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如今民族“直过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低层次,被概括为“最贫困地区、最弱势群体、最特殊族群”。
有的虽已解决温饱问题,但生活的满足程度以及发展机会低于社会的基本水准,扩大再生产能力很弱。
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他们对现金的需求急剧增长,基本生活用品诸如种子、化肥、农药和饲料等基本生产资料都要用钱来购买,原有的合作医疗制度垮台,中小学免费教育的结束,使得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大大增加,如澜沧县拉祜族家庭每年的教育支出占总收入的31%。
耕地面积少、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增长,农产品尤其是传统的粮食和畜牧产品价格下降,使农民难以仅靠农业收入来维持生活,由于历史上和迄今为止的结构性原因所造成的少数民族资金的缺失和生活的贫困。
因为经济的弱势,少数民族往往经受不住贩毒高额利润的诱惑,而被毒贩所雇佣,充当“马仔”,帮他人背运毒品获取二三千元的运费,他们贩毒,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低水平的温饱问题。
例如,宁夏同心县是我国重点整治的外流贩毒县,全县34万人口中有28万回族,典型的黄土高原,因严重缺水而贫困,被联合国确定为全球22个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长期靠天吃饭,生活困难,一些农民放下锄头,兄弟联手、父子同行甚至夫妻、婆媳联袂,背着干粮袋,成群结队地挤上火车或汽车上“前线”外流贩毒。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也是我国毒品重点整治地区,17个县市中有12个市县是贫困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60%,文盲半文盲占53%。
云南毒品犯罪的高发区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民族地区,抓获的少数民族毒品犯罪嫌疑人中,相当数量的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改善基本生活条件而参加毒品犯罪,正如当地村民说的那样:
“谁不喜欢过好日子?
但是人穷命就不值钱,有了钱谁还会去贩毒找死,只要是有钱人谁都怕死”。
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比起来,在许多方面处于劣态,可在原始动物性能方面却有着天然的强势,那就是使用暴力,就弱者而言,他们对生存的恐惧远远大于对不安全的恐慌。
如果单从社会经济方面看,似乎只能说是贩运毒品是边疆民族地区的部分农民采取的一项克服自身贫困的办法。
他们看到其他地区的群众都在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优势发财致富,而自己或自然资源贫乏,或缺乏技术和资金,也难以得到外界的帮助,长期难以改变的贫困导致很多村民丧失了以土地或正常渠道谋生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便利用地理位置赋予的“优势”贩运毒品,以期改变自己的贫穷状态。
2能力的弱势限制了就业谋生方式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改革使农村原来的隐性劳动力剩余问题突显出来,虽然近20年来我国城镇非农业经济发展飞速,劳动力需求大大增加,但面对数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各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
加上由于历史上和迄今为止的结构性原因所造成边疆民族地区的群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调整和适应力受到巨大制约,在知识和素质上先天不足,较少有机会正常地接受国民教育和职业培训,封闭的生活环境、语言的沟通障碍以及市场经济意识的缺乏导致了他们能力的弱势,表现出“获得性权力缺损综合症”,与竞争对手在一开始就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在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下,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找到工作,或者找到的工作收入太低,总之被排斥在高收入高技术行业之外,容易产生被剥夺感。
在市场竞争中,强势群体往往具有资金、权力、技术、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处于优势积累的有利地位,一旦第一步领先,便会步步领先具有滚雪球似的“放大效应”;相反,弱势群体不具备资金、权力、能力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相当少,一步赶不上,往往步步赶不上,处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这使得市场竞争中的“马太效应”日益突出,即好者愈好,富者愈富,差者愈差,贫者愈贫。
“贩毒一个显著而严重的特点,那就是贩毒以及其他犯罪活动对于连正式工作都难找到的弱势群体具有吸引力。
在里约热内卢、孟买、广州以及内地小城镇,直接涉足犯罪的是那些读不起书,学不到手艺的贫困街区的子弟,是那些一文不名的盲流,这些人在国民经济中是没有合法地位的。
全球快速蔓延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更为贩毒增添魅力,因为毒品为它们鸣锣开道。
”[8]农民、无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在新经济中缺乏可以投入交换的其他诸如财富、社会关系、知识等资源,而是以体力、时间、身体作为资源进入到市场。
贩运毒品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作周转,广泛的关系网络给予方便,重要的是贩运者需要时间条件,农民和无业人员恰好满足这个要求。
他们依靠自己的身体——劳动力、器官,通过人背马驮、体内藏毒等方式来运输毒品,无需任何成本和技术,周期短、见效快、收入高。
例如,具有“云南背毒第一村”称号的永德县班老村,村民过去经常到缅甸果敢背木炭,背几十斤木炭才几毛钱;相比之下,背毒品一次就能挣一二千元,相当于几年的收入,在他们看来,背毒品和背木炭一样只不过都是谋生挣钱的方式,是职业的平移。
因此不能认为弱势群体比起其他群体来说更乐于毒品犯罪或更具有反社会性,而是由于弱势境遇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生存与发展的障碍,限制了他们满足其基本需要的手段选择范围,不具备其他群体的生存空间,当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路、生活无着落,就会表现出越轨行为的经常性和普通性。
而贩运毒品无需任何成本和技术恰好满足了他们挣钱的需要。
3弱势群体同时也是边缘群体,被排斥在“主流”、“中心”之外
边疆民族地区在空间距离上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由于经济贫困和素质低下,边疆民族人民的人际交往和职业流动只能局限于社会底层,因此很容易成为社会的边缘或被排斥的部分,缺少话语权,得不到社会的认同。
仅就我国的禁毒工作来说,尽管开展得如火如荼,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农民、无业人员、少数民族并没有引起根本重视,作为边缘群体他们是被排斥在外的。
社会排斥导致的否定情绪,都容易使弱势群体将利用非法手段获得利益视为一种自我救济的合理方式,或作为社会对他们的应有的补偿。
地理分布的边缘性决定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一向较弱,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是禁毒宣传教育的死角和盲区。
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少数民族被挤压、排斥于中心之外,不得不处在社会的边缘,我国80%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边远山区,加之交通、通讯落后和地理的分割,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规模社会流动,城乡二元结构和封闭型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制约,强化了民族地区的地域隔离。
“山高皇帝远”,国家政权鞭长莫及无法完全延伸到边疆地区,同时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散分布也为禁毒工作带来难度,在地理的边缘定势和历史惯力的作用之下,农民变成了一个空间巨大的被漠视群体。
文化的边缘限制了少数民族对法律、禁毒宣传教育知识的接受。
我国有56个民族,民族文化差异大,由于提倡均质的以汉族为主的国民文化而把地方、民俗和民族文化边缘化,表现在禁毒工作中,没有结合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制订相应对策。
普法教育和禁毒宣传统一采用汉民族语言文字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的接受能力,一些只会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根本无法领会。
同时,知识能力贫困状态,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边缘效应,使得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利用报纸、图书、电话、互联网等现代手段获取和交流文化信息。
因此,虽然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边疆民族地区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毒品的危害性和违法性缺乏根本认识和普遍认同。
心理的边缘定势加剧了发展劣势。
少数民族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很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而难以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公共利益表达和形成过程中处于劣势竞争地位。
紧靠自身力量很难迅速改变目前的处境,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对以后的发展悲观失望,失去信心,自弃心理压力增大,形成心理上的边缘定势,对社会的敌视和社会对他们的否定,共同强化了少数民族他们的弱势地位。
这就是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由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生活环境的封闭,与社会主流文化隔绝,形成了自暴自弃、不求上进的宿命论价值观念,这种贫困文化会世代相传。
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一些缉毒基层民警也谈到少数民族犯罪跟他们“不求上进”、“堕落”、“懒惰”有关,只要有酒喝就满足了,重现在不重未来。
总之,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弱势群体的普遍贫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流、社会排斥、机会不平等与社会越轨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甚至有时互为因果关系。
换言之,贫困、失业、教育程度低下、语言文化障碍和禁毒资讯缺乏等这些都是弱势群体容易被贩毒集团所利用的的因素。
“社会、经济和体制方面的不平等既然存而不去,这种新的全球化买卖(注:
指的是毒品犯罪)就为那些遭到社会排斥的人们制订了一种悖逆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整合方式。
”[7]
三、关注弱势群体,遏制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日益猖獗,其原因除了地理、历史之外,还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从全球来看,生产毒品的国家都是不发达国家;在中国,涉毒群体以贫困的农民、无业人员为主体,毒品犯罪在贫富差异的群体和地域之间的特点和方式有着明显差异,毒品凸显了落后地区发展中的问题:
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状态,能力的弱势和机会的不平等,缺少和主流社会的沟通,获取的毒品宣传资讯有限等。
在众多的被犯罪学家们公认的致罪因素面前,弱势群体更具有易感性,压力与诱惑对他们的影响更具体和直接。
因此只有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与分配机制,并相对使弱势者摆脱困境,解决他们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才有可能控制和减少该群体的毒品犯罪行为。
1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将禁毒与发展、禁毒与扶贫相结合,大力发展边疆经济
贫困是毒品犯罪最大诱因,有民族学家指出:
“云南边疆的大部分山民生活水平仅能满足温饱,贩毒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诱惑。
如果边疆脱贫步子不大,边疆各族人民长期在贫困中徘徊,在边境地区贩毒违法活动更猖獗的情况下,很难说不会有更多的边民利用天时地利和有利条件参与贩毒”[5]。
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收入低微,在心理上易产生被剥夺感,如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就会不认同这个社会,甚至敌视社会、反社会。
因此,从长远来看,缩小“边缘”与“主流”、“中心”的差距,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文化处境,是遏制边疆民族地区毒品犯罪根本途径。
在“金三角”种植罂粟的多是经济落后的山地民族,我国帮助他们推行替代种植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
那么我们现在禁毒工作视点应从帮助境外替代种植转向境外替代种植和境内替代发展并重,实行“双向替代”,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兴边富民,大力发展边疆经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贸易与投资、旅游、禁毒环保作为一个系统,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帮助当地群众摆脱对毒品经济的依赖。
要根本性地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必须加强其自身的能力建设。
在扶贫方式上,将“输血式”的扶贫转向“造血式”的开放性扶贫,即将外力的支持与本地群众自身的力量相结合,通过或借助来自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资金、知识、技术、人才、机会及其它必要的资源的支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弱势群体的能力建设,帮助他们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努力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吸收、自我发展的能力,培植和强化他们自身的“造血”功能,增强其社会竞争力,实现由“外嵌入”转为“内源性”的自我发展。
2为弱势群体赋权,通过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环境,减少矛盾和冲突
德国犯罪学家李斯特指出:
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不要专用刑罚来遏制犯罪,而由社会政策来预防犯罪。
所谓“社会政策”是国家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正与社会进步而采取的各种原则或方针。
社会政策就是要给实际上处于不利境况或社会底层的人以制度化的实际帮助,使他们有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尽可能多的人生活于社会主流之中,使主流和而不同,使得生活在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之间有对话、沟通、交流的可能。
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能力方面处于弱势,同时在权益方面也处于弱势,在医疗保险、教育、就业、养老等权益方面得不到保护,因此必须为他们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