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docx
《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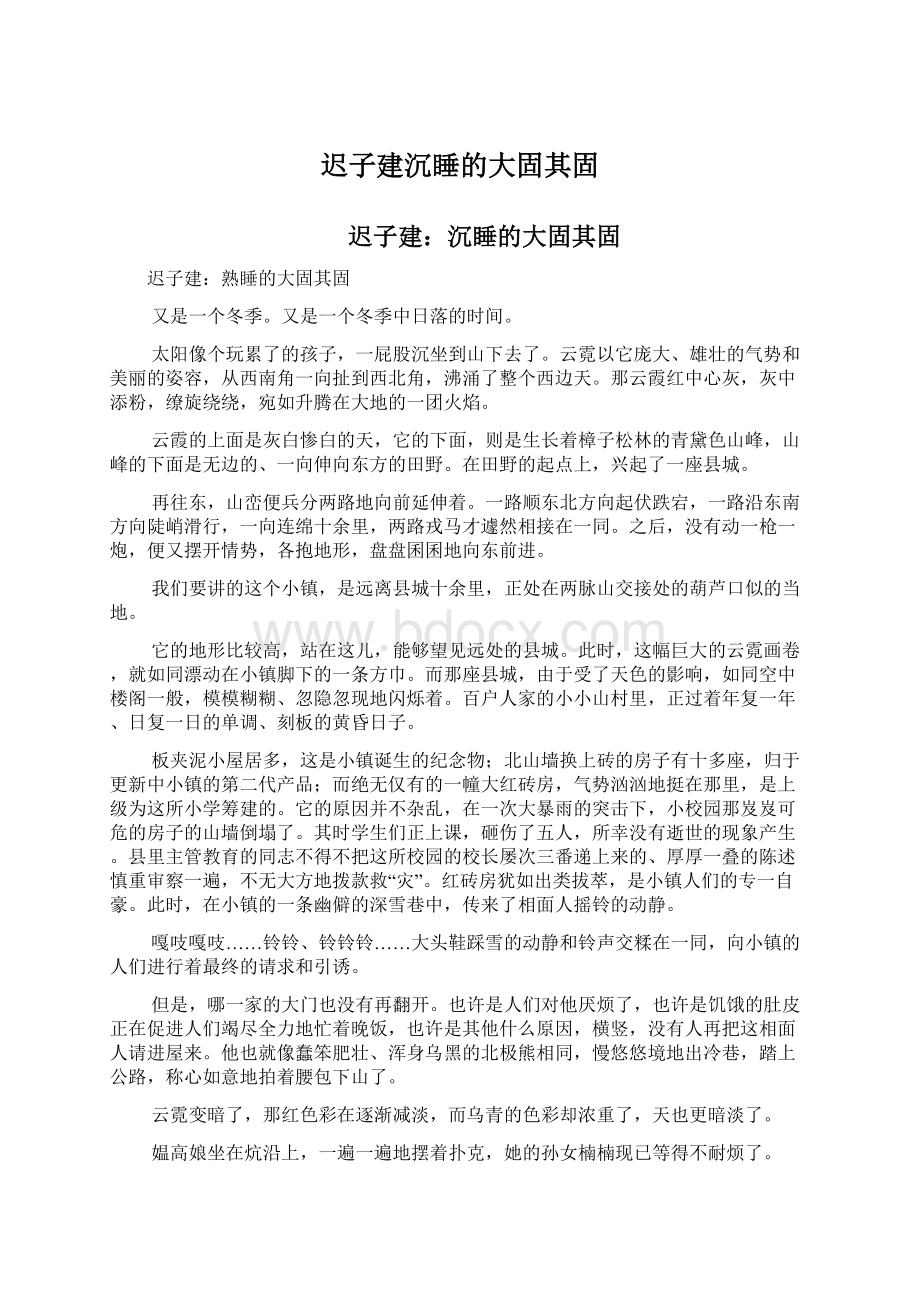
迟子建沉睡的大固其固
迟子建:
沉睡的大固其固
迟子建:
熟睡的大固其固
又是一个冬季。
又是一个冬季中日落的时间。
太阳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一屁股沉坐到山下去了。
云霓以它庞大、雄壮的气势和美丽的姿容,从西南角一向扯到西北角,沸涌了整个西边天。
那云霞红中心灰,灰中添粉,缭旋绕绕,宛如升腾在大地的一团火焰。
云霞的上面是灰白惨白的天,它的下面,则是生长着樟子松林的青黛色山峰,山峰的下面是无边的、一向伸向东方的田野。
在田野的起点上,兴起了一座县城。
再往东,山峦便兵分两路地向前延伸着。
一路顺东北方向起伏跌宕,一路沿东南方向陡峭滑行,一向连绵十余里,两路戎马才遽然相接在一同。
之后,没有动一枪一炮,便又摆开情势,各抱地形,盘盘囷囷地向东前进。
我们要讲的这个小镇,是远离县城十余里,正处在两脉山交接处的葫芦口似的当地。
它的地形比较高,站在这儿,能够望见远处的县城。
此时,这幅巨大的云霓画卷,就如同漂动在小镇脚下的一条方巾。
而那座县城,由于受了天色的影响,如同空中楼阁一般,模模糊糊、忽隐忽现地闪烁着。
百户人家的小小山村里,正过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单调、刻板的黄昏日子。
板夹泥小屋居多,这是小镇诞生的纪念物;北山墙换上砖的房子有十多座,归于更新中小镇的第二代产品;而绝无仅有的一幢大红砖房,气势汹汹地挺在那里,是上级为这所小学筹建的。
它的原因并不杂乱,在一次大暴雨的突击下,小校园那岌岌可危的房子的山墙倒塌了。
其时学生们正上课,砸伤了五人,所幸没有逝世的现象产生。
县里主管教育的同志不得不把这所校园的校长屡次三番递上来的、厚厚一叠的陈述慎重审察一遍,不无大方地拨款救“灾”。
红砖房犹如出类拔萃,是小镇人们的专一自豪。
此时,在小镇的一条幽僻的深雪巷中,传来了相面人摇铃的动静。
嘎吱嘎吱……铃铃、铃铃铃……大头鞋踩雪的动静和铃声交糅在一同,向小镇的人们进行着最终的请求和引诱。
但是,哪一家的大门也没有再翻开。
也许是人们对他厌烦了,也许是饥饿的肚皮正在促进人们竭尽全力地忙着晚饭,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横竖,没有人再把这相面人请进屋来。
他也就像蠢笨肥壮、浑身乌黑的北极熊相同,慢悠悠境地出冷巷,踏上公路,称心如意地拍着腰包下山了。
云霓变暗了,那红色彩在逐渐减淡,而乌青的色彩却浓重了,天也更暗淡了。
媪高娘坐在炕沿上,一遍一遍地摆着扑克,她的孙女楠楠现已等得不耐烦了。
“奶奶,饿死了,我先吃了。
”
“嗯,吃吧,去吃吧。
”
她仍旧在倒扑克、抽对儿。
一络青丝飘到满是皱纹的额头上。
“对圈,嗯,好,有贵人。
再抽一张看看。
”
她喃喃自语着,嘴角挂着粉饰不住的笑意,又抽出一张。
“红桃尖,好,好!
圈配尖,贵人指路,又是红的,能走通!
楠楠,给奶奶端碗饭来!
”
媪高娘兴味盎然地把扑克捋在一同,在炕沿上敦了又敦,齐刷刷地装到盒子里。
楠楠答应着,盛了一碗黏黏乎乎的大楂子粥,递给奶奶,又从咸菜缸里拽出一截黄瓜咸菜。
她们就这样开端了晚饭。
楠楠吃得很快,她放学时和同学们约好了,今日晚上去刘小娜家看电视。
听小娜说,电视上的人可清楚呢,一蹦一蹦的,有的歌唱,有的演戏,还有的说相声。
她还说那电视就跟她家装小鸡的纸盒箱子一般大,一通上电就能看见人。
“奶奶,我上小娜家去了。
”“嗯。
”“她家有电视,她让我们都去看。
”“嗯。
”“奶奶,你也跟我去看电视,行吗?
”“嗯。
”“那你就快点吃啊。
”“嗯。
”
媪高娘不住地嗯啊着,依然慢条斯理、心猿意马地吃着,她有她的心思。
其实,孙女终究说了些什么,她一点也没听进去。
在太阳还有一竿子高的当儿,她听到了相面人的摇铃声。
她叫住了他,把他带进另一家——那使小镇一切的人都恐惧的魏疯子家。
他是一个专爱捏老鼠的疯子。
他年青时是开小火车的,一次,开到与公路穿插的路口,一辆轿车抢道,两车相撞了。
他是罹难人中的仅有幸存者。
他从此便疯了,被送去北安治了两次,依然不见有起色。
他的妻子被他亲手杀死了,两个孩子由姥姥家接去抚育,这魏疯子就一个人日子在这儿。
他的街坊便是媪高娘。
刚住进这儿时,魏疯子倒也安静了许多日。
但是有一天,他遽然又犯了病,手里拎着两只老鼠,连蹦带跳地跑到宅院,大喊大叫,折腾了一两个小时,一向也没有人敢上前拦住。
后来,他咬牙切齿地把老鼠捏得吱吱直叫,然后哈哈大笑地说:
“啊哈,你再也不能欺压我了,我把你捏死了,捏死了!
你这灾星,灾星!
啊哈哈……”
他高高地挥着臂膀,那姿态,几乎像个由于得了胜而发狂的拳击家。
他就这样一次一次地扮演相似的闹剧。
只需小镇上一响起这种动静,人们便赶忙关门闭户。
年迈的人说,这是一种会带来灾害的叫声。
只需他一呈现,人们便草木惊心似的逃散了。
媪高娘是年青时就丧了偶的。
她的三个儿子都在县城上班,大儿子把女儿楠楠放在这儿与奶奶做伴。
她开了一个豆腐店,每天卖豆腐的时分,魏疯子都按时地站在门口,伸出手,要上一块。
只要媪高娘敢挨近他,他也只听媪高娘的话。
相面人说,疯子是小鬼缠了身。
由于出事的岔路口周围有几座荒坟,那些小鬼就化成老鼠来出气索命了,而疯子又把老鼠捏死了,这样,附在他身上的鬼气就更大了,很需要吃一次还愿肉。
否则,疯子就会招惹来一切的老鼠,使这个小镇都遭殃。
温高娘虽不十分信任会有此事,可她的心里依然是咯咯噎噎的。
假使真的,那这小镇不就变成一个鼠镇了吗?
她越想头皮越发麻,心也如同让麻绳给揪起来了,难过得不得了。
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像见了救星,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似的,不停地央求着:
“先生,老先生,快行行好,使个法吧。
我们这老骨头老肉的倒不怕,死也就死了,快爬到黄土边了,可娃娃们多啊、小啊,行行好吧。
”
是的,自从小镇诞生的第一天起,这儿就约定俗成地成了一个白叟与孩子日子的国际。
那时,有了劳动能力、能自己挣口饭吃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由于没有升学考学之“忧”,都报名作业了,一头扎进了苍茫的大森林,清林、伐树,住在男女之间只隔着一张草席的帆布帐子里。
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他们也就自但是然地成婚、落户、生儿育女,他们拓荒了自己日子的新天地,天经地义、不无自豪地做着诞生地的太岁爷。
而孩子们再大一些,就送到小镇上,由爸爸妈妈亲属抚育,直到上完小学。
多少年来,一向都是这样的。
媪高娘喜爱孩子。
由她亲手接到这个国际上的娃娃,算起来能编成一个班了。
一想到孩子们即将由于一个疯子而遭到拖累,嫩嫩的脸蛋即将被老鼠所啃啮,她就疼爱得直颤抖,她怎样能不请求呢?
相面人也现出很着急的神色,叹了口气说:
“做还愿肉吧。
杀一头猪,请来男女老少都吃,就把灾吃没了。
”
“灵吗?
”媪高娘站了起来,有些疑问地问。
“心要诚,方可灵啊。
”
她按照他的叮咛给了他三十元钱。
由于相面人说要由他亲手买布,给魏疯子做个“替身”,到了日子,就把它送走。
鬼气遣散,疯子也就会好了,小镇也就会得救了。
几十年的日子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
不管它多么的瘠薄和荒芜,她仍是爱这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发自内心地爱着。
一想到一次还愿肉能够免除还未降临到小镇的弥天大祸,她便是做什么也舍得出来的。
此时,她用整个身心,虔诚地这样想着、做着,为魏疯子,为孩子,为小镇。
这“贵人指路”不是清楚地向她预示了这些吗?
她喝着粥,可眼睛却盯在扑克上。
她真的把那相面人作为指路的“贵人”了,她感谢他,乃至又深深地抱怨自己给人家的钱太少了。
“三十元,太少了。
能买一个小镇人的命啊!
”
她不由又喃喃自语起来。
“奶奶,你真磨蹭,天都黑了!
”
楠楠见媪高娘嘟嘟哝哝地自顾说起话来,不由得生气了。
媪高娘总算听进了孙女的话,她急速笑吟吟地说:
“着什么急,大长的夜。
奶奶牙口欠好,你就不知道疼爱?
”
说完,她成心绷起脸。
“那人家电视都要开演了,我都找不着座了。
”楠楠好不悲伤。
这一下倒使媪高娘想起了刘适宜家买电视的事。
县里修电视塔现已有一年了,而小镇的人们却没有一家买电视机。
并非是人们手里没钱。
这小镇的白叟,几乎每一家都多子多女,这些生龙活虎的棒劳力,承揽之后,钱票子一把一把地往家里捎。
何况白叟们夏天种个菜,每天也卖个块儿八角,短不了手上花的。
有的人想买,可由于没有人打头,不乐意丢人现眼;也有的人认为买那玩意没用,整天闹闹哄哄的,连个悠闲劲都没了;也有的人想买,可却又舍不得花钱。
媪高娘呢,她是想,钱应该用到当用的当地,不能胡乱用。
就说这房子吧,确实是泥坯都掉了,柱脚也朽了,下雨天纸棚直往下漏水。
儿子早就说要翻盖一下,她硬是不愿。
一则花钱太费了,二则这老屋多少年都这样住了,觉得舒坦、服帖,若换个空荡荡的大房子,只怕连觉都睡不着呢。
再说,这做豆腐的人家,用这样的小屋最适宜,由于驴拉磨时总要把屎拉到地上,鸡呀、鸭呀的也乐意往屋里钻,显得活活生生的,多好啊。
更重要的,是她心里有她的隐秘,常言道:
盖房看位。
这盖房里可有大道理呢,万一动错了土,惊了神,地没了灵气,人便是活着也不兴隆,整天病病歪歪的,岂不是反福为祸,懊悔都来不及的吗?
房不盖、电视也不买,她心里有她的策画。
可刘适宜家买电视,她但是一点也没料到的,这太出乎她的预料了。
刘适宜是小镇上有名的拉泡屎也要跑回自己家厕所的人。
他不管做什么事,总是煞费苦心地想占个廉价,哪怕是一丁点的廉价。
人们都说,“吃亏”这个词与他历来无缘,他的眼球一转,就会生出很多道道来。
所以,也没有人再记住他的名字叫刘成贵,人们都不谋而合地称他为“适宜”。
年青的与他平辈的称他为“适宜兄弟”,后辈的孩子都唤他为“适宜爷爷”。
他听后,不光不恼,反而快乐地对人家点头哈腰地施礼,不无欢欣。
媪高娘对他的形象很坏。
文化大革命时,他曾告状说他的街坊——便是现在的小校园长,是苏修间谍。
依据是:
他家每天晚间都宣布一种不同寻常的动静,相似电影上发报机发报的动静。
这下可苦了那位干巴瘦的校长,他整日被审问、批斗,他暗自立誓再也不研讨什么无线电了,对那些红红绿绿的软线,东一条,西一根,你是无法对他们解说清楚的。
两家子曩昔原本不错,连宅院都是通着的。
夏天时各放一个方桌在地中心吃饭,晚饭后,就合拢起一堆青草,烧出团团的浓烟来熏赶蚊子,天南海北地谈个爽快。
但是这种日子因此而宣告完毕了。
老校长进了干校,他的老婆一气之下,虎着脸带领一家子人把大门外的两大垛柈子搬进宅院,十万火急地筑起了“院墙”。
两家相通的平展展的大宅院从此便被一垛高过屋脊的拌子给残暴地切成了两半。
刘适宜叫苦连天,这倒不是由于他怜惜老校长一家人,而是发愁这高高的“大墙”挡住了阳光,他家的宅院在上午的时分几乎跟牢房一般。
便是现在,老校长从头走立刻任了,那垛柴禾也仍是安如磐石,纹丝不动。
记住有一次老校长提议说要把它拿下一些,嫌这“墙”太高,看着也别扭,如同连新鲜空气都透不过来。
这话刚一出口,便被他老婆骂了个出言不逊:
“老贱种!
好了伤痕忘了疼!
”
“墙”西面的刘适宜听此言后,第一次感到悲伤了,他吸溜着鼻涕,对老伴说:
“谁知道这都是怎样回事。
那时都那么干,我也就随大流,赚了个老活跃的名。
我但是全神贯注地那么想啊,人家要求我们那么做呀。
可现在,又倒了个个儿,我便是神仙也算不出会有今日啊。
”
“你总是吃屎也抢不上热乎的!
”老伴把鸡食盆狠狠地摔在宅院里。
刘适宜蒙着头,孩子一般呜呜哭起来。
他买电视了,他有钱,可谁稀罕上他家去看?
媪高娘急速经验孙女:
“别上他家去看,有什么看头!
在家好生呆着,要不帮奶奶挑豆子泡上,明早还要拉磨呢!
”
“我不,我去看!
你说要跟我去,又变卦了,你糊弄人,我自己去!
”楠楠抓过头巾,怒冲冲地开门跑了。
“真是孩子,真是孩子……”媪高娘百般无奈地摇头叹息着。
天全黑下来了。
那条飘在西边天的大红方巾让夜给烧毁了。
天上没有月亮,只要星星在鼓着腮帮唱着那永久唱不完、也永久没有人会听懂的歌。
楠楠小跑着,她一点也不感到惧怕。
深雪巷中,回响着嘎吱嘎吱的踏雪声和短促的拉风匣似的喘息声。
她感觉到星星在跟着她一同跑,并且星星总也撵不上她,她总是占绝对优势地跑在前面。
她满意、快乐,想对着这条幽僻的冷巷喊几声,她觉得自己的四肢是那样活沷有力,她的全身心也感到轻松、自在和快活。
她一头撞开刘适宜家的大门,拼命地挤到前面。
立刻,她就被这个与装小鸡的纸盒箱一般大的、能有人说话的、靠电来分配的玩意招引住了。
媪高娘悟了被,凑在十五度的模糊的电灯泡底下,一边拣豆儿,一边想着还愿肉的事。
她估计着隔一天后就把猪宰了,逢个星期天,招来人一同把它吃完了,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思。
她觉得越快越好,由于在没有做之前,相面人所讲的耗子精随时都或许引起一场灾害。
如果说开端时她是着信若疑的话,那么现在,她是坚信不疑的了。
她越想越觉得那个人的话说得对,她的心也就越着急和发慌;这时,又恰巧赶上一只灰溜溜的老鼠从洞中爬出来,给她看见了。
她立刻赔着笑脸,道:
“别生气,别生气。
后天就给你送吃的。
”
公然,那老鼠噌地蹿回洞里了。
她再也没有心思干下活去,便又坐到炕头上诚惶诚恐地摆起扑克来。
电视放完了。
一屋子鳞次栉比的人潮水般地涌出屋子。
刘适宜扯着楠楠手,一向把她送到家门口。
楠楠闩好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子,她认为奶奶现已睡了。
“楠楠,回来了。
”
媪高娘放下扑克牌,审察着孙女:
她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闪闪的,按捺不住的振奋和快乐挂在她弯弯的眉梢和含着笑意的嘴角上。
她一把抓过奶奶的手说:
“奶奶,可好呢,电视,什么都有。
有养鸡的、有打拳的、还有说外国话的呢!
”
“我不爱听,快睡觉吧。
”
“奶奶,还有,还有……人和人搂脖亲嘴的呢,便是这样——”
说着,楠楠扑到奶奶怀里,双手勾住她的脖子,娇憨地嘬着嘴亲了奶奶一下。
媪高娘笑骂了一句:
“长大了不是个好东西!
”
“那现在我是个好东西!
”楠楠毫不示弱地答道。
对着这个只要十岁的小乖孙女,媪高娘直笑得流出了眼泪。
楠楠今日一点睡意也没有,她曲折反侧地骨碌着身子,缠着奶奶给她讲个故事听。
“我给你讲个大固其固的故事,可短呢,你保管乐意听。
”那是干涩无力的动静。
“那就快点讲吧。
”洪亮的童音在答复。
“大固其固,便是咱这个当地曩昔的名,那是……”
“这个当地曩昔的名?
奶奶?
”
“是啊,你爸爸或许都不知道呢。
”
“它怎样叫大肚(固)其肚(固)呢?
是它的当地跟大肚皮一般大吗?
”
“不是。
那是鄂伦春语,它的意思说是有大马哈鱼的当地。
”
“嗯,真好听。
接着讲啊,奶奶。
”
“大马哈鱼鳞黑个大,长在呼玛河里,可烈獗着呢,终身下子,它就死了。
”
“你怎样知道的呢?
”
“我也听人说啊。
你爷爷那时在呼玛河放排,在源头见过许多大马哈鱼死在滩头上,肚子下的鳞片都被砂石磨掉了。
”
“那为什么呢?
”
“要找到水旺的当地产子啊,没游到,就死了。
”
“那它死时必定很难过吧,它没生出子来。
”
“谁知道呢。
好了,楠楠,不讲了,困了。
”
楠楠也不再诘问。
她睁大眼睛向上望着,她什么也没望见,上面乌黑乌黑的。
她便又仰过身子,望窗外,她总算望见了星星,望见了能够消除她恐惧感的亮光,她才敢斗胆地翻开回想的闸口,回想那曩昔的事……“钓呀钓,大马哈,长长的竿,弯弯的钩。
谁要喝鱼汤,跟我上这来。
”
魏疯子经常在日落时扛着一根柳条棍,上面挑着从卫生所的垃圾箱里扯来的污秽的纱布,一瘸一拐地往塔头甸子走去。
楠楠和小伙伴总是远远地跟在他的后边,悄悄地看他去做什么。
从小镇往南走去,是一片碧绿的塔头甸子。
塔头墩上的青草一撮撮旺盛地生长着,塔墩之间有浅浅的水洼。
野鸭子和雀经常把窝做在松软的塔墩上。
魏疯子每次去都是坐在深草丛中,把竿子插在地上,对着蔚蓝清澈的晴空呼唤大马哈鱼。
一次,他发现了一窝野鸭蛋,他兴致勃勃地抱了回来,一路高叫着:
“大马哈变成蛋了!
蛋能抱鸡了!
鸡能下大马哈了!
”
楠楠他们就跟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呼喊:
“魏疯子,大傻瓜,坐在草堆钓小鱼,钓不着小鱼碰了蛋,拿回家去煮煮吃!
”
他们飞也似的跑,直跑到他的前面,转过身来,倒着走,众说纷纭地对他说:
“你怎样不去呼玛河垂钓呢?
”
“塔头甸子再往前走便是呼玛河。
”
“那里边才有大马哈鱼。
”
魏疯子停下了,愣了半晌,遽然哭了起来:
“呼玛河不好我好了!
呼玛河不好我好了!
”喊罢,就捧首狂奔起来。
一向回到家中,又拎出两只老鼠,把它们牢牢地攥在手心里,在宅院里大嚷大叫。
从那以后,小镇的人们都像惧怕魔鬼似的逃避他。
都说他不光疯,并且让鬼迷住了,尽管说谁也没见过鬼。
楠楠古怪的是魏疯子为什么总捏老鼠。
他屋子里的老鼠为什么那么多呢?
他现在怎样不钓大马哈鱼去了呢?
是冬季的原因吗?
他怎样不常闹了呢?
星星依然鼓着腮帮在唱。
可楠楠一点也没听进去。
衬托星星的仍是那蓝黑蓝黑的天幕。
她又想起了怀德叔的话。
怀德叔是和魏疯子在一个车辆段作业的。
上一年他来小镇上买秋菜,说魏疯子在出事的那天早晨,曾对他讲,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老鼠围着他的身边转,恐怕要遭灾呢。
可不是,那天真的出完事!
楠楠想,或许出事的时分魏疯子一会儿就想到老鼠了吧?
他现在或许还仅有模糊地记取那件事。
他总捏老鼠,必定是由于老鼠给他带来了灾害;他家鼠多,必定是他发狠把它们都养起来,然后再亲手把它们消灭掉。
是这样吗?
她想得不耐烦了,就转过身,睡了。
大固其固的夜,多寂静。
风儿不吹,树儿不动,鸟儿不鸣。
塞满了雪的大山静穆地立在那里,立在这广阔的天穹之下。
又是这样的一天曩昔了。
周日总算到了。
一大早,媪高娘就请来了杀猪的。
十点左右,小屋里就到处都洋溢着煮肉的香气了。
她今日像给儿子娶亲相同的快乐,请来了一茬又一茬人,又感谢十分地把他们送出去。
她觉得孩子们得救了,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疯子也该好了,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鬼气消散了,小镇复活了!
是的,太值得了。
一头猪,换来了这么大的收成,使得人们都快乐起来,让人觉得多适意啊!
当她送走了最终一批食肉者后,她不由得哭了。
拾掇了碗碟杯盏之后,天也就要黑了。
冬季的夜总是老早就厚着脸皮挨过来,才四点钟,那天就灰蒙蒙的了。
火相同的晚霞,渐渐地消散了。
夜来临了。
媪高娘极有兴致地泡上豆子,又把豆腐包洗好。
晾上,之后,用抹布抽打着结在墙上的那层细密的水珠。
楠楠正在做功课。
她要赶在演电视之前把它做完。
她闷着头,一声不吭地用铅笔写啊,画啊。
媪高娘做完了活,抽出扑克,又摆了起来。
“黑桃四,嗯,有坏事,再抽一张,是钩?
!
小人!
小人要坏事,是不是……”
她心里怦怦直跳,她立刻想到了处理的方法。
她跳下炕,颤抖着手取来香,从柜上拿起火柴,风急风火地向外走,匆忙中,竟踢翻了脸盆。
“奶奶,你干啥去?
”
“到宅院里,别作声。
一会就回来。
”
她推开门,出去了。
楠楠觉得古怪,就追到门口,摆开一条门缝:
媪高娘在与魏疯子的宅院相隔的拌子垛前停下了。
她把香插在雪地上,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它燃着,然后跪下,嘴里叨咕着什么。
冰冷的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香气。
看着,看着,楠楠忍不住要笑作声来。
她刚要吓唬奶奶一下,忽然望见柴禾垛上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她立刻认出那是魏疯子。
她张开嘴,想告知奶奶,可就在这时,魏疯子遽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要取豆腐了!
”
接着,一块圆滚滚的木头就被他推了下来,正砸在媪高娘的头部,她什么也没能喊出来,就一会儿倒在地上了。
她很快就中止了呼吸。
而就在她死前的一刹那间,她还在内心里深深地祈求着,不要把这灾害带给孩子、带给小镇,让她一个人顶了吧!
楠楠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
星光下,人们把媪高娘的尸体用草席裹上,停放在宅院中。
一个阳光格外足够的早晨,带着铃铛的马车把她运到大山脚下,她躺在那里熟睡了。
楠楠想起了,那天光临杀猪吃肉,没有做豆腐。
魏疯子是没吃到豆腐,想要跳过来取啊。
可她永久也不会理解奶奶为什么要请一切的人来吃肉,又为什么蹲在那里烧香。
就在媪高娘出殡后第三天,魏疯子遽然失踪了。
仍是楠楠把他找到的。
他冻死在塔头甸子里。
他的四周是塔墩上枯黄的败草和塔墩间丰莹的白雪。
远远望去,那一个个塔墩宛如一朵朵怒放的黄菊花,而魏疯子,也如同是卧在菊花丛中相同。
楠楠要走了,要脱离这个小镇了。
她和爸爸一同清点奶奶的遗物。
他们惊讶地发现,在一个塞满了破棉絮的纸箱中,有两摞扎得紧紧的钱,足足两千元!
两干元,楠楠看呆了!
她是留给谁的呢?
一同,人们也在魏疯子的屋子里,发现了别的的纸箱,纸箱里有一窝小鼠。
几个鼠洞前,都放有食物。
看来,他是让它死而又要它永久存在,以便每时每刻都能宣泄他那永久的一梦之“灾”吧?
楠楠没忘了向校园离别,也没忘了向校长离别。
古怪的是,老校长送给楠楠的纪念物是一个故事,并且所讲的这个故事又与媪高娘所讲的相同,都是讲大固其固的,也都讲了大马哈鱼。
不过,老校长却否定了媪高娘所讲的大马哈鱼是长在呼玛河的说法,他告知楠楠:
大马哈鱼曲折于三个水域之中。
每年秋末,老练的大马哈鱼从鄂霍次克海三五成群地涌出,冲向黑龙江巨龙般的躯体里,然后转而奔向喧嚣的呼玛河产卵,卵在第二年春变成小鱼,从呼玛河进入黑龙江,再进入鄂霍次克海。
楠楠总算理解了,鄂伦春人为什么把这片土地命名为大固其固。
她要求老校长,把那“墙”拆了吧,让他家的孩子也上小娜家去看电视。
电视上有许多这儿不曾产生过的新鲜事,让她们去看吧。
刘适宜不会再诬告你了,不会了。
他不是亲口对她说,买电视便是为了让我们看吗?
他第一次“吃了亏”,可他也第一次让人感觉到他“适宜”了。
又是一个冬季中的一天。
又是日落的时间了。
西边天又烧起了一片红红火火的晚霞。
楠楠跟在推着自行车的爸爸死后,慢慢地踱出深雪巷。
自行车在雪地上飞速滑行起来。
她把着车把,一向紧紧地把着,眼睛惊喜地盯着冲出葫芦口后那宽广的草甸和一座一座的山峦。
最终,她把视野移到那块变得越来越大的方巾形状的彩霞上,她觉得自己溶化在里边了。
她觉得奶奶、魏疯子,以及小镇曾经一切死去的人,都是那早已死在滩头的鱼,它们的鳞片部被河石磨掉了,可仍是不免一死。
而它们百折不挠产下的卵,却在第二年春变成小鱼,游出了狭隘的呼玛河,进入黑龙江,投入鄂霍次克海宽广的怀有中去孕育老练了。
她真的信任自己是()这样一条小鱼。
她不想再回头去看小镇。
她知道,它现在现已伴着夜色熟睡了。
白叟们总是贪睡的,而葫芦口似的当地又烦闷,它更要熟睡了。
不过,她又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她想到了小娜,想到了老校长家的女儿。
她们不喜爱伴着它一同再熟睡下去,由于她们喜爱唱,喜爱跳,她们身上是那么赋有奋发向上和生机,并且她们更有讨取别致事物时那永久也不会感到满意的目光!
那么,她们也必定会像自己相同,变成一条小鱼,一条游出呼玛河,到鄂霍次克海中老练后再游回来的小鱼。
对这点,她坚信不疑。
她的前面是更开阔的土地和无尽的大山。
她仰望着天上的星星,望着那鼓着腮帮子不停地歌唱的星星。
她第一次听懂了她们的歌声,听懂了这首陈旧、深重、隽永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