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docx
《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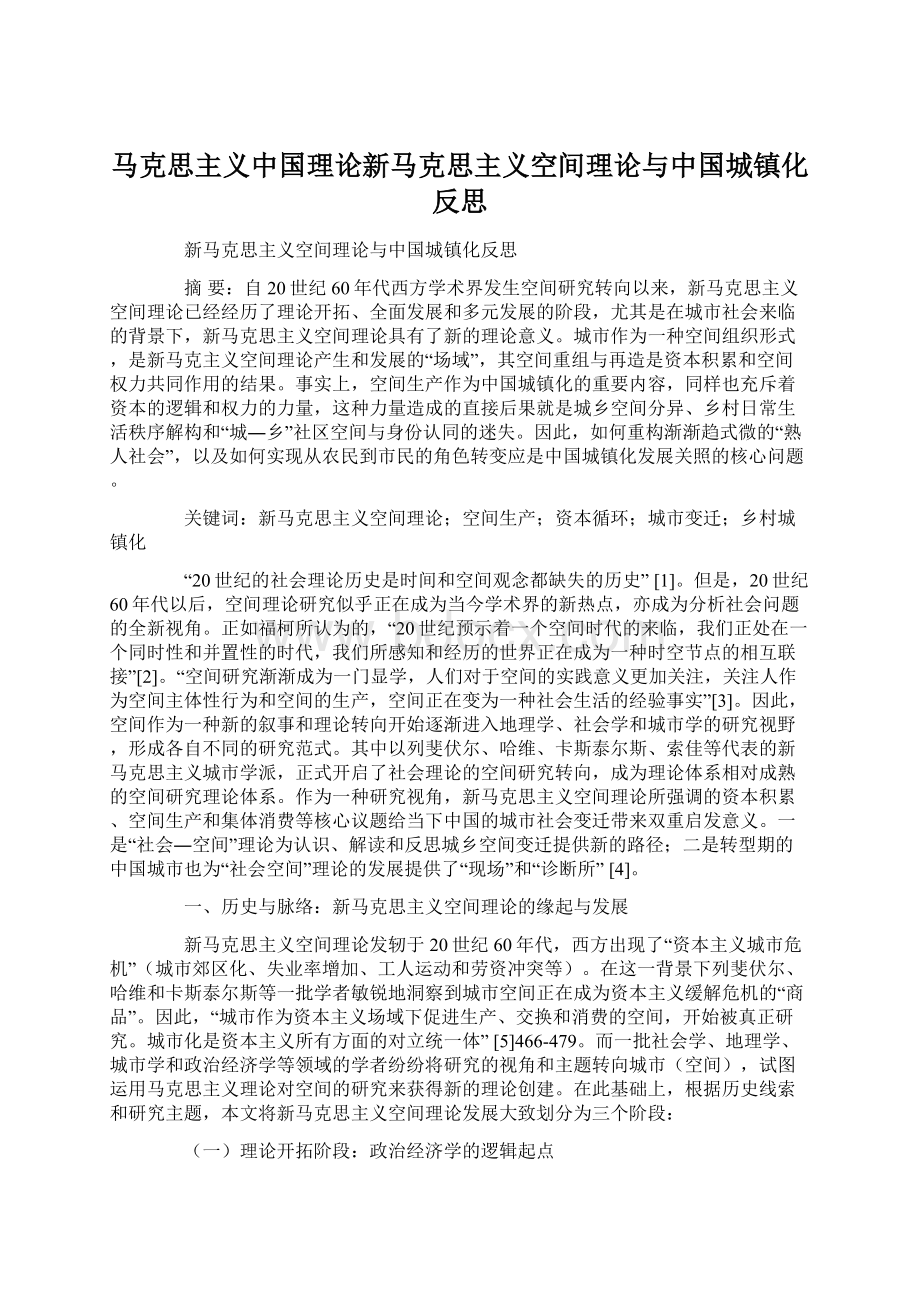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中国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中国城镇化反思
摘要: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生空间研究转向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已经经历了理论开拓、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来临的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具有了新的理论意义。
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场域”,其空间重组与再造是资本积累和空间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空间生产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充斥着资本的逻辑和权力的力量,这种力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空间分异、乡村日常生活秩序解构和“城―乡”社区空间与身份认同的迷失。
因此,如何重构渐渐趋式微的“熟人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关照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空间生产;资本循环;城市变迁;乡村城镇化
“20世纪的社会理论历史是时间和空间观念都缺失的历史”[1]。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空间理论研究似乎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新热点,亦成为分析社会问题的全新视角。
正如福柯所认为的,“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来临,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感知和经历的世界正在成为一种时空节点的相互联接”[2]。
“空间研究渐渐成为一门显学,人们对于空间的实践意义更加关注,关注人作为空间主体性行为和空间的生产,空间正在变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3]。
因此,空间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和理论转向开始逐渐进入地理学、社会学和城市学的研究视野,形成各自不同的研究范式。
其中以列斐伏尔、哈维、卡斯泰尔斯、索佳等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正式开启了社会理论的空间研究转向,成为理论体系相对成熟的空间研究理论体系。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所强调的资本积累、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等核心议题给当下中国的城市社会变迁带来双重启发意义。
一是“社会―空间”理论为认识、解读和反思城乡空间变迁提供新的路径;二是转型期的中国城市也为“社会空间”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现场”和“诊断所”[4]。
一、历史与脉络: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缘起与发展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城市危机”(城市郊区化、失业率增加、工人运动和劳资冲突等)。
在这一背景下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泰尔斯等一批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城市空间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缓解危机的“商品”。
因此,“城市作为资本主义场域下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空间,开始被真正研究。
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所有方面的对立统一体”[5]466-479。
而一批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将研究的视角和主题转向城市(空间),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空间的研究来获得新的理论创建。
在此基础上,根据历史线索和研究主题,本文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理论开拓阶段:
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这一时期的理论特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城市(空间)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的每一个理论阐释都隐含了马克思的‘幽灵’”[6]。
卡斯泰尔斯也认为自己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采用法国学者路易斯?
阿尔杜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认识城市现象的”[5]86。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涵盖了资本积累、空间资本化和城市运动等方面的内容,研究者力图分析城市空间资本化和集体消费作用下的资本主义延续和扩张。
代表人物包括哈维、列斐伏尔、卡斯泰尔斯、琼?
洛基肯、克里斯坦?
托波罗夫和戈达德等一批法国学者。
列斐伏尔在这一时期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他首先认为城市是系统性的存在,是人的社会性的空间化表现,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空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成为资本主义减缓危机和实现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之一。
为了实现其空间理论的系统化,他还通过类型学视角将空间划分为空间的实践(spatialpractices)、空间的表现(representationofspace)与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三个要素,即分别对应空间的实在(lived)、想象(conceived)和认知(perceived)等三个层面。
实际上,他的空间理论已经从研究的客体视角转向了主体视角,大大拓宽了空间理论的外延。
曼纽尔?
卡斯泰尔斯(ManuelCastells)①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研究也是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城市问题开始的。
他的代表作之一《城市问题:
马克思主义方法》(1972),被看成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最重要的城市社会学著作之一”[7]。
哈维在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则是提出了资本的“三次循环”理论,以此来分析资本主义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具体可见其《资本的城市化》一书。
在哈维看来,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表现,因此“城市化是资本的积累过程。
城市作为特殊空间,使得劳动力、商品和资本要素自由流动,见证了组织关系和空间关系的变革,同时又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资本的控制下产生的,直接体现了某种政治权力”[8]。
(二)全面发展阶段:
现代性视角下的空间思考
这一阶段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不仅涉及领域多(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等),而且研究的主题也更为多元化。
尤其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背景下,研究者更加关注空间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以及考察当代社会城市空间安排的结构化演进过程。
虽然,这一时期有关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成果的作者并非都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城市、资本和阶级冲突的理论。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是大卫?
哈维、马克?
戈特迪纳、华勒斯坦、梅西、哈维?
莫洛奇、乔?
R.费金和沙伦?
朱肯等。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社会的生产。
空间已经不仅仅是指事物处于一定的场景之中的那种经验性的设置,也是指一种态度与习惯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空间化(TheSpatialisationofSocialOrder)”。
他在《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中进一步指出:
空间已经在当前的生产模式中成为一种现实,与商品、金钱和资本一样承担着全球化进程的使命。
卡斯泰尔斯则认为,现代性背景下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国家提供的城市物品和服务,即“集体消费”,以此来充分保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集体消费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容易导致劳资斗争,进而演化为国家和城市社会运动间的矛盾。
而这一矛盾恰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的结构性矛盾,“表明马克思所关注的发端于劳动过程的矛盾已经让位于因‘集体消费’不足而导致的城市社会运动”[9]。
马克?
戈特迪特(M.Gottdiener)在批判传统城市空间研究的过度技术化倾向的基础上,强调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并认为空间关系涉及资本、劳动和技术变迁。
他还着重分析了政府和房地产在改变城市空间结构中作用及其资本运作机制。
吉登斯对于空间的研究则是放置于社会结构性视角下来分析的,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借鉴时间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诸如区域化、时空抽离、场所、在场和不在场的空间概念;二是利用这些概念来分析社会互动在空间结构中是如何影响和改变社会的资源分配和运行机制。
因此,吉登斯是将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联系在一起分析的。
(三)多元化发展阶段:
后现代视野下的空间转向
进入20世纪80年末和90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转向和趋势,突出表现为:
一些学者开始将“后现代主义、后福特制和后资本主义”等后代性的理论视角运用到城市空间的研究中。
正如哈维所认为的:
“空间重组成为后现代时期的核心议题。
时空压缩导致的文化实践与政治实践出现剧烈的变化,这构成了后现代时期的重要特征”。
苏贾则是通过批判性视角进入空间理论研究,并发展出了一套“空间―历史”辩证法。
他用“三重辩证法”(社会性、空间性和时间性)来透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
福柯则致力于权力与知识空间化趋势的考察[10],他的空间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空间是构成社会权力运作的场所和媒介,我们的生活是在空间中被安排的,如学校、医院、监狱、超市、公司等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和区域。
为此,福柯还大量使用空间的隐喻来表达空间的无处不在,如位移、区域、领土、景观、地平线、群岛等[2]。
二是福柯关于空间与知识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后现代语境下知识能够改变空间和实施权力。
“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和过度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
可见,后现代语境下新马克思空间理论更多地是沿着“空间―权力―知识”的逻辑展开的,它们不仅承认空间的实现性和普遍性,而且都对关系、知识和权力对空间的塑造进行了重点的理论关照。
苏贾更是致力于整合各种空间理论论述来形成一般意义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
哈维则提出了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空间体验与“时空压缩”。
他认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间是被淹没下“时间―历史”的维度中,而后现代主义则重新发现了空间,并将其作为独立存在来研究。
哈维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时空体验称之为“时空压缩”,旨在说明“后现代主义条件下,时间在加速和空间范围则在缩减”[11],而原因依旧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在于“用时间来消灭空间”[12]。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斯泰尔斯开始转向信息化网络研究,相继出版了《信息时代:
经济、社会与文化》(TheInformationAge:
Economy,SocietyandCulture)(1996)、《认同的力量》(ThePowerofIdentity)(1997)和《千禧年之终结》(EndofMillennium)(1998)等三部曲。
他在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
信息技术正在改变城市的形态和整个世界的秩序,另一方面“对地方之间互动性的强调,使得空间之间形成流动的交换网络,促使了新型城市空间即流动空间的兴起”。
二、资本积累与空间权力:
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也是最先被运用到城市(空间)问题的解释中。
因此,从一开始城市及问题研究就成为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主要研究议题。
可以说,城市不仅构成了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更是成为理论运用与发展的实践“场域”。
总体上来看,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关于城市研究是以空间的社会性为理论原点,进而以资本和空间为核心变量。
(一)资本循环积累:
城市空间塑造的重要动力机制
“资本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
为了解决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资本第一循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寻求新的流通方式,即资本转向对建成环境(特别是城市环境)的投资,进而推动城市的扩张和发展(资本第二循环)。
由于资本转化的暂时性和循环性,使得资本积累创造的城市空间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隐藏了一定的城市危机(城市无序扩张和大拆大建),进而为进一步的资本循环和积累创造条件”[13]。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循环和积累构成了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虽然列斐伏尔和哈维对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持批判态度,但是资本作为城市发展的要素是不容忽视的。
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研究之间嫁接了一座桥梁。
哈维延续了列斐伏尔的资本循环理论,认为面对过剩的资本和劳动生产力,资本主义往往通过城市建设等生产项目将资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以空间换时间。
哈维将资本积累与城市化的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本第一循环的结果,生产部门的危机是城市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防止危机的有效方式就是用长期计划来吸收过剩的资本。
二是城市物质环境的建设有助于加快资本积累,在一定时间内维护资本主义的稳定。
这样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嵌入到空间中被当作土地资本或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第二自然”(经由人类改造的自然,城市构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三是资本主义城市化与资本积累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为此哈维用“空间修复”(spatialfix)来说明这一空间逻辑。
理论上,这种“修复”包含着两层基本含义:
第一,资本危机在空间上的修复,是指“整个资本的其中一部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以某种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中和国土之上”[14],二战后美国郊区化的发展,为资本开拓了新的市场,也刺激了新的消费需求;第二,资本危机在时间上的修复,即“资本主义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来解决资本危机的特殊办法”,如资本主义的“分期付款”金融政策将大量住宅拥有者成为负债人,在某种意义上建立了资本与负债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在时间上达到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目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积累与“空间修复”对于影响城市化发展的意义。
(二)权力与冲突:
城市空间占有与分配的社会性与政治性
空间充满着社会关系,它不仅靠社会关系来维持,也在生产着社会关系。
正是空间的这一社会性决定了空间具有政治性,空间离开意识形态就不再是一种科学的对象,它总是包含着政治性和策略性。
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空间等级和人际距离都是空间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表现。
为了从空间主体实践视角进一步说明空间的社会属性,列斐伏尔划分出了三种不同空间活动类型:
“物质空间活动、空间性标识和标识性空间,强调不同空间给人带来的感知、实践和想象”。
在此基础上,哈维从人与空间互动出发,概括了空间的三种特性:
“可接近性与距离、空间的分配与使用、空间的控制”[15]。
进一步,哈维将空间的社会性引入到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阶级性分析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空间关系浸透着阶级含义,空间受到性别、种族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15]。
显然,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已经变成了包含社会关系的“抽象空间”,甚至空间本身已成为商品。
因此,“我们现在得出一个实质性的观点:
资本主义通过对空间的征服和整合而得以延续。
空间不再是被动的地理环境和几何体。
它甚至已经是国家机构的一种工具”。
根据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理论,城市既是社会结构,也是权力结构,具有政治性。
无论是空间的社会分异,还是资本积累和“集体消费”作用下产生的阶级矛盾和权力斗争,都决定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矛盾和紧张,“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大量产生激烈的相互冲突”[16]。
卡斯泰尔斯在《城市与民众》(TheCityandTheGrassroots)(1983)一书中着重分析了欧美社会的城市社会运动。
在他看来,城市是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城市社会运动的本质是城市居民对政府权力的反抗,是城市民众为了获取高水平的“集体消费”、社会文化的改造与认同和政治上的自治管理等目标而进行的维权斗争。
阿德尔纳?
约翰?
雷克斯是从城市住宅的角度来分析不同住宅阶级之间的冲突的。
他在《种族、社区和冲突》(1967)中指出,城市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阶级冲突中“被构建的环境”(GreatedEnvironment),其中住宅对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城市中存在不同的高低不等住宅阶级,国家提供的国民住宅为低收入者提供了优惠。
但是背后交织着多种权力关系,哪些人能够拥有国民住宅显然是官僚、市场和权力等多种因素平衡的结果。
这为不同住宅阶级之间、政府和民众之间埋下了冲突的根源。
英国另一位学者帕尔在雷克斯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管理者”理论,指出资源分配不平等是造成城市社会冲突的根源。
他认为城市资源的分配是由处在优势经济结构地位和拥有权力的科层官僚所决定,因此,城市是典型的“社会―空间”体系。
此外,哈维的《后现代性的条件》(1989)、沙伦?
朱肯的《后现代城市景观:
文化与权力研究》(1992)、乔?
R.费金的《新城市理论》(1998)和马克?
戈特迪纳的《新城市社会学》(TheNewUrbanSociology)(1994)等。
这些著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常用“权力―冲突”和“权力―阶级”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城市问题。
(三)空间重组与再造:
“流动空间”与全球城市化网络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信息技术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对城市与空间产生了实质性的冲击。
一时间“全球化空间”、“全球城市网络”、“世界城市”等概念成为潮流。
全球化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打碎了行为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成为流动的交换网络,并促使新的空间即流动空间的兴起。
为此,卡斯泰尔斯认为,全球化使时空不断被压缩,全球化中的城市社会正在变成“网络社会”。
在网络社会中,地点空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空间在新技术的作用下正在被不断压缩,地点的作用也在被弱化。
与流动空间和网络社会相伴而生的另一个主题是城市空间的异化。
萨森在其《全球城市》(TheGlobalCity)(1995)一书中提到:
所谓的全球化城市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权力交叉重合的空间。
全球化作用下的“权力空间几何学”,正在以几何级的速度和广度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实现着权力的蔓延与扩张,从而加剧了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平等。
因此,我们看到的各种空间极化现象,“富人堡垒型社区、绅士化社区、城市群、居民空间分异、边缘城市、城中村、贫民窟等都是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典型表现”[17]。
Smith在《全球视野中的第三世界城市》(ThirdWorldCitiesinGlobalPerspective)(1996)一书中以一种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式,分析了世界体系扩张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形成原因。
苏贾(Soja)在《第三空间》(TheThirdSpace)(2005)一书中主要采用了“社会―空间辩证法”分析了全球化浪潮下城市面临的诸如后殖民主义、阶级和女权主义等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沙朗?
佐京(SharonZuki)的《城市文化》(TheCulturesofCities)(2006)也认为在全球城市化背景下,文化已经不再是人类生活的附属地位,俨然已经成为同经济一样控制和影响城市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决定城市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关键性要素。
三、理论与实践:
空间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城镇化反思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乡村的城镇化,而乡村的城镇化也构成了现代意义上“城市化”过程的主要内容。
这一过程中,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现代生活方式取代传统生活方式,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逐渐代替自然增长的城市,也最终使城市战胜了乡村”[18]。
因此,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的乡村城镇化是一个交织着各种政治、经济、权力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乡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大规模的征地运动、城乡结合部的“过渡性社区”、失地农民问题、城中村和农民工进城等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出现。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源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城市危机的批判性反思,是否可以被运用到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的解释与研究,国内学者自2003年②以后已经做了积极的尝试。
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尝试着运用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逻辑和主要议题,来分析当前中国乡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现象与问题,一方面通过文献阅读梳理出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现有的理论研究的梳理,寻找到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运用到乡村城镇化分析的新视角。
(一)资本逻辑下的城镇空间生产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城市化空间即是资本的空间化,体现的是资本对利益追求在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
“城市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建构的环境,是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16]。
因此,城市空间具有资本性和文化性,具有一定的“城市文化资本”③的价值与意义。
这一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城市分析,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乡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剧烈变迁。
表面上来看,乡村城镇化过程体现的是乡村空间与社会的变迁,而真正推动乡村城镇化的却依然是资本的作用机制。
本质上看,乡村城镇化是城市资本积累在乡村的延续。
如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使得乡村土地被占用变得合法化,大量的农民被“制度性”地安排到城镇社区集中居住,形成所谓的“准城镇化群体”。
而城市的资本力量不仅获得了资本投资的新项目,而且通过房地产的开发和“房贷”与农民之间建立了某种“利益机制”。
因此,中国各地出现的各种撤村并点、过渡性安置社区和新型农民社区等,事实上依旧是城市资本力量和政府权力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
如台湾学者夏铸九④在分析台湾彰化县的空间变迁中论述了在经济发展和利益的驱动下,空间结构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过程,并开创性的提出了一个如列斐伏尔和苏贾“三元空间观”相对应的“经济―政府(政策)―文化分野”[19]新的空间观。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对于开弦弓村社会变迁的记述,同样是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乡村在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下,如何实现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观察中国村庄转型中,毛丹也认为“乡村被越来越卷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城市与农村,市场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整理和安排”[20]。
(二)城乡空间的权力性与不平等性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具有政治性。
空间不仅是发生冲突的场所,也是斗争的目标本身。
因此,空间是一种政治和权力的生产”[21]。
空间的生产、占有与分隔正是政治和权力的体现,因此,城镇空间也往往成为社会力量博弈和对抗的场所。
这一理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的乡村城镇化分析。
根据卡斯泰尔斯的观点,城市是作为“集体消费”的空间“场域”而存在的,由于集体消费品主要是政府来供给,地方政府利用公共资源的垄断权力,如企业一般地追求短期政治利益。
因此,政府利益与城市增长的双向“寻租”[22]现象就会发生。
在这一权力机制的作用下,乡村城镇化中的强制拆迁和补偿不均等现象时有发生,成为政府与群众冲突的主要原因。
而冲突中所谓的农民集体行动,已经不再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甚至演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话题”[23]。
如张鹏⑤在《都市里的陌生人》书中,指出了空间本质的政治性,并分析了表现于其中的权力关系。
杨念群则直接运用空间与权力的理论对城市医疗空间转向进行了分析,描述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秩序如何被侵入、打破和重组[24]。
因此,国家和政府权力对传统区域的侵入,不仅容易破坏原有的稳定的生活秩序,而且这种空间权力又在塑造着空间中主体的行为。
如潘泽泉主要通过运用“社会空间”理论,来研究农民工的“主体性”存在,即国家权力对农民工主体的塑造力量,以及农民工作为主体与这种塑造力量相抗衡的过程[4]。
朱健刚认为,社区存在“权力的三重组织网络”;李友梅则从社区的日常生活框架,提出了简单社区、复杂社区和流动社区的分野。
一个可见的事实是,研究者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城市空间并非一个被动的容器,而是一个“由资本、法律、秩序构造的空间,展示的是合乎资本与权力运行逻辑的自然结果:
不同收入阶层所占据的被分割的生活、生产及消费的空间和场域”。
(三)乡村日常生活秩序的冲击与解构
列斐伏尔不仅开创了“空间生产”的理论维度,还有力地将空间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引入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空间转向,将空间的普遍性分析“嵌入”到了“在场”的日常生活情境中。
因此,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分析的“三位一体”⑥架构,就成为分析空间生产对于日常生活秩序解构与重构的依据。
在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入侵下,城乡社会结构会出现“侵入与接替”⑦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三种形式:
一是城乡间物质和文化的对流;二是资本和市场的传导;三是城市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对乡村的辐射”[25]。
哈维在《后现代现状》一书中也指出,“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然通过物质实践与过程创造出来,这些空间实践过程再生产了社会生活”。
而中国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在市场和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原有的乡村日常生活秩序逐渐解体。
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中运用村落边界和生活空间半径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居民日常生活秩序的变化。
一个基本结论就是:
“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其三大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