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男性想象.docx
《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男性想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男性想象.docx(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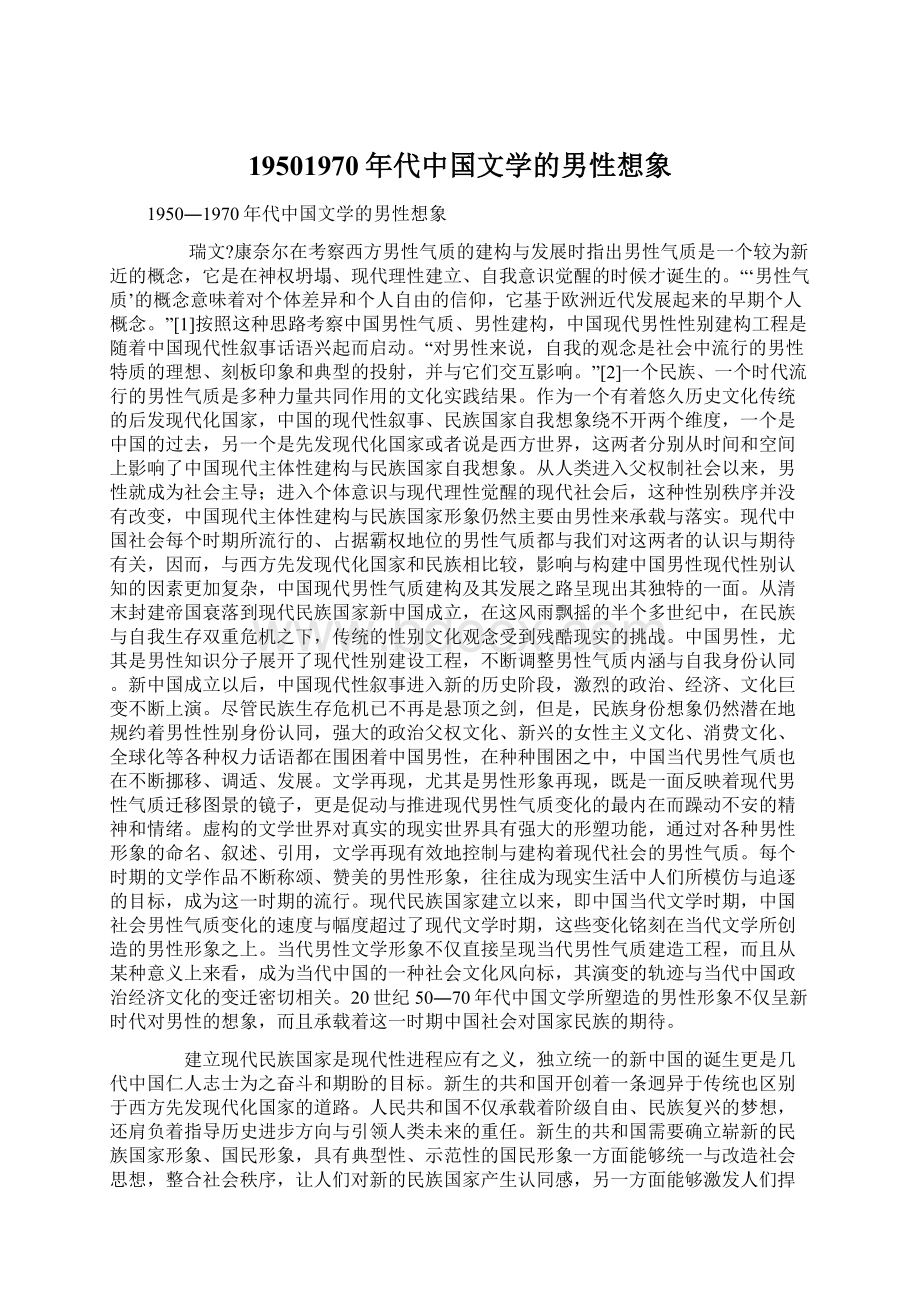
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男性想象
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男性想象
瑞文?
康奈尔在考察西方男性气质的建构与发展时指出男性气质是一个较为新近的概念,它是在神权坍塌、现代理性建立、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才诞生的。
“‘男性气质’的概念意味着对个体差异和个人自由的信仰,它基于欧洲近代发展起来的早期个人概念。
”[1]按照这种思路考察中国男性气质、男性建构,中国现代男性性别建构工程是随着中国现代性叙事话语兴起而启动。
“对男性来说,自我的观念是社会中流行的男性特质的理想、刻板印象和典型的投射,并与它们交互影响。
”[2]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流行的男性气质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文化实践结果。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性叙事、民族国家自我想象绕不开两个维度,一个是中国的过去,另一个是先发现代化国家或者说是西方世界,这两者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影响了中国现代主体性建构与民族国家自我想象。
从人类进入父权制社会以来,男性就成为社会主导;进入个体意识与现代理性觉醒的现代社会后,这种性别秩序并没有改变,中国现代主体性建构与民族国家形象仍然主要由男性来承载与落实。
现代中国社会每个时期所流行的、占据霸权地位的男性气质都与我们对这两者的认识与期待有关,因而,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和民族相比较,影响与构建中国男性现代性别认知的因素更加复杂,中国现代男性气质建构及其发展之路呈现出其独特的一面。
从清末封建帝国衰落到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在这风雨飘摇的半个多世纪中,在民族与自我生存双重危机之下,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受到残酷现实的挑战。
中国男性,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展开了现代性别建设工程,不断调整男性气质内涵与自我身份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现代性叙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巨变不断上演。
尽管民族生存危机已不再是悬顶之剑,但是,民族身份想象仍然潜在地规约着男性性别身份认同,强大的政治父权文化、新兴的女性主义文化、消费文化、全球化等各种权力话语都在围困着中国男性,在种种围困之中,中国当代男性气质也在不断挪移、调适、发展。
文学再现,尤其是男性形象再现,既是一面反映着现代男性气质迁移图景的镜子,更是促动与推进现代男性气质变化的最内在而躁动不安的精神和情绪。
虚构的文学世界对真实的现实世界具有强大的形塑功能,通过对各种男性形象的命名、叙述、引用,文学再现有效地控制与建构着现代社会的男性气质。
每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不断称颂、赞美的男性形象,往往成为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模仿与追逐的目标,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即中国当代文学时期,中国社会男性气质变化的速度与幅度超过了现代文学时期,这些变化铭刻在当代文学所创造的男性形象之上。
当代男性文学形象不仅直接呈现当代男性气质建造工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文化风向标,其演变的轨迹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所塑造的男性形象不仅呈新时代对男性的想象,而且承载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对国家民族的期待。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进程应有之义,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诞生更是几代中国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和期盼的目标。
新生的共和国开创着一条迥异于传统也区别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
人民共和国不仅承载着阶级自由、民族复兴的梦想,还肩负着指导历史进步方向与引领人类未来的重任。
新生的共和国需要确立崭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国民形象,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国民形象一方面能够统一与改造社会思想,整合社会秩序,让人们对新的民族国家产生认同感,另一方面能够激发人们捍卫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热情和力量,尽快地使梦想与目标变成现实,从而证明和宣传现代民族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初期,建立社会新秩序,反抗外敌侵犯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任务。
在这种特殊语境中,英雄形象无疑是完成这种任务的最好选择。
不论西方还是东方,现代社会通常都会通过社会典范对国民进行激励、说服、规范,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
从古到今英雄都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在新中国把具有新时代所需求的完美品格且具有广泛性的人民英雄作为社会典范、国民形象来推广,无疑能够赢得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国民的高度认同,能够凝聚起最大的力量,从而使得从旧中国混乱无序的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快速又有效地在“一个中心点上凝聚为有序的整体”。
[3]在论及非西方现代国家民族时,酒井直树指出:
“为了反对西方的侵犯,非西方必须团结组成国民。
西方以外的异质性可以被组织成一种对西方的顽强抵抗。
一个国民可以采用异质性来反对西方,但是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
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称的‘普遍同质领域’,就成不了国民。
所以,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现代国民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排除国民内部的异质性。
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要在国民整体与其中的异质成分之间如出一辙地复制出来。
”[4]按照酒井直树的论点,作为一个非西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新中国国民形象必然包含两个特点,一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即异质性,二是排除共和国内部不同观念、阶层、利益集团等的异质性,使其具有同质性、一体化的特质。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国民形象典范的英雄,决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绿林好汉”。
它是一个经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统一改造过的“绿林好汉”,其身上一方面流淌着中国传统英雄文化血脉(体现非西方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却又必须消除各种江湖习气、神仙气(实现了同质性),只有在接受现代革命伦理规训后,“绿林好汉”才能成为当代国民典范形象。
在封建时代,中国社会的各路英雄大都由男性来演绎,尽管新中国设立了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但是,男权中心文化并没有能够被推翻,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叙事中现代革命英雄的主要缔造者与实践者仍然由男性来承担。
尽管部分女性被列入了英雄的行列,比如现实世界中的刘胡兰、江竹筠,文学世界中的林红(《青春之歌》)、江姐(《红岩》),可是她们改变不了英雄的整体性别指向。
作为一个旨在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利益作为首位的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意识形态把英雄的阶层限定在劳动人民范畴之内。
人民英雄是新中国建立与发展初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形象,是具有霸权地位男性气质的承载者、创造者。
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塑造了一大批由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组成的男性英雄,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基本退出英雄行列。
从数量结构、时间空间构成来看,这一时期的男性人民英雄形象主要由历史革命英雄和当代革命英雄来组成,前者聚集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塑造的历史革命英雄,如朱老忠(《红旗谱》)、杨子荣(《林海雪原》),后者汇拢在反映现实的农村和工业题材小说中所塑造的当代英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新人”,如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所流行的、占主导的男性气质主要由这些作品中的男性英雄来担当。
除了这些被赞美、称颂的正面红色英雄人物形象在建构着现代主导性男性气质以外,那些被批判、被抨击的灰黑色反面人物形象也参与了当代男性气质的建设,如老妖道(《林海雪原》、高自萍(《野火春风斗古城》)等。
通过对这些反面男性形象的书写与批判,人们就把不符合当代社会所需求的男性气质剔除出去,保障主导性男性气质的纯正性。
现代社会多样化男性气质的建构需要自我意识的加入。
在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具有统摄性的力量与权威,个人话语的形成与表达受到压抑,而强大的意识形态又拥有巨大主体召唤力量,这一阶段中国人的主体建构主要体现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应答之中,因而,不论国家形象还是国民形象的再现与想象都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下进行。
与以往相比,当代文学领域这一时期男性气质的建构、男性形象的再现出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主导性男性气质的建构主要由来自工农兵的人民英雄形象来承担。
第二,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民英雄形象塑造的管控,不符合革命需要的传统男性特征(如粗俗、没有阶级立场的侠义等)被消除和整肃,从革命历史传奇小说中的传奇性战斗英雄,如杨子荣、刘洪(《铁道游击队》、肖飞(《烈火金刚》),到革命史诗中的成长型、殉道型英雄,如朱老忠、许云峰(《红岩》),再到反映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合作化小说中的当代英雄,如梁生宝、萧长春,男性人民英雄一步步走向高大、完美,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创造的男性英雄人物,如高大泉(《金光大道》)、欧阳海(《欧阳海之歌》,人民英雄最终走向外表坚强、人格完美、道德高尚、无私无欲的超人英雄。
第三,在人民英雄形象(包括其对立性的男性)以外,也有其他正面男性人物形象试图参与当代男性气质的建构,修订中国当代男性气质。
在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形成统摄一切的政府,知识分子被置于被改造位置,但是,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再现还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在政治一体化有所松动的时刻,没有被完全规训的自我意识仍然会在文学叙述中旁逸斜出。
这一时期作为正面人物被肯定的男性形象除了人民英雄以外,还有像林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陶渊明(《陶渊明写挽歌》)、杜甫(《杜子美还乡》这样有着现代知识分子、传统文人身份的男性形象,他们在小心翼翼、曲折隐晦地传达着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体意识,把思虑、惶惑、苦闷等特征纳入了男性形象之内。
第四,部分女作家塑造的男性英雄在补充、修订着男作家所塑造的男性形象,把优雅、柔和、单纯、羞涩等特点加入到男性英雄身上,如小通讯员(《百合花》)、卢嘉川(《青春之歌》)。
女作家塑造的这些男性形象,给渐趋单一僵化的高大、刚健、勇敢、忠诚、奉献、无欲的男性形象带来清新之风。
在新中国男女平等的国策激励之下,女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大幅度提高,作为男性性别建构的他者,女性社会形象的改变必然影响着男性形象再现与男性气质建构。
尽管在时代风向的影响与规约之下,这一时期女作家的性别意识淡化,其创作的女性英雄都呈现中性化或者雄性化的倾向,但是,获得文学再现权力的女作家,毕竟有能力去审视男性、再现男性,去创造她们所期待的男性形象,在有意与无意之中,女作家把自己的性别意识、性别期待带入了笔下的男性英雄人物身上。
总之,强健、硬朗、刚毅、忠诚的男性人民英雄形象体现了新中国对我们国家的自我想象,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弱国子民”“东亚病夫”的国民形象,这些来自劳动人民的英雄也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男性现代气质建构的走向。
然而,在这个英雄文学占据文坛制高点、男性英雄比比皆是的时代,现代中国男性气质却遭受重创:
作家自我意识匮乏,神性取代人性,群体性取代个体性,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渐渐成为这一时期英雄文学创作的通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中达到巅峰。
有学者在论及样板戏中的男性英雄时写道:
“在高大俊朗的男性表象之下,其实是男性的精神阉割,男性躯体成为一个被抽空的空壳,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
……政治对身体进行规训、设计、控制、改造、占有,使之成为‘无器官的身体’,无欲望的身体,无性别的身体,单一化的身体,标准化的身体,一个被瓦解的身体。
”[5]。
尽管文学再现在不断地批量化地生产着男性英雄,作为个体的男性并没有能够凭借英雄形象的大量存在而建立起男性性别主体地位,这些剔除“血肉之身”的男性英雄反而让男性失去了性别主体地位。
同时,国家政权构成了强大的政府,具有压倒一切的“阳”性,在“它”的统摄下,其他的一切都具有了“阴”性特征。
[6]男性的权威性被国家政权的父性权威所压倒。
在现实世界里独立自主、坚强不屈的精神存在很难寻觅,再加上逼仄的生存空间、匮乏的物质生活,男性信心与威严遭受极大打击,中国男性人格萎缩几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因此,当激进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刚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伊始,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似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了“男子汉缺失”的恐慌之中,“阳衰”再次成为社会性焦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男性再现研究”(批准号:
13YZA751025)的阶段性成果。
]
注释
[1]詹俊峰、洪文慧、刘岩编著:
《男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2][澳]雷金庆:
《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澳]刘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王一川:
《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4]酒井直树:
《现代性与其批判:
普遍主义与特殊性》,张京媛编:
《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409页。
[5]张伯存:
《中国当代文学和大众文化中的男性气质》,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19―20页。
[6]参见黄子平:
《“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作者单位:
济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