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docx
《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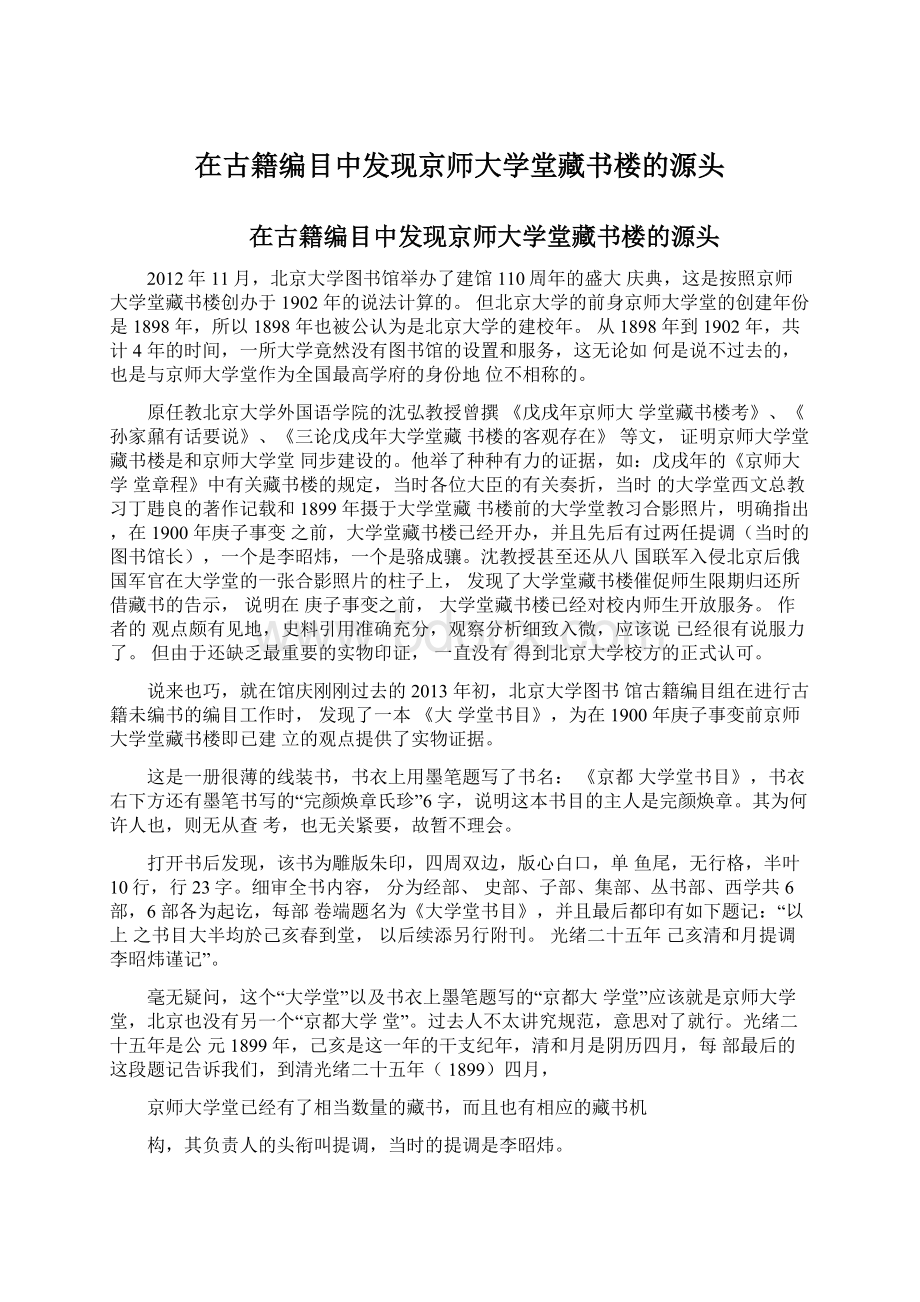
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
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
2012年1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建馆110周年的盛大庆典,这是按照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办于1902年的说法计算的。
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年份是1898年,所以1898年也被公认为是北京大学的建校年。
从1898年到1902年,共计4年的时间,一所大学竟然没有图书馆的设置和服务,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也是与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身份地位不相称的。
原任教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沈弘教授曾撰《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考》、《孙家鼐有话要说》、《三论戊戌年大学堂藏书楼的客观存在》等文,证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和京师大学堂同步建设的。
他举了种种有力的证据,如: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关藏书楼的规定,当时各位大臣的有关奏折,当时的大学堂西文总教习丁韪良的著作记载和1899年摄于大学堂藏书楼前的大学堂教习合影照片,明确指出,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大学堂藏书楼已经开办,并且先后有过两任提调(当时的图书馆长),一个是李昭炜,一个是骆成骧。
沈教授甚至还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俄国军官在大学堂的一张合影照片的柱子上,发现了大学堂藏书楼催促师生限期归还所借藏书的告示,说明在庚子事变之前,大学堂藏书楼已经对校内师生开放服务。
作者的观点颇有见地,史料引用准确充分,观察分析细致入微,应该说已经很有说服力了。
但由于还缺乏最重要的实物印证,一直没有得到北京大学校方的正式认可。
说来也巧,就在馆庆刚刚过去的2013年初,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组在进行古籍未编书的编目工作时,发现了一本《大学堂书目》,为在1900年庚子事变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即已建立的观点提供了实物证据。
这是一册很薄的线装书,书衣上用墨笔题写了书名:
《京都大学堂书目》,书衣右下方还有墨笔书写的“完颜焕章氏珍”6字,说明这本书目的主人是完颜焕章。
其为何许人也,则无从查考,也无关紧要,故暂不理会。
打开书后发现,该书为雕版朱印,四周双边,版心白口,单鱼尾,无行格,半叶10行,行23字。
细审全书内容,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西学共6部,6部各为起讫,每部卷端题名为《大学堂书目》,并且最后都印有如下题记:
“以上之书目大半均於己亥春到堂,以后续添另行附刊。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清和月提调李昭炜谨记”。
毫无疑问,这个“大学堂”以及书衣上墨笔题写的“京都大学堂”应该就是京师大学堂,北京也没有另一个“京都大学堂”。
过去人不太讲究规范,意思对了就行。
光绪二十五年是公元1899年,己亥是这一年的干支纪年,清和月是阴历四月,每部最后的这段题记告诉我们,到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
京师大学堂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藏书,而且也有相应的藏书机
构,其负责人的头衔叫提调,当时的提调是李昭炜。
查考由梁启超起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呈的《谨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其第一章第六节这样写道:
“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
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良意美!
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即是此意。
近年张之洞在广东设广雅书院,陈宝箴在湖南设时务学堂,亦皆有藏书。
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闳。
今拟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
”该《章程》第六章第六节中明确规定:
“藏书楼设提调一员,供事十员”。
第七章第二节还详载藏书楼提调每月薪水为五十两,每年合计六百两。
第七章第三节更是规定了藏书楼的经费开支:
“建筑藏书楼费约两万两,……购中国书费约五万两,购西文书约四万两,购东文书约一万两”。
吴晞先生撰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第8页则有这样一段记载:
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初三发表了一条“京师大学堂奏派总办提调名单”的消息,其中谈到:
“管学大臣孙中堂已于上月二十九日将大学堂总办提调开具衔名,缮折奏派,兹将衔名开列如后:
……藏书楼提调一员,詹事府左春(原文误为“香”)坊左庶子李昭炜”。
查北京大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44页,孙家鼐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上的奏折的原文是:
“詹事府左庶子李昭炜拟派充藏书楼提调兼官书局提调”。
由此可见,《大学堂书目》中于经、史、子、集、丛、西学每部书目之后书写那段题记的提调李昭炜,就是当时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第一任负责人,也就是第一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底被奏派为藏书楼提调,何时上任不晓,但根据《大学堂书目》每部后面的题记,至少第二年的四月仍在任上。
李昭炜,字蠡莼,祖籍江西婺源,落籍浙江常山县,清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三甲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户部右侍郎。
除了庚子事变时曾受联军辱打一事,有关他的史书记载并不多见。
其著述未见著录,但在最近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编目中,我们竟然发现了一册光绪三十二年(1906)李昭炜致仕后游览西湖与朋友唱和的诗集《湖上萍踪》一卷。
《大学堂书目》的体例是:
全书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书部、西学6部,每部下不再分类,直接著录藏书;著录内容非常简略,每书著录书名、复本数以及每部书的册数,而且用词也不规范统一。
如《江南局易本义》书名下著录为“十部每二册”,是说有10个复本,每个复本有2册,所以总册数应该是20册。
而《江南局诗经》书名下著录为“十部五册”,没有“每”字,但意思仍然是说有10个复本,每个复本有5册,总
册数应该是50册。
复本数量只有一部的,大多数著录为“一部
XX册”,有的则直接著录册数,如《汲古阁板史记》书名下只著录册数“十六册”。
不少书的复本量较多,如《江南
局相台五经》有八部,《校本史记》有七部,《大学衍义》有八部,作为大学图书馆的典藏,为了满足师生的借阅量,这些个复本量应该说是正常的。
但有些书的复本量过大,如《御制资政要览》书名下著录“每部四册重刊五百部”,总册数达2000册;《弟子箴言》下著录为“三百部四册”,总册数达1200册;《御制数理精蕴几何原本》下著录为“四部三册石印一百部”;《算学启蒙述义》其下著录为“一百部每四册”;《小学集解》下著录为“三百部每四册”;《天文揭要》下著录为“五十部每二册”;《天文须知》下著录为“一百部每一册”;《笔算数学》下著录为“三百部每二册石印一百部六册”;《代数备旨》下著录为“一百部每一册石印二十部每二册”;《格物入门》下著录为“三百部二部每七册”。
这样大的复本量显然不是全部用来典藏的,很可能有些书买来是要发售给学生的。
除绝大多数用“册”为量词外,个别还使用“本”。
如《历代名臣言行录》,其下著录为“八本”。
个别著录内容涉及到版本,如《江西局十三经注疏》下著录为“二部一百八十册,旧版二部,湖南版二部”(旧版和湖南版的册数没有著录);《康熙字典》下著录为“石印二部六册”;《御批通鉴辑览》下著录为“十二部五十八册石印五部六十
册”;《皇朝中外一统舆地图》下著录为“一部十二册石印十部六册”。
当时的大学堂藏书楼有多少书呢?
我根据这部《大学堂书目》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列表如下:
由于个别著录没有明确标明册数,无法统计,所以实际的册数应该大于44964册这个数字,应该有将近5万册。
这样一个藏书规模,并且初步编出分类目录,其工作量绝不是四五个月的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鉴于此书目中李昭炜的题记写在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可以推断,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建设一定是在前一年也就是戊戌年就开始进行了。
即便如此,这个工作效率也是很高的。
这说明,大学堂藏书楼最初的藏书建设工作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
那么,这些书的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京师大学堂第一任西文总教习丁韪良在其所著《汉学菁华: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TheLoreofCathay)一书的《序篇:
中国的觉醒》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义和团焚烧翰林院藏书楼,将京师最丰富的图书收藏付之一炬,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投入水中浸泡毁坏。
”事实上,京师大学堂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期间,先后被俄、德两国军队占为兵营,图书、仪器设备遭到严重损毁,丁韪良将之完全归罪于义和团,是一种想当然的偏见和对联军罪责的推卸。
但大学堂藏书楼的早期藏书在庚子事变中基本被毁,也许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建时,为了充实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
清廷曾下令征集各省官书局所刻书到大学堂藏书楼,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钤盖“大学堂藏书楼藏书章”的许多书,都是清末的局刻本。
但在这部《大学堂书目》中,虽也有江南局本、江苏局本、江西局本、四川局本、湖北局本等名目,但总量并不很大,且主要集中在经部,其他各部极为少见。
这似乎表明大学堂藏书楼最初并没有大规模征集各省官书局所刻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钤有大学堂藏书楼印章的局刻本并非庚子事变前大学堂藏书楼收进的局刻本。
又如《大学堂书目》中《星轺指掌》一书著录为“二部每二册”,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该书5部,但都是4册本,没有2册的。
说明最早入藏的这两部《星轺指掌》已经不存了。
那么,庚子事变前京师大学堂收进的藏书有没有孑遗呢?
有的。
我们最近在古籍编目时就发现了这样一部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
这部书即《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五卷,刻本,1册1函。
该书的卷端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印外,还钤有两方大学堂藏书印,右边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左边是“大学堂藏书楼之章”。
为什么会有大学堂藏书楼两方不同的藏印呢?
旧装书衣有林传树、勤轩识语,揭开了这个秘密:
“此编原为大学堂藏书,偶于厂肆旧书摊上得之,故仍交藏书楼加戳藏之。
预备科学生侯官林传树志。
”其左另有墨书小字:
“编首两藏书楼图记,一旧
印在庚子前,一新印系丙午收还后所记。
三月廿七勤轩识。
”其下还钤有朱印“林传树印”。
两段题记字体相同,可见林传树与勤轩为同一人,勤轩应该是林传树的字或号。
丙午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
经查考,林传树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福建乡试第一名(即解元)林传甲的胞弟。
林传甲,字奎云,福建侯官县人,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1903-1906)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员,讲授历代文章源流,著有《中国文学史》等讲义。
林传甲后来还与林传树合著有《黑龙江教科新图》一书。
由《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书衣上的两段题识可知,这部书原本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并钤盖有藏书楼藏章,庚子事变时流出,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当时身为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学生的林传树在厂肆摊上发现购下,随即交还给大学堂藏书楼,实属万幸!
京师大学堂最初的藏书印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庚子事变后重建的大学堂藏书楼改用“大学堂藏书楼之章”,所以就出现了同一部书上钤盖两种不同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印章的现象。
我利用“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检索本馆所有古籍书目记录,发现钤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朱文大印的书仅有9部计44册。
现将这9部书列表如下。
其中《行军铁路工程》一书在《大学堂书目》中也有着录。
可见,庚子事变前大学堂藏书楼收进的藏书并不是完全损毁了,还是有一些保留了下来。
由于我们仅仅是在2006年重新开始进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未编书的大规模编目后,才开始记录每部书的藏章印记,所以大学堂藏书楼早期藏书的存留数量肯定要多于上表所列的这9部,但确切的数量则有待于今后馆藏古籍重新编目的完成了。
在上述9部书中,有一部书还提供了另外的线索。
这部书即《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卷首二卷,分装28册4函。
其卷端除钤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钤册图章”朱文印章,还钤有“提调骆监置书”一方朱文大印。
查《北京大学史料》一书中所收录的《许景澄呈报大学堂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份收支情况》(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也记载有这个“提调骆”:
“藏书楼提调骆九月份薪水京平足银贰拾伍两。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只设一员,那么这个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在任的“提调骆”一定是第一任藏书楼提调李昭炜的继任。
这个“提调骆”是谁呢?
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44页所录孙家鼐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上的奏折中,也有这样一段话“翰林院修撰骆成骧、翰林院编修黄绍箕、翰林院编修朱祖谋、翰林院编修余诚格、翰林院编修李家驹,以上五员拟派充稽查功课提调。
”沈弘教授在《孙家鼐有话要说》一文中已经考证确切,这个“提调骆”就是大名鼎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状元骆成骧。
不过他最初担任的很可能是稽查功课提调,第二年才继李昭炜之后担任藏书楼提调。
骆成骧(1865-1926).字公啸,四川资中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国史馆纂修、充会试同考官、贵州乡试主考官、广西乡试主考官等职。
辛亥革命后,曾任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都督府顾问、四川筹赈局督办等职,1916年任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校长,1926年病逝,享年61岁。
著有《国文中坚集》六卷、《清漪楼诗存》五卷、《四音辨要》四卷等书。
骆成骧任职大学堂藏书楼期间,一定也积极致力于藏书建设,否则不会专门刻制“提调骆监置书”这样一方印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藏有一个《大学堂藏书楼所有光绪二十五年冬季添购各种书籍价银部册数目存案清册》,其中列举了《行水金鉴》等400余册大学堂藏书楼新购置的中文书籍。
这个清册上所列书目应该是骆成骧在其任上购置的大学堂藏书楼藏书。
他的心血并未完全付之东流,钤有他的图章的大学堂藏书楼藏书还有一些保留了下来,告诉给后人真实的历史。
一部出版于1899年的大学堂藏书楼藏书目录,9部入藏于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的大学堂藏书楼旧藏书,这些我们近年来在古籍编目工作中发现的文献,以及书上的相关文字记载和藏章题记,无可辩驳地揭示了这样的史实,即:
1)在1900年庚子事变之前,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已有两任提调,第一任提调是李昭炜;第二任提调是骆成骧。
2)在庚子事变之前,在头两任提调的主持下,大学堂藏书
楼的藏书规模已经达到将近5万册
3)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虽然在庚子事变中遭到严重损毁,但还是有一小部分幸存人间,而且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书库中。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有力地印证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在1898年与京师大学堂同步开办的各种史料记载,充分支持了沈弘教授的相关研究结论,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创建年从目前认定的1902年上溯到了1898年,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相应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也应该从1898年开始计算。
如此说来,2013年恰值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115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附注:
2013年11月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接到北京大学党办校办的书面正式批复(北京大学党办校办/内收文第2789),校方同意北京大学图书馆呈交的《关于追溯北京大学图书馆建馆时间的请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馆时间从以往认定的1902年上溯到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