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格你的白头我的陌路 文喜宝.docx
《爱格你的白头我的陌路 文喜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爱格你的白头我的陌路 文喜宝.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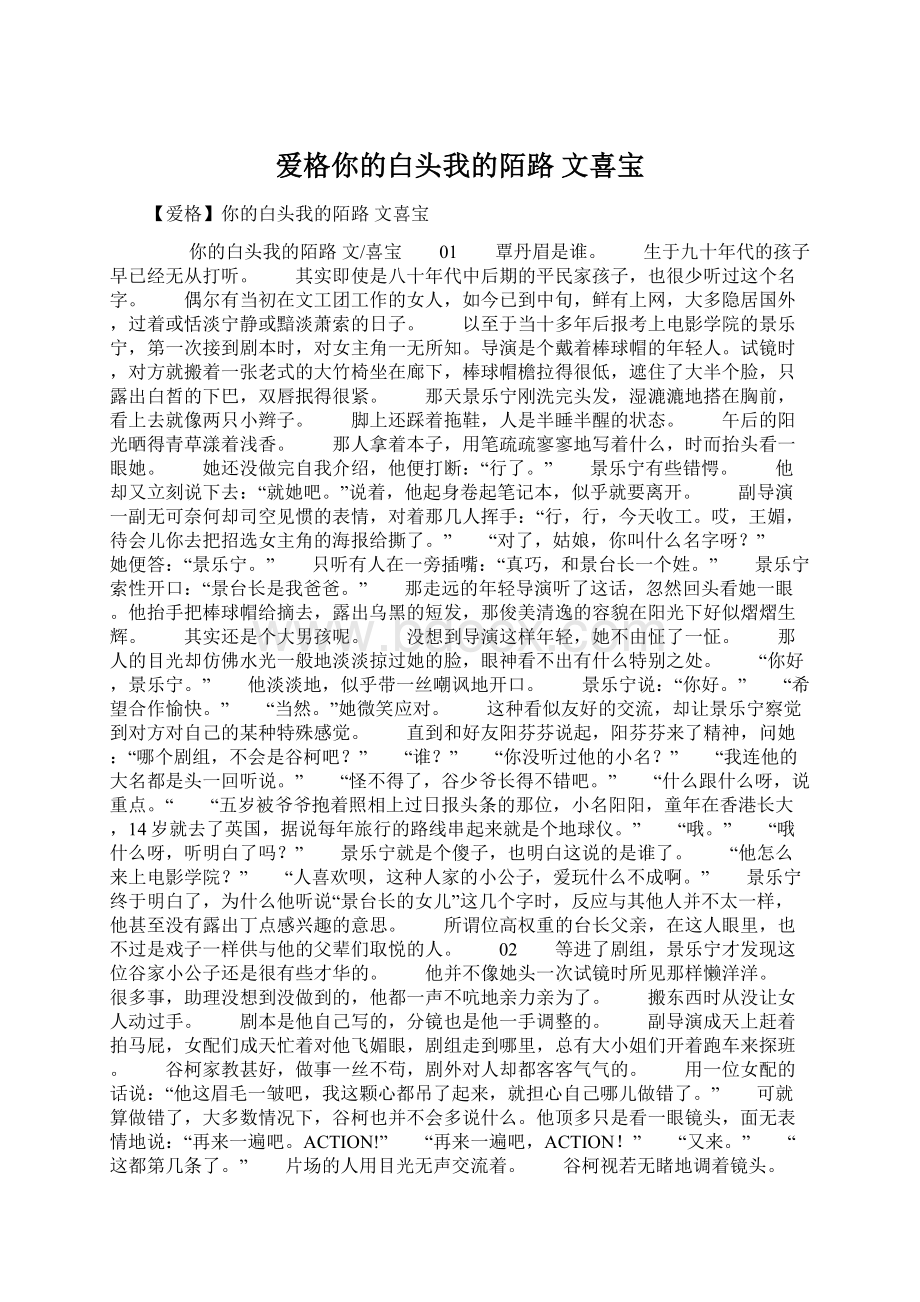
爱格你的白头我的陌路文喜宝
【爱格】你的白头我的陌路文喜宝
你的白头我的陌路文/喜宝 01 覃丹眉是谁。
生于九十年代的孩子早已经无从打听。
其实即使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平民家孩子,也很少听过这个名字。
偶尔有当初在文工团工作的女人,如今已到中旬,鲜有上网,大多隐居国外,过着或恬淡宁静或黯淡萧索的日子。
以至于当十多年后报考上电影学院的景乐宁,第一次接到剧本时,对女主角一无所知。
导演是个戴着棒球帽的年轻人。
试镜时,对方就搬着一张老式的大竹椅坐在廊下,棒球帽檐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个脸,只露出白皙的下巴,双唇抿得很紧。
那天景乐宁刚洗完头发,湿漉漉地搭在胸前,看上去就像两只小辫子。
脚上还踩着拖鞋,人是半睡半醒的状态。
午后的阳光晒得青草漾着浅香。
那人拿着本子,用笔疏疏寥寥地写着什么,时而抬头看一眼她。
她还没做完自我介绍,他便打断:
“行了。
” 景乐宁有些错愕。
他却又立刻说下去:
“就她吧。
”说着,他起身卷起笔记本,似乎就要离开。
副导演一副无可奈何却司空见惯的表情,对着那几人挥手:
“行,行,今天收工。
哎,王媚,待会儿你去把招选女主角的海报给撕了。
” “对了,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 她便答:
“景乐宁。
” 只听有人在一旁插嘴:
“真巧,和景台长一个姓。
” 景乐宁索性开口:
“景台长是我爸爸。
” 那走远的年轻导演听了这话,忽然回头看她一眼。
他抬手把棒球帽给摘去,露出乌黑的短发,那俊美清逸的容貌在阳光下好似熠熠生辉。
其实还是个大男孩呢。
没想到导演这样年轻,她不由怔了一怔。
那人的目光却仿佛水光一般地淡淡掠过她的脸,眼神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好,景乐宁。
” 他淡淡地,似乎带一丝嘲讽地开口。
景乐宁说:
“你好。
” “希望合作愉快。
” “当然。
”她微笑应对。
这种看似友好的交流,却让景乐宁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某种特殊感觉。
直到和好友阳芬芬说起,阳芬芬来了精神,问她:
“哪个剧组,不会是谷柯吧?
” “谁?
” “你没听过他的小名?
” “我连他的大名都是头一回听说。
” “怪不得了,谷少爷长得不错吧。
” “什么跟什么呀,说重点。
“ “五岁被爷爷抱着照相上过日报头条的那位,小名阳阳,童年在香港长大,14岁就去了英国,据说每年旅行的路线串起来就是个地球仪。
” “哦。
” “哦什么呀,听明白了吗?
” 景乐宁就是个傻子,也明白这说的是谁了。
“他怎么来上电影学院?
” “人喜欢呗,这种人家的小公子,爱玩什么不成啊。
” 景乐宁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听说“景台长的女儿”这几个字时,反应与其他人并不太一样,他甚至没有露出丁点感兴趣的意思。
所谓位高权重的台长父亲,在这人眼里,也不过是戏子一样供与他的父辈们取悦的人。
02 等进了剧组,景乐宁才发现这位谷家小公子还是很有些才华的。
他并不像她头一次试镜时所见那样懒洋洋。
很多事,助理没想到没做到的,他都一声不吭地亲力亲为了。
搬东西时从没让女人动过手。
剧本是他自己写的,分镜也是他一手调整的。
副导演成天上赶着拍马屁,女配们成天忙着对他飞媚眼,剧组走到哪里,总有大小姐们开着跑车来探班。
谷柯家教甚好,做事一丝不苟,剧外对人却都客客气气的。
用一位女配的话说:
“他这眉毛一皱吧,我这颗心都吊了起来,就担心自己哪儿做错了。
” 可就算做错了,大多数情况下,谷柯也并不会多说什么。
他顶多只是看一眼镜头,面无表情地说:
“再来一遍吧。
ACTION!
” “再来一遍吧,ACTION!
” “又来。
” “这都第几条了。
” 片场的人用目光无声交流着。
谷柯视若无睹地调着镜头。
片场是一处老式的幕台,看布景颇有几分八十年代初总政歌舞团的样子。
那布景的师傅就是总政退休的灯光师。
景乐宁化好妆,望一眼镜子里,有些意外。
美,真是美。
这美和她卸了妆时被人夸赞的漂亮并不同。
景乐宁的爷爷年轻时是文艺团里的音乐总指挥,又娶了个钢琴家的妻子。
景父继承父业,广播学院毕业后走上了第二代电视人的开拓路。
景家三代,到了景乐宁,真是长得标致无双。
换上小洋装,坐在舞台一边,几乎夺去镜头的所有光彩。
拍完一条后,谷柯没作声。
景乐宁有些无措地坐在凳上,双手紧抓着裙子,抓得几乎出了褶皱。
他似乎这才回过神,从镜头后歪出头:
“放松。
” 他们拍的这部电影,叫《1976往事》,剧本很简单,甚至不像一个被那么多人称赞过才华卓尔的年轻人会写的本子。
七十年代初生长于中国南方的宁波籍姑娘覃丹眉,无意中考入文工团,1978年来到北京成为报幕员,从此走上人生命运的巨大拐角口。
谷柯拍戏很奇怪,只写了一半剧本便筹备开拍。
而关于女主角覃丹眉的命运,却丝毫不提。
这天拍完后景乐宁穿上羽绒衣正要回去,无意中瞥见这人懒懒地靠在车边,借着半打开的车门,躲在阴影中点烟。
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擦着火柴。
那一点星微的光芒,燃起她的好奇。
“你用火柴点烟?
” 他听见声音,抬起眼,看了她一眼。
景乐宁才下戏,还没赶得及卸妆呢,那辫子也还梳着,和2001年的明媚时尚完全不同。
他于是吸一口烟,夹着浅淡的烟草清香开口:
“要么?
” 她是向来的荤素不忌,伸手就接过:
“好啊。
” 他于是又擦了一支火柴,笼在手指间,替她点燃。
景乐宁抽了一口,没反应过来,抽第二口时才呛得不行。
倚在车门边的谷柯看着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懒懒的,眉角眼梢都写着疏淡。
可是距离却近了:
“女孩儿抽烟不好。
” “我妈说的。
” 原来是谷夫人的教诲。
景乐宁不愿反驳,又问:
“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抽烟的姑娘?
” “怎么那么说?
” “覃丹眉就从来不抽烟。
” 03 后来景乐宁告诉谷柯:
“这是我拍的第一部作品。
我觉得和人物的距离很远,碰不着,摸不到。
我没想到第一部作品拍的就是年代剧,我回不了那个时代。
” 1976年是什么概念,改革开放尚未开始。
岁月是陈旧的,拘谨的,带一点慌张。
说这话时,景乐宁喝了点酒,一个人坐在散尽人群的片场。
空荡荡的舞台,孤伶伶的灯光,她像个小姑娘似的,抱着瓶二锅头。
看上去有一点市井气,又很可爱。
收拾完东西的谷柯是最后一个离开片场的人,也是唯一发现她躲在幕后的人。
他抢过她手里的酒时,景乐宁送他一记白眼。
他的口气轻描淡写:
“小姑娘喝这个掉价。
” 可是很快地,他自己也喝了起来。
景乐宁嘲笑地望了他一眼:
“噢,谷少爷也喝这个。
” “正儿八经叫我名字不成吗?
”他皱眉。
“导演,我演不下去了。
” “正常,我也快拍不下去了。
” “谁叫你连剧本也没写完!
” “我写不了,写到那里就难过得不行。
” 她怔住:
“覃丹眉是谁啊?
” “一个很早就过世的女人。
” “她……真有剧本里写的那么美?
” 他笑了,那笑容有些怅怅:
“很美。
”顿了顿,补上一句,“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美。
” “那么美的人,我为什么从没听过?
” “因为她后来嫁人了。
” 她有些呆呆地看着他。
他想了想:
“是来北京当报幕员的第三年。
” 她怔怔了两三秒,才问:
“嫁了人就不工作了吗?
” “她的夫家特殊,不允许她再抛头露面。
” “那她后来干什么去了?
” “生孩子。
” “可笑!
”她是新时代的女孩子,从小信奉女权,很难相信一个女人的价值就是为了生孩子。
“可笑吗?
”谷柯望着她义愤填膺的神情,笑了一笑。
那笑容很淡,淡得像阳光下的风,是透明的。
“1976年一直是她人生最曲折的一年。
那一年,她就好像站在命运的巨大峡谷前,有两条通往前方的路,一条是平坦开阔的木道,一条是颤抖着的孤索。
前方都不可知晓。
因为爱上一个人,她选了那条孤索。
” “然后——走向了荣贵巅峰的极限,直到孤独将她活生生地折磨死。
” 04 一九七六的北京,远没有二十五年后的灯红酒绿。
那时的天,却远比现在的蓝。
覃丹眉是从宁波老家坐着一路北上的火车来到北京的,在接到调令前她刚回过一趟老家。
家里她最大,底下两个弟弟,三个妹妹。
一家六个孩子,大姐也才二十出头的年纪。
覃丹眉那时的对象是景岚。
认识景岚,得从认识景澜澜说起。
那个年代的社会上下阶层流动性很大,多少高知世家的子女都听从国家的大指挥,走向基层的四面八方。
景澜澜生得漂亮,嘴刁,凭着这两个得罪了团里不知多少人。
覃丹眉的性子最好,又和她同住一个宿舍。
日子久了,两人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那会儿她和景澜澜同赴外演出,碰上正在那的景岚来看妹妹。
景岚对覃丹眉一见钟情,他生得谦谦君子模样,又出身音乐世家,才华非凡,给覃丹眉的信几乎每月不断。
旁人皆是艳羡,一旁的景澜澜又撺掇着。
日子久了,稀里糊涂地,她和景岚就谈了对象。
半年后景岚写信给家里,说自己已有心上人。
回北京的景澜澜又成日给父母吹耳边风,一来二去,景父趁着人员调动之际,心念一动,索性将这半个准儿媳调来了北京。
覃丹眉初到北京之际,连周末吃饭也是到景家。
身旁人都晓得她是景家的准儿媳,打趣时偶尔也会说起,哎,你们家那个景岚。
覃丹眉脸皮薄,可是柔中藏韧,是个性子倔,却又夹着一丝怯生生的美人。
多少年后,当那场巨大的悲剧终已死亡收场,站在灵堂祭奠着逝去美人的人们偶尔也会吃惊这个一向柔美动人的女子最后的疯狂。
多少人的记忆里,当年她报完幕,也不下台,就往舞台边那么一坐。
水盈盈也似的眸子,噙着笑,大辫子搭在胸前,很是动人。
时间一长,也没人叫她“那个景家的准媳妇”了,谈起她都说“那个报幕的覃丹眉”。
景澜澜几次听人惊叹后,心里很是得意。
此后见了她也不叫丹眉,直呼嫂子。
那时,覃丹眉自己也以为,这一辈子是一定要嫁与景岚的,就是为着报恩,也要嫁给他。
05 故事的转折点在一个谷正扬的人的出现。
起初,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每次报完幕都能看见他目不转睛地坐在台下盯着自己。
她被盯得脸红,忍不住偷看他一眼。
他却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
渐渐地,她先忍不住,下了台拦住他的路:
“你……你往后别再这么看我了。
”他吊儿郎当地一笑:
“哦,舞台是你家开的?
” 她涨得满脸通红,他倒是难得讲理:
“行,不看就不看。
” “你看着……我说话别扭。
” “我只是觉得全世界也比不上你吸引我的眼睛。
” 她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他。
而夕阳中他的眉眼却是出奇的清秀温柔。
“你好,谷正扬。
”他笑着伸出手。
覃丹眉只觉这名字隐隐耳熟,像是在哪听过,可是仔细一想,却又无从想起。
有些不安地伸出手,她说:
“你好,我是覃丹眉。
” 后来有人回忆起一九七七年的覃丹眉,不禁一声叹气。
“这也怪不得她,你们知道那时小谷公子是怎么追的她,开着车满城地招摇。
她不答应,他就敢在宿舍楼底喊一夜她的名字。
淋了雨,生了病,在病床装可怜,唬得她去看了他,又一把捉住人的手不放。
其实这小谷公子生得好,家世也好,要什么女人没有,真是吃定了她。
” 发帖人的IP追踪在美国加州。
有人在底下跟帖:
“妹妹,你知道的可真多呀。
” 那人倒是给逗得笑了,又补上一句:
“小丫头,你叫我阿姨还不够份呢。
” 景乐宁也曾对这个名字好奇过,问起自己的姑姑景澜澜。
彼时景澜澜已是资历颇深的制片人,听到这三个字,讳莫如深地瞧她一眼:
“谁和你说的这个人?
” 景乐宁把事情一股脑推到好友阳芬芬头上,只说:
“偶尔聊起,才想起这么一遭。
也就是白问问,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当事人也不知是真是假。
” 景澜澜松一口气,点上一支烟:
“人是真的,事也是真的,那会儿闹得人尽皆知。
” 再问下去,便是紧咬牙关,半点不透露。
其实这些人说的都是真的。
可这些人说的,却又都如同隔雾看花,朦朦胧胧的,说不清。
往事的真相,早已如微小的尘埃,被当事人埋进了心底。
埋得那样深,如同从不曾发生过。
06 后来人人都说她贪图荣华,抛弃了真爱,一心嫁与权贵。
景家父母面上不好发作,只是客客气气地对她说:
“丹眉,我们是清清白白的人家,虽说没大出息,待人却都是真心。
” 丹眉请求他们的原谅,却被轰出门去。
景澜澜冷笑:
“飞鸟尽,良弓藏,我算是看透了你。
”站在一旁的景岚什么也不说,眼底写满失望。
陪她一同前来的谷正扬听不下去了:
“说什么呢这是!
” “没有我哥,你也认识不了她。
”景澜澜看了一眼这人,微笑,“你能给她什么?
别拍着胸脯说婚姻。
婚姻才是苦难的开始,覃丹眉。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
” 谷正扬沉下了脸,覃丹眉却轻轻地握住他的手:
“走吧。
” 他手腕上那道自杀未成的伤疤仍在,与周围的皮肤相比,略显凹凸不平。
覃丹眉忽然半个月前的那一幕。
“你说再多的喜欢又有什么用?
有一样东西,你永远也给不了我。
” “你要什么?
” “婚姻。
” 她终于提出了那个时代最严肃也现实的问题。
彼时谷正扬这样能说会道的人,却渐渐支吾。
他的婚姻确实由不得自己做主,虽然,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最受宠爱的小辈。
那时她只是释然一笑:
“把这一切当做一场梦吧,你遇见我,是在梦里。
梦醒了,我是景岚的未婚妻,我们形同陌路。
” 谁知第二天却传出他割腕自杀的消息。
谷夫人亲自来宿舍找她,见了面,也只说一句话:
“去看看正扬吧,从小到大都不生病的人,为着你,一次躺在病床烧了三天三夜,一次险些送了命。
” 她被逼到了绝路,再也不能往回看。
结婚的前一个晚上,他陪她看《鸽子号》,16岁的美国青年罗宾独自驾驶鸽子号环游世界一周,只有船上陪伴的只有一只猫。
罗宾中途邂逅的19岁女友佩蒂,沿途遥遥追随,直至壮举完成。
最后两人见了面,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上。
等不及船靠岸,跳下海就拥抱在了一起。
覃丹眉屏住息,看得很认真。
她认真地盯着屏幕时,眼睛总是睁得很大,带着一点小姑娘的天真和稚气,让人心头一软。
谷正扬想也没想地就飞快地亲了一下。
覃丹眉转过头,死死地盯着他,没有骂出声,也没有抗拒,紧咬的嘴唇颤抖着:
“明天就要结婚了,我这是做梦吗?
”“不是做梦。
”谷正扬抱住她,身子贴得很近:
“我站在船上,你站在岸边。
咱们俩到不了一起,那就索性跳海去。
” 07 “后来呢?
” 景乐宁认真地托着腮地听他的故事。
“后来啊——”谷柯漫不经心地瞥她一眼,枕着手靠在草地上,“后来的剧本没写。
” “啊呸!
”景乐宁简直想啐他一口。
谷柯的神色很是受伤:
“平常挺文静的一小姑娘,怎么混熟了就这么皮实?
” “你才皮实呢。
”景乐宁想了想,说,“我是校花。
” “什么?
”他侧起耳朵听。
“我是校花!
” 谷柯听得笑了。
景乐宁也急了:
“真的,你问问我们高中的同学去。
” “不好意思,我在国外长大。
”谷柯忍住笑,一本正经地坐起身,抬起挂在脖子上的相机,一脸认真:
“来,校花,给你拍张照。
” 景乐宁向来大大方方,这时也就十分自然地说了声:
“好啊。
”说着,一锊头发,拉起两边的脸颊,意想不到地扮了个丑脸。
谷柯飞快地按下快门。
“真拍啊你!
” “留着纪念。
”他头也不抬地看着相片,然后一直没出声。
景乐宁起先还觉得奇怪呢,一推他,才发现他全身抖着忍住笑。
“拍成什么样了啊?
”她忍不住有些忐忑,想抢过相机,他却不给。
景乐宁翻身而起,一下子扑倒在他面前,垂下的长发软软地铺满了草地:
“给不给!
” “小姑娘这样,有失雅观。
”他提醒。
景乐宁秀气的眉头都快拧成一个川字了:
“姑娘就是姑娘,加什么小字。
” 两人正厮缠着,几米远外的草坪上走来一群人,都沉默地围观着他俩。
景乐宁满脸通红地从他身上坐起来,拍了拍沾在裙上的细草。
阳芬芬从那群人中站出身,打量了一眼景乐宁涨红的脸蛋,又看了看衣冠不整的谷柯:
“你们……” “我——”景乐宁正要说什么。
从阳芬芬身后站出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在阳光中腼腆一笑:
“乐宁。
” 景乐宁有些惊奇地咦了一声:
“是你,孟晓骏?
” 孟晓骏一米八二的个子,又是以国家运动员的身份保送进的南开大学,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阳光的气息:
“是我,我来看看阳芬芬她们……和你。
” 傻子也知道他这话里的暧昧情动。
这群来找景乐宁的都是老同学,除了阳芬芬,一个个脸上带着“嘘”似的笑意,心照不宣。
景乐宁头发上还沾着草呢,孟骁俊索性走上前: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毛毛躁躁的。
”说着,替她把头发上的草屑一点点摘去。
景乐宁总觉得在大庭广众下被人这样细心照顾有些怪不好意思的。
可是孟晓骏不许她动:
“长高了,踮起脚都快到我下巴了。
” “真的啊?
”景乐宁一乐,又笑了。
阳光下她的嘴巴大大地咧开,笑得很是没心没肺。
而枕手躺在草地上一直沉默着看着这出闹剧的谷柯,微垂的眼睛却忽然眯起。
08 孟晓骏说,自己从南开申请到了清华交流一年。
景乐宁很大方地请他吃了一顿地道的烧烤。
孟晓骏的父母都是医生,从小在家里吃饭,连咸淡也控制均匀,所以对于景乐宁动辄在路边摊流连的行为十分不解。
可是景乐宁吃得很高兴:
“高中毕业那会儿,我跟着我姑姑去青海拍纪录片,青海的羊肉串分量真足啊。
我一高兴,就吃了许多串,还喝了一大碗酸奶。
到后来撑得只能躺在宾馆的床上直哼哼。
” 孟晓骏听得一笑。
景乐宁被笑得不好意思了:
“我是不是特别没有女孩子的样子?
” 孟骁俊摸了摸她的头:
“你就是个小丫头片子。
” 啊呸,又和那个谷柯说一样的话!
景乐宁郁闷地叹了口气:
“我姑姑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她从小就崇尚西方的女权主义。
”孟晓骏是她高中三年的同桌,知道她的父母工作很忙,从小是跟着姑姑大的,就像景澜澜的一只甩不掉的小尾巴。
可见景澜澜对她的影响之深。
两人吃饭归来,遇上正拎着一袋水果从夜市回去的阳芬芬。
阳芬芬看了一眼孟晓骏,又看了一眼笑嘻嘻的景乐宁,很淡地笑了一笑。
孟晓骏说:
“阳芬芬,谢谢你一直照顾乐宁。
” 阳芬芬笑了,那笑容很特别:
“她不仅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呢,这儿轮得着你说谢谢么?
”顿了顿,“再说,你以什么名义说谢谢呢?
” 孟晓骏的神色黯淡。
回了宿舍景乐宁坐在床上很认真地啃着一只苹果,看着阳芬芬洗完裙子晾晒上架,忽然开口:
“芬芬,你是不是怪我这阵子冷落了你?
” 阳芬芬把一堆衣服放在水龙头底下冲得哗哗直响:
“没有啊。
” “来,我送你一样好东西。
”她从床上跳起,三步并作两步地趴在她肩头。
阳芬芬双手都是泡沫:
“什么啊?
” “看,这个——”她卖关子似地从背后掏出一张票。
阳芬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试镜通知?
” “对啊,我姑姑刚投的一部片,据说要拍六十集。
” 阳芬芬的表情在听到“姑姑”两字时,很快地黯了一下。
景乐宁没察觉,晃着票:
“你不要?
” “要!
为什么不要!
”一把抢过通知,她笑了。
09 从这天起,阳芬芬每天起得格外早。
不为别的,就是练一练基本功。
景乐宁是天生的美人,她不是。
景乐宁的家世在圈中人尽皆知,她也没有。
除了手里攥紧的这一张试镜通知,阳芬芬不知道自己还拥有什么。
只有努力,拼命地努力,才能让她少一点不安全感。
到了面试那天,景乐宁还躺床上睡觉呢,阳芬芬轻手轻脚地洗漱完,说:
“乐宁,我去试镜了。
” 景乐宁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加油。
” 她睡到日晒三竿才起来,正在阳台上刷着牙,楼下忽然有人喊:
“景乐宁,有人找你。
” 孟晓骏单脚立住自行车,一手遮住浓烈的朝阳,笑得帅气无比。
她很快地跑下楼,嘴边的牙膏沫都忘了抹,瞪着他:
“你怎么来了?
”孟晓骏说:
“带你去登山。
”她这才想起不久前自己说想要登山。
夏末初秋,枫叶未红,其实这时候登山并没有什么好看的。
因此一群登山的小姑娘们,眼睛都尽往孟晓骏身上瞟了。
孟晓骏倒是对大家都一样的客气,只有在景乐宁累得满头汗时,才会从包里拿出早就带的酸奶,替她撕开包装:
“给。
” 景乐宁觉得很开心:
“你还记着啊。
” 孟晓骏说:
“高中三年,托景大小姐你的福,我带酸奶都快成习惯了。
” 白给的酸奶干嘛不喝,因此她很快咕嘟咕嘟地喝了干净。
一群小姑娘们都往别处看大雁去了,只有他们俩还坐在山顶的石头上。
从山上往下望,青红不一的林木,好似一副尚未完成的宏阔油画。
她转过头,忘记了想要对孟晓骏说什么,孟晓骏忽然伸出手,喃喃:
“怎么又沾脸上了。
”一点点揩去她唇角的奶沫,他忽然伸手托住她的后脑勺,闭上眼就吻了过去。
砰!
景乐宁把他狠狠地一把推倒在地。
“乐宁……”他似有吃惊。
景乐宁的心却砰砰得跳的厉害,有点恶心,也许还有点别的什么。
“孟晓骏,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 “我喜欢你。
”孟晓骏坦白心扉。
“可是!
”景乐宁深吸一口气,“我不喜欢你。
” 她转身匆匆跑下了山林,却在半途崴了脚。
跌倒在地,正觉痛无可抑时,一只手忽然向她伸来。
没好气地拍掉那只手,景乐宁白他一眼:
“少来假惺惺!
” “你吃火药了吗,景乐宁?
” 那人扛着顶相机,懒洋洋地瞥着她。
景乐宁抬起头:
“谷……谷柯!
” “崴脚了?
”他蹲下身,主动察看起她的伤势。
景乐宁并不是娇气的女孩子,可经不住他用力一握,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你轻点。
” “活该。
”他轻描淡写:
“急匆匆跑下山,后头有鬼追你吗?
” 正说着,那个“鬼”就追了过来。
“乐宁……”孟晓骏欲言又止。
谷柯看了一眼他,又看了一眼扭过头的景乐宁:
“还能走吗?
” 景乐宁摇摇头。
谷柯把相机往地上一撂,轻手轻脚地扶起她,背在了背上:
“坐稳。
” 很快地,不远处有一个高大的保安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谷柯对那人说:
“把相机送到学校传达室门口,一会儿我去拿。
” “那谷先生……” 谷柯的表情似有嘲讽:
“想和他吃饭的人多着呢,何必我陪?
” 那人转过山头把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了负手看山的老者。
五十七岁的谷正扬看上去神色疲惫,盯着茫茫山野里那个背着女孩下山的身影,沉吟片刻,才开口:
“那个女孩儿是他什么人?
” “听口气,大概是认识的同学。
” “同学?
”谷正扬喃喃着。
“对了,听名字像叫……叫景乐宁。
” 10 他背着她一路下山,到了离学校最近的一个小诊所,上了药消肿后,才扶着一瘸一拐的她回去。
这时天色已黑,四周的明灯也渐渐亮起。
景乐宁走了一小会,忽然蹲在了地上。
谷柯问:
“怎么了?
” “疼。
” 他于是眉头也没皱一下地将她抱起。
景乐宁是真吓坏了,挣扎着就要从他的怀里跳下来,可是从小锻炼长大的谷柯结实得很。
“你这样别人会误会的!
”她哭丧着脸。
果然,不一会儿,校园中陆陆续续有人朝他们看来。
谷柯忽然问她:
“你害怕别人误会么?
” 她抛给他一记白眼:
“当然!
” 听了这话的他不知为什么,唇角微微上扬。
下一秒,他低声喊出她的名字:
“景乐宁。
” “嗯?
” “别动。
” 初吻是什么感觉?
心跳得快要爆炸开是什么速度?
当那人的唇印在自己的额上时,自己空白一片的大脑曾跳出什么?
这些她通通都不记得了。
很久以后当景乐宁想起这一刻时,只记得宿舍楼亮着好多盏灯,每一个窗口都有人探出头来观望。
有人尖叫,有人吹口哨,有人拿出相机狂拍……也有人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王子和公主身后,僵硬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乐宁?
” “阳……阳芬芬。
” 抱着她的谷柯终于肯弯下身,慢慢地放下她,转过头对着谈不上认识的女孩开口:
“她的脚崴了,登山时受的伤,几天内都不能走长路。
”顿了顿,语气似乎有些艰涩,“那么……就拜托你了。
” 等阳芬芬扶她上了寝室,她才想起问:
“你怎么也这时候回来?
” “哦,我去试镜了,你忘了吗?
” 景乐宁忙问:
“试镜的结果怎么样?
” 阳芬芬顿了顿:
“还行。
”伸手握住她的脚踝,轻轻地拿冷毛巾敷上,“怎么样,还疼吗?
” “不疼了。
”她长嘘一口气,“这几天可怎么落地?
” 夏天的夜里蚊子很多,阳芬芬蹲在地上漫不经心地点着一盘蚊香:
“那就在床上好好休息呗。
” 爬了一天的山,她只觉累极,很快就入了睡。
渐渐地……梦里的感觉越来越窒息。
半夜时景乐宁被一阵闷热逼醒,才睁开眼,却发现宿舍有点点火光。
她吓得推了一把下铺的阳芬芬:
“芬芬,怎么了?
” 阳芬芬睡得沉,扑通一声忽然倒在地上。
那小火顺着蚊帐一直往上烧着,很快成了燎原之势。
“啊,火!
” 11 谷柯赶到宿舍楼时,火已经燃得很大。
跑下楼的阳芬芬正不住哆嗦着。
他上前推了她一把:
“景乐宁呢?
” “不知道……我不知道……”阳芬芬抱住胳膊。
一旁被她电话叫来的在附近宾馆过夜的孟晓骏也是一脸着急。
消防队眼看还未到,女生宿舍楼不断有人跑下来。
谷柯的眼睛在人群中寻找着,这不是她,那也不是她……茫茫人海中似乎再看不见那个丫头片子。
他接过一人手中抱下挡火的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