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彤朴素的特级教师.docx
《邓彤朴素的特级教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邓彤朴素的特级教师.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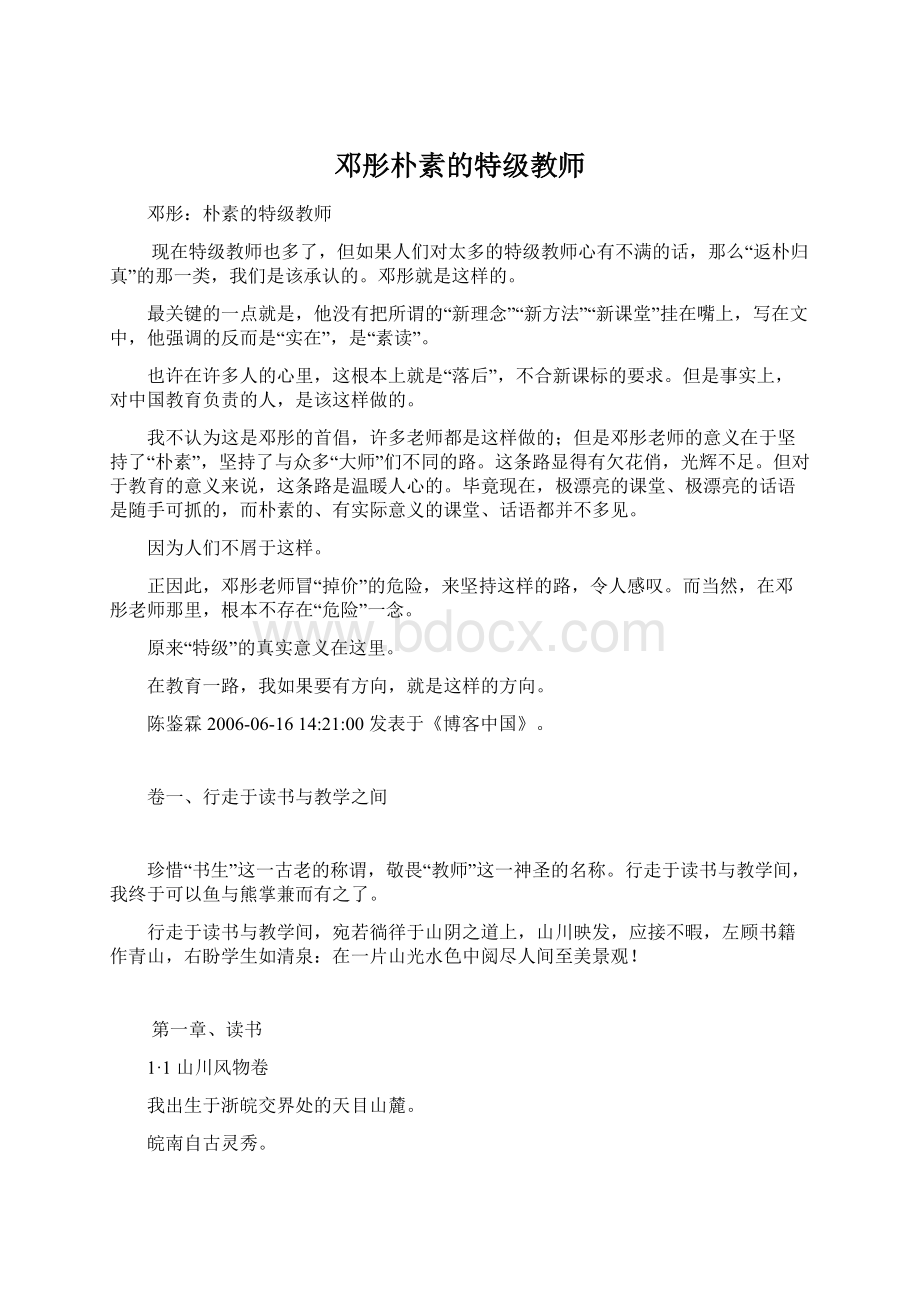
邓彤朴素的特级教师
邓彤:
朴素的特级教师
现在特级教师也多了,但如果人们对太多的特级教师心有不满的话,那么“返朴归真”的那一类,我们是该承认的。
邓彤就是这样的。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没有把所谓的“新理念”“新方法”“新课堂”挂在嘴上,写在文中,他强调的反而是“实在”,是“素读”。
也许在许多人的心里,这根本上就是“落后”,不合新课标的要求。
但是事实上,对中国教育负责的人,是该这样做的。
我不认为这是邓彤的首倡,许多老师都是这样做的;但是邓彤老师的意义在于坚持了“朴素”,坚持了与众多“大师”们不同的路。
这条路显得有欠花俏,光辉不足。
但对于教育的意义来说,这条路是温暖人心的。
毕竟现在,极漂亮的课堂、极漂亮的话语是随手可抓的,而朴素的、有实际意义的课堂、话语都并不多见。
因为人们不屑于这样。
正因此,邓彤老师冒“掉价”的危险,来坚持这样的路,令人感叹。
而当然,在邓彤老师那里,根本不存在“危险”一念。
原来“特级”的真实意义在这里。
在教育一路,我如果要有方向,就是这样的方向。
陈鉴霖2006-06-1614:
21:
00发表于《博客中国》。
卷一、行走于读书与教学之间
珍惜“书生”这一古老的称谓,敬畏“教师”这一神圣的名称。
行走于读书与教学间,我终于可以鱼与熊掌兼而有之了。
行走于读书与教学间,宛若徜徉于山阴之道上,山川映发,应接不暇,左顾书籍作青山,右盼学生如清泉:
在一片山光水色中阅尽人间至美景观!
第一章、读书
1·1山川风物卷
我出生于浙皖交界处的天目山麓。
皖南自古灵秀。
当年,语言大师赵元任与夫人造访胡适故乡皖南绩溪时,曾惊叹胡博士何得异缘生此福地。
并由衷叹服:
现在才知道胡博士何以成为胡博士。
我的故乡便与绩溪紧邻,同秉皖南山川之灵气。
皖南的山川风物,便是我幼年饱览的第一卷书。
清晨,霞光初显,峰峦云雾缭绕,山谷鸟鸣啁啾;黄昏,满目夕照,人家炊烟袅袅,山涧溪水潺源。
春日,叶嫩花初放,秋日,山山黄叶飞;最喜在冬季,大雪封山,四野寂寂,惟余雪落林梢扑簌之声……此外,烂漫的山花,扶疏的竹林,或红或黄的山果,雨后妩媚的青山……一一鲜活在我心深处,摇曳出一片片动人的风景。
如此山川,养育了我唯美的心灵,培养了我易感的习性。
如今,我每读古典诗词,那春花秋水、云烟雨露等传统意象,总使我产生如见故人之感;我每品水墨古画,那山野情趣、冲淡恬然的极为中国化的趣味,总是能够与我心中某一根情弦相互应和。
后来,我读李白《清溪行》诗“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我读鲁迅《好的故事》“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忽然间便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战栗和喜悦——诗文中的一切都似曾相识,都在字里行间撩拨着我,抚慰着我,我内心深处的最柔软最敏感之处被触动了,彼时,便有一种奇怪的哭泣的冲动。
我忽然发觉,原来文字竟然可以如此神奇,竟然可以传达如此美妙的感受。
后来,我向学生介绍读杜甫《北征》诗,对其中“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
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几句赞叹不已,而学生却默然无所动。
我知道,学生们的经验中缺乏这种深山野果罗生的图式,因而无法对此产生共鸣。
后来,我读契诃夫,书中人物的一句话令我感慨不已:
只要人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鸫鸟南飞,瞧着它们在明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
我,生于泉林、长于山野,自然清新的风总是在我心深处不停地吹拂,那种经历早已深深印入了我的灵魂。
这自然的纯美,从此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使我无论经过怎样的世风习俗的漂洗,也无法褪去内心最根本的色彩。
这些幼时便浃肌沦髓渗入心灵的纯正而本色的趣味使我后来可以轻易地区分出文与野、妍与媸,能够准确地品出境界的高下优劣。
这就是生物学中所谓的“印刻效应”吧——生命之初的印记对人生的影响注定是是永久而深远的。
幼年生活为我的将来埋下了一粒种子。
祖上几代农民,并非书香门第,但自小学起就对语文有着奇妙的爱好,对于由文字绘成的优美的境界我往往能够心领神会并心向往之。
我后来毫不犹豫地选择“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职业和事业,大概与我自小生活于秀美的皖南不无关系吧。
所以,在今日,对于脱离生活、摈弃个人体验的语文学习与教学,我总是不以为然的。
语文,是沟通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桥梁。
语文学习的第一步应该是积累起对世界鲜活的感受和体验,应该设法在大脑中刻下丰富的关于世界的表象;然后,才可以设法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
语言的学习,固然能够进一步深化、细化、美化我们的心灵,但毕竟依赖于大脑积累起的丰富的关于世界的表象。
脱离生活的语文教育是低效的、病态的、违背学习规律的。
所以,我后来的教学便始终关注学生的生活积累,努力营造适宜学生发展的教育生态环境!
我不由想到:
“地灵人杰”、“钟灵毓秀”等古语其实早已解释了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巨大作用。
物质的贫困并不会对人们的精神造成什么伤害,而环境的窳败很可能会从根本上降低人们的精神境界!
那么,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也许就不止是人类生存的需求也是人类精神发展的先决条件了。
1·2读书闽南
我常为自己少年的诸多机缘而庆幸不已。
在朦胧阶段,我得以生活于最自然、最生动的环境中;在读书时代,我居然又够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当时一般少年注定难以企及的巨大的“书库”!
时值70年代初,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个的“冰川期”,我却有机会饱览“群书”。
那时,我跟随身为军人的父亲走到闽南山区——福建省大田县。
这是一个位于福建中南部的山区县。
那也是一个群山环抱古木荫荫的所在,至今还记得随处可见的自在地散落于道路与错落旁的几人合抱的古老樟树以及极为淳朴的驻地附近的居民。
在那里,福州军区炮兵部队留守处为安置随军家属建造了一座造纸厂。
在造纸厂巨大的原料库里,堆放着无数废旧图书——大都是“文革”期间被视为“禁书”的各类书籍——出于政治考虑,这些书籍全部被运送到部队造纸厂化为纸浆销毁掉。
这巨大的资源,让我们那群成天无所事事的孩子欣喜若狂。
我开始整天泡在仓库里“淘书”。
但是,现在想来,令我至今还感到遗憾不已的是:
那时的我只知道选择“小人书”、“故事书”、“打仗书”,或者图文并茂的一些科普读物!
而当时数不清的外文书、线装书、“外国书”(我们把那些有着长长外国人译名的书籍统称为外国书)则一概不予理睬。
尽管如此,我还是比我当时的同学们有了更多的读书机会。
到了小学四年级,我便开始在作文中显示了广泛阅读的威力。
学校举办作文比赛,为给同学帮忙,我一人要写好几篇文章而且都能够得奖。
每次考试,我的作文都可以得到最高分。
这一切,都大大激发了我的表现欲和自信心。
于是,读起书来越加投入。
可惜,越是功利往往离本质就越远。
我为了迎合当时的主流思想,开始大读一些今天看来完全是“垃圾读物”的书籍,如:
《大工贼刘少奇》、《安源火炬》、《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的作文中频频出现“解放后,我们摔掉讨饭棍,拿起印把子”之类的铿锵语汇并且为此得意洋洋,自命不凡。
唉!
我就像一个突然掉进宝库的懵懂顽童,面对无数的奇珍异宝却只是随意捡拾了几块漂亮的石子。
那时,没有任何人给我做任何指点。
我至今,我还常常痴痴地想:
如果那时能有一位高人对我略加指点,今天的我会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
我在最爱读书的也是最能够从读书中受益的少年时代有幸得到了一般人难以得到的一次读书机缘,却不幸被我的懵懂无知错失了!
如今的学生,同样有许多书可以读,却没有时间读,也少有人指点他们如何读。
作为教师,我想,自己的一大任务应该是激发学生读书的欲望,指导学生阅读的门径。
当然,这首先取决于教师本人必须是个读书人!
但不管怎样,我在最需要读书的年龄段里还是阅读了大量图书,这丰富了我的知识,开拓了我的视野,至少培养了我对于语言的敏感和喜爱!
在我少年读书经历中,有几本书对我后来影响极大,我称它们为我心灵的启蒙者。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精神启蒙时的情景。
那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
学校是福建省南安县梅山国光学校(分为小学、中学两部)——这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女婿捐资兴建的一所学校:
校舍巍峨,回廊曲折,校园内绿树成荫。
整个学校依山而建——山脚是小学,山顶是中学,千百级石阶和无数回廊将整座校园连为一体。
自小学拾级而上,犹如治学之登堂入室,日日向上。
自小学三年级直到高一我一直就读于此校。
读四年级时,我有幸遇到了一位对我一生影响至为深远的教师——熊老师——很抱歉,我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
熊老师个子不高,胖胖的,脸上始终是微笑,让所有的学生一见之下即有一种亲近感和安全感。
印象最深的是熊老师的“故事会”——那时,我们的教材几近于政治教科书,熊老师有时上完课会给我们读一些故事让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安静一会。
那一课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春末的下午,太阳从长着青苔的高高的窗口斜斜射入教室,熊老师的全身被阳光映照着,仿佛披上一层金光。
此时,她正在给我们读这样的文字:
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
哗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
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
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
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
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
”
…………
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
“呵呵!
”他一手接剑,一手捏着头发,提起眉间尺的头来,对着那热的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
…………
他在暗中向王城扬长地走去,发出尖利的声音唱着歌:
哈哈爱兮爱乎爱乎!
爱青剑兮一个仇人自屠。
夥颐连翩兮多少一夫。
一夫爱青剑兮呜呼不孤。
头换头兮两个仇人自屠。
一夫则无兮爱乎呜呼!
爱乎呜呼兮呜呼阿呼,
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
…………
这篇文章和我从前所读过的任何文章完全不同——那充满神秘诡异之美的语言,那令人惊悸且复神往的奇情异景——让我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向往。
这部“武侠小说”唤起了一个孩子内心深处对奇幻事物的天然的喜好。
我想,熊老师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她在这一番朗读在一个十一二岁孩子内心所引发的震撼!
课后,我立刻追上熊老师并借走了她手中的这本奇书,于是,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本书——鲁迅:
《故事新编》。
我在似懂非懂中囫囵吞枣般地读完了全书。
我读到了滑稽戏一般的《奔月》,匪夷所思的《补天》,但最喜欢的还是如现代荒诞剧的《起死》和《采薇》。
我忽然意识到:
《故事新编》一书中折射出来的鲁迅是一个风趣幽默妙趣横生的人啊,他和我们平素从教科书中认识到的一本正经的鲁迅是如此迥乎不同!
我至今也无法真正估计出这本书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但当我反复翻阅这本小书之后,我意识到原来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种书——它和自己以往所读过的书完全不同——它充满趣味充满活力,它没有什么“政治思想高度”(这是那时我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的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的标准)却充满一种特殊的情味让人爱不释手。
反复读罢这本书,我的阅读趣味和审美标准大概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我不明所以,但我确乎不再如从前那样极为功利地阅读了。
就在这时,一套破旧的古书又出现在我面前。
跟随父亲的部队迁移,在搬家过程中,我忽然在纸箱底发现了这样一套书:
书有三本,均破烂不堪,既无封面也无封底,亦不知书名,字系竖排且是繁体。
由于有了阅读《故事新编》的经验,我不再对这些如同古董的旧书不屑一顾,而是耐下性子读了几页!
这一读,从此一发不可收,从此深陷于其中。
书中奇妙的神话世界令我茶饭不思,我日日捧读,也不知读过多少遍。
半年后,不但对全书烂熟于心,而且几乎完全认识了书中那些繁体字。
但可笑的是,我居然一直不知这部书的书名。
直到后来(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情景了)我才意识到这本书就是《西游记》!
记得有一次写作文,我在文中写到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还用上了“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些当时罕见罕用的词语来描写花木兰,一时被老师视为“神童”,被同学视为语文权威!
其实,“闭月羞花”这些词语本是我从《西游记》中描写妖精的语句中学来的。
当我进入国光初中时,我遇到了一个给我许多鼓励的语文老师。
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姓名——刘国栋(如今,30多年逝去,刘老师已是古稀之人了,愿我师健康长寿),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的模样——他有着一张典型的闽人的脸,瘦而且黑,满脸皱痕,散发出纯朴与厚道。
进入初一的当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招生。
那年高考福建省的作文题是:
将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改写为“陈伊玲的故事”。
我不知道刘老师出于什么考虑,他居然让我们这些刚进入初一的孩子也来写高考作文。
我记不清自己当时是怎样写的,但是作文交上之后,刘老师大加赞叹,立刻给了满分,并且把文章油印出来在各班发放!
我记得非常清楚,初一有16个班,我在第14班。
他甚至在班级宣布:
这样的作文就是参加高考也能够得高分!
进入初中的第一周,我成了初中的名人。
不难想像这样的经历对一个孩子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总之,我在各种合力的推手之下开始了自己第二波的疯狂阅读。
当时,政治虽然尚未解冻,但书籍毕竟比以前更多了;另外,父亲作为部队政工干部,家中毕竟还有一些藏书。
于是我得以读到一些在当时还算有价值的书籍。
印象比较深的有这么几本书:
一是浩然的《西沙儿女》,是一本如散文诗一般的小说,在当时显得很有特色;一是1975年举国上下共读的“反对投降派”的《水浒》,当时未曾读,进入初中后便很认真地读了一遍;还有一本军队总政治部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而编撰的一本辅导读物——其中有许多历史、哲学故事——令我眼界大开。
而那时的语文课本的水平也开始得到显著的提升。
许多经典佳作也被编入教材。
在初一下学期,当我打开刚领到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课本时,我立刻被这样一段文字强烈地震撼了!
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
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
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这是郦道元的《三峡》。
我只记得自己当初读到这一段文字之后,只是一阵阵发呆,我不知道这几句话何以有那么大的魔力,使我内心酸酸麻麻,想哭又想笑,似乎有一种极为美妙的情愫在心头蕴藉。
儿时铭刻在心头的那些山川风物自然而然地在我心头摇曳起来,交织成一片动人的风景。
我再一次陶醉在文字之中了。
如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就能够体会到文字的美妙,那么,他此生将永远保有对文字的敏感。
这种体验其实很多人都有。
美国一位作家克利夫顿·法迪曼在回忆自己早年读书经历时也曾这样感叹过:
十岁到十七岁之间,是我读书最多的时候,那些日子真是令人神往,我相信对于大多数热爱书籍的人,那个年纪也正是人们阅读的最美好的年华。
从那时以后,我再也不曾在一年里读完那么多的书。
十七岁以后,人们一般就不能恣情阅读了,而必须受到某种约束和限制。
一个语文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他应该在学生最适宜读书的阶段中为学生创设条件使学生阅读最有价值的书籍。
这一体会成为我以后语文教学的重要参考。
高中阶段的阅读相对贫乏,但也有值得回忆之处。
其时,我数学成绩始终不够理想,每日晚间主要精力都防在数学之上。
只是在学习之余,会翻出《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随便读上几首。
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78年出版的小册子,三十二开本,如同今日的“口袋书”,这几本书我至今还珍藏着,以为我少年时代读书的见证。
如今,摩挲着泛黄的书页,我感慨良多。
最喜白居易《长恨歌》、李贺《南园》、《梦天》等诗。
而崔护那首著名的《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时,桃花依旧笑春风”,则在我青春期少年的内心泛起层层涟漪。
如今,我所记诵的古典诗词大多积累于那一阶段。
这阶段自然成诵的诗词不过三四十首,居然就是我所积累的整个家底。
奇怪的是,后来我进入了大学中文系,也曾痛下工夫背诵一些古典诗文,但这些东西似乎总是无法像早年积累的诗文那样入耳入心,后来接触的许多诗词于我似乎总是隔了一层。
看来,少年时代的经验是难以替代的。
错过这一阶段,有时就是永远的错过。
所以,在最佳发展期让学生得到最佳的发展是教育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这代人,在少年时期,没有受到任何引导与规范的教育,缺少“童子功”,因此,常觉自己底子不厚,学养不够。
如何在今后教学中使自己的学生不再重蹈覆辙?
这是我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高中阶段受益较大的另一本书就是鲁迅的《野草》。
这本薄薄的小书,是我高中阶段用心最多的课外书。
基于早年读《故事新编》的经验,我开始细心研读《野草》。
不但阅读,还模拟鲁迅文笔,仿写了大量我自己的《野草》。
该书多写梦境,我便一连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梦之一、梦之二,一直到写到梦十四。
依着葫芦好画瓢,一段时间下来,老师竟然在我的作文中写下如此批语——大有鲁迅风味!
这一批语让我暗暗得意了许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高中阶段所涉猎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记得当时只是为了解印证历史教材上的什么知识而在家中书橱里乱翻。
找到《马恩选集》中的这篇文章后,发现阅读起来竟然也颇有趣味——文章序言引述埃斯库斯戏剧《奥列斯特》为例生动传神地介绍了母系时代——克利达妮斯特拉为了情人杀死了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为了替父亲报仇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雅典娜作为神界的裁判官,不追究克利达妮斯特拉却严厉追究奥列斯特。
神的理由令人吃惊: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关系。
”因为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
后来,阿波罗出来做奥列斯特的辩护人,最后,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宣告其无罪。
对此,一位研究者巴霍芬如是说:
《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和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
恩格斯所引述的巴霍芬对这一戏剧底蕴的揭示让我体会到:
思考现象并从中发现规律原来具有这般乐趣。
这种乐趣使我的阅读趣味再一次发生变化。
高考之后,我在所有的高考志愿栏中所填的只是两个专业:
中文、哲学。
1·3我的大学
我最后考入的是中文系。
在大学图书馆里,面对一排排如密林般的书架,我在目瞪口呆之后惟有虔诚地捧读一部部到手的著作。
20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全民崇拜知识的时代。
许多世界名著纷纷出版,那些当年与我擦肩而过的世界名著开始被我虔诚地捧读。
曾记得,一月省吃简用,只为了买得一部《神曲》;四处奔走求告,是为了借得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
那又是一个文学创作繁荣的时代。
谌容《人到中年》所引起的轰动、戴厚英《人啊,人》对社会的撞击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为每一部小说感动、争论,为每一部电影哭泣、呼喊……
后来,神州劲吹“美学风”,我又疯狂地迷上了美学,那时的李泽厚在青年大学生中红得发紫。
于是,我们读《美的历程》、《美学散步》、《中国美学史》、黑格尔《美学》、康德《判断力批判》、苏珊郎格《艺术与视知觉》……从纯文学迅速向纯思辩转化居然没有丝毫的勉强。
那时的读书,用“饿汉扑在面包上”为喻毫不过分。
恨不能一夕读遍天下书,泛泛而读,不求甚解,惟求数量,不计成效。
回忆起来,那时认真咀嚼过的大概只有一本书——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
只需翻翻该书版权页就可以知道这类纯学术性质的书籍在当时的销量完全不亚于今日的所谓畅销书——1963年7月北京第1版,1979年6月第2版,1984年4月北京第11次印刷,印数170,601——194,600。
我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做了如下记录:
1985.3——1985.5阅毕第一遍
1985.5.1——1985.7.21阅毕第二遍
1985.10.1——1985.12.30阅毕第三遍
读这本书,对我是一个挑战,一种考验,这是对自己思维和定力的一次检验。
从此,阅读理论性书籍于我不再是一种折磨,我终于学会怎样突破理论坚硬的外壳从而品尝到思想的琼浆甘露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哲学,我还特地跑到哲学系旁听了一年的“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课程。
这般狂轰滥炸式的读书学习,显然对自己后来的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也许,正因为这几年的阅读,使自己有了一点书卷气,因此,此后的教学生涯才得到许多难得的机缘。
我至今庆幸自己在八十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那是一个多么富于朝气和理想色彩的单纯的时代啊!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的大学四年,基本上是读书的四年,我至今仍然以自己没有虚度这四年而感到庆幸与自豪。
只是,那时我未曾读过一本教育教学方面的书籍。
那时,我们似乎对教育以及教育理论多少有点不屑一顾呢!
第二章、教书
2·1实习
皖南是我生命中的“流奶与蜜之地”,我常怀感恩之情歌颂这片生我养我栽培我的土地。
毕业前夕,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