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docx
《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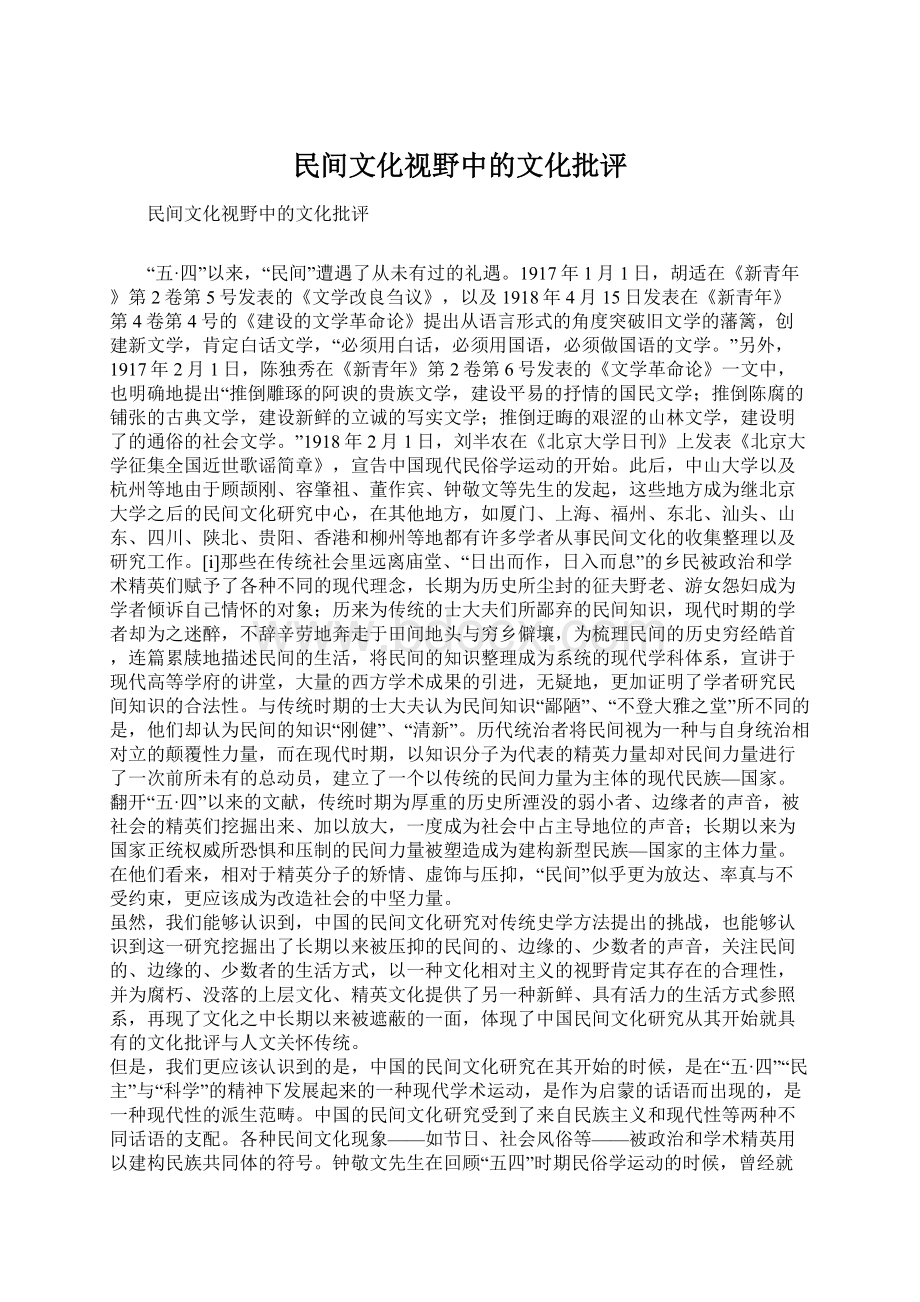
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
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
“五·四”以来,“民间”遭遇了从未有过的礼遇。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1918年4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突破旧文学的藩篱,创建新文学,肯定白话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另外,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也明确地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1918年2月1日,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宣告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开始。
此后,中山大学以及杭州等地由于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先生的发起,这些地方成为继北京大学之后的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在其他地方,如厦门、上海、福州、东北、汕头、山东、四川、陕北、贵阳、香港和柳州等地都有许多学者从事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工作。
[i]那些在传统社会里远离庙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民被政治和学术精英们赋予了各种不同的现代理念,长期为历史所尘封的征夫野老、游女怨妇成为学者倾诉自己情怀的对象;历来为传统的士大夫们所鄙弃的民间知识,现代时期的学者却为之迷醉,不辞辛劳地奔走于田间地头与穷乡僻壤,为梳理民间的历史穷经皓首,连篇累牍地描述民间的生活,将民间的知识整理成为系统的现代学科体系,宣讲于现代高等学府的讲堂,大量的西方学术成果的引进,无疑地,更加证明了学者研究民间知识的合法性。
与传统时期的士大夫认为民间知识“鄙陋”、“不登大雅之堂”所不同的是,他们却认为民间的知识“刚健”、“清新”。
历代统治者将民间视为一种与自身统治相对立的颠覆性力量,而在现代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力量却对民间力量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动员,建立了一个以传统的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
翻开“五·四”以来的文献,传统时期为厚重的历史所湮没的弱小者、边缘者的声音,被社会的精英们挖掘出来、加以放大,一度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长期以来为国家正统权威所恐惧和压制的民间力量被塑造成为建构新型民族—国家的主体力量。
在他们看来,相对于精英分子的矫情、虚饰与压抑,“民间”似乎更为放达、率真与不受约束,更应该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虽然,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对传统史学方法提出的挑战,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研究挖掘出了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民间的、边缘的、少数者的声音,关注民间的、边缘的、少数者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为腐朽、没落的上层文化、精英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新鲜、具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参照系,再现了文化之中长期以来被遮蔽的一面,体现了中国民间文化研究从其开始就具有的文化批评与人文关怀传统。
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的是,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在其开始的时候,是在“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现代学术运动,是作为启蒙的话语而出现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派生范畴。
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受到了来自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等两种不同话语的支配。
各种民间文化现象——如节日、社会风俗等——被政治和学术精英用以建构民族共同体的符号。
钟敬文先生在回顾“五四”时期民俗学运动的时候,曾经就其性质进行过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民俗文化运动可以归纳为民族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他认为,直到今天,民族自尊意识仍然是他从事民俗文化研究的精神支柱。
[ii]现代性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诉诸于进步和解放、历史和精神之辨证法、或者意义与真理的铭刻性等元叙事。
……现代科学就是通过宣称它能够将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够带来真理、财富和进步而使自身合法化。
”[iii]而且,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从西方引进的民俗学理论,由于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与西方19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的民俗研究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iv]而这一研究取向具有浓厚的进化论和殖民主义色彩。
其关于历史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世俗社会文化演进的时间观念的历史变迁,这是19世纪的人类学发展的依据,它事实上是被空间化了的时间观,其所表述的,实为那些距离文明中心最遥远的社会,如何能被认为是属于比较原始或比较早期的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的阶段。
[v]这种理论自身对民间怀抱着一种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原始/进化、乡民/工人、乡村/都市、前文字/文字等二元对立的分析策略,以此来衡定社会文化。
周作人在《歌谣与妇女》一文就歌谣研究的几个方面价值进行过探讨,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一学术取向对于“五四”时期学者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歌谣既是原始文学的遗迹,也是现代民众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从那里去考查余留的蛮风古俗,也可以看出民间儿女的心情,家庭社会的种种情状,风俗调查的资料。
……或是找出吃人妻、兽拜树、迎蛇等荒唐的迹象。
[vi]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这种理论背景,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学者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以及许多学者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采取一种传统士大夫的浪漫情调。
因此,当我们分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态度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政治与学术精英对“民间”却怀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与矛盾。
一方面,政治和学术精英将民间看作是与传统的封建帝国王朝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力量与意识形态,无论是民间的力量还是观念,都可以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性力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因素,或者寄托人生理想的对象;另一方面,“民间”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与学术精英的启蒙对象,在他们看来,“民间”虽然具有与传统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积极力量,但是,他们更多地承载了与现代性不相适应的、未经现代科学、文明洗礼的蒙昧与落后。
我们可以通过周作人发表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6号一篇题为《中国民歌的价值》的文章看看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化研究者对民间文化的态度:
“‘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农夫唱的都是一种‘鹦歌戏’的断片,各种劳动者也是如此;这鹦歌戏本是堕落的农歌,加以扮演的,名称也就是‘秧歌’的转讹:
这一件小事,很可以说明中国许多地方的歌谣,何以没有明了的特别色彩,与思想言语免不了粗鄙的缘故。
”[vii]“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现代化的诉求,在引进西方思想与学术的过程同时,也注意本土文化的生长。
因此,当我们回首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学术发展之脉络的时候,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还是其他的人文学科,都对民间怀有一种深刻的矛盾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是鲁迅对中国国民之劣根性的彻底批判,他的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viii]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
”[ix]与此不同的是,沈从文的小说则展现了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沅水流域一带人民的爱恨情仇,乡俗民风,在他的笔下,湘西独特的生命形式,则代表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x]而在人类学领域,费孝通先生首先将人类学从异文化的研究运用到本土社会的研究之中,1936年初,他在家乡江苏吴江县的开弦弓村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写作博士学位论文PeasantLifeinChina。
半个多世纪之后,1990年7月,他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回顾到,“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
”[xi]
学术精英在吸取民间文化滋养的同时,同样不失时机地对民众的愚昧、落后等劣根性进行批判。
周作人发表在《语丝》第100期的《乡村与道教思想》认为,改良乡村社会的最大阻力是占乡民旧思想主力的道教思想,他还列举了道教思想对乡民的种种恶劣影响,如教案、假皇帝、烧洋学堂、反抗防疫以及统计调查、打拳械斗、炼丹种蛊、符咒治病种种,使乡民相信“命”与“气运”,他指出,解决乡民思想愚昧的方法,有两条路:
或者发展为一神教,或者被科学思想压倒,渐归消灭。
[xii]钱理群指出:
“周作人讲神话、童话、儿歌与迷信,说男人、女人、小儿与原始人,论文学、艺术,爱与性欲,都在追求着同一个目标:
人性的和谐,精神的超越,说到底,是对‘贵族精神’的一种自觉的追求,或者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的,是希望实现‘平民的贵族化’即‘凡人的超人化’。
”[xiii]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精神追求,不仅使他对民间文化的研究停留在书斋里,而且使他对“民众”的劣根性强调得更多,他在民间文化研究中,较少地发现民众的创造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较多的是麻木不仁的劣根。
[xiv]
启蒙的悖论
实际上,“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所具有的深刻的矛盾态度,与传统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态度之间有着一定的继承性。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对于民间的态度多从有利于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所谓“观风俗,知得失”,[xv]作为统治者统治效果的一面镜子;正因为如此,统治者还认识到“移风易俗”对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重要性,荀子便主张“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
”[xvi]统治者还在民间习俗与上层礼制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认为民间习俗可以转化为上层礼制,所谓“礼失求诸野”。
这种对于民间的“重视”态度,更多的是出于统治者的利益考虑,但是,统治者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诸如礼/俗、正/野——把握民间文化与自身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将民间文化看作是非主流的、异端的,无视民间的历史创造。
所以,民间文化很少进入统治者的正史视野,而更多地保存在野史篇章。
如果我们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矛盾态度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可能更能够祛除历史的迷障。
“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使“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在全面否定一切旧的价值观念的同时,非常急切地寻找新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启蒙话语,以此建构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他们希望,对于人生、社会乃至宇宙观的理解能够用一套新的价值观念整合起来,实现社会的转型,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便将这一切寄托于“民主”与“科学”两位从西方引进的“先生”身上。
“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观念,是作为封建蒙昧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面被知识分子引入中国的。
陈独秀认为:
“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xvii]胡适则看到了新思潮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其根本的实质在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因此,对于旧的传统伦理道德、公众不加思考就信之所以然的价值与行为方式,需要重新加以评判:
“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
‘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
‘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要问:
‘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
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
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xviii]
但是,我们发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对于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念的顶礼膜拜。
西方进化论社会思潮的引进,以及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软弱无能的现实,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向往,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化象征着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朝向现代化的标志。
按照这种进化论的逻辑,中西文化的空间对比则被转化成了代表着“新”、“旧”两种不同文明的时间进程的对比。
因此,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意义在于,中国也应该沿着西方现代化的路径,才有可能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走向富国强民的道路。
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已经确立,民族已经作为历史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之中,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个人都已经为民族-国家所塑造。
表面看来,民族主义的民族认同能够充分地发掘民族的文化资源,包括民间文化资源,往往在很多情况下,具有民族认同功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文化符号为民族国家所利用。
实际上,民族-国家塑造的基础是民族历史的重建。
但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基本上采取线性叙事模式,这一线性叙事模式将边缘的、少数的、他者的声音包括进普遍历史的时间,以及置于抽象理性的名义之下,通过在自身范围内对这些声音的盗用和否定,生产了所有的知识。
假如说这种总体的线性历史叙事是一个存在的模式,那么,正是这种叙事模式使现代性成为可能的条件,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在其中作为动力。
因此,在学术与政治精英的眼里,民间固有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同时又与现代性叙事相抵牾,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具有其自身不可避免、难以超越的落后、低劣与愚昧。
政治精英在将政治理念民间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将民众从愚昧、迷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一次次进行移风易俗运动,试图改造民众的思维观念与生活方式,使其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轨道;我们以广西为例,可以看出,历经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诉求,民间固有的传统文化所经历的变革:
“民国时期批判礼教、封建迷信,广西省政府曾于民国10年开征‘巫道捐’、‘冥镪捐’,企图用‘寓禁于征’的办法限制封建迷信;民国25年颁布‘改良风俗规则’,对婚嫁、生寿、丧祭中的奢侈行为及其他陋俗,宣布取缔。
对壮、瑶、苗、侗等族的‘不落夫家’、‘赶歌墟’及服饰等习俗,实行同化政策,强令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颁布宪法和法律,宣布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民族都有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
……对一些落后习俗的改革,尊重当地干部、群众的意愿、待少数民族觉悟后自己作出决定,自己实施改革,不搞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
国家组织文化工作者,大力发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弘扬民族文化,使各民族的优良风俗习惯得到继承发展,一些陋俗逐渐破除。
……生产方面破除陈规旧习,讲究科学技术。
聚居在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改变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习惯。
”[xix]
现代性作为一个“方案”,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人们许诺从匮乏、需求和自然灾害中获得自由,社会组织的合理化以及思想的理性模式许诺我们从神话、宗教、迷信等非理性中获得解脱。
[xx]确实,我们看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以一种“大写历史”[xxi]的方式,将民间的、边缘文化的生存方式置于“大写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逐渐地以现代性的诉求取代民间的历史创造,使民间的历史再次处于湮没的状态。
民间的历史创造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民族国家时期,民间的历史已经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事所完全取代?
在政治与学术精英的现代性诉求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民间的历史创造与记忆又是作为一种怎样的图景存在?
我们应该根据现代性的时空分延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全民过程。
一如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所说:
“在资本主义的晚期,人类学关于异文化的研究被看作是一种赎罪式的‘文化批评’,即以一种道德上值得赞许的分析方式大量使用其他社会的例子来作为改正西方社会最近遇到的任何麻烦的托词。
这好像其他民族是为了西方社会才建构他们的生活的,好像是为了解答西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帝国主义等邪恶才存在的。
”[xxii]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怎么启蒙的论点。
西方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西方支配的叙述,因为在这样的叙述中,非西方的土着人是作为一种新的、没有历史的人民而出现的。
萨林斯还指出:
“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与变迁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着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
”[xxiii]这一反思的态度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化以来的启蒙之启示在于:
民间并不随着现代性的目的论叙事而停滞其自身的历史创造,现代性的总体叙事也无法包含多元的民间历史创造,传统文化、民间文化并不会随着现代性的诉求而丧失其历史的能动性,而总是以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重现出来。
实际上,民间历史与现代性宏大叙事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已经在民间与民族国家之间生产了各自的叙事话语,无论是民间还是民族国家,既在各自的利益之上表述自己,又利用对方的资源来达到自己的表述目的。
在现代中国,现代化和破除“迷信”与“传统”的现代性方案,总是面临着强大的“历史”阻力,“历史”总是如影随形地出现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民间仪式表演之间的相互利用。
许多地方的民间仪式表演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种政府行为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共谋,传统文化已经被重新发明成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有效资源。
民间的诸多庙会与节庆已经基本上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幌子下年复一年堂而皇之地叙述着民间的历史记忆与创造。
而此时的民间仪式远非昔日的面貌,在政府行为与地方精英的默契配合下,民间与政府之间相互利用,政府利用的是民间的文化资源以达到政府的经济目的,所谓“招商引资”,而民间则运用政府的行为达到民族-国家对地方文化的认同,至少是默认。
无论民间采取何种方式,许多民间仪式仍然以传统仪式为表演中心,很难使人们不怀疑庙会具有“封建迷信”的种种因素。
但是,民间却巧妙地运用多种方式使庙会为地方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增加科技与现代文化的宣传内容,将接受的捐款转献给地方的学校,邀请各路学者论证庙会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以一种传统的地缘和亲缘的方式利用地方或家族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充分获得他们的权力与经济支持,以此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
[xxiv]尽管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试图不断地控制民间意识形态,试图以一种主流的方式内化为民众的思维,以达到支配民众行为方式的目的。
但是,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民间的自我认同与民族国家、全球化的转型,表现为一种地方化与整体化的辨证关系。
换言之,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互为表里,民族国家将传统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
另一方面,民间力量的增长需要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之间寻找相应的生存空间,因此,民间力量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叙述策略,以适应民族-国家的生存环境。
民间的历史叙事与记忆主要体现在口头叙事、地方性仪式以及民间的各种地方性文献之中。
对于民众而言,记忆所保存的与它所遗忘的一样多,记忆的制约作用和改进作用同样巨大。
在民族国家处于政治高度控制的背景下,民间的历史叙事和记忆受到了制约和压抑,民间的记忆与历史基本上处于尘封的状态,无论是民间的社会组织还是民间的叙事声音都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建设秩序,整个国家处于高度一统之中。
当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和叙事声音则纷纷浮出历史的地表。
由于各种民间的利益与需求,民族国家以及现代性的诉求在民间化、地方化过程中,民间都将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予以解构,根据民间的需求加以重组。
民间在认同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的总体诉求的同时,同样也具有分散和消解的作用。
另一方面,民间的力量在认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的过程中,它们既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以民间的、地方性视野叙述着历史事件。
因此,在民族国家的总体历史的范围内,民间作为他者并非总是被动地接受总体性的叙事,而是不断地以抵抗的、否定的姿态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在民间口头历史与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的相互作用中,在文化变迁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后的决定因素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聚集起来的趣味和判断。
这些以一个民族对当代历史的创造性记忆里表达出来的各种叙事,总是无数的关注文化变迁的学者与不善言辞的民众合作的产物,总是学者们关于民间的知识与民众结合的成果。
当下流传的各种民谣与民间故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背后支配的是民间意识形态。
在关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民间的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受到民众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判断的支配,对主流意识形态或认同、或消解。
民间的各种叙事实际上表达了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形成之间形成共谋的线性历史的颠覆。
在这一共谋所达成的线性历史的暴政中,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消失了。
当我们关注民间叙事的时候,民族国家的封闭性的历史叙事策略被打破,民间的声音被挖掘出来,让人们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背后,听到了各种被压制的声音。
其实,历史的真实并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表述所遮蔽,历史并没有象杜赞奇所说的出现了分叉,[xxv]分叉的只是受不同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叙事,民族国家的总体历史叙事的企图在民间被消解了。
历史叙述主体生存的不同背景,他们所表述的对历史的理解也具有非常大的差异。
我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是处于文化上层的各种历史叙述主体的声音,而那些更多的沉积在历史底层、一向视为沉默的人们的声音却从来没有被重视。
对于“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叙事中“民间”概念之反思,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批判固有的偏见,目的不仅仅在于批判启蒙思想的霸权对民间文化、地方文化、边缘文化的压制与排斥,更在于倡导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使不同的文化形态在文化世界的秩序中获得各自的生存空间。
我们认为,关注民间的、边缘的或者地方性叙事,既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是关注主流的声音之外的民间的、边缘的、地方性的叙事。
这些在现代性叙事中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文化,并没有因为现代性的压制和排斥而消亡,现代性的同质性与民间文化的差异性同步发展。
实际上,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体系,文化的发展并不因为总体论和目的论的现代性叙事而失去多元化。
而且,就叙事本身而言,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对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可能性和多种表述方式,有些表述可能只是以一种主流的姿态出现,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解释,另外一些则可能是作为主流叙事的对立面而存在。
从事文化批评,则需要学者尽可能地揭示多元性的存在,通过将某一特定文化对象与其他的文化现象的并置,就两者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性研究来隐含作者的文化批评态度,在当下的文化批评中就有可能达成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
人类学与文化批评
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可谓景象纷繁复杂。
文化交流所带来的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奇异的文化景观。
作为批评的话语与实践而存在的文化批评,应该剖析、揭示当下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背景、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学者在从事批评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表面看来,当下的文化批评领域各种理论竞相登台,研究对象漫无边际,众多学者对这一鲜活的领域怀有极大的兴趣。
然而,我们不得不正视研究现状,面临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化批评领域则呈现出一种表述危机。
当下中国的文化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既非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也非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生产,所以无法直接套用西方的文化理论,而中国本土的话语又难以寻找到相关的理论阐释;更由于大众文化的诱惑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操纵,许多文化批评沦落为服务于满足大众的消费主义欲望,失去了文化批评所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学理性以及人文关怀。
具体而言,当下中国的文化批评的表述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浮泛的现象描述取代了全面、深刻的关于社会文本的本质研究。
研究对象的漫无边际,导致文化批评无所不包,呈现出“无边的文化批评”现状,似乎文化批评对所有文化现象皆有一种承诺。
更重要的是,现有的文化批评成果大多局限于对文化现象的表面描述,缺乏对某一具体文化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换言之,当下的文化批评者即便存在对文化现象的描述,但缺乏一种人类学视野的田野作业精神,因此也就无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文化现象描述,给广大的读者提供的则是与诉诸于广泛媒体世界的文化现象没有本质区别的表面描述。
其次,移置式叙述取代了本土文化批评理论的生成与提炼。
中国自称为文化批评的成果基本上沿用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而且比较关注于大众文化领域的批评,固然与大量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批判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有关。
大众文化批评的成长,与中国许多学科的成长有着共同的学术历程,目前基本上尚处于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理论与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之间的嫁接时期。
这些研究成果的根本缺陷与上述第一个表述危机有着深刻的联系,正是由于缺乏全面、深刻的关于社会文本的本质研究,反过来也就导致了无法形成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提升,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