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p van winkle中文版.docx
《rip van winkle中文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rip van winkle中文版.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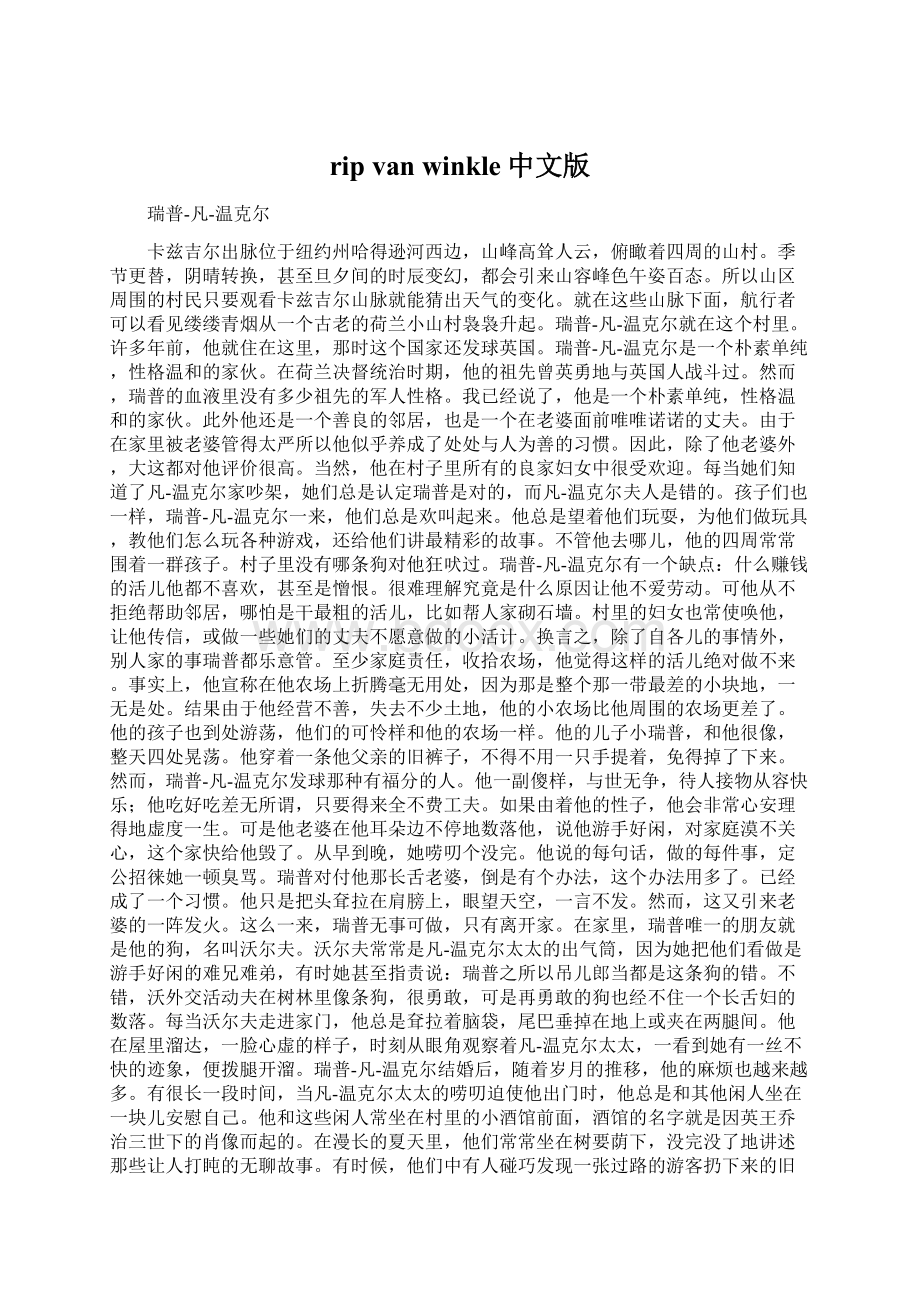
ripvanwinkle中文版
瑞普-凡-温克尔
卡兹吉尔出脉位于纽约州哈得逊河西边,山峰高耸人云,俯瞰着四周的山村。
季节更替,阴晴转换,甚至旦夕间的时辰变幻,都会引来山容峰色午姿百态。
所以山区周围的村民只要观看卡兹吉尔山脉就能猜出天气的变化。
就在这些山脉下面,航行者可以看见缕缕青烟从一个古老的荷兰小山村袅袅升起。
瑞普-凡-温克尔就在这个村里。
许多年前,他就住在这里,那时这个国家还发球英国。
瑞普-凡-温克尔是一个朴素单纯,性格温和的家伙。
在荷兰决督统治时期,他的祖先曾英勇地与英国人战斗过。
然而,瑞普的血液里没有多少祖先的军人性格。
我已经说了,他是一个朴素单纯,性格温和的家伙。
此外他还是一个善良的邻居,也是一个在老婆面前唯唯诺诺的丈夫。
由于在家里被老婆管得太严所以他似乎养成了处处与人为善的习惯。
因此,除了他老婆外,大这都对他评价很高。
当然,他在村子里所有的良家妇女中很受欢迎。
每当她们知道了凡-温克尔家吵架,她们总是认定瑞普是对的,而凡-温克尔夫人是错的。
孩子们也一样,瑞普-凡-温克尔一来,他们总是欢叫起来。
他总是望着他们玩耍,为他们做玩具,教他们怎么玩各种游戏,还给他们讲最精彩的故事。
不管他去哪儿,他的四周常常围着一群孩子。
村子里没有哪条狗对他狂吠过。
瑞普-凡-温克尔有一个缺点:
什么赚钱的活儿他都不喜欢,甚至是憎恨。
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不爱劳动。
可他从不拒绝帮助邻居,哪怕是干最粗的活儿,比如帮人家砌石墙。
村里的妇女也常使唤他,让他传信,或做一些她们的丈夫不愿意做的小活计。
换言之,除了自各儿的事情外,别人家的事瑞普都乐意管。
至少家庭责任,收拾农场,他觉得这样的活儿绝对做不来。
事实上,他宣称在他农场上折腾毫无用处,因为那是整个那一带最差的小块地,一无是处。
结果由于他经营不善,失去不少土地,他的小农场比他周围的农场更差了。
他的孩子也到处游荡,他们的可怜样和他的农场一样。
他的儿子小瑞普,和他很像,整天四处晃荡。
他穿着一条他父亲的旧裤子,不得不用一只手提着,免得掉了下来。
然而,瑞普-凡-温克尔发球那种有福分的人。
他一副傻样,与世无争,待人接物从容快乐;他吃好吃差无所谓,只要得来全不费工夫。
如果由着他的性子,他会非常心安理得地虚度一生。
可是他老婆在他耳朵边不停地数落他,说他游手好闲,对家庭漠不关心,这个家快给他毁了。
从早到晚,她唠叨个没完。
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定公招徕她一顿臭骂。
瑞普对付他那长舌老婆,倒是有个办法,这个办法用多了。
已经成了一个习惯。
他只是把头耷拉在肩膀上,眼望天空,一言不发。
然而,这又引来老婆的一阵发火。
这么一来,瑞普无事可做,只有离开家。
在家里,瑞普唯一的朋友就是他的狗,名叫沃尔夫。
沃尔夫常常是凡-温克尔太太的出气筒,因为她把他们看做是游手好闲的难兄难弟,有时她甚至指责说:
瑞普之所以吊儿郎当都是这条狗的错。
不错,沃外交活动夫在树林里像条狗,很勇敢,可是再勇敢的狗也经不住一个长舌妇的数落。
每当沃尔夫走进家门,他总是耷拉着脑袋,尾巴垂掉在地上或夹在两腿间。
他在屋里溜达,一脸心虚的样子,时刻从眼角观察着凡-温克尔太太,一看到她有一丝不快的迹象,便拨腿开溜。
瑞普-凡-温克尔结婚后,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麻烦也越来越多。
有很长一段时间,当凡-温克尔太太的唠叨迫使他出门时,他总是和其他闲人坐在一块儿安慰自己。
他和这些闲人常坐在村里的小酒馆前面,酒馆的名字就是因英王乔治三世下的肖像而起的。
在漫长的夏天里,他们常常坐在树要荫下,没完没了地讲述那些让人打盹的无聊故事。
有时候,他们中有人碰巧发现一张过路的游客扔下来的旧报纸,这时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听报纸上的内容,因为德瑞克-凡-巴梅尔会读给他们听(德瑞克-凡-巴梅尔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很有学问,词典里最长的词也难不倒他)。
接着他们会露出很有学问的样子讨论几个月前发生的新闻。
众人发表的看法完全由尼古拉斯德维达裁决,他是村里岁数最大的老人,是酒馆的主人。
他从早到晚坐在门口,只有为了避开太阳要蹲在大树树荫下面的时候,他才挪一下位置。
的确,他很少开口讲话,而是不停地抽着烟斗,但是他的崇拜者们最了解他,他们知道怎么才能让他就某个话题发表他的高见。
要是读的什么内容或讲的什么话让他不开心,他就会狠狠地抽着烟斗;要是他高兴起来,他会慢慢而静静地抽烟。
有时候,他从嘴里拿开烟斗,让烟雾在鼻子上方萦绕,点头以示同意大家正在讨论的内容。
可是就连这帮能安慰瑞普的人也最终被迫离开倒霉的瑞普。
他老婆突然破门而入,直接冲着谈笑正欢的俱乐部,将俱乐部的成员骂得一文不值。
甚至了不起的尼古拉斯-维达也难逃这位凶悍的泼妇的一顿肆意辱骂。
她指着他的鼻子责骂说,她丈夫游手好闲他要负主要责任。
可怜的瑞普因此几乎被逼上了绝路。
他唯一能逃避的办法就是拿着猎枪到深山老林去。
在山林里,他有时和他忠实的狗一起坐在树下,沃尔夫是他同病相怜的伙伴。
“可怜的沃尔夫,”他常这么对他说,“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别害怕。
只要我活着,总有一个朋友和你站在一边!
”沃尔夫听罢总是摇摆着尾巴,伤心地望着他的主人。
如果狗能有怜悯之心,我坚信他会真心实意地同情瑞普的。
在某个秋天就这样长时间地漫步后,瑞普发现自己爬到了卡兹吉尔山脉最大的山峰。
他专心于他喜爱的消遣---打猎,枪声划破了山林荒凉的宁静。
他累得气喘吁吁,到了傍晚,便在悬崖上一个长满绿草的小土丘上躺了下来。
有一会儿,他躺在地上观看着山景。
夜色快要降临;君山开始在山谷投下长长的蓝色影子。
他知道他没到村里,天早就黑了;一想到凡-温克尔太太生气的脸,他就深深在叹气。
就在他准备下山时,他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他,“瑞普-凡-温克尔!
瑞普-凡-温克尔!
”他看了看周围,除了一只大鸟孤单地飞越大山外,什么也没看到。
他判断这声音只是他的想象。
他转身准备下山,他又听到那喊叫声在寂静的夜空回荡;“瑞普-凡-温克尔!
”时他的狗感到毛骨悚然,他跑到主人身边,恐怖地望着山谷。
瑞普心里心感到害怕,不安地朝着同一方向看去。
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在岩石上攀登着,背上驮着什么沉甸甸的东西。
瑞普感到惊讶;在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竟然看到有人。
可是一想到可能是哪一个需要帮忙的邻居,瑞普赶紧冲了下去。
他再往前一靠近,陌生人古怪的模样让他更加吃惊了。
他是一个个头矮小的老头,膀大腰粗,头发浓密,还长着一撮灰白色的山羊胡子。
他穿的是以前的荷兰老款式服装---系着腰带的短布外套产层层相叠的裤子。
最外面一层裤子又大又宽,裤脚管两侧镶着几排纽扣。
他肩上扛着一只木桶,里面似乎装满了酒。
他示意瑞普过来帮他卸下肩上的东西。
瑞普虽然不完全信任这个长相古怪的陌生人,但还是走了过去帮他一把。
他们搭手抬着木桶,里面似乎装满了酒。
他示意瑞普过来帮他卸下肩上的东西。
瑞普虽然不完全信任这个长相古怪的陌生人,但还是走了过去帮他一把。
他们搭手抬着木桶,沿着山腰狭窄的溪沟小道向高耸的岩石山峰攀登时,瑞普开始听到一些异常的声音,有点儿像打雷声,似乎是从山峰间狭窄的山谷深渊中传出来的。
他止步听了听,觉得一定是不远处经过的雷暴。
穿过溪沟小道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山洞,山洞像古希腊时期建造的地下剧场。
一路上,瑞普和他的同伴一声不吭地爬着山路,因为瑞普尽管对有人在这荒山野岭竟然扛着装着酒的木桶感到不解,但他缺乏勇气去问这个陌生的新朋友。
走进山洞,只见各种令人惊奇的新鲜玩意儿。
洞里的中央有一小块平地,一帮面貌古怪的人正在玩九木柱游戏。
他们身着非常奇特的服装,有些腰带上还佩着刀,他们大部分都穿着又长双宽的裤子,和瑞普的向导的裤子差不多。
他们的长相也是古里古怪的,其中有一位,满脸似乎就是一个大鼻子,头顶一顶大白帽。
他们都有胡子,形状和颜色各异。
有一位好像这帮人的头儿,他是一个身体厚实的老者,佩着宽腰带,戴着一顶插着羽毛的高顶帽,脚上穿着红袜子和高跟鞋。
还有一点让瑞普感到特别奇怪。
这帮人显然是在玩游戏,可是他们个个表情认真严肃。
他们默默地打着球,事实上是他见过的最死气沉沉的游戏聚会。
场上除了森柱的滚动声外没有任何声音。
木柱滚动时,撞击声像雷声一样响彻山空。
当瑞普和他的同伴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突然停下手中的游戏,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看,看得他浑身发毛,两腿颤抖。
此时他的同伴将木桶里的东西倒进几个大金属杯子里,示意他端给那帮人。
他胆战心惊地照做了。
他们一声不吭地喝掉了杯中之物,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
瑞普的紧张和害怕渐渐离他而去。
他甚至趁别人不注意地时候壮着胆子尝了一口酒,他很喜欢。
不一会儿,他觉得再尝一口的时机到了。
他一口接着一口,到了最后,他的眼睛怎么也睁不开,头也耷拉在胸前;他进入了梦乡。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那个长满绿草的小土丘上,他就是在这儿看到那个扛着木桶的老者的。
他擦了擦眼睛,知道现在已经是阳光明媚的早晨。
鸟儿在树丛中欢唱,树叶随着一阵阵清新的山风摇动着。
“当然,”瑞普心想,“我没有在这儿睡上一夜吧!
”他记得他睡着前发生的一切:
那个扛着酒桶的怪老头-----他们攀越的岩石山路---表情严肃的九木柱游戏者-----金属杯里的美酒。
“哦!
好杯子!
那神奇的杯子!
”瑞普想起来了。
“我该找个什么借口对凡-温克尔太太说呢?
”他环顾四周找他的枪,可是在他身边找到的不是那支擦得锃亮的,上好了油的猎枪,而是一支年久不用生了锈的枪。
他现在知道了,是山里那帮九木柱游戏者捉弄了他;他们用酒将他灌醉,然后偷了他的枪。
他的狗沃尔夫也不见了,也许跑到什么地方捉鸟或捉兔子去了。
瑞普吹哨子,喊他的名字,可是全是徒劳。
山里回荡着他的哨子声和喊叫声,可就是不见他的狗。
瑞普决定回到昨晚聚会的地方。
“如果我见到他们,”他自言自语道,“我就向他们要我的狗和枪。
”他正准备起身要走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腿似乎不如平时灵便了;他感到两腿和后背酸痛。
“这些山床对健康不利,”瑞普想。
“要是这次经历使我卧床不起,那我又要挨凡-温克尔太太一顿臭骂了。
他有些吃力地往山下走,来到了山谷。
他找到了他和他的伙伴前一天晚上走过的那条溪沟山道,可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这条沟道现在流淌着溪流,溪水在岩石间飞溅,山谷里发出山泉流淌时的尝淙淙欢笑声。
不过,他试着沿小溪水边攀行,穿孔机过树丛和攀缘植物。
他总算来到了那个岩石张开的开阔地,也就是九木柱游戏场地的入口处。
可现在连那块开阔地的影子也没有。
那些岩石现在变成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屏障,山涧溪流从这里哗哗落到下面的水塘里。
可怜的瑞普被迫在这里止住脚步。
他又吹了哨子,喊他狗的名字,可是回答他的只是一群山鸟。
带着困惑和不安,他转身向家里走去。
快到村子的时候,他碰见了好几个人,可他一个也不认识,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以为这一带什么人他都认识。
这些人的衣着打扮也和他的朋友和邻居们不一样。
他们和他一样满脸的惊讶。
他们盯着他看,还抬手摸他的下巴。
这种频繁的举动促使瑞普不假思索地也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想象一个,当他发觉自己的胡须比以前长了一英尺的时候,他有多么吃惊!
现在他已经到了村口。
一君陌生的孩子跟在他后面跑并在他身后指着他灰白的胡子喊叫着。
那些狗也变得同他以前认得的不一样。
他们恶意地对着他狂吠。
就连村子的面貌也变了;村子变大了。
一排排房子,瑞普以前从未见过,他记得的房子全不见了。
门上写着陌生的名字,窗户里看到的是陌生的面孔,一切的一切全是陌生的。
这时,瑞普更加不安和迷惑了。
“昨天晚上那只杯子,”他想道,“毁了我那可怜的大脑。
”费了好大一会儿工夫,他找到了回有的路,他内心带着惧怕向自己的房子走去,时刻等待着凡-温克尔太太的叫骂声。
他发现家里的房子破烂不堪,几乎就是一堆旧木板。
屋顶塌了,窗户破了,门板倒在地上。
一条瘦骨嶙峋的狗站在荒废的房前,样子很像沃尔夫。
瑞普叫他的名字,可是这条狗对他露出牙齿,然后走开了。
这是让瑞普感到最伤心的事了。
“我的狗,我那踏实的狗,”瑞普叹了口气,“就连我的狗也把我忘了。
”他走进房子的废墟。
说实话,凡-温克尔太太以前总是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
可是现在房空人去。
他匆匆赶到村酒馆,在那里他打发过许多闲散时刻。
可是酒馆也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大旧木楼,窗户很大,有些已尼打碎了。
门上有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联合酒店,乔纳森-督利特尔。
”那棵原来遮着冷清的荷兰小酒馆的大树没有了。
现在是一根很高的杆子,上面是一面旗帜,旗帜上奇怪地组合着许多星条。
所有这一切都很奇怪,让人很难理解。
但瑞普认得招牌上的画像;那是乔治国王的画像,他在下面平静地抽过许多次烟斗。
可就连这画像也觉得古怪,与以前的不同。
陛下的红色上有变成了蓝色,他头上戴的是帽子而不是皇冠。
画像下面有一行字:
华盛顿将军。
和以往一样,门口有一群人,但瑞普谁也不认识。
他徒劳地寻找着智者尼古拉斯-维达(他长着宽脸,双下巴,抽着长烟斗,嘴里吐出烟云,而不是愚蠢的高谈阔论)。
他寻找凡-巴梅尔,那个人他们读旧报的小学教员。
可是这些人都不在,他倒是看到了一上瘦瘦的,长相可恶的家伙正在高声谈论公民权----选举---国会成员-----自由还有令凡-温克尔困惑不解的其它新名词。
酒店里的这帮政客不久注意到了瑞普:
他蓄着长长的灰白胡子,一身过时的服装,手里拿着一杆上锈的猎枪,身后跟着一大帮好奇的妇女和孩子。
人们簇拥在他周围,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
那个政治演说者走近他,低声问他,“您的选票投哪一方?
”还一个忙碌的小个子拖住他的胳膊,问他发球那个党派。
就在瑞普考虑着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一个模样自负的绅士穿过人群,站在瑞普-凡-温克尔面前,问他,“你为什么抓扛着枪来参加革命选举,后面还跟着嘈杂的人群?
你是不是想在村里制造混乱?
”“哎呀,老爷!
”可怜的瑞普叫道。
“我是个不爱闹事的可怜人,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村民,国王陛下的忠实臣民,愿上帝保佑他!
”一听到这句话,众人愤怒地喊道,“他说‘愿上帝保佑国王’!
把他轰走!
送他坐监狱!
”那个样子自负的人费了好大的工夫才让大家平静下来,然后又问瑞普为什么来这儿,他来找谁?
可怜的瑞普低声下气地向他保证他绝无恶意,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寻找和个以前常坐在客栈前面的邻居。
“那么,他们都是谁?
说出他们的名字?
”瑞普想了想,然后问道,“尼古拉斯-维达在哪儿?
”人群中一时没有人答应。
过了片刻,有一个老头用尖细的声音答道,“尼古拉斯-维达!
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死了18年了!
”“布洛姆-答契尔在哪儿?
”瑞普问。
“哦,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去当兵了。
有人说他在斯陡尼要塞的那场战役中阵亡了。
也许是的,也许不是,我不清楚。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个小学教员凡-巴梅尔在哪儿?
”“他也去打仗了,”那老人说。
“他是个将军,现在进了国会。
”听到他家里和朋友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心里很悲伤,感到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的人。
每个答案都让他困惑不解。
这些人的回答说明,不知许多年过去了,他们提到的事情----战争----国会----斯陡尼要塞----他都不明白。
他没敢再往下打听其他朋友,而是绝望地喊道,“这儿有人认识瑞普-凡-温克尔吗?
”“哦,瑞普-凡-温克尔,”有两三个人惊叫起来。
“是的,是他!
瑞普-凡-温克尔在那儿呢,倚在树上的那一个。
”瑞普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长得和他上山时的模样一样的男人。
显然,这个人和他以前一样对干活没有兴趣,他的衣服也和他以前的衣服一样破旧。
不幸的瑞普此时脑子被搞湖涂了。
他感到纳闷,他究竟是自己呢,还是某个其他人。
就在他困惑不定时,人群中有人问,“你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天知道!
”瑞普绝望地高声说道。
“我不是我自己我是另一个人。
那儿的那个人是我。
不,那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另外某个人。
昨天晚上我还是我来着,可我在山上睡着了,他们换了我的枪,什么都变了样。
我也变了模样,我说不出我的名字,也说不出我是谁?
”他的听众此刻开始面面相觑,会意地笑了。
不难看出这个老头发疯了。
有人低声说“缴了他的枪!
谁知道这个老家伙下面会干出什么事来?
”可正在这时候,一个长得好看的妇女挤到人群前面来看这位灰白胡子老人,她怀里的孩子被他的外貌吓得哭了起来安静,瑞普,“她对孩子说。
”安静,你这个小傻瓜,这个老人不会伤害你的。
“孩子的名字,母亲的姿态和她说话原语调,这一切在瑞普-凡-温克尔脑海里勾起了一连串的回忆。
“您叫什么名字,好夫人?
”他问道。
“朱蒂丝-嘉顿妮尔,”她答道。
“您父亲叫什么?
”“哦,可怜的人!
他叫瑞普-凡-温克尔,可是20年前,他带着猎枪离家出走了,此后谁也没有他的消息。
他的狗回来了,可他没有。
他是开枪自杀了,还是被印第安人掳走了,谁也不知道。
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女孩。
”瑞普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了。
他声音颤抖地问:
“你母亲在哪儿?
”“哦,她死了,就在不久前。
她是对一个上门兜售产品的人发火,结果血管破裂死了。
”这个消息至少给他带来一点安慰。
这个诚实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他一把抱住他的女儿和她的孩子。
“我是你的父亲!
”他哭着说道。
“从前是年轻的瑞普—凡-温克尔,现在成了老瑞普-凡-温克尔了。
这儿没人认得可怜的瑞普-凡-温克尔吗?
”大伙儿站在那儿,目瞪口呆,最后一个老太太离开人群,抬头打量了他片刻,然后惊叫起来:
“没错!
是瑞普-凡-温克尔;是瑞普欢迎您回家,老邻居!
可是这20年来你去哪儿了?
”瑞普很快讲完了他的故事,因为对他来说这整整20年只是一夜的时间。
邻居们听了这个故事都睁大眼睛。
有些不以为然的邻居彼此笑笑,表露出打趣的神色。
那位看上去自负的拉下嘴角,摇了摇头。
众人看了也一起摇起头来。
然而大家一致同意听听老彼得-范德栋克怎么说,因为有人看到他慢慢向这边走来,彼得是这个村子上年龄最大的。
他对这个地区的历史了如指掌。
他马上想起了瑞普,最让人信服地证实了他的故事。
长话短说,众人散去,回到了他们更关心的话题----选举。
瑞普的女儿领回瑞普和她一起生活。
她有一个舒适的家,丈夫是一个快乐的农夫,瑞普记得,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经常驮他。
至于瑞普的儿子,简直就是自己的翻版。
尽管像他父亲一样,也有料理百家事而不愿干自家活儿的习惯,但是他还是受雇在农场工作。
现在瑞普又回到了他从前的生活方式。
他不久找到了很多以前的老伙伴。
因为他们都已经老态龙钟了,所以他更喜欢在年轻人中间交朋友,他们很快喜欢上了他。
因为他在家无事可做,也因为他已以到了安享晚年的年龄,没人责备他游手好闲,所以他又坐在村里小酒馆的门前。
在那里,他被看做村里的老人,受人尊敬,他可以讲讲“战争前”旧时代发生的事情。
过了很长时间,他才真正搞明白他那18年的一觉期间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件。
他得弄清楚这期间发生的革命战争。
这场战争使得这个国家因此脱离了英国的统治;他不再是乔治三世陛下的臣民,而是美利坚的自由公民。
瑞普实际上不是一个政客,国家和帝国的改朝换代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有一种独立他很明白,那就是他摆脱说话尖刻的老婆。
幸运的是,他现在有了这种自主权;在家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
然而每当有人提到凡-温克尔太太的时候,他总是摇摇头,眼光投向天空。
谁也不知道这是表示他接受了命运的摆布,还是表明对自己的解脱感到欣慰。
他常对每个来督利特尔的酒店的陌生人讲他的故事。
人们注意到,起初他每次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总要改变一些细节。
但是这个故事最终固定了下来,和我上述的故事完全一样;村里男女老少无人不晓。
有些人想说他们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确信无疑。
甚至到了今天,每当他们在夏日的下午听到卡兹吉尔山脉附近的雷暴时,他们说这是享德里克-哈得逊和他的水手在玩九木柱游戏。
这一带许多在家受气的丈夫有时也希望喝上一口瑞普-凡-温克尔神杯里的酒,能一睡解千愁。
睡谷的传说
美.WashingtonIrving 刘怀远译
在哈德逊河东岸有一个小集镇,通常被人们叫做塔里镇。
离这个小镇不远,大约两里左右的高山中有一个小山谷。
这里是世界上最寂静的地方之一。
一条小溪穿流而过,潺潺的溪流声使人昏昏欲睡,只有偶尔小鸟的鸣叫声才打破了山谷的宁静。
我记得,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我第一次的辉煌业绩是在遮蔽了半个山谷的大胡桃树林中捕获了几只松鼠。
那是一个周日的中午我溜达进了山谷,当时万籁俱寂,响亮的枪声打破了周围的宁静,在山谷久久地回荡。
我想要是想逃避尘世的烦恼,安安静静虚度此生,再没有比这小山谷更理想的地方了。
这个山谷的名字由此地的永不宁静产生,来自那些住在那里象他们荷兰祖先曾有的特点。
这个山谷因此得名“睡谷”,并且这里的农夫被邻村的人叫作“睡谷人”。
一个沉睡的、梦魇般的东西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有人说一个医生曾在荷兰人统治时在那里耍过魔术,其他人断言,有一个印第安老酋长精通魔术,曾在得里克.哈得逊船长发现之前控制着这个地区……
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始终总有一种魔力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使他们行走好象总在睡梦中。
他们倾心信奉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们常常能看见奇异的光并能听到在空中有音乐和说话的声音。
在这个地区所提到的幽灵中最神奇的那个好象成了这里一切的统治者。
在睡谷的人们看来,那幽灵的形状象是骑在马上的一个人——一个无头的家伙。
有人说那是在革命战争中被枪打掉了脑袋的士兵的鬼魂。
据说这个无头骑士常见在夜间飞快地游荡。
他不光在这个山谷中游逛,而且还到邻近的路上,尤其是到不远的教堂里。
事实上,当地人相信他到教堂里是有当地历史根据的。
他们说那个士兵的尸体曾葬在教堂的院子里,那个鬼就每晚骑着马在战场周围寻找他的头。
这些权威的说法试图解释他为何在山谷中急速游荡。
他们说由于他迟到了才匆匆忙忙,而且必须在早上返回到教堂的院子里。
不管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里的许多人曾见到过这个鬼。
他们还知道睡谷无头骑士的名字。
说来也怪,能看见鬼的不仅是这个山谷里的人,就连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的人也有了这种本事。
有人肯定,既使任何一个在进到睡谷之前很清醒的人,只要在这里住很短的时间,就会做梦在梦里见到鬼魂。
我用令人满意的赞美语言提到的这个安祥的地方,人们的思想、行为和风俗习惯仍旧保留在闭塞的小荷兰山谷中,而大纽约州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睡谷这样的地方好比是急流边上小池里的一汪静水,不受奔流江水的影响。
我离开睡谷宁静的居所已多年了,我相信我仍能在那里找到那些树和人家。
在这个梦幻地区,几年前,住着一个可怜人叫伊克波德.克莱恩。
他并不是本地人,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睡谷教书的。
伊克波德.克莱恩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最合适不过。
他看起来极象一种叫鹤的水鸟,又高又瘦,窄窄的肩膀,腿长胳膊长,脚又很大,总之身体各个部位松松散散地凑在一起。
他的头很小,头顶很平,再配上一对大耳朵,一双大而无神的绿眼睛,在骨骼暴凸的颈项顶端还有一个细长的鼻子。
伊克波德教书的地方由一间大房子构成,用原木搭建。
窗户一部分装有玻璃,一部分糊着用过的习字贴。
教室位置有点偏僻,但环境很不错,刚好处在一片森林的小山脚下,一条小溪穿流而过;另一边上是一片参天大树。
夏日里经过这里的人们就能听见学生轻声背诵课文的嗡嗡声。
不时地,这种声音被老师严厉的声音打断,是一种警告或是命令的语气。
与其他教书人一样,当用语言说不动学生按要求去学习时,他就会动用一根教棍。
然而他不是那种残酷的从体罚学生的痛苦中享乐的学生王。
在惩罚学生时,他把弱小的负担加重到强大的头上。
他对那些一动教棍就哭的弱小孩子惩罚很轻。
但是出于公正起见,他把双倍的惩罚加在那些健康强壮的小荷兰人身上,他们用沉默的对抗来忍受挨打却不哭一声。
他把这一切说成是为他们的父母尽义务。
他从不打那些做过保证的学生,“你们要记住并且要感谢我,你们将来的路还很长。
”
放学后,他甚至成了大一点孩子们的伙伴。
在假期,他十分友好地到小一点孩子的家中,只要他们有漂亮的姐姐或是他们的妈妈能有一手好的厨艺。
事实上,他认为很有必要和他的学生们保持友好的关系。
他教书的工资很低,几乎不够他每天的伙食,因为对他这么瘦的人来说他的饭量太大了。
除了他的工资之外,他还给人家的孩子辅导课程混些饭吃和混住一宿。
这在当时的那个地方是一种风气。
每一家他都隔段时间会住一周,然后又挪到另一家。
他随身的财物只有一块棉手绢而已。
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伊克波德掌握了不同的方法使自己对他住宿的家庭既有用又令他们愉快。
有时帮他们在地里干点轻活,修修篱笆,去饮一下马,为冬天砍点柴禾。
他也很节约,所有的精力而且最重要的都放在他的小帝国——学校上。
他让人信服,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