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docx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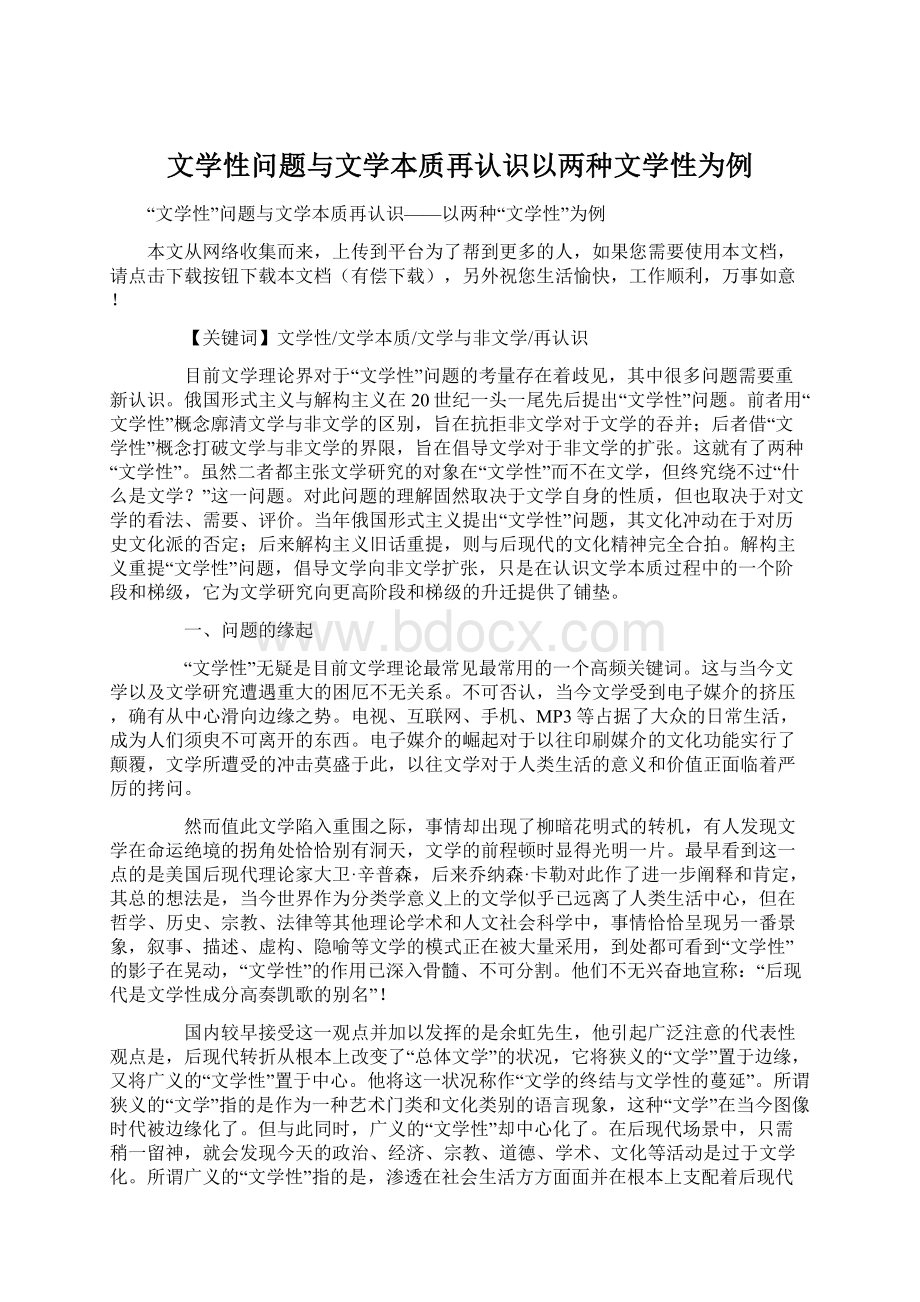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关键词】文学性/文学本质/文学与非文学/再认识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
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
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
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
”这一问题。
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
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
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一、问题的缘起
“文学性”无疑是目前文学理论最常见最常用的一个高频关键词。
这与当今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遭遇重大的困厄不无关系。
不可否认,当今文学受到电子媒介的挤压,确有从中心滑向边缘之势。
电视、互联网、手机、MP3等占据了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
电子媒介的崛起对于以往印刷媒介的文化功能实行了颠覆,文学所遭受的冲击莫盛于此,以往文学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正面临着严厉的拷问。
然而值此文学陷入重围之际,事情却出现了柳暗花明式的转机,有人发现文学在命运绝境的拐角处恰恰别有洞天,文学的前程顿时显得光明一片。
最早看到这一点的是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辛普森,后来乔纳森·卡勒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和肯定,其总的想法是,当今世界作为分类学意义上的文学似乎已远离了人类生活中心,但在哲学、历史、宗教、法律等其他理论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事情恰恰呈现另一番景象,叙事、描述、虚构、隐喻等文学的模式正在被大量采用,到处都可看到“文学性”的影子在晃动,“文学性”的作用已深入骨髓、不可分割。
他们不无兴奋地宣称:
“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
国内较早接受这一观点并加以发挥的是余虹先生,他引起广泛注意的代表性观点是,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狭义的“文学”置于边缘,又将广义的“文学性”置于中心。
他将这一状况称作“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
所谓狭义的“文学”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和文化类别的语言现象,这种“文学”在当今图像时代被边缘化了。
但与此同时,广义的“文学性”却中心化了。
在后现代场景中,只需稍一留神,就会发现今天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学术、文化等活动是过于文学化。
所谓广义的“文学性”指的是,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在根本上支配着后现代社会生活运转的话语机制,这种机制显然不是狭义文学所独有的东西。
有鉴于此,他提出所谓“文学研究内部的转向”的口号,以期推动后现代处境下文学研究的重建,具体地说有两个方面,即从狭义的文学研究转向广义的总体文学的研究,从狭义的文学性研究转向广义的文学性研究。
①
大卫·辛普森、乔纳森·卡勒以及余虹此论一出,马上引来一片质疑之声。
有论者指出,辛普森们张扬的“后现代文学性”一方面导致文学原有的精神气质逃逸、颓败和飘散在“文学性”之中,另一方面则是俗文学的逻辑进入各个学术领域,而将各个学术领域都泛“俗”化了。
这就使得后现代的文学大大地掉了档次和品位,连辛普森自己都称之为“半桶水知识”,它不足以与原先的文学相提并论。
还有,被辛普森们当作“新发现”的文学修辞同时也为其他学术理论和人文社会科学广泛运用的情况,按说乃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从古到今,比喻、象征、比拟、隐喻等修辞手法并不是文学的专利,而是一切文体公用的表达方式。
由此可见,所谓“后现代文学性统治”其实并不存在,只是辛普森们的一种巨型想象和时代误读罢了。
②也有论者认为,主张“文学性扩张”者的不足在于,其论述对于“文学性”等概念的内涵缺乏界定,而在论述过程中也含糊其辞。
他们大力肯定的经济、商业、消费中的“文学性”与文艺学中的“文学性”在各自话语中的位置和功能并不是一回事。
就前者而言,“文学性”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就后者而言,“文学性”则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的。
③
可以确定,上述“文学性”问题的浮出水面以及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并非无话找话,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其中还有一些问题是必须加以解决的,而论者对此往往有所忽视:
其一,如今“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算起应是第二次,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这两次文论的悸动之间有何联系和区别?
其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能够摆脱“什么是文学?
”的本体性思考吗?
其三,对于“文学性”以及“什么是文学?
”问题的确认肯定不能是随意的,那么它更为确凿的前提和依据何在?
其四,所谓“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这一文学状态是恒常性的还是权宜性的?
是终极性的还是过程性的?
应该说,对于文学的当前发展与未来走向来说,这些问题都可谓重大而紧要。
二、两种“文学性”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1989年在讨论“什么是文学?
”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问题的目的不是要寻找文学的定义,而是要描绘文学的特征”,从而提出了“文学性”的问题。
这让人想起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学者说过的话,如罗曼·雅各布森说:
“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
”④在20世纪一头一尾发出的这两个声音遥相呼应,为近一个世纪文学研究的精神历险描画出一个“蛇咬尾巴”式首尾衔接的圆圈,而其中心就是“文学性”问题。
然而此“文学性”非彼“文学性”,“文学性”问题在当今的旧话重提并非历史的重复,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学术格局。
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19世纪后期执掌文坛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的逆反。
以佩平、季杭拉沃夫、维谢洛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研究从属于社会学,将文艺作品视为历史文献、文化实例和个人传记,将文学史等同于社会思想史,而无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的全部复杂性。
总之,在历史文化学派那里,“文学”与“社会”几乎是同义词,文学理论与思想文化部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佩平曾这样说:
“怎么能把文学本身从社会运动中分离出去,又为它找出一条规律呢?
”⑤
历史文化学派用社会历史规律取消文学自身特性的弊端引起了俄国文论界的普遍不满,人们批评历史文化学派将种种非文学现象统统纳入文学研究,从而扭曲了文学研究的本性,使得文学研究等而下之,降格为一种例证和资料,变成了社会史、思想史、个人传记和心理研究的附庸。
作为一种逆反,俄国形式主义主张将文学史与社会、思想、政论、宗教、道德、法律、新闻、风尚、教育、科学的历史区分开来,反对用社会史、思想史、个人传记和心理研究等“外在的”材料代替文学本身,而强调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和自身规律,如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自己的文学理论旨在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
“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只数和纺织方法。
”⑥俄国形式主义据此认为,只有寻找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才是文学研究的本分,才是文学研究独立于其他知识、学问的特质和价值之所在。
而他们所说的“文学性”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的特点,即打破语言的正常节奏、韵律、修辞和结构,通过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与人们熟悉的语言形式相疏离相错位,产生所谓“陌生化”的效果。
可见,从历史文化学派到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研究取一种退缩、收敛的态势,即从非文学领域向文学领域收缩,排除社会历史、政治运动、思想潮流、道德教条、宗教观念和文化风尚等对于文学的外来干预,将文学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文学自身的规定性,限定在文学的文本、语言、形式之上。
如果说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消融在社会、历史、文化之中,抹杀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那么俄国形式主义则正相反,刻意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
然而,当解构主义再次提出“文学性”问题时,事情则发生了变化,文学研究恰恰转向了发散、扩张的态势。
解构主义学者关心的已不是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形式,而是非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了,诸如哲学、历史、政论、法律文书、新闻写作中的叙事、描述、想象、虚构、修辞等。
乔纳森·卡勒在这方面可谓得风气之先,他较早发现了这一事实:
“文学性”在非文学文本中的存在,如今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他说:
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
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
克罗德·莱维—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
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它语言之中。
⑦
在这一风气转变的过程中,雅克·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德里达认为,以往人文话语总是围绕“中心”来彰显意义,所谓“中心”,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奉为最高本体的本质、存在、实体、真理、理念、上帝之类概念。
其实这种“中心”是不存在的,是理应被消解的。
人文话语并不是通过能指与所指的转换达到对意义的把握,而是通过能指与能指的过渡实现意义的,而且这是一个无限延续的过程,构成一根长长的链条。
这就像查字典,一个词的意思要到另一个词那里去查找,而另一个词的意思要到更多的词那里去查找,这一查找的过程是无穷尽的,因而意义的实现也是无穷尽的。
这样,德里达就以能指与能指之间的横向关系取代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纵向关系,认为意义的彰显只是一场在能指与能指之间进行的游戏,它取决于不同能指之间的“延异”,亦即从一个能指过渡到另一个能指,在空间中存在差异,在时间上有所延宕,从而在能指与能指之间就出现了“间隔”和“空隙”。
在这一连串的过渡中,意义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不同能指之间的“间隔”和“空隙”之中,这就使得意义的彰显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归结于某个中心。
德里达还认为,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中,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声音中心主义,它认为只有语音能够通畅地传达意义,而文字在传达意义方面只能起补充作用。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与语音相比较,倒是文字能够更好地传达意义。
德里达说,文字是一种充满延异、间隔和空隙的系统游戏,“正是通过’间隔’,要素们之间才相互联系起来。
这一间隔是空隙的积极的,同时又是消极的产物,没有空隙,‘完满的’术语就不能产生表征作用,也不能发挥作用。
”⑧所谓“延异”、“间隔”、“空隙”,就是文字所表现出的间接性、差异性、含混性。
文字往往并不直接、明白地将意思说出来,而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托喻咏物、取类言事,就像中国古人所说:
“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⑨,“以彼物比此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⑩。
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莫过于文学,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在叙事、描述、想象、虚构、修辞等方面对于种种“延异”、“间隔”、“空隙”的创造性运用,而这也往往不失为哲学、历史、法律、新闻等写作方式传达意义的一条幽径。
因此文学不应是非文学的附庸,而应成为非文学的领军,没有任何一种写作、任何一种文本可以脱离文学。
而这一点,正是当今非文学文本中“文学性”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对此,英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列举了理查德·罗蒂的分析哲学、斯坦利·费什的法学著作、海登·怀特的历史学,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人类学,唐纳德·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以及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中的种种文学技巧和修辞手法,用来说明这一见解:
“有些时候,大学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得像文学教授的学生们一样,把阅读从头学习一遍,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处于文本之外。
”(11)
为此有人断言今天已进入“学术后现代”阶段,人们面临着“文学的统治”。
而这正是美国学者大卫·辛普森一本书的名字:
《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
值此人们普遍忧虑文学走向消亡之际发此高论着实堪称别具只眼。
大卫·辛普森认为,当今文学研究固然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精神分析等那里借用新的描述方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文社会科学反过来大量采用传统的文学形式,无论是叙事因素在历史著述中的加强,修辞手法在道德规范中的运用,大量遗闻逸事、个人自传、乡土知识在各种学术著作中被采纳,都在宣告着文学的辉煌胜利,体现着文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式的统治。
从通常的眼光来看,文学正在逐步退出自己原有的领地,被广告、通俗读物、电影、电视、网络以及各种大众文化形式所挤压和取代,但如果换一种眼光看,那么就不难发现,文学恰恰在哲学、历史、政论、法律、新闻等学术和知识领域内开辟了自己新的领地,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因此大卫·辛普森声称:
“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
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12)分化与组合共存,破坏与重建并举,这也许就是以拆除栅栏、推倒壁垒、填平沟壑、跨越边界为指归的后现代主义所演绎的新神话。
在这里作一个对比是非常有趣的:
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的问题,是为了革除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淹没在非文学之中的弊端,从而将文学退缩到用语言、文本、形式构筑的城堡之中,插上了“文学性”的旗帜,以圈定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而今天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是致力将文学从语言、文本、形式之中解放出来,使文学走出了蜗居的城堡,跨过了固守的边界,以叙事、描述、隐喻、虚构和修辞等造成“差异”、“间隔”、“空隙”的游戏给所有非文学写作统统打上“文学性”的印章纹样,将其收编于自己的旗下,文学表现出一种扩张、侵略甚至殖民的冲动,而种种非文学写作则成了文学统治的顺民。
看来辛普森此言不虚:
“非文学学科正逐渐被它们自己的极端分子对文学方法的再传播所殖民化了。
”(13)回想以往历史文化学派将文学史完全看成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科学史、政论史、宗教史,将文学之区当成任何人都可以去狩猎并收获带有自己标签的猎物的无主地;事到如今,一切恰恰反了过来,其他种种非文学学科反倒成了文学安营扎寨、圈地开垦的新大陆,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法律的、新闻的统统成为文学的。
而与这一历史性逆转相伴相随的恰恰是“文学性”问题的再次浮现,不过往日俄国形式主义刻意用“文学性”概念来厘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如今解构主义借“文学性”概念来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则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
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
在前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文论史上,两次重要转折都以“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为标志,但两者的指归却截然不同,这不能不是20世纪文论史非常惹眼的一景。
三、文学与非文学的界说
以上讨论,其实搁置了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何在?
如果缺少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上述讨论仍然是不确定因而也就是无意义的。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一直试图划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但至今这条界限仍然很不清晰,不管哪一种划界的意见,总是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相反的例证将其轻易否定。
例如西方关于“什么是文学?
”最早的经典界定是法国女作家斯达尔夫人作出的,她在1800年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该书“序言”开宗明义地宣称:
“我打算考察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对文学有什么影响,而文学反过来对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又有什么影响。
”这是欧洲文学研究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文学(literature)与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等方面区分开来,使得literature这一已经使用了2500年的概念,从泛指一般的“著作”或“书本知识”变为专指“想象的作品”(在此书中有“论想象的作品”一章),从而第一次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
然而如果今天人们对于这一沿用了两百年的说法仔细加以推敲的话,就不难发现仅仅用想象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是有缺陷的。
问题在于,凡是“想象的作品”就必定是文学吗?
没有想象的文字就一定不是文学吗?
《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中的许多篇章历来被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但这些史乘之作是严格地要求纪实而不容许丝毫想象虚构的;相反地,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文本充满了想象和幻想,但却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当作文学作品。
再如英美新批评提出的许多主张,像兰塞姆的“肌质——构架”说,退特的“张力”说,燕卜荪的“含混”说,布鲁克斯的“反讽”说等,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说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无不遭遇各种各样的异议,甚至有时搞得持其说者本人也很不自信。
例如退特的“张力”说,就是说诗既关涉“外延”,又关涉“内涵”,处于这二者所构成的张力之中。
所谓“外延”,是指语词的词典意义;所谓“内涵”,是指语词的暗示意义。
他认为,诗兼有这两种意义,体现着这两种意义相互牵制的张力;但科学文本中则不存在这种张力,因为科学文本只涉及“外延”而不涉及“内涵”,亦即只需要词典意义而不需要暗示意义,因此“张力”成为文学文本的特质而与科学文本旨趣相异,也与哲学、法律、政治、新闻的文本相左,从而“张力”成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界线。
这一见解是有道理的,无论是地质报告、气象预报、病情诊断,还是哲学教材、法律文书、政治概念、新闻报道,都是重视语词的词典意义而排斥语词的暗示意义的。
但是仅仅事关“外延”而缺乏“张力”的文字也未必不是文学,历史上许多科学著作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其中一些篇章往往作为文学作品而流传后世,其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之上,并谈不上什么“张力”或“内涵”。
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中写三峡的一段,在每一节开头反复使用“江水又东”这一整饬而又不断递进的排偶句式,既准确记叙了三峡的地形地势,又烘托出长江一往无前的壮观景象,从而常常被选为文学课的范文。
出现以上情况,可能问题出在人们习惯于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仅仅看成是客观的物理事实,是存在于作品之中的心理、体裁、形式、语言等的物化形态,却未曾考虑到其中接受者、评判者的主观因素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作用。
对此约翰·埃利斯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文学就像杂草,给“文学”下定义与给“杂草”下定义一样困难,“杂草”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它并非指一种固定的植物种类,“什么是杂草?
”的问题必须看园地的主人希望长何种植物才能确定,如果他打算长熏衣草,那么对他来说狗尾巴草就是杂草,反之亦然。
如果他打算长果树,那么不管是熏衣草还是狗尾巴草就都成了杂草。
可见在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问题上,接受者、评判者的主观因素起很大作用。
早先的诸子散文、秦汉策论,晚近的西方启蒙主义的“哲理小说”、存在主义的“观念戏剧”,人们一直习惯成自然地将其当作文学,其实无论用何种“文学”的定义来考量之,无疑都是圆凿方枘,龃龉多多。
如果要追溯下去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决定着人们将某个文本看成文学或非文学的原因很多,它们构成了特定的语境,其中有约定俗成的成分,有某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有社会体制的问题,也有某个群体的利益考虑等,如柏拉图根据城邦的最高利益,将除非赞颂神和英雄之外的诗人和诗歌逐出”理想国”,保守派将莎士比亚的剧作斥之为野蛮人的信口雌黄,布瓦洛根据至高无上的“理性”,对民间文艺大加贬黜,都可以在其“划界”行为的背后找出许多不属于文学本身的原因。
因此雅克·德里达说:
“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
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
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
”(14)可见文学是一种功能性、实用性概念而非本体性、实体性概念。
文学之为文学,并不是完全由其自身的某些特性说了算的,它要看外部的评价,要看别人怎么看待它,所以特里·伊格尔顿说,就文学而言,“后天远比先天更为重要”。
(15)但是这一理解也不宜走过了头,文学之为文学,还有其自身的某些规定性,也不是别人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一条再平常不过的道理就是,不管是何种风俗习惯,也不管人们抱有多么特殊的甚至奇怪的嗜好和趣味,也没有谁会把病历、菜单、电话簿、保险单、工程预算书当作文学来欣赏,能够当作文学来阅读的文本一定具有某种让人注意、使人愉快的语言结构和意味蕴含。
然而话说到这里,好像意思又倒回去了,说了半天最后肯定的,恰恰是前面被否定了的东西。
看来如果将文学本身的某些客观性质与外部对于文学的评价和看法这两者截然分开是永远说不清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的,因此雅克·德里达曾经发过感慨,认为文学“几乎没有,少得可怜”,这并不是说文学真的不存在,而是说如果单是在文本本身或外部评价之间各执一端地谈论文学是什么势必是不得要领的,一方面,“没有内在的标准能够担保一个文本实质上的文学性,不存在确实的文学实质或实在。
”理由是如果你刻意寻找文学作品的要素的话,就会觉得根本无法确认什么是文学,因为这些要素在别的文本中也能找到;另一方面,你要指望“一个社会群体就一种现象的文学地位问题达成一致的惯例,也仍然是靠不住的、不稳定的,动辄就要加以修订。
”(16)人们对于文学的惯例、规则、纲领、制度、传统的理解从来就是见仁见智、众口难调,因而是漫无定论的。
在这个意义上,真可以说“文学少得可怜”!
从德里达的困惑可以得到一种启发,那就是只有将文学自身性质与外部评价这两者不是分成两橛而是合为一体,才有可能将什么是文学和什么不是文学的问题说得清楚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仅仅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是什么?
”的问题,认为文学之为文学,往往取决于它自身的属性,而且往往归结为某一根本属性,例如把文学视为“想象的作品”或“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便是如此,综观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文学理论的教材和论著,也大致未曾跳出这一思路。
现在有必要打破以往的思维定势,对于文学的自身规定性与外部规定性这两者的复合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
在这个问题上,国外研究者所作的尝试富于启示意义,如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它是两种不同视角的交叉重叠,他得出的结论是:
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为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
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作程式的创造,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
哪一种视角也无法成功地把另一种全部包含进去。
所以你必须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
(17)乔纳森·卡勒的观点受到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后者更加强调社会的关注度对于文学的成立所起的作用。
特里·伊格尔顿说:
文学并不像昆虫存在那样存在着*,它得以形成的价值评定因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些价值评定本身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们最终不仅指个人爱好,还指某些阶层得以对他人行使或维持权力的种种主张。
(18)讨论至此,可以断定在文学与非文学在哪儿划界的问题上要求证一个清楚的、确定的结论是十分困难的。
现在能够说的就是,文学是一种关系概念而非属性概念,是一种复合性概念而非单一性概念。
这就是说,文学之为文学,取决于文本自身性质与外部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这二者的复合关系,而在这二者的背后,都分别展开着一个广阔的世界,其中每一桩事物、每一种因素,都可能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说产生影响。
四、后现代神话所架设的梯级
从这一思路出发,对于20世纪文论史的风云变幻,特别是以“文学性”问题的一再浮现为标志的两次重大转折中文学与非文学的分分合合将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
总而言之,无论是哪种情况,“什么是文学?
”的问题都既涉及文本自身的特性,又牵扯到外部对文学的看法、需要和评价,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
(19)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