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之光香醉泸州推荐.docx
《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之光香醉泸州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之光香醉泸州推荐.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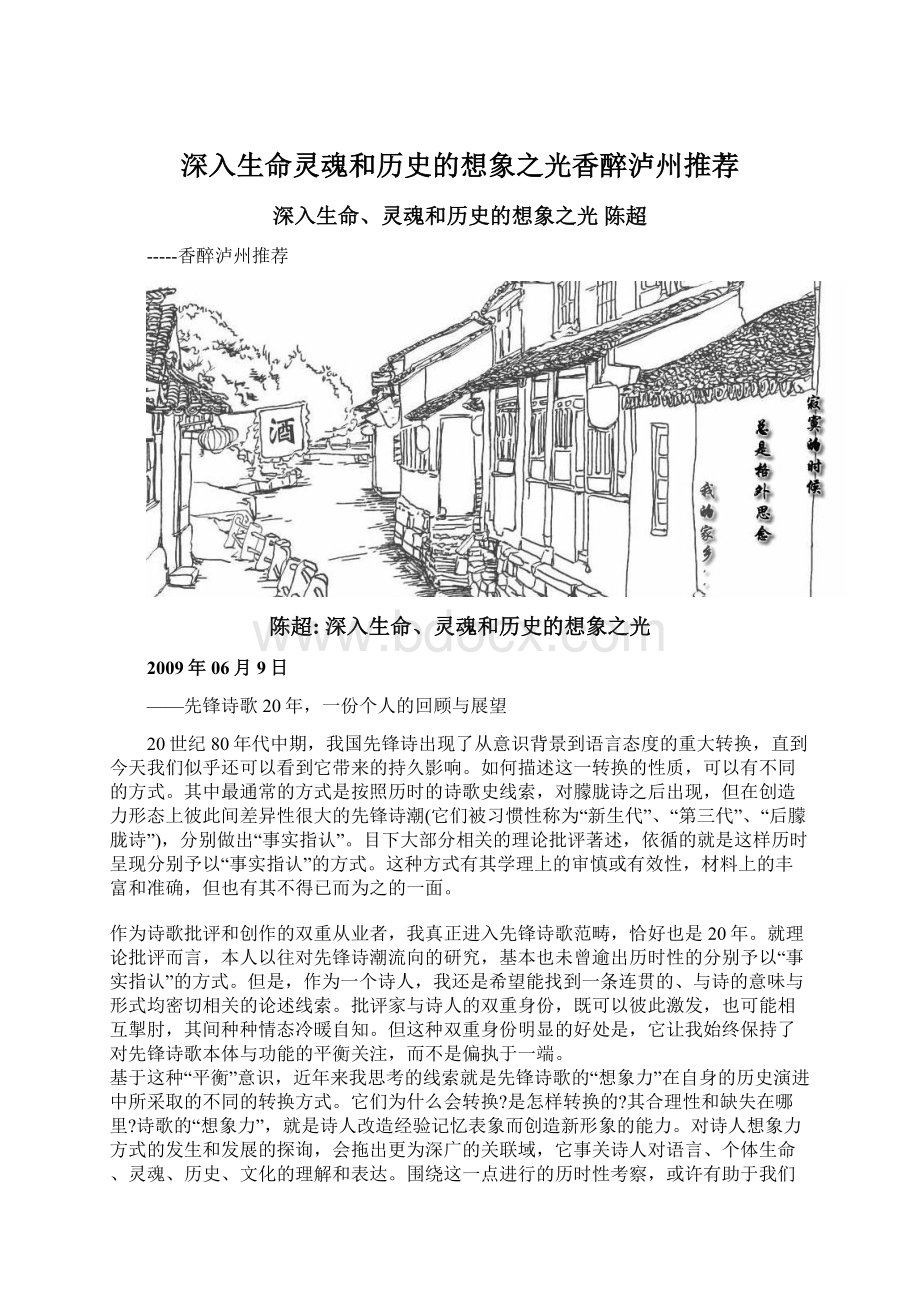
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之光香醉泸州推荐
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之光陈超
-----香醉泸州推荐
陈超:
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的想象之光
2009年06月9日
——先锋诗歌20年,一份个人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先锋诗出现了从意识背景到语言态度的重大转换,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它带来的持久影响。
如何描述这一转换的性质,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其中最通常的方式是按照历时的诗歌史线索,对朦胧诗之后出现,但在创造力形态上彼此间差异性很大的先锋诗潮(它们被习惯性称为“新生代”、“第三代”、“后朦胧诗”),分别做出“事实指认”。
目下大部分相关的理论批评著述,依循的就是这样历时呈现分别予以“事实指认”的方式。
这种方式有其学理上的审慎或有效性,材料上的丰富和准确,但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
作为诗歌批评和创作的双重从业者,我真正进入先锋诗歌范畴,恰好也是20年。
就理论批评而言,本人以往对先锋诗潮流向的研究,基本也未曾逾出历时性的分别予以“事实指认”的方式。
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条连贯的、与诗的意味与形式均密切相关的论述线索。
批评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既可以彼此激发,也可能相互掣肘,其间种种情态冷暖自知。
但这种双重身份明显的好处是,它让我始终保持了对先锋诗歌本体与功能的平衡关注,而不是偏执于一端。
基于这种“平衡”意识,近年来我思考的线索就是先锋诗歌的“想象力”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所采取的不同的转换方式。
它们为什么会转换?
是怎样转换的?
其合理性和缺失在哪里?
诗歌的“想象力”,就是诗人改造经验记忆表象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
对诗人想象力方式的发生和发展的探询,会拖出更为深广的关联域,它事关诗人对语言、个体生命、灵魂、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表达。
围绕这一点进行的历时性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在对20年来先锋诗歌的回顾和展望时,不至于“事实指认”有余,而价值判断不够足。
我认为,20年来先锋诗歌的想象力是沿着“深入生命、灵魂和历史生存”这条历时线索展开的。
其最具开拓性的价值也在这里。
当然,这里所谓的“价值”,是根据我个人的审美趣味、生存立场做出的。
因此,文章副标题中出现的“个人”,绝非是妄自尊大或自矜,只不过是昭示出一个个人的视点,并期待同行的驳难补充与修正。
(一)
对于保持着冷静的人们来说,80年代初期发展到成熟的涌流阶段的“朦胧诗”(其文脉滥觞可上溯到60—70年代后期的“X小组”、“太阳纵队”、“白洋淀诗群”、“《今天》诗群”),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先锋派诗歌,而是曾被中断了的五四运动以来,启蒙主义、民主主义、浪漫主义诗歌的变格形式。
在朦胧诗人的代表性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想象力向度与五四精神的同构之处。
因此,朦胧诗的想象力主体,是一个由人道主义宣谕者,红色阵营中的“右倾”,话语系谱上的浪漫主义、意象派和象征派等等,混编而成的多重矛盾主体。
在他们的“隐喻—象征,社会批判”想象力模式内部,有着明显的价值龃龉现象。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龃龉所带来的张力,使朦胧诗得以吸附不同历史判断及生存和文化立场的读者,不同的诠释向度。
所以,在80年代初期,虽然朦胧诗受到那些思想僵化的批评家的猛烈抨击,但这反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其站稳了脚跟。
其原因就是由于它在社会组织、政体制度、文化生活方面,与中国精英知识界“想象中国”的整体话语——“人道主义”、“走向现代化”——是一致的。
1984年后,“朦胧诗人”开始了想象力向度的调整或转型。
北岛由对具体意识形态的反思批判,扩展为对人类异化生存的广泛探究。
杨炼更深地涉入了对种族“文化—生存—语言”综合处理的史诗性范畴。
多多更专注于现代人精神分裂、反讽这一主题。
芒克则以透明的语境(反浪漫华饰)迹写出昔日的狂飙突进者,在当代即时性欣快症中,作为其伴生物出现的空虚和不踏实感。
这四种向度,是1984年后“朦胧诗”最有意义的进展。
同时,它也昭示出作为潮流出现的“朦胧诗群”的解体。
“朦胧诗”更新了一代人的审美想象力和生存态度。
从早期正义论意义上“民主、自由”红色圣礼式的精神处境的渐次淡化,到后期几位诗人对现代主义核心母题的迫近,我认为,其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休戚相关地预兆了新生代诗歌的发展。
因此,简单地将新生代诗歌看作“朦胧诗”的反对者,是一种过于幼稚的说法——无论是曾经说过,还是今后打算这么说。
但是,作为诗歌发展持续性岩层的断面,新生代诗歌的想象力方式与“朦胧诗”的确不同。
由此否定“朦胧诗”是肤浅的,但超越它(包括“朦胧诗人”后期创作的自我超越)则是诗歌发展的应有之义。
1985年前后,新生代诗人成为诗坛新锐。
随着红色选本文化树立的卡理斯玛的崩溃,和翻译界“日日新”的出版速度,这些更年轻的诗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共时”亲睹了一个相对主义、多元共生的现代世界文化景观。
在意识背景上,他们强调个体生命体验高于任何形式的集体顺役模式;在语言态度上,他们完成了语言在诗歌中目的性的转换。
语言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意义容器,而是诗人生命体验中的惟一事实。
这两个基本立场,是我们进入新生代诗歌的前提。
这里,我借用两句大家熟悉的古老神谕,来简捷地显现这种不同——
“理解你自己”:
“朦胧诗人”在这里意识到的是社会人的严峻,承担,改造生存的力量。
新生代诗的主脉之一“口语诗”,意识到的却更多是,“理解你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生命,不要以“神明”自居(包括不要以英雄、家族父主及与权力话语相关的一切姿势进入诗歌)。
“太初有道”:
“朦胧诗人”在这里意识到的“道”,是人文价值,社会理想目标,核心,主宰。
新生代诗人意识到的,更主要是这个语辞的源始本真含义;道theword(字,词);新生代另一主脉,具有“新古典”倾向的诗人,则追寻超越性的灵魂历险,而非具体的社会性指涉。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末期广泛涌流的“新生代涛歌”,只是对朦胧诗之后崛起的不同先锋诗潮的泛指,也可以说,它是“整体话语”或曰“共识”破裂后的产物,其内部有复杂的差异。
但是,从诗歌想象力范式上看,它们约略可以分为两大不同的类型:
日常生命经验型和灵魂超越型。
当然,这两种不同的范型也并非简单地对立或互不相关,特别是到90年代中期,彼此间的“借挪使用”是十分明显的。
这个特点,容我在下一部分细加论述。
对日常生命经验的表达,主要体现在对朦胧诗的“巨型想象”的回避上。
这使得新生代诗歌之一脉,将诗歌的想象力“收缩”到个体生命本身。
这种“收缩”是一种奇妙的“收缩”,它反而扩大了“个人”的体验尺度,“我”的情感、本能、意志和身体得以彰显。
1985年之后,引起广泛关注的“他们”、“非非”、“莽汉”、“女性诗”、“海上”、“撒娇”、“城市诗人”、“大学生诗派”等等,都具有这一特性。
从题材维度上,他们回到了对诗人个人性情的吟述;从形式维度上,他们体现了对主流方式和朦胧诗方式的双重不屑;从心理维度上,他们表达了镇定自若的“另类文化”心态;从语言维度上,他们大多体现了口语语态和心态合一的直接性,其语境透明,语义单纯。
最终,从想象力范畴看,他们力求表述自我和本真环境的“同格”。
限于篇幅,且以韩东的一首短诗为例。
如果说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更像是第三代诗人反对“巨型想象”的“写作宪章”的话,那么真正能代表他想象力向度和质地的,还应是表现日常生活的诗作。
比如《我听见杯子》:
这时,我听见杯子/一连串美妙的声音/单调而独立/最清醒的时刻/强大或微弱/城市,在它光明的核心/需要这样一些光芒/安放在桌上/需要一些投影/医好他们的创伤/水的波动,烟的飘散/他们习惯于夜晚的姿势/清新可爱,依然/是他们的本钱/依然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使他们度过纯洁的一生/真正的黑暗在远方吼叫/可杯子依然响起/清脆,激越/被握在手中
这里,一次普通的朋友聚饮,被诗人赋予了既寻常又奇妙的意味。
它是“单调而独立”的,但同时又是“最清醒的时刻”。
对日常生活中细微情绪的准确捕捉的“清醒”,对语言和想象力边界的“清醒”。
诗人不是没有感到“真正的黑暗”和“创伤”,只是他不再在意它。
与朦胧诗的“我不相信”相比,新生代诗人已是“习惯于夜晚”,并自信个体生命的“清新可爱”,这一“本钱”。
这是一种既陌生又古老的本土化的诗歌想象力方式,它排除了形而上学问题,不论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此刻不能解决的,还是根本永远无意义的。
总之,在上述所言的几个新生代诗歌“社团”中,尽管有情感和意志强度,语型和素材畛域的不尽相同,但就其想象力范型和“自我意识”看,却具有“家族相似性”——抑制超验想象力,回到个人本真的生命经验。
除去“影响的焦虑”因素,这种想象力转换的发生与诗人对“语言”的重新探究有关。
在日常生命经验想象力范型的诗人中,于坚是具有自觉的理论头脑的人物。
他用“拒绝隐喻”,表达了对这一审美想象力转换的认识。
从单纯的理论语义解读看,这一理念肯定是成见与漏洞重重。
但是对诗人而言,在很多时候,恰好是成见与漏洞构成了他鲜明而有力的存在。
“拒绝隐喻”,从根源上说,是语言分析哲学中的“语言批判”意识,在诗学中的“借挪使用”。
或许在这类诗人意识中,语言是表达本真的个人生命经验事实的,而“隐喻”预设了本体和喻体(现象/本质)的分裂,它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指向,和建立总体性认知体系的企图。
这与新一代诗人主张的“具体的、局部的、判断的、细节的、稗史和档案式的描述和O度的”[1]诗歌想象力方式,构成根本的矛盾。
按照语言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表述就是:
“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
如果在诗人限定的想象力范畴中,语言应该表述经验事实的话,那么超验的题旨,既无法被经验证明,又无法为之“证伪”,那就当属“沉默”的部分,可以在写作中删除了。
于坚本人及第三代诗人的某些代表性作品,其特殊魅力的确受益于这个理念。
经由对隐喻一暗示想象力方式的回避,他们恢复了诗歌与个体生命的真切接触。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对常规意义上的现代诗“想象力”的抑制,有时可能会激发扩大了读者对“语言本身”的想象力尺度。
在这点上,恰如法国“新小说”的阅读效果史,它们回避了对所谓的“本质”、“整体”和“基础”的探询,但这种回避不是简单的“无关”,它设置了自己独特的“暗钮”,打开它后,我们看到的是景深陡然加大的第三代人与既成的想象力方式的对抗。
在对抗中,一个简洁的文本同样吸附了意向不同的解读维度,“每一个读者面对的不像是同一首诗”。
这也是“他们”、“非非”、“莽汉”、“海上”、“女性”等等诗群,与80年代同步出现的“南方生活流”诗歌的不同之处。
后者仅指向单维平面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现实主义”生活题材,而前者却指向对先锋诗歌想象力范式的转换实验。
与这种日常生命经验想象力方式不同,几乎是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新生代诗歌另一流向是“灵魂超越”型想象方式。
其代表人物有西川、海子、骆一禾、欧阳江河、张枣、钟鸣、陈东东、臧棣、郑单衣、戈麦……等,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整体主义”、“极端主义”、“圆明园”、“北回归线”、“象罔”、“反对”……诗人群。
这些诗人虽然从措辞特性上大致属于隐喻一象征方式,但从想象力维度上却区别于朦胧诗的社会批判模式。
他们也不甚注重琐屑的日常经验和社会生活表达,而是寻求个人灵魂自立的可能性;把自己的灵魂作为一个有待于“形成”的、而非认同既有的世俗生存条件的超越因素,来纵深想象和塑造。
在这些诗人的主要文本里,人的“整体存在”依然是诗歌所要处理的主题。
而既然是整体的存在,就不仅仅意味着“当下的存在”,它更主要指向人的意识自由的存在——灵魂的超越就是人对自身存在特性的表达。
比如,80年代中后,海子、西川、骆一禾的诗,就确立了超越性的“个人灵魂”的因素,充任了世俗化的时代硕果仅存的高迈吹号天使角色。
他们反对艺术上的庸俗进化论,对人类诗歌伟大共时体有着较为自觉的尊敬和理解。
对终极价值缺席的不安,使之发而为一种重铸圣训、雄怀广被的歌唱。
海子的灵魂体验显得激烈、紧张、劲哀,在辽阔的波浪里有冰排的撞击,在清醇的田园里有烈焰的噼剥;骆一禾则沉郁而自明,其话语有如前往精神圣地的颂恩方阵。
帕斯卡尔说过:
“没有一个救世主,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
”但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诗人们这种“绝对倾诉”,其对象是不明确的。
他们的诗中,“神圣”的在场不是基于其“自身之因”,而是一种“借用因”。
他们诗中神性音型的强弱,是与诗人对当下“无望”的心灵遭际成正比的。
这一点,在海子浪漫雄辩的诗学笔记中,在骆一禾对克尔恺郭尔的倾心偏爱中可以找到进一步的根据。
作为此二人最亲密的朋友,西川的超越性体验,却较少对“无望”感的激烈表达。
他拥有疗治灵魂的个人化的方式,他心向往之的“圣地”是明确的——纯正的新古典主义艺术精神。
这使西川几乎一开始就体现出谦逊的、有方向的写作,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在诗艺上的小心翼翼、四平八稳;他的诗确立了作为个人的“灵魂”因素,并获具了其不能为散文语言所转述和消解的本体独立性。
正如当时西川所言,“衡量一首诗的成功与否有四个程度;一、诗歌向永恒真理靠近的程度;二、诗歌通过现世界对于另一世界的提示程度;三、诗歌内部结构、技巧完善的程度;四、诗歌作为审美对象在读者心中所能引起的快感程度。
我也可称为新古典主义又一派,请让我取得古典文学的神髓,并附之以现代精神。
请让我复活一种回声,它充满着自如的透明。
请让我有所节制。
我向往调动语言中一切因素,追求结构、声音、意象上的完美。
”[2]这是一种“新古典主义立场”,其想象力向度体现了“反”与“返”的合一。
既“反对”僵化的对古典传统的仿写,又“返回”到人类诗歌共时体中那些仍有巨大召唤力的精神和形式成分中。
总之,对这类诗人来说,使用超越性的想象力方式带来的诗歌的特殊语言“肌质”,同样出自于对确切表达个人灵魂的关注。
或许在他们看来,不能为口语转述的语言,才是个人信息意义上的“精确的语言”,它远离平淡无奇的公共交流话语,说出了个人灵魂的独特体验。
表面看来,在这些诗人中欧阳江河的情况略微特殊一点。
比如欧阳江河在1987年创作的《玻璃工厂》,就曾被视为较早带有“后现代因素”的诗作。
但深入细辨,我们发现可能它并非如此:
在同一个工厂我看见三种玻璃:
/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
/人们告诉我玻璃的父亲是一些混乱的石头。
/在石头的空虚里,死亡并非终结,/而是一种可改变的原始的事实。
/石头粉碎,玻璃诞生。
/这是真实的。
但还有另一种真实/把我引入另一种境界:
从高处到高处。
/在那种真实里玻璃仅仅是水,是已经/或正在变硬的、有骨头的、泼不掉的水,/而火焰是彻骨寒冷,/并且最美丽的也最容易破碎。
/世间一切崇高的事物,以及/事物的眼泪。
诗人意识到有“三种玻璃:
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
但最后他的隐喻—象征想象力终于自信地跃起,指向灵魂的超越性。
在此,“另一种真实”,就是本质主义的真实,灵魂淬砺的真实;而“另一种境界”,就是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本
质是由人不断新创造出的东西”所激励下的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
以上就是我对上世纪80年代新生代诗歌,在想象力的向度和质地上的不同范式的约略认识。
由于本文特殊视角的限定,这种“总结”一定会既显得集中,又显得有些概括。
(好在本人已出版有近90余万字的《中国探索诗鉴赏》,和诸如《精神肖像或潜对话》一批诗人个案研究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细加参照。
)可以看出,对80年代新生代诗歌这两大想象力范型的衡估,笔者基本采取的是多元共生、强调差异性的立场。
这里的“元”与“差异”,是互为条件又相互打开的关系。
在这点上,唐晓渡的看法颇为中肯,“我们以一种审慎得多的态度来谈论所谓‘多元化’,而不致使其成为又一个空洞的时代戳记。
‘元’者,始也,圆也,完整充实、自为创构之谓也。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和据何证明自己作为个人自成一‘元’——不仅仅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而且是在美学的意义上?
”[3]在我看来,上述的诗群和个人,其佼佼者的想象力范型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自成一“元”的条件,考虑到当时具体的写作语境和诗人们心智发展的早期阶段,“相对”来看,这种成就的取得的确是十分珍贵的。
当然,从我个人“绝对”的诗歌理想和文化价值判断来说,这两种想象力范型都不能令我真正满意。
其各自的优长前文已述,其各自的缺失是:
对日常生命经验想象力范型而言,其诗歌有对本真的世俗社会及个人经验的表述,但缺乏一种更宽阔的对“历史生活”中个人处境的深刻表达,其流弊所及使大量追随者陷入“消解一切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以庸常化自炫的写作。
而对“灵魂超越性”想象力范型而言,其诗歌有精审的形式和高贵的精神质地,但却缺乏更刻骨的对“此在”历史和生命经验的有效处理,不期然中成为一种可供遣兴的高雅读物。
其流弊特别体现在诗人海子去世之后,某些盲目而易感的追随者身上。
我们期待着能有一种新的想象力范型,来修正它们各自的缺失,汲取各自的优长,达到对一种综合创造力的开拓——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
它是指诗人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
在此,诗歌的想象力畛域中既有个人性,又有时代生存的历史性。
如果说,在艺术中极端就是自足的话,我所期待的整合性的想象力目标真的能很好地实现吗?
(三)
斯宾格勒在他的《西方的没落》第一版序言中说:
“一个在历史上不可缺少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创造那个时代。
”的确如此。
我们所期待的新的想象力范型——历史想象力,恰恰出现于一个它几乎难以出现的年代,不是时代的主流话语催生了它,恰好相反,而是它自身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时代,一个与彼时的主流话语无关的一代诗人历史想象力范式崛起的年代。
80年代末,历史的剧烈错动给诗人们带来了深深的茫然和无告,在有效写作的缺席中,诗歌进入了90年代。
90年代初期的诗坛有两种主要的想象力类型:
一种是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诗人以华彩的拟巴洛克语型书写“乡土家园”,诗歌成为遣兴或道德自恋的工具,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缺乏起码的敏感。
另一种是迷恋于“能指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的“后现代”写作。
这两类诗歌充斥着当时的诗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同充任了“橡皮时代”既体面又安全的诗人角色,并对大量初涉诗坛的青年写作者构成令人担忧的语词“致幻效应”。
诗歌在此变成了单向度的即兴小札,文化人的闲适趣味,回避具体历史和生存语境的快乐书写行当,如此等等。
先锋诗歌的特殊想象力功能再一次陷入了价值迷惑。
大约在1993年后,先锋诗歌写作较为集中地出现了想象力向度的重大嬗变与自我更新,它以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更丰富的写作技艺,吸引了那些有生存和审美敏识力的人们的视线,很快就由局部实验发展到整体认知。
正如诗人西川所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变故,才使我意识到我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
当历史强行进人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
”[4]同样,诗人王家新也深深感到了以往的写作,“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存在和痛苦在诗歌中的缺席,感到我们的写作仍然没有深刻切入到我们这一代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去。
”[5]这是一种吁求历史性与个人性,写作的先锋品质与对生存现实的介入同时到场的诗学。
很明显,它的出现,既与当时具体历史语境的压强有关,也与对早期“朦胧诗”单纯的二元对立式的写作,和对本质主义神话失效后的历史反思有关。
我认为,在那个阶段,先锋诗人对汉语诗歌的重要贡献,主要是改变了想象力的向度和质地,将充斥诗坛的非历史化的“美文想象力”,和单维平面化展开想象的“日常生活诗”,发展为“历史想象力”。
如何在真切的个人生活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之间达成同步展示,如何提取在细节的、匿名的个人经验中所隐藏着的历史品质,正是这些诗人试图解决的问题。
正是这种自觉,使先锋诗歌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技艺、思想起源和宽大的生存关怀、文化关怀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入的彼此激活的能动关系。
且让我们对几位诗人的作品略做分析。
以影响广泛、颇具代表性的先锋诗人西川为例,他此前的诗,从精神向度上是垂直“向上”升华(而其变体就是对“远方”的渴慕),通往神圣体验和绝对知识的;其隐语世界则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或许还包括对象征主义影响深远的史威登堡的神秘主义哲学)所认为的此在—彼岸、现象—本质、肉体—灵魂、世俗—神性……的分裂上。
他或许相信,在诸项二重分裂里,后一项是先然存在不容怀疑的,而诗人的使命就是使这种分裂重新聚合。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束,穿透你的心……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此诗写于80年代中期,可视为一批诗人的精神“姿势”。
仅从诗歌艺术本身看,这类作品是不错的。
然而它却无法对应于90年代以来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生存处境,甚至它也无法真实地显现我们的精神处境。
90年代以来,西川的诗歌发生了极大变化,体现了向历史想象力、包容力、反讽、情境对话、悖论、戏剧性、叙述性……综合创造力的敞开:
他的黑话有流行歌曲的魅力/而他的秃脑壳表明他曾在禁区里穿行/他并不比我们更害怕雷电/当然他的大部分罪行从未公诸于众……
他对美的直觉令我们妒恨/且看他把绵羊似的姑娘欺侮到脏话满嘴/可在他愉快时他也抱怨世界的不公正/且看他把喽罗们派进了大学和歌舞厅……
他的假眼珠闪射真正的凶光/连他的臭味也会损害我们的自尊心/为了对付这个坏蛋(我们心中的阴影)/我们磨好了菜刀,挖好了陷阱……
我们就得努力分辩我们不是坏蛋/(尽管坏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们就得献出女儿,打开保险柜/并且满脸堆笑为他洗尘接风
——《坏蛋》
在此,“坏蛋”作为一个类似儿童口语语汇的词,有分寸地悬置了斩钉截铁的道德判断,甚至反向的意识形态讥诮。
但我们感到,它的反讽却更为犀利了。
而这里我更感兴趣的还不是诗人对“坏蛋”多少有些无奈的讥刺这个声部,而是与其平行的另一声部——“自审”意识。
诗人追问道,“为了对付这个坏蛋(我们心中的阴影)”,“我们就得努力分辩我们不是坏蛋(尽管坏是生活的必需品)”,正是这突兀楔人的盘诘,令我们怵然心惊。
西川在坚持基本的道义关怀的同时,又容留了生存的含混、尴尬、荒诞和复杂喜剧性,正如他说“既然生活与历史,现在与过去,善与恶,美与丑,纯粹与污浊处于一种混生状态”,“既然诗歌必须向世界敞开,那么经验、矛盾、悖论、噩梦,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承担反讽的表现形式”。
[6]诗人同时也写出了我们内心的无言之痛和隐蔽之恶的原动力,他迫使我们看清,我们的内心其实也蹲伏着恬不知耻又屈辱无辜,狡黠狂妄又满身灰土,咻咻威慑又羸弱不堪的野兽。
在《厄运》《巨兽》《鹰的话语》中都有这种不同声部的紧张争辩,西川没有封住“个我”/“他我”/“一切我”的嘴——没有压抑或删除自己内心深处复杂纠葛的声音,没有对任何绝对主义或独断论的庞然大物的急切认同,从而使自己的诗在具体历史语境和生存处境中真正扎下了根。
再比如于坚,80年代虽然已写出影响广泛的具有“当下关怀”(张颐武语)的作品,但是他的诗真正具有历史承载力和强大命名力,还是90年代的作品。
特别是长诗《0档案》,它既可视为一部深度的语言批判的作品,同时也是深入具体历史语境,犀利地澄清时代生存真相的作品。
诗中有不少段落,甚至是刻意地以“非诗”的、社会体制“习语”或“关键词”的形式出现,诗人写出它们对个人生存的影响,激活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鉴定:
尊敬老师关心同学反对个人主义不迟到/遵守纪律热爱劳动不早退不讲脏话不调戏妇女/不说谎灭四害讲卫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积极肯干/讲文明心灵美仪表美修指甲喊叔叔叫阿姨/扶爷爷挽奶奶上课把手背在后面积极要求上进/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生动活泼谦虚谨慎任劳任怨
思想汇报:
他想喊反动口号他想违法乱纪他想丧心病狂他想堕落/他想强奸他想裸体他想杀掉一批人他想抢银行/他想当大富翁大地主大资本家想当国王总统/他想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独霸一方作威作福骑在人民头上/他想投降他想叛变他想自首他想变节他想反戈一击/他想暴乱频繁活动